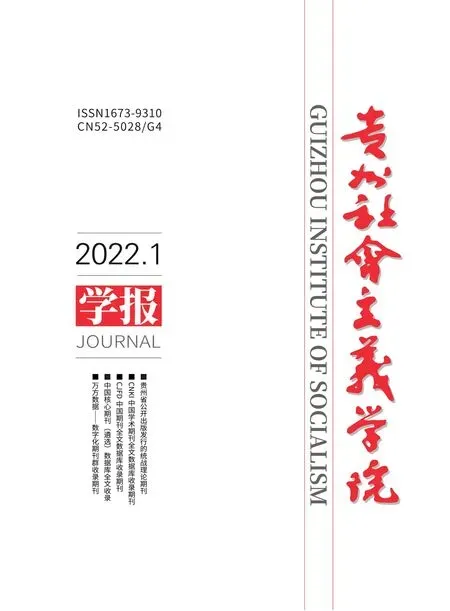王阳明黔籍再传弟子李渭“幼蒙庭训”考
王路平 石祥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贵州 贵阳 550002)
李渭(1513—1588),字湜之,号同野。贵州思南府(今思南县)人。生于明正德八年(1513)十二月,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享年76岁。青少年时代就拜楚中王门大师蒋信为师,乃王阳明黔籍再传弟子。李渭能够成为黔中王门一代心学大师,在心学造诣上取得很高的成就,最早得益于他父亲李富的启蒙教导。《道光思南府续志》说:“(李)渭之学基于庭训。”[1]288在他5岁时,父亲亲自书写明代心学第一人的陈白沙所撰《禽兽说》对他进行教导,他便开始有了省悟,给自己的人生作了定位,建立了“必为圣人”的目标。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之下,李渭13岁时就成为了当时思南府学的生员。在15岁左右,其父又以“毋不敬”、“思无邪”教导他。在他静心默坐时,竟然觉得对“本心”恍惚有所得,但下楼与朋友谈笑,似有所得之本心尽失。由是萌发了“未与人接,如何是本心?”而“既与人接,本心是何如?”的心学思考。李渭在探寻本心的道路上,父亲李富又勉励他认真学《易》,他又深入易理,刻苦钻研,终于在22岁时以《易》中举,后来他还著有《易问》一书。由此可见,“幼蒙庭训”对李渭心学思想的产生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幼蒙庭训”是李渭思想心路历程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一逻辑起点,就不可能有尔后李渭心学的整个思想体系。然而学界至今对此缺乏详细研究,不明李渭与江门学派的深厚渊源,未能重视李渭心学的湛学色彩,笔者希望本文对黔中王门特别是作为黔中王门大师李渭心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
一、授《禽兽说》以明其志
贵州思南县位于黔东北乌江中下游,自古便是贵州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因地处乌江咽喉要道,交通便利,故自明代开府以来便是黔省对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元初,李渭的家族始祖李僧随军征战至贵州思南,因功“授忠显校尉,管军民万户职事”[2]1141,其后代即落籍于思南。自高祖李斌始,李渭家族世袭蛮夷长官司副长官之职,至清雍正年间被裁撤,历320余年。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让李渭在“必为圣人”的道路上拥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他不必为食不果腹而烦恼,也不必为居无定所而痛苦,唯一的追求就是读圣贤书,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更为幸运的是他有一位有文化有见识的父亲——李富。
李渭的祖父,虽生在副长官之家,但不是嫡长子,故而没能继承蛮夷司副长官的职位,大部分时间用来研习经典,教授子弟。殷实的家庭条件,让李富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游学问道,参访名师。李富乐善好施,学识渊博,深谙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对李渭要求甚严。莫友芝认为:“同野父中宪赠公富,以支子未袭,有学识,所以期同野甚大。”[3]128正因为李富把宏大期望寄托在李渭身上,故在李渭“五岁时,父中宪公书江门《禽兽说》训之”[4],可见李富受陈白沙江门学派影响较大。
那么李富是通过什么渠道接触到江门学派思想的呢?江门学派重要人物祁顺曾经于成化年间贬谪贵州石阡,做了六年知府。(1)祁顺在《巽川祁先生文集》卷16《杂志》一文中,自言“予自壬寅(即明成化十八年,1482)岁谪石阡”。据《明实录·宪宗纯皇帝实录》卷227载:“成化十八年(1482)五月,左参政祁顺贵州石阡府知府。”成化十九年(1483)春到任石阡。弘治二年(1489)母逝,守制回东莞。说明祁顺在石阡知府任上经历了六年之久。今人温建明认为祁顺在石阡任职11年,参见温建明:《祁顺及其〈巽川祁先生文集〉研究》,《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0页。期间曾到过思南巡视,将白沙之学传播到了该地。
祁顺(1434—1497),字致和,号巽川,广东东莞人。“事陈白沙先生为高弟”(2)郭子章:《黔记·宦贤列传七》卷40,第905页,赵平略点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也认为他是“陈白沙高弟”,见《黔诗纪略》卷2,第67页,关贤柱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乾隆石阡府志·名宦》也称他是“名儒陈献章高弟”,乾隆三十年刻本。,乃江门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明天顺四年(1460)进士,历官兵部职方清吏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参政、石阡知府、山西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年(1497)卒于任,享年64岁。他为官正直清廉,所至皆有善政,兴教讲学,以白沙为宗,后人誉之为“儒臣之宗”。(3)据民国张其淦《吟芷居诗话》载:“祁巽川方伯,历官中外,以清洁自守。却海外之遗金,留江西之公帑。所谓以清白吏遗子孙者,斯人良不愧也。钟云瑞谓巽川讲敬斋(胡居仁)、白沙之学,立志于警非寡过,儒臣之宗也。”见《东莞诗录·祁顺》卷8,第76页,东莞张氏寓园1924年刊。谪守贵州石阡期间,“设馆谷,集儒生,暇则亲为讲授”[5],其功“不啻如文翁之化蜀”[5],是明代白沙心学输入贵州、影响黔东北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弘治元年(1488)二月二十日,祁顺出巡思南,有《出巡思南》诗云:“佳景逢春又喜晴,风光妆点四山明。天连直北浑疑近,路向思南渐觉平。芳草池塘蛙习吹,绿杨村郭鸟催耕。丰年有兆吾民乐,处处芦笙助笑声。”[6]祁顺出巡思南时,得到了思南当地官员和民众的热情接待,他在诗中用“丰年有兆吾民乐,处处芦笙助笑声”来描写了当时热闹的场景。此时,李富或拜谒了祁顺,并向他问学,为尔后李渭幼年时期就接触到了白沙心学思想提供了先机。
李富与祁顺见面,祁顺将其师陈白沙的《禽兽说》传授于李富。笔者在点校祁顺《巽川祁先生文集》时,发现他在附录“杂说”中谈到探求“本心”“不失此心”的话语,如:“富贵不足言功名余事耳。但得本心存,此生无憾矣。风雩咏歌是尧舜气象,陋巷传习乃禹稷事功,彼以勋业希古人者陋矣。”[7]“士君子期不失此心而已,进退荣辱有命存焉,非我所能计者,且诚能不失此心则为君子。虽一命不沾,宁不乐邪。然则进退荣辱,非惟不能计,亦不足计矣。”[7]此处所言的“本心”“此心”,即是道心,未受到污染的至善之心,乃孔子所说的仁心,孟子所讲的良心,朱熹认为的“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8]310,就是后来阳明所说的良知。程子认为“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9]331良知良能出于先天,人人本自俱足,只因受到物欲、私心杂念的污染,“溺于流俗之弊,是以丧其良心而不自知耳。”[10]236现在需要扫除遮蔽,认识到本心,故言“但得本心存,此生无憾矣”。从李富书写陈白沙的《禽兽说》给李渭学习的情况来看,祁顺给李富传授其师陈白沙撰写的《禽兽说》的事应该是可信的。因为《禽兽说》就是解决“此心此理”与“私心杂念”关系的问题,让其明白人与禽兽之别。
如何探求本心?祁顺或与李富谈过白沙筑“春阳台”静坐读《易》悟道的故事。因白沙不满意其师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回乡修筑“春阳台”静坐读《易》其中,历时十年,“静养端倪”,最终彻悟,提出“学贵自得”的为学主张。古往今来,多少圣贤在探求本心的方法有惊人的一致性,第一是静坐;第二是读《易》,而王阳明“龙场悟道”于玩易窝亦循此路。此时,思南本地已经形成了一股良好的学《易》氛围,从成化七年(1471)开始,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思南中举者如田显宗、石泉、吴溥、周邦都是以《易》中式。这种学《易》的风气由学界传播到了民间,影响了整个思南的文风。凡是在思南的有识之士都在学习《易经》,传授《易经》。李富亦不例外,在教育李渭的过程中,必然教导他读《易》、学《易》、点《易》,通过学习《易经》来探寻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历代儒家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担当。
陈白沙(1428—1500),名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晚号石翁。广东新会县都会村人,后徙居白沙村,学者因称之白沙先生。明代著名思想家,明代心学第一人,岭南心学江门学派的开创者,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硕儒。其学说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为阳明“龙场悟道”提供了参考。《禽兽说》是陈白沙剖析人禽之别的一篇短文,全文如下:
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11]83
该文形象而精辟地阐述了人与禽兽的区别:一个有着七尺躯体的人,如果没有了“此心此理”,心中没有了道德理性,那就是一包脓血裹着一大块的骨头;他们饥思食,渴思饮,贫贱的时候想要富贵,富贵了又贪图权贵,他们或是争斗,或是忧伤,或是放纵,或是淫欲,一切时候,一切行为,都只是考虑气血的需求,动物的本能,而不是从道德出发,不是从道德本心出发,这样的人“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只是行尸走肉,哪是人?只能叫他们“禽兽”!
李富以该文训育李渭,幼年的李渭得以脱胎换骨,深度警醒,思考如何超脱“禽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猛然有省: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因此而激发其此生须超脱“禽兽”行列,而尽力攀登圣贤境界的大志向,对其一生影响深刻。
受江门学派思想影响的李渭,很快在“必为圣人”之路上展露头角。他“十三岁,补邑弟子员。向黉序礼木像惟谨,归而悚然若有惕者。”[4]李渭13岁,妙龄少年,已经入选秀才,可见他天赋之聪,志向之高,用功之勤。其时,李渭以慎独的工夫,开始了他探寻圣道的尝试。他修学方法以戒慎恐惧为主,处处小心谨慎,在学校向圣人木像礼拜时亦不例外。归家自处时,仍然保持肃然恭敬、高度警惕的状态,一切言动举止都有所戒惧,生怕做出无礼非法之举动。陈白沙曾告戒弟子李承箕“求道之事,不要计较其‘高卑’,坦然处之,时常保持一颗‘戒慎恐惧’之心,这样才能达到求道之‘全功’。”[12]79作为深受白沙思想影响的李富,以“戒慎恐惧”指导李渭修学,自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戒慎恐惧,本是《中庸》之语。《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3]46“戒慎恐惧”是慎独的工夫,就是时时刻刻小心谨慎,防止自己离开了“道”,堕入禽兽之境。稍有不慎,即入禽兽之道。《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4]176人与禽兽共生天地之间,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差别并不大。然人与禽兽之所以有区别的关键一点在于人具有道德良知。人如果泯灭了道德良知,虽然表面上是人而实无以异于禽兽,君子知人性道德良知的可贵而珍视保存之,是以战兢惕厉,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所以孟子提出了“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强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5]72-73此“四端之心”归纳起来就是“良心”,发用时外化为仁义礼智、孝悌忠恕。故人能闻道、求道、悟道、修道、行道,能使思想飞跃,有道德理性,主观能动地改造世界,创造奇迹。故《中庸》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3]106只有充分体认自己天赋的道德本性,才能参与到天地之道的建设中,使万物更好地生长,社会更好地发展。这是人存在的最大意义,也是人创造活动的最大目的。这对少年李渭来说,无疑是充满了极大的吸引力,牢牢地将他吸附在为圣之路上,“拼生拼死不休”[16]980
那么,如何去体悟人与禽兽之别,体认到自己的本心呢?按照白沙的做法就是静坐,即静养端倪。白沙在《复赵提学佥宪》中云:“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17]195;又言“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17]180。静坐,是白沙为学之方,教人之法,乃使人身心与此理有“有凑泊吻合处”[17]195,进而达到“心理合一”之境。他认为,“观书博识,不如静坐”[18]85,“此一静字,自濂溪先生主静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相传授,至于豫章、延平尤专提此教人,学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如伊川晚年之训,此是防微虑远之道。”[18]84
李渭自从父亲那里受学白沙《禽兽说》起,便对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一番规划,并付诸行动,刻苦自励。在患肺病被隔离期间,仍然收束身心,危坐静心,检讨自己,灵光乍现,端倪忽生,恍惚有得,“境界一清”。虽然其间时有反复,境界消弭,但其自警之心仍在,起大心志,发大疑情,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19]930因有此大困惑,为他后来为政参学,四处拜师,获大彻悟,提供了先机。故胡庐山先生云:“黔中之学,李湜之为彻。”[16]980
二、教其“毋不敬”“思无邪”之工夫
(李渭)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无(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摄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16]979
嘉靖六年(1527),盛夏,思南山城,正值溽暑,15岁的李渭,因患肺病,被隔离在家中小阁楼里。因闷热难耐,他不拘礼节,披头散发,蹲踞而坐,显得傲慢不敬,恰巧被李富看到,很不高兴,认为他有失礼节,便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毋不敬”对他进行教诲。李富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认为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注意礼节,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讲究个人道德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因而他以“毋不敬”来严格要求李渭。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西汉戴圣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20卷49篇,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至西汉宣帝时,社会上出现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85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一是戴德侄子戴圣的49篇本,习称《小戴礼记》。自东汉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后,《小戴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被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之首。
此时的少年李渭,根据父亲李富的教诲,只能依靠外力,即以《礼记》中规定的礼仪细节、行为规范,对自身言动举止进行防检压制,使之不失礼。他并没有从心地上去做工夫,结果势必犹如以石压草,草必旁生。未几,顿觉内心妄念丛生,特别是在青春期躁动的年龄,难免要胡思乱想,心烦意乱,如何面对接踵而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便成为李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渭在自力无法除却妄念的情况下,只好向父亲求助。“请曰:‘若妄念何?’父言:‘思无邪而已。’”[20]372-373“思无邪”,语出《论语·为政》。原文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1]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意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22]55“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22]55李富以“思无邪”指导李渭要发善惩逸,从心地上去做工夫,保持性情之正,此乃诚身之要。
在程朱理学作为当时主流价值观的明代,李富用“毋不敬”“思无邪”对儿子进行引导,亦是情理中事。“毋不敬”、“思无邪”,虽源于《礼记》《论语》二书,北宋时却由程颢拈出,作为君子修身之要。朱子在《近思录》中云:
明道先生曰:“思无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23]66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别号考亭、紫阳,卒谥文,赠太师,封徽国公。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属福建省三明市),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
朱熹认为“毋不敬”是《礼记》的纲领,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时指出:“礼主于敬。”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北宋大儒范祖禹的话说:“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22]]55故朱熹为学大抵以居敬为主,时时刻刻保持敬畏之心一以贯之,即身心内外不可有丝毫不敬,且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主敬原是二程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自周敦颐主静、立人极开宗,程颢以静字稍偏,不如专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程颐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24]652,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24]652,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24]652,担心后世学者将主敬与行义看作两项工夫,主张舍敬无以为义,义是敬之用,敬是义之体。程颐据此发挥为内心涵养、进德修业的功夫,“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25]601,“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25]601他强调外在仪态、内在思虑与行为举止的敬,须使心保持在专一与自觉的状态,而不为外物所诱;又心有所主,还须处物行义,于事物上能明是非,要主敬与行义相辅,否则敬便沦为空寂无为。
朱熹继承发展二程的主敬学说为“居敬”、“持敬”。朱熹认为“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敬者,主一无适之谓。”[26]4所谓“主一”,即“主一只是心专一,无适只是不走作,如读书时只读书,着衣时只着衣,理会一事只理会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26]4持敬的方法是畏谨不放纵,需要优游函泳,不急迫、不懈怠地坚持下去,并非不闻不见不思的兀然端坐,而是要无事能安然,有事能应变。如果能够“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27]1532,则是进一步以主敬为存养之道。此处所谓“内外肃然”是指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意思。朱熹将居敬和穷理形容为人之二足,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居敬为穷理之本,穷理只明得天理,消去人欲。为使人欲不复萌,天理不复灭,应当积极以“敬字抵敌”。一方面在未发之时使心不放弛,即用戒慎恐惧、紧张敬畏来警惕情欲之任纵;另一方面则在已发之际专一集中,要求在行为举止上加强礼节的约束。
总之,主敬是一种临渊履薄、戒慎恐惧的行为或态度,程朱理学认为闲居懒散,精神无着落之时,特别容易受到外物刺激的诱发,故常成为各种恶念、恶习、恶行的渊薮,而持敬工夫即在防患此种恶的产生根源。
“毋不敬”,语出《礼记·曲礼》,主要讲述人际交往中具体细小的礼仪规范。原文为: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28]4
李富以此告诫李渭,君子处世,先立乎其大者,凡事都要保持恭敬、严肃的形象,态度要端庄持重而慎重思考,说话安稳平静而条理清晰,充满自信。心定则其言安稳而舒畅,容态恭严而言辞安定,则俱君子之形象,做到这三点,才能令人信服,获得内心的安宁!“毋不敬则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俨若思则正颜色斯近信矣,安定辞则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姓也。”[28]4-5
“思无邪”,自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历来注解此语的不在少数。但朱熹对“思无邪”的解说最为详备。他说:“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29]539朱熹认为孔子所讲的思无邪,只是一个“正”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29]538,“只是要正人心”[29]538而已。又说:“行之无邪,必其心之实也;思而无邪,则无不实矣。”[30]555思无邪,必然行亦无邪矣,强调了朱熹为学的自觉意识。
杨士训尹叔问“思无邪”,“毋不敬”。曰:“礼言‘毋不敬’,是正心、诚意之事;诗言‘思无邪’,是心正、意诚之事。盖毋者,禁止之辞。若自无不敬,则亦心正、意诚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学於文,约之以礼。’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今若祇守著两句,如何做得?须是读了三百篇有所兴起感发,然后可谓之‘思无邪’;真个‘坐如尸,立如齐’,而后可以言‘毋不敬’。”[29]546
朱熹认为,思无邪,不必说是诗人之思及读《诗》之思,大凡人思皆当无邪。如毋不敬,不必说是说礼者及看《礼记》者当如此,大凡人皆当毋不敬。“见说‘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见说‘思无邪’,便定定著‘思无邪’始得。书上说‘毋不敬’,自家口读‘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诗上说‘思无邪’,自家口读‘思无邪’,心里却胡思乱想。”[31]2759
父亲李富指导李渭的为学方法主要是由外而内,即从外在规范的“毋不敬”到内在自觉的“思无邪”。这个递进关系,符合传统朱熹理学的修学路径。
1534年,李渭中举后,曾作《思南府学射圃记》谈到了礼让的内容:
射以教让也,将以反己,非以人胜也;将以祛戾,非以能角也。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执弓以延,昭其族也;鹄己为射,昭其正也;正直审固,昭其度也;进止揖纾,昭其节也;中的以祈,昭其中也;弛张以别,昭其劝也;采蘩以章,昭其职也。匪族斯乱,匪正斯迷,匪度斯离,匪节斯鄙,匪中斯饰,匪劝斯弛,匪职斯荒。族善天下之比,正端天下之趋,度轨天下之物,节文天下之固,中正天下之一,劝鼓天下之动,职矢天下之勤。让而敬,可以摄勇;和而平,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恬忿。他日济济相让于朝,以养天下不争之化。举此以措之耳![1]26
这时李渭仍然沿着“毋不敬”的路线做工夫,他在文中引用了孔子的话,君子与人无争,“仁者无敌”,不搞对立。就算要比射箭,也要符合规矩,有礼有节。射箭比赛的目的是使人们懂得礼让,长养辞让之心,这就是礼,“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取胜不是目的,要消弭胸中之戾气,并不是成为神射手。只有敬让可以摄勇,和平可以怀强,爱恕可以恬忿,如此便可“济济相让于朝,以养天下不争之化”,以趋于修齐治平之道。
李渭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屏息妄缘”[4],“危坐”静心,反复思索,“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16]979,“静默中恍若有得者。”[19]930但是,当他下楼与朋友交流谈笑时,境界顿消,“前境随失”[19]930,“恍惚似有得”之心不复存在,“楼上光景已失”,烦恼又生起。自言:“处楼中觉境界一清,独下楼应酬辄不肖。”[4]所以他认为这个“恍惚似有得”之心,并非本心。因为本心应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在圆满,浑然天成的,也就无所谓得失。于是他又生起大疑情,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19]930即下定决心,“专求本心”,自是“求心者日切”。
他的“求心法门”,以“危坐”(即静坐)为主,读书为辅,这与陈献章教学路数相似。李渭在求心过程中,不断起疑,“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16]979陈献章教育弟子时,以“静坐”为主,在他看来“静坐”即“觉悟”,在静坐中思索检讨,生起疑情有助于对本心的探求。“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17]220,把“疑”当作“觉悟”的契机。李渭在父亲的帮助下,按照白沙的教授方法,沉心静坐,反复生起疑情。当自己独处时,自问:“什么是本心?”在与人交往时,又问:“本心是什么?”他如此探求,用功不可谓不勤,用心不可谓不诚,而结果又如何?这个结果就是为李渭日后向蒋信陈述“楼上楼下光景”而被蒋信棒喝点醒埋下了伏笔,亦为其一生最后归宗阳明心学而开启了逻辑起点。青少年时期的李渭,能有如此向学之心,觉悟之境,诚属难能可贵。
李渭在不断静坐求心,读书悟道的经历中,刻苦努力,广学博览。他在读《孟子·伊尹耕莘章》时,似乎又有所悟入,慨然曰:“作圣必以一介不取为始。”[4]圣贤大业,要从廉洁克己开始,不符合道义的,哪怕是一点儿小东西也不拿。所以,他认为“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16]979于是他慎交友,严交际,为学作圣以“一介不取”为起点,处世交友以谨慎为要务。而这种“一介不取”“交际甚严”的箴言,又为他后来为官从政、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理想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勉其学《易》以入科场
嘉靖十三年(1534),李渭22岁,赴云南昆明参加乡试,以《易》中举,获得第三十名。(4)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九记载:“李渭,贵州思南人,贡士。”《康熙云南通志》卷十八上记载:“李渭,思南人,进士。”笔者按:李渭一生未中进士,而民间有把举人敬称为进士或乡进士的习俗,如田秋长女婿张钦辰,癸卯(1543年)科举人,历官武隆知县、梧州府通判,然其在《广东右布政使田公行状》一文中,落款为“承德郎、广西梧州府通判、前乡进士、子婿张钦辰泣涕谨状”。李渭精通《易经》,曾于思南府城西小崖门(小岩门)左旁山崖洞穴中学《易》,后称之“点易洞”,著有《易问》一书。其号同野,取自《易·同人卦》,卦辞有言“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野”乃郊野旷远之地,只有超越自己,广结善缘,才能做到与人和同,同心同德,诸事亨通。同人卦象,下卦离为文明,上卦乾为刚健,二五爻中正二应,正而不邪,乃君子正道。故《易传》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32]58故非刚健精明,肫肫无倚者,不足以上达天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告诉人们,应当破除一家﹑一族的私见,重视大同,不计较小异,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以道义为基础,于异中求同,积极的广泛与人和同,才能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这也是李渭对自己一生抱负的期许。
《易经》是一部蕴含无穷人生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宝典,既是我国儒、道两大学派的渊源,也是诸子百家的发端,乃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历代圣贤无不因学易玩易而悟道,如文王拘羑里而演《易》,如孔子韦编三绝以学《易》,如阳明困龙场而玩《易》。他们在演《易》、学《易》、玩《易》得过程中,受到了《易经》的启发:使人们懂得了做任何决策都要计量为易、化繁为简,显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以利于由决策预测转化为决策导行;任何决策都要统观世界、广收信息,处理好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任何决策,都要立足变化,持发展变化观点;任何决策都要具有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思想;任何决策都要懂得简易、变易、交易、不易的道理;任何决策都要记住亢龙有悔、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哲学;任何决策都要坚持刚健中正,持盈保泰的原则。精通《易经》的李渭,肯定也在点易洞中得到了《易经》的某些启发,才使得他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积极作为,奋发向上,戒骄戒躁,好学不止!
当年,在思南与李渭一起中举的还有田时中、田时雍以及敖宗庆。李渭、田时中、田时雍三人以《易》中式,敖宗庆以《诗》中式。[1]61从李渭、田时中、田时雍等人以《易》中式来看,思南早在明代中叶,已成为了贵州易学重镇。据史料记载,思南易学得传,始于思南府学教授李悦。
李悦,福建莆田人,明成化年间(1465—1487)任思南府学教授,《万历贵州通志》称他“学识弘博,尤精于《易》,每为诸生讲授,朝夕不倦。易学由此有传。”[33]303《嘉靖思南府志》评价他“学识宏博,倡道诸子朝夕不倦,尤精于《易》,每为诸生讲授,至今《易》盛于思南焉。”[1]53自李悦任思南府学教授后,在思南教授生徒,传播易学思想。从成化七年(1471)开始,至嘉靖十三年(1534),思南举人以《易》中式者有田显宗、石泉、吴溥、周邦、田谷、吴孟旸、田秋、任相、宴应魁、田时中、李渭、田时雍,足以说明易学在思南的传播获得了巨大成功。
根据明代科举制度,其乡试主要以《四书五经》内容命题试士。文仿古人语气,体用排偶对仗,谓之八股,统称制义。三年考一次,考试地点在省会,称为乡试。乡试安排在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官方指定考试内容为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经集传》,蔡沈的《书经集传》,陈澔的《礼记集说》,胡安国的《春秋传》,另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各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以上程颐、胡安国、朱熹、蔡沈、陈澔等人,都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重要人物,由此可知,青少年时代的李渭受到程朱理学影响较大。
李渭与田秋长子田时中、田谷之子田时雍三人以《易》中式。而早在明弘治五年(1492)[34]80和正德五年(1510)田谷、田秋兄弟都以《易》中式,二人则是精通《易》学的大家,当时“家之子弟,乡之后生,及门受业者甚多。”[1]60且李渭与田秋还是儿女姻亲,如此亲密的关系必然是早年培养的,早年或受教于这二位同乡前辈。
田谷(1473—1527),号素齐,贵州思南府(今思南县)人。明弘治五年壬子(1492)举人。[34]80田谷少聪敏勤学,年十九,领乡荐,授新津令,清慎严明,方正端严,赈穷锄奸,筑城兴学。升曲靖府通判,寻以亲老告终养归,遂不复仕。嘉靖十五年(1536),知府洪价采士论,举入乡贤祠。[1]60他精通《易》学,铜仁知府刘瑜曾邀请他到铜仁聚会,临走之时,刘以诗赠别:“十载纬编理学精,几多门弟赖陶成;须知霄汉致身远,不说功名唾手轻。文字正堪供夜话,风雷又觉动春声;相期早际云龙会,共秉忠真答圣明。”[1]60此诗赞叹田谷在《易经》的研究上着力较深,所谓“十载纬编”,源自于孔子学《易》的典故“韦编三绝”而来,形容读书勤奋,刻苦治学。田谷不仅自己精于《易》理,且能在易学教育上有很大成就,“家之子弟,乡之后生,及门受业者甚多”[1]60,故“几多门弟赖陶成”。在这众多弟子中,李渭必然名列其间,且为佼佼者也。
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贵州思南府(今思南县)人,田谷之三弟。是明代贵州教育先贤,被后人誉为贵州科举考试之父。明正德五年(1510)以《易》中举,九年(1514)进士,历官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户部给事中、礼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福建右参政、四川按察使、广东右布政使。嘉靖三十五年(1556),卒于家,享年62岁。
作为李渭的父亲,李富乐于自己的儿子能够得到田氏兄弟这样的大家指导,自然勉励儿子精研易理,探幽阐微,未来能有一番大作为。因为学《易》有三个好处:一是能够使李渭进入科场参加科举;二是可以帮助李渭静思玩索,探求本心;三是激发李渭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目光远大、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果然李渭不负父望,一试以《易》直接中举。
四、结语
李渭“幼蒙庭训”,对他尔后的儒学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经过李富的“庭训”,使李渭的青少年时代迎来了人生的曙光,为日后李渭建立自己独特的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在当时程朱理学盛行的明代,青少年时代的李渭受父亲庭训时,也只能走朱熹的为学路线,故他的父亲用“毋不敬”和“思无邪”对他进行教诲。但朱熹“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27]1505的路线已经不适应明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李渭必然转向更为直截了当的心学。因而“幼蒙庭训”又为李渭从程朱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准备了思考契机。
第三,李富将陈白沙的《禽兽说》写给李渭,让李渭很小就明白人与禽兽之别,为李渭立志“必为圣人”确定了人生价值取向,激励了李渭主体精神的觉醒,为李渭后来亲近江门学派大师湛若水和兼王、湛二学之长的蒋信埋下了伏笔。
第四,李渭在“庭训”时期采取的静坐求心的方法,为日后被蒋信点破“楼上楼下光景”,而由楼上静坐走向世上磨炼开启了前行闸门,不仅为他将来入仕为官保持廉洁奉公、操行清白的品德夯实了心理防线,亦为其一生最后归宗阳明心学开启了逻辑起点;同时也为李渭后来师从湛甘泉,理解“随处体认天理”,以至晚年著书立说提出“先行”哲学提供了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