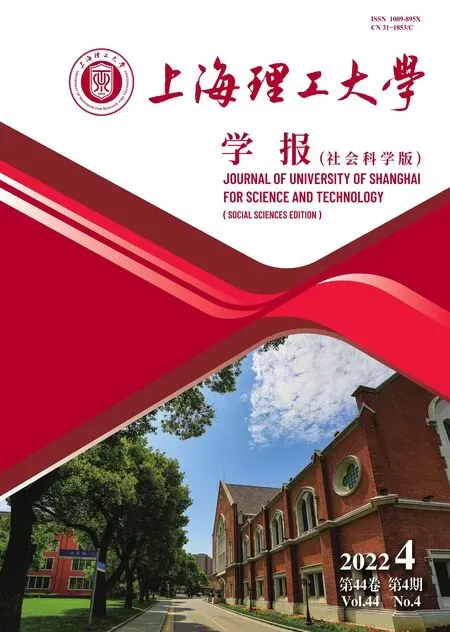叙述冲突中的海达·高布乐: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
邱利萍,金文宁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创作于1890 年的《海达·高布乐》大概是易卜生所有剧作中最专注于人物刻画的,就连易卜生自己都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并非讨论什么社会问题,而是想在现实社会条件和原则框架下描述人性,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1]3。作为剧中的主角,海达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谜团。她离经叛道却也安于懦弱,她渴望自由却采取毁灭的方式,不仅毁灭自己,也毁灭他人的幸福。正是海达的复杂性,百年来随着这一剧作被无数次地搬上舞台,对于剧作文本新的诠释也从未停止。
有学者不仅从海达身上看到了现代人的特征,还认为她具备现代女性的觉醒意识。詹妮·比约克隆德(Jenny Björklund)认为,与泰遏身上明显的女性气质不同,海达拒绝女性气质而拥抱男性气质,她渴望像男性一样生活[2]。徐燕红从女权主义的理论视角论述海达“是一个藐视男性主宰和男性优越的不同凡响的女性,一个为甩掉枷锁和桎梏而斗争的勇敢的斗士”[3]。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朱晓映和托瑞尔·莫伊(Toril Moi),前者指出海达的自杀源于她的诗性人生追求,表达了对男权的抗争和自由的追寻[4],后者解释海达身上展现了其对美的追求就是她对自由的渴望,海达不仅代表了被压抑的女性,还暗含了对现代人的追问[5]。那么海达是否真的代表了一个现代女性?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同。汪余礼贬斥了海达的“魔性”,认为她“内心的诗源于她的空虚感、荒谬感”,是为了探索“不可能的存在”[6]。何成洲则认为海达符合颓废者的特征,对现实生活极度“厌倦”,寻求操纵男性命运的刺激,对“死亡美”有着执着的追求[7]。总的来说,对海达这个人物的消极意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哈尔·布莱斯(Hal Blythe)和查理·斯威特(Charlie Sweet)提出的海达性格存在的两方面缺陷,一是对身边人绝对的控制欲,二是无法忍受残酷的现实之光[8]。
上述研究分别从海达的行为动机出发分析了海达或“女斗士”或“颓废者”的人物形象,但尚未将海达这个人物置于整个叙述框架下考察,忽略了其中各种人格的叙述意义及对人物形象的揭示作用。本文试图根据赵毅衡提出的叙述框架—人格理论,探讨海达这一叙述人格的主观认知与其他叙述人格所展现的客观实际的冲突,从而揭示更为客观,更为真实的海达和其周围人物:海达并非现代女性的化身,为挣脱父权社会性别枷锁而抗争,而是一位以绝对的自我为中心的悲剧人物;剧本中的其他人物也并非如海达的叙述人格所展示的那样是一个无趣而庸俗的群体。
一、叙述人格
赵毅衡在其《广义叙述学》中提出了叙述框架和人格填充的概念。在涉及第三人称叙述及叙述者隐身时,他指出,“隐身叙述者呈现为叙述框架”,但叙述框架并非完全是非人格的,叙述文本由各种主体性填充,即叙述文本充满人格因素,而“充填叙述框架的人格可以有各种形式,包括叙述者、次叙述者、受述者、评论者、言语人物、视角人物。结果是框架与各种人格结合,构成一个人格化的框架”[9]245。剧本往往是第三人称叙述,在其叙述框架下,也“由许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人格充填”,即赵毅衡所说的“‘叙述框架中的人格填充’现象”[9]244。
如果考察《海达·高布乐》的叙述框架,就可发现,剧本由各种各样的叙述人格(言语人物)组成:海达、泰斯曼、朱黎阿姑姑、泰遏、乐务博格、勃拉克等。每个叙述人格都有其人物意识,都可能携带其自身的价值观,给我们呈现一个他或她所认知的世界。但是带有人物自身意识的叙述往往跟真实情境是有偏差的,出于人物自身的价值观及立场所作的叙述使观众更易产生同情,而不自觉地忽略其与其他叙述人格的叙述冲突,掩盖了事实真相。因此,聚焦叙述文本框架下的多种叙述人格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剧本中不同人格的叙述,及与主要叙述人格发生的冲突与碰撞,一幅更客观、更真实的人物画卷得以展开。
二、海达之自我中心叙述:海达眼中的周围人物
海达是剧本中的主要叙述人格,从海达的言语行为看,她感知的周围世界是一个无趣的、庸俗的世界。她眼中的丈夫是无趣的书呆子,就算在蜜月期间也流连于各地图书馆,无视她的社交需求。在与勃拉克聊起她的新婚旅行时,她说:“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回来。”她认为泰斯曼埋头于图书馆是乏味的且无法理解的。
海达:泰斯曼!你知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埋头于图书馆抄写那些老古董更有趣的了。
海达:跟专家一起旅行毫无乐趣可言,至少长途旅行如此。
海达:你真应该试试!每天早上、中午、晚上耳边都萦绕着文明史。
海达:对对对!然后就是中世纪的家庭工业,这真是最让人倒胃口的部分。[1]66-68
对于海达来说,离开了舞会、玩乐、交际的生活是乏闷的,虽然她承认泰斯曼是一位专家学者,是一位适合结婚的对象,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他无趣的定论,对于泰斯曼的潜心专研,她也不无揶揄。但对泰斯曼而言,海达叙述中的“无趣”却是他的热枕所在。
泰斯曼:太兴奋了,姑姑,我的旅行皮箱里装满了抄写的资料,你不知道我在档案室获得了多少我心心念念的资料——别人都不知道的让人新奇的古老的东西。
泰斯曼:姑姑,这对我来说还是一场学术研究旅行,我徜徉在无际的古老文献中。[1]20-22
泰斯曼从蜜月回来后,就一直兴奋地向他姑姑“炫耀”他的“战利品”。在他与朱黎阿姑姑的对话中,泰斯曼的叙述人格所展现的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事业野心、价值追求,对学术充满热枕的年轻人。这一点在剧本的后几幕也可以得到佐证。泰斯曼在听闻乐务博格即将出的新书时难掩兴奋与憧憬,甚至无意中捡到乐务博格的手稿后,因为知悉没有底稿的手稿的重要性而决意将代表名利的手稿送回去。最能代表他学术热情的是最后一幕,海达选择自杀之前,为了整理泰遏手中零碎的笔记,他坦言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并即刻邀请泰遏去里屋投注全部精力阅读笔记,甚至还把妻子海达推给勃拉克。虽然他也因此被读者诟病对妻子缺乏应有的关心和爱护最后才导致了海达的绝望自杀,但不可否认的是,泰斯曼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与海达无时无刻的空虚感,对生活强烈的倦意,而执着于“死得美”不同,泰斯曼有人生的目标,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他的无趣也只是由于与海达的生活理念相悖而已。
如果说海达对泰斯曼的叙述呈现的是一种蔑视,海达与泰遏的叙述冲突则更多地表现在她对泰遏的嫉妒上。在得到通报泰遏前来拜访时,海达就一腔怒火:“就是那个有一头烦人的头发的女孩,她以前经常炫耀。”[1]35可是事实上,唯唯诺诺的泰遏却表示她以前十分惧怕海达,因为海达每回和她在楼梯上碰见总要揪她的头发,并扬言要烧掉她的头发。所以海达对泰遏炫耀的叙述是出自泰遏的真实行为还是出于她自身嫉妒的臆想?笔者认为是后者。
海达对泰遏的嫉妒形成了对泰遏的不真实叙述。从第一幕海达与泰遏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泰遏的丈夫并不知晓她进了城,她再也无法忍受她可以预见的凄凉孤苦的下半生,于是她收拾了必备的行李就出走了,并且打算永不回去。就连海达问她:“别人会怎么说你呢?”她也满不在乎:“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在乎。”[1]49泰遏在这段对话中表现出的勇敢甚至海达都惊呼她竟敢做这种事。泰遏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行为是海达渴望而不敢做的,于是嫉妒之心悄悄萌芽。在与乐务博格终于会面之后,她故意把她们早上偷偷见面的事捅了出来,并且添油加醋地形容早上的泰遏神思混沌、惊惧异常,让乐务博格以为泰遏并不勇敢,也不信任他。
一手摧毁了他们两人的幸福之后,海达塞给乐务博格一把他父亲的枪,并嘱咐他一定要“死得美”。海达教唆乐务博格自杀是为了拯救她的“理想信念”,因为她认为现在的乐务博格已经被泰遏驯化了,整日循规蹈矩,行为无可指摘。乐务博格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风流才子,会跟她描述他的风流韵事和荒唐行径。乐务博格已经“改邪归正”了,他正在泰遏的帮助下写作著书,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这是海达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在她的心中,昔日的乐务博格才是她怀念的美好形象,才华横溢,肆意风流。但是过往的乐务博格真的是自由的化身吗?还是这只是海达出于对自由的渴望而对乐务博格的形象做的美化?毕竟连乐务博格自己都坦白从前做的事有多么荒唐和邪恶。从泰斯曼和勃拉克的叙述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全然不同于海达眼中的乐务博格,以前的乐务博格的行为习惯不仅令泰遏厌恶,也让泰斯曼震惊他竟然能胜任爱尔务斯泰家的家庭教师一职。现在的乐务博格在与泰遏的互相帮助下像“战友”一样彼此成就[1]50。对于乐务博格的转变,泰斯曼也感到十分高兴。
泰斯曼:听说他彻底地转变了性格,我真高兴。
勃拉克:他们是这么说的。
泰斯曼:真好,好消息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一想到他以前一步步地自我毁灭的样子我就特别难受。
勃拉克:大家跟你想的一样。
勃拉克:有段时间大家认为他是家族的希望。
泰斯曼:是的,但是他把这一切都毁了。[1]55-57
不仅仅是泰遏,泰斯曼和勃拉克,所有人都认为乐务博格的性格转变是一件好事,除了海达。
海达的叙述带着她自己的价值观,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美的想象。她不愿意承认,是她自己一直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乌托邦,不愿面对真实的世界,而乐务博格“已经完成了伦理选择,成为有着强烈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人”[10]。
从海达的叙述人格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趣的泰斯曼,一个被刻意曲解的泰遏和一个沦为平庸之辈的乐务博格。然而,框架下的其他人格却以更加客观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不同于海达认知的人物群体。作为海达丈夫的泰斯曼,有着自己的学术热情。向海达求助的泰遏,是一位善良、勇敢的女性。海达的昔日恋人乐务博格发生的转变也更多地呈现出积极意义。在海达与其他言语人物的叙述冲突中,我们也能窥见海达的个人中心主义,这一点在下一节更能得到佐证。
三、海达形象的揭示:周围人物眼中的海达
当乐务博格问海达从前是否爱过他,海达回答如下。
海达:无法理解吗?一个年轻女孩,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海达:雀跃地、偶尔地,窥探一下那个世界——
海达:那个她被禁止接触的世界。[1]94
对于海达来说,乐务博格所代表的世界是她所向往的而又不能实现的自由。她与浪漫、不羁的乐务博格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她渴望过上不被她所处的上流社会允许的肆意的生活。在海达的心中,不管她以前作为海达·高布乐的生活,还是现在成为海达·泰斯曼的生活,都是乏味、无聊的,她的丈夫、朱黎阿姑姑等人也是无趣、庸俗的代表。但是,尽管海达对生活诸多不满,对自由保有热烈的幻想,但是她无所作为,她既没有像泰遏一样不顾一切离家出走追求想要的生活,也没有试图改变她厌倦的生活和周围环境,从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一点乐趣。
所以说她是一个为挣脱传统伦理束缚的勇敢的斗士是不成立的,海达并不具备现代女性的品质。
首先,海达是一个胆怯的人。这在乐务博格的叙述中可见一斑。乐务博格问海达为什么从前没有一枪打死他,海达回答如下。
海达:因为我怕丑闻。
乐务博格:没错,海达,你真是个内心怯懦的人。[1]95
虽然泰遏对乐务博格展现出一副唯命是从,柔柔弱弱的态度,但是她尚且能不顾传统礼教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海达这样一个自命清高的人对流言蜚语的惧怕却超过了她对爱情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甚至最后勃拉克能以乐务博格的中枪和她的联系所可能引发的绯闻来威胁她,这样看来,海达对于自由和理想的追求是不堪一击的,她也并非是一个勇士。
有学者认为海达身上体现了一种男性气质。的确,海达从小在将军家庭长大,受她父亲的熏陶,喜欢骑马和射击。她更喜欢把玩她父亲留下来的枪——男性气质的象征。剧中她父亲的枪多次出现,海达用其瞄准勃拉克戏谑他,最后还唆使乐务博格用它来自杀。与泰遏身上明显的女性气质不同,海达对于枪的迷恋,蔑视一切的姿态,对于试图用语言操控他人命运的驾驭能力,都体现了她非柔弱女性的一面。但这并不能代表她的男性气质掩盖了她的女性气质。当勃拉克疑惑海达为什么选择泰斯曼时,她的理由是他是一个适合的结婚对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受人尊敬,并且她相信他会获得成功,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他能打败其他追求者的关键,是他愿意倾其所有负担她的生活。
从勃拉克和海达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一个寄希望于男性,依附男性的传统女性。虽说海达喜欢把玩枪,但是她并未真正从枪中获得勇气,她希望有人提供给她想要的生活,尽情玩乐。
海达:我们说好的,我们要踏入社交圈,我们要敞开门欢迎客人。
泰斯曼:对,你不知道我盼望多久了——看你成为女主人——处于交际圈的中心。[1]60
泰斯曼知道海达热衷于被众星捧月的交际应酬,并且也乐于满足她。他对海达的迷恋不仅暴露了海达的世俗物质观,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海达的癫狂。当泰斯曼得知海达烧了乐务博格的稿子时,他反问海达:“你脑子里装了什么东西?你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1]144不仅泰斯曼对海达的行为迷惑不解,众人也对海达听到乐务博格中枪的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愉悦十分意外。
海达:我说这事儿真有美感。
勃拉克:嗯?泰斯曼太太。
爱尔务斯泰太太:海达,你怎么能说这种事美?[1]152
如果说海达最终选择自杀可视为她追求自己所谓的“诗性”理想和灵魂自由,那么她最开始试图把自己对美的执着追求寄托于乐务博格的“死得美”上则展示了她最本质的一面,一个以绝对的自我为中心的人。她在教唆乐务博格自杀的时候已经深知她与乐务博格再也无法心意相通(因为乐务博格的头发里再不会插葡萄叶子),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自己对于美的想象强加于乐务博格身上,事实也证明乐务博格并不想自杀。她不仅想以毁灭他人的行为来测试自己是否具有支配别人命运的能力,而且还想让别人的死来完成她对于自由,对于美的执着追求。就这一点而言,海达如果不是出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是玛丽·凯·诺森(Mary Kay Norseng)认为的海达患有精神疾病,也正是她的精神疾病导致了她的疯狂行为[11]。
最后,海达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到底是什么呢?是物质上的优越感还是灵魂的自由抑或是快意人生?从泰斯曼一家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高在上,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从前的将军的女儿,现在的女主人。从勃拉克与海达的私密谈话中展露的是不甘于生活的庸常却贪恋社会名声和地位的上流社会的女人。通过泰遏的叙述及对比,海达是一个懦弱的,只会疯狂嫉妒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她得不到的东西不如把它毁了。她说:“现在我们三个可以痛快了。”[1]101最能展现海达所谓的人生追求的大概是乐务博格的叙述,他问海达,既然你对人生有追求,为什么不继续寻找伴侣呢?我知道我们的共同点是对于生活的热烈追求[1]95-96。在一定程度上,乐务博格是了解海达的,至少比泰斯曼更懂海达。通过这些叙述人格,我们看到了全方面的海达,却其实看不到她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换言之,她到底追求怎样的人生?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她不仅符合何成洲所说的颓废者的特征,即出于对生活的厌倦而寻找极端的刺激,更可视为一位缺乏人生真正目标,妄想肆意生活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旦周围人物不符合她的期待,即采取毁灭的方式。
四、结束语
如果把海达和其他人物置于整个叙述框架下考察,就会发现,海达眼中的周围人物和周围人物眼中的海达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海达眼中的泰斯曼是无趣的,泰遏的一切本该是她的,就连旧情人乐务博格最后也让她失望透顶。周围人物眼中的海达虽渴望自由和热烈生活,却也懦弱、嫉妒心强、贪恋名声和地位。通过框架下叙述人格展现的矛盾和冲突,则会发现众多更为客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热枕的泰斯曼、勇敢的泰遏和回归正途的乐务博格。而海达的自我中心主义、病态的控制欲和人生目标的虚无也得到了揭示。最后,虽然海达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社会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不可否认,海达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其追求自我,渴望自由的女性形象对今天的社会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该人物的理解也可从更宏观的艺术层面和历史背景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