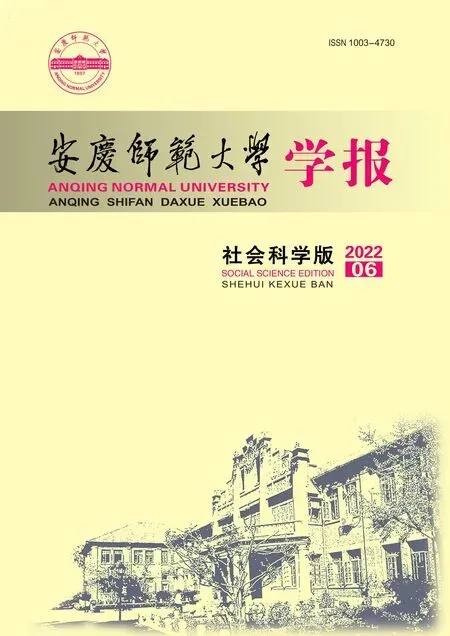桐城派诗人许所望和他的诗歌
杨化坤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许所望,字叔翘,号蔬园,安徽怀远县人,生活于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师从姚鼐,著有《蔬园诗集》《经荫堂文集》,生前以诗名世,是桐城派诗人中较为重要的一位。许所望性情豪迈,慷慨任侠,渴望通过科举之路,建立一番功业,然而终其一生,只是一介诸生。或许因为身份的低微,加之生平材料的稀少,许所望在后世并不为人重视。但与一般的底层文人不同,他有着传奇的人生,主要表现在:一是许所望因两次平定叛乱为皇帝嘉赏,但他坚辞不受,颇受时人赞誉;二是许所望交游广泛,以布衣身份与当时大批政界、学界、文坛之人多有来往;三是许所望文采卓越,尤精于诗歌,甚至袁枚、姚鼐这样的文学巨擘也对他称赞有加。可惜的是,如今各种清史著作均对他视而不见,甚至一篇专门的研究论文也没有,殊为可惜。作为乾嘉时期的重要诗人,我们有必要加以研究,揭示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杰出的诗歌成就。
一、历游诸侯间:许所望的生平与交游
许所望祖籍浙江东阳,是《晋书·孝友传》中记载的孝子许孜之后,祖上于明朝初年迁至安徽省怀远县。许氏家族在明朝即以孝睦著称,《怀远县志·艺文志》著录:“明《褒孝集》八卷,文二卷,诗六卷,为孝子许本忠作,潘府序。”据李兆洛《褒孝集书后》可知,许本忠,字克孝,为许所望九世祖,颇有孝行,当时许氏“三世孝子旌于朝,啧啧于人口”,为此,“一时贤士大夫咏歌其事,以美盛德,而维世教之所为作也”[1]。这些诗文被汇为一册,名为《褒孝集》,由著名儒者潘府(字孔修,1453—1525)作序,可见许氏家族当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只是由于材料的缺乏,许所望的家世已无法考证,目前只知其有二子,一为许星,幼年颖慧,能诗文,不幸早卒,《(嘉庆)怀远县志》载有其长篇古诗《涂山》一首。另有一子名叫许镛,许所望卒时尚在世。
许所望生活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李兆洛《许蔬园诗序》中提及许所望、张翰风(琦)、包慎伯(世臣)三人,称“蔬园年最长”[2],其中张琦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包世臣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则许所望的生年在1764年之前,具体哪一年,就无法得知了。许所望的卒年也无法确考。孙让任怀远知县时,主编《怀远县志》,许所望曾参与编纂。其所提供的材料,时间最晚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管同在《跋〈团勇助军约记〉》中说,许所望六十八岁时,意气谈论未衰,但特别穷,吃不饱穿不暖。《(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称许所望“年八十余卒”,但究竟何年去世,则没有确切记载。
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许所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其一生,也没有获得一官半职,《清史稿》记载其身份为“诸生”,《(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称其“增生”,《(嘉庆)怀远县志》称之“增广生”,周仪暐在与他的唱歌诗中称他为“明经”,伊秉绶称他作“秀才”。可见,许所望只是一介布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他文武双全,胸怀大志,丝毫没有穷酸之气。范锴称他:“膂力过人,复精枪法。”[3]李兆洛描述他“修干亭伟,视有奇气”[2],高锡基说他“身长八尺,顾视不凡”。据此可知,许所望迥异于普通文士,完全是豪侠的形象。许所望对剑情有独钟,他的很多诗歌中都有“剑”字。他曾绘有《说剑图》一幅,不少人题诗于后,现有文献可查的如周济《题许叔翘说剑图》、周仪暐《许叔翘说剑图并序》、陆继辂《许所望说剑图》、林晋奎《题许叔翘说剑图》,都是其中的作品。高锡基说,许所望晚年隐居乡里时,“徜徉修竹间,飘飘然有古剑侠气”[4],体现了他任侠的性格特点。尽管以诗著名,但他向来不以诗人自诩,刘开评价说:“怀远许君叔翘,以诗学名一时,其动于中而发于辞也,往往豪荡有奇气,见者咸惊叹而弗置,而许君顾不是重也。盖素挟奇伟非常之气才,每慷慨激烈,欲以气节功名自见,故能慎取与重然诺,济人之困而不自德焉,此诚古侠烈之士所不能过,而世徒以诗人目之,无惑乎?”[5]刘开(1784—1824),字明东,安徽桐城人,古文名家,亦师从姚鼐。在刘开看来,并不能把许所望简单视为诗人,他的诗歌“豪荡有奇气”的原因,是源于其人有“奇伟非常之气才”。其中“重然诺”出自《史记·季布列传》:“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6],对许所望的侠义气概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李兆洛称他:“淮颍间固多伉健特绝之士,无不奉手愿交者。”[2]“淮颍间”即皖北地区,这里常出一些武将和豪侠,“伉健特绝之士”指的即是这些人。
许所望好壮游,足迹遍布天下,“关山之阨要,河渠之通塞,靡不究悉”[4]。他的同乡林晋奎在《与许叔翘茂才书》中说:“古之好游者,唯龙门太史,于山则探禹穴、窥九疑、上邹峄,于水则沅湘也、淮海汶泗也,故其文伸缩变化、崛强自喜,虽好学深思者之力,而实有山水助焉。阁下游闽浙,登武夷、匡庐,岂不欲踵武龙门耶?”[7]龙门太史即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司马迁到过很多地方。林晋奎将他比作司马迁,认为他的诗文之所以汪洋恣肆,变化万千,与他的游历天下密不可分。许所望在《和吴清夫翰簿韵》(其二)中说:“青萍按剑常为客。”“常为客”即时常外出远游。他的现存作品中,很多都是记游之作,如《项王庙》作于古垓下(今安徽固镇县),《虞姬墓》作于安徽灵璧县,《大泽乡吊陈胜》作于安徽省宿州市大泽乡,《登亳州戊楼》作于客居亳州之时,《木兰祠》作于商丘县银哥集,《呈毕秋帆沅先生》是丙午年(1786)客居河南时所作。寓居金陵时,许所望留下了《栖霞道上》《黄天荡夜泊》《金山寺》《金山吊韩蕲王》《望焦山》《登北固山》《出润州》《夜泊燕子矶》等诗篇,这些都是他外出游历的见证。
长期的游历生活,不仅有助于开阔眼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素材,也让他结交到当时许多政界、学界及文坛的巨子,李兆洛因此称他“历游诸侯间”。与他交游之人,无不为他的豪气折服,对他评价甚高,高锡基说他:“足迹半天下,所在交其豪杰,而一时贤士亦愿与之游。管异之赠句云:‘海内名家皆地主,江南贤士半门生。’可以想其人矣。”[4]管异之即管同,赠诗体现了许所望的影响力。周仪暐在《许叔翘说剑图并序》中回忆与许所望的交往时称:“叔翘豪迈卓荦,怀古奋发之气,奕奕动眉宇,遂共定交。”[8]329辛亥革命元老、著名书法家张树侯(1866—1935),曾通过友人获得《蔬园诗集》四卷,亲为抄写。他说:“余不解诗,但见集中有与袁简斋、姚惜抱、孙渊如唱和,其人可知矣。”[9]说明许所望的交游之广。
许所望交游的人,如袁枚、姚鼐、孙星衍、毕沅、马瑞辰、李兆洛、周济、刘开、胡克家、陈用光、伊秉绶、宋翔凤、邓廷桢、陶澍等,大都是当时的名流,这在他的诗作中均有所体现,如进呈其师姚鼐的诗歌有《呈姚姬传鼐先生》(二首),与姚鼐论诗的作品《与姬传先生论诗》,姚鼐去世时,作《哭姚姬传先生》。赠给孙星衍的有《五松园赠孙渊如星衍观察》,怀念檀萃的有《檀默斋萃大令招集草堂书屋》,赠予袁枚的诗有《过访随园赠简斋先生》二首、《莫愁湖棹歌呈随园老人》十首,进呈毕沅的有《呈毕秋帆沅先生》,毕沅去世时,又作《挽秋帆中丞》以示哀悼。进呈珠伊庭隆阿的有《谈天》(三首),赠予孙世昌的有《赠孙少兰世昌检讨》,赠予张问陶的有《吴门晤张自渡问陶有赠》,赠予李兆洛的有《小金牌为申耆大令赋》,纪念与李兆洛等人雅集之作《八月七日李申耆、汤颍川、林念航、郑春山小集抱璞岩山楼》,赠给胡克家的有《军中呈胡果泉克家中丞五首》,赠给林岚的有《军中呈林晓岑岚太守调任彰德》,赠给伊秉绶的有《寄伊墨卿秉绶太守》,与宫樟、林晋奎等人雅集的有《十一月五日宫寉臞招同吴荆氓、林念航雪后小集二石轩,五古分韵得集字》,寄给沈钦韩的有《行路难寄沈小宛钦韩》《马献生瑞辰庶席常出其尊人稷甫先生夏日校经图卷子索题》。此外,他的诗集《蔬园诗集》卷六中,载有《怀人诗》一组共三十首,分别怀念三十位旧友:长洲顾日新剑峰、桐城刘开明东、天长程虞卿禹山、泾县包世臣慎伯、秀水王曇仲瞿、荆溪周济保绪、桐城方梦松子固、桐城方于毂石伍、吴县沈廷照芷桥、吴县沈钦韩文起、滁州张葆光仲千、武进董士锡晋卿、杭州朱文震午山、蒙古法式善梧门、定远方积有堂、姚梦谷先生、赵州师范荔扉、太和沙琛雪湖、相城汪正鋆均之、常熟邵渊跃君远、仪征吕彩双桥、定远陈俊千常佰、桐城汪镇光星石、婺源董炼金牧塘、怀宁劳崇勋让泉、凤阳王鼎禹夫、桐城马瑞辰献生、吴县王渭小梧、同邑宫樟寉瞿、汉军鳌图沧来余。这三十首作品连同前文所举诗歌往来中的人物,均为一时之选。
许所望交游的士人群体,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以桐城派文士为主,如姚鼐、刘开、管同、陈用光、吴贤湘等,属于师徒与同门关系,体现了许所望的流派属性;二是以江南一带的士人居多,如管同赠诗“江南贤士半门生”,还有李兆洛称许所望以诗“名噪江表”,江表即长江以南地区,体现了许所望活动的地域范围。从社会阶层看,许所望的交游上至封疆大吏如汪志伊、胡克家、毕沅、陶澍等,下至底层文士乃至江湖豪侠,无不往来,说明许所望交游的广泛性。作为一名没有功名的文士,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许所望的生平,也有助于交游对象的研究。只是由于篇幅关系,这方面的内容暂不展开,留待日后进行。
二、书生拜大将:嘉庆年间两次助军行动及影响
许所望虽为一介儒生,但他十分关心社会现实,除了研习举业之外,还通晓兵法,时时留心实用之学。陈用光在《书许所望》一文中说他“通兵法,喜慷慨趋义”[10]305,高锡基称:“自诸子百家以及天官五行诸书,无所不读,又所至之地,关山之扼要,河渠之通塞,靡不悉究于心。虽不得志于时,无所用,而经世之意未尝一日去。”[4]体现了他强烈的经世之心。许所望作文讲求实用,吴德旋评价曰:“叔翘文自兵家言入,盖尝已见之施行,而非空言无实者之可比,故屡为当代巨公所赏。”[11]又管同在《许叔翘文集序》称他“时时键户读书,研究当时利弊,著文数十篇,以待世用”[12]。与他交往的封疆大吏对许所望的器重,除了其杰出的诗歌才华外,看重的还是他经世致用的才能。终于,许所望的军事本领,在嘉庆年间的两次剿匪行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第一次是嘉庆七年(1802)冬,安徽宿州百姓王朝明、李胜才造反,攻破州城。许所望与亲戚王冠英捐献粟米三千石资助征讨,并在陈家集助军攻破叛贼。由于记载简略,具体过程不得而知。第二次是嘉庆十八年(1813)秋,天理教林清起义,许所望参与平叛,也藉此名扬天下。当时,归德(今商丘市南)杨七郎盘踞在引河集,其党羽洪广汉占据保安山,与颍州沙占魁等遥相呼应,形势十分危急。两江总督百龄驻徐州,安徽巡抚胡克家驻亳州,随时准备战斗。胡克家素来知道许所望的威名,遂写信求助。收信之后,许所望迅速赶来,任邱惠龄、张国纲、谢崇训为队长,率领八百人到达亳州,并在霍邱平定了趁火打劫的土匪。胡克家幕下多一时俊杰,许所望每日参议军事方案,并对军情进行了冷静分析。他说:“杨七郎猛且狡,闻吾在军备,且密宜计诱之。”遂命张国纲、谢崇训率领健卒八人假装为逃卒奔赴杨七郎,五天后将他引诱到邱家集。杨七郎忽然怀疑说:“若为许所望来耶?”崇训出其不意砍断他的手臂,众人大惊,国纲大叫:“吾张国纲也!”随即击杀数人。张国纲与谢惠龄一同攻破宿州起义军。许所望率兵到来,这时杨七郎已死。于是保安山洪广汉众人也溃败而逃。沙占魁等人奔走永城,会师攻克滑县,其余起义军与他们会和,焚烧会亭。许所望与他们在公基湖激战,在土埠上排列十杆火枪,说:“贼至二百步发。”又令众人伏地勿动,并说:“枪发乘烟突击之。”结果大败敌军,追杀数十里,斩获无数,于是亳州罢防。
这次军事行动,许所望功劳最大,但事毕之后,他分别辞去庐凤道珠隆阿及安徽巡抚胡克家为他叙功,乃至嘉庆帝诏书嘉奖,也推辞不受,仍以诸生的资格参加考试。他的这番行为,为他赢得了身前身后很高的名声。同时代人张宗辉作诗《赠许叔翘》曰:“未老参军已白头,兴酣横槊尚风流。金戈铁马铮鏦地,玉帐牙旗啸咏秋。檄到果真能却敌,功成何必定封侯。况闻天语亲垂慰,便较书生胜一筹。”[13]描摹许所望在战场上的豪迈形象,称赞他功成而弗居的义举。民族英雄邓廷桢(1776—1846)也对他的豪气和文采大加称赞,作诗《题怀远许叔翘所望〈蔬园诗文集〉》三首,前二首说:“如此书生未易才,万言献策在平台。缦胡缨短招摇急,争看将军揖客来(一)。三河年少罢防秋,拂袖归耕涡水头。齿冷扶风班定远,匆匆投笔为封侯(二)。”[14]第一首称颂许所望剿灭逆匪之事,其中的“万言献策”即许所望为剿灭杨七郎所献之计。第二首赞扬许所望辞封归乡之事,班定远即班超,曾为定远侯。班超投笔从戎是为了封侯,许所望却不齿于此,选择归乡种菜,高下立判。多年之后,合肥狂生王尚辰(1826—1903)仍对他赞不绝口。王尚辰,字谦斋,合肥人,恃才傲物,因排行第五,人称“王五疯”。张树侯说,“谦斋非轻许人者”,但“亦曾推许为江北名士”[9]。王尚辰生活的年代,许所望已经去世,但仍对他推崇备至,说明许所望在江淮地区的声望之高。
许所望助军事迹最早由吴贤湘(字清夫,1748—1828)作文记载,后陈用光(1768—1835)根据吴贤湘的文字,撰写了《书许所望》一文,以史传文体详细叙述了这次剿匪事件,正文记事,文末论赞,上面的叙述即基于此文。这篇文章又被沈兆沄《篷窗续录》及李桓编纂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录,《清史稿·许所望传》中的记载也源自于此。吴贤湘又将文章寄给他的好友、著名书法家伊秉绶(字墨卿,1754—1815)。伊氏与许所望本不相识,听闻他的壮举之后,十分钦佩,特为他创作歌行体诗《义士行》,前有长序,叙述许所望的事迹,后以歌行体赞颂他的义行:
叔翘名所望,怀远诸生,工诗,精天文,慷慨任侠。嘉庆癸酉秋,逆匪扰滑县,安徽巡抚胡公克家驻亳州,以书聘之,曰:“官军少且难信,叔翘天下义士,忍坐视哉?”于是感焉,集以勇得八百人赴亳。贼杨七郎者最狡猛,渠魁也,拥众四屯为颍匪声援。叔翘命勇士张国纲等九人伪为逃匪者投之,诱之游邱家集,杨七郎忽疑曰:“若为许叔翘来耶?”勇士未应,出不意,刃之断左臂,同呼曰:“身某是也!”时贼众数百,方惊愕,叔翘兵至,贼溃各屯卷窜无踪。抚部欲馈金奏绩,叔翘力辞之归,抚部拱手谢曰:“奇男子!”次年,叔翘访汪均之太史二公子于福州,枉惠予书,吴清夫征君为书事寄予,因作诗定神交焉。
君不见,秋高河北束萑苻,慎固封守诚堪虞,秀才仗剑一奋呼。志士赴义期敢逾,饮酒百斛心胆粗,白日市上戕封狐。喧传杨七郎受诛,观奇男子如吴姝,十年亦聘朱大夫。季布诺行淮泗趋,更闻卜式家资输。国家养士文武俱,如君不媿谭诗书。吁嗟鲰生无远图,阳明山好思真儒①本诗据西泠印社(绍兴)2018年秋季拍卖会邓实“风雨楼旧藏明清翰林学士手札专题”图片所录。。
《义士行》序文记述了许所望的英勇事迹,正文称赞他过人的军事才能和英雄气节。此诗不见于伊氏诗集《留春草堂诗》,但检现存《蔬园诗集》,中有《寄伊墨卿太守》一首,自注曰:“余与墨卿未识面,书札往来,各以气节相许。”[15]证明二人交好的事实。
许所望对自己的这次表现也非常满意,他将事迹写成《团勇助军约记》一卷,随身携带,所遇之人,纷纷题咏。邓廷桢曾作《百字令》一首,序文称,“用东坡韵题许叔翘《团勇助军约记》卷子”,词曰:
八公山下,倚寒风,凭吊千秋英物。手把龙韬谁继起,又见淮南坚壁。短剑喑呜,长缨通侠,血染弓刀雪。菰芦深处,就中原有奇杰。
听说平揖军门,留君不住,挥手归鞍发。老屋三间无恙在,户外清涡明灭。窗爱闻鸡,市羞屠狗,江上从晰发,酒徒云散,幅巾闲弄明月[16]。
淝水之战是发生于八公山的著名以少胜多的战役,此词上片以此为开头,描写许所望战场上的英勇,下片描绘他功成弗居的洒脱。
著名词人宋翔凤(1779—1860)曾于孝逸含山官舍见到许所望,叔翘出其《团勇助军约记》。宋翔凤读后,钦佩至极,亦作《念奴娇》一首,歌颂他的义举:
唾壶缺后,尽消除不去、胸中何物。草木淮南全刬处,历历犹存垒壁。瘢拭刀鋋,沙埋箭镞,人事更霜雪。后生乡里,近来莫问英杰。
《世说新语》记载,王敦每于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壶口尽缺。此词开篇即用这个典故,表达许所望的英雄之志。一战成名之后,许所望选择返乡,仍旧过着耕读生活。词作表达了对许所望品质的称颂。
著名词人周济(1781—1839)与许所望堪称挚交,他读过《团勇助军约记》之后,作有歌行体长诗《书许叔翘从军纪略卷后》,先赞颂许所望助军事迹,后回忆了与许所望的深厚交情。前半部分诗曰:
古寓兵于农,今寓将于士。寓兵作其勇,寓将厉其志。不然承平二百年,小丑跳梁何术制。羽檄征兵转饷难,中宵风鹤动江关。定知剧孟非豪侠,犹在条侯疑信间。许浑跌宕原诗客,那识谈兵有奇策。轻挥白羽度如仙,兀坐交床心似铁。推诚伍士醪屡投,抗揖名卿袜争结。已将大义伏椎埋,肯累清时破资格。浩荡江湖养四灵,趋跄台省辞三杰[17]。
诗歌夹叙夹议,盛赞许所望平定叛乱之功。其中的许浑代指许所望,世人只晓他是一位诗人,谁知亦精通兵法,很快剿灭了乱匪。许所望虽建立大功,但他不愿破坏科举制度,毅然婉拒封赏,归于江湖。作者虽然只是客观叙述,但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个讲究气节之人,许所望追求的只是立功,对于利禄看得很轻。上述对许所望的赞誉,不仅源于他助军平乱的义举,更是为他淡泊名利、洒脱超逸的品质所感动。他的这番行为,与战国时期鲁仲连功成身退极为相似,颇有名士风度。如此超脱之人,虽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却少之又少,或许正因如此,才会引发人们内心的触动,以文学的形式,对许所望不吝以最热烈的赞美。
三、江北第一家:许所望的诗歌及评价
许所望生前即以诗文为人称道,他亲炙桐城派大师姚鼐,所作古文带有兵家的凌厉之气,谈古论今,纵横捭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管同说:“叔翘之文,皆有用之文也,其《答胡中丞》一书,深处远谋,尤为切于时务。”[12]指出了其文章务实致用的特点。其所著《经荫堂文集》,由管同及吴德旋作序,惜亡佚较早,具体内容现已无从得知。
较之古文,许所望的诗歌影响更大。高锡基《许所望传》记载,许所望早年以《十大将军诗》见知于袁枚,“简斋因问所得,对以字里生音,简斋谓为知言”。汪志伊任福建巡抚时,寄书与许所望,索其所作《落花诗》《落叶诗》,许所望只寄与《落叶诗》,汪志伊复书称为绝唱,并诘问为何不寄《落花诗》:“向闻‘无主园亭积更多’诸句传遍大江南北,何特靳之?岂以不能如《落叶》之独步一时,遂欲取而怀之耶?”于是再三索求,并力邀入闽。两江总督陶澍登上长江边上的采石矶,偶然发现石壁间题有两句诗:“天地有谋能设险,江山无故不生才。”诗句属对工整,气势恢弘。陶澍极为欣赏,遂延礼之。后作《黄牡丹诗》,陶澍读至“亲为山人脱白衣”句,不觉抚掌大赞曰:“人与物俱得之矣,咏物诗不当如是耶?”[4]给予了极高评价。
李兆洛《许蔬园诗序》中,提到了与许所望同时的张翰风(琦)、包慎伯(世臣),他们三人生逢盛世,却都怀才不遇。李兆洛评价三人诗歌说:
三君者,皆工诗。翰风清修绝俗,希心建安、黄初间。慎伯则镵削如宋之半山、山谷、诚斋,皆不自收拾无成轶。独蔬园以诗名噪江表,选家刊行之者屡矣。其诗沉酣于三唐,雄岸卓铄,语出胸臆,而出奇无穷,盖其迈往凌厉之气,一寓于诗,故能肖其心之所得如此也[2]。
综上所述,此次以某商住小区工程项目建设实例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根据建筑施工过程中有关节能环保技术的运用和实践问题,展开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介绍了外墙钢丝网玻化微珠保温施工方式、屋面保温隔热施工方式和节能门窗施工方式运用的关键点,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了节能环保理念的合理渗透和运用。从整体看,在现阶段的建筑施工过程中,节能环保技术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所以相关研究人员应当专注于对节能环保技术的进一步运用,在减少资源浪费问题产生几率的同时,减少工程施工成本,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提升建筑工程环境效益。
张琦(1764—1833),字翰风,张惠言胞弟。与胞兄合辑《词选》二卷,开创“常州词派”,嘉庆十八年(1813)方中举人。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吴(今安徽泾县)人。嘉庆二十年(1815)举人,曾官江西新喻知县,后被劾去官。三人虽然都工于诗歌,唯独许所望“以诗名噪江表”。李兆洛认为,许所望的诗歌用语自然,气势雄壮,出奇无穷,其豪迈凌厉的性格,通过诗歌得以很好地抒发。周仪暐在《答许明经》一诗中,评价许所望诗歌曰:“玄言如环笔如铁,论说波翻思云谲。琅琅掷地金石坚,诩诩回春肺肝热。”[8]331认为许所望的诗论说奇谲,音韵铿锵,与李兆洛的评价颇为相似。又《(嘉庆)怀远县志》载,怀宁潘瑛为许所望同乡宫樟《二石轩诗集》作序说:
余于怀远识二诗人,其一为蔬园许所望,一则鹤癯君也。蔬园才气疏宕,有纵横蹀躞之慨,所为诗歌卓躒负彩,光怪变现。鹤癯则恬愉水澹冶,如澄潭万顷,微风动波,又如远山平林,境与意会。一草一石,具有天趣,令人棲迟而不能去。故余尝目二君之为人:鹤癯似欧阳永叔,蔬园似石曼卿,而诗亦肖之,不能置甲乙也[18]。
宫樟(1767—1816),字鹤癯,安徽怀远人,官至颍州广文,著有《二石轩诗集》,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颍州与友朋泛舟载酒,每有诗作,人们竞相传写。潘氏将许所望与宫樟对比,认为许所望的诗歌,雄奇瑰丽,变化多端,与北宋著名诗人石延年(字曼卿)相似,给予了高度评价。
许所望诗诸体兼擅,尤长于七律,如颇受推崇的《十大将军诗》《落花诗》《落叶诗》《黄牡丹诗》等,均为七律作品。阳湖派诗人陆继辂(1772—1834)评曰:
许叔翘七言律诗最佳,咏《王景略》云:“管仲一身齐治乱,武侯孤掌汉兴衰。”《李药师》云:“蛇门未必开禽虎,鱼腹居然祖卧龙。”《宗留守》云:“南渡尽容追发佛,东迁犹可振髭王。”《登亳州戍楼》云:“干年望草如生谷,泽国登楼当看山。”《咏史》云:“霜戈夜指王罴冢,雪帐宵移李愬移。”“寒炉尚可挥任扇,败鼓何堪补智囊。”“侏儒失势羞韩绛,奴婢登坛笑卫青。”《生日书怀》云:“野戍频年惊鹤唳,江邨中夜感鸡鸣。”“多情只欠看花福,久病难为照镜人。”“公等大都皆碌碌,铁中何必又铮铮。”《友人弃妾生子》云:“金镮故宅生羊祜,芳草新名锡寄奴。”类此数十首,皆足夺卧子之席,元孝瞠乎后矣[19]。
文中提到的卧子、元孝,指的是明末清初两位著名诗人陈子龙和陈恭尹。陈子龙(1608—1647)是明末诗人,为云间诗派首席,被公认为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对清代诗歌与诗学影响较大。陈恭尹(1631—1700)为清初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陈子龙与陈恭尹均为一代文坛领袖,陆继辂将许所望与他们并论,评价之高,可见一斑。又邓廷桢《题怀远许叔翘所望蔬园诗文集三首》其三曰:
哀艳能追锦瑟篇,短衣射虎兴犹偏。剑南豪气樊南笔,兼擅当时一辈贤[20]。
“锦瑟篇”即李商隐的《锦瑟》,“短衣射虎”出自陆游《过采石有感》:“短衣射虎早霜天”。邓廷桢认为,许所望诗律精工如李商隐,性情慷慨又似陆游。高锡基曰:“其论诗也,以为学少陵者,当从义山入手,则可免粗豪之病。学长庆者,当上追初唐,下究梅村诸老,则声情愈茂,而才气益横。”[4]皆说明许所望诗歌尤其七律,确实从李商隐获益良多。他的这种诗歌创作特色,与其师姚鼐有密切的渊源。姚鼐极为推崇杜甫和李商隐的诗歌,所编《五七言今体诗钞》中,五、七言律诗选录杜甫和李商隐最多,认为晚唐诗人“唯玉溪生乃略有杜公遗响耳”,“玉溪生虽晚出,而才力实为卓绝。七律佳者几欲远追拾遗,其次者犹近掩刘、白”[21]。姚鼐对杜甫和李商隐的推崇,显然对许所望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许所望去世后,他的诗名仍在江淮地区广为流传。杨寿宝在《寓无竟斋诗话》(一则,附《寓无竟斋诗存》后)中评价说:
吾邑乡先辈多能诗,尤以蔬园老人为巨擘。老人讳所望,字叔翘,姓许氏,诗有正始音,为姚惜抱先生所称许,其《题燕子矶》有云:“天地有灵能设险,江山无故不生才。”《咏落叶》诗有云:“孤鹤入巣筛冷月,一僧无语扫空山。”尤脍炙人口……搜罗放失,摘其与先辈倡和者著于篇……诸作皆逼近唐音[22]。
杨寿宝(1826—1909),字鹤卿,晚清安徽怀远诗人。文中列举了许所望的诗歌名句,及与其先人的酬唱之作,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另外,杨寿宝又在《寓无竟斋诗存》跋语中说:“唯记幼时读书家塾,于残卷中检得《半舫楼咏史诗》一卷,卷首弁蔬园老人跋语。余既喜卷内有吾父诗在,又震老人名,诗曾经其所评点者也,置之案头,不时批吟。”[22]此则跋语主要记述其父辈的诗作,同时也体现了许所望诗名之高。
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藏书家杨钟羲(1865—1940)在其《雪桥诗话》中摘抄了李兆洛《许蔬园诗序》中的文字,说:“至檀默斋推其诗为‘江北第一家’,则过誉矣。”[23]①笔者认为,许所望与檀萃俱为安徽人士,檀萃称许所望“江北第一家”乃就安徽省境内而言,杨钟羲世居辽阳,他理解的“江北”应该是全国范围的长江以北,故而不能认同檀萃的观点。另外,王尚辰也是安徽籍,称许所望为“江北名士”,应该也是就安徽省内而言。杨钟羲的生活年代较晚,故而对许所望的了解,只能通过前人的文字记载。他引用李兆洛《蔬园诗集序》对许所望的评价,认为许所望乃淮颍之间的奇人。檀默斋即檀萃(1725—1801),字岂田,号默斋,安徽望江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历官贵州青溪、云南禄劝知县。工诗,著有《滇南诗前集》《草堂外集》《滇南草堂诗话》。杨钟羲认为檀萃对许所望诗“江北第一家”的评价过高。许所望的诗究竟是否“江北第一家”,其实并不重要,但通过檀萃及时人的评价我们看到,许所望的诗歌成就在当时是公认的,这应该是杨钟羲也不否认的事实。为此,他又在《诗话》中引了许所望的七律《和吴清夫翰簿韵》两首:
一
不负此番归去来,新诗闻唱夕阳催。
公孙五十犹征士,弟子三千尽妙才。
弦板乍翻江上曲,烟涛真夺海南魁。
山程细数图中句,知我如君事可哀。
二
一识荆州髯绝伦,胸藏十万忆前身。
青萍按剑常为客,白羽谈兵大有人。
宣室何年收李广,邺台终古吊张宾。
箧中共有英雄记,投老相逢泪满巾[23]。
这两首诗音韵铿锵,意境混融,确如邓廷桢所评,精工如李商隐,慷慨似陆放翁,因而也为陈诗《皖雅初集》收录。
许所望的诗集生前即已刊行,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著录:“《蔬园诗集》十四卷,清怀远许所望撰,嘉庆二十三年刊。”[24]可惜诗集雕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杨寿宝说:“所著《蔬园集》版毁于兵燹,集之流布人间者,亦多化为灰烬,其剩简断编,不过存十一于千百。”[22]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也称,许所望“诗文集已梓行,咸丰戊午毁于粤贼”[25],故而《蔬园诗集》在后世流传不广,也是情理之中。今天能看到的《蔬园诗集》共有四个版本,分别是存于吉林省图书馆藏的十二卷本,藏于南京图书馆的足本十四卷和残本八卷,另一个是张树侯手抄的四卷本,藏于安徽省图书馆。
四、余 论
许所望以极高的军事才能和文学才华,获得了世人的一致认可,可在后世,由于身份的低微,以及文集的稀见,很多人逐渐将其淡忘。郭则沄《清词玉屑》评曰:“怀远许叔翘尝从事团防事,后以《团勇助军约记》装卷,盖以官军袖手,厥功不竟,若有余憾。邓嶰筠用东坡《百字令》题云……如叔翘者,猿臂不侯,豹文终隐,独赖是词传之。”[26]对许所望名声的隐没表示遗憾。陈用光在《书许所望》中,还记载了参与另一起助军剿匪行动的严如煜,以佐川楚军功,至汉中府知府。陈用光将他与许所望对比,颇为感慨地说,严氏“至功皆为朝廷显擢矣,人多知之者”[10]306,而许所望两辞军功,晚年凄凉。陈氏虽未明言,但惋惜之情不无可见。又管同在《跋〈团勇助军约记〉》中感慨说:“嗟夫!天下有事,则勇略奇士唾手而成封侯之业,顾安所得穷奇士?而至于穷者,宇内承平,才无可见故也。然则今日于叔翘为穷,于天下事则为福,叔翘又何憾?”[27]在管同看来,许所望功成之后,富贵简直唾手可得,如今海内太平,自然也没有遗憾了。许所望的一生中,“义”字占据重要的位置,伊秉绶称他为“义士”,陈用光说他“慷慨趋义”,所谓“义”,即合乎正义或道德规范,以儒家济世思想为核心的行为表现,而不以个人利益为终极追求目标。显然,许所望的行为是对“义”的最好诠释。
作为一名诗人,许所望对当前的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不可否认,如今的文学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较为明显的,即我们该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如何判断文学家的研究价值?笔者认为,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家固然值得深入研究,但一些本身具有研究价值,而在后世因各种原因被遮蔽光芒的文学家更值得我们关注,许所望即是这样。时至今日,毋宁说各种《中国文学史》没有提及,甚至连近年出版的《安徽文学史》①陈友冰,刘良政编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也视而不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②钱仲联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介绍了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十九年(1839)之间的文学家共3 124人,可并未收许所望。作为有清一代文学文献渊薮的《清代诗文集汇编》③《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重要成果,共收录清代诗文集四千余种,然而亦未收录《蔬园诗集》。还有新近出版的《桐城派文集丛刊》(曹辛华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亦未收录《蔬园诗集》。这种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许所望生前未能取得一官半职,以布衣身份终老,自然不易为人重视;二是由于书版被毁,《蔬园诗集》难得一见。但《蔬园诗集》毕竟仍然存世,并且收录了很多优秀的诗篇。怎奈当代竟无人关注,殊为可惜。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案例,这提示我们当前在进行文学研究时,除了要研究一些大家、名家之外,更要关注那些中小作家,尤其要能以自己的阅读体会判断研究对象的价值,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推动文学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