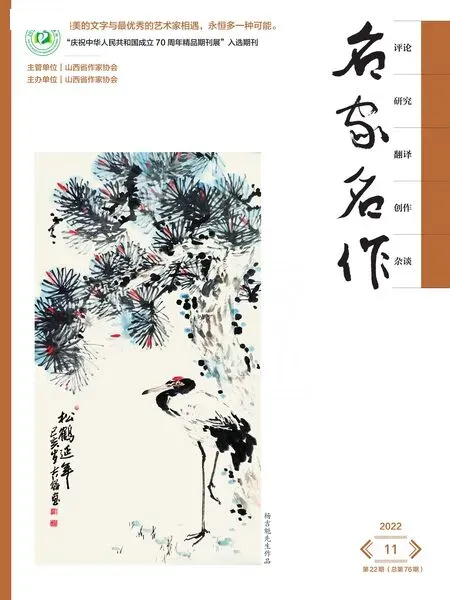流散视阈下V.S.奈保尔《米格尔街》的多维度漂泊
李晨阳 韩 秀
一、因流亡漂泊产生的“无家感”
“现代西方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流亡者、移民和难民文化。”地域的迁移早已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而流散书写所表达的流亡、寻根主题与全球化时代巨变不谋而合。流亡,“是一种被外力驱逐出家园,并且放逐出异地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和奈保尔本人一样,出生在特立尼达这样殖民国家的人,如果他们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钟情于这样一个整个国土先后被西班牙、英国殖民的破碎故乡的。那种无法选择归属的苦涩与心灵落差也是像奈保尔这样的“世界公民”一生的羁绊。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在伦敦工作,在1954年5月3日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不想强迫自己适应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卑微狭隘、目光短浅。您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英国。这是一个种族偏见肆意横行的国度,我当然不愿意留在这里。”在《米格尔街》中,奈保尔也表示特立尼达是被殖民文化侵蚀的地方,一个任何人不会把眼光放在这里的街道。“任何一个人无意间开车经过这里,他肯定说一句:‘这里是贫民窟!’”特立尼达给奈保尔带来的创伤可见一斑。
奈保尔的“无家感”情愫即是上文提到的“迁移”。“在地理层面,迁移通常指从一个地区、国家,或是社区中驱逐出来。”这些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想在某种单一文化中扎根。现实是他们深处被殖民的特立尼达,对于命运毫无选择权。小说中博加特就经历着空间迁移,难以实现想依托单一文化的愿望。从抛弃第一任妻子来到西班牙港,而后失踪前往鲁普卢尼草原放牧,中途再回到西班牙港又失踪几次,他一直在模仿攀附中过着漂泊流浪的人生。出生在特立尼达可能是造成他们一生文化创伤的开端,没有一个人能逃过这种命运的戏弄。
《米格尔街》中有很多像博加特这样难逃漂泊无根境地的人。迁移是流散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但未曾有过跨国经历,却要饱受本土流散之苦,身居“家乡”却深觉“无家感”是不是更为可悲呢?“由于殖民者推广殖民语言、传播基督教、侵吞土地、实行种族隔离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原住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被迫进入一种“流散”的文化语境。”这一章节着重刻画了街上的群众角色,也恰恰体现人们不知道该依附于何种文化的荒谬,街上的人们相信疯子曼门的话,甚至还产生了一众追随者。由于陷入文化的囹圄,人们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对这些疯子的言论趋之若鹜。即使没有空间上的迁移,他们在社会层面上也深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摧残。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产生纠结;他们的思想受到殖民国家价值观的统摄,却又难以与本土传统文化完全剥离,从而在心灵上造成一种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的中间状态。
这样的“无家感”,无论是迁移还是本土流散,都会成为特立尼达人一生的羁绊,可以说几乎无一例外。无论是因流亡、迁移而产生的无根思绪,还是因殖民者使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统治而产生对家园的纠结与疑惑,都难以被轻易抚平和治愈。空间层面上两种流散对人们已经产生难以磨灭的创伤。而在殖民国家“他者化”的摧残下,人们流散身份也大多随时间推进而流动、变化。
二、因身份流动而产生的“无家感”
上文提到流散在地缘上的不同形式,而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摄下,特立尼达人的流散身份也会随时间的推进而变化。流散身份,即“拥有共同的流亡历史的人,他们的流散身份随着时间和地点而进行改变,这是一种流动的、会随之改变的概念”。在地缘因素之后,随着时间的演变他们会面临对身份的疑惑与纠结,对家寻觅无果的遗憾与绝望。
身份流动带来的创伤最痛之处还是“无家”,而西班牙港最不缺的就是在模仿中迷失自我的流散者。由于外界的影响,爱德华的人生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中。最开始他和博加特很像,对于美国文化有着极端的崇拜。这也与种族主义社会向有色人种灌输的白人优越论有着密切关系,内化的种族主义应运而生。爱德华自我安慰道:“我的作品送给特立尼达人去评头论足,他们懂什么?美国人才算是人,才是真正在行的人呢。”战争爆发后美国大兵进入了米格尔街,爱德华操着地道的美国腔,在外形上也彻底模仿美国的时髦。爱德华是米格尔街上部分人的缩影,在他们眼中特立尼达混沌不堪,相反美国是天堂般的存在。抨击同类也许就是在寻求某种优越,“身份的高尚感”。街上的人对于他“成功地”模仿美国人确实存在一种羡慕的情绪,“我想,也许是我们都在妒忌他。”爱德华因被殖民者的地位、文化决定了以模仿攀附来获取身份认同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最后只能归于迷惘与流亡。学者王岳川说:“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的立场的做法,其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事实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忽视自身而盲目效仿只会彻底丧失前行的方向,一生都陷入漂泊流散的迷惘孤寂之中。
生活在米格尔街的人们是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具有比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小人物更复杂的性格和命运,“边缘人的形象占据了伟大的文学的一角”。 而在这种压迫下,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由于多种交叉的环境因素塑造出自己的杂合身份。《慎重》中的博勒,偶然知道《卫报》上可以赌球,从那之后每周买很多份,却没有一次成功。“怪不得黑人过不上好日子呢”,这是米格尔街上人们常说的话,博勒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在特立尼达被骗的经历一步步压垮他。对此他选择了逃离,命运像是一直拿他开玩笑,就连想离开这个对他下了“诅咒的小岛”都是这样的难。他们对于好生活的向往与实际得到的很难适配,因为这样一个殖民主义横行的国家是灰暗的、遗世独立的。诚然,像奈保尔这样获得宝贵求学机会的人还是有的,但却是凤毛麟角。就算冲破特立尼达地域的禁锢,也难逃他者化对他们一生的折磨。因为任何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建立在种族层面上的,还有各种不同的困境一层层形成了牢固的茧房,任你挣扎也只是白费心力。
这些人物趋向于通过改变自己的穿着、口音等,来证明自己的文化归属感,来找寻自己的身份。例如博加特等,用模仿美音、赋予绰号等方式强调自己的身份特征,实际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他们也成功中了殖民者的圈套,成为殖民主体,即“那些接受了殖民者向他们灌输的观念,认为英美人是优秀人种,自己是劣等人种。”这是一本讲述弱势群体如何自欺欺人的书,因为谎言是他们唯一所拥有的。残缺的文化导致他们很难有身份认同感,过度关注外部世界和外在自我,失去了心灵的慰藉,因而只能一生都遭受漂泊的迷惘之苦,并妥协于自己流动的流散身份。
三、因文化错位而产生的“无家感”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特立尼达拥有独一无二的民俗文化,如传统的狂欢节服装,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陶器、纺织品和装饰品,低矮的木制建筑,克里普索小调和被称为“凌波(limbo)”的舞蹈等。在《米格尔街》中,奈保尔也多次提到克里普索小调。很可惜的是克里普索小调作为民俗不但没有发扬光大,还极其成功地成为街上人互相嘲讽的媒介,比如当地人用小调来传播街上令人唏嘘的八卦轶事。霍米巴巴说过“文化错位是一种政治化的转喻, 关键并不在于错位发生在何处, 而在于社会和文化中的哪些结构性的因素系统性地‘制造’着错位”,而造成特立尼达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就是殖民国家的文化侵蚀。书中也提到学校、报社、医院和监狱都受着殖民者的高度管辖。当街上人每天听的新闻、看的图书等都是殖民者渗透给你的时,恐怕没有人能挣脱这种文化囹圄。尽管个体在追寻文化归属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却还是时时刻刻遭受着文化错位带来的“无家感”。
文化混乱加剧了米格尔街上有些人近乎疯癫的行为举止和漂泊感。例如焰火师墨尔根,对他来说,通过出洋相而招来他人的嘲笑才是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身份是焰火师,可没人买他的焰火。除了做焰火实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以获得更多的存在感。事实上,大街上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是真正地快乐。当他出轨时,母老虎妻子把他拎到门外,打开门灯让全街人看到他的哀求。讽刺的是,这可能是墨尔根第一次真正把大家逗笑,完成人生的一大奢求。这一章节最后,他家燃起了一场大火。关于那次火灾有一首卡里普索小调这样唱 :“多么壮丽的景象,就是那场国库燃起的大火。”他一生最追求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制作出世界上最灿烂的烟火,另一件就是让人们笑话他,这回他都做成了。其实不难发现,米格尔街上的人总会给自己找这样那样的差事,但大部分人都做不成功。而街上多的是信口开河,捡笑话看热闹的人。一定程度上看,民俗文化之于当时的特立尼达人,不是民族瑰宝,而是调侃取乐的工具。在每个章节的最后,这些小人物都会离开米格尔街,带着生活的不如意继续漂泊游荡。
除了曼门、墨尔根和博勒这样带有疯狂思维的人,还有一部分是在尽力维护特立尼达文化的。“往昔深邃而奇妙”,这是街上的一位诗人沃兹沃斯和我交谈时说到的。沃兹沃斯的诗无人在乎,从书中母亲在他来卖诗时的粗鲁态度便可看出。只有“我”喜欢听他诉说他和一位女诗人的故事,以及知晓他在筹划一篇震惊世人的诗作,已经写了五年,还需要二十二年。沃兹沃斯每年靠唱克里普索小调的季节去献唱挣钱,平时则专注于创作诗篇。但可悲的是,最后的最后,他向时光、向命运妥协了。“往昔深邃而奇妙”,我看到他的衰败后回到家痛哭起来,像个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其实这也是一种坚守,全书中只有我获得了“成功”,离开了米格尔街前往英国留学。但坚守特立尼达文化的人其实并没有成功,没人能改变这个局面,唯有妥协以及和自己和解才是唯一答案。
历经流散自我调和都是被殖民者面临的文化困境。学术上有一种想法是杂合其实是一种对于“无家感”的积极替代。但无论怎样,被殖民者依然面临如何争取独立人格和群体身份,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机遇,摆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压迫的问题。奈保尔谈到自己的出生地时曾说过:“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他在社群中的地位而奋斗,但社群却并不存在。我们处于不同的种族、宗教、群体和集团,除了共同的居住地,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可见,奈保尔对文化维度的无家困境是持相对悲观的态度的。《米格尔街》便记叙了街上人们一心想逃离苦难,却因没有文化自信等原因无法摆脱命运束缚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四、结语
在经历地缘、身份和文化多维度流散后,特立尼达的人们最终找寻不到根,在不同的文化缝隙中失去精神寄托。奈保尔本人最初也是随着家人从查瓜纳斯到西班牙港居住,而后去往英国,再到印度,他也在经历不断的迁移与流散。细数他的一生,他每次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文学批评家查尔斯· 奥古斯汀· 圣伯夫(Charles·A·Sainte-Beuve)等人的作品中所获得的活水源头,以及孩提时代搬到西班牙港,再到后来去英国求学,多次回到印度旅行等经历,甚至是他后期所感兴趣的非洲、南美洲等,都成为填补他文学创作“世界地图”的一个个拼图。但他创作漂泊流散的主题却大多数源于他的孩提时代,也就是《米格尔街》所描述的他童年的黑暗生活。从《米格尔街》获得成功开始,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写作主题——加勒比地区流散文学。米格尔街上的人物出生在特立尼达,就是他们一生流散的开端。如果他们试图追随某个特定的文化身份,就必须搜寻自己的内心,努力重建自我,或是拥抱杂合身份才有可能实现。但可惜的是,特立尼达是殖民文化占主导的地域,大多数人可能注定在追寻中不断经历失望,最后向命运妥协,并且麻痹自己,陷入一生摆脱不掉流散身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