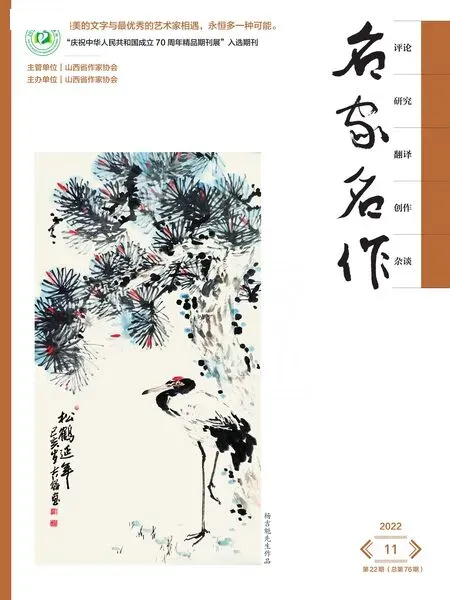文学疗救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
陆天一
一
古代小说批评中的疗救论与东周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中产生的“精气说”相关。所谓“气”,老子有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为调和万物“阴阳”的抽象媒介。《管子》认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可见“精”乃“气”之精华。“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①(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28页。,人是精神气韵与物质形体二者的结合体。
“精气说”为传统医学病理解释的基础。《内经》论述了万物之“气”与人体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②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09,第33页。邪气的侵扰会扰乱人体的“精气”,出现有损寿命的后果。人的情感活动则会破坏“精气”的平衡,导致邪气入内,“精气”失衡阻塞,则人的精神、情感出现忧郁、愤怒等状况,导致健康受损。例如,《内经》中有一段关于气愤失声的病症的探讨:“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少师答曰:‘……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少师认为咽喉、喉咙、会厌、口唇、舌、悬壅、颃颡、横骨是人体发声的器官,人的忧愤之情会导致寒气作于会厌,发声器官失效,因此“卒然无音”。至于治疗方法,岐伯提出通过针灸疏导阻塞的血脉,从而恢复肌体的正常运转,达到精气的畅通。
文学也有类似的“疏通”功能。西汉枚乘在《七发》提出了“要言妙道”之论,成为最早提出以文学疗救病人的批评家。楚太子有疾,不能见客,吴客便以文学来疏导他的情绪,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求病源。吴客以“精气说”入手,认为其病症是因为“邪气袭逆,中若结轖”而导致的“精神越渫,百病咸生”。二是开出药方。吴客认为,去除“邪气”则需要君子的“博见强识”,以“承间语事,变度易意”。三是诊治病症。吴客认为“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结果楚太子从萎靡不振到“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身体明显“有起色”。直到吴客提出“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成功激发了楚太子“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的渴望,他从病榻上“据几而起”,“涩然汗出,霍然病已”③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6页。。枚乘的“要言妙道”论认为特殊内容的文学可以起到疏导的作用,这就把文学对读者的功能与医学对患者的疗救结合起来,从而从文学文本、读者的角度启发了文学疗救论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
早期文论以疏导功能为核心建立起文学与医学的联系,正如枚乘的《七发》把文学的疏导功能指向文学的接受者,即患病的楚太子,从而发挥文学的疗救功能,使得患者病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文学疗救方面的认识有所丰富,将文学的疏导功用指向了创作者。
“发愤著书”说的重点在于,文学创作活动可以疏导、宣泄作者的负面情绪,从发生机制探析了文学的疗救功能。“发愤著书”说与传统文论中的“言志说”密切相关。《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④转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62页。文学的产生在于情志之变动,作者的多样化的情绪可以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通过疏通得到疗救。
“发愤著书”说则特别强调了“愤”的负面情绪在文学发声中得到疏通和宣泄的过程。此前,已经有不少批评家提出相关的看法,如孔子明确指出“诗可以怨”;屈原则有“发愤抒情”的创作思想。基于与屈原相似的经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①转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82页。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是作者自我疗救的结果。司马迁在孔子、屈原理论的基础上,用“抒愤”解释文学的产生,及其对于作者的疗救功能,丰富了文学疗救理论的内涵:一是从疗救功能发生的过程来看,从文学的接受转向文学的生产;二是从文学疗救的对象来看,从患者指向作者;三是从疏导的具体内容来看,从患者病理上的邪气转向作者的郁愤情绪,从而把文学表现情感的本质与医学对肌体的治疗联系起来。此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也有类似的基础。
如果将“文学疗救”的语义从医学扩展开去,着眼于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么“文学疗救”可开展的对象另有社会、家国、民众等。传统儒家思想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这孕育了文学疗救论的另一方面——救助民众和推动社会变迁。一是《毛诗》多以“刺时”“刺世”等语解诗,把“刺”的对象指向“时”“世”,显然扩大了文学疗救的对象。例如,毛诗释《唐风·鸨羽》“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②(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唐) 陆德明音释,朱杰人、 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560,236页。;《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③(汉) 毛亨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唐) 陆德明音释,朱杰人、 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560,236页。。东汉赵壹将怨刺传统引入辞赋,作《刺世疾邪赋》。“刺时”或“刺世”在此后的文论批评中多有出现。二是“文以明道”论的兴起,较为明确地把文学疗救指向时代和社会。柳宗元处于安史之乱后衰颓疲惫的中唐,用世之心强烈,故而提出“文以明道”论,强调以诗文救治社会。“文以明道”论的“救世”之意是非常显见的。变风—刺世—救世的发展路线体现儒家学说中文学社会功用的上升。文学去除了政治的媒介,直接影响社会。其中隐含着文学地位的上升,对社会“疗救”也由“可能性”成为现实的可实施性。
三
传统文论中的疗救思想主要针对诗文。明清时期,随着小说的繁荣,批评家也汲取疗救论的思想,把“要言妙道”扩大至小说,这不但有益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同时也丰富了古代小说批评理论。
从接受者而言,文学疗救论的核心在于疏导病体阻塞的精气。古代小说批评受此影响,认为小说谈笑解颐,可以发愤纾解,疏导病体之郁愤之气,恢复健康。这一看法源于古代小说地位不高,被视为“丛残小语”“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④(汉)班固:《汉书 中》,中华书局,2005,第1377页。的娱乐性。如《搜神记序》记述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使“将来好事之士”“游心寓目而无尤”⑤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这里明确强调小说对于读者放松身心、消除负面情绪的作用。读者汤显祖阅读小说的感受是这样的:“《虞初志》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皆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口张眉舞。”⑥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明清小说批评中亦有类似评语,例如谢肇淛认为《金瓶梅》“穷极境象,駴意快心”⑦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令读者身心放松。
古代小说批评家对文学的疗救功能理解得更为具体深刻。首先,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所能治愈的病症归结为心理疾病。例如,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有关于忧郁致病的论述:“人有七情,忧郁为甚。……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⑧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心理抑郁可以导致各种心理病症。其次,小说批评家对小说疗救病症的功能更加清晰。一是可以宣泄情感。如前文欣欣子所言。二是可以涤荡烦思。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谈到小说“真足令人燥思顿清、烦襟尽涤”⑨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最后,小说批评家明确了小说的疗救作用,认为小说可以治愈病症。例如,李汝珍《镜花缘》:“其友方抱幽忧之疾,读之而解颐,而喷饭,宿疾顿愈。”⑩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闲斋老人《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评吴敬梓笔法:“文章至此篇,可谓极尽险怪之致矣。长夏摊饭时读之,可以睡醒,可以愈病。”⑪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变化多端的故事,令人“喷饭”“解颐”,各种病症自然痊愈。
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相联系,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也可以治疗作者,起到与诗文相同的作用。例如,《忠义水浒传序》以《水浒传》替代《史记》:“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⑫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25,184,204,235,387,548,523,225 页。除了小说批评家的理论总结,小说家们也亲身试法,以示小说抒愤之功效。例如,蒲松龄指出《聊斋志异》就是自己抒发悲愤之情的结果:“……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①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406,235,137页。无论是“解颐”,还是“抒愤”,小说对于接受者和创作者都有益于宣泄情感、涤荡愁思,犹如药丸疏散郁积的精气,达到疗救的效果。
四
明初,小说的“救世”功能已经得到批评家的认可,瞿佑于《剪灯新话序》自云:“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②转录自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下》,齐鲁书社, 1990,第956页。”作为“史馀”“补史”的小说具有“劝善惩恶”“裨补风教”功能。
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有助风教,从而疗救社会,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谈到该书“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③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406,235,137页。。袁宏道于《与董思白》中认为:“《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④转录自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山书社, 1986,第170页。枚乘在《七发》中用吴客之言来治疗病症,最终楚太子痊愈。袁宏道则认为《金瓶梅》胜过《七发》,那么从文学疗救而言,《金瓶梅》叙事精彩,“云霞满纸”,正如“要言妙道”,这对小说群体可以起到疗救病症的作用。
小说对社会群体的疗救主要有两种。一是劝惩,主要是将小说比拟为承载劝惩功用的汤剂,类于“保健品”,即前文所云“裨补风教”,往往指文学的教育功用。例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如此论述:“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诊,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⑤转录自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第406,235,137页。这将稗官小说比作牛溲、马勃两种常见中药,其本意指小说犹如良药,治愈群众的病症,从而“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二是救弊,主要是将文学比拟为承载救弊功用的药石针灸,即救治重病的“猛药”,以正人心,扭转世病,即所谓“针砭”,往往指文学的讽刺与揭露时弊的功用,如华阳散人所作拟话本小说《鸳鸯针》。《鸳鸯针》自序道:“医王话国,先工针砭,后理汤剂。迨针砭失传,汤剂始得自专为功。然汤剂灌输肺腑,针砭攻刺膏肓。世未有不知膏肓之愈于肺腑也。世人黑海狂澜,滔天障日,总泛滥名利二关。”这就道出本书为针砭世事所用。再若黄小田《儒林外史序》“然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⑥(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688页。,亦以“救世”为关门,认为该书以图救治世事人心。从“世”到“名士”的范围不同,可见批评者对作者针对的集体心理原型认知有不同。但二者均指向对群体心理、社会问题而非个人心理的疗救。
近代“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观也强调小说对群体的疗救作用。梁启超期许的疗救效果是单个读者受到小说的感染,最终存在群体性的治疗效果,达到开国民心智的目的。
结语
南宋曾慥《类说》把小说的功能归纳为“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四种⑦(宋)曾糙:《类说序》,转录自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3页。。从疗救论来看,这些都是对作者、读者以及群体和社会的救助。古代小说批评家从传统文论中获取养料,与古代医学相联系,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小说疗救思想。
近现代以来,西方现代派兴起了精神分析学派,这种思想把宣泄应用于临床医疗,是中国古代小说疗救思想的实际应用。精神分析学认为,感情的郁积容易产生病症,而宣泄感情可以使病人得到救治。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下写出《苦闷的象征》一书,该书将精神分析引入文论,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⑧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 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第223页。。然而放眼于中国古代文论,未经西方精神分析学派导引时确已存在“文学治疗”观念,并且在医学、文学两门中均有出现。可惜现有论文论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治疗观”时,往往与现代的精神分析相对应,未见古代文论的“文学疗救”论于千年前早已成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