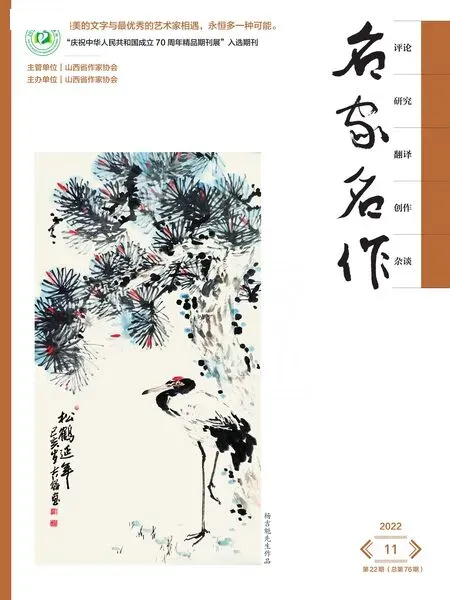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面纱》与《寒夜》中疾病叙事研究
李俊宇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世界文学日益发展为多元文学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世界文学中曾出现的有关疾病的叙述重新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如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面纱》以及巴金的小说《寒夜》都有对民国时期西南地区霍乱、肺结核等疾病的叙述。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探寻其“同”和“异”,即东西方两位作家是如何对相同类型的叙事进行处理的,如何探寻个体与共同体的结合方式,以及我们怎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一、个体与共同体:《面纱》中的疾病叙事
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9年冬启程前往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奉天、成都和香港等地。在这个几年前推翻了帝制的东方国家,一边是军阀割据下混乱、落后的市井生活,另一边是壮观的城墙、神秘的庙宇以及闲适优美的乡村景致。中国之行让毛姆收获了一部游记《在中国屏风上》,一出戏剧《苏伊士之东》以及一部精致的小说《面纱》。
在《面纱》中小说的主人公沃尔特将与他人通奸的妻子带到了霍乱肆虐的贵州湄潭府,沃尔特在当地的医院医治病人。小说中出现的瘟疫横行的地方是贵州的湄谭府,根据周振鹤 、傅林祥 、郑宝恒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1914年湄谭府隶属于黔中道[1]。然而根据1919年北洋政府公报中所列出的出现霍乱的地方为廊坊、沙河、天津、营口、沈阳、福州、厦门、上海、无锡、苏州、安庆、哈尔滨、齐齐哈尔、郑州、开封等地[2],并没有提及贵州的任何地方。另据《民国时期贵州传染病初探》一文中的研究指出,1919年贵州并未出现霍乱的大规模流行[3]。这点也可以在民国两大报刊《申报》和《大公报》的新闻中得到印证。
基于上述对社会共同体的重构,毛姆为什么会选择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作为文本的背景,将此问题搁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视阈下,首先需要了解历史上霍乱的七次世界性大流行,根据流行病学霍乱全球流行史1899—1923年为第六次霍乱全球大流行。在 Sovereignty and Imperial Hygiene:Japan and the 1919 Cholera in East Asia 一文中提到1919年霍乱的爆发横扫了中国、日本、泰国、印度、阿富汗、俄国和瑞士;其次在霍乱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也不可幸免遭受了冲击,东亚疫病最开始是由菲律宾传播到中国的两个港口汕头和福州,并肆掠了日本、中国、朝鲜半岛、上海、香港和满洲里。[4]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下,“流行病学的东方主义”(Epidemiological Orientalism )由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其意旨在于制造欧洲的瘟疫都是来自东方的文化背景。霍乱由此成为维系东方主义的方式之一,其核心概念是北非、中东和亚洲的社会一直处于异质的、落后的、迷信的以及专制的状态。在19世纪欧洲人的观念中,“流行病学的东方主义”有着双重目的,一方面它有助于凸显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将欧洲塑造为一个没有瘟疫的文明社会;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欧洲将公共卫生政策合法化,并有益于采用科学技术来控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因此,在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的医疗卫生状况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社会的风俗习惯与疾病控制紧密相连,公共健康和卫生作为公共资源而被推崇[5]。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彰显着“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病态”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东方被描述为瘟疫滋生的温床,而且政府无力控制其蔓延,在霍乱还未传播至欧洲之时,霍乱与肮脏环境的关系便取代了霍乱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肮脏的环境代表着贫困,其不仅预示着霍乱所带来的痛苦,更是引起霍乱的原因[6]。因此,在早期的旅行文学中常见的东方体裁包括:狭窄、弯曲的街道,被掩埋的瘟疫感染者,民众对瘟疫的无知,不注意个人卫生等。在《面纱》中出现了 “中国城镇肮脏不堪”“街道垃圾堆积如山”“从垃圾堆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等描述。由此毛姆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贵州湄谭府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下用以满足西方对东方形象的集体想象,同时将其笔下的东方形象与西方相对照,使毛姆得以冷静而严厉地观察散居在中国各地的英国人士和团体,这些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臣民,远离本土,远离英国社会的道德禁忌,他们各种隐藏的私欲和邪念也表现得更加放纵、露骨。
二、个体与共同体:《寒夜》中的疾病叙事
巴金的小说《寒夜》完成于1946年冬天的重庆,小说中的情节发生在1944年至1945年这一年的时间中,在《寒夜》中主人公文宣的同事钟老因患霍乱而死去,对于文宣来说,霍乱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这里所说的“麻脚瘟”是四川地区人民对霍乱的俗称。民国时期重庆霍乱的流行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难民的涌入,相较于和平时期,战争时期的难民所包含的范围无疑更广,再加上难民是瘟疫的易感人群,因此1939 年 4 月底伴随着侵华日军陆空的联合袭击,霍乱开始在重庆蔓延。
重庆自1939年霍乱后,截止 1944年再未出现过较大的霍乱疫情。1945 年四川省霍乱爆发后,重庆首当其冲,重庆的霍乱传染始于1945年6月3日,这可从《申报》1945年7月15日的两篇报道:“成都虎疫猖獗”以及“渝蓉虎疫蔓延”中得到印证。[7]
巴金亲历了1945年重庆霍乱疫情的爆发,除了在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中得到证实以外,在1946年《第四病室》的小引中巴金回复陆怀民的信中写道:
收到你的“日记”的时候(它在路上走了四个月),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副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今天在人死了数百(至少有数百罢)而局长也居然“发现”了霍乱之后,我还看见苍蝇叮着的剖开的西瓜一块一块摆在街头摊上引诱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车站旁边人们大声叫卖冰糕,咖啡店中干净的桌子上,客人安闲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倾在泗瓜水杯子里,无怪乎盟国的使节也染到了虎疫。[8]
这次霍乱的爆发在巴金心中烙下了印迹,同期创作的《寒夜》中有三次提及霍乱,第一次出现在文宣的妻子树生离他而去,文宣自己深感生命受到肺病威胁而拼命想活下去时,文宣家对面裁缝店里的人害霍乱而死;第二次出现是文宣的同事钟老因患霍乱而被送进了医院,文宣梦到钟老死去,于第二天上班时知晓钟老过世的消息时,文宣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第三次出现在文宣生命要走到尽头之时,隔壁人家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文宣想起自己如果死了,母亲会不会痛哭。
在《寒夜》中除了霍乱以外,主人公文宣还患有肺病,文宣自身的懦弱,青年时代理想的幻灭,凡此种种。肺病慢慢地消耗着文宣的生命,而每当文宣身心受到肺病侵蚀时,他便听到有人患霍乱而死去的消息,通过疾病叙事使疾病对主人公及周围人的影响跃然纸上。疾病使文宣变得脆弱,并无法控制外部所发生的事件,他的生活习惯、期望以及个人能力都受到疾病的侵蚀,文宣生命的连续性被打破,这更加深了文宣心中各种不安的情感,疾病带来的死亡深化了巴金文本中家的主题,通过家庭关系的冲突来表现社会问题。战争和疾病使文宣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也无法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这与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出的个体对封建家庭和社会制度的抗争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窥见巴金所处的社会共同体的变迁。
时代造就他,同时也损毁他。一百年间,他在不断蜕变,化蛹成蝶。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系列悖论的发生: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主义者;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社会批判家、政论家到小说家;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国家领导人;从大家族的叛逆者到家族的大家长和保护人。他一面努力抵制这种变化,另一面又顺应这种变化,他本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挣扎”。直到晚年,他仍然在痛苦的挣扎。[9]
文宣被夹在代表着传统家庭观念的母亲与代表着现代新女性观念的妻子之间,因此文宣代表了生活在民国时期小人物的遭遇。而肺结核在巴金小说中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巴金的第一部小说,即发表于1929年的《灭亡》,巴金曾经因为肺病的缘故,而放弃了报考北京大学,肺病对于巴金来说,更可谓是一种心理上的顽疾,伴随他终身而阴魂不散。因此,他以诚实的笔触刻画了杜大心这一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肺病的痛苦以及在寻求社会解放道路上的苦闷和抗争。其后便是出现在《雨》中的陈真、熊智君,《家》中的梅芬、剑云,《秋》中的周枚等因肺病而发烧、咳血的悲惨结局,由此可见疾病叙事在巴金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从《面纱》与《寒夜》中的疾病叙事,可纵观民国时期(1912—1949)的公共卫生现代化进程,国民党政府进行医学现代化改造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持续性的实现,而且将医学现代化与加强政府统治、民族强盛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医学现代化不仅是对人民进行健康管理的手段,更是政治立法、民族强盛的工具以及国家现代化的标志。[10]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重构,1919年的毛姆选择贵州湄潭府作为瘟疫之地以满足西方对东方形象的集体想象,具有“流行病学的东方主义”的倾向。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陌生化的环境中,用东方感悟式的语境与西方存在式的叙事相融合,以达到揭开面纱让凯蒂重新认识自己和丈夫沃尔特的目的。而1945年的巴金经历了重庆霍乱的爆发,加之战争带来的贫困和伤痛,疾病便同故事的主题一道勾勒了一幅冬夜清冷的画面。文宣则代表了生活在民国时期普通个体的遭遇,每当文宣身心受到肺病侵蚀时,他便听到有人患霍乱而死去的消息,疾病使文宣变得脆弱,并无法控制外部所发生的事件,文宣生命的连续性被打破,这更加深了文宣心中各种不安的情感,疾病叙事深化了巴金作品中家的主题,通过家庭个体关系的冲突来表现社会共同体问题。
虽然《面纱》和《寒夜》中的疾病叙事发挥着不同的审美功效,东西方两位作家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建构采用了不同的视角,通过民国时期东西方作家对疾病的描写,不难看出当人类面临疾病的威胁时,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只有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平等的整体,抛弃共同体中的排他性、对立性,甚至是殖民性的思维,才能找到个体与共同体最佳的结合方式,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