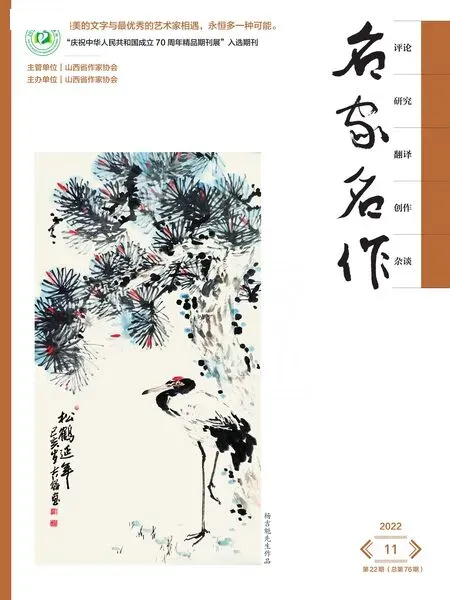自我的解构与异化
——《解剖课》的存在主义书写
汤艳娟
菲利普·罗斯(1933—2018)是美国当代最有名的犹太作家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写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小说,获得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美国几乎所有的文学奖项,一度被称为美国文坛的“活神话”。《解剖课》是“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第三部。故事的主人公内森·祖克曼在历经成名、父母双亡、妻子和情人相继离开后,患上了不知名的疾病,全身疼痛不已,医生们诊断治疗之后仍然毫无起色,并怀疑该疼痛是祖克曼由于内疚而臆想出来的。
有学者认为《人性的污秽》从人物形象到情节设计,从叙事手法到语言措辞,都与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全方位地相呼应。细读《解剖课》之后,会发现萨特的两大核心理念“存在是虚无的”和“他人即是地狱”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祖克曼和他周边的女性在荒诞的现代社会中,承受着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疼痛,以一种自我解构和自我放纵的方式活着,感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一、自我的解构
罗斯在《解剖课》中,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通过祖克曼给读者展现了一种人生百态的社会面貌。解剖课不只是医学院的必修课,还是罗斯解剖现代人的示范课。在他的笔下,作家、医生和各式各样的女性纷纷展露自己的本性,以一种近乎真实的虚构来证明存在主义的思想是多么合理。
内森·祖克曼在凭借《卡诺夫斯基》一书出名后,收获了大量的金钱和知名度,但在这本以揭露犹太民族一些恶习和弊端的小说里,人们把祖克曼等同于卡诺夫斯基,并把故事的情节自然地看成是祖克曼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人们对他和家人指指点点,母亲受到恐吓威胁,父亲在临死前骂他“杂种”后含恨而终。母亲最终也由于癌症离开了人世,弟弟一家与他断绝了来往。自此,祖克曼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对于作家的孤独,祖克曼甘之如饴。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只有孤身一人,才能像一个狂热症患者一样,创作出具有“吞没和净化生活”[1]的文学作品。孤独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虚无。自我的放逐是孤独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孤独的存在,痛苦如影随形。
通读全文,整本书都充斥着“痛苦”。“每次写字,他都咬紧牙关,面露痛苦之色。”他四处求医,整骨专家、神经病学专家、风湿病学专家,甚至是生发专家、枕头推销员、昂贵的淋浴头,都被他寄予厚望。尝试过各种治疗和理疗无果后,祖克曼转向照顾他的女人和作为止痛药的大麻寻求缓解。矛盾的是,祖克曼被这种“沿着右耳穿过脖颈底部一直延伸到上背部的针刺般的疼痛”日夜折磨,不能写作,不能休息,废人一个。医生的诊断确是查无此症,并得出结论,祖克曼的疼痛感是他臆想出来的,是因为他靠出卖家庭的故事成名而产生的负罪感。“什么病都不是。”但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是的如幽灵一般的疾病,让他失去信心、理智还有自尊。在这里,我们不难想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存在先于本质。疼痛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医生来说,此疼痛是虚无缥缈的,是主观意识导致的,是不存在的。在此矛盾前提下,祖克曼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痛苦永无休止地自我循环,吞噬着一切,只留下孤独。”
罗斯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文学创作者应予以痛苦本身应有的关注和足够的承认[2]。作家应关注疾病与痛苦对人的理性、自尊及成熟等所带来的损伤——对人的性格和性情所造成的冲击与磨损。罗斯曾说过:“当我在写作《解剖课》时,我想到了许多关于疾病和痛苦的小说”[3]。但在这里,痛苦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表象,象征着人类的生存状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而受苦。与祖克曼有什么共同点呢?普罗米修斯的痛苦是宙斯给予的惩罚,祖克曼的痛苦来自对披露犹太人的恶习而出名的意识和父母家人因此遭受骚扰和惊吓的内疚感。普罗米修斯虽然最后被寻找金苹果的赫剌克勒斯解救,但他永远都要戴着拴着石头的铁环,祖克曼永远都要被缚犹太人的责骂和失去父母的痛苦和兄弟的仇恨。
二、 自我的反抗
祸不单行,著名犹太作家和学者米尔顿·阿佩尔公开发文谴责批判祖克曼的作品,指责祖克曼的文学是伪文学,祖克曼是伪君子,这令祖克曼忍无可忍。在电话里强烈表达了对阿佩尔的不满无果后,在去芝加哥的路上,他谎称自己是阿佩尔,从事色情行业的,并创办了色情杂志。这令他的同座尴尬不已,像看疯子一样看待他。当他向女司机瑞普吹嘘自己的换妻俱乐部是如何伟大,如何顺应时代的时候,瑞普冷静而礼貌,完全没有被祖克曼的天花乱坠的吹嘘而吓到,更不用说被吸引了。甚至,在别人眼里,祖克曼就是一个疯子。“语言是疯癫最初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4]。在墓园里,弗雷塔先生对自己犹太家庭的回忆,对去世的妻子的想念,使祖克曼内心的愧疚和压抑终于爆发。他用虚弱的胳膊里仅存的力气,抓住老人的脖子,企图以此次犯罪来“终结否认 ;终结最沉重的有罪指责”。他大吼:“我们就是死人!那些坟墓里的骨头就是犹太人的生命!他们就是那些主导一切的人!”祖克曼在此刻变成了福柯笔下的狂躁症患者,在药物的作用下,疯狂起来,变得毫无理智,最终以严重受伤才从疯狂中清醒过来。
在情人们相继离开,创作灵感丧失,疼痛无法根治的情况下,祖克曼不由回想起了在芝加哥读大学期间目无一切、无所畏惧的生活,并最终下定决心重返芝加哥,攻读医学。“成为一名医生,不仅能逃离永无休止的往事追忆,同时还为了逃离从家庭纷争中提炼出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导致的一切争吵。”
“性格就是命运,然而一切皆是机会”[5]。为什么是妇产科医生?医生和作家一样,都是孤独的存在,并且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如同自己重生,拥有自己的绝对自由。同时,祖克曼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死于疾病,他的这一选择也算是赎罪。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祖克曼决定放弃父亲一直反对的写作而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医生,即使对于他这种理科差得一塌糊涂的文科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6]。产科医生接生新的生命而受到人们的感激和爱戴,作家因虚构的故事严重影响家人的生活最终终结了父亲的生命。“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照顾关心,而是自己掌控这个提供这一切的职业。”祖克曼在了解了麻醉科医生和急诊科医生的工作后,转而思考成为他们之一,甚至是整形医生。最终,他因大量服用致幻药和伏特加后,在葬满犹太人的墓地陷入了疯狂,严重受伤,成为一名医院里的病患。在医生们的努力下,祖克曼的不知名的疼痛随着新的伤痛慢慢治愈。在如同幽灵一样感知其他重病患的伤痛的过程中,作为作家的祖克曼宛如在艰难中寻找新生,与这日益衰老的躯体不屈服地作斗争,与这荒诞而排他的世界作斗争。
原始自由即原始的主观意识。自由只有通过选择才能获得,这是一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人的一生都面临各种选择,直至死亡。但是选择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的双重制约,所以不一定能实现。但萨特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本身,而不是选择的结果。个人存在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人们对自己的状况总是不满意,进而忽略现在而不断追求未来,即虚无。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犯罪导致人类的各种疾病和痛苦。世界是残酷的,人类是痛苦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存在是一种探险。每个人都是别人的他者,人们试图改变这种对立,但无法实现。
三、 自我的异化
艺术来自生活,但高于生活。在“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中,不仅仅是读者,甚至是祖克曼本人经常把艺术和生活混淆在一起,虽然祖克曼宣称“生活和艺术是截然不同的”。在这荒诞而又真实的世界里,祖克曼与初衷渐行渐远,因为写作而“自我监禁”,成为犹太人中的异类。祖克曼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的作家。他早期和其他新兴作家一样,虔诚而又纯真。把洛诺夫、阿佩尔之流当作自己精神和创作上的教父。在不断发现这些犹太人眼中的高尚作家的背后的阴暗后,在来自本民族的嫉妒和仇恨的折磨下,祖克曼变得冷漠而自私。母亲的辞世摧毁了他的最后一丝理智和善良。自此,与他人的交往不再单纯。与女性交往只是为了性,对待他人只有怒火和欺骗。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他者的世界。罗斯在接受采访中曾说过,“每个人的工作都很辛苦。——写作保护了我,让我远离更大的威胁”[7]。
祖克曼来自纽瓦克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足部疾病专家,母亲勤勤恳恳地照顾着家里,弟弟也是一名医生。在祖克曼二十岁读大学离家出走之后,在他发表第一篇作品《高等教育》之后,他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差。母亲被人们认为是卡诺夫斯基夫人,因为有一个下流无耻的儿子而经常受到骚扰和羞辱,重病的父亲最终死不瞑目,亲密无间的弟弟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四任妻子都离开了祖克曼,情人们也因无法忍受他的冷漠和枯燥的生活分手。
在祖克曼看来,婚姻只是他“保障自己不被女人分散注意力的盾牌。他结婚是为了秩序,为了亲密,为了可以依靠的同伴情谊”。在这里,爱情从来不是祖克曼考虑的内容。他需要女人,如同需要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自然。身体健康时如此,痛苦时更需要女性的陪伴和照顾。他自以为是他的财富和名气征服了这些女性,其实他只不过是她们生活的调味品。即使有爱情,也在祖克曼的疯狂和怯懦中消失殆尽。来自底层社会的雅嘉躲在祖克曼的公寓里寻求家破人亡后的短暂栖息,拥有幸福家庭的格洛丽亚在祖克曼身上寻求身体的满足,独立勇敢的珍妮尝试以纯真的爱情和鼓励治愈祖克曼的疼痛,而年轻充满活力的戴安娜充当着没字可打的秘书的职责。她们与祖克曼相互利用,共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顽强生存。祖克曼作家的身份注定他的孤独和疯狂。只有独处在一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他才能反思自我,沉淀过去,从对自己的家庭、国家、信仰等复杂的情感中书写作品和自己的命运。不愿被束缚,家庭、亲情、爱情甚至是自我都被放置一边。存在是肉体的存在,精神上的极度空虚才是最真实的存在。
在祖克曼看来,作家的终极信仰来自写作本身。“战争、毁灭、反犹主义、极权主义,承载了文化命运的文学,在动乱的中心诞生的写作”才有意义。他的无归属感、陌生感、恐惧感和孤独感与卡夫卡感同身受。“当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从他生活的世界返回自身世界,这样孤独感便成了一个必然的产物”[8]。
随着《卡诺夫斯基》的出名,祖克曼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他被患有臆想症的佩普勒跟踪威胁,被控窃取了别人的故事,甚至被敲诈勒索。在父母居住的犹太人社区,祖克曼本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卡诺夫斯基本人,而他的家人都被对号入座,被人指指点点。一度对他的作品赞赏有加的阿佩尔公开指责祖克曼为反犹太主义分子。祖克曼渴望变成一个身高六英尺的魁梧热忱的美国人,但对于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来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已经被边缘化,更不用说这样一个狂热的“书呆子”。他的满腔怒火无法通过文字宣泄,只能通过丑化自己的职业,谎称自己是一名色情杂志《立可舔》的创办者,又臆想自己是一名挽救广大妇女于无知和贫穷的换妻俱乐部的老板。他把对道貌岸然的美国和伪君子的阿佩尔的嘲弄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发狂的状态宣泄自己对这个所谓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的不满。被痛苦折磨的祖克曼如卡夫卡笔下的萨姆沙,背负着沉重的赎罪外壳,在这充满仇恨和嫉妒的世界艰难前行。他拖着这具日益衰老的躯体,面对几乎丧失殆尽的创作灵感和众叛亲离的家庭,把社会、家庭和自己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解剖自己,更解剖这个荒诞的社会。在罗斯的笔下,歌德、贝克特、萨特你来我往,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于阅读中增长见识,于思考中解读人生。
四、结语
痛苦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世界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人性是善良的,也是丑陋的。祖克曼终其一生都在逃离,逃离家庭的羁绊,对妻子们的责任,犹太民族感和使命感,逃离痛苦和折磨。在萨特看来,主体性就是主体。正是人的主体性给了我们在生活中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我们是谁或我们是什么的本质,不由社会标准决定,而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祖克曼在自我的放逐和消解中,深刻体会到存在的虚无性,在迷惘中孤独前行,于虚构中见真实,于痛苦中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