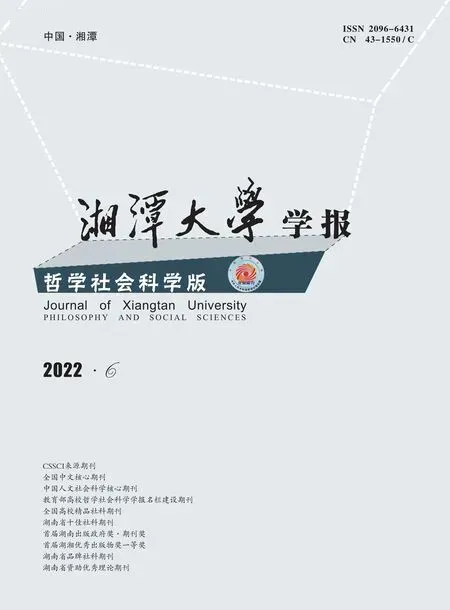希利斯·米勒文学伦理批评演进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陈 勋,王洁群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邵阳学院 文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2021,下文简称米勒)参与、见证了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从其早期的意识批评,到后来的解构主义批评,再到后期的文学述行批评,可以说其文论思想的变迁就代表了美国当代文论思潮的更迭。特别是其后期以《阅读的伦理》(TheEthicsofReading:Kant,deMan,Eliot,Trollope,James,andBenjamin, 1987)和《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VersionsofPygmalion,1991)为标志,米勒进一步凸显其隐含在早期与中期文学批评思想中的文学价值追寻,阐述其“阅读的伦理”和“写作的伦理”观,系统地从文学述行出发建构他的文学伦理批评,文学伦理批评成为其新学术思想标签。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TheConflagrationofCommunity:FictionBeforeandAfterAuschwitz,2011)以及《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inFiction,2015)等著作中,米勒继续用伦理批评方法观照文学作品,进一步彰显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关注。
学界高度评价米勒的文学伦理批评思想,认为“米勒以其独到的理论阐述和细致的文本分析开辟了美国文学伦理批评的新领域,不仅把解构主义更推进了一步,还为伦理批评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61,仔细考察米勒的文学批评思想发展历程,他从意识批评起步到解构批评再到后来的文学述行批评,都在思考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读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等文学活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将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各个因素聚合在“文学共同体”中来整体考察它们在伦理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整个伦理秩序运作的机制,人们可以发现,米勒对美国伦理批评的贡献,正是从不同角度用文学批评介入伦理问题,不断推进文学伦理批评的发展,其中贯穿着比较清晰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路径,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意识批评:寻找理想的作者
米勒在任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期间,结识了现象学批评家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米勒自述受到普莱的影响,并最后“成了现象学批评家的一种美国版本”[2]165,现象学批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识批评。米勒的意识批评理论主张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他批评生涯的前4部著作中,分别是《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CharlesDickens:TheWorldofHisNovels,1958)、《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的作家》(TheDisappearanceofGod:FiveNineteenth-CenturyWriters,1963)、《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形式》(TheFormofVictorianFiction,1968)以及《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PoetsofReality:SixTwentieth-CenturyWriters,1969)。米勒的意识批评从作者的写作出发,认为作品是作家整体意识不同面貌的展示,因此“主张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任务和目的不是理解个别文本,而是通过众多繁杂的个体作品,找出‘作者内心原初的整体’,通达作者‘单一的意识’”[3]66。在这里,米勒的文学批评看似在追求还原作者的意识,实际上已经在考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总结米勒的文学批评观念:“文学作品是作家独特、多元、矛盾的意识的表现形式,文学批评应以揭示文学作品中作家独特、多元、矛盾的意识为重心,这是米勒早期最基本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路。”[4]12米勒的这种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路在其前4部批评论著中都有体现,较早地反映出了米勒文学批评中的伦理维度。
在《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中,米勒认为文学批评方式“不仅仅是将文学作品视为某种先在心理状况的表征或产品,更是将它看作是作家用来理解甚至创造自己的方式”[5]IX。同时米勒认为:“一部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外部结构,也不仅仅是我们从外部来理解的客观叙事,同样也是作者独特个性和具体灵魂的表达。”[5]X也就是说,除了从作品的内部语言结构和外部文化语境来切入文学批评,还需要考察作者的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意识相对时代精神而言具有独立品格,另一方面是作者意识需要通过文学叙事生产出来。在这里,米勒突出了作者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米勒早期文学批评思想对作者意识的定位。他的这种批评方式“克服了西方传统的客观再现论和主观表现论各执一端的弊端,开发出了一种以作家的主观意识为依托将文学的两大核心因素即客观现实和主观心理融为一体的文学观念,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文论史的一大创举”[4]14。
在后续的《上帝的消失》和《现实的诗人》里,米勒继续完善自己的意识批评,并将之发展到新的阶段,并更进一步体现出米勒对伦理问题的思考。在米勒看来,近代以来的一些西方作家如托马斯·德·昆西、罗伯特·勃朗宁、艾米丽·勃朗特、马修·阿诺德以及曼雷·霍普金斯等人认为,在他们的时代人“和上帝之间的连线已经断裂”[6]2,上帝已经隐退,但他们无法忍受,所以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态度来在作品中重建人与上帝的联系。米勒把他们作品中的这种伦理关系称之为“原始世界场景”,并从这个总的判断出发,“具体分析了每位作家如何在自己作品中开辟与神沟通的道路,以部分回复对原始世界场景的体验”[7]前言003。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象征”,其实是个体性的作者所建立的与巨大的、神圣力量的关联。在其中,“作家经历了一种人神合一的回归:这不是启蒙时代之后那个自大的人,而是浪漫主义作家接近其理想的、与上帝融合的人”[8],他是一个大写的人、具有神性的人。在《现实的诗人》中,米勒将目光对准了20世纪的作家诸如叶芝、艾略特等人。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世界并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于是这些作家的“起点与基础从神的隐没转为神的死亡”[7]前言003。此时,上帝已不仅仅是隐退,而是死亡,米勒引用尼采定义并解释的“上帝已死”观念,认为“人类从除了自身以外的所有事物分离出了主体性,从而杀死了上帝”[9]3,而“当上帝以及上帝创造之物成为意识的客体,人就变成了虚无主义者”[9]3,而人的自我主体性(ego)质疑外部的一切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力定义了一切。米勒认为要逃离虚无,就要像《现实的诗人》中所说的6位作家那样,“思想必须要在现实中抹去自我,或者将之潜入到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中,将自己分散到一个超越而不是人造的世界中”[9]8。此时,米勒修正并发展了自己的意识批评,认为人类的主体性应该整体融入外部世界,与那个“超越”的世界融为一体,作者的创作不是简单的自我意识的客观显现,而是其与世界特殊关系的体认与表征。
米勒早期的意识批评,对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以及人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进行了探索和思考。“米勒梳理了19世纪中叶及20世纪初作家的两类不同的整体意识,从狄更斯到康拉德,从浪漫主义到虚无主义,米勒对主观主义的消极性进行了意识批评的反思”[8]133。这一时期,米勒对文学活动过程中的叙事者进行了仔细考察,进行了仔细考察,认为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也是其意识的产物。人类应该保持清醒,过度强调人的主体性,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因此作者应该在作品中尽量抹去自我,将自己分散到一个超越的外部世界中去,并由此限制人类的无限膨胀。他的意识批评实践,开展了一种对话式的文学批评,给作者设定了理想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是给作者做了较为平衡的伦理安排,体现了米勒对于叙事伦理的独特看法,为米勒后期的更为系统和清晰的文学伦理批评做了铺垫,与其阅读伦理思想遥相呼应,贯穿于其中的是米勒相对平衡而理智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解构批评:解放多维意义世界
虽然米勒的意识批评突破了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等外部研究视域,深化了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等开辟的内部研究,但“忽略了对作家意识和作品意识得以构成的一个关键性的层面即文学结构和文学构造模式的深入探讨”[4]42。所以在接触德里达以后,米勒选择转换批评方式,成为解构批评的实践者,并且最终成为解构批评阵营中最重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
在米勒看来:“解构主义批评的基础是,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实在,因此,文本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者是意义不确定的。”[7]前言005如果说米勒的意识批评是在给作者定位,那么到解构主义批评中,米勒的重点就是要给文学语言和文学文本定位。虽然解构批评的基础就是将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悬置,通过考察语言符号能指的滑移,观察其中的语义延异,从而解构语义阐释的唯一性。像德里达一样,米勒的解构批评挑战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而文学批评也并非单义性的独占式解读,“揭示了经典作品的丰富多样的内涵和意义,和解读文学作品的无穷可能性与潜在多样性”[7]前言011,解放了文学意义的多维性。他这种激进的文学观引发了传统文学批评界的强烈批评,一些批评家比如艾布拉姆斯和韦恩·布思,都认为他的理论使得文学脱离了历史和社会。为此,米勒辩解道,“解构主义强调文本的解读,恰恰是注重对这种抽象的研究,本质上并没有脱离物质基础,因而也没有脱离社会现实”[10]7,同时,他也否认解构批评脱离历史,“解构主义者在分析具体文学作品时,无一不把作品置于具体历史时间中来考察,因为强调每一次阅读行为的特定时刻,正是与整个阅读行为(包括本人过去的阅读和他人的阅读)相对而言的”[10]7。米勒的这些争辩,表明他所理解的解构批评,其实乃是一种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的独特关系,一种解放性的阅读、批评伦理。
事实上,米勒的解构批评虽然赋予语言和文本一定的自我运作权力,但是米勒同时还利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从另外角度阐明文本与历史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米勒在第二篇《史蒂文斯的岩石与作为治疗的批评》中,较为详细地论述到文本间性理论对文学意义生产的作用,他指出“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反过来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10]5,文本的意义就在文本和文本的“中间”得到实现,同时,文本意义的产生也一定程度受到了传统的约束,“历史的传统像密码似的编进了文本之内,或者说陷进了文本的囚牢”[10]5,因此,要想揭开文本的秘密,也要掌握历史传统这个密码,这就意味着文本意义的生产是受到“历史传统”约束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解构主义批评并没有脱离社会更没有脱离历史。米勒其实就是从伦理的角度介入文学批评,即用一种伦理规范将文学、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并置在一起,从而使得文本的自我赋权不至于使文学成为脱缰的野马,任何关于文学的阐释,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
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1977)一文中,将“单义性解读”和“解构主义”解读等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形象地形容为食客与食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两种方法都是‘坐在食物旁边’的同桌食客,是主人兼客人,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这是一种三角关系,并非两极的对立”[10]102-103,同时“两种解读共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被一种相互负有义务,馈赠物或食品分发和馈赠物或食品接受的奇特关系制约”[10]103,一个文本意义的产生,不仅仅是文本自身语言所指涉的意义,它还受到不同批评方式的影响。在文章中,米勒继续批评那种认为“解构批评”是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解构批评旨在抵制批评的笼统化……它要超越虚无主义,不断向前运动”[10]132。文本不可完全把握,其意义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文本意义在各种不同批评模式的相互关系以及文本间性中产生。因此,米勒进一步提出“如果生活行为中包含的事情会依次地做出其他事情,那么它们就具有伦理性”[11]237,由此开始正式提出他的文学伦理批评思想。同时,米勒认为阅读也是“生活行为”的一部分,阅读也能促成其他事情的发生,阅读也同样具有伦理性。于是在1987年,米勒将其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韦勒克图书馆讲座论文编辑成《阅读的伦理》,进一步自觉建构他的文学伦理批评。
解构主义批评属于后现代主义批评最为声势浩大的流派,“这种解构主义思想蕴含着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传统思想模式、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巨大破坏力量”[7]前言007。但另一方面,就犹如哈尔·福斯特所总结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一种是抵抗的、有抱负的,另一种则是反动的、好玩的[12]129。当时的情境就是西方世界传统文科的整体衰退,米勒认为这或许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更大的政治变迁,但文学和文学批评依然能够对社会发挥作用。因此,米勒认为解构批评虽然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但依然是一种有抱负的文学批评。他说:“文学是一种公共制度,置于它周围的整个文化中。文学的权威性来自其社会功能。它的效用是由它的使用者赋予的,由那些给它价值的记者、批评家赋予的。”[13]147在这里,米勒实际上还是认为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拥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就如其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解构主义学者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并没有脱离历史和政治,而他自己在《阅读的伦理》以及《文学作为行动》等著作中都表达了对于类似问题的关注[14]51。而对于解构主义者的历史贡献,就犹如丹尼尔·斯瓦茨(Daniel R.Schwarz)在《人文主义遗产》(TheHumanisticHeritage:FromJamestoHillisMiller,1986)中所说的那样:“即使我们抵制将批评家的思想凌驾于作者之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为文学批评增加了重要的概念,并成为重要催化因素,帮助传统批评定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15]265的确如此,米勒的解构批评,实际上已经跳出了语言学意义上的解构主义,他在试图纠正当时存在的批评笼统化倾向,暗含在尊重社会历史规范的同时促进文学阐释走向多维解放的思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米勒来说,文学的修辞性阅读绝不是阅读的根本目标,文学研究的伦理责任才是文学行为的目的所在”[16]导读Ⅶ。可以说,米勒的解构批评,同样饱含着伦理诉求,它旨在让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既得到解放又不失责任,让文本中的意义既多维敞开但又不至于散漫无度,而这也正是米勒的人文主义底色。
三、述行批评:意义在言语行为中实现
虽然米勒认为解构批评并没有脱离历史和政治,但人们对解构主义的质疑并没有终止,尤其是保罗·德曼事件被披露以后,解构批评更是被猛烈批评,其受到的挑战依然是“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指责解构批评的虚无色彩以及漠视政治、社会、历史的倾向”[17]XIV。在这样的背景下,米勒“晚近的发展:明显地表露出对于伦理的关切,以及透过德希达(德里达,引者注)等人的中介,乞灵于言语行动理论”[17]XIV。米勒也承认,美国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跨国性,而各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欧陆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纷纷涌入美国,使得美国的文学研究机构成了“自我分裂之屋”[18]3。米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系统探讨文学中的伦理问题。米勒在《阅读的伦理》中,“将解构主义与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形成写作和阅读伦理述行观”[3]66。而《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则体现了他对“叙事的伦理”的考察。这两种“伦理”考察,既与前期意识批评中对作者地位的界定形成一种呼应,又表明他已经挣脱解构批评的束缚,进入文学言语行为伦理批评范式,开始强调文学与日常言语一样具有行事能力,能够产生述行效应。
朱利安·沃尔夫雷(Julian Wolfreys)在编辑《希利斯·米勒读本》(TheJ.HillisMillerReader, 2005)时将《阅读的伦理》和《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中有关阅读和叙事伦理的核心章节编入,整合成“阅读的伦理”一个版块,王逢振等主编的《J.希利斯·米勒文集》沿用这一思路,得到了米勒本人的认可。这说明米勒的文学伦理批评已经开始全面考察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同时学界也开始有意识地将米勒的文学伦理批评进行整体呈现。米勒在《阅读的启示:康德》一文中指出“我的兴趣不在于伦理,而在于阅读伦理,以及阅读的伦理性与讲述、讲故事和叙事之间的联系”[18]24。米勒的文学伦理批评从意识批评注重作者,到解构批评关注文本,再到关注作者、文本以及阅读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了其文学伦理批评的演进,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闭环。
米勒为了寻找阅读伦理,将阅读文本扩展到诗歌、哲学、政治文本甚至是文学批评文本,将文本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以及阅读者的伦理选择进行类比,从而考察文本中人物的伦理行为与文本外读者的伦理行为是否一致[19]2。之所以要考察这一问题,是因为美国文学研究理论背景的国际化趋势已经遭到诸多非议,而米勒认为“对于将这些新发展事先诅咒为不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或者非美国的看法是否基于对它的理解,还是真的超越了它们所提出的挑战,或仅仅是个掩盖或压抑,只能通过对每一种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方能得出结论”[18]6,正是为了厘清这些问题,米勒对文学这种虚拟现实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考察,一方面论证虚拟现实中的伦理行为是否会外溢至真实社会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伦理考察,将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冲突或者禁忌置于文学之中,进行一种想象性体认与协调。
米勒在《阅读的伦理》一书中说:“即使他们的关系既不对称,也不和谐,但是伦理和叙事却不可分割。”[19]2在2005年出版的《文学作为行动:亨利·詹姆斯的言语行为》一书中,米勒将作者的创作看成是一种用语言“唤醒幽灵”(raise a ghost)的行动,而所有的故事都只不过是一种有关于幽灵复活的故事,当然这种幽灵复活并不仅仅是死去之人的重生,它还可指未来之人的提前到来,其实质还是皮格马利翁故事的翻版[20]20。米勒继续指出,谁“唤醒幽灵”就必须要为他的行为负责,“准确地说,这种责任体现在谁唤醒了幽灵,谁就要满足幽灵对他的要求。正如哈姆雷特的父亲要求哈姆雷特给他复仇那样”[21]18,作者的创作实现了幽灵复活的第一步,叙事和伦理也由此实现了连接。
在《文学死了吗》(OnLiterature,2002)一书中,米勒将读者的阅读作为唤醒幽灵的最后一个环节。米勒认为,“他们体现在书架上所有这些书页中的词句里,当书从架上取下被阅读时,这鬼魂就又被呼唤了出来”[13]47。只有在读者阅读的时候,幽灵复活的最后一步得以实现,文学也才真正实现了用言语做事。这是米勒对其早期意识批评的一种发展和完善,他在此进一步论证了作者创造的虚拟现实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述行式的重构,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性协调。
在文学述行理论的推动下,米勒在其中后期的《新的开端:文学和批评中的述行地志学》(NewStarts:PerformativeTopographiesinLiteratureandCriticism, 1993)、《地形学》(Topographies, 1995,又译地志学)、《纪念德里达》(ForDerrida,2009)以及《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和《小说中的共同体》等系列著作中,继续进行更为深入的文学伦理批评探索。这一批著作以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从文学阅读伦理、叙事伦理、地志伦理、政治伦理等多个方面对文学伦理批评进行了拓展。
在《新的开端》(繁体中文版译为《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1996)中,米勒对地志伦理进行了思考,他关注的问题是:“在诗歌或小说中的风景描述有何作用?这种描述如何对读者产生伦理的要求,或迫使他担负伦理的义务?”[17]Ⅶ通过细致地分析史蒂文斯诗歌中的风景意象,米勒认为诗歌中的地形学同样牵涉到言语行为、伦理义务等问题。他发现其中的“拟人”与伦理问题密切相关,“鉴于任何地形地貌的呈现都会运用到拟人手法,而拟人又牵涉到伦理责任问题,于是米勒通过一系列的解读,阐释了他的地志伦理思想”[11]251,拟人手法的运用,实质上是言语行为的体现,可以看出米勒即使在阐释文学中的地理、风景,其关注的依然是地形地貌与人类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以及《小说中的共同体》等著作中,米勒“开始涉足一些更具政治历史意味的题材,尝试在政治伦理领域说明作为语言动物的人如何应用语言这件并不称手的工具”[22]63,即使语言作为一种不称手的工具,但是文学依然是见证奥斯维辛的有力方式。米勒认为“文学本身成为见证,特别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逝去的超过六百万的生命,并由此指引我们从记忆走向行动”[23]前言4。用文学见证、记忆并走向行动,这是米勒文学伦理批评的核心要义,体现了他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有学者认为对于米勒而言,“《小说中的共同体》就是这样一部饱含着伦理诉求的批评实例”[16]导读Ⅶ。这一时期的米勒强调,文学有一种介入现实社会的作用,“一部小说、一首诗或一个戏剧,就是一种证言”[13]59。在《共同体的焚毁》中,米勒认为那些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见证”文学“是通过语言传达的一个人在极端环境中的极端经验,这种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只能通过语言才能得到生动表达”[24]117-125,因此,它们就不仅仅见证了奥斯维辛,历史上任何其他灾变都有可能通过文学作品来见证,这些作品在保留那些即将走向死亡的记忆的同时抵制了遗忘。米勒通过言语行为发现了文学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行动伦理,这种行动伦理关涉文学对于人类文明崩解的见证,也关涉文学通过以言行事来抵制人类对于灾变的遗忘,由此可以看出米勒对于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关切。
在文学述行批评上,米勒的贡献在于他证明了文学叙事这种虚构语言及文学共同体的有效性,它们都是述行的,都会产生相应的言语效应。在米勒看来,阅读伦理的实现,是通过文学言语行为得到保障的。同时,文学活动作为整体也具有述行性,米勒认为作者、文本和读者在复杂的文学活动中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它可能难以言明,甚至无形,但它依然紧密联合文学活动各方促成文学意义的实现,而且基于文学与历史、政治的关系,文学共同体也因此必须与这些社会因素产生紧密联系,所以,不仅在文学共同体内部,在其与这些外部因素的联系中,文学创作、阅读、批评等活动,它们都需要具备必要且适宜的伦理规范,其中可以见出米勒文学伦理批评的人文主义精神。
结语
米勒在早期意识批评中认为要通过找到“作者内心原初的整体”从而通达作者“单一的意识”;进入解构批评后,他否定作者的绝对权威,质疑文本的单一意义;再到言语行为批评阶段,他“将解构主义与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形成写作与阅读伦理述行观”[3]66,他的文学伦理批评呈现出不断发展、深化和系统化的建构过程,其关注的重点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不断探索文学活动的伦理规则。其关注的对象虽然不断转移,所依托的批评方法也不断转换,但他“不仅没有忽视社会意识形态与人文责任,反而是一种自觉承担伦理诉求的‘作为治疗的批评’”[22]58。可以说,他的整个文学批评生涯都在寻找真与善,贯穿在其文学伦理批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其最为鲜明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