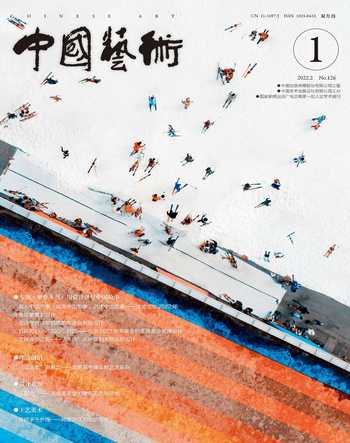理何求于外饰
韩倩
摘要:兩宋陶瓷品类繁多,面貌丰富,在三百余年的发展中,逐步确立了清隽典雅的时代风貌。领导审美潮流的是官窑器和民窑的供御器,它们洗尽绮罗香泽,直抵优雅清纯。那时,同官府、宫廷联系越多,陶瓷的造型就越单纯古雅,装饰就越平和简素。两宋宫廷用瓷的取舍揭示了风尚的演变,玉成为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陶瓷艺术典型,展现了旷绝古今的时代风貌。
关键词:两宋 宫廷用瓷 清隽典雅
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者,不得臣庶用,故云秘。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迺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南宋 顾文荐 《负暄杂录》[1]
南宋的顾文荐和叶寘对两宋宫廷用瓷有过颇为相近的记载。在文贵求简的古代中国,它们弥足珍贵,对其的解读亦从未间断。本文无意于对各窑口的属性或细节进行考订,只希望借此做些审美流变的探讨。
艺术史家常常满怀以新视角架构历史的渴望,这就导致了一个主张长期流行:既然政权的更迭不会引来艺术的根本变化,那么以艺术自身的特点解说其发展演变就更有道理,唯此方能建设更纯粹、更有艺术品格的艺术史。这个主张实在浪漫,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艺术的创造者无法挣脱时代的约束,特别是关联制度、服务日用的工艺美术,作品的变化常常是政治、经济、文化、信仰、民俗、民族、地理、材料、技术等众多因素引出的艺术表现。
赵宋在立国之初,就立下抑武修文的国策,这既使寒门士子能凭借科举进入统治集团,又培养了一大批读书人,打造出空前的文化盛世。工艺美术基本是在民族传统的滋养中发展起来,并开创了清隽典雅的一代新风的。作品于淡中见浓、浅中显深、平中寓奇,正是文人审美主张的精髓。不炫耀技巧,不使人惊诧错愕,质地、造型、装饰、色彩的单纯、简练、含蓄才是宋代的审美典范。不妨与唐代做个比较:同是咏庐山,李白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而苏轼却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中将唐诗比作“少年人的歌唱”,宋代则多了“人到中年”的沉稳。宋人的审美标准由前朝的好勇尚武转向文质彬彬,相对于唐代艺术的富丽、华美,宋代则推进到一种精致、深沉、纯熟的境界,正是“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两宋工艺美术的时代风貌并非一蹴而就,而宫廷用瓷的取舍正揭示了时代新风逐步确立的过程。
一、土贡赋税:地方窑精品进入宫廷的途径


北宋早期和中期,宫廷用瓷来源已多。所谓“越州烧进者”即是地方政权进奉。自晚唐开始,上林湖越窑烧造的秘色瓷,已用来贡御;五代时,吴越常以“秘色瓷器”“金稜秘色瓷器”“金银稜瓷器”贡献后唐、后晋、后周。[2]在北宋初期不到20年的时间里,钱氏曾以“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贡献中央政府。[3]其供奉器物数量之众,自有地方政权倾其国力以事中原王朝的大背景。宋辖境内,各地要依据出产情况,定期进奉中央,即“任土作贡”。瓷器也会通过土贡进入宫廷。《太平寰宇记》录太平兴国年间(976—984)贡瓷有定州“瓷器”、邢州“白瓷器”、越州“瓷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记熙宁元年(1068)贡瓷有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元丰九域志》(1078—1085)载贡瓷有河南府“瓷器二百事”、邢州“瓷器一十事”、耀州“瓷器五十事”、越州“瓷器五十事”;《宋史·地理志》与《元丰九域志》大体相同,有河南府“瓷器”、信德府(邢州)“白磁盏”、耀州“瓷器”。[4]在宋代,土贡除供皇室自用外,还要在每年元旦大型朝会上“赍擎陈列”[5],显然有纳诸方贡物以示天下一统的政治色彩。
从文献看,土贡产品十分有限,赋税可能是宫廷用瓷的主要来源。宋代陶瓷赋税形式很多,如瓷课、商税,另外还会采用科率的方式直接向地方采买。[6]据《曲阳县志》载,定窑附近有后周显德四年(957)王子山院碑,立碑者冯翱的署名为“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使”。这说明五代时的定窑已设“瓷窑商税使”。周密说李公略的收藏中有一件“雷威百衲琴”,其题款为“大宋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可见,吴越归顺后,宋廷也曾在越窑设瓷窑务,管理陶瓷税收等事宜。[7]神宗熙宁十年(1077),景德一镇商税收入已与邻县相当。虽说景德镇也包括其他行业,但元丰五年(1082)朝廷又专设了瓷窑博易务,显然与窑务在商税中所占比例令人瞩目有关。“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8],即对政府用科率法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反映。[9]虽其貌似公平交易,实际上却是一项最无章法和规矩可言的赋税摊派。[10]


两宋陶瓷品类繁多、面貌丰富,但在300余年的发展中,艺术走向仍然大体整一而明确。领导审美潮流的是官窑器和民窑的供御器。定窑成名较早,它秀美的造型和本色的装饰已展示出对优雅的追求,但在北宋晚期,其供御的荣誉却为汝窑夺去。究其原因并非全为口沿毛涩,而是纯然一色的汝窑,比加釦的定器更素雅,是和谐胜过对比、单纯压倒装饰。从汝器开始,宋瓷之美已更多地凝聚于造型和釉质,斧凿之痕稍重的装饰也不见于供御的官窑器物。南宋中后期,龙泉青瓷发展迅速,它们洗尽绮罗香泽,直抵优雅清纯。[33]两宋宫廷用瓷的取舍揭示了风尚的演变,玉成了旷绝古今的时代风貌,创造出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陶瓷艺术典型。


注释:
[1]参见:陶宗仪所著《说郛》册4卷18(涵芬楼影印本,1986年中国书店出版,第10页)。与此类似的记载还有南宋叶寘《坦斋笔衡》,除个别字增减外,时代由“宣政间”(1111—1125)改为“政和间”(1111—1118),“袭徽宗遗制”改称“袭故京遗制”,“郊下别立新窑”后无“亦曰官窑”,“余姚窑”作“余杭窑”。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511-6512. 谢明良先生对《笔衡》“窑器”条是否出自叶寘之手提出质疑。他考订《笔衡》约成书于南宋淳熙丁未(1187),《杂录》刊刻于景定庚申(1260)之后,“两书年代相距约六十年”。涵芬楼排印张宗详校一百卷《说郛》中收有二十条题为六卷本叶寘《笔衡》(陶珽重编一百二十卷本未收录),其中并无上述记事。《笔衡》“窑器”条记载系转引自陶宗仪友人孙作序于至元二十六年(1366)《辍耕录》所收辑的佚文。“因此《笔衡》……和《杂录》相关记事是二或一?仍有待厘清。”参见:谢明良.北宋官窑研究现状的省思[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05):26-54. 刘未先生也指出《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均已失传,二者在《说郛》中编次前后相继,但《说郛》辑录的《笔衡》并无“窑器”条,仅在《南村辍耕录》归入叶寘笔下。并且,《笔衡》与《杂录》所记内容不同,前者为朝野轶事,后者除窑器外,还有盐、纸、墨等多种手工业和博物方面的内容。“由此,颇疑窑器条原本出自《负暄杂录》,陶氏于《南村辍耕录》中误系《坦斋笔衡》名下。”参见:刘未.邵谔、王晋锡与修内司窑[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05):111-130.
[2]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266-271。
[3]钱俨:《吴越备史》卷4:“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带、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稀世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黄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千余两,绫罗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十余事,珊瑚树一,高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万事,白龙脑二百余斤。”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本,第41页。
[4]陈彦姝.宋辽夏金工艺美术[R]附录1《宋代土贡表》.清华大学,2009:295-308.
[5]脱脱等修撰《宋史》卷163《职官志·户部》:“国初以天下财计归之三司,本部无职掌,止置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充,以受天下上贡,元会陈于庭。”中华书局,1985年,第3846-3847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庚寅)诏自今诸州土贡物至京,令户部牒合属库务,先次受纳,来人遣回。候正旦朝贺排仗,别差人赍擎陈列。”中华书局,1995年,第1810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四月癸未)凡中都岁用百货,三司视库务所积丰约,下其数诸路,诸路度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然用有缓急,物有轻重,故方上所须,轻者反重,贱者反贵,而民有受其弊者,肃等既受命,建言京师库务所积可给二年者,请勿复科买。诏从之,后下赦书数以为言。”第2471页。
[7]王光尧.“监瓷窑务”官考辨[J].考古与文物,2005(01):78-80,86.
[8]周煇《清波杂志》卷5《定器》:“煇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謂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册5,第5067页。
[9]王光尧.宋代官窑制度初探[J].文物,2005(05): 74-79.
[10]王曾瑜.锱铢编[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533-577.
[11]孙新民.宋陵出土的定窑贡瓷试析[J].文物春秋,1994(3):49.
[1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册4,第3466页。
[13]按:学者通过对部分五代及北宋早期加釦定窑的研究,发现它们底部无釉,且粘结烧窑时的细砂粒,显然是仰烧产品,而其“芒口”亦较后来覆烧产品细窄。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7.
[1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太祖乾德)六年二月十二日……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金稜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开宝)九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稜……(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俶进……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三年)四月二日,俶进……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中华书局,1984年,第7841-7844页。
[15]《吴越备史》卷4:“庚辰五年(980)……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第33页。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56,75.
[17]同[8]。
[18]按:陳万里先生根据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时间和书中有“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的20年之间。参见:陈万里.汝窑之我见[J].文物参考资料,1951(02). 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即哲宗、徽宗时期。参见:叶喆民.汝窑廿年考察纪实[J].中国陶瓷,1987(06):41-46.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40.
[20]王光尧.汝窑与北宋汴京官窑——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代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5):90-100.
[21]吕成龙,丁银忠.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J]//故宫博物院八十五华诞——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M].故宫出版社,2010:117-129.
[22]按:在2015年“故宫博物院汝窑学术研讨会”上,宝丰县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团乐先生提出“北宋汝州为京师辅州,京师应指广义京畿之地,而非狭义京都、汴京之意。‘京师自置窑烧造系指朝廷在京师辅郡汝州青岭镇(现宝丰县大营镇)置窑烧造。”参见: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汝窑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03):152—158.
[23]按:李辉柄先生在《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中国陶瓷全集》总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等著录中提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认为《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讲的是汝窑从作为民窑受命烧造贡器到成为朝廷专设官窑的转变过程。他还进一步指出汴京并不具备设窑的自然条件,汝州则资源丰富、技术成熟,得出的结论是“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是北宋官窑,亦即是汴京官窑的结论。”另外,随着2000年张公巷窑的发现和随后的考古发掘,在2004年5月郑州“巩义黄堡窑、汝州张公巷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亦提出张公巷即北宋官窑的观点。参见:孙新民,郭木森,靳鹭.北宋汝官窑与张公巷窑珍赏[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9.
[24]同[20]。
[25]唐俊杰.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的比较研究——兼探张公巷窑的时代及性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05):102-121.
[26]庄绰.鸡肋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册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978.
[27]《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四九:“徽宗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诏:诸路州军见贡六尚局供奉物多不急之用,兼闻拣造科配劳民费财,可令殿中省并提举六尚局同共相度具的确合用名色外余停贡……熙宁诏书首罢四方岁贡,明训具在,祗若先酞蔽自联躬理宜损益,应殿中省六尚局诸路贡物可止依今来裁定施行……尚食局……中山府瓷中样矮足裹拨盘、龙汤盏一十双……”,第2318页。
[28]胡云法,金志伟.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M]//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285-299.
[29]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宋太庙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8.
[30]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6.
[31]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南宋临安府衙署遗址[J].文物,2002(10):32-46.
[32]赵永春.宋金交聘制度述论[M]//宋辽金史论集(第四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248-259.
[33]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8-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