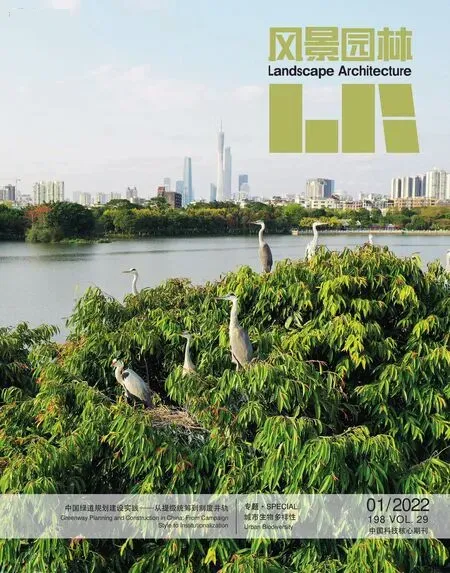邻里福祉视角下国外社区公园社会效益的研究进展
何琪潇 谭少华申纪泽 孙雅文
社区公园正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城市高密度建成环境中的重要绿色空间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地方民生工程建设的大量投入。根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站公布,香港有26个大型公园及2 199个小型公园(社区公园、花园、休憩处、儿童游乐场等),小型公园已成为这座高密度城市中人们主要接触自然的绿色开放空间[1]。深圳市在提出“出门500 m可达社区公园”的建设目标以后,编制完成《美丽深圳社区共建花园工作手册》,提出在不改变现有绿地空间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建设120个社区花园来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度、优化景观与生态环境、构建社区和谐人际关系[2]。
社区公园具有典型的“多功能、复合价值”特征[3]。除了游憩和休闲功能以外,由于具备呈斑块状散落的结构特点,社区公园能为城市环境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如明显表现该特点的口袋公园,能够实现局部地区的降温效果,帮助缓解城市居住区热岛效应[4];同时,在面积和形状相同情况下,其降温效应比生态公园、综合公园、游乐公园等更明显[5],当公园形状趋于圆形或正方形时降温效果达到最佳[6]。另外,在当前城市住房条件紧张的背景下,社区公园具备显著的经济溢出效应;与其他景观相比,邻里公园是诱发购房置业行为中最强烈的投资意向,据统计,在香港1 471笔高层私人住宅单位的交易中,紧邻公园的住宅平均能提高16.88%的成交价格[7]。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公园的社会效益开始进入中国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领域研究者的视野。江海燕等总结了国外公园绿地在社会分异方面的研究成果[8];邱冰等从经济学属性、社会学属性等方面对中国社区公园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分析[9]。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探索能够显著发挥邻里交往、精神恢复等社会效益的社区公园空间特征及设计策略[10-12]。从近年中国学者的研究趋势来看,社区公园社会功能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得到重视,并在社会效益认知层面形成了一些共识。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领域对社区公园的概念认知还比较混淆,如社会学较少关注公园与建设用地的从属关系,仅将其视作公共领域和资产,使得在进一步开展评估、探索机制、设计反馈等规划工作时陷入困境。社区公园概念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美,经过70余年的发展历程,国外发达国家对社区公园的理论研究已领跑全球。尤其在城市中心区衰落、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国外研究者很早就开始重视如何发挥社区公园的社会效益,至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系统地总结国外当前社区公园的研究进展,有助于深入剖析社区公园发挥社会效益的运行机制,为中国社区公园建设以及社区营造提供丰富的可借鉴经验。
1 国外城市公园的发展历程和功能演绎
1.1 应对社会问题的发展历程
纵观城市公园的发展和建设史,每一次重大的转变都是为应对不同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1)。自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引发人口急速膨胀导致的社会矛盾,间接促进英国和美国首个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为满足美国郊区居民建立亲密社会互动的需求,在城市更新行动鼓励下,当局政府开始整合利用居住区的周边绿地修建活动场所和游憩设施,“社区公园”概念被提出;20世纪70年代城市中心区衰落导致社会隔离加剧,美、英等国家以社区为单位鼓励渐进式的“社区行动计划”,带动了社区公园建设的迅猛发展;到了21世纪,人群陌生化和行为失范化形成一股社会冷漠的激流,社区公园演变成为“促进社会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场所,充当着异质性社会黏合剂”[8]。当然,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地域背景不同,欧洲、美洲、亚洲的发达国家对社区公园社会效益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但作为调控邻里层面居民日常生活质量的社会空间载体,塑造优质的社区公园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地方发展战略。
1.2 作为社会空间的功能演绎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产品,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16]。可以发现,社区公园作为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演绎不同的社会功能属性,这正是它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作为回应不同社会问题的重要载体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功能的演绎对于空间距离最近的邻里生活的影响最大,集中表现在空间特性对邻里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影响。
1)空间占用性,表现为公共空间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会逐步演化为不同群体广泛冲突的地域。如在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中,公园的实际占用和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更有力群体的手中。2)空间类聚性,空间生产会造成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和矛盾,会产生功能的吸引和排斥[17],如公园可为房屋商品进行交换带来增益,是开发商刺激房价上涨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以公园为中心向外削弱的住房分异现象。3)空间支撑性,即公共空间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社会关系,不仅由社会关系支持,还生产着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如熟识群体和陌生群体在公园产生互动,即开始了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重塑和构建。4)空间干预性,即城市的空间会影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力[18]。如住区居民在附近公园的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休闲方式的转变,使得公园发挥了对日常行为生活的主动式干预。
2 社区公园对邻里福祉的潜在影响
邻里福祉也被称作社区福祉,是国外近年来衡量社区发展质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其内涵不仅反映在交通可达、住宅供给、能源使用、废物管理等社区服务水平上,还可体现在个人健康、人际沟通、安全与归属感等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内容中。随着社区公园逐渐成为城市与地区的标准配置,其对邻里福祉的影响愈加强烈。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在拓展本地社区公园建设范畴,如美国国家游憩与公园协会(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NRPA)制定的城市公园分类体系中的微型/口袋公园(mini/pocket park)、邻里公园(neighborhood park)、社区公园(community park),英国的本地公园与开放空间(local parks and open spaces)和小型开放空间(small open space),新加坡的城镇公园(town park)、邻里公园、游乐场(playground),以及日本公园体系中的居住基干公园(日语:基盤としft公園)等,都是与当地邻里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社区公园代表。遵循社区公园4类社会功能的演变特征,笔者收集并提炼了Web of Science数据库自2000年以来,风景园林学、社会学、预防医学、犯罪地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在社区公园对邻里福祉的潜在影响研究的主要成果,可归纳为占用性、类聚性、支撑性、干预性4个方面(图1)。

1 社区公园影响邻里福祉的传导路径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community park influencing neighborhood well-being
2.1 占用性:邻里安全的威胁
社区公园分布在相邻社区管理的接壤区域,既可以成为社区居民建立联系的中心场所,也是容易被忽略和缺乏维护的“危险地带”。自20世纪60年代始,社区公园被看作是美国社区犯罪的潜在热点区域。直到现在,Stodolska等通过评估21世纪后美国芝加哥城市社区的犯罪情况,发现社区公园仍然具有潜在的吸引毒品交易、帮派斗殴、游荡的流浪汉等负面作用[19]。Hipp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犯罪空间分布的调查,发现该区域的社区公园对周边居住群体有较大吸引力,但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从事非法活动,成为犯罪活动的制造者[20]。排除地域背景和文化特征的影响,Boessen等调查了美国9个城市的109 808名居民居住地附近社区公园与犯罪的关系,结果显示,社区公园周边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社会人口特征是决定公园内或附近是否会发生犯罪的关键驱动因素,周边分布住宅用地的社区公园与更多的犯罪数量相关且呈现出随距离衰减的变化,距离公园最近的住宅边界犯罪增加幅度最为强烈[21]。除此之外,社区公园与犯罪的联系还体现在对社区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上,Christopher等在德黑兰的实证研究表明,犯罪率是研究城市绿地与幸福感关系的前置条件,即在调查绿地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所在社区的犯罪率情况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对女性而言该影响尤其明显[22]。
社区居民经济收入的差异同样影响社区公园对邻里安全的威胁程度。Cohen等发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低收入社区的公园使用率低于高收入社区,其原因可能与居民感知到的威胁有关[23],主要源于公园内可能发生的犯罪活动、交通事故或卷入帮派斗争等;他们进一步系统观察洛杉矶48个邻里公园的使用情况,并调查了低收入社区的公园使用者和家庭居民,发现使用率较高的社区公园与其存在流浪汉的数量有关,使用率较低的社区公园与园内存在醉汉的数量有关[24]。同时,社区居民的民族文化和地域认知也会影响其对公园的使用情况,如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等少数群体排斥使用当地的社区公园;墨西哥裔美国青少年在有安全监督的情况下才会增加在社区公园开展体育活动的频率[25]。
2.2 类聚性:邻里分异的排斥
20世纪90年代,社区公园曾被视为种族隔离的物理围墙。Solecki和Welch最先提出“绿色围墙”假设:位于不同种族或民族群体社区周围的社区公园缺乏使用和维护的概率较高,其原因是这类社区公园会被视为阻碍族群之间沟通与交流的围墙[26]。Corcoran等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148个社区的4 132名居民进行了调查,发现社区公园的存在降低了本地公民行动的积极性,潜在原因与“绿色围墙”假设有关:从表面来看,社区公园可能有利于加强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却阻碍了当地社区居民与外部其他居民建立联系[27]。若社区公园削弱了社区之间的联系,便会缺乏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增加社区犯罪的潜在概率,该结论间接解释了某些社区公园存在高犯罪率的原因[28]。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绿色围墙”的观点。Paul从物理障碍和心理感知障碍两方面对芝加哥某社区公园存在的跨种族关系进行了实地测度,发现当地社区公园更像“绿色磁铁”,其指出社区公园有潜在的促进种族间融合作用[29]。随之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佐证了“绿色磁铁”的观点。尤其是不少社区公园具备免费进入和步行易达的特征,方便失业和低收入群体访问,这对居住社区的种族融合发展尤为重要[30]。Krellenberg等在智利圣地亚哥的研究表明,当地社区公园分布在不同经济收入群体社区之间,但并不影响社区之间居民的集聚与来往[31]。综上,在全球化移民浪潮的趋势下,关于社区公园对不同种族或民族、经济水平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程度仍在检验过程中。
2.3 支撑性:睦邻关系的凝聚
社区公园一直都被视为能够培育良好睦邻关系的公共场所,更能增进社区满意度、社区归属感[32]。睦邻关系与邻里居民参与公共活动的频率有关,邻里之间在活动中可通过建立反复的视觉接触和短时间户外对话机会,维持邻里间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33]。Seeland等通过对瑞士青少年社会习惯调查发现,同龄人之间建立彼此认同感、形成稳固友谊往往发生在可达性较高的公园[34]。对于身体机能下降、社交网络范围受限的老年群体,社区公园的可达性对其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更为重要[35]。同时,在荷兰某社区公园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地年轻人更愿意在社区公园中结交新朋友,由此可认为社区公园能够刺激人群产生参与交往活动的意愿[36]。
为了探索社区公园在营造良好睦邻关系过程中的功能机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社区公园与社区集体效能之间的潜在联系。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J·桑普森(Robert J. Sampson)在1997年《科学》杂志中提出,指“城市居民为了社区的共同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与共同干预意愿的联系”[37]。2000年以后,集体效能理论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城乡规划学、城市社会学、人口学和公共健康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运用该理论来研究城市发展进程对社区居民居住、生活和健康产生的影响。Cohen等发现,社区公园与集体效能之间存在某种积极影响,即所在社区辐射范围内,社区公园的距离与集体效能水平显著相关,高水平集体效能的社区居民更愿意访问离家更近的绿地[38]。同样,与集体效能概念相近的社会资本也与社区公园相关。Broyles等衡量了新奥尔良市27个邻里公园参观者的社会资本水平,相较于低分值,高分值的邻里公园能观察到超过约3.5倍的参观者,并发生超过4倍的体育锻炼活动量[39]。可以预见,开展社区公园与睦邻关系相互联系的深入研究,仍需考虑类似邻里集体效能和社会资本等社会感知因素。
2.4 干预性:邻里健康的促进
随着居民个体使用社区公园频率的增加,有关公园暴露和经历对个体健康水平影响的医学报道正在逐年递增,目前集中表现在疗愈精神状况和促进体力活动两方面。虽然两者之间的因果路径和医学机理仍不明晰,但通过科学合理配置社区公园,营造优质的公园环境特征,引导社区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最大限度地为邻里居民追求更高水平健康提供有效的空间支撑。
1)精神疗愈。Ulrich发现,较少接触自然的人群易患某些慢性病,如肥胖、糖尿病、骨质疏松症、抑郁症及心脏病等[40],而社区公园能为居民提供接触自然的机会。Nordh等调查了挪威多个社区公园后,发现小型绿地对人群精神恢复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最能发挥促进作用的环境要素是草坪、花卉、水面、乔木灌木等自然元素[41]。Peschardt等发现哥本哈根市的人们到达小型绿地的主要原因是社交休息和恢复精力[42]。在社区公园对精神疗愈的影响方面,有学者开始关注其与人体心理认知老化的关系。主要基于两项队列研究:①Keijzer等对英国6 506名人员做了10年的队列研究,发现住宅周边拥有较高绿地数量对预防高龄群体的认知能力下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43];②Cherrie等追踪并定时评估了1 091名苏格兰居民分别在70岁、73岁和76岁的认知水平,发现居民认知功能衰退的程度与其居住地附近1 500 m范围内的公园数量有关,最早可追溯到其童年或成年时期的居住地[44]。显然,社区公园与认知功能老化的机制仍需探索,但已形成的一些初步共识,如社区公园有着促进邻里凝聚力和社会支持、减轻居民精神压力[45]、提高居民体力活动水平[46]的社会效益,都被认为能减缓认知功能老化的速度。公园绿化的减噪作用也是潜在原因[47]。
2)促进体力活动。在美国大约有30%的体育运动都发生在公园,住所附近的社区公园数量、可达性和环境质量,决定了当地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水平。Cohen等对美国25个城市的174个邻里公园进行了一项近10万人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一个面积约为3.5 hm2的社区公园,平均每小时会有20名用户,每周有1 533名用户,每周能发生221小时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48];为了解公园与体力活动的定量关系,Cohen等进一步分析了其中162个配有游乐设施的邻里公园,发现滑梯和秋千是儿童主要的体力活动设施,如每增加一个滑梯或秋千设施,便会增加近1/2的儿童数量和中高强度体力活动量[49]。国际健康标准表明,每天保持30 min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能有效预防肥胖,住所远离社区公园的青少年由于缺乏运动机会和场所,形成肥胖和超重的概率更大[50]。
3 社区公园增强邻里福祉的空间路径
邻里福祉通常由当地区域政策、经济水平、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大量实践研究证明,社区公园与邻里福祉存在潜在的影响关系,这给风景园林和城市规划领域参与社区建设、调控社区发展质量提供了可能的路径。综合优化社区公园的区位分布、形态特征和设施配置,营造科学合理的社区环境,逐步引导和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为增强邻里福祉积累一定程度的积极效益。实际上,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已经围绕该路径开始了详细的探索,涉及政策指引、设计优化和管理精细等多方面。本研究从空间的增效和减负2个维度,总结了由空间行动计划、空间营造锚点、空间经营模式构成的增进邻里福祉的空间优化路径(图2)。

2 社区公园增强邻里福祉的增效减负空间路径The spatial path of community parks to enhance neighborhood well-being
3.1 空间行动计划
3.1.1 拓展服务半径
自1967年纽约的佩雷公园(Paley Park)建成以来,口袋公园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由于面积小,可广泛存在于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口袋公园投入使用后得到附近写字楼职员、中心购物市民以及游客等的高频度使用和褒奖[51]。在城市土地利用不足的窘境下,口袋公园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有限条件下拓展绿地服务半径的首选形式,更有利于社区公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促进邻里人群健康的社会功能。英格兰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于2015年实施了“口袋公园计划”(Pocket Parks Scheme),目前已创造了80个社区新公共中心;2018年又开展了“口袋公园+”(Pocket Parks Plus)行动,将资助198个新建或改建的公园[52]。NRPA于2013年发布了《提供健康活动的口袋公园建设导则》(Creating Mini-Parks for Increased Physical Activity),总结了口袋公园应具备的4项设计导则:1)构建良好衔接的城市绿道、自行车道及游憩小径;2)有效支撑周边群体多样需求的活动;3)塑造融合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城市美丽风景;4)配置实现社交自由的空间设施[53]。
3.1.2 引导群体包容
社区公园不仅应该供目前身体健康或努力保持健康的人使用,还要考虑某些边缘群体使用的便捷。加拿大公园娱乐协会(Canadian Parks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CPRA)提出“公园社区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Canada’s Parks Community),通 过 合作、联系、保护、引导等方式建立全民共享的公园社区。NRPA还制定了《公园包容性开发指南》(Guidelines for Developing an Inclusion Policy),围绕美国4类易被忽视的群体:多文化民族群体、身体和认知残疾群体、性少数群体、新移民和难民群体,制定了需求评估、社区参与、改进计划修订、操作方法集成、可持续性发展策略5项社区公园应具备的核心开发准则[54]。新加坡发布的《2019年总体规划》,五大核心策略之一是强调营造一批包容、绿色的街区,为全年龄段人群提供社区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构建儿童和老年人友好的社区。
3.2 空间营造锚点
3.2.1 规避威胁设计
社区公园独特的环境特征既会带来犯罪风险,也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保护,通过合理的环境和景观设计将有效规避威胁。NRPA目前制定了《通往公园的安全路线:通过步行性改善通往公园的通道》(Safe Routes to Parks:Improving Access to Parks Through Walkability)的设计导则,明确了影响犯罪活动的物理环境特征,包括人行道狭窄且设置在茂密植丛间、居住地到公园的线路受到密集灌木遮挡、大部分的行人路线隐蔽且不受监控、照明不足和涂鸦泛滥的空间大量存在等[55]。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创造防御空间的设计准则》(Design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中也提到犯罪地点与建筑空间之间的巧妙关系,具备开放视线的空间意味着人们更有可能注意周边环境,有助于安全感的感知。最近研究表明,社区公园内的空间识别性(结构清晰、无视觉障碍、可达性)与社会互动强度(公园参与度、接触强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56]。
3.2.2 提升支撑设施
社区公园对邻里福祉的积极效益大部分源于其对集体活动的支撑。NRPA自2008年开始倡导“公园建设社区”计划,重点开展了处理中水、拆除不安全的游乐设备、重新铺设公园道路、建立周围社区与体育活动场所的连接性等措施。如超过600个家庭住在华盛顿特区马文盖伊公园(Marvin Gaye Park)附近的社区,该公园曾因吸毒和贩卖毒品而被称为针头公园(Needle Park)[57]。通过实施该计划,成功地将其改造为当地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再如新加坡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已建设了347 km的公园连接道,完善的公园连接道系统让其成为全球绿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并计划至2030年将连接道长度提高到400 km,使得90%的家庭步行10 min即可到达附近公园,同时也希望通过绿道使社区间能够建立更紧密的纽带[58]。
3.3 空间经营模式
3.3.1 延长活动时间
充分的市场运营能使人们每周在公园里进行中强度体力活动的时间增加,如使用横幅和海报等节庆活动的气氛营造工具有助于增加公园游客的体力活动时间。在日本,围绕近邻公园体育锻炼的营销策略十分丰富,例如,东京都足立区近邻公园策划了“公园肌肉训练”活动,在公园安排体育协调员负责为运动者提供专业肌肉训练、步行热身和身体伸展等的指导,同时,协调员也会定期根据周边住户体能评估结果,帮助设置适宜的锻炼目标[59];东京都武藏野地区倡导社区公园开展“自然观察”“园艺活动”“工艺制作”“健康锻炼”等活动的培训课程,还提供包括肩部僵硬和背部疼痛缓解方法的传授、身体成分的检测、体育活动计划的咨询等服务[60]。日本近邻公园增加人们活动时间的常用策略还包括网页宣传、鼓励志愿者参与、定期清洁和翻新、强化社区警务和邻里监督、倡导减少可达距离和增强公园识别性的法律和规定等。
3.3.2 激活活动契机
建立不同居民参与社区公园公共活动的契机,可增强邻里的融合度和凝聚力。日本公园绿地协会提出,社区组织应充分利用节庆活动日、清洁日、兴趣课程和俱乐部会议等机会增加公园场地的吸引力,提高公园利用率,同时提供人际交往的机会。新加坡国家公园局致力于推广园艺活动,2005年以来,推出了“绽放社区”计划,面向当地多民族的社会,打造能够聚集不同社区邻居和同事共同分享知识经验的平台,还通过设置一年一度的社区花园节(Community Garden Festival),曾吸引超过4万人次的园艺爱好者[61]。同时,新加坡自2011年开始进一步推进“自然社区计划”(Community in Nature Initiative),将自然保护活动推广至社区范围,让公共的社区公园成为不同社区的重要共享空间,使得不同群体能够有机会在大自然中共享和交谈[62]。
4 启示与展望
2018年“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以及各地的丰富实践,加快了新时代城乡人居环境的建设和理想城市模式的建构。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和首倡地,提出要以社区公园作为公园城市建设的基本单元,实现从“社区中建公园”到“公园中建社区”转变,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充分发挥公园绿地的社会效益。基于国际先进经验,针对中国社区公园发展的现状,笔者从增强邻里福祉的视角提出未来社区公园建设和管理的4点启示。
1)保持口袋公园形式绿地的建设投入。相比于政府运作的传统社区公园,以私人捐助或第三方部门筹款形式建成的口袋公园,在建设时序和进度上更具优势。从土地利用角度看,大部分口袋公园的选址体现了“存量转变为增量”的基本用地思想,改造前后提高了存量空间的用地效率。从邻里福祉的影响程度来看,密集建成区的口袋公园发挥的社会效益更加显著。深圳实行的“出门500 m可见口袋公园,2 000 m可达综合公园”的建设目标可作为下一阶段各地区制定绿地规划实施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2)重视社区公园的包容作用。虽然中国目前不存在类似于欧美国家因历史原因产生的少数族裔的住房歧视等社会问题,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地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文化差异导致的邻里关系对立疏远,城市中心高档封闭型小区与城市边缘地带城中村的居住格局差异等突出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因此需重视社区公园的空间增效路径并营造出更具包容性的社区。
3)把握社区公园增强社会效益的设计锚点。社区微更新是中国当前社区空间规划和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对社区中广场、街心花园、游园等微型绿地的更新是主要的载体。在老旧社区的微更新中,可以效仿国际层面增强社会效益的设计方法,侧重于消除使用频率较低、受到遗弃的消极空间,或将之转变为能预防犯罪威胁、增强交往活动机会等减少邻里矛盾的积极空间。
4)拓展社区公园的经营和参与主体。目前国家虽然加大了对社区公园的建设力度和资金投入,但日常管理和后期运营水平仍然有待提高。社区公园是涉及社区居民日常事务的公共项目,理应学习国外公园管理办法,拓展居民成为日常监护的主要力量。聘请物业管理、吸纳第三方组织运营,动员和创造本地社区建设的共同参与。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其中表1根据文献[9, 13-15]整理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