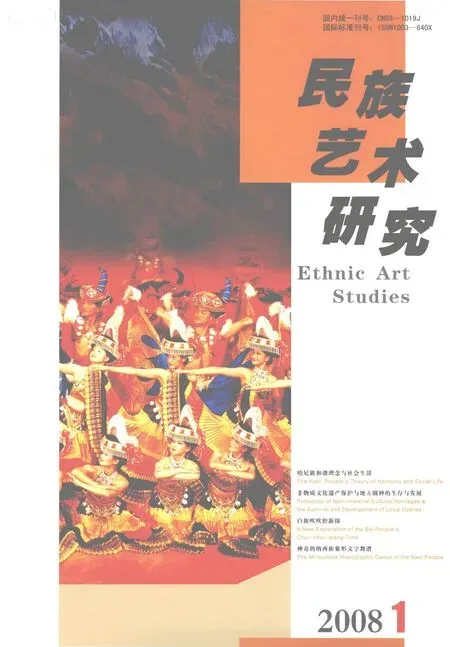中国民族艺术学:谱系、定位与格局
彭兆荣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世界公认的表述单位,其合法性表现是以“民族”和“国家”作为两个重叠的边界,学者们将其描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至为重要的是,“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价值”①[英]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页。。换言之,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族性认同”都无例外地使用一套与“民族”有关的概念——无论是在工具理性层面,还是在逻辑理性层面,同时也在“建构他者”,以分辨“确认自我”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从逻辑上看,“民族艺术”作为与之相关的学科,无论是作为特殊政治语境中的策略性概念表述,还是作为中国特定的学科建构目标,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厘判,了解“民族”和“艺术”在不同的文明体系、文化背景、国家形制与历史语境中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民族”是一个舶来概念,中国的民族学也是由西方传入的。②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这在学界已为共识。而当我们用“民族”概念为学科定位时,总是避免不了两个最基本的走向:世界趋势与中国特色。“中国民族艺术学”也不例外。
一、“民族”之滥觞
作为学科,“民族学”ethnology与“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公认正统学科的表述。虽然这两个概念有着各自语言和文字上的语义滥觞与流变,发展至今,在学科上大致已经合流。最具有说明性的例证是,作为“国际学会组织”的名称已合二为一: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英文缩写为IUAES),即“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事实上,在当代的西方国家,“人类学”anthropology与“民族学”ethnology已经被视为一个学科,相关的分支学科,如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与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也已趋同化。
从词源的发展线索看,民族学ethnology的词根ethnic源自希腊语ethnos,而ethnos则由形容词ethnikos演变而来,原用来表示不同的“人种”(race,即种族)。所以,作为学科的专用语,ethnic用来表示“种族的”“人种的”。早期在使用上,ethnic和race语义接近,旧时可相互替换,因此中国早期的翻译也常常将其译为“人种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race在战争中曾经与racism(种族主义)发生一些政治瓜葛,其语义表述也由此受到影响,学术界趋向于用ethnic一词来取代race和racial。人们也更多地使用“ethnic groups”取代“种族”,以避种族主义之嫌。
另一条线索是“民族”(nation),也译为“国族”。虽然英文中的Nation(民族、国家)最初从拉丁语nasci的过去分词演化而来,意为出生(to be born)——指一类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其本义最初是指那些具有特定地理空间的人类群体。①Mostafa Rejai,Political Ideologies:A Comparative Approach,M.E.Sharpe,1995,p.24.也就是说,它的最初语义是指籍贯。到了中世纪,它被附会了神职的意味。“民族”一词出现在英文中稍晚,13世纪时,它主要指种族群体或血缘群体,并非指政治群体。直到16世纪,nation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个曾经指称籍贯、种族和教会神职精英的词语与国家的公民(people)结合在了一起。②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载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页。后来的欧洲历史以及不同国家各自情形的变化,使这一概念经过了不同的流变和不同国家“各自表述”的过程,不同国家的文字语汇在使用上也有差异。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它才定型于“国家”的阈限。
由于民族(Nation)与现代国家的形制发生历史关联,现在通行于全世界,而且成为联合国UN(United Nations)公认的“国家”代名词——即现代世界上的国家皆属于“民族国家”。因此,在许多场合,Nation也就成了“国家”的代码,比如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即“美国国家篮球协会”)。但是,以Nation代表“国家”的语义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它与现代国家的形制存在内在的关联,其缘生地在欧洲,而法国则为代表。众所周知,欧洲在十七八世纪基本处于封建农业的庄园式社会时期,同时新兴资本主义力量快速出现,传统的贵族,包括帝王贵胄、宗教僧侣、地主(庄园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形成了明显“三个等级”的社会结构:第一等级是僧侣(所谓“以祷告为国王服务”);第二等级是贵族(所谓“以宝剑为国王服务”),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贫民和新兴资产阶级(所谓“以财产为国王服务”)。
1789年法国发生了震撼世界历史的大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以波旁王朝为代表的君主制度宣告结束。在10年的酝酿、变革中,新型国家呼之欲出。然而,用什么工具概念足以概括整个法兰西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当时的三个等级,最终人们选择了“民族”(Nation),它作为现代国家的工具形制出现——借以代表法兰西的整体社会。这也是法国国旗“三色”(三个等级)的意思。其也成了后来通行于世界政治舞台“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雏形。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在总体上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政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的公民社会,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决”和“公民意识”。也就是说,“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在欧洲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生成的一种现代国家制度,它形成了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民族”成了现代国家特殊的表述符号,多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事实。
历史地看,民族国家属于欧洲历史“长时段”演变的“合成果实”,“历史学家们担负起筛选往昔事实的责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会发展路线的潜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新的政治实体——民族(nation)——能够体现新的目标”①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这样,民族就成了历史和科学以外的“第三个现代力量”。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概念“民族”也应运而生。“民族”与“国家”成功地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合二为一。这也是吉登斯从“传统国家”“绝对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替换模式。②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简言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制正是以欧洲历史为背景,以法国大革命为基型的现代国家建制。
今天,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2500个民族,除了日本、朝鲜、韩国、冰岛、葡萄牙等国家可以达到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95%左右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标准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民族“共同体”国家。③[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制为近代民族主义的渊薮。诚如韦伯所说:“在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清晰地植根于政治领域。”④Max Weber,The Nation,In Hans H.Gerth and C.Wright Mills(trans.and 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Routledge&Kegan Paul,1948,p.179.盖尔纳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认为民族单位应该与政治单位相吻合的政治信条”⑤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Basil Blackwell,1983,p.1.。简单地说,“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
然而,“民族”并非将政治性工具概念视为唯一的表述。人类作为社会“族群”实体,也并非只涂上政治彩色。恰恰相反,族群的基本原色是社会和文化。正是基于此,“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概念也越来越趋向于表述“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研究。从词源上看,anthropology一词是希腊文anthropos——“展示人类”的借用。虽然人类学在不同的分支上有“体质-文化”的宽泛区分,但该学科强调整体性。⑥[日]祖父江孝男、米山俊直、野口武德编著:《文化人类学事典》,乔继堂、鲍良、朱丹阳、袁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相比较而言,民族学ethnology这个词——作为学科归属概念的出现则较为晚近。依据学者的考据,它是1839年由爱德华兹(W.F.M.Edwards)在一个人类学团体“巴黎社会学会”开会时提出来的。后来,这个概念也逐渐生成出了“民族志”(ethnography)——指对一个特定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制度进行详细的调查、描述与研究。⑦参见吴泽霖主编《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都侧重于研究“文化”。
今天,anthropology与ethnology在词义上呈现出越来越趋同的态势。在托马斯·巴菲尔德主编的《人类学词典》中,人类学直接被置于“文化和社会”范畴。⑧Thomas 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17.作为学科性概念的“策略性表述”,“族群”ethnic groups便呈现出了历史特殊的价值:当“民族”(nation)被作为政治表述的概念的历史演变中,“族群”也在复合的语境变迁中突显出新的趋向性价值——即侧重于表述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的意义:“族群ethnic groups和族性ethnicity,即作为人类学概念大致上用于指涉特定的人群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⑨Thomas 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152.也就是说,“族群”在当代的人类学学科中更加侧重于表述人类学学科范畴中的“社会与文化”,以保持与“民族”(nation)的区隔和距离。
粗略地对西方“民族(学)”进行“词与物”的知识考证,特别是辨析了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之后,我们发现,任何相关的认知、经验与表述都围绕着“人(我)”——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都属于“人学”范畴。西方在知识传统中与“人学”相关的词汇原有不少,维柯在《新科学》中专此做了考据,比如在“certum”(确凿可凭)和commune(共同的)的演变中,派生出了与humane(人道的)和civilized(文明的)的,因为这个词一般都可能指“人的”时代,以别于“神的”和“英雄的”时代中那种“人的”意义。①参见[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1页。也就是说,西方的“人学”是与“神-英雄”时代相对应的分类。这既是西方的历史背景,也是西方现代的语义诉求。
概而言之,“民族(学)”无论作为概念还是作为学科,都是西方知识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西方(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在逻辑。
二、交错与交集
回观中国传统的认知分类,西式的“神-英雄-人”的三分形制与中国传统的“天-地-人”貌似神非。中国传统的“人学”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交织与交集。大致上看,中华民族传统的“人学”伦理交汇在“二三四五原理”之中。所谓“二原理”,指中国的宇宙观最基本的元素划分为阴阳。所谓“三原理”,指中华文明的“天-地-人”与“时-利-和”的“三才体制”——既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致中和”原理;亦为自然的“道理”。所谓“四原理”,指一年四季和一日四时。《礼记·孔子闲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一年的“四时”为四季农时;一日的“四时”为朝、昼、夕、夜。所谓“五原理”,指五行。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将宇宙万物划分为五种元素:木、火、土、金、水。同时将万事万物按照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的属性归到五种元素中,《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滋润),火曰炎上(燃烧),木曰曲直(弯曲,舒张),金曰从革(成分致密,善分割),土爰稼穑(播种收获)。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换言之,“二三四五原理”集中式道理于一体。
如是观之,中式的传统学问中的“人学”与西式的“人学”同中有异:同者,西方的“人学”贯彻“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之精神;而中国的“人”被表述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解字》)②[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1页。异者,中西方的“人说”中的三维结构是倒错的:西方的“人”是至高无上的,“以人为本”是谓也。中国的“人”是支撑的,“天-地-人”共同支持,取“人和”为圭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被视为最高的德行。③[日]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60页。“人和”——“和为贵”也成为至高无上的境界。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中国古代的群体也以“人”(不是“民族”)为基本的表述范式。具体而言,古代的人群多以“人”指称,有指称族群的如“汉人”“苗人”;有指称区域的如“南人”“北人”;有指称外来者的如“胡人”“洋人”等等,且多为泛称。“民”与“族”只是以上诸类的代词,可独用,亦可连称。如《左传·僖公十年》“民不祀非族”。《礼记·坊记》“民犹淫佚而乱于族”。虽早在元代就出现“民族”一词,元世祖时的大学士许衡在《时务五事》中说:“国朝土宇旷远,诸民族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④参见伍精华、杨建新主编《民族理论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与当今人们所使用的“民族”迥然不同。至于古代“民族”的概念,据郝时远先生考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语义有二,即“宗族之属和华夷之辨”。①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虽有“民族”,却无当代“民族”的语义,只是语词的叠合,边界范畴完全不同。
如上所述,我认为今天在学术上所使用的“民族”为舶来概念,该词的现代语义出现于晚清,且由日本传入。理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人所铸,原即富含种族意味的汉字新词——‘民族’,广泛接受国族主义的洗礼”。②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有意思的是,这一从日本借的民族其意接近现代西方nation,读音却是汉语(ming chu)。事实上,日本近代所谓国民国家的创成期,汲取了大量中国文化(汉学)的养分。③张明杰:《明治汉学家的中国游记》,《读书》2009年第8期。所以,即使是“民族”概念,中日也存在“历史错综”现象。中国近代最早使用“民族”概念是1899年梁启超在他的《东籍月旦》一文中。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我相信,任何借用都会渗透传统的文化因子,任何被动的借用都包含了主动的选择,任何客观事实都包含了主观的渗入。
有学者认为,日本的“民族”不能和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民族”对号入座,是与“华夷之辨”向“五族共和”“五十六个民族”的不完全过渡。⑤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载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至于中国人类学界使用的“族群”(ehtnic,ethnic group,ethnicity)也是外来概念,尽管学者侧向于将“民族”作政治表述,而“族群”作文化表述的区隔,但事实上二者却很难泾渭分明。作为国家的表述单位,“民族”的悖论性早已潜伏其中。一方面,它具有官方政治性国家特征;另一方面,它试图将世界族群的多样性以及历史的变迁都置于国家政治的专属性之中。⑥E.Hobsbawm,An Anti-nationalist Account of Nationalism Since1989,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eds.),The Ethnicity Reader: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and Migration,Polity Press,1997,pp.69-71.
除了“民族”,“国家”也值得辨析。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以农耕文明背景、具有浓厚封建等级家长制的“家国”,并与“天下”观结合在一起的形制,形成了有明确“中心/边缘”的“天下体系”。⑦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就传统的“华夏秩序”而言,中国的“地理”是以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地理学。就传统“一点四方”的方位律制和人群关系格局而言,历来重“一点”而轻“四方”。《博物志》卷首之“地理”载:“七戎六蛮,九夷八狄,经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⑧[西晋]张华:《博物志》,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地理之误有三:一,来自对地理客观上的无知。二,对于“华夏中心”和“大一统”的坚持与固守。三,过分相信史籍的记录,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关于此,梁漱溟认为“司马迁《史记》多不可信。”⑨李凌己编:《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所谓“不可信”是指与自然地理的指示多不吻合,而只满足于“地理”的政治意义。
从逻辑上来看,“中华民族”也随之出现了另一种“交错-倒错”现象:政治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有了统一的国家。秦始皇建立强大帝国开始就实行“五服”政策。“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10[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一体”实为中国民族之历史景象和实情。近代以降,特别是孙中山借用了“民族”的概念,于1911年建立新型国家,即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历史国家遗产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民族学家的调查、识别,确认了中国境内获得认定的56个民族。也就是说,就“民族国家”作为国体形制而言,中国仅有110年的历史。
然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这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国家政治与历史文化上的交错现象;即在政治上表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导价值的“共时性”的“一体”表述;在文化上则需要到数千年历史中求取“历时性”的“多元”价值。具体而言,“中华民族”的表述羼入了两种基本的认知和分析维度:一种是国家政治意识中作为“民族”的“共时性交错”;另一种是历史文化积淀中作为“族群”的“历时性交集”。二者构成了中国民族艺术学的两个基本视野。
概而言之,中华文明有着自己的生成和生长原则,自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我认知和表述的体系。在近代以降的“西学东渐”中,西方的“民族(学)”借道进入中国传统的表述体系,既交错又倒错,需要加以反思与辨析。
三、艺术与镜像
“艺(藝)术”作为一种综合性认知、分类和表述形态,特别当其以“民族”为前缀,以西方艺术为参照时,中国民族艺术学便出现了多维现状和变异景象。
(一)知识谱系方面
中西方“艺术”概念迥异。西方的“艺术”(Art)从“手”(arm),强调“手工作业”。“艺术”谱系承海洋文明的根脉,“以人为本”为基本线索,以“人文学”(the humanities)为学科框架,突出“人-艺”的关系。从学科上看,艺术属于人文学,而人文学来自人文主义(humanism),强调的正是“人(human)”。该词曾经表示“对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作品的研究。”②[美]理查德·加纳罗、[美]特尔玛·阿特休勒:《艺术:让人成为人(人文学通识)》(第8版),舒予、吴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西方的“艺术”与“人”是互证性的。换言之,“艺术”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西方教科书的基本命题。③[美]理查德·加纳罗、[美]特尔玛·阿特休勒:《艺术:让人成为人(人文学通识)》(第8版),舒予、吴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则不然。如上所述,中国以“天-地-人”为一体,以农耕为正统(正-政),以“社稷”为国家。艺(藝)从农。艺(藝)的本义表示作物的栽培。从造字上看,“藝”的形态原理为种植庄稼草木,为“農”的本相。《说文解字》释:“埶,种植。字形采用‘坴、丮’会义,像手持种苗而急于种植。”“艺”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妇女跪在地上,捧着一株麦穗。最开始是种田的意思,后来才有其他意思的衍生。④徐艺乙:《传承与发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193页。另外,在古代社稷国家的事务中,“祭祀”为重者。也有学者将“藝”类归于“祭祀”,认为这个字形既有象人种植之形,为树艺的本字。⑤参见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5页。研究表明,殷墟卜辞中的“受年”与“受禾”,以及“年”与“黍”、“秬”(应为稻)、“鬯”(既是黑黍,也是古代祭祀用的酒)等常连用,说明国王重要的祭祀是为了五谷丰登。⑥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十六章“农业及其他”,中华书局,1988年版。故以“巫—舞—藝—農”于祭祀之判断当不意外。⑦参见彭兆荣《艺者 农也》,《民族艺术》2019年第2期。
(二)分类形制方面
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最基本的线索。“艺术(学)”原本即属于分类范畴——无论是概念分类、应用分类还是学科分类。西方的“艺术”(art)从古希腊肇始时期就将艺术二分为“美(fine art)-用(useful art)”。依照欧洲的艺术传统,将“艺术”分为“有用的”和“审美的”;前者指“工艺”,后者指“艺术”。①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42.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 “美术”(Fine Art)这一术语虽然出现在18世纪中叶,但继承了古代的分类形制,指的是非功利的视觉艺术,包括绘画、雕塑与建筑等。②贾晓伟:《编者序》,载《美术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具体而言,在西方艺术的分类范畴体系里,“艺术(美)”与“工艺(用)”是对峙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方的博物馆、美术馆里看不到在生活中有用的手工艺作品。这种形制早在古希腊的文艺女神(缪斯)所掌管的“七艺”——历史、诗歌、喜剧、悲剧、音乐、舞蹈和天文学中就已成形。③李修建:《序》,载[英]罗伯特·莱顿《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李修建编选、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至于“有用”的手工技艺,不管是抄写员还是木匠,都是“卑贱的”,他们甚至不适合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艺术”成了“自由”的艺术与“奴性”的技艺之区别。④[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中国则不然。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是“务实”的,有“用”才“美”,“美-用”同构。任何与中国古代文物相关的博物馆里都少不了“礼器专区”,那些诸如“尊”“鼎”“爵”等礼器,无不因“用”而“美”。分类方面,中国也自有一套体系;《尚书·尧典》这样开篇: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促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义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段话阐释了中国“藝術”的发生道理:天帝承自然,按时节,取法天时与地利,遂予百业兴盛。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艺术”尽在“百工”中,而中国的“百工”又皆为“有用”者。比如,由于中华农耕文明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衣食”“温饱”之生活必需也构成了艺术上的“耕织”主题(男耕女织、“牛郎织女”),最典型的当数中国古代以耕织为主题的《耕织图》,尤以南宋的楼璹《耕织图》为著名,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独特的“耕织图现象”。⑤南宋时期楼璹绘制《耕织图》,并呈献给宋高宗,深得高宗赞赏,并将其《耕织图》宣示后宫,一时朝野传诵,自此“耕织图”主题和《耕织图》绘画也成了中国绘画艺术史中一个独特的现象。——笔者。
(三)“人类学”视野方面
人类学有一个学科上的“规约”:研究对象在时间上侧重于“过去”,在空间上突出“边缘”。这也决定了人类学与“原始艺术”有着天然的缘分。“现代艺术的发展和‘原始’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清楚地揭示了艺术与人类学的这种关系。”⑥[美]乔治·E.马尔库斯、[美]弗雷德·R.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梁永佳译,王建民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人类学在研究上有一个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原始主义”(primitivism)。在这方面,美国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堪为典范。他曾对北美西北海岸部落的各种艺术风格、工具、装饰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不仅研究当地原住民的“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留下了大量艺术遗产方面的著述,①Franz Boas,Primitive A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还监督美国自然史(Natural History)②Natural History亦翻译为博物学。——笔者。博物馆中大量相关原始艺术作品的遴选、收集和收藏工作。③Aldona Jonaitis,Art of the Northwest Coas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xiv.
然而,当我们使用“原始”概念时,却清晰地瞥见“现代”的身影,特别是在艺术形态和形式中。④Robert Layton,The Anthropology of Ar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1.在西方历史上,“原始文化”是“原始主义”的具体体现。时间上,它针对“现代主义”;关系上,它是一个“对话性分类”(a dialogical category)。⑤Fred Myers,“Primitivism”,Anthropology,and the Category of“Primitive Art”,In Chris Tilley,Webb Keane,Susanne Küchler,Mike Rowlands and Patricia Spyer(eds.),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SAGE Publications,2006,p.268.因此,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的研究视野,以及对民族艺术的擅长还潜藏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与文字表述“对话”和对文字话语的批判。⑥参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E.马尔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作为常识,文字表述只是人类诸多表述方式之一种;由于文字与国家政治、印刷技术相结合,遂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性权力表述。然而,在“史前”(特指文字出现之前)社会,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艺术”。对于它们的研究,人类学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二,人类学、民族学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形成了民族艺术学的特色,有助于对族群文化、地缘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艺术的“多样性”除了强调“民族-族群”之外,还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即地方性、区域性:“区域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这是因为每一个区域都有它自身的情感价值。在各种不同情感的影响下,每一个区域都与一种特定的宗教本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赋有了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具一格的品性。正是这种观念的情感价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观念联系或分离的方式。它是分类中的支配角色。”⑦[法]爱弥尔·涂尔干、[法]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而族群与区域又成为既融合又区隔的“边界关系”(boundaries)。巴斯认为:“民族确认的最重要价值与族群内部相关的一些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建立其上的社会组织同样受到来自族群内部活动的限制。另一方面,复合的多族群系统,其价值也是建立在多种族群不同的社会活动之上。”⑧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p.19.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艺术学也要将地缘性艺术包容其中。
中国的族群(人、人群)来自古代“一点四方(五方)”,即“东西南北中”形制,不同的民族、族群与地方、地缘保持着亲缘关系。虽然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迁徙民族”“游牧民族”等,都不妨碍在族群的“边界”确认中所包含着“地方-地缘”因素。所以,“民族-族群-地缘文化”也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单位范式”:“在当代人类学的分析中,地缘性(locality)无疑成为一个关键性视角。”⑨Marilyn Silverman and P.H.Gulliver,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ic Tradition:APersonal,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Account,In Marilyn Silverman and P.H.Gulliver(eds.),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24.所以,当我们将目光投视于“民族艺术”的时候,“地方性族群”所表现的“地方艺术”无疑成为重要的投视点。
概而言之,“民族艺术研究”仿佛是文化之于镜像,有形象,有景象,有具象,有抽象,有印象,有幻象……民族艺术的多样性嘱托民族艺术学致力为之。这也是中国当下语境的一种特殊表述。
结 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繁荣和发展也成为中国民族艺术学重要的历史契机和认知形态。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自在”与现实“自觉”的格局中,中国的民族艺术研究尤其需要凸显“两翼”:政治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体性,艺术上真实地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多元性。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艺术学重要的价值追求和学科的格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