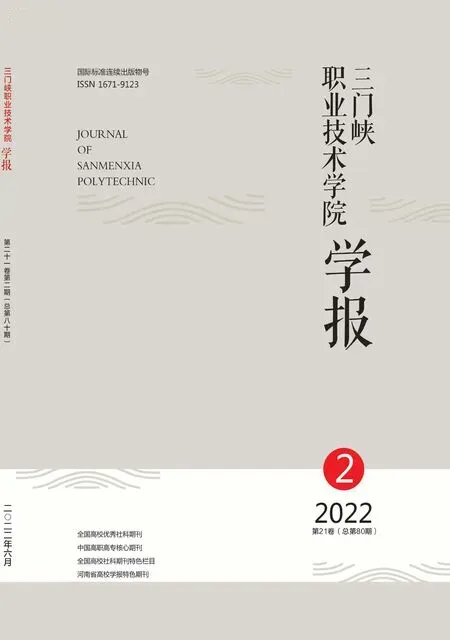古代洛阳私家园林的文学书写谫论
◎钱 伟 王雨晗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阳 550025)
一、天下名园重洛阳
洛阳位于黄河中下游,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一直被称为“华夏根脉”。历史上,夏朝、商朝、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共计13 个朝代先后建都于此。
作为京畿之地,洛阳城郭巍峨、宫阙壮丽,文化昌盛、名士云集,其繁华正如明代文人李梦阳所描述“洛阳亭榭与山齐,北邙车马如云逐”。昔时衣冠人物、文人雅士常在此营建私家园林作为欢聚宴饮、隐居休憩之所。洛阳私家园林因而繁盛一时,其风格或规模宏大、奢华壮丽,或精致典雅、灵逸隽秀。这些园林“虽由人作,宛如天开”,对文人墨客而言,不管是隐居避世、寄情山水,还是风流雅集、纵论诗文,皆为理想之所。
关于洛阳私家园林的文献记载始于东汉,至魏晋、唐代和北宋最为集中和丰富。历史上,洛阳私家名园的主人多是政坛名流兼著名文人,他们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描绘园林风貌、体现生活态度、反映审美情趣的诗文作品。现撷取若干有代表性的私家园林依时序列述。
二、古代洛阳私家园林的文学书写举要
(一)东汉
东汉时期佞臣梁冀当政20 余年,在洛阳及周边方圆千里修建了大量园宅。据《后汉书·梁统传》载:“冀乃大起第舍,而寿(孙寿,冀之妻)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1]
文中所提的“菟苑”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描写,如《古诗十九首》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1]。崔骃《大将军临洛观赋》云:“滨曲洛而立观,营高壤而作庐。处崇显以闲敞,超绝邻而特居。列阿阁以环匝,表高台而起楼。步辇道以周流,临轩槛以观鱼。”[1]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东汉私家园林内已开始建置高楼,这显然与秦汉时盛行的“仙人好楼居”之观念关系密切。
(二)西晋
西晋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中如“昙花一现”般的大一统时期。立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力行新政、移风易俗、劝课农桑、重视生产,社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出现了10年的“太康盛世”。这一时期,豪门贵族在都城洛阳建造了大量的私家园林,其中最著名、最奢华的当属石崇的金谷园①石崇在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后拜太仆,又任征虏将军,在朝为官20 余载,攫取了无数财富,生活奢华,无人可比。后世常将石崇视作巨富的象征,将金谷园作为奢华园第的代称。。
关于建造此园之缘由,石崇在《思归引》的序文中说道:“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石崇还在《金谷诗叙》中详细描述了此园之景象:“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2]
与石崇交往密切的潘岳亦有诗咏此园之景物:“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所。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保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2]
唐代诗人李益的《上洛桥》中“金谷园中柳,春来似舞腰。那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3]描绘了园中林泉丘壑、河岸柳明的盛景。阳春三月时的金谷园赏心悦目、风景宜人,被称为“金谷春晴”,列“洛阳八景之一”。
除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色之外,金谷园还因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情故事而被历代文人墨客津津乐道。据史载,石崇有宠妓名绿珠,美而艳,擅吹笛。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专断朝政,派部将孙秀去索要绿珠,石崇出其园中数十名美婢艳妾,任孙秀挑选。孙秀却说,自己是奉命来索要绿珠的。石崇怒斥之:“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于是,孙秀回告司马伦,赵王不罢休,又派人来抓。石崇对绿珠说,我因你而获罪。绿珠泣答:“当效死于君前。”言毕,纵身从楼上跃下而死。
这段凄美故事,历代文人咏叹不绝,留下众多诗文。其中,唐代诗人杜牧的绝句《金谷园》流传最广,诗云: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2]
杜牧另有一首七律《金谷怀古》,诗云:
凄凉遗迹洛川东,浮世荣枯万古同。
桃李香消金谷在,绮罗魂断玉楼空。
往年人事伤心外,今日风光属梦中。
徒想夜泉流客恨,夜泉流恨恨无穷。[2]
金谷园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据史载,石崇与刘琨、陆机、陆云等24 人常聚于此园吟诗作赋,史称“金谷二十四诗友”。他们几乎涵盖了西晋所有的重要文人,是当时文坛的缩影。耐人寻味的是,太康文学风格特点也与金谷园的审美特征如出一辙,均崇尚形式华丽。
除金谷园外,另一处洛阳名园是潘岳的私园。他在《闲居赋》中云:“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樆,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溧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4]这段文字描述了其在庄园中的惬意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西晋国祚短促,很快便消逝于历史的长河。及至东晋,只余南方半壁江山,北方则陷入混战,其间虽有国君兴筑大型苑囿,却难见对于私家园林的记载。
(三)北魏
孝文帝迁都后,洛阳作为京城,社会经济繁荣,私家园林兴盛。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①《洛阳伽蓝记》是北魏之际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体的名著,后世将其与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中这样描述:“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5]同书还详细记述了司农少卿张伦的宅园:“敬义里南有昭德里。里内有尚书仆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尚书崔休、幽州刺史常景、司农张伦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俭素。惟伦最为豪侈,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相属;深蹊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5]
由此得知,北魏时期洛阳的私家园林中已出现了叠石假山。人们借助人工叠山理水的造园手段把广阔的大自然山水风景缩移模拟于咫尺之间。叠山理水的创作往往既重视物境,更重视由物境而幻化、衍生出来的意境,即古人所谓的“得意而忘象”。
(四)唐代
有唐一代,太宗、高宗、玄宗10 余次从西京长安到东都洛阳“移都就食”,武则天在称帝之后则将都城由长安迁往洛阳,还赐封了一个霸气的称号“神都”。由于政治地位的加持,唐代洛阳的城市发展很快进入鼎盛期,同时也迎来了园林营造的高峰期。对此,唐代文人宋之问有诗赞曰“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北宋晚期文学家李格非则在《洛阳名园记》中记述:“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6]其中最有名私园当属白居易的履道坊宅园与李德裕的“平泉山居”。
公元824年(长庆四年),白居易在洛阳购置履道坊①据考古发掘,履道坊的位置约在今洛河南狮子桥村东。宅园,在此植树、种花、挖池、建亭、开路、筑桥,晚年在此病故。其诗《池上篇》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7]这俨然一副悠闲自在的隐士园居图。
除了城内的履道坊宅园,洛阳南郊也有一所著名的私园,这就是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山居”。李德裕常和文人名士在此园饮酒唱和,共赏风光,留下洛阳八景之一的“平泉朝游”。江南的“珍木奇石”在当时深受文人士大夫的爱赏。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李德裕以洋洋自得而汪洋恣肆的笔墨罗列了这些“珍木奇石”,摘录如下:
“予尝览贤相石泉公家藏书目有《园亭草木疏》,则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 予二十年间三守吴门,一莅淮服,嘉树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于樵客,始则盈足,今已丰寻,因感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荪荃之美,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
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稽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柽、木兰、天日之青神、凤集、钟山之月桂、青飕、杨梅、曲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栾荆、杜鹃、茅山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
其水物之美者:白苹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白莲、茅山东溪之芳荪、复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在焉。 其伊、洛名因所有,今并不载。岂若潘赋《闲居》,称郁棣之藻丽;陶归衡宇,嘉松菊之犹存。 爰列嘉名,书之于石。[8]
李德裕完成《平泉山居草木记》后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又撰写了《平泉山居诫子孙记》一文。通过此文,李德裕试图告诉后人,此园是隐居养德、远祸避灾的世外桃源,希望它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遗憾的是,其子孙虽然读懂了先人的心思,但无法完成其愿望。唐朝末年,战乱频繁,洛阳数度陷入战火,平泉山居也难幸免。无园可依,李氏后人可念的唯有李德裕的系列文章。
《平泉山居草木记》在后世备受重视。其原因在于:一是人们倾慕李德裕的为人,如唐末诗人李商隐在《会昌一品集》序言中将其誉为“万古良相”;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更是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为古代六大名相;二是《平泉山居草木记》所记载的园林植物对后世博物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兵火燹焚以后,洛阳已无盛唐时的气象,后又经唐末黄巢、秦宗权之乱,城市更加残破,如《旧唐书·哀帝纪》中所述:“(唐末)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9]
(五)北宋
北宋时期,经济、文化发达,文人的社会地位较高,文学艺术从雄健豪放转向婉约精致,社会普遍讲究饮食、服装、用具的品位,流行饮茶、熏香、赏曲等风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富庶为私家园林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司马光在《看花四绝句·其一》所云“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胜墙里看”即为明证。
《洛阳名园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洛阳最著名的18 座私园。其中,最被李格非称道的是司马光的“独乐园”。①独乐园系司马光在熙宁六年(1073年)修建的园林,其遗址在今洛阳伊滨区诸葛镇司马街村。 此园因诞生了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宝”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而名声大噪。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②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王安石产生了严重分歧。 改革派王安石力主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尽快改变北宋积贫积弱之局面,而保守派司马光则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政坛失意,于是退居洛阳,在伊河南岸建造独乐园作为著书会友之所,“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10]。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解释了此园得名的由来:“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10]这段话暗示了“独乐”系反用《孟子》中“与民同乐”的典故,看似消极无为,实则蕴含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追求,彰显了园主通达的个性气质。
遗憾的是“酒有兼旬绿,花无百日红”。自北宋以降,古都洛阳如夕阳西下,暮霭重重,逐渐褪去往昔的辉煌与艳丽,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沧桑巨变,正如司马光所云“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三、园林与文学的关系摭论
(一)园林与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上文对洛阳古代私家园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意识到园林和文学虽分属不同艺术门类,但其同步发展、互相参悟、触类旁通的特征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多是“诗文园”或“哲理园”,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事实上,在对园林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古人早有精辟见解。如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妙喻“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11];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则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错杂,方称佳构。”[11]这些话深刻道出造园和诗文在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处,二者互相影响和作用,可互通互鉴。
(二)文学书写赋予园林不朽生命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文学书写的传统。曹丕在《论文》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代洛阳私家名园得以传世,文学作品功不可没。古人创作园林诗文的热情不仅是因其喜好园林,更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实体园林常兴废于倏忽,唯有文字可使其恒久流传。因此,古人常将园林传承的希望寄托于诗文之中,期待后人能通过阅读诗文来畅想昔日的园林胜景。事实上,今人正是通过《金谷诗序》知晓金谷园的名流吟咏之兴盛;通过《池上篇》感受白居易“中隐”之意境;通过《平泉山居草木记》了解李德裕对珍木奇石的痴迷。
(三)文学书写赋予园林文化意义
古代文人群体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文化优势和科举为官的权力优势,能获得普遍的社会关注,其园林也因此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古代园林诗文的主旨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不在于对园林的传颂,而重在对园主志趣的表达,所谓“物不自美,因人而彰”也。长期以来,园林被视为主人道德、品行和功业的象征,园林的地位深受主人的声望影响。因此,人们对于园林的评价有时并不在其花草、水石、建筑以及布局,而是生活于其中的人。这既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也是文人一贯遵循的价值判断。
总之,古人在洛阳园林书写的过程中,一方面借助华美的文辞使园林成为后人心驰神往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借助诗文创作体现自身的价值追求,标榜道德功业。园林就是在这样反复的题咏和称颂中,超脱于实体本身,成为被追慕的对象,获得了显赫的声望,化身为不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