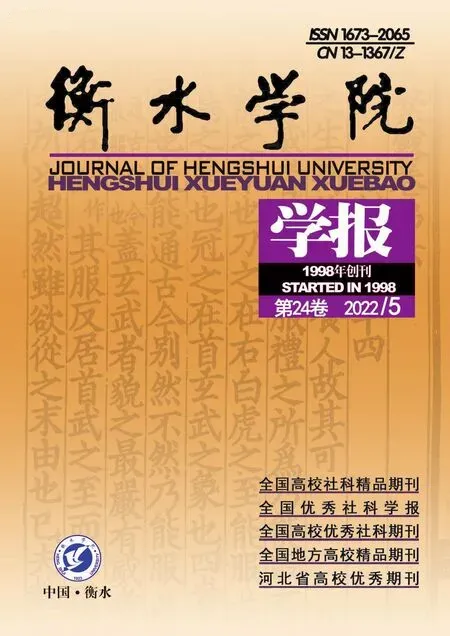中西哲学互镜下的孟子人性论新诠
罗惠龄
(浙江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及语言使用,相较之下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什么(What),用以穷尽系统性的知识理论来对存在界作为本质性的终极说明;反观中国哲学却是着重怎样(How),敞开教化之学,而非是作为系统性的知识理论。
一、中西哲学的实践进路
20世纪后的哲学家痛切深刻地反省“人”的这个议题,因为过往的基督教传统认为人是具有原罪的。从柏拉图开始的希腊典型的观点,认为人基本上是由灵魂与肉体组合而成的,大部分的希腊哲学家相信灵魂是属于精神,有了灵魂便是价值尊严的可贵所在。灵魂与肉体相互结合的今生今世,主要表现在理性的活动上,反观感性则无法彰显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与价值,这便是希腊哲学的灵肉二元论。到了笛卡儿开始的心物二元论是由心灵和物质所构成,真正的尊严与价值代表着人的精神,而所谓的心灵则与物质无关。于是,对于人的心理层面构造皆以理智、意志、感情三方面来加以区分。
中国哲学在谈及知情意时是相互渗透影响的。王阳明所言的“主于身也,谓之心也”[1]74“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1]140,意思是儒家的学问是一套身心之学,在心上用力可也从不荒废身体。因为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甚至身心是能够相互渗透的,一如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志壹则动气(《孟子·公孙丑上》)。心智集中同时改变我们的形躯,而当形躯专务一致时,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智。因此,孟子一方面强调大体和小体、心官及耳目之官,看上去好像截成身心二元区分,却能够清楚地感受在孟子的引领下,从不间断地强调心灵,而与身心相互渗透并理解的传统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一开始便是要拯救现象世界,要为世界找到一个能易理解的必然是恒常、普遍、固定及不变的秩序。举例来说:潜能(potency)这个概念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的概念,而如何去为这个变化做解释,便是要将它化为一个能够被理解的真实存在。首先,一个事物的构成原理即“潜能”和“实现”,将其潜能充分地完成发展和实现,便是作为成就圆满的实践;其次,因为变化始终是为理性所困扰,一个事物的充分实现便是取决于它的本质,这个本质通常是作为这个事物的形式因。换言之,假设作为一粒苹果的种子,如何能够理解它在摒除外力干扰之际(如:狂风暴雨、被鸟啄食……),能够顺理成章地发挥它的成长而使之成为苹果树。在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里,指出了“实现”原理必是先于“潜能”。理解事物的潜能,必须得以充分彰显并实现发挥才能够得以理解。所谓的“潜能”,若无外力的介入干扰,便注定是且也只能是成就它的“实现”。一个事物最终必然是顺着它的本质去发育成长并完成的,它的本性也只能由苹果种子发展成苹果树,而无法成为别的,也不允许是别的。
苹果种子与苹果树的关系,作为这个实现是没有创造性的,潜能的实现是派生关系的生物,仅仅是将生物的本质充分地豁显出来。“本性”便是作为一个外在最高的创造本源所赋予事物的既定潜能,这样的本质终究不过是上帝的创造赋予,只能是服从实现而无法扭转更动,最终也仅能实现那个不会是创造第一义的事物,是属于第二序的,非为自主性的创造。由此得知,“西方文化实有神道与地道,而无真正之人道。所谓人道者,除吾儒之主立人极,言心性外无他,他人若无此智慧此情感,则世界悠久和平不可能,世界亦终究是悲剧”[2]192。
反观中国哲学从来没有像希腊哲学般地将灵魂肉体、理智感性作为这种迥然严格的二分,这种绝对二分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实是不相类属的。孟子的“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说的并非是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依旧将尧、舜两位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人性的典范,特别是这个“性”的概念作为动词用法的出现实属罕见。孟子所谓的“性”即是一个实现的过程,而别于西方哲学注定成就的意义上的给定。
过去一百年来,哲学发展迈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处境。当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化侵袭,西方哲学之于神及中国哲学之于天的挑战,不可免俗地以各种带有浓厚西方哲学意涵的语言来诠释中国哲学。于是,当我们面对一知半解却又照单全收地来加以诠释自身时,就人与人的共通性来做出强加的理解区分,皆是对于人性造成扞格不入的扭曲扼杀。
换言之,中国哲学是一套教化之学,“它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它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3]7。它更强调成德之教,在生命实践的过程当中作为圆成天人合德的最高智慧。对于孟子所描述的圣人人格,“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全幅展现举手投足尽是道德光辉的发露,这便是所谓的“浩然之气”,即是人性于人的生命行动展开的生命场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孟子·滕文公上》)便不是某种被预先给定的“本性”,而是一个真实受到尊崇欣赏的典范人物。由此可见,见贤思齐的成圣仿效中,人的生命尽可以于人文生活世界中敞开,而在历史的不断生成变化发展当中,得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意义价值。
二、上不在天的超越失坠
西方哲学通过对于事物的分类、范畴,标定出一个事物是什么,从而掘发事物的本质。追溯存在的原因便是来自上帝的创造,也就是西方哲学所谓的“本质先于存在”。西方哲学中的19世纪的欧洲人,在过去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直至工业革命以来,对于文明的进步主义充斥着乐观自信。一如孔德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人类历史循环将经历三个阶段发展:“即宗教—神话—宗教的神学阶段、哲学形上学阶段与科学实证阶段”[4]327。人类历史的脚步不断地从蒙昧的宗教信仰渐次以其哲学理性进步抬头,到了启蒙运动之后进入了科学理性的全盛时代。随着工业革命发生的不断进步,在此乐观主义涌现的氛围中,其生活方式早已与公元1、2世纪的欧洲大相径庭。因为当时还在基督教文明下的欧洲人,对于人生活于当下幸福的认知并非是今生今世,而是在彼岸的世界。因此,相对于早期的基督徒而言,人所能希冀的幸福绝对不会是发生于现世的当下,而是死后经由上帝审判进入了天堂之后,以一种最简陋的生存环境支撑,并拳拳服膺于价值信念的源于彼岸世界的幸福。
哲学家最大的兴趣即是对于林林总总的事物,通过本质的发现,将其纳入分类范畴当中,从而加以确认固定。人类知识活动化为两个基本要件:其一是以简驭繁;其二则为以静制动。如同对于一张桌子而言,一旦它取得了桌子的性质和结构,它便因此成了桌子,而不需要担心将会成为什么。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事物的本质运用重要的知识活动而将其置于框架,分门别类地理出秩序眉目而予以固定下来。通过一些共相、共通及普遍性而将事物的差异性给排除,不允许也不能够是别的。上帝根据西方神学作为一个无限的完美者,它便是一个不需要担心会成为什么的一个全全然然的上帝。
笛卡儿的至理名言“我思故我在”,怀疑便是一种思维,是第一真理。可作为思维我又该如何展开对于世界的说明呢?因为思维我这无限完美概念的另一含义便是上帝。上帝作为一个无限完美者,倘若它仅仅存在于我的思维里,而非是存在于真实的世界。这样一来,它也不可能是真正无限完美了。原来思维我的概念反映出上帝一定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存在,作为一个创造世界的无限完美的上帝,它将怀疑的世界拯救回来,上帝的存在是靠着思维我来得以存在。因此,思维我比上帝还具有其知识的优先性。到了19世纪,人类的理智已然从宗教的蒙昧当中解放出来。理智能够看透整个自然世界的律则,并通过技术研拟的掌握开发,遂将整个自然界化为完全为人所用的资源。作为19世纪存在主义先驱者的尼采言之的“上帝已死”[4]352,宣告人类就是上帝,所谓的幸福,便不再是需要等待上帝救赎之安身立命的信仰。
作为人的生命在天地人我之间展开的过程当中,因为整个人类文明快速地发展进步,让我们在传统生活里的人我之间关系开始解构。从前根据人我认识关系的理解,到了19世纪,随着文明快速的发展而与之崩塌。天不再是以前的天,天地人我亦面目全非,对于自我的认识也产生了模糊。比如天是神圣超越的世界,在人类历史的文明当中,在长期的发展下都会有一个超越的世界,借以代表着活在天地支撑的理想。科技长足的进步,发现整个自然世界皆在我们充分的认知下,让它为人类的福祉而服务,所要追求的快乐幸福也无须等待死后的上帝审判,便能够夙愿以偿地步入天堂之境。我们尽可能地凭借着我们的理性发展,于今生今世享有着幸福快乐。于是,相较于传统信仰,开始有了怀疑的态度。因此,超越的上帝已然不再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凭借与依靠。
上不在天,指的是人类生存世间需要有的超越神圣的世界,可是这个神圣的世界却是失坠了,何以故?对于人性“扩充,不仅是精神的境界,而且是要见之于生活上的实践。……由存养而作不断地扩充,扩充到底,孟子称之为‘尽心’”[5]180。换言之,尽心不是仅仅局限于内心的一种自觉能力,不能只是一种人性精神的境界,而必须是在通过现实中的具体实践才能得以呈显其张力。因此,“孟子的尽心,必落实到践形上面,……践形,乃是把各官能所潜伏的能力(天性)彻底发挥出来,以期在客观事物中有所作为、有所构建,否则无所谓践形”[5]185-186。因为整个真实的世界便是在生灭变化当中呈显,一如10 岁的我、20 岁的我……,其容貌、心态、思维,经历不同变化,有了很大的差异,但究竟哪一个阶段才是真正的我呢?意思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那个贯穿于10 岁的我、20 岁的我……,那个属于并保有我的那一部分的层面。虽然我和你同样是人,你我皆有着共同共通的部分,但是显然我和你仍存有着极大差异,比如说高矮、美丑、胖瘦……。所以,一旦讨论本质,便是指那个可以经历变化,却又能够确认的是这个事物就是这个事物,而非是别的物种的那种普遍、同一的部分。你我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你我之间却有着共同之处,即是“人性”,而此人性是普遍的,它是能够在经历变化且在变化当中保持不变。倘若它改变了,那将衍成不可思议的终结,遂无从辨识你我是谁了。尤有进者,不论我处于几岁的样态,我仍旧是我。在变化当中仍有着不变的部分,即便我和你有其差异,但是我们皆属于人,何以故?因为我们拥有着共同且同一的部分,即是我们常言的“本性”抑或“本质”。
10年前后的我的容貌、心态、思维肯定是不同于今的,因为人在时间的变化当中,呈显出不同于以往的千变万化。唯独作为人的你我,却是注定无所逃地必须去关心并成就未来的我们是什么,以及将会是成为什么的开放性问题。因此,只有人在天地万物当中会形成一种自我的投射关怀,不断地对自我形成诠释做出选择的叩问,并通过实践完成属于自我的成就。换言之,活着,便是不停地自我叩问、抉择、成就……,作为孟子人性论下的存有,能尽其所能地将天地敞开并赋予动态的意义。人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下去领纳、迎接造物主丰富蕴藉的生命意涵,这便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哲学的殊胜之处。
中国哲学于传统中论及人性,极易紊乱于西方哲学的超越世界,沉醉于形上学领域而与之天道背离。孟子人性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并以天这个范畴为其基石从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的天人合一,就是在天与人性的道德意义上提炼出来的。孟子把天与人性联系起来,扩充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是故“尽其心者,知其性者;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主张心、性、天的同一,终将尽心即能知性,知性明其知天。由是,若我们对于传统认知的人性,如同西方哲学所言的普遍天生的本有认知,即本身具足、不假外求的本质潜能,仅需觅寻并扩充人性,即能完成成圣成贤的工夫。试问,人性果真如此简单易取吗?唯有正视上不在天的超越失坠,面对西方哲学传统将人性视为一种静态且内在于人本有潜能的错误,予以修正并加以重铸厘清,才能缔造那种属于动态、超越、变化人性的所有可能。这种丰富的可能性,亟须人们不断地在剑及履及的实践中开显,并完成本真存有的理境与意义,才能够是成就自我最大圆满的可能性。
三、下不在地的自然失衡
西方文艺复兴后数学物理学的兴起,认为整个物理世界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一个被数学定律量化支配的物质世界。支持哥白尼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伽利略,以为这个世界是上帝运用数学原理所创造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过后进入工业革命,19世纪的欧洲人认知的自然世界,就是一个可以完全用数学公式表达物理定律,从而决定智慧的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所以,整个地球是纯粹理性认知的对象,是一条数学公式,是物理化学结构,人类可以透过科学知识去揭露的内在结构,因此,仅具有工具价值而等待我们征服它,让它们为我们所用,这便是我们和自然世界的关系。
存在主义的先驱“齐克果”[4]334-339,认为欧洲经过了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的带动,整个都市文明开始集中。以往在农业文明下,人类散落在大自然依山傍水的环境中,是群聚而自然紧密的依存关系。当工业革命通过了机器劳动,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而创造了价值,人们便离开乡村集中于都市生活。随着生存形态发生变化,人际关系和信仰模式亦随之改变。白天过着劳动或是从事商业活动挣钱,到了假日,却又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前往教堂讴歌祷告,并于忏悔中重整精神心灵的净化,而大异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模式。于是,齐克果便开始反省:“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平日的声色犬马,假日的讴歌忏悔,如此一来还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基督徒吗?这其实也反映出在此都市文明当中,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虽然彼此家庭背景不同、长相不一,可在更多的时候因为随着大众流行、吃喝相同,再找不回一个活活泼泼的活的真实个体,便顺理成章地冠上类化一致的标签。于是,到了20世纪工业革命后科技文明的加速,回不去亲密如昔的自然世界,下不在地的价值崩塌后,便开始有了深刻痛切的反省。
自然世界之于我们,纯粹是等待人类去加以认知理解并征服利用的一个隶属于资源的世界吗?这个世界仅仅只是一个作为被撷取掏空的资源世界吗?张横渠所言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生命倘若缺乏父母的生养是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如这个自然世界有其真实的生命,它是我们的伙伴友朋。于此,儒家更加扩大反省,假如缺少自然世界,根本不存在我们。因为自然世界提供给我们生活必需,所以中国哲学总是强调敬物、爱物、惜物。“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由此观之,孟子强调的人性即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友善关系,绝不仅是理所当然地将它视为一种认知的对象,一个具有工具价值的资源而已。艺术生命情调充分展开的时代,人的生命情怀亦希望在此世界中发光发热,在诗的浸濡蕴蓄下,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整个大自然中的山水情趣,即是人类生命安顿的栖息所在。因此,我们用孝敬的心来孝敬父母,同时也必须要以敬物、爱物、惜物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藏修游息,即安顿、即游玩、即休憩。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之中”,这便是中国哲学勾勒出来的自然与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
可如今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越来越难以理解了。比如在南亚海啸发生时,在那滔天巨浪的冲击下,曾经以为的自然世界是如此安定安全,为我们尽情索取挥霍的资源,那样规矩的臣服于我们的理智规范之中,竟在猝不及防的瞬间,毫不留情地天摇地动起来。迄至现今,自以为是的观察、解释、预测,构成了整个西方科学文明进步的精神标杆,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下,将整个世界纳入被人理解的框架范围。可到了最终,无论科学再进步,也是无从做出精准的预防措施。
世界果真能被我们预知而得以全知吗?西方哲学执意将所有的不可测性全都化为可测、可预期性。若我们的人生不断地被环境牵引拉扯,理不出自我的方向,便看不到它庄严动容的意义价值。可一旦落入已然被我们完全预测时,这个世界的变动性将因此被取消,变成了只能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透显出“在孟子的观念中,天地所造化的自然世界,与君子所教化的人间世界,并无任何实质上的差异”[6],他们都来自自然世界的创造,贯穿着人文世界的秩序,因此才有所谓的“浩然之气”能够“塞乎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而君子的“存神过化”(《孟子·尽心上》)亦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如何为自己的生命做主。由是,在孟子的人性论述中,不仅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不隔,且是即存有即价值,整个人文自然界都洋溢着创造生机的美好。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孟子一文中揭示了人性即是此山之性,是超出基本状况之外的文化和特性。对于此山而言,那些覆盖其上的树木是自然的,并非为西方哲学所谓的本质上的天赋,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美化、全化或善化(refinement)。山经过了培养润泽,山之性已非山本身,而是成了山林,指的是呈现在其上的树木。并非本身具足、天生存有,而是在不断的变动发展当中,成就那些美化、全化、善化,据此而丰富这座山的所有要素。
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富足,同时也衍生诸多存在的不安全感及与日俱增的文明匮乏。不断进步的文明世界,快速变迁的不确定性,又将引领我们置于何处。今日科学技术是西方哲学长期于历史发展中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样的发展当然有其动人的一面,但是它在人类生命所造成诸多安全匮乏的限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诸科学将依据科学规范……对那些只被允许有一种控制论功能而被剥夺了任何存在论意义的范畴的假设”[7]。按海德格尔的说法:“科技便是将存有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储存之物。”指的就是对造化形成过度理解的“资源”。换言之,面对自然世界的生成变化,自然世界的不可测性,对于下不在地的内在失衡,解决的方案便是重新检讨。倘若一味汲取西方哲学而抛掷中国哲学自身的丰饶价值,无疑是缘木求鱼。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永远都要保持着开放谦卑的亲和力,才能在历史长流当中共生长存。
四、丰富蕴藉的生命缺口
西方哲学特别看重理性,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尊严源于理性。可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能够拥有无法于生命任意抛掷割舍的他者。于是开始重新探索理解,天地互镜下的展开意义即是生活态度,是一种表现于人的生命力中的自我反省。而孟子人性论中所彰显的哲学价值,便是要求我们做出心灵的探索,让心灵拉开高度,高到能够俯瞰各式各样的生命经验。不但反省自我,也参酌他人,观照往圣先哲的人物,将其过往的历史经验收摄仿效。换言之,不断地让心灵跃升,于混乱的生命风暴中理出头绪,找出领悟的规律,并在这些抽丝剥茧的条理眉目中,让过往的先圣先哲成为照明的灯光。得出历史精彩的跃动趋势,让心的生命缺口光明起来。
“依吾人之意……首非将人或人性,视为以所对之客观事物,来论述其普遍性、特殊性,或可能性等,而主要是就人之面对天地万物,并面对其内部所体验之人生理想,而自反省此人性之何所是,以及天地万物人性之何所是”[8]。人性考察天地万物,存有在此得以显现。人的可能性,不仅基于假设推理的方法得以客观认识,亦是能够开显、揭露并领纳人之所以为人的存有意义。换言之,只有人性才会探问存有,并将此能力发挥作用。因为一件事物的存在并非是无理的存在,它肯定是以某种特定的意义被接纳理解,而进入生命当中。如同中国哲学喜谈的天人合一,是从天来理解人的不同之处。因此,人更能够顾及天地万物,一旦敞开天地互镜下的人性,便是进入爱物惜物之境,人性便如造化天地万物的心一般。孟子是从人、人与天及人与地的关系当中来理解人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第二十章》),理解人的所有须回溯到天来作为理解人、人和天的那种特殊的关系。唯有不断地敞开自己,爱人敬人、敬物惜物来成己成物,作为自我实现中仿佛如同和天地一般的存在,便是在天人合一,天地不断生成变化当中的脉络下,去理解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
西方哲学的理论立场是用本质主义,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道德都有着一些本质性的看法。根据这个原则所衍出本质性的看法,究其实也只能是这样做,而不能是那样做。其结果不是错,便是对;不是道德,便是不道德。中国哲学就不是这样的形态,因为它并没有那些不变的本质可以作为那样的要求,它并不那样在乎要提出一套标准,而在乎的是要如何涵养开发并修养自身。因为生命所积累的深度和厚度,总是让我们面对环境挑战时,予以充分的发挥掌握,并在当下做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尤有进者,作为一个有修养且对于历史脉络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以及身处当前处境的复杂性而能够全盘掌握的人,必能找到一个对于现阶段而言的最佳解决方案。
让人性保持着最大的弹性,避免让自己被意、必、固、我的观念所限制,避免人性在天地互镜下的冲突关系中,对生命形成焦虑痛苦的诸多制约。中国哲学中的人性,是静待生命的展开,是迎向生命的不同,去对它进行体贴的领悟、领纳、欣赏并歌颂赞叹,从而成就一个大自在的生命。如此一来的一个大自在的生命,便是让自己的生命,于天、于地、于道、于造化中而与天地同流,和造化同感。最后,也都将在历史脉络的存在当下,保留着一个缺口、一份空虚,在未能填补的理趣下彰扬人性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更有空间余地,容纳把握出与我不同的样态。敞开孟子人性自我,并如天一般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