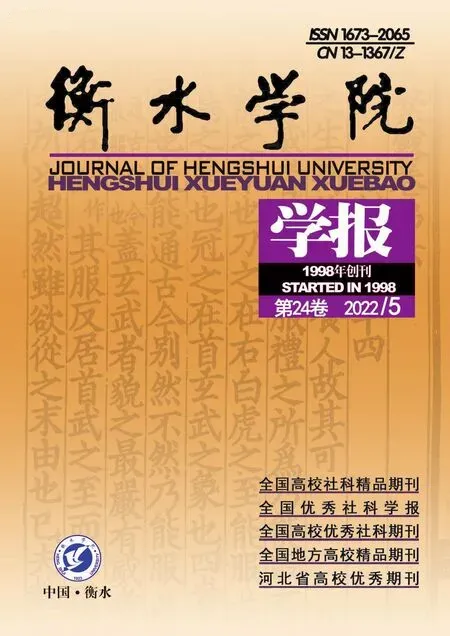从“天人”合一到“天仁”合一
——董仲舒仁学一议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董仲舒是儒学史上天人合一论的重要代表,他所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曾长期被视为维护古代社会制度的教条。但是,天与儒家的核心范畴“仁”是何关系,董仲舒之前的诸子论说,对此虽已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总体上还处于萌芽阶段,董仲舒是首先将本源性的天与儒家仁学直接关联并为之进行系统论证的哲学家。
一、董仲舒之前的天仁关系
董仲舒之前,儒家对于天与仁之间的关系,一般多属于间接性的思考。“仁”的观念,不论是作为情感、德性还是境界,主要是在“人”的视域下被理解和运用的。孔子答“樊迟问仁”的“爱人”,孟子概括的“仁者爱人”,以及《礼记·中庸》讲述的“仁者人也”等,都是对这一情形的典型概括。
但是,“仁”与“人”之间的关联,并不能直接过渡到“天”。作为仁学奠定者的孔子,并不以为仁的情感需要植根于一个天命或天道的渊源。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与宰我关于君子是否当守“三年之丧”的争论,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双方这里争辩的实际看,孔子主张实行“三年之丧”,出发点是人之亲情,守丧“三年”是基于父母子女之“情”而立的,非此不能表达子女对父母的真切思念和悲痛。所以,在孔子心中,“仁”的基点就是人的亲情,它集中体现了仁的“爱”的情感。宰我既然不愿意为父母尽孝而守丧三年,背离了曾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的亲情,所以孔子给出的评价便是“不仁”。
可是,在宰我一方,他所以要坚持自己守丧一年的主张,在于他不是从人情而是从天道运行的规律出发的。不论是新谷替代旧谷,还是钻燧轮流改火,天道运行、四时更替都是一年一易。“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礼记·三年问》)。天道自然循环就是一年,一年一更始;人道仿效依循天道,为父母守丧一年就是恰当的,更不用说君子三年不为礼乐而导致的礼乐崩坏了。
但宰我的立场在孔子并不能得到认同。孔子尽管“畏天命”(《论语·季氏》),强调“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但这并不等于天与人就完全一致,人道、人情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既然宰我幼年也享受了父母的三年之爱,就应该以三年之丧来回报父母,而这与天道运行的规律并不直接关联。即在仁学的层面,孔子实际上是持天、仁相分论的。
孔子坚守仁爱的人道立场无疑有自己的理由。“仁”作为人的情感世界和道德价值的集中体现,的确只是属人的产物,它与天道的周年运行并不发生关联。人道的“心安”与天道的“无情”是对立的关系。这在后来荀子,更提出了典型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人之分”(《荀子·天论》)说。但是,人毕竟生活于天地之中,人之德性在孔子亦是来源于天命;即便人的情感,也离不开在天地寒暑变迁中生息繁育的人的物质生命。考虑到这一现实,就有必要在天人或天仁之间,找到一条可以衔接和过渡的路径。事实上,接续回答孔子“三年问”的战国时期的儒者,在认识上已前进了一步,他们对之提出了“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礼记·三年问》)的消解天人扞格的新解释。即所以要守丧三年,是基于人情而在天道周年运行的基础上“加隆”,以敦厚推重仁爱自身的价值,于是倍加了守丧之年限。从而,基于人道的三年(满两周年)与依循天道的一年(周年)之间的冲突终得以化解。
但是,《礼记》对天人矛盾的消解,说到底还只是一种取巧的解释。天道与人情、仁爱究竟是何关系,还须有进一步的理论发明。先秦时期直接考量天与仁关系的,其实不是儒家而是道家,最典型的语句,就是《老子·五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生长发育万物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天地不以生养为意,万物亦无所谢答,每一物的生存价值,就体现在它当用就用,用毕自然被遗弃,并无任何仁爱恩德存在于其间。天地如此,道家的圣人也是如此。圣人效法天地引导百姓,非有心施恩于万民,百姓万民依循其禀性各取所用,其间同样不存在仁爱的情感。
圣人与天道在老子是合一的,所以“不仁”成为天与人的共性。但老子所以以“不仁”作为天人的共性,在于“仁”本为大道离散之后消极的后果,是有为而非无为,是以“人”意(私意)去干扰天地自然的常道。就此而言,孔子基于亲情区分开人道与天道,为的是维护仁爱情感的自身价值;老子基于“不仁”合一天道与人道,目的则在否定有违于天道自然的仁爱的价值。在后者,“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这与宰我立足于天道运行规律而质疑不合时宜的三年之丧,所遵循的实际是同一的思路和原则。而且,老子判定,“夫子(孔子)亦放德而行,遁道而趋,已至矣”——这符合孔子对天人关联的认可和对天意的敬畏,那么,既然孔子自己也仿效和依循“道德”,就不再应该“偈偈乎揭仁义”,其讲仁爱或兼爱就完全是“乱人之性”了①参见《庄子·天道》所述孔与老的“仁义”之辨:“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78-479页)。。
那么,儒家仁学要发展,就必须要回应老庄从反方面提出的质疑或曰启示:这就是倡导仁爱离不开对天道运行规律和“人之性”问题的认识。与庄子同时的孟子,对此已有了自己的思考。在《孟子》书中,随处可见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人心中所具仁义礼智“四德”即是性体存在的证明。仁德不再与天道相分离,“夫仁,天之尊爵也”(《孟子·公孙丑上》)。在仁学史上,孟子以“尊爵”之称突出宣示了仁的价值和地位,直接将天与仁联系在一起。但天道和仁德之间具体如何过渡,则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解说,毕竟“六合之外”的问题不是孟子关注的重点。但是,天人一致的信念和思考,的确有助于仁学理论的发展,时人对此已逐渐形成共识。在实际的理论进路上,这表现为诸子合力对此课题进行解答,以为仁爱提供宇宙论的根源。这一方面的努力,明显地表现在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上。
《易传》作为儒道各家学者共同贡献的成果,其中不少篇目涉及天与仁的关系。《说卦传》以为,圣人作《易》为了“顺”性命之理,确立起了天道阴阳、地道柔刚和人道仁义的“三才”。如此天地人“三才”虽然是并立的关系,但天道(含地道)的阴阳柔刚与人道的仁义实际已发生关联,因为他们都整合在“六画而成卦”的一卦的卦体之中,尽管相互间还是并列而非融合的关系。《文言传》相对前进了一步,它提出了“元者,善之长”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之说。“元”作为众善即元亨利贞“四德”之长,可以“统天”,天与仁在正面意义上关联起来。在这里,君子以此仁为体则足以“长人”,而君子以仁德长养人又是由乾元(天道)开始的。《文言传》还提出了“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著名“天人合德”说,此天之“德”可以融会在“四德”的界域中并因之与“仁”联系在一起。从而,圣人的诸般德性和制作既都与天德相符,其长人化民统属于“仁”之中就可以理解了。
同时,《周易》复卦《彖辞》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赞叹,这个“天地之心”就是初六阳爻。一阳于众阴之下复生,体现了天地(生生)的本性,这也就是“仁”,所以,复卦六二《象辞》谓“休复之吉,以下仁也”。“复”能休美而吉,正在于和煦阳气的复生正是仁的爱意的形象展现。所以,六二要下到初九之仁,亲仁善邻而关爱他人,从而体现出“复”的美好[1]。那么,从“复(生)”的角度看,天地之心已开始发挥出支撑仁爱的一定宇宙论效力。
可以说,从《论语》《孟子》到《易传》,其所敷陈的天与仁的关联思考,为董仲舒系统性地以天意释仁做了基本的铺垫。
二、董仲舒的“天意之仁”
汉代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是一位主要的代表。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既是理论的创设,也是现实的需要,后者即在借天意制约君权,体现了明显的爱民导向,仁学精神也在此体现出来。
董仲舒释“仁”,从天之仁开始,人之仁是由天之仁赠予的结果。他说: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2]329
仁所以美好,实在于天之美好。天之美好,就体现在天生育、抚养和成就万物上。天生育抚养万物,在《老子》已有,天地阴阳和气生物。但《老子》的生养,在体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老子·十章》),突出的是无为和自然;董仲舒却相反,他强调的是天有意识的作为。天生养万物不止不息,劳苦功高,但天却把它所做的一切举归于人,天之仁也就成为人之仁。而且,如果认真去考察天之意,就会发现此乃无穷无尽的仁德!
董仲舒将《老子》的无为整个倒转为有为,天地的“不仁”被根本转为天地之仁。但是,《老子》的天人一致却得到完全继承,而且还大大推进,天之仁直接成为人之仁。这一转换之所以可能,根据就在董仲舒的“人副天数”:“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2]318人之仁的存在和价值,不仅体现在精神的层面,它也随着天数、天志和天理的降而在人,固化为人的形体、血气和德行,仁已内化为人的现实生命。
本来,天覆育化生万物,只是天道流行的自然过程,无关乎价值。因此,《老子》对天道运行规律的概括,是具有真理性的知识。董仲舒以“仁”来概括天意,实际是把人世间的仁义忠信之德,抬高到了天“尊”的地位,从而增强了仁德的威严。至于天本身的权威性,在董仲舒的时代是不需要论证的,天就是当然和绝对。要在社会推行仁爱,借助于天的权威就既必要也迫切。
有鉴于此,董仲舒强调,人世的仁德都是摘取和仿效天意而来。他说:
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2]329-330
人既是天的副本,自然就要受命于天。但人之受命并非被动地等待天的赐予,而是主动地索取,以成就人世之仁。这从天索取来之仁,包括父子兄弟的亲情、忠孝慈惠的爱心、礼义廉让的品行,社会秩序的规范治理等整个人世间的情感、德性和价值。孔子当年斥责宰我“不仁”时相对无力的窘境,在董仲舒这里已不再存在。因为此时的人道仁爱,本来就是基于天道变化而来,上天成为推行仁爱的内在驱力。因此,人便能够凭借其广大博厚的文理智慧,与天相参。
可以说,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在董仲舒理论的核心,就凝聚在一个“仁”字上。当然,能够承担起与天相参的责任的“人”,不是普通的庶人,而是王者:“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2]330“爱利天下”,可以解释为王者承接天意而爱民利物,长养百姓,这本身属于儒家仁学的内涵,尤其是在孟子阐发他的王道仁政学说之后更是如此。但董仲舒相较孟子,更强调王者的责任,提醒王之好恶喜怒,源自天之春夏秋冬:天运适时则岁月美善,王者喜怒哀乐之发,需要像寒暖暑清一样适时变化。尽管天也有寒暑“恶岁”,但基本点在“天常以爱利为意”,“常爱”是常数,是根本,是天人之际的主题。所以,王者治国,应当坚守仁义,因此才能走向“与美岁同数”的“治世”。这可谓本质层面的“人理之副天道”[2]330。
在董仲舒,天是为民以立王的,而不是相反:“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220天既是仁德的化身,仁德的基点就在爱民,如果不能使民安乐,则王本身的设立便失去了意义,害民者受到天的抛弃,也就成为必然。天人的一致,是天道和人道的一致,是宇宙论和道德论的一致。当然,天是爱民也是爱君王的,天所以会出现灾异和惩戒,既是在维护天的权威,也是上天珍爱君王不得已而施行的手段,“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2]259。这里,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反面去体会天意的“无穷极之仁”,即为了使民安乐和珍爱君王,天真的是“穷极”了一切手段去铺陈其仁德。
三、“仁者,爱人之名也”
“仁者爱人”的命题一经孟子概括,后来成为儒家释“仁”的基本见解。“爱”无疑是人的情感,但此情感能得以持续和深化,又离不开理性的支持。情感的深化,可以有内化和外化两个面向,内化即为爱的情感寻找人性的根源,在孟子即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也即所谓“天爵”,在后来这被发展为仁性爱情说;外化仍按孟子,则由爱的情感衍生推广和落实为君王的爱民政治即所谓“仁政”,最终表现为亲亲-仁民-爱物的博爱仁说。一言以蔽之,“仁者,爱人之名也”[2]251。
从“爱人”的“名”来看,由于“我”也是“人”,“爱人”在逻辑上就应当包括“爱我”。但在董仲舒,“人”特指“他人”而不包含自我,“仁”是“爱人”而非“爱我”之“名”。这是符合孔子“爱人”是爱他人的基本蕴含及其价值指向的。进而,董仲舒对此仁爱,从内在人性的剖析和外在仁德的推广两个方面向前推进。
首先,从内在面看,重在对人性贪仁两面的剖析。董仲舒的人性说,后被通称为“性三品”。但严格地说,性只有“一品”即“中民之性”,因为上之圣人之性和下之斗筲之性都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2]312也。那么,作为仁善根据的人性,也就只能是中民之性。他分析说:
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2]294
贪仁二气在人是事实存在(诚)。天施阴阳二气,人成身遂有贪仁两性,这是人身“受气”而形成的必然。但不论天还是人,又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在天是禁阴而不使干阳,在人就是禁御情欲而不使伤善,从而使潜在的仁性终成就为现实的善德。
同时,天性属于潜在,故为内;人事则是现实,故为外。人身“取诸天”,实际又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被动意义的“人副天数”,人是天的副本,这是“天所为之内”;另一则是主动意义的人继天成事“而成于外”:“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2]297由此内外看,董仲舒并不把一切都归于天,人世的价值、仁善的意义终究还是靠人自己去造就。他又说:
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未易当也,非善于禽兽则谓之善也。使动其端善于禽兽则可谓之善,善奚为弗见也?[2]303-304
孟子善言人禽之辨,人高于禽兽在于有仁义,似乎对人之为人的本质有较深刻的揭示。但在董仲舒看来远不充分。因为,人若基于自身的品性而超越于禽兽,那禽兽也可以基于自身的品性而超越于草木;圣人还可以自身的品性超越于常人①余治平说:“孟子将人与动物比较,原则是‘就低不就高’‘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是‘性已善’。而董仲舒却积极把凡人往高处送,要求‘就高不就低’‘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所鼓吁与主张的是‘性未善’。”见《唯天为大:见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6页)。!因此,人不能因为善于禽兽就称名为“善”,就如同禽兽不能因为比草木聪明就称名为“智”一样。所以,基于人性论基础的孟子之善是不周全的。
董仲舒所揭示的问题非常值得人们思考,即思考仁的价值和善的德性,需要有量的尺度在其中,善是相对性的范畴,仁其实也一样。孔子所以称未见有善人或仁人②善人与仁人在孔子的语汇中,大致属于同一的范畴。参考《论语·尧曰》篇“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等言说。,就在于孔子不是从人禽之辨而是从人自身之辨去着眼的,是“人道之善”而非孟子之善。所以善才是“未易当”的③对于如何判断“仁人”,董仲舒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鉴别标准:“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即绝不能以功利为先务。所以,他决然否定胶西王(江都王)“越有三仁”之说,而认定“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见《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苏與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68页。。“不教之民,莫能当善”。董仲舒反问道:“使动其端善于禽兽则可谓之善,善奚为弗见也?”如果认定善端发动而优于禽兽就可谓之善的话,孔子就不会认为他没有见过善人了!因此,把“善于禽兽”意义上的“人性善”作为一般命题,其实是不成立的。
在董仲舒,孟子之善只应当放在善之发端或曰“善质”的意义上去看才有意义。因为它揭示的,是人之善端发动而呈现出的对父母的亲亲之爱情感。在此之后,民在受教的情况下,“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在儒家的名言系统中,性与善与仁的联系,是在圣人的仁德教化下才真正得以打通的,所谓“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2]319。博爱固然缘起于爱亲之情,但在境界和程度上又高于爱亲之情。重要的其实不在于潜在的善性,而在于现实的善行。董仲舒作为儒家王道政治及其治国理想规范化的关键性人物,将三纲五纪和八端之理都融入了善的德行,以期民众能“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这也是他推崇圣人之善的真实目的所在。同时,董仲舒从《孝经》而来倡导“博爱”,因为只有博爱才能最充分地展现仁的情感和境界。
可以说,“博爱”充分扩展了“仁者爱人”的蕴含,这在董仲舒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他提出统治者爱人当“以仁厚远”和“远之为大”。“厚远”观念从孟子“推恩”而来,“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2]52。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大夫华元和子反私下会面结盟而休兵止战,后人有不同的评价。董仲舒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出发,肯定子反“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2]52,故其立场和决策具有正当性。人的爱心和仁德的推广是出于自然的情感,故应当跨越诸侯与诸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普遍的人道关爱即“远”为王者治理天下的优先选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2]252。爱及“独身”并非是真正的爱身,因为它背弃了“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④张立文先生说:“董仲舒主张仁爱要厚远,而把爱的远近、亲疏分成五个等次:‘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施爱于不同空间范围内的人,所产生的效应也不一样。梁亡和秦亡都是爱及独身而不爱人的效应。”见《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因而,对国家的统治者来说,爱及天下而保有万民,才是真正的自得和自好。董仲舒如此的讲法,既是立足于思想家的远见,阐明越是普遍之爱,越能保统一国家长远的道理;同时也在于通过他所高擎的“仁义法”对统治者进行规劝。
在这里,“以仁厚远”的“远”,在董仲舒不仅是一种空间距离的扩展,也是一种时间先知的远见。他以为:“夫救蚤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2]252先觉其萌,绝乱害于未形之时,是有远见的王者应该具备的智慧,这是孔子修《春秋》所要特别彰明的心志。董仲舒论仁,注重爱的情感与智慧辨识的统一。“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2]257。“仁”是爱“人”这个类的,这是董仲舒普遍仁爱观或曰博爱的典型反映。但仁爱的施行也当考虑是非曲直,秉持兴利除害的原则,而这就是智慧的预见和指导作用了。所谓“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远,而《春秋》美之,详其美恤远之意,则天地之间然后快其仁矣”[2]252。空间与时间之“远”,由于智慧的作用又统一了起来。
不过,如果将董仲舒“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2]252的主张继续向外推,则爱及四夷、爱及百姓又不够了。从孟子到董仲舒,都强调重民和爱民,但仅仅如此,还不能算是仁的完全实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2]251仅仅“爱民”还不能算是“仁”,需要将“爱”扩展到“鸟兽昆虫”等自然万物。即人不是“善于禽兽”,而是“爱禽兽”,才真正可谓之善,谓之仁。“推恩”就不应当止于人,还应当及于物:
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鳣鲸不见,群龙下。……恩及于火,则火顺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黄鹄出见,凤凰翔。……恩及于土,则五谷成而嘉禾兴;恩及倮虫,则百姓亲附,城郭充实,贤圣皆迁,仙人降。[2]371-375
天人感应在这里固然是一个基本的架构,但统治者行仁和推恩也是核心的内容。而且,如果“恩及倮虫”,兼及于鸟兽昆虫,结果自然是“百姓亲附,城郭充实”,爱物与爱民统一了起来。
因此,讲善行和仁德,就需要从狭隘局限的人性扩展到宽阔广大的物性和物类,扩展到整个天地。可以说,这是将孔子的“泛爱众”和孟子的“仁民爱物”观做了更彻底的推广。在此天地人一体的意义上,仁与天打通,就不仅仅是提高了仁德的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利用至尊至大的上天,帮助落实博爱或仁德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