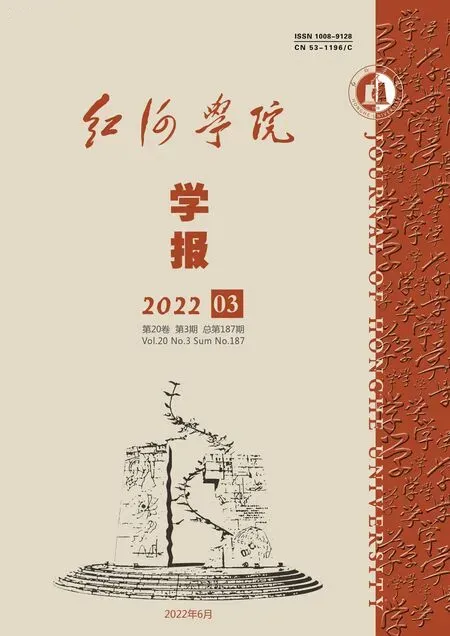苏幕遮与傩舞的跨文化研究
汪 琳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安徽芜湖 241008)
处在不同地域的苏幕遮和傩舞文化,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艺术奇葩,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而核心则是研究两者文化形态下形成机制究竟有什么异同?它们的发生、发展与结局为何有如此差别?这正是研究的艺术价值关键。不同区域的人们用智慧和信念,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从根本上体现着自己的生命价值。苏幕遮的盛极一时和傩舞的源远流长,表明它们都是最可贵的艺术珍宝。因此,我们对二者来进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 苏幕遮与傩舞辨析
苏幕遮是西域的一种歌舞戏,为丝绸之路南部绿洲的乞寒习俗,自波斯起源后,经中亚传至西域,隋唐时传播到中原,现已失传。傩舞是隶属于傩文化当中的一个子概念,其内涵以及形式颇为丰富的傩文化当中,并呈现一种艺术形态。傩文化是以傩仪为开端,经历了傩舞之后逐渐发展为傩戏。傩仪、傩舞、傩戏之间互为影响,共同发展。而傩舞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演形态,是傩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今仍活跃在民间。苏幕遮与傩舞的功能和特征的异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两者所信仰的宗教不同。苏幕遮是原始宗教与佛教契合的产物,由粟特传入龟兹等地区,而傩舞是中国南方本土巫术起源的原始信仰,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二是两者所处的地区不同,苏幕遮远在西域,傩舞置身吴越古地,居于较为封闭的山区。三是两者的表演形态不同。苏幕遮是集歌舞戏为一体的表演形式,而傩舞则是相对单一的舞蹈形式。苏幕遮的表演具有情节性,是一个完整的歌舞戏模式,而傩舞隶属于傩文化的一部分,只是整体中的一个段落,并不能替代完整的傩文化。由此可见,无论是苏幕遮还是傩舞,二者都与原始宗教信仰密不可分。虽然同是驱邪禳灾、祈神纳吉,但两者间却有明显的差异性。苏幕遮所代表的是西域游牧民族原始文化的继承,而傩舞代表了南方稻作民族的巫傩文化的特质。此外,外部表现形式的不同也是二者差异性表现所在。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都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生态环境的不同就会造就事物形态的不同,乃至本质相同的事物亦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苏幕遮主要在中亚和西域绿洲地区传承,历经千年才衰落。傩文化是以我国南北为分界,越往南傩文化越密集。傩文化就像一张巨型的网,辐射到诸多农耕民族地区。东起苏、皖、赣,路经湘、鄂、粤、桂;西至川、黔、滇,北到陕、冀、晋。放眼望去,傩文化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苏幕遮作为一种西域祭祀文化形态演进和传播中,秉承其精神内核与兼收并蓄,取精华弃不美而融合,从而形成与民间文化相契合的乞寒驱邪仪式。苏幕遮在西域原本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神圣仪式,但传至中原后变为宫廷的一种纯娱乐性活动。从神圣性到世俗性的转变,难免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会有所变异。傩是巫的高级阶段,具有娱神性,从室内的驱邪傩仪开始,傩舞的产生成为傩仪的极大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傩仪无疑是能够影响傩舞精髓的因素,而傩舞反过来就是对傩仪的一种合理扩充。在不断的完善中傩戏的出现,连同其中存在的傩祭、傩技等多种形态,从而同构了完整的傩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自古多元,但南北生活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也有所不同,处于其中的人文也迥然不同。南傩北萨的原始信仰,不仅成为先民们各自的信仰系统,而且应运而生,顺势而为。苏幕遮和傩舞的产生,首先都具备功能性的特征。在认识力低下的先民,人们被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所困惑,为了求得生存,也为了给自己一个完满的解释,苏幕遮与傩舞的产生被赋予了历史的蕴意。于是,苏幕遮因乞寒祈水而产生,傩则为了驱邪纳吉而形成。从功能上看,两者是存在异同。第一,两者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趋同性,都是为了达到内心对渴求的满足,从而衍生出寄托之物,但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呈现。第二,两者功能的差异性。苏幕遮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来达到乞寒禳解和祈福,完全处于娱神的立场之上。而传至中原后的苏幕遮,渐渐具备了娱人的功能。除了完成某些礼仪外,还变为统治者的娱乐活动。同时,也成了民间文化艺术从民间到宫廷的典范。而傩舞是傩仪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处在发展的阶段,傩舞与傩仪共同完成了驱邪纳吉的使命。起初纯粹是为了发挥娱神的功能,但其娱神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淡化。娱人功能的增强为傩舞拓宽了生存空间,并发展为傩戏之后,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拓展了外延,更是为日后诸多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苏幕遮和傩舞在表演时均戴有各式面具,载歌载舞,并且有乐队伴奏。苏幕遮在西域文献中记载甚少,唯一较为完整佐证的具体资料,就是龟兹昭怙厘佛寺出土的舍利盒。虽是在佛寺出土,但其并非是佛教的产物。西域文化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苏幕遮有了极大生存的空间。苏幕遮曾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高昌、康国、焉耆等地广为流传,后传至中原才被更名为“泼寒胡戏”。盛行于隋唐的这种歌舞戏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后,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一些变异——借用西域歌舞戏形式和相关元素为架构,注入全新的中原文化内容。而众多文献中记载的《苏幕遮》《拨头》《西凉伎》《舍利弗》都属于此例。笔者认为,傩舞和傩戏是互嵌的,是一种互为存在的关系。而傩舞的分类与傩戏就有必然的联系。根据现状,可分为仪式性和表演性两大类。“仪式性戏剧是一种以驱邪 纳吉、禳灾祈福为功利目的的聚戏活动,名称各地不同。汉族地区沿袭《论语》‘乡人傩’和汉代宫廷大傩的称谓,泛称傩、跳傩、傩戏;也有地域性称谓,如傩堂戏、庆坛、跳山魈、跳五猖等等。”[1]仅就江西南丰一地的傩舞而言,就有较为丰富的种类,如“跳傩”“鬼舞”等。又其他地区,不仅在名称上有所变化,形式上也会因地而异。如贵州“地戏”,南宁“师公舞”等。表演性质的傩舞则显而易见,具有观赏性,附带着商业化功能,均是为了表演而进行表演。
二 苏幕遮与傩舞的文化生态
如果说,环境是从广义上来影响文化的关键因素,那么生态之于文化的影响,便是具体阐明产生其相异性的根本。苏幕遮是西域绿洲农耕文化的产物,傩舞是南方稻作民族文化的产物。西域绿洲农耕文化是一切绿洲艺术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决定了其生存环境的封闭性。同时,由于生存的需要,对水的渴望成了绿洲居民永恒的表现主题。在历史上,西汉的西域三十六国以及东汉的西域五十五国都是绿洲城各国,而绿洲经济非常脆弱,所以抵御天灾人祸的唯一办法是乞寒禳灾。虽然,古代绿洲的五大城邦已随历史逝去,但以绿洲为载体的经济和文化格局依然存在,因而绿洲艺术凭着它独有的特性仍焕发着勃勃生机。
自古以来,不同文化艺术之间发生碰撞后,所产生的效应成就了文化的回授性,而文化艺术也就在往返反复中日趋成熟,遂形成了多元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绿洲艺术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民族的,而是多民族的;不是某一地域的,而是多地域性的。”[2]105这不仅是对多元文化的出现予以最佳概括,也从侧面反映出苏幕遮在西域发生属于必然。
傩文化的产生与巫密不可分。先民崇拜也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而傩崇拜更是处于巫崇拜的高级阶段。有人曾说,傩文化是“糯文化”“鸾鸟文化”,这无疑已透露出傩与稻作文化的关系,透露出鸾鸟曾是先民的鸟灵崇拜。“鸟灵崇拜可能是人类社会最早崇拜的动物灵之一,它几乎同太阳崇拜一样古老。因为,在人类的原始思维中,太阳就是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火鸟。”“全世界的鸟灵崇拜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文化的趋同性。如都崇拜太阳鸟。中国的鸾、雒,日本的天照大神,蒙古的脱翰林勒鸟,古埃及的赖鸟,古希腊的克劳诺斯(宙斯),古美洲的雷鸟……都是太阳鸟,都与农业文化有关,而且还有语言上的类似。”[3]农耕民族从原始狩猎渔集开始诞生了植物崇拜,继而图腾崇拜,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农耕后的巫傩崇拜。这意味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思维模式同时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傩’最原始的形态,非戴面具、执戈扬盾驱鬼,而是上古先民有了神鬼观念之后,‘见’到鬼时一声不自觉的惊呼。”[4]康保成研究认为,“傩”的音、义均无法显示出其驱疫逐鬼的意思,而是由某种音义符号的转换形成的最终结果。“傩”纯为一个假借字,所替代的字即为人驱疫逐鬼而进行的一项仪式。从以上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傩追根溯源的各种观点,孰是孰非并不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关键,但从表层的文化来看,傩的出现与原始崇拜、稻作文化以及人类心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周礼》中曾有关于“索室逐疫”的记载,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大型仪式。而巫与傩所形成的一种源流关系,决定着南方农耕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巫傩崇拜的发生,无疑给了当时人们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支撑生活的信念。而生活环境和生产力的改观,促进了傩文化的发展和辐射性传播。有利于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展,更是成为傩文化源远流长的必要条件。
总之,两者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环境亦是关系密切。苏幕遮和傩舞都是同质异构的,只是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出现在仪式中而已。无论是苏幕遮乞寒还是跳傩,仪式是无法逾越的重要环节。仪式预示着开始和集结,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过渡的前奏,甚至成为整个族群必须遵守的约定俗成。人们在阈限中思考,承前启后完成仪式固有的使命。以至发展到后来,就转变成为族群首领管理族群的形式和手段。如苏幕遮在表演中,佩戴动物和人形面具、朝路人泼水等;跳傩时摆放祭坛、佩戴各种面具,且口中念念有词等。均可视为一种仪式性、神圣性、规范性的举动。
此外,苏幕遮与傩舞在演进方式上也存在差异性。苏幕遮的东渐呈现一种线性的传播模式,隋唐与西域的交流促进了苏幕遮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文化的回授性特征在此并未体现出来。究其原因,苏幕遮地处西域,后因宗教文化相互碰撞,且主流信仰文化冲击和影响,将兴许有机会演变为一种民间娱乐形式的艺术扼杀在摇篮中。因而,苏幕遮这种娱神性的歌舞戏,便迫不得已地消失在本土,而以另一种形态在中原发展。大致可归纳为:其一,苏幕遮在西域的消失是因为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尊奉一神教,使得西域的信仰体系中,众多宗教信仰的解体,包括了其他信仰有关的所有文化,苏幕遮也因此而消亡。其二,苏幕遮从唐代传入中原地区后,必然与中原文化发生一定的碰撞。在失去了本土生态与文化环境依托后,逐渐与娱神的合理旨归背道而驰。苏幕遮在中原被解构后又重构,被汉族文化的强大基因所改造,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傩舞处于相对稳定的南方农耕民族文化之中,其形态的固定和发展的平稳,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在本质上发生改变。从其分布范围来看,我们发现很像一张摊开的网。由此可见,傩文化的传播是呈一种辐射性的传播。虽不能以中心主义传播论来断言,但其传播方式可以理解:以某几处为主要发源地,继而渐渐向四周扩散。当传播网络的格局一旦形成后,傩文化便以稳固态势发展。苏幕遮的消亡有其必然的因素,傩文化的继承也有自身的先决条件。起初同为娱神的功能,之后由于宗教的改制而分道扬镳。然而,无论宗教改制也好,还是被汉族文化所濡化也罢,苏幕遮始终无法逃脱其消亡的宿命,而傩舞从神圣仪式变为世俗文化后,顺应了发展的潮流。在无重大宗教改制的情况下,傩舞只是在不同语境中继续重构,保持其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借用其他方式呈现。
三 苏幕遮与傩舞本体论的比较
苏幕遮是歌舞戏一体的表现形式。从史籍记载“以泥水沾洒行人”“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油囊取得天上水”[5]124的娱神形态来看,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为了乞寒祈水,人们裸露身体泼水起舞。此种行为在弗雷泽的《金枝》中也有相似的描述,而祈雨则作为一种巫术仪式存在在各种文化中。
无独有偶,塞尔维亚人在遇干旱时,将一个少女的衣服脱光,从头到脚用野草、香草和鲜花穿戴起来,甚至在她脸上也罩着一个用新鲜的绿色植物编成的面罩。之后,就称她为杜多娜,让她在一队女孩的伴随下走过村庄。她们在每所房子面前都停下来。女孩们在杜多娜四周围成一个圆圈并唱着一支叫杜多娜的歌曲,杜多娜自己则不断的旋转跳舞,这时那家的主妇便将一桶水泼往她全身。[5]105
从这段田野材料中,我们发现其与苏幕遮的一些共性特征:有仪式性行为以及裸体、泼水、面罩等内容,有歌舞形式。可见,人们的思维方式有极大的趋同性,所不同的是,具体到每一地区之时,表现形式会随着当地的文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异,以更加适应当地的需求。因而苏幕遮作为外来文化传至西域地区,再东渐到中原后,便如《一切经音义》中的形态,完全不同于波斯的苏摩了。
傩舞自傩仪开始就有驱邪之功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似乎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个案。在整个过程中,跳傩之人均佩戴面具手持道具,在屋内将邪气驱逐出去,并且驱邪仪式是一种定期的行为。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诸多记载也无独有偶地描述了北方民族的驱邪方式。均有用水洁净,众人用道具、歌曲、声响等手段来驱邪。我们认为,所谓傩舞起初的形态并不是真的舞蹈,而是人们利用一些人体动作来构成符号语言以象征驱逐,这些动作在傩仪中发生。继而当傩文化的内涵不断拓展,功能从娱神向娱人转变时,傩舞才有了独立存在的空间。
苏幕遮和傩舞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戴面具游走,以及伴有载歌载舞。苏幕遮表演时所戴的面具多为动物形态,傩舞表演的面具为人形,这可能与当地初民信仰有关。苏幕遮与西域绿洲文化的不解之缘,苏幕遮所佩戴的面具是为了通神,用动物的造型实为借用动物精灵来辅助,因此,苏幕遮的狗头猴面等造型自有出处。傩面具一般采用以恶制恶的巫术原则,面具狰狞恐怖,认为只有比鬼怪更为凶恶才能顺利驱逐鬼怪。但傩舞作为后来发展的艺术形式,采用人像做面具,更多的是由于模拟角色和崇拜情结所致。在傩文化中有“傩公傩婆”“傩兄傩妹”之说法,这些象征人类繁衍和再生能力的角色,赋予了人们更多的想象。
我们再从舞蹈文化的角度依次对苏幕遮和傩舞进行比较。首先看苏幕遮,龟兹昭怙厘佛寺舍利盒上描绘的乐舞图清晰可见:二十余人的队伍中,人们形态各异。所持道具、乐器不同,所佩戴的面具也有不同。队形的排头有一男一女,手持各一旄且四目相望。紧跟的三男三女错开排列,均佩戴动物面具。六人牵手起舞,姿态各不相同,或弓步状的,或半立脚尖端腿状态的,或抬起大腿,小腿自然下垂状,右手低左手曲肘且肩部上抬,体态呈现出不完全的S型。而如弓步形态者则像跳跃跨步,紧跟其后,或一手持木棍的独舞者身着甲胄,佩戴浑脱帽和长尾,一如往前的体态,且右手置于大腿。其后,两名孩童抬着大鼓,一名鼓手双手高低摆放,呈现擂鼓状。接下来的五人是手执乐器的乐手,乐器依次为竖箜篌、凤首琵琶、排箫、鼗鼓以及铜角。五人演奏时彼此有眼神的交流。最后的四人中,手执木棍者动作幅度较大,头戴浑脱帽身配长尾。右手执棍,左手抬臂,食指指向后方。抬吸左腿,右腿略有弯曲,拧身后视。而三名孩童,击掌开胯注视独舞者起舞。值得一提的是,乐舞图中的服饰华丽繁琐,多姿多彩,具有异域的风格。虽然这幅关于苏幕遮的乐舞图仅是一个定格的画面,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乐舞形态。同时,从舞蹈本身来看,乐舞图中舞者的姿态也体现出丝绸之路上的舞蹈特征,蕴涵了龟兹舞蹈与印度舞蹈交相辉映的元素。
由于傩舞的地方域性特征比较明显,虽同为傩文化,但在名称或者表现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在此我们仅以安徽贵池傩舞为例:
贵池傩戏在当地又称池州傩戏。据吕光群先生考察,池州傩戏剧目有两类:一是舞蹈,包括傩舞和吉祥词。如傩舞有《伞舞》《打赤鸟》《魁星点斗》《舞古老钱》《舞回回》《舞滚灯》《舞芭蕉扇》《舞旗》《舞判》(亦称《判官捉小鬼》)《三星拱照》《关公舞大刀》《出将》(亦称《杀四门》)《童子拜观音》《舞财神》《舞土地》《舞合和》《踩马》等;二是傩舞中有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如《伞舞》《舞滚灯》是单人舞,是迎神的舞蹈。[6]70-71
书中插有一幅《伞舞》表演的图片:跳伞舞的男子面戴有白色人相面具,上身蓝色衣服,下身红色裤子,手持一把跳傩专用的彩色大伞正在旋转伞把起舞。动作幅度较大,有力度。可见《伞舞》属于男子独舞的表演形式。另外,此舞蹈在室内表演,室内布置也有讲究。室内中堂有画有对联,四周均有大红纸张包裹柱子,并且上面都写有字样。柱子间隔处挂有类似灯笼的物件。舞者正前方摆放着诸多蜡烛。这些物品设置也可以想象各自反映的功能。从中说明舞蹈包括了傩舞和吉祥词,图片中虽然不能体现动态有声场景,但我们可以推断舞者口中有说词的,并且周围应有伴奏的乐队,而乐器自然离不开锣、钹、鼓等。从图片描述与文字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傩舞与苏幕遮的不同表演形式。
我们知道,萨满会尽量选在夜晚做法,利用发光器、响声器等营造氛围,傩舞也是一种仪式性表演,人的表演和道具的使用亦是烘托气氛的关键。傩祭具、傩乐器、傩服饰等也极为讲究。祭坛布置包含神像、祭品、香烛等。或在室内挂上各种不同的神像,或只挂一个神像。神像必定是有主神以及小童构成,主次分明。道具也因地区不同而各异,锣、钹、鼓、法衣等自是必不可少。此外,还有法杖、伞、刀、剑等。“中国傩作为民间艺术来说,最有特色的就是傩面具了。面具如果按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类:祭祀面具、跳神面具、镇宅驱邪面具、戏剧面具等。”[6]120可见,傩的面具含义深刻。也由于区域的不同,在其称呼上也会出现不同。再则,傩服饰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服饰是身份的象征,跳傩时的服饰是具有法力的,从头饰、法帽到法衣,无一不体现其所具有的功能。人们对于傩服饰的讲究,自然也会与傩文化紧密结合,一针一线都是精心设计,以表现其文化内涵。
从前述比较中不难看出,其表现的内容是以各自的民间文化为依托,民间文化是形成它们各自不同形态的关键要素。西域的苏幕遮与南方的傩文化,有其相似的思维意识形态,但也具有各自特色不同表现形式。文化的交互性使得文化变得更为多元发生与发展,有诞生就有消亡,有冲突就有融合。苏幕遮已从历史中褪去,而傩舞的名称、道具、乐器以及舞姿,我们发现,其与后来在民间流传的诸多民间舞蹈有较多的重叠。新事物的产生,必然是现有元素与后文化相契合所衍生的,因此,傩舞与民间舞蹈的内在渊源关系,一目了然。
四 结语
苏幕遮和傩舞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一次尝试性比较。其意义就在于:能够更为深刻地了解艺术背后之文化内涵,厘清文化与艺术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艺术形态所起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对于具有原始万物有灵观念的仪式性文化活动,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讨论,在二者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于游牧民族文化与农耕民族文化之间的精神文化差异。正因为精神文化的相异性,使得两种艺术文化一个已经消亡,一个仍活态传承发展。
正如千人所言:“相反,我们愈仔细观察自然界的更迭现象,愈加感到它们严密的规律,绝对的准确,无论在什么地方观察它们,它们都是照样准确的进行着。”[4]106一些艺术形态的发生和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因而对于已经逝去的苏幕遮,我们如何从历史遗存中去寻找其原型的密码,再用现代人的视角重构苏幕遮艺术,对于流传至今的傩文化现象进行新的诠释,在传统中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才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