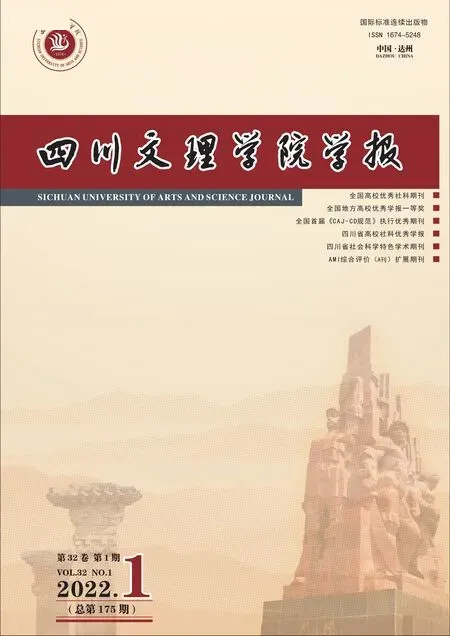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有所思》与《上邪》两首诗的互文性解读
杜自波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关于《有所思》与《上邪》二诗关联性的研究,一以清人庄述祖《汉铙歌句解》为代表,他解两诗“当为一篇”,前后姻联,是“叙男女相谓之辞”;一以闻一多《乐符诗笺》为代表,他解为二诗“不见问答之意。反之,以为皆女子之辞,弥觉曲折反复,声情顽艳。”然从这两首诗的本事、结构、情感进行观照,不难发现前后文本的互文性逻辑,即是说后文本是对前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是同一文本中不可割裂的前后两个部分。
一、《有所思》与《上邪》的本事关联性
本事者,本于事者或根于事者,即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之“缘事”,是“诗性的历史实存”。[2]其词最早见于东汉桓谭《新论·正经》:“《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3]乐府本事,固然就是指一首乐府曲辞创作之初所依据的事情之本来,所依据的“诗性的历史存在”。向回《乐府诗本事研究》:“乐府诗本事,就是指那些与乐府曲调、曲名或是歌辞的创作、传播、变化等有关的历史事实或是民间传闻,它是对与具体作品直接相关的作者(或故事主人公)行事(包括逸闻逸事)及其创作、传播过程的真实记录,或是对它们的艺术化处理。”[4]乐府诗本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结构,因为它涉及作品创作、传播、变化。就《有所思》与《上邪》而言,我们可以根据“本事——本意——本义”的进行态对二诗进行一个“人类文化的集体回忆和诗性还原”。[2]即是说先考究文本创作的历史背景,然后去推论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最后形成读者对文本的原义集合。当然本事在这里只是较为指向性的被定为创作背景。故此,在庄述祖和闻一多关于二诗本事批评的指引下完成进一步的本事探究和考证,从而证明二诗“实为一篇”之可能。并不是所有如此背景本事相关甚至一致的不同诗文都可以当做一篇而论,《有所思》与《上邪》同属《汉铙歌十八曲》中的情爱诗,原列第十二和十五,我们就有一定理由去猜测二诗可能为一篇之文。《汉铙歌十八曲》据《宋书·乐志》所载之汉明帝四品乐和蔡邕叙汉乐中,可见“短箫铙歌”之名,并独得一类,由此可证《汉铙歌十八曲》确属西汉之作。《古今乐录》载汉短箫铙歌古辞存二十二曲:
《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翁离》《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君马黄》《上陵》《有所思》《雉子斑》《圣人出》《芳树》《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钓竿》,[5]后四篇古辞俱已亡佚,故其实存十八曲。其中可约略推定创作年代的是《上之回》《上陵》《远如期》。《上之回》后世多从吴兢之言:“汉武帝原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后数出游幸焉。其歌.......皆美当时事也”。[6]也就是说大都认为《上之回》作于汉武帝时期(-156年~-87年)。《上陵》因诗中所记“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甘露是汉宣帝第六个年号,从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50年共4年时间。而《远如期》则写于甘露三年述匈奴单于来朝之事。虽然其余诸篇创作时间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根据郭茂倩《乐府诗集》之编类法即时间推移法进行推测,《上陵》至《远如期》之八篇是在汉宣帝甘露年间(-53年~-50年)即西汉中后期所创,包括《有所思》以及《上邪》。在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是处在一个不断下降的境地。杨树达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收录了《史记》《汉书》里关于汉代主动改嫁和被迫离异的史料,其中主动改嫁的有外黄富人女、张负孙女、朱买臣妻、王皇后、苏武妻、淳于长的小妻共七条,除淳于长之小妻出自汉宣帝外,其余皆出于汉武帝及以前。被迫离婚或被丈夫驱逐回家的有五条,包括陈平嫂、王吉妻、霍光女、王政君的母亲以及枚乘小妻,而王吉妻、霍光女、王政君的母亲多生活在汉宣帝时期。她们被弃原因不尽相同。陈平嫂之被弃因口舌之嫌“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也就说了句陈平不务生产的闲话却被离弃。王吉妻之被逐因“盗窃”之事,史载:
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日:“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7]
王吉休妻是因为他妻子摘了邻家几颗垂到自家院的枣给他吃,这也是为彰显自己学官之志气。而王政君的亲母是因妒忌之故遭丈夫休离。
据此,我们可以对比得知,第一,在汉宣帝以前,妇女在家庭、婚恋中的地位较高,而汉宣帝及以后的妇女地位渐趋弱势,其命运多受制于丈夫。第二,妇女被驱逐或休弃的原因并不是不忠不仁不孝,而是男子主观认为妇女不守礼节,行为出格。这种妇女地位的变化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一是儒学的影响日渐扩大,二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礼教逐渐形成。儒学和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在汉宣帝时期已渐趋强化了。
综而论之:《有所思》与《上邪》的背景本事是汉宣帝时期,妇女地位渐趋下降,妇女在曲辞中激情热烈的怨诅决绝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保留着一片贞洁之操守的,指日可鉴,同时讽刺男子仗着政治优势二三其德。我们来细究文本,先看《有所思》之所言: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8]
这是言男子二三其德,女子怨而怒,怒而不可得便生思情,而后欲告知上天一些东西,这大可认为是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以及一个完整本事的上半部分。我们再看《上邪》之所言: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8]231
这是言女子向上天表明自己的贞洁誓言,这大可认为是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以及一个完整本事的下半部分。
因此,笔者认为二诗若合而为一,便成就一个完整的背景本事,也就是说汉宣帝时期,妇女地位渐趋弱势,妇女在曲辞中表现的是在男子政治优避下深沉而无奈的盟誓,《有所思》是为盟誓之深沉,《上邪》是为盟誓之无奈。所谓深沉,是女子祈望“与君绝”之权利,而所谓无奈,是女子面临着“为君绝”的现实。此本事之断论较庄述祖之“男女相谓之辞”更确切的表明是女子一人之心声,而绝无男子之言;较闻一多“独立各篇”更趋向于“合为一篇,成其完整”。故此论综合二人之言说,并详加补充其本事,以构建二诗“层累型发展”的完整结构。这是从本事出发对文本本义进行阐述,其“实为一篇”之论证虽为可行,但还需要从二诗文本的结构与情感进行具体的解读论证。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在本事探究或是本事批评的指导下,我们可对文本进行多元开放的解读甚至对其进行二度生成。
二、《有所思》与《上邪》的结构衔接性
已被广泛接受的文本自有其结构的完整性,内容的统一性,意义的相对稳定性。[9]《有所思》与《上邪》在结构上的首尾衔接、前后照应以及时空对接关系能更进一步说明本事探究或是本事批评的可行性。
《有所思》之诗末言“东方须臾皓知之”,其中“东方”一词出自《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东方自出。”[10]汉·司马相如《长门赋》亦有言曰:“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於东方。”[11]此东方之意即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可代指“上天”。“知之”一词是说等天亮了,上天自会明白我的心意,可是我的心意是什么呢?觉得“知之”其后还有话说。故《上邪》开篇一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顺势承接前文之“东方须臾高知之”,“上邪”即承接“东方”,“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承接“知之”。女子向上天所要表露的是自己的钟情以及贞操:上天啊,我不仅与他相知,而且要到天荒地老的永远。正如余冠英在《乐府诗选》里所注:“上”指天,“邪”音“耶”,“上邪”犹言“天啊”,指天为誓。“相知”相亲也。“命”令也,使也。从“长命无绝衰”以下是说不但要“与君相知”,还要使这种相知成为永远,除非天地间起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化,一切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如高山变为平地等等,咱们的交情才会断绝。这也是情诗,似和上篇有关联,有人认为合为一篇。两篇同是一女子的话,上篇考虑和情人断绝,欲决未决,这篇是打定主意后的誓辞。[12]
此二诗便是在“指天为誓”之下完成了巧妙的结合。曲辞中女子本是因对远隔天涯的心上人“有所思”,故打算用玉缠绕的“双珠瑇瑁簪”来表达自己一片钟情痴爱。然男子二三其德,心有他者,这不得不使女主人公由爱而恨,因恨而怨怒,故将这信物“拉”“杂”“摧”“烧”“扬其灰”,以发泄内心积郁的情感,可谓是不如此深刻描写,难以窥见女子一时之憨恨。本是要忘掉负心人,并断绝关系,但是“情不知所起,以往而情深”啊,便在欲决绝之际怀想起过往约会惊动巷犬与兄嫂的事,这决欲不决的矛盾心理昭然若世,但女主人公内心真实的想法只有上天知道。此诗怨且怒,怒之急切,是为望之深切。行文至此,女主人公的“望之深”并未戛然而止,而是继续潮涨,其望之深切便在这天地四时万物之间:山丘没有了棱角,江水枯竭了,冬天打雷,夏天飘雪,天地合而为一,我们的交情才能断绝。故二诗合为一体成其文者如是: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是据二诗结构之一进行论证的,整篇文章以“上天”前后衔接巧妙过渡,使得结构完整浑融,绝无隔断,自然形成一篇文章的前后两部分。笔者认为二诗如此整合为一,便是本事探究以及本事批评对文本分析的作用——文本再生成,它能够让“互文性”更加作用于此文本与他文本,并让“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忠实存在”。[13]
前面已从结构之一首尾衔接进行论证,这里将从结构之二前后照应进行论证,力求证据的充足性。《有所思》有“相思与君绝!”之句,而《上邪》有“乃敢与君绝”之句,二诗因此形成前后照应的关系。“相思与君绝”是因为钟情之女子得知心上人“有他心”,自己的一片痴情化为憨恨,于是想要与他断绝关系,但想起昔日约会惊动巷犬和兄嫂,这是多么惬意浪漫的回忆,怎么能说断就断的呢,这说明的是“与君绝”很难。若是“与君绝”,又应该如何?《上邪》作为整篇文章的下半部分给出了答案:山丘没有棱角,江水枯竭,冬雷轰隆,夏日飞雪,天地合一。唯有这样,女子才能“与君绝”。这些超自然的现象说明了“与君绝”不可能,可能的只有“为君绝”。整篇文章,由《有所思》之“与君绝很难”辗转为《上邪》之“与君绝不可能”,其实质是“为君绝”的可能性结果甚至必然性结果。
最后,我们再从时空维度来进行探究。《有所思》之女子,立足现在,有所思念是因为“乃在大海南”,有所怨怒是因为“闻君有他心”;回溯过去,有所牵挂还有所缠绵是因为“秋风肃肃晨风飔”;祈望未来,有所期待还有所无奈,是因为“东方须臾高知之”。这是根据“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维度演绎的。而《上邪》言“山、江水、冬雷、夏雪、天地”之物象,则是根据“天——地——自然”的空间维度演绎的。也就说,两者形成时空维度的对接互补,形成了文本与文本在横向上以及在纵向上的“文本性”或是“文本间性”关系。
三、《有所思》与《上邪》的情感接续性
正因为《有所思》与《上邪》在结构上的衔接关系,才有了二诗在情感上的接续关系。《有所思》是为情感之蓄势,表现成激情深沉,《上邪》是为情感之接势,表现成热烈决绝。我们细析文本便可知二诗如何蓄势与接势的:《有所思》起篇便着一“思”字,为全文垫下缠绵悱恻的情感基调。继而因其所思者远在大海之南,引发女子造信物以能睹物思人也。然现实不成所祈望,男子二三其德,有了他心,女子之信托之情陡然枯索,顿生怨怒,使一连串动作“拉”“杂”“摧”“烧”“扬”似与之断绝,此女子憨恨之态也。转念思之,过往之缱绻令女子难能决断,一负心人如何挽回?只能述己愿于天,方可鉴也。此部分由思转怨,怨而怒,怒而复思之,欲决未决,但可是未决耶?非矣,《上邪》之辞以详其心意。《有所思》之情感蓄积于此,欲破未破,似有下文,故《上邪》顺其自然接其情势而述之。“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就是此女子的决绝,她以天为证,发出誓言要同心爱的人相识相知,相亲相守,并且到永远。“上邪”之声再并之“欲”字,将此女子激情深沉之情推向另一个浪峰即热烈决绝之情,其表现为五个异常的奇特想象,合其为三,即山水、气候、天地,合其为一,即自然。其意表明自然的一切,连绝非出现的物象都无法阻止我的情誓贞节,况一切正常之物象?
二诗合成的总的情感实为炽热背后的无奈,炽热是就二诗言辞而论,无奈则是就其背景本事而论。炽热之情,在《有所思》中主要是五个动词“拉”“杂”“摧”“烧”“扬”的表达效果,这一连串的动作行为将憨恨之女子的“思—怨—怒—望”的情感变化生动地表现出来。在《上邪》中则主要是五个超凡想象“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的表达效果。当然,二诗言辞除却炽烈,其背后也潜藏着无奈的。再论其无奈,主要是二诗所构成的背景本事造成的,在封建等级制度社会,在汉宣帝那个儒学与礼教盛行的朝代,女子只能是“为君绝”,而非“与君绝”,因此就算是男子变心,女子也难能主动取得生命支配权。
结 语
通过《有所思》与《上邪》两首诗的互文阐释,[14]可以发现彼此有着严密的互文性逻辑。它们在本事上互为补充,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本事结构:在汉宣帝那个儒学与礼教盛行的朝代,女子只能是“为君绝”,而非“与君绝”,因此就算是男子变心,女子也难能主动取得生命支配权,若得贞节,需指天为誓,故感其“哀乐”,成二诗之文。它们在结构上首尾衔接,形成密合无间的文本故事:《有所思》之尾句“东方须臾高知之”与《上邪》之首句“上邪”的巧妙衔接;《有所思》之“相思与君绝”句与《上邪》之“乃敢与君绝”句的前后照应;《有所思》之时间维度与《上邪》之空间维度的妙合无间。它们在情感上前后呼应,以形成连绵接续的情感场域:《有所思》实为情感之蓄势,表现成激情深沉,《上邪》实为情感之接势,表现成热烈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