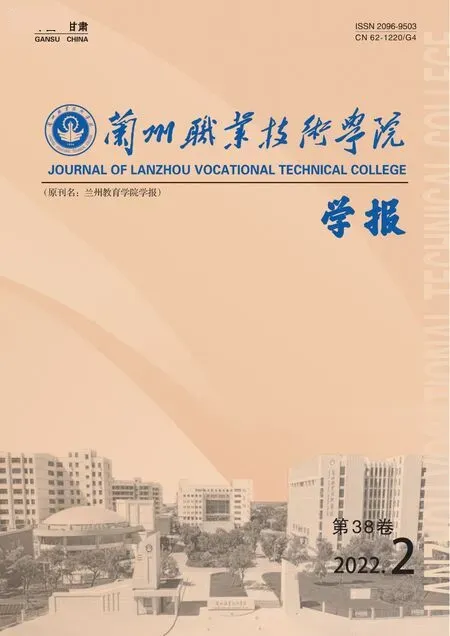成长小说视角下《灿烂千阳》中莱拉的女性成长
曹颖哲,郭 菲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一、引言
《灿烂千阳》作为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部小说,于2007年出版。该作品成功问世后,胡赛尼已经从当初的一举成名,成功提升为知名度超高的成熟作家。《灿烂千阳》采取女性视角,详细阐述了处于战火中的阿富汗女性的悲惨命运。莱拉是这个作品的女主人公,在其苦难的成长经历中,充斥着爱与恨、宽容与救赎,其中不乏社会的阴暗,但也处处彰显着人性的光辉。本文依据成长小说的相关理论,从侧面揭露了以女主人公莱拉为代表的阿富汗女性,长期禁锢于阿富汗封建的思想和体制下所遭受的迫害。同时,还揭示出女主人公莱拉在成长引路人的引导下,领略不同的生活态度,重塑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激发其内心潜在的成长顿悟,最终得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成长。
在《小说理论》一书中,巴赫金提及成长小说的类型,并且针对主人公形象阐释为:“成长小说中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不是简单的静态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1]就巴赫金对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准确把握而言,他阐明了成长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本质特点,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呈现的动态性变化。主人公的动态性成长包括生理和心理成长,其中心理成长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体现的是在主人公整个成长经历中,对自身的审视、对他人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的思考等系列问题。国内学者芮渝萍对此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人物形象——成长主人公的导师,或者叫做成长主人公的引路人。引导主人公成长的领路人包括多种类型。她将其分成三类:正面、反面引路人和精神伙伴。[3]大部分成长主人公获取成长经验,都是通过引路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引导,最终完成精神飞跃,长大成人。在《灿烂千阳》中,作者塑造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引路人形象,他们在莱拉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引导主人公在成长旅途中解决成长困惑,获得社会认同,并实现自我价值。
二、正面引路人——破除思想禁锢
正面引路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具有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人相处,与主流社会有一定差距等。在《灿烂千阳》中,胡赛尼塑造了自信、积极的正面引路人形象,即莱拉在知识和道德上都接近于完美的父亲。该正面形象对莱拉在政权变动、战火纷飞、性别歧视的压力下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莱拉自小受到父亲的宠爱,他鼓励她实现生活中的所有愿望和抱负,帮助她最终实现生命价值,并追寻人生意义。作为莱拉生命中重要的启蒙导师,她的父亲是一位受过教育且重视教育的教师。莱拉从小就知道,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她的安全,就是她的学业。他带着孩子们去看矗立了两千年之久的巴米扬峡谷,以领略祖国的文化遗产,传承家国情怀。正是他身上蕴藏的民族文化意识成为了培养莱拉健全人格的沃土。虽然他连日常的维修工具都不会使用,涂抹润滑油后的房门铰链仍会吱吱作响,修补过后的天花板照样漏水,但这些丝毫没有削弱父亲在莱拉心目中的地位。是父亲为莱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还为她扫清了成长过程中可能遇见的各种痛苦和迷惘。正是这种引导,使莱拉多年之后仍然选择回到家乡,重建家园。即便当莱拉和塔里克在穆里享受舒适和宁静时,她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毅然回到家乡喀布尔。在家乡,莱拉参与了孤儿院的建设,成为了一名同她父亲一样优秀的教师,她不辞辛劳的工作让一个又一个阿富汗孩子避免成为文盲。在实现梦想的同时,她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为阿富汗的改革和建设贡献着力量,也为阿富汗社会和文化的重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男权对女权的压抑现象既普遍又复杂,至今仍然通过或明或暗的形式存在。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就是阿富汗,在阿富汗,女性被男人所支配,没有话语权、受教育权、生育权、劳动权,只能听从男人的安排。与此同时,她们的命运似乎已经被命中注定,社会把她们安排成做家务的机器,以及生育后代、供男性释放欲望的工具。缺乏自我独立意识的阿富汗女性已然麻木,疲于自救。莱拉则有所不同,父亲时常教导她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要成为有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女性。正是得益于父亲的正面引导,莱拉才得以在混乱的社会中始终怀揣信仰、保持独立、肩负责任、追寻自由。
三、反面引路人——唤醒女性意识
如果说,正面人物带给主人公的引导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反面人物的警醒作用同样巨大。“反面引路人虽然对主人公的生活起到消极破坏作用,但从成长的角度而言,他们间接推动了主人公的成长。”[4]28事实上,他们完全丧失了导师资格,但是,就是这些没有精神操守和道德自律之人,却在另一个维度上充当了主人公成长的引路人。
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会经历一个充满挫折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成长故事中必不可少。“只要作品遵循成长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清晰地展现成长主人公青春期的成长经历,从而透视了成长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皆属成长小说范畴。”[4]25因此,成长的质变是发生在青春期,还是在数十年之后,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谁也无法否认,某些成长者长大成人的时间注定会被延长,《灿烂千阳》亦是如此。胡赛尼除了刻画女主人公莱拉的青春期之外,莱拉不幸的婚后生活也是胡赛尼着重塑造的成长历程。《灿烂千阳》中,莱拉的丈夫拉希德作为父权制度的代表,他的存在时时令莱拉警醒,并充当其成长的反面教材。
父权制度重压之下的阿富汗女性,其生活处处受到限制。在拉希德的逼迫下,莱拉出门时强制性地被要求穿戴布卡,“当然,这些要求看似束缚,其实质完全是在保护你自己。如今城市里的男人大多数都很下流。”[2]228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表面上好像是在保护她,而实际上只是拉希德的自私心理的表现,他对妻子毫无信任,始终认为漂亮的女人会背叛自己,招惹是非。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布卡代表着丈夫对妻子的钳制,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禁锢。此外,拉希德心里充斥着男尊女卑的观念,得知莱拉怀孕后,他立即奔赴清真寺,祈祷真主保佑他生个男孩。“肯定是个男孩。我的儿子将会是一个英雄好汉!跟他父亲一样。”[2]237在陪莱拉生产的过程中,拉希德难得露出了极度关心的神色,短暂地尽到了丈夫的责任。而当莱拉产下女孩后,他态度骤变,对妻女冷眼旁观。此后,他从未称呼过女儿姓名,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婴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军阀。”[2]242每当婴儿的啼哭扰乱自己的心智,拉希德便会目露凶光,把愤怒倾泻在莱拉母女身上。除了承受无故的打骂,莱拉还要忍受丈夫的囚禁,被禁止与他人交流。婚前的莱拉有相知相伴的朋友,青梅竹马的恋人,相对和睦的家庭。婚后的她饱受战乱和贫困带来的疾苦,还要忍受拉希德守旧观念与家庭暴力的双重压迫,身心丧失自由。
在男女平等的气氛中长大的莱拉被迫遵守谦卑、谨慎、沉默的处世原则。面对拉希德的控制,她选择一再忍让。在拉希德多变的情绪和冲动的恐惧性格中生活,莱拉逐渐丧失了话语权。这种权力关系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变得越发的不平等,经过持续恶化,终究会变成蔑视、嘲笑或者暴力殴打。正是拉希德身上集中体现的阿富汗男性惯有保有的暴力和强势,唤醒了莱拉逃离苦难生活的决心。莱拉面对初恋情人塔里克的感情坚守,对女儿阿兹莎的细心呵护,以及同挚友玛丽雅姆制定的逃离计划,无一不是体现着她时刻想要挣脱父权制社会强加的枷锁,争取身体和精神上的独立与解放。在反面引路人的刺激下,莱拉身心承受的压迫达到极值,其内在的女性人格发生蜕变,女性意识得以唤醒。
四、精神伙伴——构建身份认同
除了上文提及的正面、反面引路人给成长主人公带来的影响,伙伴式的人物也为主人公的成长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精神伙伴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给予无限的力量支持,它是一种无法磨灭的信念和强劲动力,永远都不会被物质所代替。
玛丽雅姆作为阿富汗千千万万被压迫妇女的代表,除了对莱拉的成长起到了精神伙伴的促进作用之外,也给了她精神世界的坚定力量,并重新点燃了莱拉的生活希望。玛丽雅姆一生都在私生女的阴影笼罩下委屈求全地生活。在被迫嫁给拉希德之后,她饱受家庭暴力的折磨,却找不到伸张正义之处,不得不选择忍耐。她在忍受精神摧残的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长期受到观念和权力的压迫,仅存的一点反抗意识也渐渐消磨于漫漫岁月中,最后只剩下忍受屈辱,并沦为丈夫的附属品。实际上,不仅仅是玛丽雅姆,莱拉也逃脱不掉拉希德的打骂和虐待。疯狂至极的他还将窗子用木板钉住,将其囚困于见不到阳光的房间,并且不给他们食物和水,想要通过饥饿和暗无天日的折磨来教训这两个女人。拉希德的专制和残酷,使得玛丽雅姆和莱拉的关系愈发亲密,她们之间坦诚,彼此之间的眼神交流都会在煎熬的岁月中感到慰藉,最终找到了摆脱痛苦的方法。
对于女性来说,长期禁锢于夫权与家庭枷锁中,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逃离国境,寻找真正的自由和幸福。1994年的春天,莱拉下定决心,要带着孩子和玛丽雅姆一起逃往白沙瓦。在逃跑途中,她们被警察遣送回家,接踵而来的便是拉希德的责骂和暴打。她们在丈夫长期的歧视与压迫下,放弃了争执,逃离计划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象征着不同背景下的阿富汗女性产生了觉醒意识,反思了自我的身份定位。当阿兹莎的亲生父亲塔里克返回喀布尔,与莱拉再次相遇,拉希德看到他的到来十分愤恨,再次爆发了长期以往的暴虐性,用皮鞭不停的抽打莱拉瘦弱的躯体。一直选择忍让的玛丽雅姆回到工棚拿起了一把铁锹,用尽全身力气用铁锹猛砸下去,拉希德终于倒下,没了气息。为了莱拉日后的幸福生活,玛丽雅姆独自一人承担下罪行,并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玛丽雅姆对于莱拉的关爱,如同母亲爱护孩子那般的自然和纯粹,因而她能平静和坦然的面对死亡。
玛丽雅姆的反抗,不仅实现了她对自己和他人的救赎,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玛丽雅姆甘愿奉献、无怨无悔的精神,不仅使她在生命的最后获得了身份认同,而且使身处辛酸与苦涩的莱拉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无私和勇敢。玛丽雅姆和莱拉因为大时代的变迁而同舟共济,正是因为玛丽雅姆的爱与牺牲,促使莱拉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意识到坚守责任、不忘初心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角色和性别平等的必要性。
五、结语
总体来说,莱拉的成长历程,本质上是其理想信念和自我认知逐步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人物角色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但都促使莱拉成长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同时,作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莱拉的成长历程实为封建礼教和男权笼罩下的阿富汗女性命运的缩影。胡塞尼极具感染力的表述将阿富汗社会中的弊病完全剥离、层层放大,同时,在他完整勾勒的女性视角下,女性自身的尊严与价值也突显出来。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光辉碰撞之时,作者已经给出了答案——一千个太阳终究能照亮无底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