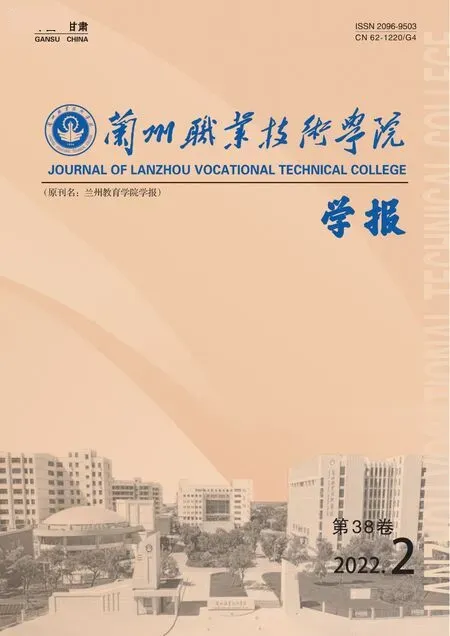现代汉语中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现象新探
伦昕煜
(澳门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 澳门 999078)
一、引言
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是目前汉语划分词类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缺乏形态的变化,汉语中产生了大量的兼类词。实际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已经提出了“通名假借”的概念,并认为跨类现象都属于词类通假现象。杨伯峻的《文言文法》和朱德熙的《语法讲义》,都探讨过兼类词特点的问题,认为这类词的特点是一个字同时起两个不同词性的作用,兼类的词只能是少数的。汉语中词的兼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其中,如何区别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现象是讨论的重点。这是因为,现代汉语中,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现象有大量的交叉,二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基于此因,有必要从新视角出发,去考察二者的特征,更好地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但二者共同构成了言语行为。这一说法,出自上个世纪初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根据他的理论,为了更好地将言语机能现实化,社会成员制定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例如汉语、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较为固定的模式,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并遵照规则来进行言语活动,因此语言具有社会性[1]。而言语是同一集体中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它即是动态说话行为和静态的说话结果的总和,也是个人言语行为和社会言语行为的总和[2]。从这个意义来说,言语是经验现象的东西,具有个性化和暂时性的特征。语言和言语的特征与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特征有极大相似性。因此,从言语和语言角度的出发,解释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的特征与区别,是符合现代汉语语言规律的,这也为汉语中词的兼类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二、语言层面下的兼类词
兼类词是指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两类(或以上)的语法功能,而其词汇意义又有密切联系的词[3]。兼类词产生的原因常被学界归为两种。一种是由于词类引申而产生的兼类。例如“荫”本为“树荫”,名词。《荀子·劝学》中提到:“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由于树荫有遮蔽和保护鸟儿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引申为“庇护”,从名词变成了动词。另一种是由临时性的活用变成了经常性的使用,从而形成兼类词。例如“目”本是名词,《左传》中出现了16次,只有一次可以理解为动词“看”。《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文献中的“目”的动词用法也相对较少,所以“目”作动词的用法在先秦时视为名词活用比较妥当。到了汉代,“目”的动词用法多了起来,并以“注视”和“使眼色”为其常用义项,这时便作为词的兼类而存在。
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兼类词有“一词两性”和“一词多性”。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名动兼类,例如领导、通知、指挥、笑话等;名形兼类,例如精神、意外、光彩、理想等;形动兼类,例如抽象、冤枉、概括、麻烦等;形副兼类,例如临时、定期、绝对、共同等;动副兼类,例如仿佛、肯定、胜利、瞎等;动介兼类,例如给、用、向、跟等;介连兼类,例如为、和、同、与等;名量兼类,例如口、尺、碗、勺等;动量兼类,例如回、封等;介量兼类,例如把;形动名兼类,例如方便、便宜等;名形副兼类,例如光、自然等;名动副兼类,例如保管、保险等。其中,以名动兼类、形动兼类和名形兼类最为常见。
通过梳理兼类词的类型和用法,可知兼类词这种“语言规则”是相对静止和稳固的,具有经常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即同一个词的每一类用法和意义都已被人们约定俗成,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同时,作为一个正式的固定含义被收进辞书。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得兼类词的每一个词性都是合法的,同时所有运用语言机能的社会成员都可以理解并使用。因此,可以将兼类词看作是对词类的归纳和认可,是汉语词义系统性和词汇规则性的体现。
三、言语层面下的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指的是“某些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其基本功能,在句中充当其他词类,这种灵活的运用称为词类活用”[4]。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临时性”和“灵活性”,读者必须联系整个句义,联系上下文才能明白词语活用后的含义。而言语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其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这与词类活用的特点有很大的相似性。
词类活用现象在古代汉语和成语当中出现得最为频繁,例如:
(1)晋灵公不君(名词用作动词)
(2)春华秋实(名词用作动词)
(3)焉用亡郑以陪邻(动词的使动用法)
(4)君子正其衣冠(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5)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名词的使动用法)
(6)以贤勇知(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7)友风而子雨(名词的意动用法)
(8)失期,法皆斩(名词作状语)
(9)争割地而赂秦(动词作状语)
以上几种用法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词类活用。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生动形象,讲求句子的押韵和谐;另一方面,使使用者更加注重对意义的阐述,渴望用更少的语言表达出更深刻的感情。如此来看,词类活用满足了言语活动中个人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但是由于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存在临时性,即不同的词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活用现象,所以无法将一些词的活用现象看成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词类活用也常见于文学作品和网络语言中,例如:
(10)百度一下(名词用作动词)
(11)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黄牛、水牛都欺生......(名词用作不及物动词)
(12)你这个党员还没正式吧(名词用作及物动词)
(13)很中国(名词用作形容词)
(14)真是杯具了(名词用作形容词)
(15)各种累各种忙(形容词用作副词)
(16)云计算(名词用作副词)
(17)我也很不爽这部剧(形容词用作动词)
(18)我们孤独着(形容词用作动词)
(19)这件事也太赞了吧(动作用作形容词)
(20)明星搭档素人(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
现代汉语中,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很快,新词语和词语的新用法层出不穷。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弥补言语活动中个人生理和心理的空缺。“各种+形容词”的形式是为了满足一个横向的、数量多的情感体验,它与“特别+形容词”这一表示纵向的、程度深的情感体验形式相呼应。但是,正是因为如今语言的流动性比较快,一些词语的使用热度并不持久,这就导致虽然使用的人很多,但是使用的时间却很短,所以很难将新出现的用法确定为“经常化了”的用法。
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都是一种新的用法。这种新用法,总是从一系列个体事实开始,属于索绪尔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些利用已有系统的特殊的而又纯属偶然的方式”。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凸显了汉语词汇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表现为用这种语言使用方式造出的句子不一定是完全合乎语法的,但是同样可以表达大众都能理解的含义,这是基于交际双方对已有“语言规则”的掌握。这种语言使用方式是言语活动的一种创新,只有当它被经常反复使用,铭刻在记忆中,并进入系统的时候,才能产生转移价值平衡的效果。而语言也就根据事实本身而存在,并本能地变化着,其外化表现即为一种说法用的人多了,也可以变为“语言规则”。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如果这种活用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5]。
四、结语
现代汉语中,兼类词和词类活用现象可以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出发进行讨论。兼类词具有经常性、稳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它是一种“语言规则”,是语言层面对词类的归纳和认可,是汉语词义系统性和词汇规则性的体现。而词类活用具有灵活性、临时性等特点,是一种“语言习惯”,它体现着汉语词汇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相似,当某些词类活用现象被经常反复使用,并进入到语言系统时,这种现象便转化为语言规则,相应的词便具有了兼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