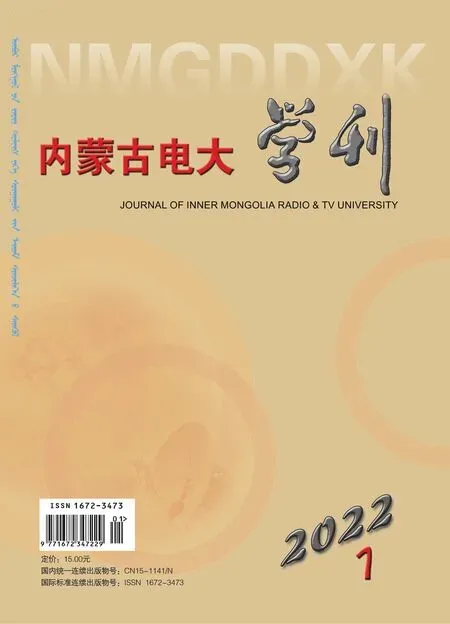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的国家责任探析
张 进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地震,引起近40米高的海啸,正面袭击福岛核电站的海啸高达14米,致使日本在役的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福岛第一、二核电站——严重受损。2011年4月4日,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将核电站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约1.15万吨核废水倾倒入海。2015年9月14日,东电公司开启“排水入海”计划,将2014年实验性抽取并保管的核废水倾倒入海。迄今为止,日本已多次向海洋倾倒核废水,不仅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而且危及其他国家及其国民的利益。本文首先厘清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逐一分析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是否符合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以及是否具有免责事由。
一、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国际责任是国际法的核心理论,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从传统的国家责任到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再到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最后至跨界影响的国家责任。[1]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以下简称ILC)认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就是“国家责任”。国际责任是指对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的责任。当国家的行为与其承担的国际义务不符时,损害了他国利益,国家就必须承担国家责任。[2]国家责任协调着国际法主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纠正国际不法行为、维护正常稳定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是一项国际法原则,构成国家责任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第一,国际不法行为可归责于国家而被视为“国家行为”;第二,国家的行为违背了承担的国际义务。前者一般被称为主观要件,后者被称为客观要件。
(一)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
构成国家责任必须满足主观要件,即某一国际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判断是否归因于国家需要通过国际法,而非国内法。国家违背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并非都属于国际不法行为,只有在可将该行为归责于国家时,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继而引起国家责任。一般认为,可归责于国家的行为主要有:第一,由一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实施的行为;第二,由外交代表实施的行为;第三,一国的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第四,一国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政府权力的行为;第五,经授权代表国家、政府的个人的行为;第六,通过叛乱、革命取得成功而建立新的国家或新政府时的行为。此外,一国国家机关未经授权、超越权限做出的行为也可归责于国家。总之,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整体上要求行为与国家具有联系。
(二)国家责任的客观要件
构成国家责任必须满足客观要件,客观要件是指国家的行为违背了承担的国际义务,违反国际法。这一行为可以是作为或不作为,作为是指国家通过积极的、直接的行为违背承担的国际义务,并导致他方利益受损;不作为是指国家通过消极的、放任的行为违背承担的国际义务,未有效地进行制止或补救进而导致他方利益受损。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存在一个现实前提,即国家做出或不做出行为时有关国际义务对国家仍然有效。如果不受某一国际义务的约束,显然不会导致违背国际义务的后果,自然亦不构成国家责任。ILC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17条规定,如果国家的行为构成对习惯法、条约或其他国际法中的国际义务的违背,都是国际不法行为,国际义务的起源不影响国际不法行为的定性和国家责任的构成。因此,无论违背的是因条约、习惯国际法或其他国际法而承担的义务,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都可能引起国家责任。
二、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的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分析
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要求某一国际不法行为可归责于国家,可被视为该国的国家行为。是故,要想判断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是否构成国家责任,首先必须分析东电公司倾倒核废水的行为是否可归因于日本而被视为国家行为。
迄今为止,日本已多次倾倒核废水入海。比如,2011年东电公司倾倒1.15万吨核废水入海。2015年东电公司开启“排水入海”计划,将2014年实验性抽取并保管的核废水倾倒入海。从主体看,倾倒核废水是由东电公司实施的,但实际上,日本政府完全控制、掌握着东电公司。东电公司虽为私营企业,但其主营业务——核电开发利用与其他种类的活动不同,核电产业具有高度危险性。诞生之初,核能利用、发展一直受到本国政府的严密监管。东电公司的任何行为都是在日本政府的严格控制和授权下实施的。2011年东电公司倾倒核废水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核原料物质、核燃料物质及核反应堆规制法》批准了这一行动。
可见,东电公司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行动工具”,东电公司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完全由日本政府控制。东电公司实际上成为首相的下属,其作用也只是传达首相的意图。[3]东电公司倾倒核废水的行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许可和支持,其倾倒核废水只是在执行日本政府的想法和计划。换言之,东电公司只是实施倾倒行为的“载体”,真正的意志完全由日本政府发出。
根据国家主权理论,一国对国内事务享有优先管辖权,但同时也负有不得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以损害他国利益义务,在“科孚海峡案”中这一原则已得以明确。同时,在“纳米比亚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法院提出如果一国控制着某一行为,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国家必须对其控制下的行为负责,这是基于优先管辖权的必然义务。在倾倒核废水入海这一行为中,虽然是由东电公司直接实施的,但完全处于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下,东电公司的行为显然可归责于日本,可以视为是日本的国家行为。另外,由于核事故责任的特殊性,1994年《核安全公约》规定了一切与核设施相关的安全问题必须由管辖核设施的国家承担,日本是该公约的成员国。因此,虽然倾倒核废水入海行为的实施主体是东电公司,但鉴于核事故国家责任认定方面的特殊性以及核能开发利用中国家和私主体利益相关性,东电公司的行为可以归责于日本,日本是这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主体。
三、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的国家责任的客观要件分析
国家责任的客观要件要求国家的行为违背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义务既可以源于国际条约,也可以源于习惯国际法或者其他国际法。有论者提出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违反了1972年《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如李毅认为日本倾倒放射性核废液是符合公约中的“倾倒”,且放射性核废液是公约禁止倾倒的“强放射性物质”。[4]彭丁带指出从整体来看,日本和东电公司排放核废水的行为有违《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5]此类观点乃是基于“结果说”和“目的说”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条约解释的角度来看,日本倾倒核废水的行为并不是公约中规定的“倾倒”,因为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是从陆地倾倒入近海,与《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规定的从船舶、航空器、平台等设施倾倒不同。如果强行将日本倾倒核废水解释为公约中的“倾倒”,有违国际法的判断标准和条约解释规则。整体来看,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主要违反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以下简称《及早通报公约》)。
(一)违背《海洋法公约》中的义务
《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的“宪章”,系统全面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保全的义务。日本于1996年6月20日批准加入《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其应当善意履行其中规定的海洋环境保护义务。
《海洋法公约》既从原则上规定了各缔约国保护、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还对各缔约国防止、减少、控制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的具体义务做了十分细致的规定。这些义务主要包括:第一,采取一切措施控制海洋环境污染来源的义务;第二,不得损害他国及其环境的义务;第三,不得妨碍他国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第四,采取合理措施,不得直接或间接扩大损害或危险范围或转变污染类型的义务;第五,在海洋环境即将遭受污染的迫切危险或已遭受污染时,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和国际主管机构的义务。[6]这些义务共同构成了日本在《海洋法公约》下应承担和履行的义务。
从事实角度看,2011年4月14日,东电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1.15万吨含有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废水排入大海。[7]2013年9月19日,日本气象厅官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论坛上表示,日本倾倒入海的核废水具有超600亿贝克勒尔的放射性物质,主要包括铯137、锶90。[8]这些核废水入海后无疑会引起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造成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美国《科学》杂志曾指出,将核废水倾倒在海洋中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将危害环境几千年,并有可能损害人类的DNA。[9]环境无国界,环境要素是相互连通和流动的。一个地方的环境灾难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其他地方的环境状态,危及其他国家和人民。[10]由于海洋是一个自然的流动的系统,日本不负责任地向近海倾倒核废水,虽然声称核废水的放射性物质检测结果已经符合排放标准,但事实并非如此。核废水入海不仅直接造成了海洋污染,而且核废水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变得更加不可控,核废水会随着洋流运动对他国管辖海域的环境和公海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妨碍他国行使本国的权利如捕鱼权,履行相关义务如保护管辖海域环境的义务。随着核废水的扩散,核污染的形式将从一个区域的一种污染形式转变成另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的另一种污染形式。譬如,德国一家海洋科学研究机构就曾对核废水扩散情形进行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在核废水倾倒入海后的57天内,辐射就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半年后高剂量辐射大规模扩散;只需3年,美国和加拿大就将遭到污染。在洋流作用下,放射性物质将扩散到整个太平洋甚至全球海洋环境。[11]另外,日本倾倒核废水并未向可能受影响的其他国家或主管国际机构通报,相反,日本故意进行秘密排放,有意不履行承担的义务。这些行为显然有悖于日本基于《海洋法公约》承担的义务。
(二)违背《及早通报公约》中的义务
基于苏联隐瞒掩盖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前车之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国际社会于1986年制定并通过了《及早通报公约》。公约旨在强化核能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借助各国提供情报尤其是核事故的情报预防核事故,或者在发生核事故时尽可能降低危害后果。日本作为《及早通报公约》的缔约国,应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通报义务。
《及早通报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本公约的适用范围,福岛核电站属于《及早通报公约》第1条第2款(a)项中的“任何核反应堆”。由此,日本福岛核事故可适用《及早通报公约》,是公约的调整对象。公约的核心就是通报义务,即缔约国对有关核事故的一系列事项的通报和情报提供的义务。《及早通报公约》第5条详细列举了缔约国应提供的情报种类,如核事故的时间、性质、起因等,包括了有关核事故紧急情况的进一步情报。这些事项共同构成了缔约国的通报义务。一旦发生核事故,缔约国应严格按照《及早通报公约》向有关国家和国际主管机构进行通报并提供情报。
根据文义解释,缔约国提供的情报应包括核废水处理情况。换言之,倾倒核废水入海亦应属于日本的通报事项之一。《及早通报公约》序言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措施减轻已经发生的核事故的后果。因此,将核废水处理纳入通报范围也符合《及早通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因为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事关避免放射性废物超越国界影响他国或公域环境。《及早通报公约》中的通报义务不是一次性的义务,基于风险预防原则,通报义务应是持续的,通报的内容和信息应当是充分合理的。[12]日本不仅应在核事故发生时通报他国和国际主管机构,还应将核事故发生后的与核事故相关的一系列事项通报他国和国际主管机构。然而,日本在排放核废水之前,仅通知了远在万里之外、几乎难以受到影响的美国,没有正式通知周边可能遭受超越国界影响的国家和国际主管机构,更没有提供处理核废水的情报,如时间、地点、放射性物质参数等。[13]韩国称在当晚19点才通过传真得知日本倾倒核废水,而俄罗斯发表声明称其在2011年4月6日才获悉日本倾倒核废水一事。[14]日本外务省在2011年4月13日的日本众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也承认,并未在事前就倾倒核废水一事向周边各国进行通报。[15]由是观之,日本单方面把核废水倾倒入海洋,不仅在核事故发生时没有及早向有关国家和国际主管机构进行通报,在倾倒核废水时没有向可能受到核辐射影响的国家和国际主管机构提供情报,或与邻国进行协商并提供污水核辐射浓度报告,日本未能切实履行承担的通报和情报提供义务。
四、不具有免责事由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规定国际不法行为必须可归责于国家才能引起国家责任,国家行为可能会因被排除不法性而不引起国家责任。[16]此处所指的“排除不法性”是指因某一行为满足免责事由而不具备可归责性,国家不对此承担责任。当代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因某些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可能会由于国际法规定或其他因素被排除不法性,此前产生的国家责任也就可以得以免除。
从理论上看,国家责任的免责事由主要有同意、国际不法行为的反措施、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危难与紧急状态。[16]就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这一行为而言,借助免责情形免除国家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故意倾倒核废水入海行为的自身属性决定了这些情形无法适用。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其他国家不可能容忍和同意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如日本在2020年10月17日声称要将123万吨含有放射性物质氚的核废水排入大海的举动不仅引发了日本渔业协会和福岛当地民众的反对,也招致韩国等周边国家的不满。[17]其次,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不构成反措施,因为反措施是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反应,倾倒核废水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显然不属于这种反应,道理不言自明。再次,倾倒核废水并非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而是日本故意为之。虽然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如地震引起了海啸这一自然现象,但将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应用在倾倒核废水入海行为中明显不合适。最后,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很难被认为是危难与紧急状态下采取的不得不为的行为。日本政府有多种选择处理核废水,如封堵核废水、向其他地方转移核废水、存储在油轮中。英国核燃料公司就曾采用提取、处理、贮存、玻璃固化等方式处理核废水。[18]实际上,自2013年以来,日本也提出了如地层注入、蒸汽释放、氢气释放和地下掩埋等多种核废水处置方案。[19]另外,即使核废水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且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紧急状态,但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不仅会使这一危险性加重,而且会导致一国的紧急状态演变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紧急状态。因此,不可能借危险与紧急状态免除这一行为的国家责任。概言之,日本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不具有国际法上的任何免责事由。
核废水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何况日本倾倒的还是超过法定排放标准500倍以上的核废水。虽然危害后果在短期内不会显现出来,但必然是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的。海洋不是天然的“垃圾场”,核废水的处理无疑关系着各国的利益,这从日本决定再次倾倒核废水入海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就可窥见一斑。倾倒核废水入海的行为可视为日本的国家行为,不符合公约的规定,违背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构成国家责任是无可辩驳的,且不具有任何可免责的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