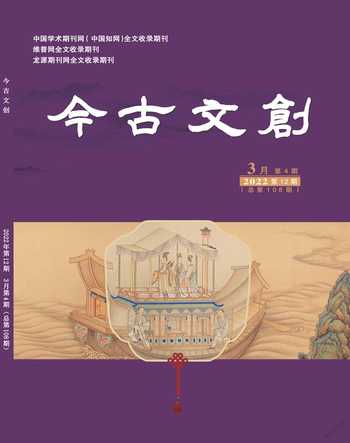“和合共生天下同, 漫瀚调调蒙汉情”

【摘要】漫瀚调是蒙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及生活中共同创造出的产物,是蒙汉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漫瀚调依傍着草原与黄河走来,其产生与发展无不体现着“和合”的人文思想。本文所提到的“和合”是建立在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理论之下,即是指:在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以及文明等多种元素之间相互冲突、融合,进而形成新的事物。具体来说,蒙古族的游牧文明、汉族农耕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所孕育出的音乐文化经过岁月的洗礼,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合而为一,产生出漫瀚调这一新歌种。本文通过对漫瀚调产生的梳理,通过“和合”这一人文思想,进一步讨论漫瀚调的多元文化交融性,进而尝试去阐释这一新歌种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漫瀚调;蒙汉交融;“和合”人文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2-0081-03
基金项目:2019年度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内蒙古蒙汉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交融研究》(课题号:2019NDA047);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血缘—地缘—业缘”三维空间下的漫瀚调》(课题号:CXJJS20065)。
《和合学》是由当代著名哲学家张立文教授所创建。“和合”这种人文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再生。引用作者的文本,“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内涵,也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内在意义;它是中华文化生命智慧和智能创新的彰显”。漫瀚调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一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文化形式,即漫瀚调。正如《和合学》中所说“和合是各生命要素的创生、发展、整合而融突成整体的过程,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描述”。漫漢调是蒙、汉民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整合融合而成的一种民族民间艺术,进一步研究漫汉调的交汇融合,也是对蒙、汉两民族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与描述。
一、《和合学》中“和”“合”
(一)和合的产生与发展
和合二字不仅是人类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形相及是无形相的组合,而且是人类对生存、意义、可能世界的自我观念及自我创造的活动。张立文先生说:“现代和合学,是传统和合论的转生,这个转生是批判、转换合创新式的转生,是化腐朽为神奇、转神秘为科学的转生。”因此,和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性的特点,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的全过程,和合二字存在于各时代诸家诸派的文化思想中,和合经历了由“和——合——和合”的发展。
从字形与意义上来讲,《汉字源流字典》中:“和,甲骨文从龠(口吹排箫),禾声。金文大同,古文简化,省作从口,禾声。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分别写作龢与咊。俗又改作和”。和,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而龠是一种多管的管乐器,因此,不同的音调声律相互配合,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而“合”一字,在《汉字源流字典》中有这样的解释:“合,从亼,从口,会器盖与器体相扣合之意。隶变楷书写作合。”合是一个共生体上的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种集合状态。
“和”与“合”作为两个单一的概念被提出来。殷周时期,《易经》中出现了关于“和”的阐释,而“合”字并没有出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在北坡鸣叫,小鹤与它相应和)中的“和”解释为声音相应和。“和兑,吉”,中的“和”解释为和谐、和善。《尚书》,“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中得“合”指符合,“罪合于一,多瘠罔诰”中得“合”指会合、聚合。
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共同被提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从和谐与聚合两方面来阐释“和”与“合”。春秋时期,各家各派分别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方面所产生的融突现象进行“和合”的探索。《尚书正义》中晏婴向齐景公用“味”与“声”类比政治,《国语》中,虢文公与周宣王谈论关于农业的问题时讲道“民之大事在农……和协辑睦于是乎兴”,其实,这里的“和协”已经具有了“和合”的概念。可见,从西周到春秋,围绕和合的辩论不但是当时思想与学术界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还是先哲们对于自然、政治、事物各种事物之间冲突融合的一种理性探索。《管子》一书“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则将“和合”二字作为一种连接的概念出现。
(二)《和合学》中的“人文和合”
在《和合学》中,张立文教授将“和合”二字作为一种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去阐述:和合是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和《周易》《管子》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同时也是东方日本文化 、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价值的取向。因此,和合作为一种人文精神,蕴含在中国各民族、各家各派的文化中,成为一种基本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又以“文”为本性或自信。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来达到“和合”。
二、漫瀚调中的人文和合
漫瀚调是蒙、汉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蒙汉两个民族属于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又由各自不同的个体构成。那么,在蒙汉两个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交融必定是由许多不同个体的交流与交融开始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漫瀚调产生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蒙汉两个民族交流交融上,实质上,漫瀚调的产生集当时准格尔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社会生态资源以及人文生态资源的综合发展。自然生态就是当时促成汉族民众向蒙地迁移的自然生态因素,社会生态就是当时蒙汉两个民族人民相处的社会环境,人文生态就是指进入蒙地的汉族与蒙古族团结友爱的人文情怀。以下将上述三点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
(一)促进漫瀚调产生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先秦时期准格尔旗已有人类在这里活动,那是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民众以游牧为生。后来,秦始皇派军队征服匈奴,在这一地区实行了军垦农业,军垦的劳动力成为最早进入到准格尔旗的外来民族。从14世纪开始,晋西北地区有大量的民众进入到蒙地谋生,历史上将这一大型的人口迁徙称为“走西口”。晋西北地区为黄土高原地貌,大部分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再加上降水量较为稀少。这样的自然环境让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农民贫困化加剧。因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去维持生存。而与山、陕一水相隔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是急需劳动力去建设与开拓,因此,蒙地便成为晋西北地区人民外出谋生的最佳选择。
清嘉庆、道光年间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同时,蒙古族王公贪图地租而私自放地,从此,汉族民众大量进入蒙地进行谋生。后来,清政府组织汉族民众移民到该地区进行垦殖,由此,清初政府全面开放了曾为隔绝蒙汉两民族而建的“禁留地”,俗称“黑界地”。这一政策让“私招私垦”变得合法化。清康熙三十六年(1689),清政府下令允许汉族民众进入蒙古地区进行垦殖,又设蒙旗垦务大臣和垦务局。与蒙地相邻的陕西、山西等邻省的汉族人民大量涌入内蒙古地区。进入蒙地的汉族民众从最早的雇佣到最后的定居,蒙汉两个民族开始了和合,有的还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组成的家庭。这样的例子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依然可以见到。曾经拜访过一位漫瀚调市级传承人——奇俊文老师和她的丈夫王怀玺先生就是这样的。奇老师是蒙古族,蒙语和汉语都会讲,王怀玺先生则是一位汉族,她们都出生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蒿召赖嘎查。
谈起她们村里的汉族与蒙古族结婚的现象,王怀玺先生讲道:
“听我父亲讲,我们家祖上原本是现在陕西省府谷县的一个村里的,后来那边发生了旱灾,颗粒无收,好多人被迫离开家乡到外边闯荡,刚开始来这边是给一家蒙古族的地主种地、打短工,一开始是每当春种和秋收的时候过来,后来家里老人不在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而后在这边成家立业。自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就来到这里,后来一直在这生活,但现在已经由四代人了吧。”
在他们生活的蒿召赖嘎查,已经不再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农田,在农田里活跃着各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嘎查里不见往日的蒙古包,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嘎查里由的村民还在自家的屋外还供奉着象征着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长矛的苏鲁锭,据奇俊文老师讲,每年农历三月十七她们都会在苏鲁锭前举行祭祀仪式,敬献哈达、神灯、全羊、圣酒,意在永远仰望苍天,日月相昭,平安幸福。
(奇俊文老师家门前的苏鲁锭)
蒙古族与汉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她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趋于融合,好多蒙古族也开始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她们的饮食也受汉族的影响,像炸菜丸子就是晋陕地区汉族日常的饮食,但现在在准格尔旗的好多地方都能看到。在漫瀚调歌词中更能体现这样的现象,在漫瀚调的歌词中有一种叫“风搅雪”的现象,所谓“风搅雪”就是在漫瀚调歌词的使用上,既有汉语又有蒙语,这源于该地区蒙汉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交流交融。晋陕地区的人民来到蒙地后,在劳动生产之余与当地的蒙古族一起娱乐,因此,在语言文化上也受蒙古族的影响,在歌词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如:
三十三颗荞麦“依仁依松达楞太”(蒙古语音译,译为九十九道棱),再好的妹妹“忽尼混拜”(蒙古语音译,译为人家的人),“毛日呀呼奎”(蒙古语音译,译为马儿不走)拿鞭鞭打,“奴呼日依日奎”(蒙古语音译,译为朋友不来)捎上一句话。
在歌词中,选用的词语较为精细,荞麦是当地民众一种熟悉的农作物,也是大家日常的一种食物“荞面碗坨儿”的原材料。因此,不论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对其都比较熟悉。不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听到上半句或者是下半句都能准确地猜出整句的意思。
漫瀚调所用的曲调大部分为蒙古族短调民歌的曲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智慧的劳动人民将这个地区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曲调填上新的词,有的将曲调稍加改动,就形成了漫瀚调的曲调。就笔者本人对于目前所搜集到的曲调来看,有很多都是蒙古族短调民歌的曲调,如《马什掌沟》《韩庆召》《达庆老爷》《韩庆大坝》等曲调在民间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将曲调与歌词分离开来,于是当地的民众就在这些曲调的基础上随人遇事、有感而发的填入一些即兴编的词进行演唱,因此,便形成了漫瀚调一种独特的蒙调汉词的结构。究其原因,这与短调民歌曲调短小、旋律优美的特点有关系,因而,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记住其旋律,将注意力集中在歌词的即兴编创方面。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漫瀚调随口编词、即兴演唱的特点。
以上充分说明,漫瀚调之所以能够产生,晋陕一带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其相邻的蒙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构成了一个互补的系统,成为蒙汉民族共生、共融的“天时”前提。晋陕地区由于与蒙地相邻,为蒙汉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优越的“地利”条件。晋陕地区的民众平时喜爱唱山曲儿、信天游,而蒙地的民众自古以来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共同的歌唱爱好成为蒙汉民族兄弟情谊的人文基础。虽然进入到蒙地的汉族人民与当地的蒙古族人民在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最终漫瀚调作為一种连接蒙汉两组人民情谊的优秀民间艺术便产生了。
三、总结
漫瀚调作为蒙汉两族人民友好团结的文化结晶体,从其产生的角度来看,无不体现着蒙汉音乐文化融合的魅力,是蒙汉人民群众用鲜明、生动、朴素的语言表达人民共同的思想感情和心声。蒙古族人民以宽容的胸怀、开放的心态去接纳来自其他地方的汉族人民,共同建设他们的家园,以至于产生漫瀚调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不仅完美地呈现了漫瀚调中所体现出的和合人文精神,而且实现了两个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转生。从漫瀚调产生所体现出和合人文精神来讲,漫瀚调作为蒙汉两个民族和谐共处人文精神的实证,那么对于当今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来说,人们要以这样的一种共处意识超越不自觉的外在他为的强制层次,为人类自觉的内在主动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魏)王弼,(晋)韩康伯注.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第1辑3:周易正义[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4]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M].上海:中华书局,2002.
[6]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上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7]准格尔旗志编纂委员会编.准格尔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8]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
[9]李克仁.走西口与漫瀚调[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白宇,男,汉族,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音乐与舞蹈学,研究方向:内蒙古区域音乐文化研究。
2853500783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