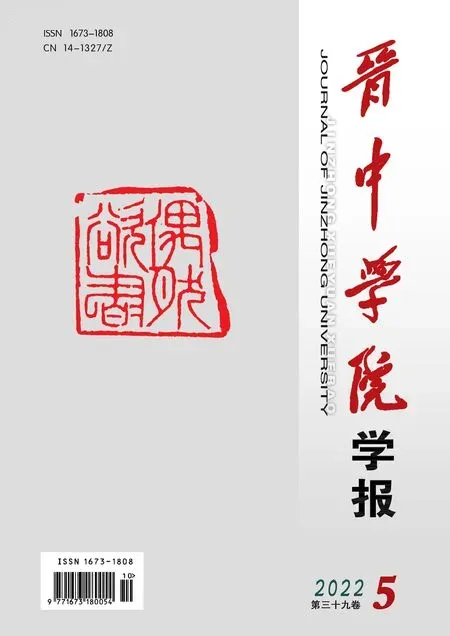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索
李冰强,张小康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黄河流域是一个水、耕地、森林、草原、岸线、湿地等多个资源要素汇集的区域,是重要的人口聚集地和经济建设区域。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也是急需解决的便是整个流域内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空间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以黄河全流域为单元践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进一步对我国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进行全方位管控,从流域全局出发,针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体系进行系统性治理,对整个流域范围进行统筹规划,从而进一步发挥我国国土空间管制的整体性合力,对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性治理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困境
(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与综合空间规划缺失,规划碎片化问题突出
自然资源监管的源头和用途管制的基础是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必要手段[1]。一方面,以往黄河流域以部门职权为主导的规划和沿黄各省(区)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规划互不衔接、标准不统一,缺乏在宏观层面上以空间规划为载体统筹考虑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城镇体系建设与乡村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国土空间综合规划。(1)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方面的相关上位法缺失,现行法规政策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力,但其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需求,这也对我国国土管控进一步发展的责任落实造成一定困难,亟需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体系,构建面向黄河流域所有自然系统的统一规划体系。
(二)国土空间布局缺乏合理性,黄河流域环境承载力超限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针对黄河流域的国土管控政策实际上主要针对耕地及建设用地,缺乏对整体空间的规划考虑,从而导致黄河流域在发展过程中无法形成自身缓冲地带,与我国所制定的黄河大保护要求相违背。当前,黄河流域的污染问题已经由原来的主要的工业污染源转变为工业、生活、农业三方交叉污染,其根源在于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布局缺乏合理性,空间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除此之外,在黄河流域相关补偿方案未落地前,地方的国土空间布局纠错动力不足,流域空间错配纠错机制的建立存在较大困难,进一步加大了黄河治理的难度。
(三)单要素管理模式尚未形成水陆一体化的系统整体管控模式
黄河流域包含了水、森林、耕地、草地等在内的众多自然资源要素[2]。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开发保护应以各环境要素为基础实行综合治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黄河流域的治理整治目标单一、治理手段简单,难以体现生态环境各要素相互联系的关系。一方面各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方式,虽针对性较强但割裂了生态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对黄河流域生态空间功能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认识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在针对相关问题制定治理方案时,仍然过分坚持“就河论河,就水治水”,忽视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命共同体内在的关联性。
(四)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不完善
2018 年行政体制改革后,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这样的行政机构职能整合有助于国土空间的集中管理,但是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过程中还涉及到除自然资源部门外的其他部门职责,此外如何将黄河流域的管理体制与我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有效衔接,是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关键。此外,针对水资源的建设与保护政策并不十分明确,上下游之间所规定的生态保护线也只是空间地理的约束,并不足以约束水资源的流动,实践中管制的具体对象尚不清晰。管制手段方面,现有用途管制措施简单粗暴,强调刚性管控,忽略了流域治理中的时空差异,针对黄河流域不同的生态特征和季节性的流量变化缺乏差异化、精细化的管制手段。
二、黄河流域治理中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价值凸显
(一)完善黄河流域空间用途管制是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内在要求
全域全类型管制是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要求[3]。我国“国土空间”的具体概念已经由原来的“国土”定义转变为现在的“带有经济属性的自然资源及要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质内涵是运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对于耕地、林地、水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管制,对各种资源要素开发利用行为进行监管,达到优化空间资源利用的目的[4]。我国长时间内形成的由各个部门分散管理自然资源的单一管制手段和内容已无法满足生态系统建设的需求。黄河流域是由“山水林田湖草”等多种要素共同聚合而成的,其空间特性和空间范围内所存在的复杂利益关系,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这一生态环境治理利器的使用提供了场所。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视阈下,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完善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机制,有利于实现黄河岸线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布局。
(二)构建基于全流域统筹的用途管制体系是黄河流域治理的现实需求
我国的空间治理是按单元进行的,即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实施——实体性单元治理的。这种传统的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导力量的流域管理模式在现今条件下其碎片化、短视性等弊端日益凸显[5]。跨行政区域的治理单元是虚体性治理单元[6],它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域的限制,是一种有效的国家空间治理手段。黄河流域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单元,必须选择全流域型虚体性治理手段。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统筹推进黄河全流域国土空间开发和完善黄河流域治理体系的重要战略手段,通过统筹规划国土空间,建立全域全要素的保护对象体系,打破目前黄河流域各种资源要素、各行政区划的隔绝状态,可以改变过去标准体系庞杂、各地标准不一的混乱局面,加强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改进黄河流域整体保护[7]。
三、健全完善的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路径探索
(一)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专门立法
目前,我国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流域综合法规,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迫切需要专门性、综合性的《黄河保护法》,而《黄河保护法》需要确立完善黄河流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将黄河流域内的一切自然资源均纳入考虑范围。《黄河保护法》的目的在于协调各个流域的关系,明确黄河流域治理机构的责任,统筹资源分配和利益规划,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目标。因此,在未来的《黄河保护法》中应加快构建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分区分类用途管制法律规范,要落实好黄河流域用途管制方面的央地事权划分及具体责任,监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权力运行,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强度、“三区三线”划定等有关内容进行规定,建立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有效程序和保障体系,通过流域综合立法对这些黄河流域进行系统部署和科学防治,牵制住流域全面整治和系统治理的牛鼻子,为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同时也为今后《国土空间规划法》《国土空间用途管控法》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管控法律体系提供地方实践基础。
(二)构建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在黄河流域现有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对当前涉及各项自然资源的规划进行梳理,以流域空间为单元,将流域各省市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系统整合,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加强空间规划整体的协调性。(2)在空间规划中要明确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流域、左右岸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空间的未来发展目标,综合考虑黄河流域各省的环境承载力,贯穿山水林田生命共同体的综合理念,进行生态分区并编制详细规划,通过统筹规划来综合布局全流域发展,量水而行。严格按照国家关于生态区、城镇区和农业区的划分依据,对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进行严格监管,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目标要求。在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央地事权进行重构,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制定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准入清单
合理优化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的布局,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准入清单,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提高准入条件,制定明确的土地空间行业准入目录,建立生态节约型的利用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制定负面清单,明确行业限制和空间准入禁止目录,从源头严防严控,避免再产生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此外,应当划定特殊管控单元,对于污染严重的区域要重点管控,将水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作为重点管控区域,加强陆源污染防控和污染源头排放监管,实行负面清单管控制度,禁止使用化肥和农药,禁止规模化禽畜养殖等。
(四)构建河流及沿线周边一体化的系统整体管控模式
贯彻全要素统筹管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念,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上中下游的协调性贯穿到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坚持水陆统筹的理念,构建以全流域为单元的黄河流域用途管制体系,有序开展黄河流域开发、保护与修复各类活动。首先,对于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应当以自然修复为主,加强如三江源、甘南、若尔盖等区域的生态修复力度,提升区域的生态供给能力。其次,中游地区要坚持水资源合理分配,加快产业转型发展,限制污染企业排放和风险企业的发展。最后,下游地区以修复生态环境系统为主,对流域内整体的生态环境体系进行综合治理,严格管控黄河流域生态空间转用,支持黄河沿线建设用地转为生态用地,从源头上预防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五)加快构建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指导下,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复杂性难题,构建以黄河流域为单元的空间用途管制体系,运用全局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管控手段,从源头预防流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首先,要明确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控主体责任。《宪法》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所有权,那么针对环境进行保护与监管也同样属于国家的责任,但是国家是虚拟监管主体,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及其部门有义务承担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职责,在黄河流域治理的全过程中进行管制和参与。其次,要明确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对象。管制的对象包含黄河流域涵盖的国土空间及其附着的各类自然资源、以黄河流域为载体的开发利用等人类的活动,其中最核心的需要管制的对象是人类的行为,包含建设活动与非建设活动。最后,要丰富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控手段体系。一是通过空间规划来合理布局,科学安排顶层国土空间布局,合理分配黄河沿线资源,有效配置土地资源,通过污染防治和限制资源方式倒逼污染企业转型,提倡资源重复利用落实节水节能的政策,向绿色和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家生态友好型的目标要求。二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管控,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重要性的空间和自然资源设立不同的管理规则,弹性和刚性相结合,最大程度发挥制度的普适性,在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上,实行地上地下间、水陆间差别化管制,最终实现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1]。
总之,黄河战略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全域、全类型、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建设要与当前强调黄河流域整体性、协调性发展内核相一致,构建完善的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冲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条块分割的架构和行政管制的单一结构,形成强大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治理格局,实现黄河流域的系统治理目标。[8]
注释
(1)现阶段我国涉及国土空间的规划众多,由政府编制的各类法定规划有80 多种,不同规划之间在基础数据、规划内容、规划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国土空间利用方式与用途管制上相互矛盾。
(2)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有机融合”,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