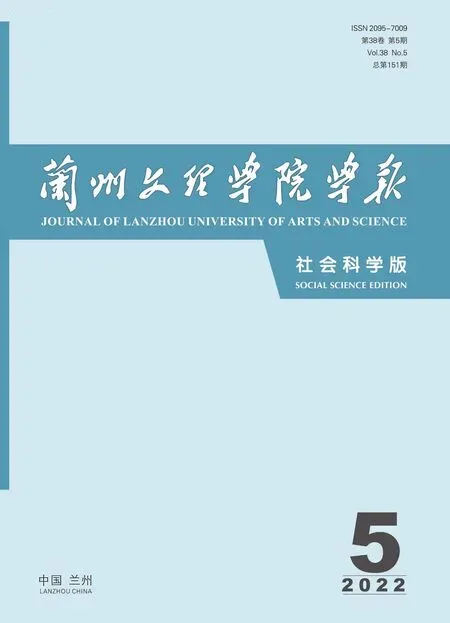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甘肃文学外译现状概览
马 冬 梅
(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创作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风貌。在重返文化自觉、重塑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甘肃文学在作品数量、创作质量、传播渠道、队伍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文艺评论家杨光祖所言:“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一种城市与乡土的碰撞,开始出现在甘肃作家的笔下,甘肃文学终于融入了全国文学的合唱”[1]。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著名作家马步升看来,“甘肃文学也到了全面繁荣期……小说题材涵盖乡土的、都市的、历史的、儿童的、玄幻的,等等,国内文坛所涉及的题材,甘肃作家都曾涉及,也都有可观的数量和相应艺术水准的作品出现。至于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网络文学、文学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都形成了阵容整齐的创作团队”[2]。综观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艺术表达,甘肃文学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地方品格而个性十足,引起广泛关注,获得海内外读者的青睐,为文学外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从译介内容、译介主体、译介策略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概述甘肃文学外译之现状。
一、译介内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甘肃小说创作中,王家达、牛正寰、邵振国等人的作品很有代表性,被经常译介到国外。其中,王家达的中篇小说《清淩淩的黄河水》讲述的是年轻、俊俏的尕奶奶和来村里“要饭的年轻人”二哥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成功刻画了一位像黄河一样汪洋恣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西部农村妇女形象。小说最初发表在《当代》杂志1984年第2期,1988年收入《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The Chinese Western: 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一书,由纽约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地发行。牛正寰的短篇小说《风雪茫茫》讲述的是特殊年代的人间苦事,小说原载于《甘肃文艺》1980年第2期,后被《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引起较大争论,1992年收入《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由纽约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出版发行。邵振国的短篇小说《麦客》主要写出生于陇东庄浪的父亲吴河东和儿子吴顺昌两代麦客,为了生计,到陕西赶场割麦,经历各种诱惑和考验,彰显了人性的坚韧和善良。小说原载于《当代》杂志1984年第3期,后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入选中等师范学校《文选和写作》等多种教材和选本,曾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改编为电视剧,影响广泛。1988年,《麦客》英译本发表于《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春季刊。 2007年,《麦客》被收入由莫斯科АСТ出版社和圣彼得堡Астрель出版社联合发行的《红云: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一书,向俄语读者公开发行。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甘肃小说创作中,雪漠、马步升、叶舟、严英秀、徐兆寿等人的作品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其中,叶舟的中篇小说《姓黄的河流》“请一位叫托马斯·曼的德国青年来兰州,在姓黄的河流旁……讲述一则远方的故事”,故事里有艾吹明和妻子迟牧云的日常危机,也有托马斯·曼(李敦白)神秘复杂的命运身世。小说原载于《钟山》杂志2010年第4期,后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先后翻译为英法日韩等十几种文字,借助互联网络广泛传播,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雪漠的短篇小说《新疆爷》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位中国西部老人关于“爱”的故事,“新疆爷”在新婚之夜被抓壮丁,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逃回,不料自己的新娘已被卖为人妻,无奈之下,孑身一人的“新疆爷”只好以贩卖水果为生,终其一生帮助曾经的“妻子”一家,用苦难温润人世间的大爱。小说原载于《飞天》杂志1999年第3期,2012年被英国著名翻译家、英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席、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译为英文,在《卫报》(The Guardian)上推荐发表,赢得了广泛赞誉。201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小说系列英文译本,其中包括雪漠的《雪漠小说精选》《大漠祭》《猎原》等。严英秀的小说集《纸飞机》包括《玉碎》《纸飞机》《沦为朋友》《芳菲歇》《前后左右都是喜事》《自己的沙场》等多篇小说,以日常生活中的现代人为表现对象,一次次地发掘成长中的疼痛与坚守过的梦想,2015年其英文版首次由英国欧若拉出版公司(Aurora Publishing LLC)出版,之后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译出版社于2016年再次发行,同时以电子书形式向海内外传播,影响较大。此外,徐兆寿的小说《生于1980》《非常日记》被译介到越南,张弛、马步升、王新军、弋舟、向春等作家的小说作品也被零星地译为多种文字,走向海外市场。
相对于小说而言,诗歌因篇幅短小,更加容易赢得翻译工作者的垂青。甘肃是诗歌大省,著名诗人和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不断涌现,在新时期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甘肃文学的外译过程中,诗歌涉及的范围更广,数量更多。可惜的是,因材料散佚和时间仓促,本文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挂一漏万,点滴呈现。老一辈诗人中,高平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诗歌创作与时代同行,先后出版短诗集《珠穆朗玛》(1955)、《拉萨的黎明》(1957)、《心摇集》(1992),长诗集《大雪纷飞》(1958)、《古堡》(1979)、《冬雷》(1984)等10多部,是国内诗坛的常青树,经常代表甘肃参加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的会议,获得过许多荣誉。2001年,高平的诗集《高平短诗选》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发行。次年,《高平短诗选》的英文重译本再度由该社出版发行。中青年诗人中,娜夜的诗歌创作以冷冽细腻见长,其诗集《睡前书》被译作英文,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高凯的诗歌创作追求纯粹、简约、质朴,有时甚至充满了童趣,他的诗歌作品,国内举办的几个国际诗歌节零星翻译过一些。另外,关于诗歌和童年的一本长篇随笔《高小宝的熊时代》被译为英文,由英国卡兹班出版社出版发行。古马的诗歌里根植着一种流浪的情愫,常常在不经意间把读者引至自我的山山水水。阿信久居甘南,他的诗歌创作像还愿似的,把神衹借给他的所有意象,通过文字又原原本本、很有节制地还给了多年经营的情绪。古马和阿信的诗歌作品,与另外11位当代中国诗人陈先发、胡弦、毛子、雷平阳、蓝蓝、汤养宗、王家新、李少君、潘维、池凌云、于坚一起,被收在一部名为《十三片叶子》(Thirteen leaves)的诗集当中,该诗集由旅美作家谢炯(Joan Xie)和Sam Perkins合译为英文,由纽约Three Owls Press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发行。诗人阳飏和人邻的部分诗作也有被翻译成英文,被读者所接受,也有部分诗歌作品在美国的华人诗刊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现。新生代青年诗人中,藏族诗人扎西才让早年以狂放的想象驰骋诗坛,近年来潜心于民族题材创作,诗风偏于冷静,忠实于语言本身,忠实于自然的哺育。他的诗作被译为英文,选入Mark Bender主编的《亚洲边疆》(The Borderlands of Asia: Culture, Place, Poetry)一书,该书作为坎布里亚汉语语系丛书之一,在英语世界大量发行,影响较大。当然,更多诗人的作品被断断续续地译作英文,在纸媒和网络平台上传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份名为《廿一世纪中国诗歌》(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的季刊,由美国华盛顿同道Pathsharers Books出版发行。笔者检索发现,从2012年起,从中可以发现许多甘肃诗人的身影,主要有牛庆国、叶舟、阿信、离离、娜夜、李志勇、阳飏等,刊登的都是这些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从2018年开始,Pathsharers Books与中国诗歌网进行合作,开展汉诗英译活动,有不少甘肃诗人的作品因此而被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另外,甘肃诗歌外译,不只是英文,还有其他语言文字的译介情况。如2019年出版的名为《要走的路还长》的韩语诗集,其中收录了50多位甘肃诗人的诗歌作品。
小说和诗歌以外,文学翻译的对象就变少了,甘肃的数量更加稀缺。据作家自己介绍,王家达的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曾被译为日文和韩文,在日本、韩国面世。雪漠的随笔《无死的金刚心》《世界是心的倒影》等作品被译为英文,在欧美国家发行。此外,还有少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其他文字,连同上述所有被翻译的文学作品一起,接受跨文化的洗礼。
二、译介主体
文学作品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介主体的知名度、权威性及被读者的认可程度等都会影响译介效果。通常来说,译介主体的知名度越高,译介效果就会越好,反之效果将大受影响。
梳理新时期以来甘肃文学的外译现状,我们发现,小说的译介主体大多为知名度较高且为读者所信赖的译者,比如韩斌(Nicky Harman)、史蒂芬·伯姆瑞(Stephen Pomroy)、刘祖勤(Liu Zuqin)、柯利瑞(J.C.Cleary)、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及其夫人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墨普德(PriyadarsiMukherji)等,大多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已成功翻译多部国内知名作家的作品。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推手。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翻译和推介,莫言的作品才能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了解和接受,从而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上世纪70年代起至2015年,葛浩文“翻译、出版了37位作家的 66 部小说、小说集、诗集译著(不含再版、修补版译作);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评论在内,他共出版(发表)了96位中国作家的201部(篇)作品的译作”[3],可谓“译作等身”,其中包括多位国内著名作家的作品,如莫言、贾平凹、杨绛、萧红、张洁、李昂等。由此可见,葛浩文的国际知名度首屈一指。如此名家翻译出的作品,译介质量必定有所保障,受欢迎程度指数亦不会太低。近年来,葛浩文对甘肃作家雪漠的作品情有独钟,被其作品中所描绘的西部荒漠、河西走廊等神秘元素所吸引,难掩偏爱之意。“看雪漠的作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阅读经验,翻译他的小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葛浩文在《大漠祭》《猎原》英文版首发式上如是说[4]。截至目前,葛浩文夫妇已翻译出版雪漠代表作“大漠三部曲”中的《大漠祭》和《猎原》,“三部曲”中的《白虎关》和雪漠另一部重要作品《野狐岭》也正在翻译之中。
相较而言,甘肃诗歌的译者较为多元,有业余爱好者,也有专业翻译团队。以前文提到的《廿一世纪中国诗歌》(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为例,其中的翻译活动主要由美国同道出版社(Pathsharers Books)“鸭先知” (Duck Yard Lyricists)编译团承担。这一翻译团队的名字源于宋代名家苏轼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有四位成员,分别是:Meifu Wang, Peter Micic, Michael Soper,和Johan Ramaeker。团队中的Meifu Wang (王美富)是美籍华人,生于台湾,获台湾大学外文学士,加州大学和普度大学双科学硕士,现任《廿一世纪中国诗歌》主编兼翻译。Peter Micic (彼得)是澳大利亚墨尔本人,通晓多种语言,蒙纳西大学语言学学士,音乐硕士,音乐历史学博士。Mike Soper(苏浪禹)是美国华盛顿人,曾任报社编辑,对中国文字和诗歌有浓厚兴趣,已出版四本个人诗集。Johan Ramaekers(约翰)是比利时根特城人,通晓多种语言,诗人,歌词作家。很明显,“鸭先知”团队专业程度高,学术背景强,在翻译界有一定知名度,是读者可以信赖的翻译机构。与源语语境的本土译者(译出译者)相比较而言,他们具有更强的目标语语言能力,更通晓目标语文化,更善于在目标语环境中对译作进行系统运作。从中也不难看出,甘肃文学“走出去”的起点较高。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水平的专业译介主体更多地瞩目于甘肃文学,就一定能够把甘肃文学向全世界传播出去。
三、译介策略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不仅是两种语言的文字转换,还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受制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魏泓等认为,“翻译系统与原作系统、传播与接受系统、研究系统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另外,经济政治等无形系统也会影响着翻译系统的运转与优化”[5]。可见,制约译介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多,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和互相作用都会对翻译行为乃至最终译作产生一定影响。翻译质量的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西方汉学家群体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为了满足读者预期,大多遵守译入语文化规范,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大胆删减、修改,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葛浩文就认为,“译者需要同时做三项不同的工作:阅读、阐释(或批评) 与创作”[6]。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者、译者,汉学家们具有独特的见地,更熟悉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对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也具有很高的敏感度,面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他们会从“增益”的角度出发,力求平衡,对原文进行再创作。“译者的‘创作’ 不在于故事的原创性, 而在于故事的新的呈现方式, 包括风格(厚重、现代、嘲讽、简洁、深邃、俚俗, 等等) 与话语习惯(句长、节奏、措辞, 等等)”[6]。葛浩文曾明确地说:“就其本质而言, 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归化(domesticating)与现代化(modernizing)的一种努力, 是真正的转换, 这一点无可改变”[6]。
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甘肃文学外译作品中的翻译策略主要以“归化”为主。以葛浩文翻译的《大漠祭》为例,译者就非常灵活地处理了原文中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词句。如“兔鹰长着千里眼,看不见眼前三尺网”[7],句中“千里眼”“三尺网”中的“千”和“三”并不表示具体实际数目,而是虚指。汉语数词这种弃实就虚的现象实则变成了一种修辞手段,有生动夸张之功效。葛浩文深谙此道,没有将数字具体翻译出来,而是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其译为“With eyes that can see for miles, it did not notice the snare right in front of it”[8]。仅举一例,或许无法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但是,从翻译策略选择的角度看,国外译者的优势就在于对目标语文本的敏感和把控,读者取向下自然会以“归化”策略为主。而在现阶段,“归化”策略的选择,不仅会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而且也是甘肃文学外译的最经济的选择。
当然,文学翻译离不开出版行业等专业机构的传播与推广。就当前国际合作的主流而言,出版界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内出版机构与国外出版机构联合,充分发挥对方成熟的营销主渠道作用;另一种是国内个别知名出版机构尝试在海外建立分支,以实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本土化。相较而言,当前甘肃文学外译的传播途径还略显单调,主要由国内或国外出版社独立出版,尚未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多种交流渠道,尚未进入政府主导的对外推介项目或平台,尚未主动选择合作对象。对外输出渠道单一,势必导致传播效果不理想。
四、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事业也随之发展。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文学外译的规模更加蓬勃壮大。与火热的全国情形相比较,甘肃文学的外译现状不容乐观,作家和作品数量较少,相关信息搜集困难,材料难以查证。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作家们在其简介和接受采访中谈及自己的作品被翻译为一种或多种文字出版,但是无法提供具体而准确的支撑材料,究竟是哪部作品在什么时候被翻译为哪种文字。限于时空阻隔和语言瓶颈,我们多方动员,反复核实,也只能大致勾勒出当前甘肃文学外译的粗线条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中国文学主要外译渠道中,甘肃作家作品比较少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外译,主要途径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学主动“走出去”,以办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为代表,及时精选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向海外读者推介。据统计,《中国文学》自1951年创刊以来,20世纪80 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达到顶峰,共出版590期,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有英文和法文两个版本,总印数在6万份以上[9]。此外,进入21世纪以后,先后启动了多项中国文学翻译工程,如国新办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发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申请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等。二是海外出版社与汉学家、翻译家合作,自觉地译介中国文学,主要有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杜迈克(Michael S. Duke)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后毛泽东时期的小说与诗歌》(1985)、《中国的小说世界》(1991)等[10]。三是互联网络兴起以后,文学爱好者和翻译爱好者自发地译介中国文学,由无序逐渐过渡到有序,由网络空间逐渐扩展到线下的现实空间,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纸托邦”(Paper Republic),原本是一个翻译爱好者施展语言才华的公益性平台,由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创办,起初主要“依靠译者个人趣味确定作品的选择、译介,依靠单篇作品在海外杂志的发表,依靠单个作家在海外文学节上的交流”[11],从而逐步推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后来与《人民文学》合作出版《路灯》(Pathlight)杂志,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作家的优秀创作。据笔者统计,以上三种渠道中,甘肃作家作品都比较少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可能与甘肃文学的创作实绩有关,在全国文学创作的百花园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无论代表性还是影响力,甘肃文学既没有形成历史群像,也没有达成时代合力,没有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一些文学创作之外的因素有关,作家完成创作以后,其作品的生命延续就交给以读者为中心的出版和阅读市场了。文学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牵涉的要素有所不同,每一种要素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而在文学传播的某些要素的调度和利用上,甘肃长期处在一个落后的状态。
二是对文学外译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甘肃文学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甘肃作家群是一个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作家群体。他们坚守西北地域文化阵地,以大西北这片黄土地为依托,以陇原历史文化为根本,围绕丰富而厚重的始祖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黄河文化、伊斯兰和藏传佛教文化,基于现实生活,积极开展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勾勒出了西北人,特别是甘肃人的原生态生活,书写着陇原大地浑厚质朴、苍凉贫瘠的“西部风情”,也记录着这片热土的传统、突破和创新。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丝绸之路”不断升温,“敦煌文化”星光闪耀,古朴的陇原,神秘的河西,无不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毋庸置疑,特色鲜明的甘肃文学有效地“走出去”,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国外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西部,鲜活的西部文化,强化“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然而,在我们大力对外宣传敦煌文化、西部风情的同时,对生于这块热土、讴歌这片热土的文学作品的对外宣传和推介还远远不够,没有积极主动选择将其中优秀的作品翻译推介出去,也没有系统成熟的组织或机制去完成对外推介的工作。很多优秀的作品,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无法引起较大的反响,也无法吸引译者或出版机构的眼光。换言之,在甘肃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的过程中,在加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各项措施里,对于文学外译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笔者翻阅《新时代甘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文化制高点实施方案》(2019)、《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等政府文件以及甘肃省文联的相关工作报告,均未发现有关甘肃文学外译的规划设计。对偌大一个省的文艺事业而言,文学外译或许属于领域较小的范畴,但是,从文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真正把文学外译重视起来,它的带动作用还是很大的。
三是本士翻译人才匮乏。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引人注目,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中国文学也尝试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学领域。包括甘肃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必须借助翻译人才的力量,因为“翻译始终担负着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12],优秀的翻译人才是确保文学翻译数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就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好的作品,而是翻译得不够,合格的译者太少”[13]。如果单纯依赖海外学者或汉学家的翻译,往往使译介作品局限于译者的学术背景、汉语水平和个人喜好,不能全面推介国内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也不能主动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化成果。要想真切地反映我国国内的生产与生活,让中国文学不仅“走出去”,而且“走进去”,更多的则要靠本土翻译人才的努力。本土译者最大的优势是对源语文化和语言的熟悉度,对作品的选择能够较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突显社会热点,实现主动选择。与此同时,本土译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更加深刻,有助于全面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传递作品信息。当然,本土译者如果能够和国外译者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会是一种理想化模式,把各自的优势突显出来,扬长避短,相得益彰,从根本上保证各类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然而,从全国的趋势来看,我国目前依然缺乏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著名作家张炜几年前曾说过,“在文学走出去中翻译问题成为重要掣肘,好的译者不多,尤其那种能把作品的意境、语言的特质,甚至地域色彩都能呈现出来的译者,更是少之又少。翻译不是简单的技术工作,懂中文、能够流利地用外语表达并不够,它是一种语言艺术向另一种语言艺术的转换”[14]。相比较而言,甘肃省内的翻译人才更加匮乏。以高等学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为例,截至2021年,甘肃高校中设有外国语学院或外语系的院校有19所,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的统计数据,只有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兰州城市学院和兰州文理学院等少数几所高校招收翻译专业本科学生。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交通大学招收翻译专业硕士,每年毕业的本科生人数不足两百人,专业硕士约100人,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等学校也招收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学术性研究生。他们中从事文学翻译且符合作家们高标准高要求的优秀毕业生更是寥寥无几。
总而言之,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艺术作品是世界人民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15]。由此观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之路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甘肃作家“走向世界”的梦想依然在路上。然而,“路虽弥,不行不至”,只有主动选择优秀的作品、译者,培养固定的海外读者群,遵循出版发行和文化传播的规律,才会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