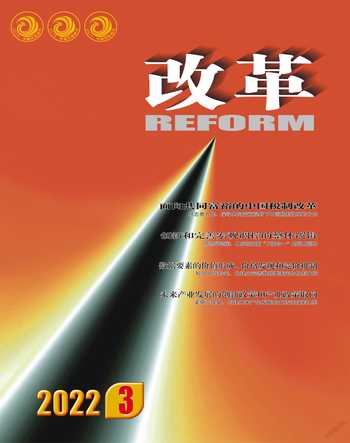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及其经济效应:综述与展望
余泳泽 尹立平
摘 要:通过对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的梳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探讨中国式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式环境规制是以政府行政命令和绩效考核式为主,并与市场式规制工具相结合的一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方式;第二,就宏觀层面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更多是通过前期成本效应和后期补偿效应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双赢,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贸易利得,抑制了产品出口;第三,就中观层面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一定程度上促使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并促进了技术创新,提高了产业效率;第四,就微观层面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增加了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负担,迫使在位企业改进生产与经营方式,实现了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提升。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环境规制的社会功能,合理测度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协调配合的作用机制,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中国式环境规制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方面。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应强调引导环境规制良性竞争,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畅通公众环保诉求渠道,灵活运用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形式,促进中国式环境规制与市场化工具相结合,保证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正向经济效应的有效发挥。
关键词:中国式环境规制;环境绩效考核;经济效应;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3-0114-17
中国依靠重工业先行的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3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全部城市数的40.1%。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导致社会福利降低,更给中国造成了约占GDP 8%~15%的经济损失[2]。加强环境治理、减轻环境污染,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已成为当下全社会共识。
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各项环境治理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98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出台,1998年实行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2003年《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实施,都凸显了中央保护环境的决心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地位。2006年,中国将减排目标分解落实到省级层面,逐步实现了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的转变,由环境规制“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实施环境税收或财政补贴等市场化为主的环境规制方式,中国主要采取行政命令式或者政府绩效考核式的环境规制方式。例如,2009年中国发布《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管理办法》,正式推行环保督察制度。2015年,中国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2016年底全面推行的河长制,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任命为河流的污染治理责任人,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益,为破解环境治理低效难题提供了新思路[4]。“十一五”以来,中央将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确立为约束性指标,并将其完成情况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蕴含了中国特色环境规制方式的独特探索。那么,这些环境规制到底有没有作用,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中国式环境规制的政策演进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中国式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方式、增强环境治理效果提供文献支撑。
一、环境规制的相关理论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Grossman & Krueger建立了环境质量与国家收入水平之间的经验关系,发现了污染排放水平与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曲线关系,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5]。国外许多文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普遍采用污染绝对水平或污染强度来衡量环境质量的退化程度,但没能取得一致结论。一方面,支持者认为,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确存在。甚至一些学者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从倒U型扩展到了N型(或倒N型),认为存在两个转折点[6]。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发现倒U型、N型或倒N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存在。研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能否得到证实或者其形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的选取:SO、NOX 等重点监管的污染物,与CO2和固体废物这类没有得到普遍重视的污染物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如,Shafik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线性上升态势[7]。但Perman & Stern的研究认为,在硫污染物和GDP之间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8]。
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相继开展了关于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主要从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拐点的位置,以及其他经济因素是否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
关于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的验证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9];二是认为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10];三是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不存在[11];四是考虑到区域异质性,研究得到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但是西部地区不存在该曲线[12]。
关于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位置的探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段,离转折点尚有一段距离。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当前大部分城市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但已临近转折点[9]。二是具体到中国各省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研究,宋马林、王舒鸿发现,上海、北京等省份已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而辽宁、安徽等省份则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3]。
关于其他经济因素是否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目前文献主要从国际贸易、FDI、外贸和环境政策、财政分权等方面考虑其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所得结论不一[14]。
(二)波特假说
在探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文献中,波特假说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研究大多认为环境规制会挤占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不利于企业进行创新投入。但是,Porter & Van der Linde认为,严格且适宜的环境管制将引致技术创新,这可以部分或完全补偿企业遵守该环境标准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15]。此后,很多文献对“波特假说”的存在性进行了验证。一方面有不少文献证实了环境规制与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16],另一方面有文献对波特假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技术进步本身难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有的新技术会降低污染,有的却会增加污染,环境规制更严格的产业可能会出现竞争力下降[17]。
具体到关于中国情境的研究,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同样未在文献中达成共识,但是总体上多数文献所得结论支持了波特假说[18-19]。很多学者根据中国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分析中国是否实现了波特假说,归纳如下:一是支持者发现,2000年APPCI修订政策显著提高了空气污染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其边际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20]。还有学者以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地区和行业層面研究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减排效果和经济绩效[21-22]。二是质疑者发现以二氧化硫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研究表明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中国未能产生波特效应[22]。三是从地区层面考虑环境规制的影响,发现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都实现了环境和绿色经济的共赢,东部地区效果更佳;但西部地区出现了环境和绿色经济的“双重恶化”[23]。
(三)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当一国加强环境规制后,为了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污染企业会迁移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国家,该国则为污染企业提供了避难所[24]。一方面,有不少文献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并发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污染避难所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文献对污染避难所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污染避难所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25]。早期研究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文献大多从国家层面展开,核心问题在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偏好于环境规制更弱的国家。后来,围绕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讨论逐渐深入,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跨国样本,而是深入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污染转移。
具体到中国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结论尚不一致。有些学者证实了中国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26],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不成立[27]。二是论证中国的FDI流入是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多数文献都认为会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并发现FDI对中国环境质量的不良影响与其投向区域之间是一致的,基本空间分布为“东高西低”。即便国内环境规制对FDI流入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地方政府有动机以放松环境规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的凸显[26]。
二、中国式环境规制的政策演进
1949年以来,中国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保护在治理过程中不断深化。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法律法规出台为主的探索阶段(1949—2006年)、以政府绩效考核方式为主的政策落实阶段(2007—2011年)和以政府行政指令式和市场化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环境规制政策的提升阶段(2012年至今)。
(一)以法律法规出台为主的探索阶段(1949—2006年)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我国经济规模小且环境容量大,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凸显。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开始显现。中央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并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这为构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环境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原则按照国际规则作出了相应调整,变得更加规范化和体系化。中国在环境规制的治理实践中,对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入。
第一,从局部单项向全面法治建设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行政指令主要以关注环境卫生和改善自然生态为主。1956年,国家卫生部与国家建委联合发布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确定了“综合利用工业废物”的方针[28]。改革开放至21世纪前,环保意识从启蒙期逐步进入初步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央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提出“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并积极推进中国工业“三废”的综合治理。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各类污染物环境治理,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等。21世纪后,中国的环境规制理念进一步提升。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循环经济立法,标志着中国污染治理模式开始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中国基本形成由人大立法监督、政府负责实施、环境行政部门统一监督的环境规制体系。
第二,重点强化区域环境治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水平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以二氧化硫污染排放为例,1995年中国有超过60%的城市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将二氧化硫和酸雨作为重点控制对象,把全国的175个城市划定为“两控区”,并提出“两控区”城市短期(到2000年)和长期(到2010年)环境控制目标。中央不仅从源头抓起,限制高硫煤的开采、生产、运输和使用,推进高硫煤矿配套建设洗选设施,优先考虑低硫煤和洗选动力煤向“两控区”的供应,而且着眼于对生产的全过程控制,选择低污染的原材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降低生产能耗,加强生产各个环节的管理,并进行必要的尾端治理。“两控区”政策作为中国加强环境规制与降低环境污染的一大创举,经过多年实施与发展,成为维持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限制粗放型生产活动的重要支撑点,在环境规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向西方学习环境保护经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对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了环保工作的“32 字方针”,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28]。之后,中国代表团多次参加国际环境会议并对其他国家进行考察,全球环境治理的最新理念、现代制度和市场机制被带回国内。中国的“清洁生产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以及21世纪以来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都是与国际接轨的体现[29]。
(二)以政府绩效考核方式为主的政策落实阶段(2007—2011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发展模式,对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的扩大提出了新的期许,对污染物的排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是生态文明观念的体现。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困境使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实施“绿色新政”,生态文明理念被各国摆在突出位置。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推动政府、企业、民众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治理成为中央关注的重点。在环境友好型战略的驱动下,中国将环境目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政策落实效果得到大幅度提升。
第一,实施官员任期环境考核。官员任期环境考核是政府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抓手。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与各省(区、市)政府签订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明确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中。2009年7月,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级机制,制定了考核评价办法,再次明确将“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列入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并作为领导干部换届考察及提拔任职考察的参考依据。2011年,国务院发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更是增加了环保考核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一票否决”制作为中国特色绩效评估体系中的一项干部考核制度,彰显了中央对地方干部污染物减排绩效的考核力度,是中国官员考核体系的巨大转变。
第二,实施节能减排五年规划目标考核。以五年规划为纲领的环境考核制度是一个基于结果的目标考核制度。中央在五年规划中设定一个全国性的节能减排指标,然后将总体指标分解为省级指标并分配给每一个省份,并将指标完成情况纳入政府领导干部的综合考评,不能完成任务的领导干部将被处罚或撤职。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约束性节能指标后,中国减排指标的属性便由过去的预期性改为约束性。节能减排“五年规划”作为公共环境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在整个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规划,有意识地引导资源配置,以推动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第三,初步尝试环境司法考核。为提升环境司法效率,中国开始探索在法院原有的审判组织体系中单独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促进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设立环保法庭。通過设立专门负责环境资源类案件审判的环保法庭,一方面,法院可以培养和选拔具有专业背景的法官专门负责环境类案件,提高案件取证、裁定的准确性。最早设立的贵阳清镇环保法庭就设立了环保专家咨询委员会, 通过“法官+专家”的模式降低了错审和误审,提升了环境类案件的司法处理效率。另一方面,这一专门性的审判机构具有环保案件的集中管辖权,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内针对环境纠纷案件的特殊性采取一系列变通的司法制度,实现既利于此类案件诉讼推进又不违背现有法律规定的司法创新。当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专门审理环境案件的组织机构虽然仍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式,如环保法庭、环境保护审判庭、环保合议庭、环保巡回法庭等,但其实质大体相同。
(三)以政府行政指令式和市场化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环境规制政策的提升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治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自此,政府绿色治理进入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第一,实施分类型专项治理。首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大气污染的空间扩散性要求大气污染防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以区域为单元的一体化控制模式。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细颗粒物(PM2.5)浓度作为主要评估指标,考察三大目标区域作为整体或独立个体时的雾霾治理效果。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如建立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兼顾各地区差异,统筹区域环境治理。2018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明确要求“继续发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作用”,而其他重点区域则需进一步建立或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其次,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工作。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江河湖海实施分流域、分区域、分阶段科学治理,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提出了短期(2020年)和长期(2030年)的具体工作指标。最后,开展土壤污染防治。2016年,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的要求;到2030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要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要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要得到全面管控;到21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要全面改善,生态系统要实现良性循环。这体现了党中央意图从顶层设计角度对推进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第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多维度体系。积极调动各主体积极性,参与环境治理。首先,实施排污许可证交易。排污许可证是指在排污单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经审查发放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物的凭证。在中国,环境保护部负责指导全国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和监督。其次,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2021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仪式于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同时举办,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中国碳交易市场主要以配额交易和CCER自愿减排两种机制构成,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当污染型企业的CO2排放超过其排放配额,主体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从政府或者其他企业处购买其抛售的碳排放量,通过市场导向机制控制企业碳排放水平。碳市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最后,建立公众参与平台。201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法制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公众环境实体权益得到保障。此外,各级政府网络信息平台、专题听证、投诉电话和信访体系等也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平台。
第三,推进环境监察定点到位。为进一步完善环境执法体系,提升环境治理效果,中国不断完善监管方式。一是河长制。它是指由中国各级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组织指导各区域内相应河流的生态环境的行政监督管理和资源保护工作。各河段的水质检测审查结果作为各区党政主要领导和责任人员的业绩组成部分之一,各市(区)对延迟报告、拒报或谎报有关水质检测审查结果的具体责任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追究责任。二是环保督察制度。环保督察制度是指负责环保督察的国家机关通过调阅相关资料、听取客体汇报、现场检查、接受群众举报等方式了解和监督地方党委政府、环保部门以及环保工作相关业务部门的履职情况,确保各级政府环保工作的落实。三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2015年,《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印发,进一步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强化了中国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控、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管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四是环保约谈。2020年,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对未依法依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职不到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未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以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环境主体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落实责任。
三、中国式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一)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中国式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贸易模式、环境污染治理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1.中国式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主要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10]。从短期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污染治理支出通常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压缩利润空间,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会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符合“遵循成本说”。“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不会对经济体的生产绩效与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甚至会具有抑制效应[30]。从中长期来看,有学者提出质疑,祁毓等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会被逐步抵消,且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协调性,且随着环境规制执行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31]。还有學者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城市规模具有累进式的“边际递增”效应,即城市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32]。但也有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发现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33]。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很多文献认为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有少部分文献并不赞同。一方面,支持者认为,施行合适而严厉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史贝贝等通过分析“两控区”政策,发现这一政策不仅缓解了大气污染,而且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32]。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二者不能实现“双赢”。在中国式环境规制下,即便在约束性考核中加入环境治理指标,地方政府仍然可能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杨丹辉和李红莉基于损害的污染损失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较全面地测算出了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退化[34]。
就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总体来说,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河长制作为新型河流治理模式,将河流环境治理效果直接纳入地区主要党政领导人的政绩考核,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短期内会抑制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长期能够实现双重红利[35]。第二,从区域异质性角度分析对各省份的经济影响。一方面,“十一五”以来,中国将能源消费强度目标和碳排放强度目标作为控制能耗和碳排放量过快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基于中国的强度减排目标以各地区原有排放强度为基础的设定,中西部省(区、市)获得了较大的排放空间。虽然青海、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湖南、广西等省份经济增长的能耗与碳排放强度较高,但这些省份在工业化转型的推动下,经济增速大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6]。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赵霄伟研究发现,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为负增长效应,西部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增长效应[37]。第三,从政策推广有效性角度分析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环境规制工具主要采用试点—再推广模式,部分学者分析了已有环境规制工具推广的有效性。王班班等在对河长制推广扩散有效性进行评估后发现,河长制在“平行扩散”地区对不同规制对象的异质性效果明显。对排放规模较大的行业规制略松,能增加其产出,从而补偿一部分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38]。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当前文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不利于经济增长。基于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在经济增长上较大程度地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耗。涂正革和谌仁俊认为,排污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能源的使用,无法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22]。二是认为能促进经济增长。支持者认为,碳市场的建立能够有效降低全社会能源成本,提高生产要素的福利和配置效率,从而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39]。
2.中国式环境规制与贸易模式
一个国家的资源、环境问题,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工厂选址、贸易模式,并最终影响到贸易利得,由此一些学者开始探讨环境规制对中国贸易模式的影响。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而言,大多数文献认为环境规制抑制了中国贸易的发展。皮革、羽绒制品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这些产业的发展会导致区域性水污染严重。政府采取“两控区”政策后,“两控区”城市的出口显著下降,污染行业的出口有所降低[40]。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两控区”政策对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明显,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环境规制对中国贸易有利。盛丹、张慧玲认为,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1]。李小平等也指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提升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其对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才会有所降低[42]。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而言,当前文献大多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中国的贸易发展。中国过去是以自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为代价来维系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出口产品以高资源和能源投入、低产品附加值的商品居多。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存在不平衡,净出口隐含碳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额。特别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隐含碳排放失衡对总体失衡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实施碳交易的环境规制工具,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碳排放,不利于对外贸易[42]。
3.中国式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治理的影响而言,不少文献认为各地区共同监督、协同治理能有效改善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天然地具有“搭便车”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低效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约束的困难。仅凭属地治理和末端治理难以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只有在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的原则下,构建区域合作协同机制,才能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建立地区间联合组织能有效促进联合治理程度的提升[43],如“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的治理效果。但也有部分文献认为,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没有真正改善环境。首先,从整体来看,没有达到污染治理的目标。有学者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进行比较,发现降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约束性指标PM10(PM2.5)的排放浓度,削减SO2等生产性敏感污染物的排放峰值,并未带来空气质量的全面整体改善[44]。其次,从持续性来看,缺乏治理效果。Chen 等研究发现,关停或搬迁污染企业显著改善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但空气污染在奥运会之后快速反弹,并未真正实现污染治理[45]。同样,有学者发现,各地的临时性管控措施显著改善了“两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但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报复性污染[46]。
就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治理的影响而言,该方面的文献结论尚未统一。一方面,很多文献认为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治理的效应明显,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具体污染物来看,治污效果明显。王岭等发现,无论是首轮中央环保督察还是“回头看”,都对降低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显著效果[47]。其二,从区域异质性分析,存在治污差异。沈坤荣和金刚认为河长制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4]。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河长制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是否呈现差异,仍值得进一步分析。其三,从绩效考核方式来看,环境污染治理的政治周期性规律显著。五年规划在公共环境治理中有重要作用,基于政府五年规划中对能源强度目标的设置,研究发现政府的指导性目标能够对工业排放起到约束作用,显著降低单位GDP能耗[48]。另一方面,也有文献对污染治理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从政策推广的有效性来看,现有文献并未深入分析河长制政策扩散和演进过程中对排放主体的区域差异化政策效应及其原因[4,49]。王班班等发现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果在由上级政府主导推广的“向上扩散”地区得到了成功复制,但在地方政府主动模仿的“平行扩散”地区并不明显[38]。在“平行扩散”地区,既不会降低企业产出,又不能产生减排效应。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治理的影响而言,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方面,大部分文献认为其对污染治理效果显著[22]。从企业角度来看,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即使碳排放权交易对不同工业污染物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但整体减排效果仍是逐年增加的[50]。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中央提出碳交易可以激励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有学者发现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是无效的。李永友、沈坤荣发现,2002年启动排污权交易后,试点地区污染排放上升了[21]。具体到行业内部发现,碳交易能有效促进煤炭、重工业、电力和轻工业部门的碳减排,但对高排放部门交通和建筑业的减排效果不明显[51]。
4.中国式环境规制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
这部分文献主要讨论了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绿色消费和区域发展差异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就中国式环境规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言,中国式环境规制会促使不同行业差异化发展,主要体现在清洁品和污染品两部门上,会影响两部门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及政府补偿率的环境政策组合,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环境质量提升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三重红利[52]。但过度的政府补偿政策,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延缓收入分配格局改善进度;而不足的政府补偿政策,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扩大的产出规模也不会带来社会福利增进。就中国式环境规制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影响而言,学者们分析了不同补贴力度下政府补贴对消费者的影响[53]。就中国式环境规制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言,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整体上朝均衡化方向发展[54]。
(二)中观层面的经济效应
从中观层面上,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中国式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升级、技术创新、产业效率、产品质量和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等方面的影响。
1.中国式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升级
产业转移方面,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差距,地区间会自然出现产业梯次承接,引发污染产业转移。具体到行业内部,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密集型产业成本增加,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为了降低成本,可能发生“污染避难所”效应[55]。产业升级方面,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存在冲突,只有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实现二者共同发展。当前,环境规制大多通过影响工业生产活动来实现工业行业转型升级,主要呈现J型特征,但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最低、西部最高的特征[56]。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转移升级的影响而言,不同的学者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模式看法各不相同。自《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以来,各地区地方政府注重水污染治理,沈坤荣和周力发现中国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呈现“逆流而上”的态势,并在地方政府竞争下引致“污染回流效应”[57]。但曲玥等认为,由于要素成本及生产率的区域性差异,下游省份会逐渐淘汰污染产能,同时升级自身产业结構以获求经济增长新动力源泉,进而呈现污染产业转移的“飞雁模式”[58]。与此同时,中国式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升级具有区域异质性。一方面,从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严格的环境管制使得部分商业活动撤离,改变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Hering & Poncetand发现,“两控区”政策导致污染行业中采用低效生产技术的小企业退出市场[40]。另一方面,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呈显著负向影响[59]。
就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转移升级的影响而言,面临环境目标约束的地方政府的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较为明显[55]。因为地方政府在面临强环境目标约束时,会出台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完成环境目标约束的考核目标。此外,省份之间存在政府间竞争行为,环境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间环境规制力度,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绩效考核式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转移路径的影响,发现中国河长制政策的实施,使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污染回流效应”,水污染密集型产业“逆流而上”,向中上游省份转移,其污染物则“顺流而下”[57]。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转移升级的影响而言,中西部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逐渐提高,推动了高耗能产业内移。碳交易机制下,控排企业无论自身减排还是购买排放许可,均需承担减排成本,碳排放许可价格在区域间趋于均等,许可的供应与需求在空间上高度分离,不再由减排目标的分配直接决定。这样不仅降低了“污染天堂”效应,而且促进了中西部工业化转型地区经济增长[36]。另外,这一减排政策还从生产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影响了地区产业结构。从生产侧来看,减排政策限制企业排放,提高能源投入成本。不同行业由于排放强度不同,生产成本受到的影响也有差异,从而引发资本积累路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需求侧来看,政策冲击会通过价格机制向下游产业和消费者传导。此外,市场型工具可以诱发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去产能”和工业生产方式绿色升级的“双赢”[60]。
2.中国式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言,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中国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方面的创新。在水污染防治技术方面,中国学者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一些研究忽略了实际情况,缺乏实用性,难以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方面,有学者发现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工具对于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技术创新的产出效应不够[61]。但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控防治领域内,中国是依据各个阶段需要攻克的空气污染物,选择不同的科技创新技术手段。现阶段中国现代化通信技术、大气颗粒物的源解析、激光雷达探测技术都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得到发展与应用[62]。
就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言,总体呈正向促进作用。自“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明显变得更为活跃,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出现跨越式增长。虽然反对者认为,五年规划环保目标考核只是促进了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扩张,相关创新活动质量在下滑;认为中国绿色专利申请质量似乎并未得到明显提升,中国绿色专利申请可能存在一定的泡沫现象,专利数量激增而专利质量下滑[63]。但支持者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治污技术的提升,而且能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技术支持[64]。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言,大部分文献认为会促进技术创新。齐绍洲等发现,排污权交易试点能够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产生诱发作用[65]。任胜钢等也赞同,并发现在减排方面,试点地区二氧化硫减排显著高于非试点地区[66]。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李青原、肖泽华发现,企业为了获得补贴,会迎合政府的环保方向,在政府的支配下进行资源配置,造成一部分的资源浪费。因此,排污费会倒逼企业创新,但环保补贴会抑制企业创新[67]。
3.中国式环境规制与产业效率
国内学者主要从中国工业两分位行业[20]、省级地区[64]和企业层面[68]三个方面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效率的作用。虽然中国工业行业能源环境效率水平不高,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19]。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产業效率的影响而言,经验研究的结论莫衷一是。支持者发现,利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表明相对于非空气污染密集型工业行业,空气污染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显著提高[20]。此外,与其他环境管制指标相比,“两控区”政策的外生性相对较强。因此,大多数学者通过对“两控区”政策的生产率影响来衡量中国环境管制的政策效果。部分文献发现,相较于非“两控区”,“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这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了“两控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也有学者发现,“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68]。
就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效率的影响而言,约束性污染控制目标显著降低了污染行业内的资源错配水平,提升了污染行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3]。有文献从城市层面考虑地理相邻和经济相邻下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由于地理相邻城市在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上既存在逐底竞赛,又存在竞相向上,地理相邻城市间环境规制执行程度差异不断扩大,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一个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以其地理邻近城市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经济相邻城市在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上表现为竞相向上的形式,避免了高污染企业在经济相邻城市间迁移,反而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33]。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效率的影响而言,环境管制对中国工业增长尚未起到实质性抑制作用[69]。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工业高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初步彰显了环境政策的绿色革命成效[18]。但也有文献提出质疑,李胜文等利用排污成本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研究环境规制与中国各地区生产效率关系时,发现1986—2007年环境规制只对东部省份的生产效率具有促进效应[70]。
关于中国式环境规制在中观层面的影响,现有文献还讨论了其对产品质量和产口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就环境规制工具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而言,整体上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利于提升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41]。具体到企业性质层面来看,韩超、桑瑞聪发现“两控区”环境规制政策虽然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率,但国有资本越高的企业对“两控区”政策越不敏感,其产品转换率越低[71]。就环境规制对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而言,清洁生产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关键因素。清洁生产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加速企业内部产品转换,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退出率来实现。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 U 型特征;但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而且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72]。
(三)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
就微观层面而言,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中国式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这里主要对中国式环境规制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进行总结。
1.中国式环境规制与企业治理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治理的影响而言,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承担着节能减排的重任,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和其他投资者开始关注环境规制对公司的影响。大多数文献认为,政府通过实施约束性政策工具,增加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负担,迫使在位企业改进生产与经营方式,最终实现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提高[22,47]。
就政府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治理的影响而言,有学者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能通过创新驱动改善上市工业企业绩效。随着中央明确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当官员任期考核在五年规划目标考核之前时,其对企业环境治理作用更强[73]。具体到企业性质,有文献发现环境问题约谈政策显著改善了被约谈地区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但并未在民营企业中得到显著体现[74]。但质疑者认为,环境规制造成的治理压力过大,而资源支持不足,不会对企业环境治理产生明显正向影响。
2.中国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就政府行政指令式和绩效考核式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而言,当地方污染治理压力较大时,城市迫于环保压力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特别是加大对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但也有学者发现,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环境绩效考核标准提出后,企业环保投资的官员任期周期性规律开始变得显著,而五年规划周期性规律则变得不显著,二者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73]。
就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而言,大部分文献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显著正相关。问文、胡应得、蔡荣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强度越大,企业主动选择环保投资的意愿越强。尤其是近年来排污权拍卖价格不断上涨,企业购买并拥有排污权成为企业环保投资和资产增值的一种投资策略[75]。也有少数文献考虑到企业性质,认为国内企业环保投资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且个体差异较大[76]。
四、中国式环境规制研究评述、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现有文献从各类中国式环境规制工具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多角度对中国式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现有文献对中国式环境规制影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其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对社会活动影响的研究关注不足,即还需进一步关注中国式环境规制对居民福利或幸福指数等方面的影响。其次,中国式环境规制很多是政府下的行为,即作为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一种工具,现有研究没有很好地将其与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相结合,对此展开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最后,现有文献重点关注中国式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企业成长等方面的影响,而对其进行福利分析的文献较少。
鉴于现有研究存在以上不足,经济学学者可以在三个方面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第一,借鉴社会学家对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加重视环境规制的社会功能,就中国式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各个行为主体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第二,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合理测度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协调配合的作用机制,并阐释建立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性。第三,将研究视角拓展至中国式环境规制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方面。分析中国式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中的地区和行业福利差异,可为提升整体福利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的完善建议
1.引导环境规制良性竞争,增强环境管理集权
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同时,为体现地区差异,适当赋予了地方在规定幅度内制定征收标准和管理办法的主动权。当前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导致了宽松的环境监管与治理标准,出现了破坏性的“逐底效应”现象。即使近年来各地虽然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环保督察等措施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但中国环保形势严峻的基本态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当污染损害较高时,地方政府竞争也可能产生“别在我家后院”的结果,即各地區会竞相提升环境税来竞争,直到污染企业被逐出市场,出现“别在我家后院”的结果。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尤为关键。
2.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促进区域间绿色发展均衡状态的形成
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有所不同,地方政府在进行规划与建设时,需要考虑当地生态承载力。此外,环境规制竞争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相邻城市政府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对本地经济具有正增长效应,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空间外溢性对本地经济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外溢性对本地经济增长影响不够显著。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区域定位,制定地区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政策。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国家在制定宏观整体战略后,在实施具体的环境规制时要注意地区城市因素所带来的政策效果差异,并配合其他相关政策,在维持整体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3.畅通公众环保诉求渠道,强化其对策略互动的削弱效应
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中社会公众力量偏弱。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公民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实施中仍存在公開主体有限、公开与不公开界限模糊等问题,一些地区以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为由对相关环境信息不予公开。公民对环境的了解和需求最为直接和快速,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够让公民对环境治理提供关键的信息和帮助。公众环保诉求有助于弱化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形成政府非完全执行的约束因素。因此,应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环保参与度,加强公众与政府、企业的沟通,使各方在知情、参与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共识,以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形成合力,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4.灵活运用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形式,促进中国式环境规制与市场化工具相结合
环境规制的效果与规制工具的选择密切相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是一种强制政策手段,政府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数量和方式制定统一标准,违反规定的企业会受到行政处罚。这种规制方式有时只能起到增加企业成本的效果,当这一行政命令撤销后,企业甚至会产生报复性排污行为。而基于市场力量实施的环境规制工具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污染水平,主要是通过市场信号影响排污者的行为,能够给予企业持续的激励,促使其寻找更好的降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和手段[77]。但由于中国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尚不成熟,市场化环境规制还没有全面推行。因此,积极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推进环境规制工具的多元组合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2]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111-118.
[3]韩超,张伟广,冯展斌.环境规制如何“去”资源错配——基于中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4):115-134.
[4]沈坤荣,金刚.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8(5):92-115.
[5]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 353-377.
[6]FRIEDL B, GETZNER M. Determinants of CO2 emission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 45(1): 133-148.
[7]SHAFIK 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econometric analysi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4, 46(1): 757-773.
[8]PERMAN R, STERN D I. Evidence from panel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oes not exist[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3, 47(3): 325-347.
[9]袁鹏,程施.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1(2):79-88.
[10]张成,朱乾龙,于同申.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研究,2011(1):59-67.
[11]于斌斌,金刚,程中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J].统计研究, 2019(2):88-100.
[12]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5):37-47.
[13]宋马林,王舒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中国“拐点”:基于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1(10):168-169.
[14]何静,许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污染转移效应测度方法研究[J].统计研究,2007(3):26-30.
[15]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16]MOHR R D. Technical change, external economies, and the Porter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2, 43(1): 158-168.
[17]WILS A. The effects of three categori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use and price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7(3): 457-472.
[18]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赢发展:2009—2049[J].经济研究,2010(3):129-143.
[19]杜龙政,赵云辉,陶克涛,等.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10):106-120.
[20]李树,陈刚.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以APPCL2000的修订为例[J].经济研究,2013(1):17-31.
[21]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7):7-17.
[22]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J].经济研究,2015(7):160-173.
[23]王兵,刘光天.节能减排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5):57-69.
[24]COPELAND B R,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 755-787.
[25]MANI M, WHEELER D.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 1960 to 1995[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8, 7(3): 215-247.
[26]陈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J].世界经济研究, 2009(6):3-7.
[27]周浩,傅京燕.国际贸易提高了中国能源的消费?[J].财贸经济,2011(1):94-100.
[28]张小筠,刘戒骄.新中国70年环境规制政策变迁与取向观察[J].改革,2019(10):16-25.
[29]高世楫,王海芹,李维明.改革开放40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历程与取向观察[J].改革,2018(8):49-63.
[30]PALMER K, OATES W E, PORTNEY P R. Tighten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 benefit-cost or the no-cost paradigm?[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119-132.
[31]祁毓,卢洪友,张宁川.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6(9):126-143.
[32]史贝贝,冯晨,张妍,等.环境规制红利的边际递增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40-58.
[33]金刚,沈坤荣.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J].管理世界,2018(12):43-55.
[34]杨丹辉,李红莉.基于损害和成本的环境污染损失核算——以山东省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0(7):125-135.
[35]王力,孙中义.河长制的环境与经济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河长制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软科学,2020(11):40-45.
[36]汤维祺,吴力波,钱浩祺.从“污染天堂”到绿色增长——区域间高耗能产业转移的调控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16(6):58-70.
[37]赵霄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J].财贸经济,2014(10):105-113.
[38]王班班,莫琼辉,钱浩祺.地方环境政策创新的扩散模式与实施效果——基于河长制政策扩散的微观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20(8):99-117.
[39]FAN Y, WU J, XIA Y, et al. How will a nationwide carbon market affect regional economies and efficiency of CO2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8(4): 151-166.
[40]HERING L, PONCETAND 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4, 68(2): 296-318.
[41]盛丹,張慧玲.环境管制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J].财贸经济,2017(8):80-97.
[42]李小平,卢现祥,陶小琴.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J].世界经济,2012(4):62-78.
[43]胡志高,李光勤,曹建华.环境规制视角下的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治理——分区方案设计、协同状态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9(5):24-42.
[44]黄溶冰,赵谦,王丽艳.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空气污染防治:“和谐锦标赛”还是“环保资格赛”[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23-41.
[45]CHEN Y, JIN G Z, KUMAR N, et al. The promise of Beijing: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2008 Olympic Games on air qual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3, 66(3): 424-443.
[46]石慶玲,郭峰,陈诗一.雾霾治理中的“政治性蓝天”——来自中国地方“两会”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5):40-56.
[47]王岭,刘相锋,熊艳.中央环保督察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地级城市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5-22.
[48]胡鞍钢,鄢一龙,刘生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之手”——基于能源强度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7):26-35.
[49]金刚,沈坤荣.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河长制演进:基于官员年龄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9(4):20-34.
[50]李胜兰,林沛娜.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82-194.
[51]孙睿,况丹,常冬勤.碳交易的“能源—经济—环境”影响及碳价合理区间测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7):82-90.
[52]范庆泉.环境规制、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J].经济研究,2018(5):14-27.
[53]孙迪,余玉苗.绿色产品市场中政府最优补贴政策的确定[J].管理学报,2018(1):118-126.
[54]曹鹏,白永平.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甘肃社会科学,2018(4):242-248.
[55]余泳泽,孙鹏博,宣烨.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是否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20(8):57-72.
[56]童健,刘伟,薛景.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16(7):43-57.
[57]沈坤荣,周力.地方政府竞争、垂直型环境规制与污染回流效应[J].经济研究,2020(3):35-49.
[58]曲玥,蔡昉,张晓波.“飞雁模式”发生了吗?——对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3(3):757-776.
[59]高雪莲,王佳琪,张迁,等.环境管制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地理,2019(9):122-128.
[60]王班班,齐绍洲.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工具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专利数据的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6(6):91-108.
[61]史长宽.基于Soble-Bootstrap检验的大气污染防治增长效应与创新路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1):175-178.
[62]蓉倩.整合利用高新技术治理呼和浩特地区大气污染的动力机制及其创新模式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20(2):96-103.
[63]陶锋,赵锦瑜,周浩.环境规制实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环保目标责任制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2):136-154.
[64]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
[65]齐绍洲,林屾,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12):129-143.
[66]任胜钢,郑晶晶,刘东华,等.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5):5-23.
[67]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9):192-208.
[68]盛丹,张国峰.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管理世界,2019(2):24-42.
[69]涂正革,肖耿.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研究[J].世界经济,2009(11):41-54.
[70]李胜文,李新春,杨学儒.中国的环境效率与环境管制——基于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估算[J].财经研究,2010(2):59-68.
[71]韩超,桑瑞聪.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产品转换与产品质量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2018(2):43-62.
[72]余娟娟.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8):125-134.
[73]王红建,汤泰劼,宋献中.谁驱动了企业环境治理:官员任期考核还是五年规划目标考核[J].财贸经济,2017(11):147-161.
[74]沈洪涛,周艳坤.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境绩效:来自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7(6):73-82.
[75]问文,胡应得,蔡荣.排污权交易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战略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15(11):152-155.
[76]梁晓源,谭跃.绿色税收能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吗[J].财会月刊,2020(16):9-17.
[77]房宏琳,杨思莹.金融科技创新与城市环境污染[J].经济学动态,2021(8):116-130.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and Its Economic Effects: A Summary and Prospect
YU Yong-ze YIN Li-pi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discusse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cro, meso and micro.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1)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thod with typic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based o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s combined with market-style regulatory tools; (2)At the macro level,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promot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through early-stage cost effects and late-stage compensation effects, but they also affect China's trade gains and inhibit product exports to a certain extent; (3)At the meso level,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have to some extent promoted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 to the western region, promo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d industrial efficiency; (4)At the micro level,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have increased the environmental cost burden of enterprises' production, forcing incumbents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ethods, and have achieve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asonably measure 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and focu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overall welfare of society.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should emphasize guiding healthy competit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romote a differentiated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unblock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appeal channels, flexibly use the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tools, and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rket-oriented tools to ensure that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re positively exerting economic effect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economic effects; eco-development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20&ZD089)。
作者简介: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尹立平,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