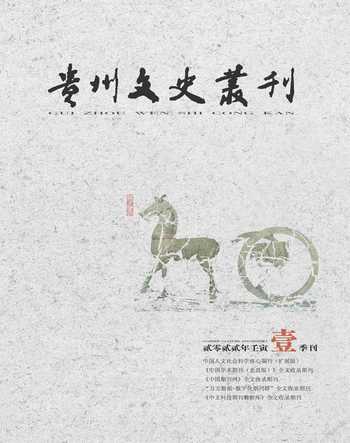唐代传奇骈化及其原因探析
朱银宁
摘 要:唐代传奇具有“骈散相间”的语体特征,在古代“文备众体”说以及西方文学体裁分类的影响下,相关研究一般囿于文体交互的角度。将唐代传奇中夹带的骈文文体排除后,对其语体重作历时梳理,可知唐代传奇的骈化程度总体递增,至晚唐达到巅峰。其骈语表达形式的特征,大致经历了说明性、文艺性、表达技法固化的文艺性语体三个阶段。唐人传奇语体骈化的直接动因,其一是功能意图从垂诫变为娱乐,其二是傳介方式从口述-记录变为个人创作。在中国传统“骈散之分”的体裁分类与批评语境下看,骈化现象是唐人传奇与史传逐渐分化的重要指标。此外,灵活运用骈散体与语境的相对关系,以此制造特殊的表达效果,也赋予了唐代传奇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唐代传奇 语体 骈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1-26-37
近代以来,唐代传奇文体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宋人赵彦卫评唐代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也被广为引用以描绘传奇之文体特征。由于诗歌是唐代文学之大宗,古人对诗与唐代传奇之关系已有关注;西学东渐以来,受西方文学体裁分类理论影响,比起“史才”与“议论”,“诗歌”相对于“小说”更显云壤之别2,故而唐代传奇的“诗笔”“诗化”问题尤为瞩目。自中国小说史建构伊始,鲁迅、陈寅恪、汪辟疆即张扬这点3,其后愈多,大致包括“诗文并行”与“文有诗意”两方面4;从“诗歌”扩展到其他文体(诸如变文、辞赋)进行探讨者亦是荦荦大观。当下对唐代传奇“骈散相间”的理解角度,基本经由这种路径形成。不可否认,唐代传奇中往往夹带其他文体,其诞生也可能受到过多种文体的影响,但其“骈散相间”的语体形式并非仅有“文体交互”一种解释框架。我们毋宁回归中国传统“骈散之分”的体裁划分与批评语境,适当借鉴现代语体研究方法解析归纳,试图通过新的研究路径发现新问题。本文的探讨对象,以李剑国先生《唐五代传奇集》所收作品为范围,也许这并非全集,但我们可以拥有足够大的样本量。第一部分,勾勒唐代传奇骈化的总体进程;第二部分,根据语料描写不同时段言语表达形式的特征体系,分析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第三部分,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探讨功能意图、传介方式两种语体变量对唐代传奇语体变异的推动,并揭示这一现象的小说史意义;第四部分,对骈体在唐代传奇中所承担的艺术功能,择要判断其美学价值。
一、唐代传奇历时骈化进程
唐代传奇中往往夹带有其他文体,包括诗、词、歌、赋、状、表、疏、奏、书、铭等骈文文体;有些骈文文体喧宾夺主,占据了绝大篇幅,如《吴保安》所载书信、《牛应贞》所载《魍魉问影赋》1,使唐代传奇在萌芽期就呈现出使用大量骈语的风貌。被鲁迅定为中国第一篇传奇文的《古镜记》作于隋末,就夹带了“歌”:
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不必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2
事实上,这种夹带现象早在战国已经出现,后世羼于子史的作品中亦不鲜见,而非唐代传奇之独创。下面略选与《古镜记》中情形相似者以示大概: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3
酒酣,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终,顾而流涕,张躬而舞。4
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欷流涕。5
这种骈语诚然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其之所以运用骈体,是源于其他文体的固有传统,子史之夹带则主要出于记录之需,唐代传奇中也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排除夹带骈文文体的情况,只关注以骈语作传奇的现象,以避免囿于文体交互的困境。关于以骈语作传奇,学界多举张鷟《游仙窟》与裴铏《封陟》为代表,前者作于永隆元年(680)或次年,后者作于乾符中,分处唐代传奇发展史首尾两端,遥相呼应。这一观点可能与常理不符,如作为传奇之渊薮的杂史、杂传以散体为正宗,然则唐代传奇萌芽期的《游仙窟》何以突变;《游仙窟》同期传奇何以全用散体,甚至对稍后时期之传奇也毫无影响。事实上,《游仙窟》的文体性质是在西学影响下建构的6;若以文体学眼光加以观照,《游仙窟》实以“体物”为核心,以客主问答为框架,通过“合纂组以成文”1,具有“内序”与“乱词”,多隐语、辩论、嘲戏,风格俚俗,应该是一篇文人戏拟的俗赋,与其他传奇文差异很大。2
与《游仙窟》同期的《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以散体叙事,只有少量吉光片羽式的四字句3以状景;至名篇倍出的贞元、元和前后,以散体为传奇的内在规定性业已形成,这种宽松的骈体4依然得以延续(如《洞庭灵姻传》《柳氏传》《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但这一时期的骈语功能局限于描写,篇幅也仅占零星的几句;至太和中,牛僧孺传奇集《玄怪录》中有多篇作品存在骈语5,且功能基本覆盖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骈体方始抬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李复言于大中中修订成集的《续玄怪录》中,《尼妙寂》《齐饶洲》两篇乃据旧题改编而成,我们可通过对读同一情节,略见语体之嬗变:
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李公佐《谢小娥传》6
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获释惑,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李复言《尼妙寂》7
李曰:“为之奈何?”——阙名《齐推女》8
韦曰:“夫妻之情,事均一体;鹣鹣翼坠,比目半无。单然此身,更将何往?苟有歧路,汤火能入。但生死异路,幽晦难知;如可竭诚,愿闻其计。”——李复言《齐饶洲》9
咸通中,骈散二体渐呈势均力敌之态,如袁郊《红线》通篇杂以骈语,功能覆盖了叙事、状景、状人、人物语言,共计骈文七百二十字,占全文一千六百六十二字的百分之四十三,近乎一半的篇幅;乾符中,裴铏传奇集《传奇》则宣告了骈化巅峰的到来,几乎每篇作品都含骈语10,单篇比例以《封陟》为最,骈语几乎占百分之百。此后,骈体写作持续走高,同期的《双女坟记》《灵应传》都是以骈体行文的言情作品。至于唐末五代,杜光庭《仙传拾遗》、沈汾《续仙传》、刘崇远《耳目记》等传奇集中的人物议论颇多,能助语势的骈体也屡用不鲜。
可见,唐代传奇语体的骈俪程度总体上是递增的。贞元、元和前后,唐代传奇以散行为主,只在描写处萌生了宽松的骈体;太和以降,骈体抬头,至晚唐逐渐达到巅峰,在篇幅上多全文骈俪,功能上则涵盖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等各方面;五代沿其流波,骈体篇幅并未大减,但功能主要退缩到议论一隅。
二、唐代传奇共时语体特征
文章学角度的语体属于文体的下属概念,故而宋代以来同被归为唐代传奇的作品,其言语特征具有一定的共性,如鲁迅就用“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1定义传奇文体;然可以肯定,不同作家又有其言语个性。现有研究不乏从作家-作品角度进行微观赏析,虽各有亮点,却难以得出一般发展规律。鉴此,我们根据语料重新分析,试图整合唐代传奇在发展各阶段的言语特征体系。
萌芽期的唐代传奇,即使在骈语的部分亦无“华艳”可言:
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古镜记》 2
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补江总白猿传》3
颗大如斗,状白似玉。——《梁四公记》4
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镜龙图记》5
色比蒸栗,泽若凝脂。——《得宝记》6
食器有七子樏、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汝阴人》7
此阶段的骈语多为松散的短句,多以描述颜色、数量、方位、质地来下定义和打比方。需要辨析的是,屡次出现的“如”“似”,并非文艺性的比喻修辞,而是中国古代惯用的说明方式:
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8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为怪草。其叶郁茂,其华黄色,其实如兔丝。故服怪草者,恒媚于人焉。——《搜神记》9
这种语体为笔记体小说所惯用,而此时的唐代传奇确实未脱志怪之藩篱,形式与内容得以两相配合;然而,以言情为大旨者也没有偏离这种语体,甚至在《任氏传》《枕中记》已经诞生的贞元中,被盛赞“撰述浓秾”10的《洞庭灵姻传》亦如此:
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罗霜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帷,施水精玉华之簟……并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郭翰》 11
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馀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赵旭》1
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圭……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馀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洞庭灵姻传》 2
以上描写看似铺张,实则仍为直接说明;发展之处在于进行了形容词的迭加,如“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使单句变长。因此,从隋末《古镜记》到贞元前后的《洞庭灵姻传》,叙事虽渐趋宛转,文辞却不见华艳,可视作唐代传奇语体发展的第一阶段。其骈语以准确说明为主要功能,多使用颜色、数量、方位、质地等形容词,后期发展为单句中形容词的简单迭加;风格质朴,不假藻饰,从语域方面比较,类似于博物类小说。
元和前后佳作井喷,第一阶段的说明性话语在这一阶段依然留存3,但主要的言语特征已发生质变:
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柳氏传》4
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莺莺传》5
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欷歔。——《长恨歌传》6
每至春风动处,秋月明时,众乐声悲,征鸿韵咽。或辗转忘寐,思苦长叹;或伫立无憀,心伤永日。如此者,逾年矣,全失壮容,骤或雪鬓。——《许元长》7
受益于此阶段作品情感的“凄婉欲绝”8,状景也通常“着我之色彩”9;而“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10,骈语部分也转而以表情为大要,如“摇六铢雾绡之袖,驾五色宝马之车”与“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的意思相同,但前者是准确具体的说明性再现,后者是使用迭词的文艺性表现。这种文艺性体现的方式还有很多,如“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春风动处,秋月明时”运用了互文修辞,“幽辉”“欷歔”“征鸿”“雪鬓”也是诗歌中高频度出现的词汇。即使在不太需要表情的环境交代中,作者亦能炼字:
有下坞林,月光依微,略辨佛庙。——《东阳夜怪录》11
时春物尚馀,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恶萦怀。——《霍小玉传》12
唯见芫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崔书生》13
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风和月莹。——《嵩岳嫁女》1
时雨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蔼然。——《张逢》2
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何让之》3
因此,从贞元中《柳氏传》起,至咸通九年(868)的《红线》,可视作唐代传奇语体发展的第二阶段。其骈语以文艺表现为主要功能,使用迭词及其他属于诗歌语域的词汇,注重练字;修辞手法多样,有互文、比喻、拟人等;句式上产生了明确的排比意识;风格雅洁清峻,言有尽而意有馀;从语域方面比较,类似于汉魏古诗。
自裴铏《传奇》出,语体又为之一变。其骈语功能承袭第二阶段的文艺性表达,而又进一步发展,极尽工整华艳之能事;但它与上一阶段的核心区别,在于表达技法固化,不复自出机杼、匠心独运。如状人方面,多套用风花雪月之属的常见喻体:
玉莹光寒,花明景丽,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真烟霞外人……睹一女子,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裴航传》 4
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濯艳。——《封陟传》5
韦氏美而艳,琼英腻雪,莲蕊莹波,露濯蕣姿,月鲜珠彩。——《郑德璘传》6
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孙恪传》7
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寒空。——《文箫传》8
甚者连“欺”“夺”等体现巧思的动词也舍去,只是罗列成语、獭祭喻体:
良久,二女齐至,正是一双明玉,两朵瑞莲。——《双女坟记》9
不食岁馀,肌肤丰莹,洁若冰雪,螓首蛴领,皓质明眸,貌若天人,智辩明晤。——《王奉仙》10
除了状人,一般行文中也多使用指代性词汇与固化的偏正结构词汇:
绣户不扃,金微明。——《昆仑奴传》11
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昆仑奴传》12
每弹至《悲风》及《别鹤操》,未尝不玉箸滴干,金缸耗尽,庭月色苦,壁蛩吟悲。——《萧旷传》13
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却要》1
此外,由领起词“但见”“是时”引出一段骈文铺叙的模式,是典型的“以对语说时景”2。试看以下片段,无怪乎《岳阳楼记》会被讥为“传奇体”了;反过来说,宋人认为“传奇体”有这样的典型模式:
但见危桥千步,耸柱万寻;若长虹之亘青天,如曳练之横碧海;势连河汉,影入沧溟,玉莹无尘,云凝不散。……于是红鸾舌歌,彩凤羽舞;笙箫响彻于天外,丝桐韵落于人间。——《许栖岩传》3
是时也,风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鸟翔集于乔木,佳鱼踊跃于长波。——《张郁》4
因此,自乾符中《传奇》起,至隐夫玉简所处之五代,可视为语体发展的第三阶段。其骈语延续了第二阶段的文艺表达功能,但无论是词汇、修辞还是句式都缺乏个性,高度模式化、套路化;风格流于靡丽,从语域方面比较,类似于六朝赋。
三、唐代传奇骈化之原因
元和前后的传奇体,自谓以惩恶扬善为写作意图,譬如《莺莺传》从内容本身来看显然是“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5,却曲终奏雅地称写作目的在于使“智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同叙杨贵妃事,《长恨歌》作为歌行体,自称创作是缘于“感其事”,而《长恨歌传》则声称是为了“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不选择当时流行的骈俪语体为惩劝功能服务,或与当时“文以载道”思潮及“史传书写”观念有关。
众所周知,古文运动以“复古儒学”为核心,“文以载道”为文学功能,散文为语体要求。文章以思想内容为重,正如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云:“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语言则沦为传道工具,甚至“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6,对语言美的追求被压制到了最低点。古文运动对传奇体生成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学界尚没有定论7;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古文运动同时兴盛的唐代传奇多旌美儒家人伦,托赞褒贬,垂戒教化,与“文以载道”的精神一致。
另一方面,初唐已分设“文学馆”与“史馆”,文史分流、各有体制的观念已成共识。“文”的定义源于六朝“沉思翰藻”的判断标准,而六朝以降出现骈化的史传,被初唐史官刘知幾评价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8,并批评当下“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9;“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10。这里论及了文与史的差异:史追求理之实,文追求辞之华,各有语体,不当混杂。至于传奇体,其作为“史官之末事”11,本就以散行为宗;适逢“文以载道”观念出现之时,士人又以修史为风尚,“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1,导致唐代传奇正体在形成过程中,从观念到形制都更向史传靠拢。如《任氏传》云:“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着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惜哉!”这与刘知幾对史官“才、学、识”兼具的要求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的旨趣如出一辙;从同期唐代传奇的风貌来看,文约事丰、形象饱满、作者个人感情充沛的特点也很接近刘知幾推崇的《史记》。“文以载道”也好,“史传书写”也罢,乃至于同时代“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3的新乐府运动,皆是儒学伦理复兴、士人积极匡正朝纲的产物。
太和中,牛僧孺《玄怪录》使唐代传奇正体遭受冲击,其意义破大于立。由于“故示其诡设之迹”4,怪妄不经的《玄怪录》历来被视为下流;但同为“作意好奇”5的《毛颖传》《南柯太守传》,却在鄙夷“幻设”的胡应麟处得到了相反的评价,实则后者顺延了六朝杂传记“以寓言为本”6的传统而具有虚构之合法性。反观《玄怪录》既非实录,也“无关风教”7,故以儒家文史观相衡量,简直百无一用。作为反功利主义唐代传奇的发轫之作,《玄怪录》虽然口碑欠佳,但续书颇多,影响深远:李复言即因为《续玄怪录》“事非经济,动涉虚妄”8而被罢举;裴铏《传奇》也因为缺乏“理”而遭宋人诟病9。伴随着垂诫意图脱落,用于“载道”的散体也同时式微,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也就此消彼长起来。如胡应麟对裴铏的创作动机解释道:“裴晚唐人,高骈幕客,以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并评价《传奇》 “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晚唐文类尔”10,则《传奇》既以娱乐幕主为意,选择作为“文家之戏”的“偶俪之词”11来运文也就是形式与精神相契合的自然结果。至此,唐代传奇正体的史传品性从内到外全面消弭,真正淪为了唐代史家所指斥的“体兼赋颂,词类俳优”12之“文”。
于此儒学精神退潮之际,佛道的影响在唐代传奇中显现出来。太和以降,骈体的隐语、口诀在作品中屡见不鲜,如李德裕谓《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13;这源于“幽冥之意,不欲显言”“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14的宗教神秘主义,使唐代传奇的娱乐特质进一步强化。此外,唐末传奇中以骈语议对的现象涌现,亦与道教说理有关,如杜光庭《道士王纂》:
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亿劫以来,未始暂辍。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1
杜光庭笃信道教,他的《广成集》中即有大量骈体“青词”,风貌与上文大类2;这段内容本来也出自杜光庭为《太上洞渊神呪经》所作的序3。如果说儒学精神的衰微导致了唐代传奇功利主义的逆转,那么佛道文化就为其走向唯美主义添砖加瓦了。
除了功能意图的转变,文本传介方式也决定了语体的骈散。一般来说,散体源于实录,如高彦休《皇甫湜》在人物语言下有小注云:“以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4;而晚唐传奇中的人物大多出口成章:
二女皆诺曰:“虞帝为君,双双在御;周郎作将,两两相随;彼昔犹然,今胡不尔。”致远喜出望外,乃相与排三净枕,展一新衾,三人同衾,缱绻之情,不可具谈……小顷,月落鸡鸣,二女皆惊,谓公曰:“乐极悲来,离长会促,是人世贵贱同伤,况乃存没异途,升沉殊路;每惭白昼,虚掷芳时;只应拜一夜之欢,从此作千年之恨;始喜同衾之有幸,遽嗟破镜之无期。”——《双女坟记》5
显然,二女不可能同时说话,这种骈体的人物语言是由作者转述或整合而成的。正如前文所论,这种转变与唐代传奇大异史传有关。史传即以实录为要,记录人物语言甚至不避俚语6,并借此刻画人物形象7,但传介方式的改变也是骈化的主因。中唐好事成风,连白居易都有“寄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8的意识,不少传奇也是“宵话奇言”“征异话奇”并请人记录的产物。小南一郎曾提出,传奇小说的基础是知识人聚谈的“话”;但与话录小说的如实记录不同,唐代传奇中也添加有在场者共有的价值观。以此投射到语体层面,则通过口述-记录方式生成的唐代传奇无疑以散体为主,但也不排斥在细节处发挥经主观创作的“才子之笔”9,化入骈语稍作装点。
太和以降,个人创作的情况转多。有些作品是作者养病期间所作,如“李玫以养病端居,乃《纂异》之记作”10;《甘泽谣》是“久雨卧疾所著”11;又据赵彦卫所言,《玄怪录》《传奇》乃投献主司之作12,欲逞才则必然需要个人苦心经营;至于李复言、薛渔思、张读的作品皆为前人之续书,主观创作意味就更明显了,是故唐代傳奇得以“摛词布景”13、文采斐然。
总而言之,从语言学下属的语体学角度来看,推动语言从散体变异为骈体的直接动因有二,其一是功能意图从垂诫变为娱乐,其二是传介方式从口述-记录变为个人创作。从文体学下属的语体角度来看,散骈之分各有所用,散体近史,骈体近文,唐代传奇语体骈化的现象,也标志着传奇体发展后期与史传的分化。两种角度殊途同归,都指向中央集权衰弱而藩镇坐大、甘露之变后士人心态消极、儒学式微而佛道大兴等社会历史环境发生改变,这应该是谈论唐代传奇语体变异不可回避的宏观背景。
四、骈语文学效果举隅
《文心雕龙》“丽辞”篇云:“言对为美,贵在精巧”1,由于骈俪语体注重藻饰、用典、韵律、节奏等,比起晓畅流利的散体来,更富于文采;而唐代传奇作为史传之流裔,虽以叙事为宗,却也追求“著文章之美”。因此,在散体叙事中适当夹入骈体,不失为增色妙法。不少名篇都善于在叙事中穿插骈语描写,使叙事张弛有度:
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任氏传》2
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馀樽尚湛于东牖。——《南柯太守传》3
才出,妻已不见,但自于一穴中。唯见芫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崔书生》 4
汪辟疆先生评价散文派传奇“文中渲染点缀之处,亦复潜气内转,情韵悠然,犹时时露其复笔之描写”5,盖此之谓。不过,一味铺张则过犹不及。试比较以下两篇的开端:
任生者,隐居嵩山读书,志性专静。常夜闻异香,忽于帘外有谓生曰:“某以冥数,合与君偶,故来耳。”——《任生》6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薮,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愒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猱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阒。烟锁筜篁之翠节,露滋踯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辎軿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濯艳,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鸯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嚬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封陟》7
此二者情节如出一辙,但《封陟》全用骈语,用八倍于《任生》的篇幅表述了同样的内容,使读者过分关注语言美而无限推迟了叙事节奏,伤害了情节的紧张度。除了“写物图貌”8,骈体在唐代还多用于议论1。在散行传奇中,人物也通常在论对时使用骈语以增雄韵:
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霍小玉传》2
其义正辞严之形象如吮出,颇能感发人心;但若全用骈语进行长篇大论,则骈语不但失去了刻画人物形象的功能,还会使可读性降低,未免膏腴害骨:
问于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
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渍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之危疾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原竭涸,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销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孙思邈》3
更有待关注的是灵活运用骈散以增强文学效果的现象,如张读《石龛胡僧》描写一胡僧立志献身:“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萨埵投崖以伺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而当寻访者提出“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时,他提出先要“说《金刚经》奥义”:“《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4《金刚经》的骈体具有远奥典重的风格,可文中的胡僧根本没有献身的觉悟,原本典重的骈体经文也就与实际语境发生了冲突,变成了“诨经”,从而突显出胡僧装腔作势的形象。又如“人化虎”是志怪旧题,而张读所记《李征》一文所写老虎重逢故人后的语言却别出心裁使用了骈语:
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5
老虎本为禽兽,而禽兽能言,甚至以骈语酬对,套话连篇,颇有书生酸腐气,体现出“资笑噱”的小说功用。
相对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散体自然流利、长于叙事;骈体繁缛华丽、长于描写。唐代传奇以叙事为第一要义,当骈语比例过大,则不利于叙事的流畅与紧凑,使文体核心性质遭受撼动;如果能在叙事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则能获得“宛转有思致”1的美学效果。而如何利用骈体与语境的相对关系来制造特殊的表达效果,是骈语的文学功能中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The Parallel Style of the Tang Legend and the Motivation of it
Zhu Yinning
Abstract:Tang legend with "A mixture of parallel prose and prose" style i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consensus, but there is no further research about style because the "poem" and other parallel prose in the Tang legend have received too much attention, which leads to the cogni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style. In this paper, we have made a distinction on the “parallel legend " and " parallel prose in the legend” to re-examine the style of the Tang legend. By the time of combing, the degree of the parallel style is increasing to the peak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From the synchronic level, the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verbal expression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ree stages: illustrative style, literary style, literary style which has a fixed skill. Combining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otivation: the functional intention from the admonition to entertain (from utilitarianism to aestheticism),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from the oral record to personal cre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enre classific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context, the prose is used in the history while the parallel prose is us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the style of Tang legend changed from prose to parallel prose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change of stylistic nature, the literatures named "Tang lege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vel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well. In addition, how to use the rel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allel prose and the Tang legend to create a special expression effect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Legend of Tang Dynasty;Style;The process of streamlining
責任编辑:李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