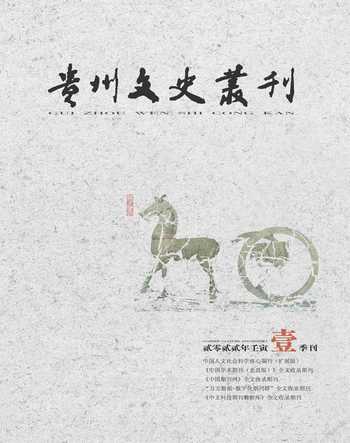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对朱熹的学术批评
陈必应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其中关涉朱熹及其学说的内容颇多,《总目》中仅“朱子”一词出现就达一千七百馀次。《总目》对于朱熹的学术批评呈现总体认同而局部批判的局面:一方面在理学占据学术话语统治权的历史语境下,《总目》对于朱熹的评价坚持着“集大成”观点下的总体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学术话语的争夺和清学的不断发展,《总目》对于朱熹及其学术亦有着局部的批判。《总目》中的这种学术批评现象,体现出朱熹及其学说在清代的地位与处境。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朱熹 宋明理学 学术批评
中图分类号:G257;B24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1-58-65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规模庞大、卷帙浩繁,“(全书收入)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1。《总目》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对于每一部著录书籍的提要,“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定‘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等”2。自南宋晚期以至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学术主流及官方哲学的地位逐步确立,在学术话语中处于统治地位。作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3的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4 的学说体系而受到后世不断推崇,同时学术批评之声亦历代不衰。《总目》全二百卷中有大量关涉朱熹及其学说的书目,《总目》全书中“朱子”出现一千七百馀次,“程朱”“晦庵”“紫阳”“朱熹”“晦翁”“元晦”“文公”“考亭”等关于朱熹的称谓也颇为频繁,《总目》在有关书目的选取及编排、提要的辨定及论述之间,体现出在清代学术环境之下对于程朱理学,特别是对于朱熹及其理学的学术批评,反映了自南宋至清代对于朱熹理学的认识及态度上的变化。
一、“集大成”观点下的总体认同
在“庆元党禁”中朱熹学说被视为“伪学”而处境困厄,但自庆元党禁之后的南宋晚期开始,朱熹及其学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及各方面因素而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推崇,在学术思想及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朱熹门人黄幹在所作行状中称:“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1随着朱熹著作逐渐成為科举选士的标准教材,其学说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朱熹在儒家道统及道学谱系中的地位亦随之上升。到了清代,统治者继续推崇儒学、理学,“清朝统治者力倡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恢复科考,以赢得汉人之心”2,清圣祖玄烨御纂《性理大全》《性理精义》诸书,更于《御制朱子全书序》中明确朱熹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3这是清代统治者对于朱熹及其学说的官方定论,《总目》卷九十四于《御纂朱子全书》条亦载明: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南宋诸儒,好作语录。卷帙之富,尤无过于朱子。咸淳中,黎靖德删除重复,编为一集,尚得一百四十卷。又南宋文集之富,无过周必大、杨万里、陆游,而《晦庵大全集》,卷帙亦与相埒。其记载杂出众手,编次亦不在一时。故或以私意润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说托名,全然无据。即确乎得自师说者,其中早年晚岁,持论各殊,先后异同,亦多相矛盾。儒者务博笃信朱子之名,遂不求其端,不讯其末,往往执其一语,奉若六经。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朱子者所淆。考《朱子语录》,称孔门弟子留下《家语》,至今作病痛。憾其择之不精也。然则读朱子之书者不问其真赝是非,随声附和,又岂朱子之意乎哉。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独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乃特诏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分为十有九门。金受炼而质纯,玉经琢而瑕去。读朱子之书者,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于多岐矣。4
玄烨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的评论并非一己之见,实际代表着南宋以至明清时期对于朱熹及其学说的主流共识,正如《御制朱子全书序》所言“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辩论是非,凡有血气,莫不遵崇”5,《总目》既是官方组织支持而编纂的,在对于朱熹的学术批评上也同样秉持着这种“集大成”观点下的总体认同。
首先,这种总体认同表现在《总目》肯定朱熹在理学乃至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认同其在“道统”上的重要地位。《总目》于《闽中理学渊源考》条云:“宋儒讲学,盛于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辗转授受,多在闽中。”6《伊洛渊源续录》条:“盖继朱子《伊洛渊源录》而作,以朱子为宗主。始于罗从彦、李侗,朱子之学所自来也。佐以张栻、吕祖谦,朱子友也。自黄幹而下,终于何基、王柏,皆传朱子之学者也。”7《识遗》条云:“自伊、洛发明孔、孟,便觉欧、苏气象不长。又谓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诸家经解自晦翁断定,然后一出于正云云,盖传朱子之学者也。”8《理学正宗》条:“是编列宋周子、张子、二程子、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子、张栻、吕祖谦、蔡沈、黄幹、元许衡,明薛瑄共十五人。人各一传,并取其语录答问及著作之切于讲学者录之,附以己见,而于《太极》《通书》释之更详。大旨以朱子为宗。李侗以上,开其绪者也。黄幹以下,衍其传者也。胡安国等皆互相羽翼者也。”1《总目》肯定朱熹于道统中的地位,是为朱熹学说的官方统治地位寻求法理上的依据,也给朱熹及其学说的批评定下了一个总基调。
其次,表现在《总目》肯定朱熹之学对后世的影响。道统是理学乃至儒学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朱熹认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2,故朱熹尤重孔孟至北宋诸子以来的理学道统传承,绍绪濂溪、二程之学而下开考亭一脉。《总目》认为“至于朱子之学上接洙泗,诚宋以来儒者之宗”3,因此提要著述往往视之为“朱子之学”“朱子之传”,如《易经粹言》条云:“《河图》《洛书》,数学也,邵子之传也。吉凶、法戒,理学也,程子之传也。兼而言之,是朱子之传也。”4《岁寒居答问》条:“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泻。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5《三鱼堂剩言》条:“昔朱子博极群书,于古今之事,一一穷究原委,而别白其是非。故凡所考论,率有根据。陇其传朱子之学,为国朝醇儒第一。”6《总目》强调朱熹创立理学之功,注重在学术上上承下启的作用,明确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实际上都指向共同的目的,即从学术及思想发展史上来肯定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7的历史地位。
再次,《总目》肯定朱熹著作宏富,尤其对其在四书学、小学、性理诸书上的重要成就。认为“南宋诸儒,好作语录。卷帙之富,尤无过于朱子”8。对南宋晚期以来朱熹之学流行的价值给予肯定,《朱文公易说》条:“当理宗以后,朱子之学大行,剩语残编,无不奉为球璧。” 9《云庄礼记集说》条:“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10朱熹学说在宋代以来的影响逐步扩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学说与科举的结合,“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使四书成了宋以后高于五经的经典体系”11,在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教程。《总目》注重朱熹在四书学上的开创之功,如《总目》四书类一:“朱子书行五百载矣。……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12朱熹构建儒家四书系统,后世四书之学不可免受其影响,《四书纂疏》条云:“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于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13《尚书集传纂疏》条:“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14又谓《近思录》为性理诸书之祖:“书凡六百六十二条,分十四门。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然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由博反约,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15
同时,《总目》对朱熹易学、春秋学、礼学、尚书学亦多持肯定态度,赞扬后世著述宗于朱熹之学的做法。朱熹对前代易学多有微词:“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1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对后世之影响亦为《总目》所关注,《周易本义原本》条:“其说皆以朱子为宗,不容一字之出入。”2《田间易学》条:“其学初从京房、邵康节入,故言数颇详,盖黄道周之馀绪也。后乃兼求义理,参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而大旨以朱子为宗。”3《读易举要》条:“考琬之《集说》,以朱子为宗,而此书论刚柔往来,则以两卦反对见义例,以《泰》《否》二卦彖辞,较朱子卦变之说更近自然。”4《易纂言》:“其馀亦多依傍胡瑗、程子、朱子诸说,澄所自为改正者,不过数条而已。”5《总目》对朱熹春秋學于《春秋辑传》条云:“其《辑传》以朱子为宗,博采诸家,附以论断,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犹为醇正。”6评朱熹尚书学于《尚书纂传》条:“其大旨则以朱子为宗,而以真德秀说为羽翼。”7评朱熹礼学于《俟后编》条:“所定四礼,大抵以《朱子家礼》为蓝本,而参以乡俗,亦吕坤《四礼翼》之支流。惟《补录》一卷,颇嫌驳杂。如谓朱子误解格致不及阳明之说。又谓朱子后日自悔。又谓王守仁、陈献章皆理学之宗,王艮见道甚确。又谓庄子甚高旷,使在圣门,则为曾点之流。老子比庄子更高一步。皆不可训。”8诸如此类。
最后,除了从道统地位、学术成就、学术影响等方面来肯定朱熹外,《总目》还在提要间不时将朱熹视为后世学者之宗向,以彰显朱熹理学集大成者与一代儒宗的历史地位,如《云峰集》条:“炳文之学,一以朱子为宗。”9《畏斋集》条:“夫朱子为讲学之宗,诚无异议。至于文章一道,则源流正变,其说甚长。”10总之,《总目》对于朱熹及其学说的肯定与认同是全方面的,是在其“集大成”官方定论与经受历史考验而得来的学术话语统治权之下的总体认同,无论是对朱熹及其学说的道统地位与后世影响,还是具体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方法,《总目》中的论调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当然,这些肯定与认可是朱熹及其学说自南宋以来在不断的学术话语权及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中奠定的,这是能得《总目》高度认同的根源所在,从此也可见朱熹及其学说在南宋至明清时期的顽强生命力与可持续性发展。
二、清学视野下的局部批判
清圣祖玄烨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言及编纂《朱子全书》之动机时称:“唐、虞、夏、商、周,圣贤迭作,未尝不以文字为重。文字之重,莫过五经、四书。每览古今,凡传于世者,代不乏人。秦汉以下,文章议论,无非因时制宜、讽谏陈事、绳愆纠谬、绝长补短之计耳。若观文辞之雄、摛藻之严,古人已有定论,予何敢言?但不偏于刑名,则偏于好尚;不偏于杨墨,则偏于释道;不偏于词章,则偏于怪诞。”11该序认为古之文章定论多有失偏颇,而不能持论公正,故未至至善。作为后来的继承者,清高宗弘历在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同样继承了这种追求不失偏颇的评价态度,这种原则置诸朱熹及其学术的评价上,则表现为在对朱熹给予“集大成”观点下总体认同的同时,《总目》也对朱熹及其学说进行了局部的批判。但同时又正如梁启超所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对。”1“明清之际文学思想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汲古返经。这主要开始于明末复社等团体的积极倡导并逐渐流行开来,经明清易代这场社会巨变的感激而得以进一步加强,几乎成为文人一种普遍的认识”2,《总目》对朱熹的批判也是在清学视野之下进行的。批评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经学及理学两个方面,朱熹作为宋学的代表人物,对其经学的批评是在汉学与宋学之间相互冲突矛盾的背景下进行的,《总目》在经部总叙中有总体的论述: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3
《总目》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而宋学“具有精微”,“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因此在对朱熹的学术批评中,最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是宋学与汉学比较下所具有的不足,最为典型的是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相关批评。朱熹的诗经学著作以《诗集传》为代表,其中“淫诗说”“废《序》说”等主张在后代争议颇大,《总目》批判的重点则集中在“废《序》”这一主张上。《总目》于《诗集传》条云:“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意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自是以后,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钦定《诗经汇纂》,虽以《集传》居先,而《序》说则亦皆附录,允为持千古之平矣。”4又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中认为:“《诗序》自古无异说……盖《集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5对于朱熹在诗经学上废序的作法,《总目》认为《诗序》自古无异说,或为当时学术之争下的结果,同时又为朱熹回护,认为“非朱子之初心”,对于后儒从朱的作法多有微词,《毛诗正义》条云:“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6《总目》所批判的不仅仅就诗经学上盲目从朱的一派,实际上是对整个宋代诗经学的不满,认为宋代诗经学重义理而疑古非古风气盛行,“由己意说经发展至末流,由于过度的自信、过度的怀疑,甚至非传诬经,造成学说太过武断,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其弊也悍”7 。
《总目》对朱熹之批评不仅限于诗经一学之上,对其经学的其他方面亦能发其不足,如《易学启蒙通释》条:“朱子因程《传》专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数以补其偏,非脱略《易》理,惟著此书以言数也。后人置《本义》不道,惟假借此书以转相推衍,至于支离轇轕而不已,是岂朱子之本旨乎?”1朱熹的易学著作主要是《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总目》在此处批判后学者不取学《周易本义》而反以《易学启蒙》转相推衍的做法。《伊雒渊源录》条:“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家,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2《伊雒渊源录》为朱熹对理学道统溯源弹流的著作,此处“未尝逆料及是”是指自此书后漫谈道学宗派,声气攀援,转相依附,为各执所见而党同伐异乃至无所不及的作法。《名臣言行录前集》条:“则是书瑕瑜互见,朱子原不自讳。讲学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转非朱子之意矣。”3《总目》能揭示朱熹学说的不足,但往往以“非朱子本义”之类委婉的说法来回护,尤其反对墨守朱熹之学而无所创获的作法,如《周易集传》条云:“今观所注,虽根据程朱者多,而意在即象诂义,于卦象爻象互观析观,反复推阐,颇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旧文者也。”4清代的经学“虽守宋学之门户,然多采汉人训诂”5,《总目》虽然以朱子之学重在义理而不拘训诂来加以回护,但对于朱子后学日趋空谈守旧的批判确是态度明确的。
《总目》除了对朱熹经学上的不足加以批评外,也对其理学一面展开了审视,而批评的基调继承清圣祖玄烨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的定论:
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五章补之于断简残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贯通之为止,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此。问《中庸》名篇之义,则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未发已发之中,本之于时中之中,皆先贤所不能及也。论《语》《孟》则逐篇讨论,皆内圣外王之心传,于此道人心之所关匪细。以《五经》则因经取义,理正言顺,和平宽弘,非后世借此而轻议者同日而语也。至于忠君爱国之诚、动静语默之敬、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辩论是非,凡有血气,莫不遵崇。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6
《御制朱子全书序》对于朱熹理学定了总基调,如“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辯论是非,凡有血气,莫不遵崇”诸语,相较于《总目》,经部总叙要推崇得多。在这种基调下,《总目》对朱熹理学的批评远不如对其经学那般直接,而往往是通过对后人宗朱的些微弊端和不良情况进行批评来委婉指出。如在《书集传》条云:“则《序》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黄景昌等各有正误辨疑之作。”7又《四书通证》条:“乃但引《周礼》于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8虽云“区区训诂之间”不必为之讳,但也点出有所窜易等不足,这实际上隐晦地反映出清代学术由义理而转重训诂的风气。又如赞扬陈亮《龙川文集》:“盖以微讽晦翁,晦翁亦不讶也云云。足见其负气傲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1《总目》云《尚书辑录纂注》以朱翼朱:“然则鼎于《集传》盖不免有所未惬。恐人以源出朱子为疑,故特引朱子之说补其阙失。其举《集传》归之朱子,犹曰以朱翼朱,则不以异蔡为嫌耳。非其考之不审也。”2又谓《周易蛾术》:“其言象占,则遵马、郑、荀、虞之说而自称折衷于朱子。然以世应纳甲列图于每卦之前,乃京氏之学,非朱子之学也。”3南宋以后,学者往往于学上以朱熹为宗,以致风气沉滞、渐成禁锢,《总目》反对此种不良学风,故对与朱熹同时期的陈亮“未尝委曲附和”的作法表示激赏。《总目》对于朱熹的局部批评反映出在清代多种思想影响下的主流学术认识,对于程朱理学给予总体的肯定,然而其中的一些批评已经显示出程朱理学在晚清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可以一窥朱熹学说在清代的地位与处境。
三、朱熹学说在清代的地位与处境
朱熹及其学说自南宋后期以来逐渐取得官方哲学的地位,然而亦不乏争议之声,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对于理学的非议之声越发激烈,极大冲击着处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对于朱熹及其学说的批判亦不断增多。《传习录》载王阳明论述朱熹之学云:“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既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4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认为:“朱子以知觉运动为形下之气,仁义礼智为形上之礼,以此辟佛氏,既未可为定论。”5这种批评和怀疑精神最为强烈的是陈确,他作为“一往直前不顾利害亦推翻理学的宝座”6而“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7。陈确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8又云:“儒者果有意穷理尽性之学,而将究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复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则博是徒博,学是伪学,而凡所谓问、思、辨、行者,亦无之而非伪也。”9还说:“今之士者,但知以读书为学,深可痛也。举子之学,则攻时艺;博士之学,则穷经史,搜百家言;君子之学,则躬仁义。仁义修,虽聋瞽不失为君子;不修,虽破万卷不失为小人。”10这一方面是由于晚明的社会背景及学术风气所导致的审视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诸多思潮及心学兴盛而带来的学术争鸣与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
清代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空前加强,继续推崇程朱理学使其成为官方哲学的地位续而不断,于是对于朱熹及其学说的批评自然不如晚明时期那般激烈,但晚明以来对于理学的批判氛围依然有所影响,在《总目》之中这些影响便不时流露出来。如《总目》于《孝经疑问》条云:“夫《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变乱古籍乎。况惟圣人能知圣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一分别此为孔子之语,此非孔子之语,若亲见圣人之原本耶。”11此语虽是就姚舜牧《孝经疑问》而言,然而谓其“以朱子之学”云云,抵牾已寓其间。又如《瞿塘日录》条云:“故所注《周易》,虽穿凿而成理。至于天下之事物,非实有所见,则茫乎无据。朱子之学必以格物致知为本,正虑师心悬想,其弊必至此也。知德以是讥朱子,宜其敝精神于无用之地,至老死而终不悟矣。”1《总目》谓来知得之注《周易》,既不能把握朱熹格物致知之学,而反道以此讥朱子,实际上是对后世学人口必称朱子,而又不得其学要之风气的批判。而在《李见罗书》一条中《总目》谓:“材尝患世之学者每以朱、王两家格物致知之说,争衡聚讼。因揭修身为本一言,以为孔、曾宗传。而谓知止即知本,又谓格物之功散见八条目中,以朱子补传为误。其学较姚江末派稍为近实,故顾宪成颇称之。”2所谓“世之学者每以朱、王两家格物致知之说争衡聚讼”,实际上正是表明了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行于世的现象。
总的来看,《总目》虽有对于朱熹及其学说的诸多批判,然而主要的方向不在于朱熹本人及其学说,而在于后世宗朱或习朱而不得其传的风气。虽然清学对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本身不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如陈确一往无前致力于推翻理学宝座,梁启超也认为清学的出发点在于对宋学的一大反对,然而理学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朱熹在尧、舜、禹、汤、文、武以下,承绪北宋诸子特别是二程一脉下来的道统脉络,以及以其四书学为核心的科举取士系统,仍然在清代的学术话语中居于统治地位。所以《总目》在《毛氏残书》一条中称:“书中颇诋斥朱子。如谓性与天道,晦庵以词章晦之,而晚更以与季通所言者与众共言,虽欲使禅宗不寄我篱下不可得。其说颇悖。”3在朱熹学说影响力空前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也并不乐观,虽然這些冲突与矛盾还不足以冲击或取代朱熹学说的统治地位,但随着时间的积累,最终为程朱理学在晚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沉寂埋下了伏笔。
Academic criticism of Zhu Xi in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四库全书总目》)
Chen Biying
Abstract:As a master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has a lot of contents related to Zhu Xi and his theory. The word "Zhu Zi" has appeared more than 1700 times in the General Catalogue alone. On the one han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Neo Confucianism occupying the ruling power of academic discourse, the evaluation of Zhu Xi in General Catalogue adheres to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under the viewpoint of "inte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competition for academic discourse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Qing learning, General Catalogue also has a partial criticism of Zhu Xi and his scholarship. The phenomenon of academic criticism in General Catalogue reveals the status and situation of Zhu Xi and his theory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Zhu Xi;Neo 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cademic criticism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 栏目组稿: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