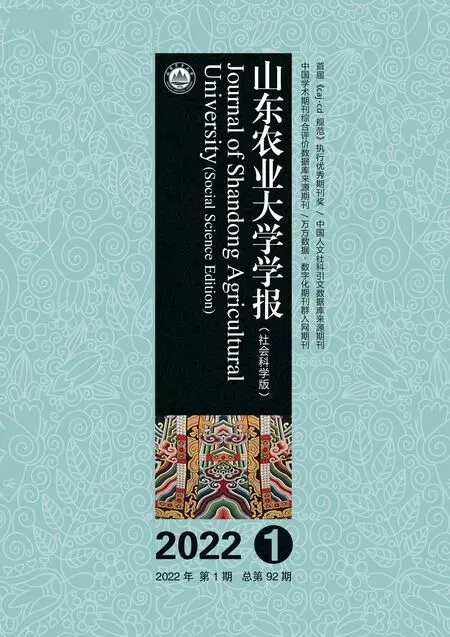新冠疫情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黄俊辉 于铁山
[内容提要]就业风险感知对农民工就业选择与迁徙流动有重要影响。广东东莞131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就业风险感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计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年龄越大,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其就业风险感知更高;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面临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相比国企和外企,在民营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其就业风险感知更高;灵活就业群体在本次疫情中遭受的就业冲击最大,是当前主要的就业弱势群体。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积极关注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做好社会心理预警,从宏观层面营造就业信心,避免农民工就业中的不理性行为。
一、问题与文献述评
目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后文简称新冠疫情)总体上得到有效控制,但国外形势仍不乐观。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统筹的形势下,以加工制造业和外贸出口为主要产业的部分沿海城市出现农民工进城复工后的“返乡潮”现象[1]。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部分企业被迫选择倒闭,部分企业策略性地选择“停薪放假”,从而引发农民工的主动或被动失业,“返乡潮”由此产生。可以说,新冠疫情作为危机事件,对农民工就业已产生显著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91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亿人。农民工作为我国的就业大军,其能否实现稳定就业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后劲、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农民工不得不在诸多不明朗因素(何时能彻底解除疫情、能否短期内研制出特效药等等)的情景下作出返乡还是留(进)城的就业决策,加之知识水平整体偏低,农民工往往难以做出理性决策。相反,农民工此时的决策可能更容易受以往经验、社会情绪、大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依靠心理或主观上的风险感知而作出决策。就业风险感知是个体对就业市场中可能风险的态度与担忧,它反映着个体对就业形势的心理预判。如2003年的“非典”时期,农民工群体曾因恐惧心理而出现大规模的非正常流动返乡,造成大量的自愿性失业[2]。在新冠疫情这一危机事件之下,农民工对就业有着什么样的风险感知?受哪些因素影响? 这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与迁徙流动,更关系到就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新冠疫情中的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涉及社会心理及行为的预测问题,它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如果从政府的角度看,要针对新冠疫情这一危机事件下如何建立适应农民工的社会心理预警机制,让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监测到农民工就业的风险感知以及社会心理,从而前瞻性地采取对策。对于当前来说,这一方面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预警信息,预防农民工在就业中的不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科学的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助其克服恐慌。对于今后来说,不排除还会出现类似危机事件的可能性,研究农民工在遭遇新冠疫情后的就业风险感知,也可为今后遭遇类似情况时提供应急管理措施。
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风险感知的理论研究。风险感知属于心理学范畴,它主要指个体对外界各种风险的感受与认知,强调个体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所获得的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3]。自Bau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风险感知概念[4]后,逐渐形成了风险心理测量流派和风险的文化理论流派。前者主要借助心理学方法来测量、分析风险感知问题。后者主张从认知主体自身的生活方式来分析风险感知,代表性人物是Douglas M和Wildavsky A.B,他们认为风险感知不仅受个体层面的影响,更是个体与所处社会关系的互动结果[5]。
第二,农民工就业风险研究。农民工就业风险属于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范畴,从国内外文献的研究脉络来看,其先后历经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范式的转移。国内文献认为,农民工作为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其就业风险较大[6][7]。车蕾和杜海峰的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风险高于老一代农民工[8]。农民工就业风险的相关文献主要与非农劳动供给[9]、公共服务均等化[10]、工资水平[11]等方面结合起来。
第三,就业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微观和宏观两大方面。从微观上看,Moore、Campbell、Hénin等学者基于不同国家的实证调查,发现性别、年龄、区域、婚育、财富等个体特征对就业风险偏好存在影响[12][13][14]。此外,车蕾和杜海峰基于生计资本的视角,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就业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8]。总体上看,就业风险感知主要与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等因素相关。不过,包括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就业风险感知的影响关系还存在一定差异。从宏观角度看,就业风险受到制度政策、收入变化、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的影响[15](谌新民,2010)。而且,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重大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非典等)等不同背景下,就业风险感知存在很大差别[16]。
已有文献对风险感知的测量与产生形成了相应的流派与主要观点,为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的研究提供理论视野。然而,研究不足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于农民工风险感知的调查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而危机事件下的就业风险感知研究不多见。尽管早年有少量文献关注非典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但此次的新冠疫情比非典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更广,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更深刻。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整体偏低,是否会在危机事件中做出有异于平时的就业决策?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对于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文献主要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个体特征等角度进行分析,行业职业这一因素没有被纳入到分析当中。本文认为农民工就业风险的感知被嵌入在个体、家庭、区域、行业职业当中。尤其是新冠疫情对不同行业职业的冲击是有差异的,很有必要将行业职业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当中。第三、我国农民工群体已逐渐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其成长环境、文化程度、就业特点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很有可能会呈现出不同之处。
二、理论分析
经典的风险决策学说是以认知测量为基础而形成的分析范式,它认为风险感知是决策者的理性认知结果。在人的理性认知与计算下,风险感知聚焦于风险概率及危害的严重程度。决策者通过利益和风险的权衡后形成风险感知[17]。该范式在风险决策与分析中占据主流位置,得到广泛应用。不过,不同的风险事件会促使人们按照不同的逻辑作出感知[18],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下,由于风险的强破坏性和决策信息的有限性,人们的决策并非完全按照理性决策原则,而是更多地受心理、情绪等的影响。以认知测量为基础的风险分析范式并不能揭示人们在一些极端风险或危机事件场景中的反应,如地震、瘟疫等重大突发事件。
由此,心理学家们开始采用以情绪测量为基础的感知风险范式。该范式认为,感知风险应集中在风险因素可能引发的各种负面心理情绪,如风险事件本身的突发性、灾难性、不可控制性及其所引发的影响而带来的心理恐惧与不确定性。部分学者也以情绪测量为基础,对SARS、汶川地震等危机事件中的风险感知作出研究[19]。不过,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已远远超出一般的风险事件,给人们带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风险感知。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就业风险感知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本文所讲的就业风险感知偏重心理学的视角,是指农民工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失业可能性的担忧的主观感知。农民工因为个体、家庭、行业、职业等方面的不同,掌握的信息也不同,从而导致就业风险感知不尽相同。
在个人特征方面,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遭遇性别歧视,失业可能性相对较高[20]。由此可以推断,女性的就业风险感知更高。在面临新冠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时,女性的就业风险感知会进一步加剧。可以假设,与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更高。
农民工主要从事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的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难以支撑繁重的劳动生产,而且其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难度也在加大,进而导致年龄大的农民工就业面趋于变窄,促使其产生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而且在新冠疫情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遭受的冲击较大,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可能成为被解雇的对象。可以假设,年龄越大,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越高。
学历层次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人力资本的高低。学历层次高的农民工拥有更高的能力与素质,可以胜任更高的职位,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其就业稳定性更好,相应地,其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即使在单位裁员或经济形势不好时,学历层次高的农民工被解雇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由此,在新冠疫情之下,学历层次高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低,而学历层次低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高。
在经济能力方面,拥有较多的经济储蓄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疫情之下,经济能力应该用“经济储蓄能维持生活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经济储蓄可以反映农民工维持基本生活时间的长短。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部分用人单位会采取降工资的做法,导致农民工收入减少甚至中断。对经济储蓄较多的农民工来说,即使暂时没能实现就业或者失去就业岗位,也能依靠经济储蓄维持基本生活,其对就业的忧虑程度相对较低,就业风险感知自然也较低;相反,经济储蓄较少的农民工基本完全依靠就业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其对就业的迫切性更为强烈。如果没能获得就业机会,经济储蓄较少的农民工对就业的忧虑程度将会提高,其就业风险感知也就较高。
在地域特征方面,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包括省内和跨省两种流动形式。已有文献一般认为,跨省流动尤其是大范围的跨省流动就业意味着农民工在流入地将会遇到更多的文化、习俗、饮食、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省内流动相比,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可能要面对更多、更难的文化调适过程[21][22],从而加大了就业难度,导致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与风险,但与已有文献的机理分析存在差异。因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多数采取长途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方式,部分边远地区的农民工可能还要多次转车,病毒感染风险更高。疫情扩散导致很多企业复工复产时间推延甚至停工停产,更有部分企业在疫情冲击下被迫倒闭,导致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推延进城就业计划,因此,他们对企业的用工、工资发放等方面表现出担忧,从而会有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
在家庭状况方面,未婚的农民工在家庭照顾方面的开支较少,即使因新冠疫情影响而没能就业,其经济压力也较小,从而导致就业风险感知较低。而已婚的农民工因为家庭照顾等各方面的开支较多,在遭遇新冠疫情而未能就业时,其经济压力较大,从而产生较高的就业风险感知。如果农民工育有孩子,就意味着在食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越大,抚养压力越大,当面对新冠疫情时,对就业形势可能会有更多的忧虑,从而有着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
在职业特征方面,不同行业职业的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存在差异。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以外贸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不仅受国内疫情影响,受国外疫情影响更大;以餐饮、旅游、娱乐、运输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尽管在疫情早期受到很大影响,但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各类服务业逐步得以恢复。因此,新冠疫情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大、更长远,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风险感知更高。此外,在国有、集体等单位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好,与民营单位相比,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小,就业风险感知自然较弱。即使在同一行业或同一类型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因为自身的可替代低,就业稳定性更好,而一般员工和产业工人的可替代性较高,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其就业风险感知稍高。此次疫情对农民工的经营与创业产生较大冲击,工资性收入减少的效应明显[23],与有雇佣单位的群体相比,灵活就业者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其收入减少效应尤为显著,就业风险感知更高。
综上所述,从个体、地域、家庭和职业四方面构建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0年3月下旬在广东东莞开展的专项调研。东莞作为“世界工厂”,吸引了近600万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典型的流动人口大市,选取东莞开展调研具备典型性。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调查采取网络调查方式,通过异地商会、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协助,借助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共有1310名农民工接受了问卷调查,受访者覆盖农民工从事的主要典型行业,来源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二)数据描述
对于1310名受访者的个体、家庭、区域和就业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此处重点介绍受访者的就业风险感知。调查中有564名受访者表示“发生新冠疫情后,就业风险没有变化”,占样本总量的43.1%。与此同时,有676名受访者表示“发生新冠疫情后,就业风险变高”,占样本总量的51.6%,只有70名受访者表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就业风险变低”,仅占样本总量的5.3%。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在新冠疫情之下,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高,这意味着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就业依然是最大的民生,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保障是就业服务中的一个重要工作。相关的信息也表明,与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相比,农民工是城市里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24]。

表1 受访者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置
就业风险感知为“变低”“没有变化”“变高”三种类型,分别赋值为1、2、3,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排序关系,数值从低到高意味着农民工在新冠疫情下的就业风险感知程度的上升,适合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建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其基本函数为:
(1)
在式(1)中,yi是响应变量农民工i的就业风险感知;Pi代表农民工yi的就业风险感知受因素j影响的概率;影响yi的自变量分别记为x1,x2,x3,……,xm;α为回归方程的常数;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计量检验结果
建立新冠疫情背景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从相关检验系数来看,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总体上看,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年龄、学历层次、经济储蓄、地域特征、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存在影响,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个体特征来看,相比女性,男性的就业风险感知更低,但这种影响关系并不显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年龄上,与年龄较大的组别相比,年龄较轻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相对较高,不过,只在“30-39岁”这一组别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往往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且已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支柱,既要抚养未成年孩子,又要赡养年迈的父母,家庭开支较大。年轻的农民工大多还未成家,还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家庭支出,而年龄稍大的农民工经过多年打拼,积攒了一定的财富,家中的抚养赡养压力相对较小。“30-39岁”这一组别的农民工正好处于夹心层,他们的财富积累尚不足且家庭开支大。他们主要通过进城就业而获得经济收入,当遭遇新冠疫情时,他们会更担心疫情对自己就业的冲击,其就业风险感知自然会更高。从学历上看,学历层次对就业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学历层次更高的农民工意味着更高的文化素质和更强的就业能力,当遭遇新冠疫情时,其被解雇的可能性也低于学历层次低的农民工。即使被解雇,学历层次高的农民工的再就业能力更强。由此,学历层次高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经济储蓄反映出农民工财富的积累状况,也体现出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农民工如果被解雇,其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就要依靠自己的储蓄加以维持。在新冠疫情下,这一就业风险感知会被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储蓄多的农民工相比,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更高,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经济储蓄较少的农民工与经济储蓄较多的农民工相比,前者就业风险感知增加一个等级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06倍。
地域特征对就业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相比,省内流动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变低的可能性更大。易言之,从省外流动至东莞就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就业风险变高。与省内流动相比,跨省流动大多意味着更长的地理距离、路途更为遥远,农民工基本都选择长途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农民工出于路途遥远和新冠肺炎的恐惧而推延进城就业计划,同时也担心企业的经营状况、用工情况和工资发放因疫情而遭受影响,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和未来出路有着更多的忧虑,从而产生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
在家庭特征方面,未婚相比于其他婚姻状态,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变低的可能性更大;在生育方面,与有孩子的相比,没有孩子的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变低的可能性更大,不过二者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职业特征上,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类型对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前文的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不过,这表明新冠疫情对第二、三产业形成全面的冲击。尽管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国外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外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第二产业,而是通过一系列产业链条传导至所有产业部门。职业类型与就业风险感知存在负向影响关系。与“灵活就业及其他”相比,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对就业风险感知的影响关系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这两类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偏低,也表示“灵活就业及其他”这一组别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高,灵活就业群体在新冠疫情中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也是本次疫情中的就业弱势群体,相关部门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保护。在单位类型上,与“民营企业或其他”这一组别相比,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低,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来说,员工的就业风险感知与企业的规模紧密相关。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往往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容易给员工提供较好的就业保障,从而降低员工就业风险感知。相比较而言,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偏弱,不容易给员工带来较好的就业保障,从而导致员工就业风险感知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新冠疫情对民营企业的冲击更大,在稳定农民工就业中要重点关注民营企业的稳就业作用。

表2 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广东东莞131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对新冠疫情下的就业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有:
第一、新冠疫情加大了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尽管有四成的受访者表示“发生新冠疫情后,就业风险没有变化”,但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就业风险感知变高,即新冠疫情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在新冠疫情之下,就业依然是最大的民生,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保障是就业服务中的一个重要工作。而且,与疫情发生之前相比,保就业、稳就业的压力更大。
第二、年龄、文化程度、经济储蓄和地域特征等个人特征对就业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尤其是“30-39岁”这一组别的农民工正好处于夹心层,其就业风险感知偏高。与经济储蓄多的农民工相比,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学历层次对就业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
第三、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面临更多的困难与风险。因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多数采取长途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方式,部分边远地区的农民工可能还需要多次转车,在新冠疫情之下,其病毒感染风险更高。疫情扩散导致很多企业复工复产时间推延甚至停工停产,更有部分企业在疫情冲击下被迫倒闭,导致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推延进城就业计划。由此,他们对企业的用工、工资发放等方面表现出担忧,从而会有更高的就业风险感知。
第四、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等职业特征对就业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与“灵活就业及其他”相比,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这两类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偏低,“灵活就业及其他”这一组别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高,灵活就业群体在新冠疫情中遭受的就业冲击最大,也是本次疫情中的主要就业弱势群体。在单位类型上,与“民营企业或其他”这一组别相比,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较低,相比较而言,在民营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较高。
(二)政策启示
第一、建立大数据平台分析农民工就业风险并做好社会心理预警。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可能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就业风险对迁移就业选择有重要影响[25]。所以,应及时披露有关就业信息,做好就业形势研判,以稳定农民工的就业心理预期。建立大数据平台甄别出高就业风险农民工群体,从学历层次、工作技能、家庭状况、职业类型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信息收集,并建档立案,基于大数据技术预判高就业风险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为就业政策以及就业服务的精准实施提供基础性数据。与此同时,建立针对农民工就业的社会心理预警机制,及时监测农民工的就业风险感知,前瞻性地采取对策和提供必要的预警信息,预防农民工在就业中的不理性行为。
第二、实施更加精准的农民工就业帮扶服务。一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加强与行业协会、人才市场的信息对接,为高就业风险的农民工群体提供转岗就业、职业培训的资源平台。二是相关部门应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和远程职业培训,帮助学历层次偏低、年龄较大、经济收入偏低、就业稳定性差等为特征的高就业风险农民工群体提升学历和技能,为疫情后的恢复性生产提供人力资源的储备。三是通过补贴培训、发放生活补贴等方式,鼓励和引导企业对员工开展职业培训,达到优化存量人力资源的效果,助力农民工群体就业。
第三、积极发挥新经济形态在促就业、稳就业中的作用。在新冠疫情之下,数字经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催生了多种新经济形态,如直播带货、云办公、在线医疗、线上教育等得到快速普及。应该积极发挥新经济形态及相关产业链吸纳就业的作用,通过新经济形态加快吸收闲散劳动力和灵活就业者,发挥其促就业、稳就业的作用。
第四、对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民营企业给予更多政策帮扶。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本次疫情中遇到的冲击更大。在我国,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相当优势。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重点关注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民营企业,如外贸出口型、劳动密集型等民营企业的用工和经营情况,为其提供充足的政策帮扶,以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达到稳就业、促就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