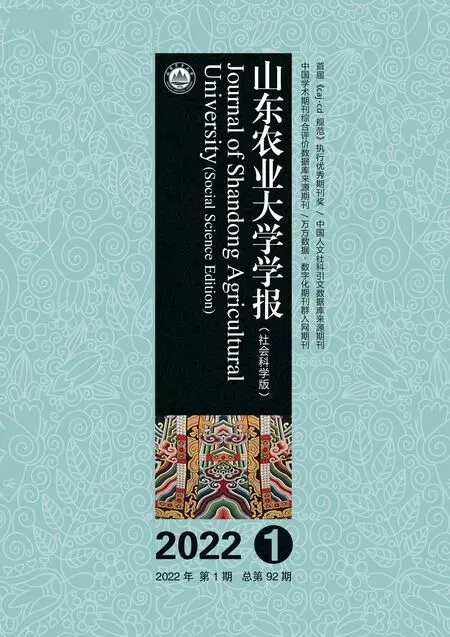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信息素养对社区融入的影响研究
□张晓雨 张 亮 崔丙群 刘一漩
[内容提要]针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信息分化现象,以及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社区融入障碍问题,通过构建农民信息素养和社区融入的测量模型,研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利用调查问卷收集403份山东省农村社区的相关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民信息素养水平对其社区融入程度的影响作用,分析农民信息素养各测量变量对社区融入的作用系数。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信息安全意识随着农民信息获取和识别能力的提升而逐渐提高,而农民的心理文化融入与日常生活融入紧密相关。在农民信息素养中,信息理解利用对其社区融入的影响作用最大,而信息共享交流通过改变农民的社会资本对其社区融入也能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在社区融入方面,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文化融入是首要问题。农民的信息素养对其社区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意见》提出将农村社区作为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公共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因此,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融入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已经习惯乡土生活的农民,在社区融入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和困难,甚至对城乡一体化产生了抵触情绪,出现了“反城市化”或“逆城市化”现象[1]。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融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息问题,信息贫困和短缺会对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负面影响,而信息能力能够促进移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定居和社会融入[2-6]。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信息分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并且阻碍着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7,8]。本文通过对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信息素养与其社区融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农民信息素养的各构成维度对其社区融入的影响路径,从而为推动农民更好地融入新型农村社区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信息素养与社区融入
信息素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泽考斯基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80年代末,美国图书馆学会下设的“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给出了信息素养的权威定义,其认为信息素养应该包括信息需求的确认以及信息搜索、评价和利用方面的能力。自此对于信息素养的关注逐渐增多,一方面,以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关机构纷纷提出自身的信息素养标准。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了针对学生培养的信息素养标准[9]。而另一方面,信息素养的学术研究也成为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对信息素养的内涵与外延、构成维度和影响作用展开研究,包括数据素养、媒介素养和元素养等新概念的提出和由信息素养差异而导致的信息分化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10-15]。但是,在目前的较多研究中,会将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而本文认为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存在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对于农村居民,其首先对于信息的价值认知不足,而这种价值认知的缺少导致农民缺少提升信息技能的动机。随着信息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安全成为人类面临的必然问题,因此,在现代人的信息素养构成中还应该包含信息安全意识或信息道德。随着我国农村社区化进程,农民的信息化环境的改善和信息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民同样面临着信息安全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农民信息素养体系在传统的信息能力构成即信息获取识别、分析利用和分享交流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信息价值认知和信息安全意识两个维度,从而形成农民的信息素养指标体系。农民信息素养的指标构成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农民信息素养的指标构成关系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面临着多方位的社区融入问题,包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和心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16-18]。社区化进程中很多农民面临着失地的问题,同时,社区的居住环境也不太适合从事农事活动。而伴随着城乡的融合发展,农民的消费水平却在逐步提升。因此,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农民面对个人生计问题,即社区的经济生活融入问题,使其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需要进行调整。社区化会带来生活环境的变化,体现在社区环境、规章制度、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时,撤村建居的过程中,社区居民往往来自于多个自然村,因此农民也面临着社会网络重构的问题,体现在其社会交往和社区活动等方面,都会有所调整和适应,即社区日常生活融入问题。此外,社区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同样面临着地域和心理等方面的融入问题。由于农村社区化进程大都是改变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但是其地理位置不会有太大改变,而社区心理融入主要体现对身份、文化的认同和其内心的归属感上。农民社区融入的构成维度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农民社区融入的构成维度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采集
(一)概念模型构建
基于信息素养和社会融入已有研究结论[19-21],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的信息素养水平对于社区融入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由此构建本文的理论概念模型,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农民信息素养对社区融入的影响概念模型
(二)研究数据采集
概念模型中的农民信息素养和农民社区融入均为潜在变量,不可直接观测。因此,本文在信息素养[22-24]和社区融入[25-27]的相关研究基础上,选择信息价值认知、信息获取识别、信息理解利用、信息共享交流和信息安全意识五个观测变量来测量农民的信息素养。同时,选取社区经济融入、社区生活融入和社区心理融入三个观测变量测量农民的社区融入,并通过具体观测问题项的设置形成调查问卷。信息价值认知方面,通过信息影响认同、信息作用认可、信息需求程度和信息支出意愿来四个问题项来测量。信息获取识别方面,通过信息渠道数量、新型渠道使用、信息来源发掘、信息及时获取、信息分辨过滤、信息真伪辨别六个问题项来观测。信息理解利用方面,通过信息有效利用、信息整合使用、信息大意提炼、信息用途思索和信息应用扩展五个问题项进行观测。信息共享交流方面,通过信息分享意愿、信息表达能力、信息传递手段、信息技能分享和信息分享收益五个问题项进行观测。信息安全意识方面,通过相关法律了解、不良信息识别、个人信息保护和违法行为规避五个问题项进行观测。每个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及问题项如表1所示。社区经济融入方面,从收入来源调整、收入差异缩减、收入影响适应、消费水平承受和工作机会发掘等五个方面来测量。社区生活融入方面,主要从生活环境融入、社交网络融入、社区管理认可、社区活动参与和生活习惯适应五个问题项来测量。社区心理融入方面,主要从居民身份认同、文化风俗融入和社区心理归属三个方面进行测量。具体的观测变量和测量问题项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信息素养对其社区融入影响测量模型
本文依据上表的测量问题项,基于5点的Likert量表形成调查问卷。选取了山东省43家完成社区化改造的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每个社区发放调查问卷10份。共发放问卷430份,收回有效问卷403份,有效问卷比例为93.72%。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一)信度检验
在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是指对同一事物进行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整体一致性程度。本文采用克隆巴赫α系数对问卷数据进行效度检验。利用SPSS 16.0软件测算的结果显示,总体数据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07。而各潜在变量指标数据的克隆巴赫α系数如下:信息价值认知为0.776,信息获取识别为0.811,信息理解利用为0.827,信息共享交流为0.742,信息安全意识为0.716,社区经济融入为0.840,社区生活融入为0.795,社区心理融入为0.700。由此可知各潜在变量的克隆巴赫α系数也均大于0.7。这说明测量模型的内在一致性较好,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
(二)效度检验
效度指测量得出结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效度越高代表测量事物真正特质的效果越好。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测量数据的效度检验。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农民信息素养测量量表的KMO值为0.919,农民社区融入测量量表的KMO值为0.893,均大于0.8;两者的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值分别为4194.346和2114.771。其P值均小于0.05,因此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农民信息素养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信息素养因子载荷分析结果
根据表3的因子分析结果可知,公因子1主要载荷了信息理解利用的四个问题项,因此该因子命名为信息理解利用。而公因子2方面,农民信息安全意识的四个观测变量与信息获取识别的四个变量共同负荷在一个公因子2上,这说明一方面,农民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不良信息辨别和筛选的意识,另一方面,在农民获取的信息中就包含部分关于信息安全的相关内容,这使得农民的信息安全意识得以提升。此外,伴随着农民获取信息的增多和对信息的辨识能力提高,农民逐步形成了信息安全意识。这说明信息获取识别与信息安全意识很好地融合到了一个观测变量中,为了同时兼顾信息获取和信息安全两个方面,本文将公因子2命名为信息获取辨识。公因子3主要载荷的是信息价值认知的指标,因此命名为信息价值认知。公因子4主要载荷的是信息共享交流的指标项,因此命名为信息共享交流。而对农民社区融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社区融入因子载荷分析结果
从农民社区融入指标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来看,社区生活融入和社区心理融入两个观测变量的指标共同负荷在一个公因子上,这说明农民在日常生活逐步融入进社区的过程中,心理也跟着一起融入到社区生活中,即生活融入与心理融入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本文将该公因子命名为社区生活融入。而另一公因子上负荷的仍然是社区经济融入的各指标,则仍旧命名为社区经济融入。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农民信息素养的观测变量调整为信息理解利用、信息获取辨识、信息价值认知和信息共享交流四个,而农民社区融入的观测变量调整为社区经济融入和社区生活融入两个。两个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调整后,本文对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重新进行检验。信度检验的结果表明,总体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0,各指标的克隆巴赫α系数如下:信息理解利用为0.833,信息获取辨识为0.844,信息价值认知为0.801,信息共享交流为0.788,社区经济融入为0.840,社区生活融入为0.852,均大于0.7,这说明量表数据依旧具有很高的信度。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对测量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对农民信息素养水平与其社区融入程度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利用AMOS 20.0软件对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进行测算,并验证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为了提高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需要对模型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度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修正后的模型输出结果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的参考理想值,可以发现,通过模型修正,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值有较为明显的改善,模型修正前后的整体拟合指标值对比如下表5所示。

表5 修正前后的模型整体拟合结果对比
利用AMOS 20.0软件测量出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表6所示。

表6 修正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二)研究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输出结果可知,首先,外生潜变量农民信息素养对内生潜变量农民社区融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84,大于0。这说明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成立,即农民信息素养的水平对其社区融入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民的信息素养水平能够有效地消除农民在社区融入过程中的障碍,促进农民更好地融入进社区化的生活中去。
其次,根据输出的路径系数,农民信息素养的观测变量对社区融入的影响作用依次为信息理解利用0.90>信息共享交流0.78>信息获取辨识0.76>信息价值认知0.75。这说明信息理解利用对于农民的社区融入影响最大。信息在农民的社区经济、生活和心理融入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只有实现信息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社区融入,而信息融合又与农民的信息利用处理紧密相关[28]。只有提升农民对信息工具和信息本身的利用和处理水平,才能推动农民从经济、生活和心理方面全面融入到社区当中去。信息手段的丰富和信息的有效利用能够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工作信息、创业信息、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经济收入,使其非农收入增加或者从传统的种养农业向新型农业转变,消除社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实现社区经济融入。另一方面,现代社区化的管理更趋向于信息化管理,会更加依赖信息工具和手段来实现社区的管理与服务。不论社区是采用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在线社区还是新型手机应用来协助社区管理与服务,都对农民的信息理解与利用能力有所要求。因此,信息理解利用水平对于农民的社区生活融入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包括包含在生活融入中的心理融入。
此外,信息共享交流对农民社区融入也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通过信息的共享交流除了可以使农民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共享交流的过程可以改善农民的社会资本特征,优化农民的社会网络结构。农民社会资本形成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是一种典型以强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网络。信息分享交流的能力可以让农民打破原有的社交范围限制,提升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比重,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重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比如新媒介提供的基于位置的服务就可以让农民在新的社区环境下较快地形成新的邻里关系[29]。但是,这种信息分享交流是建立在信息工具和手段利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量表调整前部分信息分享交流的观测变量融入到了信息分析交流维度中。而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又能够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异质性资源,推动其社区经济融入的进程。
再者,农民的社区生活融入的路径系数为0.85,大于社区经济融入的路径系数0.74。这表明农民的社区融入过程中首要的是日常生活的融入,以及伴随着生活融入过程中的心理文化融入,然后才是经济融入的问题。农民的社区日常生活融入既包括对于社区生活环境、管理服务和日常习惯的适应,也包括对新的社交网络和组织活动的参与。农民的信息素养能够让其快速地了解社区管理的规章制度,充分利用社区的服务支持网络,并通过社会资本的连接性较快地融入新的社区社交网络中。此外,较好的信息素养可以让农民更多的接触到新的社区文化,了解城市居民的生活特征,从而促进其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和自身的身份转变。因此,推动农民的社区融入时应该以文化和生活先行,然后再考虑经济生活的融入问题。
五、结论
本文利用403份山东省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通过农民信息素养对其社区融入影响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民信息理解利用能力的提升,其信息安全意识也逐步形成,而农民的社区心理融入与日常生活融入两个过程融合在一起。农民的信息素养对其社区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信息素养的四个观测指标中,对于农民社区融入影响最大的是信息理解利用的能力,其次是信息分享交流,然后是信息获取辨识和信息价值认知。而在农民社区融入过程中,首先应该注重的是要实现社区的日常生活融入,包括心理文化的融入,然后才是社区的经济生活融入。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农民信息素养对于其社区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需要注意通过提升农民的信息素养去加快其社区的融入过程。要提升农民的信息素养首先必须要农民意识到信息的价值,认识到信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典型事例的宣传唤醒农民的信息价值觉悟,提升其信息消费的支出和水平[30]。其次,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加强农村社区的信息服务网点建设,积极搭建农村社区公共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目前,我国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覆盖率要不足三成,这使得农民的信息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再者,加强社区的志愿互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建设。非正式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是社区的经纬线,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已经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主体。通过社区的志愿互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建设,能够拓展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交网络,增加其信息来源渠道,并有效提升其信息分享交流的能力。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组织对于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在民政部发布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就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力争到2020年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最后,要实现农民社区居民信息素养的持续提升,必须要让信息化专业人才扎根于农村的基层服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社区基层管理组织中需要配备具有信息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积极开展针对农民的信息技能公益性培训,甚至可以考虑把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到农民的职业培训中来[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