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分钟你是和谐的
长安

诗人郑敏
金黄的稻束,还有橘子
年初得知郑敏先生仙逝,便翻出陈年日记。一九八八年春天为写毕业论文曾去清华园拜访过郑先生两次,五月一日和二十八日。郑先生讲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她讲到了西南联大,讲到了《金黄的稻束》,也讲到了里尔克的诗和纪德的《窄门》。她还说家庭是个橘子,每个人都是橘子瓣儿,彼此相伴又各自独立。又说自己非常喜欢唱歌,乐在其中,并嘱我一定要好好享受年轻的日子。本以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该是位龙钟的老者,她却仿佛超乎时代,有活力,有气场。那年她六十八岁,作为诗人渐入佳境,作为学者踌躇满志。
论文的诗歌评赏部分后来略加修改,题为《沉思的诗》,投给了《名作欣赏》。不久该刊编辑吴方先生约我面谈。吴先生面色黯淡凝重,似乎亦有几分颓唐,颇像鲁迅笔下的吕纬甫或魏连殳。那是我头一次见识校外编辑,觉得与校刊那几位温雅清秀的大男孩不太一样。那篇文章刊于《名作欣赏》一九九○年第二期,旧作重读,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看到自己谨谨慎慎地写论文,小心翼翼地旁征博引,黑格尔、罗丹、梵高、艾略特、鲁迅、梁宗岱、托尔斯泰、泰戈尔……啧啧,多乎哉,可引可不引啊。
金黄的稻束,还有橘子。她的金黄的四十年代,我的金黄的八十年代。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应该也不会两次读出同样的郑敏。
我是“五四”培养的
五四,说不尽亦绕不开。郑敏的同龄人张爱玲在散文《谈音乐》里说交响乐乃“有计划的阴谋”,“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在小说《五四遗事》里则讲了个五四时代自由恋爱的故事,结局是三美团圆、妻妾同堂,不三不四也不五四。张爱玲对新文学始终有所保留,曾在致友人信中说:“我是真的看见坏文章就文思潮涌,看见好的就写不出。以前我有《五四新文学大系》中的两本,写不出就拿来看看,奏效如神。”(《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新文学如此读法,大概空前绝后。后来张爱玲为《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撰写英文小传,谈到面对文化隔阂不得不自我理论化,遂发现新文学早已深植心中,也算为五四新文学正了一下名。
回首来时路,年过七旬的郑敏说:“我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我觉得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太糟糕了,在那时的国民教育中完全忽略中华文史哲的传统”,“我再回去找的时候觉得很痛苦,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再返回去挖掘这些东西,的确很难”。(《诗歌与文化》)年逾八旬的郑敏说:“我是‘五四培养的,所以我在青年时期绝对是打倒传统,根本就不去看古籍。”(《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年近九旬,郑敏又说:“‘五四的大师们他们自己都是在古典汉语的丰富词汇喂养中长大的,却由于意识形态的取向,限定我们只许吃口语的萝卜白菜,不许使用文学汉语宴席上的山珍。”(《中国新诗与汉语》)郑敏谈到五四便纠结,甚至有些情绪化。五四之于郑敏意味着一场断裂、一份遗憾,漫长的晚年里郑敏一直在反思,在寻觅,在弥补。
文学革命废文言兴白话,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地貌。谈到自己那辈人的文学起点,郑敏道:“在这样重大的语言断裂之后,我们那时候唯一的路子就是用翻译来充实……就这样,我们的语言慢慢走上另一条道路。当然这其中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在于我们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语法结构等,逐步建构了自己的白话文学语言;坏处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史结合进来,做到民族语言与西方语言相融合,而是把古典汉语给扔开了。”(《诗歌与文化》)这里所谓的翻译主要指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丛刊中的汉译外国名著,郑敏在《我的小传》里曾说:“当时的《世界文库》是我痴爱的读物,通过它我接触了西方文学的精华和有哲学深度的散文。”这份痴爱酿就了郑敏的“洋味儿”,也成就了日后的女诗人。《世界文库》中亦有中国古典文学,她不看。

从前我在《沉思的诗》里曾拿郑敏与穆旦做比较,认为郑敏的诗即使写痛苦“也不像穆旦诗那般强烈,而是在静默沉思的氛围中自然流露”。穆旦的诗更炙热、更沉重、更有“洋味儿”也更像翻译诗。郑敏认为穆旦的语言主要来自“西方的语言文学,因为穆旦的成长注定他比卞之琳、戴望舒、冯至离古典文学更远”(《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说穆旦好像也在说她自己。二十年前江弱水曾经为文批评穆旦,认为“他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傍;他过于仰赖外来的资源,因为他并不占有本土的资源”,指出对古典“‘彻底的无知造成了穆旦的失败”(《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行文精彩痛快,只是似乎有些小瞧了穆旦的主体性。诗乃语言之花,诗里异质元素的冲突亦来得尖锐决绝。化欧化古融会贯通乃理想境地,融了通了异质性多半也就消失了,雅了驯了也就不是穆旦了。
穆旦、郑敏、张爱玲皆同代人。张爱玲曾将母亲的新天地与父亲的旧世界“强行分成两半”(《私语》),因为自小浸润于古典,不“强行”便分不开。幼少时浸润过了便可能化为血肉,跟学语言一样,要点儿童子功。现代作家里行文够得上简劲雅驯者屈指可数,鲁迅、钱锺书、张爱玲……都有童子功。鄭敏、穆旦们却是五四培养的,他们的世界大致泾渭分明,不必“强行”分割。郑敏与穆旦都于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穆旦一九五三年回国。一九五二年郑敏到纽约学习音乐,张爱玲赴香港写作。一九五五年郑敏离开纽约回国返乡,张爱玲则来到纽约开始自我流放。
那一分钟你是和谐的
“1942-1947年,我走过一条典雅的小道。”(《我的爱丽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郑敏被唐湜形容为“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郑敏静夜里的祈祷》),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融知性、理性于感性,散发着宁静肃穆的学院派气息。赴美后郑敏在布朗大学研究院攻读约翰·顿(John Donne)的玄学诗,“由于研究的角度是学术性的,身份是研究者,日久就对诗失去诗人的兴奋和创造冲动”(《我与诗》),回国后则“随着知识分子大军在风暴中旋转,直到1979年”(《闷葫芦之旅》)。她曾把自己的诗集付之一炬,还做过一个天真的梦,“梦见母亲的餐桌上铺满佳肴/当我们尽情地咀嚼/桌下的鳄鱼咬断了我们的脚趾”(《天真的梦》)。诗歌生命冬眠了近三十年,郑敏自云:“我的诗神也由一个青春的女神变成一位沉思的智者,他递给我的不再是葡萄美酒,而是一种更浓烈的极香醇的白酒,我的诗有时有些不胜任。”(《郑敏:跨越世纪的诗哲人生》)郑敏认为冬眠初醒时创作的《寻觅集》“带着很重的枷锁,政治的枷锁”(《读郑敏的组诗〈诗人与死〉》,《诗探索》1996年第3期),“有时候它太概念化了,有时候又太追求透明度了,所以,内涵受到很大损失”(《诗歌与文化》),“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闷葫芦之旅》)。后来郑敏受到解构理论启发,慢慢又找到了艺术转换的途径,便以解放的诗心创作了另一本诗集《心象》。在《创作与艺术转换—关于我的创作历程》一文中郑敏说:“我的心灵深层如一扇教堂的大门在管风琴声中徐徐启开,我感觉好像有很多小小的精灵飘进我的深处,它们唤醒了我的深处沉睡的无意识。”教堂、管风琴、小精灵,都带着洋味儿。
再度提笔诗人已年近花甲,感叹“懂得爱落叶的人/早已不再是睡莲样洁白”(《深秋的林地》),亦醒悟“真正的诗人不知要经过多少次危机,蜕去多少层皮”(《诗人必须自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郑敏在《树》里写道:“当春天到来时/它的每一只强壮的手臂里/埋藏着千百个啼扰的婴儿。”一九八七年则写道:“我受到惩罚/在充满谎言的春天。”(《充满谎言的春天》)一九四三年郑敏写了一首《寂寞》:“在我的心里有许多/星光和影子,这是任何人都看不见的”,“一块块的岩石,一颗颗的大树,一个不能参与的夢”。一九八九年又写了一首《成熟的寂寞》:“当我合上眼睛,门就开了/山谷里充满寂寞的雾/像幽灵样飘荡。”此春天早非彼春天,此寂寞亦非彼寂寞。郑敏自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坚硬的但却有积极意义的寂寞感,这种寂寞是一个人为了走自己的道路所必须拥有的。”(《闷葫芦之旅》)郑敏的寂寞像雾,然而却是坚硬的。

“穿过穿不透的铁甲/它回到我的意识里/在那儿放出/只有我看得见的光。”(《“它”》)时间之花再开,里面读得出时代的荒谬与诗家的觉醒:“我们宁可在海浪里/和鲨鱼搏斗/也不能再做天真的梦/梦见和鳄鱼握手”(《天真的梦》),“需要一个黑色的铸铁座/来托起仍在流血的心灵”(《沉重的抒情》)……然而郑敏心中依然装着那个静夜里祈祷的少女:“不肯消逝的童年/埋藏在阿丽丝的小屋里”(《用阿丽丝的天真》)。少女变母亲,又变祖母,诗歌里亦多了些母性话题。当年读《金黄的稻束》像看油画看雕塑,如今更在意诗中对母性的吟诵。《郑敏诗集:1979-1999》第五卷《母亲没有说出来的话》便是“献给所有因母爱而时时痛苦的母亲”的。她描述母性的惆怅:“你的手自我的掌中消失/玫瑰告别了晚秋的花枝。”(《后悔》)她怀念少年时代的儿子:“那逝去的你的影子仍站在风前/操场上,课堂外,马路边/朦胧地走着、踢着石子,难解/这小命运和大命运的结。”(《生命的距离》)她遥望追梦的女儿:“也许梵高的彩舟再次浮现在雾中/载着你和你的一代从绝望里航来。”(《一个雨急云飞的下午—给蔚》)而她写给外孙的诗则像寂寞主题的少儿版:“小松鼠忽然长大了/它知道这山上/谁也看不见谁/谁也都是一颗雾珠/永远永远在飘浮。”(《留给豆豆的诗》)这些诗作印刻着一位知识女性丰盈细润的人生体验,与《金黄的稻束》里的母性话题遥相呼应。
郑敏在文论中呼唤古典,在诗歌创作上却并没有那么意气用事。关于诗中的“洋味儿”,关于使用西方意象,郑敏认为要从文化素质上考虑,关键是得真正有所感受、有所渗透,并坦言:“我觉得我是渗透了。”郑敏强调写诗要有一种和谐的状态:“我绝不能生硬地说,我现在要吸收中国的,就生硬地把自己的写作改了,我决不这么干,除非那个东西融入了我。写作的时候,那一分钟你是和谐的,你要对它进行什么有意识地改造啊,扭转啊,那必然失败。”至于对外国文学、文化的所谓误读,她也说得很明确:“我是作为中国人来研究它。所以,所有的误读都是允许的……你不能接受的就不要接受,等你以后觉得应转变时再转变,只能如此。” (《读郑敏的组诗〈诗人与死〉》)坚硬的寂寞罩着一个坚硬的自我。
唐湜在那篇《郑敏静夜里的祈祷》里称赞郑敏诗中有“虔诚的祈祷与真挚的思索,丰盈的思想与生动的意象”,但在文章结尾处还是一吐为快:“这仅仅是过于绚烂、过于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一种偶然的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郑敏如何评价自己?八十二岁时,她说:“我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歌在寓一切于感性方面比较成功,遗憾的是过多沿袭以歌德、里尔克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的境界与感情,而缺少自己的特殊心态。”(《创作与艺术转换—关于我的创作历程》)所谓“特殊心态”或许亦关乎时代、历史,但恐怕更关乎阅历、经验乃至表达方式。八十三岁时郑敏自我总结道:“早期的作品中关于画的诗,在艺术上比较完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了一首《诗人与死》,也比较完整,我还写过一组《诗的交响》,比较能够融合我的各个方面。其他零散的作品就不太好说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过渡者,是中国新诗寻找、走向它成熟阶段的一个诗人,后人来看肯定会发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探求新诗内在的语言规律》) “过渡者”一语,让人想到鲁迅所谓的“中间物”(《写在〈坟〉后面》)。八十四岁时郑敏又说:“我的诗歌文本很少很少能完成它所肩负的对深刻的感受和思想的艺术转换这一崇高职责。我为此深深负疚,这是永久的遗憾和无奈。”(《诗、哲理和我》)对自己似乎越来越不宽容。
百岁新诗,仍属幼年
郑敏在文论中屡次提及二十世纪汉语文化的两次重创。五四废文言,郑敏叹惋:“对古典诗词这种登峰造极的凝练艺术,若白话文先驱们不是遗弃,而是精心钻研,白话文及新文学的成熟、深造,要到临得早得多,而整个新文学史的面貌都将为之改观。”后面的创伤亦令郑敏怃然且惘然:“五十年代至一九七九年间,汉语在用词、含义方面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改革,与世界其他说汉语的华人与汉学家所使用的汉语,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有了根本的差异。”(《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对中国当代诗歌郑敏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她指出,一些青年诗人“本质上缺乏个性,营养不良,表面上又闪闪发光。这个贫乏、营养不良的‘我,在意识深处没有历史,没有人类的命运,没有昨天和明天,而他(她)的今天又是如此闭塞”(《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今先锋派新诗创作》)。她断言:“在遗忘了自己的文化,又不理解世界的文化的中国诗人中很难出一个有二十一世纪代表性的大诗人。”(《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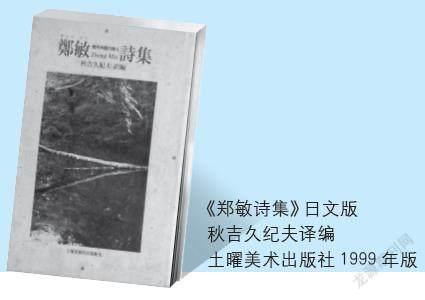
郑敏认为新诗“没有形成文学语言”(《探求新诗内在的语言规律》),指出“今天有些新诗作者忽略了汉语诗的特点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写出一批非汉语的汉语诗和非西语的西方诗”,这些诗歌“颇有寄生于西方诗歌之嫌。由于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巨大差异,这种寄生是没有前途的”,而翻译体则是“一条饮鸩止渴的路”(《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话说得够重,里面应该有她自己的遗憾与无奈。郑敏依据解构主义语言学及哲学,认为“民族语言的根是生在民族无意识中,文言文与白话文自古就并存在中国文学创作中”(《中国新诗与汉语》),还指出西方现代诗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汉诗及古汉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出现与复苏究其源头亦在古诗词,强调要与古典接轨,找回新诗自主权。
郑敏非常关注新诗的音乐性,自云从小受到的熏陶及训练不足,对汉语不够敏感,每次写诗都觉得有些遗憾,“我对我的诗最大的不满足就是没有多少音乐性”(《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与吴思敬先生谈诗》)。关于白话格律诗她也指出:“由于在音乐方面长期忽视探讨,白话格律诗多半只做到押尾韵,控制行数,并没有关于‘内韵,即行内及行间的韵的自觉呼应。”(《探索当代诗风》)谈到新诗的形式,郑敏认为:“所谓自由诗不是没有形式美,而是允许诗人拥有最大的自由来创造自己诗作的形式美。”(《郑敏:金黄的稻束—答安琪问》)具体到新诗的分行问题,郑敏认为新诗如何分行并没有达成任何诗学共识,直言“新诗的分行问题对我是最大的困惑”(《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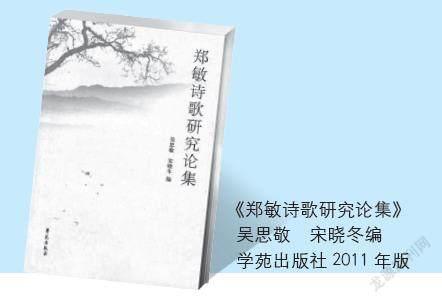
郑敏得出结论:“汉语新诗虽也近百岁,在诗的艺术形式,文本内涵的深邃上仍属幼年”,至今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自己的传统。她认为欧美诗学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二十一世纪中国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征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我与诗》)。郑敏的言论引起论争,争来论去,她的文章亦越写越多,有时难免重复,有时略嫌笼统,但她却似乎越战越勇。择善固执?从前对《世界文库》的痴爱呢?那一分钟的和谐呢?
浸满浓雾的话
在《给M. L.罗森萨[Rosenthal]的复信》一诗中郑敏这样描绘自己及自己的同类:“像被但丁送往深渊的人们/我们有时浮出浓雾/向诗人和朋友/说出浸满浓雾的话。”在诗人与学者之间,郑敏似乎更倾向于做诗人,她曾说:“其实我是一个很不正规的教师,并不喜欢做所谓的‘学问,但有不少对知识的好奇,对事物的好奇,我更重视的是东方的智慧。这也是我的诗的领域。”(《致牛汉》)在小传《闷葫芦之旅》中郑敏写道:“当年龄跨出了七十大关,我得到一种自由,就是不必再考虑填写各种表格给人带来的种种压抑感。”七十岁那年夏天,郑敏边读德里达的《书写与歧异》边吟就一诗:《对自己的悼词》,里面说:“那海啸,地震,都发生在平静的躯壳里。”写毕“悼词”,轻松上阵。《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等有影响的论文,《诗人与死》等受瞩目的诗歌都作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郑敏长年研究、教授英美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研读解构理论,获得了新的思维、新的史观以及与现实抗衡的精神资源。郑敏勤学苦思,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举目四望:“我们摧毁自己的画梁/换上西方的钢筋”(《诗的交响》),“肥胖的学童,头脑/背包都装满了汉堡”(《城市一景》)……现实总让她忧心忡忡。

郑敏(1920-2022)
郑敏晚年的纠结、困惑来自诗歌,更来自林林总总的当代文化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业主义泛滥,重实利轻美育,艺术与哲学总难接上地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主人公的文化贫血及自我膨胀,电影《红高粱》的艺术失调及情绪宣泄都令她不安。静夜里祈祷的少女已变成一位忧愤深广的知识分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拳拳切切,口燥唇干,“说出浸满浓雾的话”,发出坚硬的呻吟。诗神所赐葡萄美酒亦变成辛辣白酒,在浓雾中为她驱寒祛湿,尽管她未必喝得惯。
年届九旬,郑敏愈发迷戀汉字,赞美汉字“实是一种介于绘画、音乐与文字之间的文字,兼有画之形美、乐之声美与字之深意”(《新诗面对的问题》),像当初痴恋《世界文库》一样。二○二二年一月三日,一百零一岁的郑敏带着坚硬的寂寞离去,化成一棵沉思的树(墨西哥诗人广场公园种有一棵“郑敏之树”)。
二○二二年三月九日,格罗宁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