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戴维斯“贴近翻译”福楼拜
唐小兵

莉迪娅·戴维斯(Lydia Davis)
在《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的第五章,福楼拜用了一大段文字,来描写夏尔医生跟爱玛新婚后的快乐。这是夏尔的第二次婚姻。一年前的春天,他的第一任妻子,那位手脚冰凉的寡妇,可以说是知趣地死掉了;耐心地等了一年之后,夏尔终于再次完婚,把年轻的爱玛带回村里。新娘稍事歇息,便开始更换墙纸,刷新楼梯,布置花园,让生性木讷寡言的夏尔大有苦尽甘来、前半辈子都白活了的感觉。在这个甜蜜的新春里,每当夏尔早上出诊,爱玛都会披着晨衣来到窗前,目送丈夫骑马远行。这时,马背上的夏尔是多么踌躇满志、无忧无虑:
他的双肩洒满阳光,鼻孔吸着早晨的空气,心中充满夜晚的欢愉,精神平静,肉体满足,他咀嚼他的幸福,就像饭后消化中还在回味口蘑的滋味一样。(李健吾译)
太阳照在肩上,鼻孔吸着早晨的清新空气。心里充满了夜里的欢乐,精神安然、肌肤满足。他一边行路,一边回味自己的幸福,就像有的人饭后还在咀嚼他们正在消化的美味松露一样。(张放译)
正是上面这段文字的法文原文,提供了一个契机,让《包法利夫人》的英译者,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法国文学翻译家莉迪娅·戴维斯(Lydia Davis)来谈翻译的乐趣。
二○一○年,企鹅经典丛书出版了戴维斯翻译的《包法利夫人》,译者因此而再度获得法兰西-美利坚基金会的翻译奖。在这之前,戴维斯因为重译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第一卷《斯萬的道路》而声名鹊起。据译者所述,她的这本《包法利夫人》应该是这部法国名著自一八五六年出版之后的第二十个英译本(2010年之后至少又出了两个新译本)。该书最早的英译者,据说是福楼拜的英国恋人朱丽叶·赫伯特,在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七年间就开始动手翻译了,那时福楼拜还在因为这部小说被起诉而打官司。不幸的是,这个在福楼拜眼皮底下完成的翻译手稿后来下落不明。一直要到一八八六年,福楼拜离世六年之后,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英译全本才问世,译者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包法利夫人》最早的中译本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李劼人译《马丹波娃利》,备受推崇的是李健吾译本,此外,据笔者所知,还有许渊冲、周克希、罗国林和张放的译本。
戴维斯之所以对上面这段文字念念不忘,以至于在译书出版好几年之后还专门写文章来讨论,是因为最后一句里的一个动词。法文原文和她的英文翻译是这样的:
Il sen allait ruminant son bonheur, comme ceux qui m?chent encore, après d?ner, le go?t des truffes quils digèrent.
He would ride along ruminating on his happiness, like a man continuing to chew, after dinner, the taste of the truffles he is digesting.
这个动词是m?cher/m?chent,与其直接相对的英语是chew,中文是“咀嚼”。戴维斯翻译时的纠结在于:你怎么去咀嚼一种味道?这个说法,对她这样一位资深的作家来说,在英语里是不太通的,至少是不常见的。这句法文最贴近的中文翻译应当如下:
他这样边走边回味他的幸福,就像有些人,晚餐之后,仍在咀嚼他们正在消化着的松露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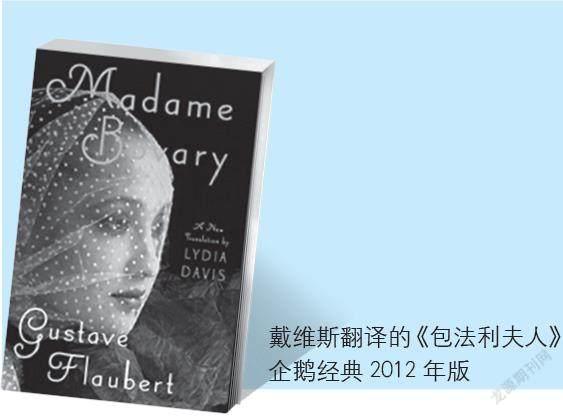
也就是说,夏尔此时是在“回味”幸福,“咀嚼”滋味。有趣的是,在中文里,“咀嚼幸福”和“回味滋味”似乎更常见,比如李健吾、许渊冲、罗国林的译本,就都是用的这两个搭配。上面引用的张放译文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夏尔“咀嚼”的也还是“美味松露”,而非“松露滋味”。周克希的译本对这一句的处理则略有不同:“他一路细细品味着自己的幸福,就像有些人饭后想起胃袋里的块菰还觉得其味无穷。”
福楼拜在这里用的“回味”和“咀嚼”两个动词都很有深意。法语和英语里的ruminer/ruminate来自同一个拉丁词根,其首要意义是“反刍”,比如说食草动物里的牛、羊等,都是反刍动物。而包法利(Bovary)这个名字,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过,其词根是拉丁语里的bov,即“牛”。在为周希克的译本所写的序里,施康强就指出,福楼拜给小说的女主人公起名为爱玛·包法利,可谓煞费苦心,已经暗示出“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换到中文语境里,这就简直等于是把一部小说的标题和女主角叫作“牛丽莎小姐”。
因此,此时沉浸在“回味幸福”和“咀嚼滋味”中的夏尔,虽然骑在马上,但其形象和神态其实还是憨头憨脑的牛。而这也是夏尔最后的快乐时光了,因为很快(两段之后),爱玛就觉得婚后的日子并没有给她带来满足,她想要知道:“幸福、热情、陶醉,这些在书本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字眼,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许渊冲译)也就是在这一章的结尾,小说的叙述视角从夏尔转向了爱玛,转向了她令人扼腕唏嘘的心灵和情感史。
尽管戴维斯在翻译时觉得一种滋味似乎有点不太容易去“咀嚼”,但她还是按照自己遵循的“贴近翻译”(close translation)的原则,把这个动词和宾语的搭配用到了她的译文里。所谓“贴近翻译”或“贴译”,就是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表达法、句式和意象,传达原文的形态和语气,同时尽量使用对等的词汇,达到相同的效果,译文相对于原文应该不增不减,不做额外的解释。用她的话说就是,一本小说翻译出来,页数应该跟原著大致相等。

显然,这个“贴译”,跟人们已经谈论了很久,且引发不少争论的“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很接近,但又并不是直译,而且也确实比“直译”听着舒服,有道理,因为怎么去“贴近”,就已经很有讲究,有很大的施展空间。戴维斯认为“贴译”比“直译”要胜出一筹,也有具体的例子,这个我们下面将看到。
与逐字逐句去比照对应的“直译”相对的,一般认为是“意译”,英语里通常将后者称为free translation,或者是更强调文字效果的literary translation。戴维斯认为“贴译”跟“意译”或者“活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但关于后者,她谈得很少,仿佛是个不言而喻,或者难以拿捏的事,不好谈,反正也不是她取的方法。在《包法利夫人》的翻译手记里,她指出之前的一些译本添油加醋得太厉害,比如原文里一个动词“思考”,被夸张译成“陷入犹豫不决的痛苦之中”等,很不以为然。
这篇很是散漫的手记写到最后,戴维斯总结说,她的目的是通过翻译来为原作创作出一个替身,而不是对原作做一个解释:“我要创作出来的是如此贴近原文,以至于一位研读福楼拜的人可以确切地,或者说尽可能确切地,看到福楼拜在原文里所做的事情。”正因为《包法利夫人》不仅仅是一部依然鲜活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被人反复讨论和研究的巨著,因此她希望自己的翻译能尽可能地像原著一样被人认真研读。
這个目标当然很崇高,但也有让人犯嘀咕的地方:那何不干脆去读原文呢?或者,是不是可以说翻译想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其实就是成为原著本身,让原著成为翻译的替代?换个角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每一个新的译本都力争接近原文,那么时间上离福楼拜越远的译本,反而会离原文更近?
这里确实涉及翻译的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译文感”的分寸,比如翻译对“译入语言”的生态所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译出语言”所依仗的文化资源及其在新的语境里所具有的不同层次的联想和意义,不同译本之间的关系,不断推出新译本的必要性,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在现代中国的翻译史和文化史上,有过很多的讨论,也有很丰富的思想积累。比如鲁迅就很鲜明地提出,直译,甚至“硬译”,就是“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而这种翻译策略,归根结底,“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正是通过大量的翻译,日语、德语、俄语等语言对现代汉语的词汇、句式、语法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大规模的、迫切的翻译,往往是为了输入新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的变迁和革新。
但在戴维斯那里,并没有这种通过翻译来改造本土文化的迫切感或使命感;翻译给她带来的,首先是写作的乐趣。作为一位作家,她把翻译视为创作,是在一个既定的空间里进行的精雕细琢、反复打磨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体验,有怡情养性的味道。虽然也有抓耳挠腮的时候,但比起面对白纸一张,去无中生有地写出一篇小说,还是要轻松、好玩得多。当然,她也说过,在应邀翻译普鲁斯特之前,她基本上是靠接翻译的活来谋生,资助自己的小说创作;几十年里所译的文字包括良莠不齐的小说、人物传记、艺术画册,甚至还有跟中国历史有关的书籍,而最初开始译的,也是她译普鲁斯特之前译过的最有名的法国作家,是莫里斯·布朗肖,前后一共译了他六本小说和哲学著作。

现在回头看,二十世纪下半叶里,对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翻译工作,当推各类法语著作的译介,从萨特、拉康、福柯、德里达到德勒兹,虽然没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但知识界对跟上“法国理论”确实一直有紧迫感,至少是时髦感,搞到后来,连政客都会脱口说出“解构”,以为就是“破坏”的意思,只不过文雅一些。戴维斯应邀译布朗肖,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精英崇尚现代法国思想界的一个具体表现。
关于“贴近翻译”,戴维斯并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理论,只是在译完普鲁斯特动手译福楼拜之前,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或者说追求做的一个比较感性的总结。
一九九五年,英国的企鹅现代经典丛书邀请戴维斯加入了一个由七位翻译家组成的团队,准备根据一九八八年法国出版的《追寻逝去的时光》修订本推出一个新的英译本。七年之后,也就是二○○二年,企鹅新译本正式面世,共六卷,戴维斯翻译的是第一卷,题为《在斯万家那边》;一年之后,维京出版社在美国出了个修订版,她把标题改回了之前的译本比较通用的《斯万的道路》。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普鲁斯特这部巨著在英语世界里就一直以《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而为人所知。这个英文标题来自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是该书最早的英译者,苏格兰作家和翻译家斯哥特·蒙克利夫(这是个双姓,有时也写作斯哥特-蒙克利夫)选定的,算是对法语标题的意译或活译。一九二二年九月,斯哥特·蒙克利夫翻译的《斯万的道路》出版,那时候普鲁斯特还在世,一身的病痛,勉强读完译本,十月份便写信致谢译者,同时也对英译本语言的花哨和一些误读提出了异议。译者很谦恭地做了回复,但十一月十八日普鲁斯特便离世,终年五十一岁。
斯哥特·蒙克利夫本人也于一九三○年初病故,还不到四十岁。此时他已译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前六卷,未译完的最后一卷由英国作家和译者悉尼·席夫完成。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斯哥特·蒙克利夫的译本,或者说重写,是英语读者欣赏普鲁斯特这部巨著全貌的唯一途径。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两位译者分别根据新修订的法文版对这个译本进行过修订;二○一三年起,耶鲁大学出版社甚至陆续推出了斯哥特·蒙克利夫译本的注释版,但改名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一九八二年,澳大利亚人詹姆斯·格理夫出版了他翻译的《斯万的道路》,这也是斯哥特·蒙克利夫之后,这一卷的第一个重译本;格理夫后来加入了企鹅现代经典丛书一九九五年组织的七人团队,翻译了全书的第二卷。在戴维斯翻译完普鲁斯特后写的随笔里,她介绍了斯哥特·蒙克利夫和格理夫的译本,尤其对前者,有相当详细的点评。
顺便介绍一下,中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七卷,有十五位译者参与,由译林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首次推出,后来在二○一二年出版了修订本(企鹅的2002年版把中文版中的第五卷《女囚》和第六卷《女逃亡者》合为一卷)。其中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由李恒基、徐继曾合译。此外,译林出版社还于二○○五年出版了徐和瑾翻译的《在斯万家这边》,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二○一○年出版了周克希翻译的《去斯万家那边》,全书的标题也改为《追寻逝去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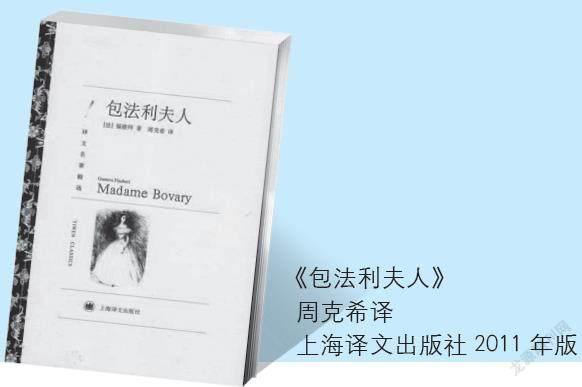
戴维斯在谈如何贴近翻译普鲁斯特的随笔中,总结出十来条规则,详加说明,指出译文不仅应该力求复制出原文的韵律和音响节奏,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要贴着译。她这个“贴译”,可以说是对斯哥特·蒙克利夫式的活译的一次全面修理或者反动。同时,她提供的例子也说明,法文和英文,相对于法文和中文,哪怕是法文和德文,其实是多么地接近,不仅有很多词汇都同样来自拉丁语,而且不少句法和表达法都可以直接对换。因此,戴维斯总结出的“贴译”方法,还真不是随处可用的翻译指南,但也不意味着法译英就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关于后面这一点,她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斯万的道路》第一部里,年幼的叙述者家里的帮厨女工因为产子,卧床不起,于是用人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做一些平常会让女工去做的粗活。这天叙述者去到厨房,目睹平日很善良的弗朗索瓦丝在奋力杀鸡,失态地大骂“畜生!畜生!”这血腥的场面让“我浑身发抖,扭头上楼,恨不得马上叫人把弗朗索瓦丝赶出家门”(李恒基译)。但转念一想:“Mais qui me?t fait des boules aussi chaudes, du café aussi parfumé, et même... ces poulets?”戴维斯最初的“贴译”是这样的:“但谁又会来给我做如此热乎乎的面包,如此喷香的咖啡,还有……这些鸡?”(她还提供了一个更“直译”的版本,即保留原文的词序:“面包如此热乎,咖啡如此喷香。”)她对斯哥特·蒙克利夫把在这一句里只出现了一次的动词“faire”(做)变作三个并列的词组(烤面包,煮咖啡,焙鸡肉)是既欣赏又觉得不妥,并借此指出:
我坚持认为应该尽量贴近原文作者所做的选择,而不是对其做过度的解释或者“改进”,原因就在于,我们作为译者,不应该自认为懂得了作者想做的一切;只有当我们尽量把他的文本以他所呈现的方式呈现出来时,英语读者才有机会在没有我们搅合的状态下来进行阅读和解释。
但上面这句法文原文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那就是“boules”这个词既可以是“圆面包”,也可以是“热水瓶”,而这两个可能在这里都说得通,都是能给叙述者带来安慰的东西。斯哥特·蒙克利夫说是“圆面包”,而格理夫说是“热水瓶”。一番周折之后,包括去法式面包店做调研,咨询上了年纪的法国人,再加上一位研究生的质疑,戴维斯最终决定应该是“热水瓶”,因为,如果家里需要面包,弗朗索瓦丝会直接去面包店买。(三个中文译本里,李恒基将此处译作“谁给我做热乎乎的卷子”,徐和瑾和周克希则分别是谁来“给我做”和“给我吃”圆面包。)
但戴维斯的“贴译”也有贴得不好,遭人质疑的地方。二○一○年十一月,她译的《包法利夫人》刚出版,《伦敦书评》便刊登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一篇颇为犀利的长篇评论,指出这个译本的可取之处在于力求福楼拜文字的精确,句式也接近原文,但不成功的地方,是读起来跟英语有点隔,与其说是让我们体验福楼拜的文体,不如说是体验戴维斯所体验到的福楼拜。巴恩斯举了好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来自第二部的第九章,也就是爱玛和罗道夫骑马去到山顶看永镇全景,然后在树林里偷欢的那一刻。
这是爱玛第一次偷情,却远非情场老手罗道夫的第一次。寂静的夕阳里,委身于人的爱玛眼睛发花,闻着树丛温馨的气息,感到自己心跳加速,血液在体内流涌,一声模糊而悠长的叫喊从另一个山峦传来,“她静靜地听着,那声音有如一曲音乐,与她的心弦震颤的余音融合在一起”(罗国林译)。这样一段引人遐思的文字,却有一个冰冷的结尾:“罗道夫嘴上叼着雪茄,在用他的小刀修理一根断了的缰绳。”(张放译)
巴恩斯在评论文章里引用了四个大同小异的英译,其中只有戴维斯,把原文里最后的过去分词变成了一个从句(他在修理“缰绳之一,断了的那根”),也只有戴维斯,在巴恩斯看来,没有捕捉到罗道夫若无其事的神态,这个从句也无异于画蛇添足:难道他会去修一根好好的缰绳吗?因此巴恩斯直言,这句译文显得笨拙,并不贴切,也很不福楼拜。
巴恩斯没有提到的是,他列举的四个英译,都有不贴近原文的地方:一个说两根缰绳都断了,一个说只有一根缰绳,另外两个(包括戴维斯)则没有明确一共有几根缰绳,只是其中的一根断了。可这句原文里的每个细节都是如此重要,喻意又是如此丰富,真有点细思极恐的味道:两个人刚刚做完爱,断了或者说破裂了的是谁,是什么?谁将从此失去控制?小刀又如何能修理好断绳?(遗憾的是,五个中译本都没有点出断了的是两条缰绳中的一根。)
确实,无论是从语意还是句式来看,戴维斯这句译文都没有达到她自己定下的“贴译”标准,无法替代原文,也不能像原著一样让人去研读。而一旦意识到译文与原著之间的隔,我们只能更加赞叹福楼拜语言的精练和耐读。
在她译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几年之后,有一次戴维斯跟几位朋友去法国东部一小镇品酒,兴头上听到酒庄的导游要大家“M?chez le vin”(请嚼一嚼酒!或者:好好咂这酒!),立刻让她想起福楼拜,想起夏尔那天早上的惬意,想到自己翻译那段文字的经验,尽管还是觉得无法去咀嚼松露或红酒的滋味。品酒归来,她写了一篇随笔,列出翻译带来的十一种乐趣,第一句便是:“那些让你绞尽脑汁,却似乎总也没有满意解决的翻译难题,会一直缠绕着你—这一点是肯定的。”等到这篇随笔出现在她二○二一年出版的、厚达五百五十多页的《随笔集卷二》时,所谈的翻译乐趣已经有二十一种之多,还加上了乌云密布时让人看到希望的一线光明。
戴维斯从翻译中体会到的,有解答一道难题后的乐趣,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阅读别人译文的乐趣,从文本内部细细欣赏原作的乐趣,为了翻译而做研究的乐趣,精神漫游的乐趣,反观自身文化、加深对母语认识的乐趣,乃至跟伴侣或朋友们分享翻译中的困扰的乐趣。其中谈到的第三个乐趣,应该是很多做过翻译的人都有的经验,那就是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做翻译,不管你是精力充沛还是疲倦不堪,就连坐在公交车上,你都可以去思考怎么翻译一个字句。有时候,正是翻译,可以让心烦意乱的你平静下来,走进一个似乎有根有据,但其实可以是无边无际的文字世界。说到底,翻译是咀嚼文字的乐趣。
二○二二年三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