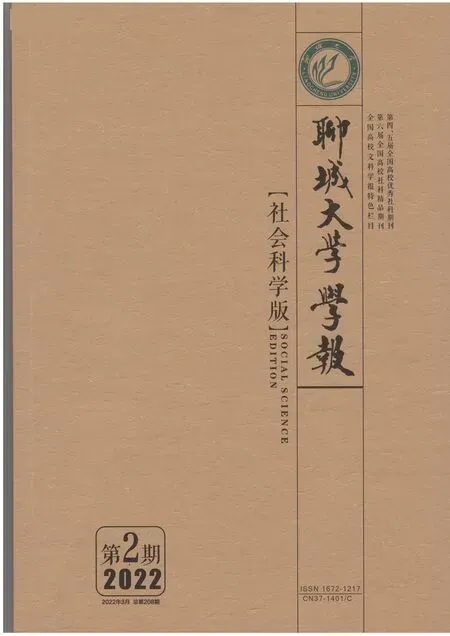正史所见汉唐间的“富民”、“富人”
陈 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富民”、“富人”的概念或名称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富民”,最初只有“使民富”的含义,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富民思想,如《荀子》曰:“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①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3页。;又如《韩非子》云:“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②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八《八说》,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28页。。“富人”,原本是指“富有之人”,如《荀子》中言及,“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③《荀子集解》卷三《仲尼篇》,第107页。;又如《韩非子》所载:“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④《韩非子集解》卷四《说难》,第93页。。
其后,“富民”、“富人”的含义逐渐趋同。“富人”一词也具有“使民富”的含义,如《汉书》中提到,“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⑤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50页。。若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汉代,“富民”一词已有“富有之人”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富民”、“富人”同义。当时人已有此认识,已将二词并用,如《汉书》记载:“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⑥《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42页。。
随着“富民”、“富人”两个概念的同义化,尤其是特指“富有之人”时,其实已经昭示出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富民”阶层或群体的出现。本文拟对正史中所见汉唐间“富民”、“富人”的出现频次及其时代特征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正史所见“富民”、“富人”的数据统计
“富民”“富人”与“富室”“富户”“富家”“豪民”“大姓”等词往往为同义语,且在正史中出现频次较高,尤其是在宋代以后的史籍中已大量出现。因本文讨论的时段重点在宋代以前,故分别统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等20部正史中“富民”“富人”的含义及出现频次,来分析其所反映的社会变化。
(一)正史中“富民”一词的统计情况
《史记》中“富民”一词共出现7次,其中意指“使民富”4次,见于卷70/112(2)①卷数后()中的数字,表示该词在同卷正文中出现的频次,下同。/120;指西汉封国3次,见于卷20/22(2)。
《汉书》中“富民”一词共出现12次,其中意指“使民富”2次,见于卷50/84;意指“富有之人”4次,见于卷11/48/64下/91;指西汉封国6次,见于卷17/18/24上/66/73/96下。
《后汉书》中“富民”一词仅出现1次,意指西汉封国,见于卷90。
《三国志》中“富民”一词共出现2次,皆意指“使民富”,见于卷15/28。
《宋书》中“富民”一词共出现3次,其中意指“使民富”1次,见于卷66;意指“富有之人”1次,见于卷100;指称村名1次,见于卷28。
《南齐书》中“富民”一词仅出现1次,意指“使民富”,见于卷40。
《梁书》中“富民”一词仅出现1次,意指“富有之人”,见于卷10。
《魏书》中“富民”一词共出现2次,其中意指“使民富”1次,见于卷7上;意指“富有之人”1次,见于卷97。
《周书》中“富民”一词共出现2次,皆意指“使民富”,见于卷6/23。
《隋书》中“富民”一词仅出现1次,指渠名,见于卷61。
《旧唐书》中“富民”一词仅出现1次,指西汉封国,见于卷89。
《新唐书》中“富民”一词共出现2次,其中意指“使民富”1次,见于卷149;意指“富有之人”1次,见于卷210。
《旧五代史》中“富民”一词共出现2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42/108。
《宋史》中“富民”一词共出现62次,其中意指“使民富”2次,见于卷265/406;意指“富有之人”57次,见于卷14/15/22/26/32/35/66/153/173/176(3)/178(2)/181(2)/198/247(2)/255/266/270(2)/277/278/285/288/298/300/301(2)/303/314/318/331/336/337/338(2)/339/34 1/347/354/373/384/402/408/409(2)/411/413/436/463/469/470/471/475;指铸钱监名3次,见于卷88/180(2)。
通过对正史中“富民”一词的统计,可以明显看出:
1.由汉代到宋代,“富民”一词意指“使民富”,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富民思想的延续。
2.在《汉书》中,“富民”一词总共出现12次,其中指西汉封国有6次,占总频次的50%;意指“使民富”出现2次,占总频次的16.67%;而意指“富有之人”出现频次较高,共有4次,占总频次的33.33%,已超过“使民富”的用法,这一现象的确值得思考。
3.在《宋史》中,“富民”一词总共出现62次,其中指铸钱监名有3次,占总频次的4.84%;意指“使民富”出现2次,占总频次的3.22%;而意指“富有之人”出现频次极高,达57次,占总频次的91.94%,远远超过“使民富”的用法,这一现象非常引人关注。
(二)正史中“富人”一词的统计情况
《史记》中“富人”一词共出现18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30(3)/41/56(2)/63/71/89(2)/101(2)/104/117(2)/123(2)/129。
《汉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33次,其中意指“使民富”1次,见于卷65;意指“富有之人”32次,见于卷7/24上/24下(3)/28下(2)/32(2)/40(2)/48/49(3)/57上(2)/58/64上/70/72/76/89/90(2)/91(2)/92(3)/96 上 /96 下。
《后汉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3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32/34/82下。
《晋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4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38/43/60/96。
《宋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4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66/71/83/84。
《南齐书》中“富人”一词仅出现1次,指“富有之人”,见于卷44。
《梁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2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50/53。
《陈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3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14/21/26。
《魏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4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19上/33/97/114。
《北齐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2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11/47。
《周书》中“富人”一词仅出现1次,指“富有之人”,见于卷37。
《隋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8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24(4)/25/29/70(2)。
《南史》中“富人”一词共出现16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5/15/25/27(2)/30/49/55(2)/62/65/70(2)/74(2)/77。
《北史》中“富人”一词共出现9次,其中意指“使民富”2次,见于卷3/63;意指“富有之人”6次,见于卷17/34/41(2)/52/70;避讳,指渠名1次,见于卷74。
《旧唐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11次,其中意指“使民富”1次,见于卷169;意指“富有之人”8次,见于卷5/55/100/118/154/184/197/199下;避讳,指西汉封国2次,见于卷119/123。
《新唐书》中“富人”一词共出现19次,其中意指“使民富”1次,见于卷179;意指“富有之人”16次,见于卷2/55/86/111/120/131/145/149/162/164/171/180/207(2)/219/224下;避讳,指西汉封国1次,见于卷142;指塘名1次,见于卷146。
《旧五代史》中“富人”一词仅出现1次,指“富有之人”,见于卷58。
《新五代史》中“富人”一词共出现7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43/46/47/51/64/68/69。
《宋史》中“富人”一词共出现54次,皆指“富有之人”,见于卷12/176/178/179(2)/184(2)/1 86/201/247/254/268/274/276/286/289/291/298(2)/299(3)/301(2)/302/303/304/305/316/319(2)/328/333/334/355/384/395/407/414/426/427/432(2)/433/436/437/438(3)/450/451/456/459/464。
通过对正史中“富人”一词的统计,我们有以下思考:
1.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等19部正史中,“富人”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富有之人”。
2.在《史记》《汉书》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分别出现18次和32次,合计共有50次之多(含重复记载)。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确发人深省。
3.在《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分别出现3、4、4、1、2、3、4、2、1次,合计共有24次;而在《南史》《北史》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分别出现14次和6次,合计共有20次。这两个统计结果远远少于《汉书》中的统计数据,原因为何?需要进一步分析。
4.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分别出现8、8、16、1、7次,合计共有40次(含重复记载)。这一统计结果与之前相比再次增多,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
5.在《宋史》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出现高达54次。这一数据背后昭示着何种变化,也值得探讨。
二、正史所见“富民”、“富人”的综合分析
我们仅对“富民”、“富人”两个概念同指“富有之人”的含义加以汇总(表1),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显著差异。

表1 正史中“富有之人”含义综合统计表(含重复记载)
以上正史中的统计数据已然反映出不同时代“富民”、“富人”的阶段特点,总体而言,最主要的当是与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密不可分。具体来说,又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春秋战国至秦、西汉时期,“富民”、“富人”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结构面貌和社会群体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基本特点是新、旧交替,上、下易位”。“如果说春秋以前的历史时期社会群体还不怎么明显的话,那么,从春秋时期开始,社会群体则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并且表现出日益巨大的社会影响。”①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31、689页。“富民”、“富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大抵‘家赀千金’的富商大贾从春秋中期开始出现,至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更加迅速膨胀,‘家累千万’的富商大贾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②冷鹏飞:《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学术研究》1999年第10期。。史籍中将“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与“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③《韩非子集解》卷六《解老》,第136页。并列,足以表明这一新兴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也正是《史记》、《汉书》中“富民”、“富人”概念同指“富有之人”含义的总频次颇高的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至秦、西汉时期,“富民”或“富人”阶层大体上具有这样四个显著特征:
其一,是拥有雄厚的财富力量,这是首要的和最本质的特征。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批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富民”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如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猗顿“用盬盐起”,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埓富”;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等,司马迁将他们称之为“章章尤异者”。④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7、3259、3279、3281页。
又据《汉书》记载:富人常“积钱满室”⑤《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5页。,如“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⑥《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田延年》,第3665页。;而“临邛多富人”,仅卓王孙家就有“僮客八百人”⑦《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第2530页。。
其二,是无官位,即没有政治特权。
当时的“富民”阶层都是非有爵邑俸禄而富的,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即“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唐人张守杰《史记正义》中解释为“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2页,第3281-3282页。。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则明确指出:“乡曲豪富无官位”②《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第1420页。。可见,至少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将没有政治特权作为“富民”阶层的一大特征了。
其三,是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这一阶段,“富民”群体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那些“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更是“不可胜数”③《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2页,第3281-3282页。。而秦朝建立后,曾一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足见该群体的规模之大。
其四,是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富民”阶层没有政治特权,但是因其群体规模较大、财富力量雄厚,故而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富民”阶层往往“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⑤《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2页。,能够“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⑥《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第3024页。,甚至还“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⑦《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第1420页。。
据《汉书》记载:“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⑧《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36页。这里将“豪富民”与“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并列,显然表明在西汉前期“富民”阶层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一群体不仅可以“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⑨《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71页。,而且成为游侠的金主,游侠所需“费用皆卬富人长者”⑩《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原涉》,第3716页。。
(二)第二阶段: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富民”或“富人”阶层的分化、重组与南北差异
据表1可知,《后汉书》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仅仅出现3次;《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民”、“富人”两词,合计出现24次;《南史》、《北史》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人”一词分别出现16次和6次,共计22次。
从上述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富民”、“富人”的出现频次较西汉时期大大减少。其原因在于“富民”阶层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且受到东汉以降商品经济衰落、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富民”阶层出现分化,呈现出新的变化:
其一,“富民”阶层的分化。
一方面,有的“富民”或“富人”的财富力量丧失,自身的社会地位改变,更有甚者丢掉性命。典型事例如东汉时,梁冀及其族人对当时富民的巧取豪夺。据《后汉书》记载,梁冀为人贪婪,“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而梁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11]范晔:《后汉书》卷三四《梁统附玄孙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81页。。又如陈朝时,宗室陈方泰“在郡不修民事,秩满之际,屡放部曲为劫,又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①姚思廉:《陈书》卷一四《南康愍王昙朗附子方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12页。。
另一方面,有的“富民”或“富人”在确保财富力量的基础上获得官位,取得政治特权。如东汉时,豪富子弟王龚“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帝嘉之,征拜尚书”②《后汉书》卷五六《王龚传》,第1819-1820页。。又如北朝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③李延寿:《北史》卷四一《杨敷附赵元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1页。。
其二,“富民”阶层的重组。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富民”、“富人”同义的“大姓”在正史中出现的频次颇高。如东汉初年,“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冯)异代禹讨之”④《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第645页。。东晋初,“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按:指南兖州),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⑤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页。。魏晋南北朝以降,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⑥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90页。,如西晋时,“强弩将军庞宗”为“西州大姓”⑦房玄龄等:《晋书》卷六〇《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9页。;又如南朝杜稜,“吴郡钱塘人”,“世为县大姓”⑧《陈书》卷一二《杜稜传》,第191页。。
“大姓”一词的频繁出现,反映着东汉以来的社会变化,即随着“富民”阶层的分化,这一群体又与其他社会群体结合形成新的“豪族”或“豪民”,进而促成了“豪民社会”⑨关于汉代豪民的研究,可参看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汉代豪民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形成。因此,真正具备第一阶段特征的“富民”的数量急剧减少。
其三,“富民”阶层的南北差异。
《南史》中“富人”一词的出现频次两倍于《北史》,这与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当时南朝商品经济发展逐渐繁荣,北朝商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史载:“晋自过江……历宋齐梁陈……人竞商贩,不为田业”⑩《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689页。,“(梁时)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11]李延寿:《南史》卷七〇《循吏传·郭祖深》,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0页。。与此不同的是,北朝则“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12]魏收:《魏书》卷六八《甄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0页。。
正因如此,在南北朝时期就真正具备第一阶段特征的“富民”阶层而言,与北朝相比,南朝的“富民”群体规模开始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具体事例如史书记载,刘宋永嘉二十七年(451),“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富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后因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13]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9页。者,再次出钱助军;齐梁之际,邓元起患资粮不足,涪令李膺“率富民上军资米,俄得三万斛”[14]姚思廉:《梁书》卷一〇《邓元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9页。。
(三)第三阶段:隋唐五代时期,“富民”或“富人”阶层逐渐崛起
据表1可知,《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民”、“富人”两词,合计共有43次(含重复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富民”、“富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开始逐渐崛起,并仍然具有前述四个共性特征:
其一,是拥有雄厚的财富力量,这还是首要的和最本质的特征。
如唐高宗时,长安富民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①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九五《杂录三·邹凤炽》引《西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62页。。又如唐玄宗时,彭州导江县富民冯大亮,“其家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虽王孙、糜竺之家,不能及也”②《太平广记》卷三五《神仙三五·冯大亮》引《仙传拾遗》,第226页。。再如唐僖宗时,江陵富民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③《太平广记》卷四九九《杂录七·郭使君》引《南楚新闻》,第4097页。。
其二,是“富民”群体虽然无官位,即没有政治特权,但是某些个体出现入仕现象。
如唐玄宗时,富民康谦“资产亿万计”④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六下《酷吏传下·敬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861页。,“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九《酷吏传·敬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19页。。又如唐肃宗时,严震“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已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⑥《旧唐书》卷一一七《严震传》,第3404-3405页。。
其三,是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隋代时,“富民”群体就已经颇具规模。在隋炀帝营建洛阳的过程中,曾“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⑦《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3页。。唐代中期以后,“富民”群体的规模更是越来越大。
其四,是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一时期,“富民”阶层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影响,如隋代黔安郡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⑧《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30页。。正面影响,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咸亨二年二月丁亥,“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赈济贫人”⑨《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95页。。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乙丑诏曰:“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⑩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28页。。从诏书中将“王公百官”与“富豪之家”并列,可知当时“富民”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已非同一般。
自唐代中期以降,随着“富民”群体的规模日渐庞大,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唐文宗时,出现“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傜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11]《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第1361页。的严重情况。至后唐长兴二年(931)九月,朝廷下诏,“天下州县官,不得与部内富民于公厅同坐”[12]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四二《唐书一八·明宗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82页。,其实是中央政府试图从国家制度层面限制各级政府官员与富民私自交通,而这又恰恰反映出“富民”阶层在当时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至于需要中央政府直接进行干预。
(四)第四阶段:宋代,“富民”阶层地位凸显
据表1可知,《宋史》中作为“富有之人”使用的“富民”、“富人”两词,出现高达111次。倘若翻检宋代史籍,关于“富民”的记载更是举不胜举,“富民”成了当时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和名词。[13]林文勋:《唐宋“富民”阶层概论》,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2页。北宋时期,业已出现“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14]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三集》卷八《杂说·诗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页。的情形。可见,“富民”阶层在宋代绝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具体事例如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三月,朝廷下诏,“京西民饥,宜令所在劝富人纳粟以振之”①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仁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6页。;又如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宋金战争中“命州县谕富民捐赀助国”②《宋史》卷三二《高宗纪九》,第604页。;再如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发廩贷给,趣州县决狱,募富民振济补官”③《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第674页。。
宋代以后,“富民”、“富人”的出现频次激增,昭示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④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有关宋代“富民”阶层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故本文不予赘述。
三、结语
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任何概念或名称的出现,背后都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富民”、“富人”的概念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存在,“富民”原来只有“使民富”的含义,“富人”本意是指“富有之人”。其后,两词的含义逐渐趋同,“富人”也有“使民富”的含义,“富民”也可意指“富有之人”。至少在汉代,随着“富民”、“富人”两个概念的同义化,尤其是特指“富有之人”时,已然昭示出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富民”、“富人”阶层或群体的出现。
以正史为例,纵观“富民”阶层或群体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春秋战国至秦、西汉时期,“富民”、“富人”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富民”或“富人”阶层出现了分化、重组与南北差异;隋唐五代时期,“富民”或“富人”阶层逐渐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