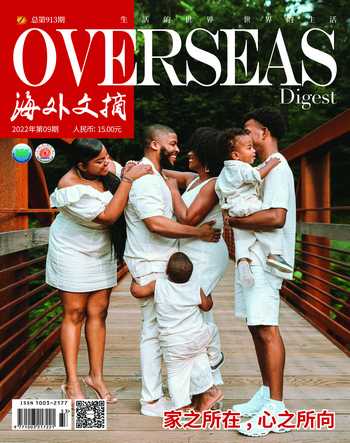好妈妈是什么样子?
劳拉·贝兹伦

我卧室壁橱的一个抽屉里,装着我出生后妈妈收到的贺卡。小时候,我很爱翻出来看。我最喜欢的那张卡片上画着一对母子,母亲用洁白柔软的胳膊将孩子环绕胸前。那个母亲有着美丽的侧影——小巧的鼻子、长长的睫毛,眼中只有那个熟睡的小婴儿。她微卷的金色秀發垂下,将孩子环绕起来。在她的世界,孩子就是一切。
我妈妈却和她大不相同。我妈妈的头发颜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剪成了短发,发型几十年来都没变过。她的皮肤是浅棕色的,胳膊上的肌肉天生就很强健。她的怀抱短暂而生硬,她眼中只有下一项工作任务。虽然我从未怀疑过妈妈对我的爱以及我对她的重要性,但我几乎从未体会过卡片上的小孩所感受到的那种母爱光辉——全心全意、无微不至的母亲关怀。这在我们家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要养育四个孩子,我妈妈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她是个精神科医生。
那么,那张卡片何以让我如此耿耿于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40年后,我仍能清晰地记起卡片上的图案,还有随之而来的感受:一种对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的怀念和渴望,因为我确信它存在于别的小朋友家里。
| 完美母亲神话 |
我就认识这样一位母亲,至少从小到大我一直这么认为。格雷琴是我童年时期最好朋友塔玛拉的母亲。在小时候的我看来,格雷琴和我妈妈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格雷琴似乎永远在家,不是在做点心,就是在缝制漂亮的洋娃娃裙子;她也不是医生,不过她丈夫是。
她简直完美得不可思议,没有哪个妈妈能比得上她。塔玛拉的万圣节服装堪称艺术品,令所有人赞叹不已。有一年万圣节,我想扮成一只老虎,就像我整天抱着的那个毛绒玩具一样。我跟妈妈说这件事时,我们正站在妹妹的房间里,房间正在改造,要把妹妹的婴儿床换成普通床。妈妈指了指地上堆着的一卷黄白条纹的墙纸,建议我说:“不如就用那个把你包起来?”
格雷琴是否就是我所认为的母亲典范——那张贺卡上永远无微不至地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母亲形象?八年级开始前,塔玛拉就搬家了,我们从此断了联系。几年前,我在谷歌上搜索她妈妈的名字,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格雷琴竟然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国际教育名誉教授,名下有十部著作,还是享誉全球的教育改革专家。
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复制粘贴了她的邮箱地址,开始给她写邮件。“敬爱的格雷琴,”我写道,“请原谅我的冒昧,请问我可以对您进行一次采访吗?”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还记得我。她回信的语气打消了我的疑虑,证明她确实对我还有印象。回信中,她让我把想聊的话题发给她。在给她的回复中,我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我对您印象深刻,”我写道,“但不确定这些记忆是否真实。”

在我和塔玛拉一起玩的那段时间,她的妈妈格雷琴一直在读教育学专业的博士。
结果是,我的记忆既真实又虚幻。在我和塔玛拉一起玩的那段时间,格雷琴一直在读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她出生于一个学术世家,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母亲是经济学学士,但全职在家。“我的动手能力就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她在视频采访中告诉我,“她总是在织毛衣、做果酱、腌咸菜或烤饼干。但我觉得,她对这种生活充满失望。”
1968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后不久,格雷琴就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米尔特,他当时还是个医学生。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格雷琴那时24岁。她在1971年生下了大女儿达拉,1974年,塔玛拉也出生了。
“我当时觉得我是个很称职的全职妈妈。”她说,“我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但那还不够,我需要为自己做点什么。”1977年,在达拉六岁,塔玛拉三岁时,她重返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后,格雷琴决定去一所大学全职任教。当得知马萨诸塞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有一个终身教授的空缺时,她说:“我太激动了,感觉这个职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但是,当时米尔特作为医学教授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不愿搬家。尽管如此,格雷琴还是拿下了这份工作。在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她每周穿梭于两个城市间,努力兼顾两头,但最终还是不堪重负。“一切都很平静。”她说,“我们去办了离婚,把所有东西平分了。”读完七年级后,塔玛拉搬到马萨诸塞州艾摩斯特市和格雷琴一起生活,达拉则跟着米尔特留在费城。
我现在才明白,格雷琴和我母亲的共同点远比我想象的多得多。她们都在矛盾中挣扎,在传统面前一边妥协一边反抗。然而,格雷琴朝着职业理想迈出的步伐——即她所谓的“事业抱负”——使她更偏向于一个叛逆者。为了实现职业理想,她不惜放弃婚姻、家庭和一个女儿。
尽管人们都说,我们这一代女性不必再像格雷琴那样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作艰难抉择,但是,听格雷琴讲述她的故事时,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 事业家庭二选一?|
我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和法学教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曾面临一些会使我们暂时分离的职业机会——到离家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代理案件,去另一个州作学术报告——我都去了。我的工作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和方向,但与此同时,我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只能压缩。我一次次缺席家庭晚餐、生日派对,当然,还有万圣节。我的事业心也成了我和丈夫马特的矛盾点,我们的争吵往往是由于他埋怨我对工作过分投入,而我则不满他对我的事业不够支持。
最终,事实证明,我对工作的热忱无法与我的婚姻共存。和格雷琴一样,我经济上足够独立,使我能够离开家,开启新生活。然而,这并不能减轻家庭破裂带给我的伤痛。我开始感觉到,尽管已是21世纪20年代,追求职业理想与尽好母亲责任仍然只能二选一,这与上世纪70年代并无不同。那张贺卡上的母亲形象及其背后的东西也仍然牵动着我。
我的母亲角色扮演得断断续续、马马虎虎,我孩子的朋友也绝不会将我错认成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这曾经一度成为我愧疚的源泉。不过渐渐地,我有了不同看法。尽管我在家务方面很不合格,但我知道我的儿女能感受到我的爱,正如我能感受到我事业心颇强的母亲的爱一样。意识到这一点,我开始反思,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将事业追求和成为一个好妈妈对立起来?实际上,以事业为重心的妈妈们,能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教给他们优秀的品质。
研究表明,与全职妈妈的孩子相比,职场妈妈的孩子表现得并不逊色。2018年一项涵盖29国10万人的研究发现,母亲在外工作的女孩,她们自己的事业也会更成功,幸福度并未减少。对于男孩来说,母亲是否在外工作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并无显著影响。不过,母亲在外工作的男孩在婚后倾向于承担更多家务,并更提倡性别平等。
我儿子在懂事后曾这样对我说:“做父母就是不断地将砝码从天平的一端滑到另一端,天平的一边是家庭,另一边是工作,它能保持平衡的时间极少。”如果能达到完美平衡,那当然最好不过,但偶尔的失衡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它能让孩子们认识到照顾家庭的重担和牺牲不应只由母亲一人承担,也让他们明白,为何母亲不能永远只围着他们转。
我的孩子们也曾因我过于投入工作而怨过我。2020年3月,他们俩一个11岁,一个9岁。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三人一起在家度过了前几个月,但这并未给我们带来什么明显好处。有一次,我正和一个法官和一群律师开视频会议,女儿这时打开我身后的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暴露在众人面前,大声责备我忘记给她买枫糖浆,这实在有损我的职业形象,让我非常怀念办公室的清静。
不过,孩子们偶尔出现在我身后,越过我的肩膀偷偷看我工作这种事,也帶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他们开始明白我每天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同时,我的客户和同事也得以一窥我在法庭和课堂以外的生活,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随叫随到。
在我母亲那一代,男女平等的主要关注点是同工同酬,消除导致女性离开工作岗位或只能找到低薪兼职的不公现象,最终实现家庭分工平等。在这一事业远未完成的今天,男女平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些结构性变革,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好妈妈的标准。
实际上,母爱既如贺卡上描绘得那般美好,又可能一团糟,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除非有工作的母亲不再设法照顾到所有事、所有人,或除非她能同时扮演完美的工作者、完美的妻子和完美的妈妈,并保证每个角色完全不会彼此影响。女性应该接受不同角色的相互渗透,而不是把母亲角色摆在事业奋斗和成功的对立面,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儿女。
我深知自己为人母的经历无法代表大多数女性,但过去几年,我同许多不同肤色、阶层的女性交谈过,发现在事业和家庭间达到完美平衡的愿望是许多人所期盼的。
| 现代超级妈妈 |
达芙妮·杰克逊是一名空军中校及军法署署长。2013年她的大儿子降生时,她所在的律师团队负责为被指控炸毁美国“库勒”号驱逐舰的关塔那摩监狱囚犯辩护。军方拒绝了达芙妮带儿子一起前往古巴的请求,但她还是接下了这件案子,并随身带着吸奶器。“我不得不在拘留所、飞机上甚至是会见客户的间隙吸奶。”她告诉我。
如今,达芙妮有三个孩子,作为一名母亲,她不仅体贴周到,而且效率极高。我们第一次视频通话时,她正在给女儿换尿布。她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换完尿布,跟丈夫和两个儿子亲吻告别,然后开着她的面包车前往附近的麦克斯韦–甘特空军基地。
在军队的职业发展意味着达芙妮仍然不时需要离开家人很长一段时间,比如最近,她被派往卡塔尔八个月,在此期间,她需要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通过视频向孩子们道晚安。要抓住这样的事业机会绝非易事,但她每次都欣然接受,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他们一生都会记得我每天起床穿上军装的样子。”她对我说,“这让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妈妈有多伟大,因为他们见证了我对国家的忠诚与牺牲。”
我还曾与一位名叫黛安娜的女性交谈,她15岁那年从越南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在一所大型公立高中上学。她学英语的方式就是每天背着一本巨沉的词典,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查,并完整地看了《老友记》全集。
高中毕业后,黛安娜就和男友结婚了,开始在一家发廊做美发师。“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她告诉我,“有时要同时接待两三个客人,即使有客人在关店前15分钟才来,我的老板也会说:‘接下这单。所以我常常很晚才回家。”她的时薪很低,但小费不少,每天大约能挣130美金。

以事业为重心的妈妈们,能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教给他们优秀的品质。
多年来,她一直在努力兼顾工作和家庭,但当两个孩子分别到了10岁和12岁时,这种状态就再难维持了。老板让她每周两天做接待员,还要负责店铺开关门。额外的任务延长了她的工作时间,然而接待的客人却越来越少。“每天我到家时都筋疲力尽,如行尸走肉一般。”她说。
2018年,一个机会降临到她头上。黛安娜的一位客人在附近也有一家发廊,以前租那里的美发师最近退休了,房子就空了出来。黛安娜怕被同事听到,弯下腰在那位女客人耳边轻声问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那天晚上,黛安娜下班回家后,激动之情久久难以平复。“我明白我的机会来了,也知道我的客人会跟随我。”然而,她丈夫却只看到了风险。她说:“他不停地问我,万一失败了呢?我告诉他我很自信能成功。”他的回应是让黛安娜和现在的老板好好谈谈,调整一下工作时间,但被黛安娜拒绝了。多年来,她一直在为家庭妥协,这次,她决心坚定自己的立场。“几天后,”她说,“他终于想通了,说:‘好吧,如果这样做能让你开心,那就去做吧。”
在离开原先工作的前几周,黛安娜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她的客人们,尽管她没有主动提,但许多客人都向她要了联系方式。在新店铺开张后不久,她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每次有老顾客打电话预约,我的孩子们都特别激动,这让我很开心。”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的嘴角一直上扬着。她的孩子们不仅见证了她的事业成就,而且满怀崇敬。
当然,像黛安娜这样的成功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可能转瞬即逝。新冠疫情影响了数千万美国人的工作,包括很多女性。疫情暴发后的前几个月,由于零售业、服务业等女性主导产业的就业岗位大量削减,350万母亲离开了工作岗位,其中就包括黛安娜,她也被迫关店。她丈夫的兼职收入不够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全靠黛安娜之前的存款,他们才得以勉强度日。不过后来,她的店铺又重新开张了,今年2月我碰到她时,她告诉我她比以前更忙了。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