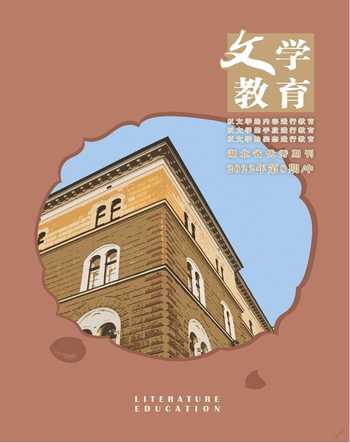主流意识下解读《红豆》的情感追求
卢青楠

内容摘要:在“十七年”文学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宗璞的《红豆》迥异于五十年代的文学公式化,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这篇小说讲述了知识分子江玫放弃爱情选择革命道路的历程,表面上迎合当下主流政治话语,但从文本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个体意识和情感追求。小说突破文学服从政治的时代禁锢,刻画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真实自然的美好情感。本文将结合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文本,分析《红豆》的真实主题是人物主体的情感追求。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宗璞 《红豆》 情感追求
解放前,知识分子江玫面临人生艰难抉择时理性战胜了感性,但人性中真实美好的情感在时代洪流中脱颖而出。“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那两粒小小的红豆,是江玫情感记忆里缠绵的伤口,也是她放不下的相思哀愁。
一.主流意识时代下情感追求的萌芽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当代文学的方向为延安文学代表的方向,主张坚持文学“一体化”和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革命事业,这大大限制了文学艺术发展的自由和创新。迫于时代洪流,作家将个人意识和主体情感溶解于浩浩荡荡的时代主流意识与宏大历史题材中,歌颂党和社会主义、追忆战争岁月和与资本主义等恶势力作斗争的题材成为文学创作的潮流,千篇一律的英雄人物形象和公式化的情节模板跃于纸上。1956年,国家试图调整文学路线,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激发了当时作家心中压抑已久的个体意识,动摇了僵化的文学束缚,也给当时的文学界带来崭新的朝气。
宗璞的《红豆》诞生于百花时代,讲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与资产阶级出身的齐虹的爱情,以及与无产阶级工作者萧素的友情。在经历一番斗争后,江玫放弃了爱情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在宗璞细腻而唯美的笔触下,这篇小说打动读者的却不是作者原本设想的江玫选择革命道路艰辛曲折的思想斗争,而是江玫与齐虹立于不同阶级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悲剧爱情,小说中自由追求真实情感的绚烂夺去了主流革命主题的光辉。所以,即便这篇小说主题符合一体化的主流政治意识,但隐匿在作者创作轨迹的情感流露依旧不被当时时代所认同。
《红豆》引来的批评集中认为宗璞没有表现出知识分子怎样经历着曲折痛苦的道路走向革命事业,没有表现出知识分子彻底的改造思想情感。[1]当时有不少保守学者表示,《红豆》文本中的情感叙事线过于喧宾夺主,小说中人物的政治思想觉悟仍不够高。
宗璞在谈及创作《红豆》时承认,“当初确实是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而且她所经历的不只是思想的变化,还有尖锐的感情上的斗争,是有意要描写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以自拔的境地中拔出来,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2]宗璞在初始创作时的理性必然选择了服从符合集体利益的主流意识,但随着故事情节蔓延发展,作者感性上不由自主地加重文本中的个人情感表达,无意中流露出作者潜在的个人意识与情感,最后便呈现出披着主流意识革命外衣却流露追求个体意识和人性情感内核的《红豆》。这种理性服从主流而感性追求情感表达的分裂矛盾表现了文学一体化规范强烈束缚的挣脱尝试,同时也展现了《红豆》在十七年文学中对文学主体情感追求的探索。
二.浪漫的爱恋情节
《红豆》的主要情节围绕着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展开,也正是这细腻而浪漫的爱情情节构成了小说情感追求的主体部分。在浪漫的雪日里,如太阳般明媚的少女江玫初遇了文艺青年齐虹,仅是这惊鸿一瞥,江玫先猜想对方没有看到自己萌生遗憾的念想,脑海里又不时浮现齐虹的面容,这一处的心理活动生动描绘出江玫少女初恋的情态。而在后文齐虹对江玫说道:“我看见了你,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这前后文一呼一应,描绘出一场一见钟情的动人桥段。江玫与齐虹从第一次散步开始,走过了春夏秋冬里的风花雪月,畅谈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享受着这世俗里平凡情侣间的甜蜜爱恋。这一段爱情描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让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读者在戎马倥偬之余领略到爱的柔美与缠绵。据说在当年,一些大学生还专程到颐和园去寻找江玫和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可见宗璞的爱情描写的确有着感人的力量。[3]
但江玫和齐虹所处不同的阶级立场,注定着他们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不会一致。”小说从江玫与齐虹热恋期就对他们后来的争吵做铺垫。齐虹不满江玫跟随萧素去游行,两人的争执不断恶化,江玫对齐虹的态度由惊讶和气愤渐渐转为辛酸与痛苦,情感色彩一笔笔有层次地加重。最后齐虹前往美国,江玫选择分手留在中国,两人痛苦地结束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宗璞将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写得细致入微,也将自己的情感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江玫在恋爱中的喜愁交加,沉溺爱情时流连于幻想和现实中,在分手时对齐虹的依恋和痛苦地决绝,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一个恋爱女性复杂丰富的情感内心世界。而对于齐虹,他对江玫早已种下情种,而他疯狂的占有欲体现了他自私的爱情,甚至在情到疯狂时说出“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的言论,但最后他还是尊重江玫,选择独自远去。因为立场的不同,他们之间的爱情尖锐而激烈,但却又因为细腻的描写和真情的流露让他们的爱情更加缠绵动人。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在那个以颂歌为主“文学独白”的年代出现,的确是引人注目的。[4]浪漫而清秀的少年,活泼明媚的少女,这也许是大多数人们心中初恋的蓝本。他们的情感像是种子历经春夏的萌芽开花后又走到了结果和凋零,一切描写自然却又激烈,但也正是这样真实细腻的情感才能如润物细无声般沁入读者的心房,引起大众的共鸣。
三.苍白的革命引导
而作为《红豆》真正的革命主题,江玫与萧素的友情革命情节相较于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情节则要显得简单许多。于江玫而言,萧素像是夜里海上的一座灯塔,一步步引导江玫走向革命道路,她对革命事业倾注的热血和激昂触动到了江玫,这也是江玫最后选择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小说情节中,作者并没有注入过多的笔墨打造这条主题线,萧素作为一个革命引领者,先是與江玫一起看《方生未死之间》,带给江玫奋斗的力量,随后,萧素又带着江玫一起参加朗诵节目,使江玫渐渐融入集体生活,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在紧要关头,萧素卖血救江玫的母亲,使两人结下生死不渝的友情。最后萧素被捕,江玫只觉得天旋地转,她在悲愤中明白“逮走一个萧素,会让更多人都成长为萧素”,于是江玫也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萧素对江玫的影响是成功的,但萧素在引导江玫的方式却显得过于苍白。小说里革命叙事的情节大多都是萧素引领江玫参与革命活动,江玫思想上逐步受到启发和鼓舞,萧素的思想输出和江玫的思想输入都是单向且绝对的。这样的情节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相当常见的,是借用了主流文学情节公式化的模板。对比细腻浪漫的爱情情节,萧素的革命引领就会更显得单一和模式化,很难给予人思想上的震撼以及心灵上的洗礼。从某种程度上看,萧素引导江玫走上革命道路像是断裂的情节拼接穿插在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叙事线里,革命叙事的情节发展远不如爱情情节的连贯和细腻。
在萧素引导江玫选择革命的情节的逻辑上也略显苍白和生硬。江玫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萧素卖血的友情选择了革命道路,但这是外界事件刺激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江玫内心深有感悟后主动追求革命的结局,这样的革命引导的情节逻辑较于自主追求真实情感的爱情情节也是不够自然和严谨。江玫的心理活动描写也倾向于简单化和符号化,且多为类似于口号的“激动”“力量”“鼓舞”“崇敬”“愤慨”之类的抽象情感[4],因而她对萧素的情感更多是理性的选择,所以读者也多是从理性而非感性地体验感知,无形中疏远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较难触动读者的内心感受。
四.迫于现实的选择
《红豆》这篇小说最亮眼和富有张力的矛盾冲突便是江玫对于革命和爱情的选择。于江玫而言,齐虹是她在雪日里遇见“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一见钟情的少年,也是她深爱着的初恋。但江玫也预感到自己与齐虹生活及价值观存在分歧,而在当时文学创作的背景下,是不会容许选择个人情感放弃革命这样的小说结局出现的,在小说故事背景中,战争时代和阶级对立也注定了江玫与齐虹分离的结局。所以为了使江玫知识分子的身份成功转向无产阶级工作者,作者塑造了萧素这一革命者形象,不断引导江玫。但作者也深知光有萧素的引领还不足以江玫发生真正改造,所以加上了萧素卖血和父亲冤死的情节。在亲情和友情外在力量双重夹击下,江玫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放弃了她刻骨的爱情。
“我不后悔”与江玫内心真实情感是相背离的。为了表现小说最后的立场和结局,小说在两处提到了江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第一处是齐虹与江玫分离的时候,江玫对齐虹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不后悔”,但那时的江玫是“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对比江玫所说的话语和实际的内心反应,让读者很难确信她是真的不后悔,更像是江玫为了欺骗自己和齐虹而被迫说出来的谎言。江玫知道自己心理上深沉依恋着齐虹,但理性和现实告诉她必须要放弃爱情,她害怕自己真实情感的流露让她失去理智,更害怕齐虹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想法重新燃起他们这段不可能的爱情。所以江玫选择欺骗自己和齐虹,但却没有瞒过大众读者们雪亮的双眼。
第二处是从第三人称视角中写道“江玫果然没有后悔”,这是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叙述的声音。从情节来看,多年后江玫成为了革命者,母亲也为她骄傲,她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可是当她回顾六年前这段爱情时,只觉得“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还有“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起来,泪水遮住了眼睛”,这一段细致的描写其实是赤裸裸地展现了江玫不止没有放下这段爱情,甚至这段爱情已经是深深扎根在江玫内心,如那两粒红豆般历经岁月沧桑而没有失去颜色,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使人无法忘却。
从小说里现实的故事情节来说,江玫最后选择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工作者,是革命战胜爱情,但从人物的内心情感来看,江玫珍藏着那代表他们爱情的红豆并流下泪水,处处表现她对爱情的难舍和放不下,是爱情和人性战胜了革命。在小说的结局中,读者们只看到了一个追忆爱情而流泪的女子,并没有看到一个成熟的党的工作者,江玫重新收拾自己的笑意掩盖自己的难过,也正像《红豆》这篇小说用革命主题掩饰了人物主体的情感追求。
五.真实的情感追求
在文学高度一体化的时代,《红豆》这篇小说被指出它呈现出感性重于理性、个人情感重于革命政治的客观效果。《红豆》创作的时代里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主流意识影响下,江玫必须要选择革命,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齐虹会被丑化贴上自私的标签,而作为革命引导人象征的萧素则被赋予光辉完美的形象。但哪怕小说被设置了这么多条条框框的规则,读者依旧被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所打动,江玫经历痛苦的思想纠缠后选择了革命,可她的内心从来没有舍弃过她的爱情,这是《红豆》中尊重人性真实情感的体现。如果按照文学服务政治的时代标准,江玫选择革命后对过往爱情心无波澜或者只是一笑而过,那这篇小说就缺少了一些人情味,也许也无法獲得现在的成就。这些在当时文化语境里不被接受的思想、感情恰好就是自然真实的情感的流露,是人类的自由精神和生命本能的表现,表达的也正是人类生活最真实的感受。[1]
宗璞的创作轨迹在潜意识中最终也是偏向了对人物主体的情感追求。宗璞的理性创作设想也只是描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却也没有料到自己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情感追求造成的客观效果。在当时,批评者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批判江玫选择革命道路后不应该对爱情仍存有留恋,却从没有走进文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宗璞从尊重人性和情感的角度下,给予江玫与齐虹鲜活立体的塑造,也使他们的爱情深刻缠绵中具有真实性和感染力。正像宗璞自己所说的:“有时这种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5]而这种情感流露也是作家创作时的自然反应,也是作者在投入真情实感创作中的文本自然反馈,所以《红豆》中江玫与齐虹深刻而凄婉的爱情能打动广大读者,而正是因为作者宗璞在创作中潜意识下在文本中倾注情感追求。
《红豆》这篇小说历经多年依旧能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便是因为其中真实的情感追求。在十七年文学中,主流意识的约束冲淡当时的文学作品的情感流露,按照时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则和标准进行创作的文学往往难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6]。而无论古今内外,人们对美好情感的向往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从情感追求为创作出发的文学才更容易驻留在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也正是如此,《红豆》中江玫与齐虹真实而缠绵的爱情是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引起大众共鸣的。《红豆》中的情感追求突破了当时主流意识文学规范的束缚,开启十七年文学中文学创作新的探索,也开始尝试回归文学抒情的功能作用。
在十七年文学主流意识规范下,宗璞借助“百花时代”的契机进行文学情感追求上的探索而创作了《红豆》。《红豆》由爱情叙事和革命叙事两条故事线交织而成,但小说主要细腻地描绘了江玫与齐虹浪漫缠绵的爱情悲剧,极重笔墨地渲刻画了小说人物的情感追求,与此同时反衬萧素引导江玫的革命情节略显苍白和生硬。小说的结局从现实上看,江玫选择了革命道路,但从内心看,情感追求和人性却战胜了革命。所以,《红豆》在本质上是一篇披着革命外衣表达情感追求的爱情小说,它突破时代的文学规范尊重人性情感,成为十七年文学中情感追求探索的一抹重要色彩。
参考文献
[1]黄娟.从《红豆》看百花文学中的爱情选择[J].青年文学家,2019(30):32-33.
[2]王力可.显在的皈依与潜在的反抗——谈宗璞《红豆》的创作[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9(12):242+247.
[3]于立辉.政治裂隙下凋零的爱情之花——论宗璞《红豆》主体情感诉求与文本表征之间的裂隙[J].语文学刊,2008(21):42-43.
[4]胡晓.爱情的梦境或革命的伪装?——试析宗璞《红豆》的潜在叙事结构与思想内涵[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03):1-3+6.
[5]《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J].1958(9).
[6]齐思原.红豆的隐喻与文艺工作者的异化——略谈宗璞《红豆》[J].名作欣赏,2015(02):102-103.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