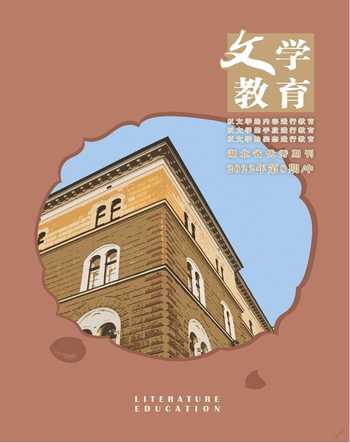北村《水土不服》中小知识分子的存在危机
周君萍
内容摘要:《水土不服》作为北村转型期写作的典型文本,是北村重建小知识分子自我的尝试。他偏执地重复书写信仰的救赎意义,使其文本呈现出固态化、宣教化的姿态,看似确定的文本意义,实际上潜藏着深刻的存在危机。
关键词:北村 《水土不服》 小知识分子 耻感 信仰
1992年-1993年,北村的转型期的小说以“神性写作”成为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水土不服》作为其转型期写作的典型文本,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广泛注意。评论多就“罪”这一概念作为北村小说的焦点,探讨其小说中“神性书写”模式给当代文坛带来的冲击与神圣价值,而对于北村“神性书写”模式化的弊病,部分批评家虽然指出了,却没有深究这种现象之所以呈现出一种“模式化”的内因。本文就北村的神性写作为何呈现“重复化”、“偏执化”这一问题,探讨深藏在其文本之下的存在危机。
一.何以为“罪”
“犯罪-信仰-救赎”的神化路径在《水土不服》中主要体现在女性人物张敏身上。作为康生与现实相接的桥梁,张敏实际承担着康生的理想寄托和现实需求两重责任。她曾是学校里的“交际花”,因与康生相爱而成为一个矛盾重重的、“被审判”的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现实生存,她陷入了欺瞒和背叛的自我谴责当中,正是因为张敏的“堕落”,让康生跌入了现实的失乐园,他先是试图参与现实建构,去苏林的公司上班,却因无法融入现实秩序而愤然离去,退回自封之地。文本以张敏的堕落牵引出所有人的“罪”,苏林的世故爱财、小芳的淫秽不堪……北村展示出的一幕幕“现实快照”,最终都指向了“信则新生,不信则死”的宗教信条。但颇令人疑惑的是,“罪”真的能够包罗现实堕落万象吗?作为文本中自认有罪的“审判者”康生,却为何无法在“犯罪-信仰-救赎”的模式里获得救赎?
二.“耻”的倒置
在笔者看来,以“罪”的名义来定性上述的“堕落”现象并不准确。我们在《水土不服》里或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
“有时借来一辆车,还要我载他……康生说,他们在笑我们吗?我们走路吧。我说走路多慢哪。他说慢点怕啥,没什么重要的事。”
“轮到新郎送新娘礼物时,大家至少以为康生会送给我一对戒指什么的,料不到他掏出一块饼来,……我堆着笑脸应酬,康生一直观察我,直到婚礼结束。①”
笔者注意到,文本中不断出现他人的注视这一关键行为。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范畴之内,与他人无关、指向个人自我与神之间的称之为“罪”,且罪并非因为世事变化或民风沦丧所致。因此,我们与其将《水土不服》中的世相人心视作为“罪”的工笔画,不如将其划归到另一个审视范畴之中——耻的维度。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将羞耻感描述为自我存在确认的情感现象,是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作为行为主体的“我”产生了自我意识并开始将“自我”作为审视和反思的对象时产生的②。如果我们将康生的耻感判断作为一个正向的参考物,那么在康生注视下的张敏、苏林一干人等的耻感判断就是倒置乱序的。在这种因金钱浪潮冲击而倒置的耻感维度之中,追逐金钱、无视感情成为正向目标,纯粹干净的情感成为一种让人难堪的存在而被竭力嘲讽忽视,人的自我遭受着“金钱”浪潮的话语暴力。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向金钱的时候,作为在这一秩序以外的他者——康生——所带来的正向的“耻”的目光就被无视了,在文本之中,康生坚持的生活在小芳等人看来是可笑的,甚至被他们所鄙夷的,令康生崩溃的一段性关系在小芳看来不过是“肉跟肉碰了一下”。北村本是安排康生作为神一样的“他者”来带给这群已经同质化的人启示,然而“他者”却因无法融入而退居到自我的内心空间,康生的“声音”——对他们“无耻”(耻的倒置)的指责——并不能唤起他们对“耻”的觉醒,恰恰相反,他们却认为康生是可耻笑的,滑稽的,将其纳入了同质化的现实逻辑之中,使他者失却了否定性的力量,从而消解、甚至吞噬了他者。
三.以何存在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水土不服》中总是有勇气让人难堪的康生,作为一个理想的神性人物,他沉迷诗歌、音乐和爱情,是文本中一个截然不同的、刺眼的存在,他几乎是用审判的目光来审视所有失却耻感维度的人。然而,不同于北村小说“犯罪-信仰-被救赎”的典型模式,康生却从对爱情与生活的虚幻信仰中猛然醒来,最后却无法得救。这一特殊轨迹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为何康生“信”了却依然无法得救?
回到90年代的历史现场,作为小知识分子的他者——意识形态赋予小知识分子责任和精神内蕴,而当他者(意识形态)将重心转移以后,小知识分子就失却了他的能指。脱离了西方和五四的啟蒙镜像的小知识分子,正是再建自我绝好的机会。如何重建?北村在其小说中给出的答案是信仰神、依靠神,通过向神忏悔自己的罪而达到救赎,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诸如康生、玛卓等人,都是北村答案的“文本案例”。
北村首先要在文本中解构的,是关于爱情、诗歌和音乐的乌托邦。《水土不服》中的康生是一个只知道诗歌和爱情的“神”一般的人物,他纯净单纯,不谙世事,与众人格格不入,在他原先的个人的琉璃世界里,他始终与除爱人张敏以外的世人保持距离,维持了其内心的平衡。然而现实以不可抗拒的冲击力迅速打碎了乌托邦,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张敏不得不偷偷背着康生靠美貌做兼职赚钱,在得知此事以后的康生,首次为了家庭踏入陌生的现实世界,却终究因为无法与商人同流合污而退回个人的精神世界。此后,张敏一边以康生作为精神彼岸,一边又为其内在的世俗欲望所驱使,这样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张敏堕落了,康生也随之破碎。在张敏向康生坦白了自己和苏林的事情以后,她等待着康生的审判,然而作为他者的康生,却烧掉了爱情诗,要求张敏埋葬他,爱情作为康生的信仰倒塌了,而康生作为他者的强大力量也就此萎靡了。就这个维度上来说,康生其自身也是虚无的,他靠爱情建构起自我,然而这爱情并不能由他一方的坚守所维持,他的自我也掌握在他人(张敏)的手上,这是康生作为北村所安排的他者的自身的薄弱。北村意在指出,爱情等需要靠与他人建立关系来维持的乌托邦并不能给人带来精神救赎,只有通过信仰神,也就是作者借康生之口所说的“看来人非靠信不能活着”,才能得救。
然而,其真正的症结真在“信”吗?在我看来,神性人物即使信仰了神,也失去了重构自我、成为他者的力量。
按北村的救赎之道来说,小知识分子希冀地通过完全退向个人而达到的自我重建,实际上就是一个悖论的存在:个人自我需要爱情,而爱情需要他者的参与,所以他认为,这样的救赎必然幻灭。他否认了人作为他者的可靠性,认为“人皆有罪”,转而寻求神的庇护。但新的矛盾就在于,这种与“神”建立关联而完全与现实割裂的选择依旧是一条完全推向自我的、封闭的道路,依旧是一条无法建立起现实他者形象的道路。如果都信了神,还要小知识分子做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康生真正失败的原因是:他只在自己的维度里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没有接受来自诸如张敏等人的他者的目光,这就犹如当今世界的各种“圈”,康生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同者,而放弃了对他者的追寻与质询。康生由于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退缩到了自己营造的一个伪诗意的世界,他对他者的无视使他在受到现实世界的冲击时毫无还击之力,由此可见,他所选择的隔绝并不能帮助他建构自我,只有直面对立才能确认自我的存在。
北村将一切矛盾错误都归咎于“罪”的做法,在康生的身上得到了强烈的印证,他将自己受小芳引诱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的原因全都总结为自己犯的罪,他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因为他发现自己竟与他人并无区别,长久以来的隔绝居然是虚幻!他只能无助地哭喊:
“谁能伸手拯救我,掩面不看我的污秽,把我洗得像雪一样白?使我可以活下去!③”
北村在这段极具宗教意味的话里暗示得很明显,只有神才能够拯救犯了罪的康生,所以信“爱情”的康生注定毁灭。但问题在于,这个罪名只是康生一个人需要承担的吗?康生找到神了吗?
在文本中,康生最终一个人承担了这份罪,陷在“无边的罪里”的康生最终决定自杀,在自杀之前,他曾向每个与他的“罪”里有关的人道歉。荒谬但真实的是,所有被道歉的人却都在笑他,康生在跳楼的时候反复质问自己“我真的洁净了吗?”的这一行为,是他向自己、也是向神的反复确认。然而他前两次的自杀失败了,坐在屋子里少有言语的康生喃喃道:
“我过去有一个想法,我是为诗活着的,就是为美活着的,也为爱活着。……看来人非靠信不能活着,但你背叛了我,我除了死,只能堕落。④”
也就是说,康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过去想法的不可实现,转向了新的信仰——神,但他却依旧绝望、执著寻死,为什么?
我们从康生的自我陈述里可以听到,“我能死在鲜花里,我就不害怕,我真的不害怕,但我要死在唾沫里,泡沫里?塑料泡沫?”由此来看,康生的死绝非能由一个“罪”字来概括,这里面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耻”的意味——康生的“罪”由于小芳的“四处宣扬”已经转换成了“耻”——成为一种社会的、集体的目光注视下的情感体验,而光靠个人内心的忏悔是无法逃离耻的目光的。因此,与世界的紧张关系才是康生的真正症结所在。
然而北村并未给康生一个与世界和解的方式,康生不是成长型人物,他始终沉湎在自我的罪之中,断绝了与外界的沟通。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作为他者的小知识分子退出对公共空间秩序的参与時,他就已经失却了自己的羞耻感知能力了呢?
北村给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失败的,他试图重建一个宗教他者来维持内心平衡,然而现实问题必须在现实中得到解决。小知识分子一味地从现实生活撤退到内心、仅仅依靠信仰是不能够在当今的社会中建立起自我的,因为基于信仰建立起的自我最终会因为信仰的破灭而破碎,这不过是从对启蒙的信仰转移到另一个信仰上去,其本质还是自我的虚空。人作为一种群居生物,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信什么,而在于如何在群体之中确认自我。要建构自我,便需要重拾“耻感”,建构起与集体的关系。北村将“神”引入,作为他者来帮助小知识分子建构自我,然而“神”是在现实世界以外的。小知识分子不应沉湎在自己的“罪”中,来渴求“神”的回应。而应将回应他人的目光,将自我纳入集体。北村在文本中书写神性人物,企图由此告知世人接受信仰的力量,“这是一个人否认自己之后又拒绝神圣启示的荒谬境遇,……对于人自身最坚决、深刻、彻底的批判与否定,只能来自于信仰⑤”,然而他的人物不是悲剧收场,就是一旦到了要解决矛盾的时候,便只能依靠虔诚地信仰“神”,因此失去了他的现实力量,也减弱了他的批判的精神力量。
信仰的力量在现实面前如此薄弱,这是北村的矛盾,也是他重复书写的症候所在:北村试图在一次又一次找到信仰在现实中的力量,甚至从不质询。他以神性批判堕落的众人,然而他忘了神性人物早已失去诗意栖居的自由,现实世界的他者带来的是“耻感”的注视,神性人物必须融入集体才能够真正地建构自我并且拯救他人。正如韩炳哲所说的:“愤怒的浪潮缺乏集体认同性,因此,它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社会性忧虑结构的‘我们。⑥”
信徒是北村在转型期作出的身份选择,然而作家的身份与信徒的身份并不统一在他自身,他越来越显示出对文学身份的偏离。对于文学和自己的关系,北村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当我信主后,对文学之于我从一个神圣的追求突然下降为混饭吃的营生感到无比震惊,但我实在无法重新确立对它的信心。⑦”这样,到了后期,北村的文学叙述便渐趋模式化,文学成为他的布道场,犯错——忏悔/不忏悔——被救赎/堕落成为他小说的固定模式,“信”成为他思考的起点和无需怀疑的终点,他的精神探索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正如北村对文学现状的诊断:
“人放弃了神给他定的边界,作家也一样。苍白的文学,里面似乎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心灵的质量,这就是它不会让人感动的原因。我把它称为无耻的文学⑧”。
然而,神能赋予文学“罪感”,“耻感”却需要人与社会赋予。真正的出路在于:小知识分子如何能够于群体之中独立地思考,重新建构社会的公共耻感。更为重要的是,在无神论作为基本语境的前提下,北村竟从未怀疑过神是否存在,在对本体存在问题的搁置这个层面上来说,仪式性地重复叙说是否能证明:他的信仰只是一种“姿态”,“信”是否只是他躲避现实——无法对无耻进行审判——的路径呢?
参考文献
[1]北村著.周渔的喊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04.
[2](法)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11.
[3](德)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著;罗悌伦等译.价值的颠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04.
[4]荆亚平.神性写作:意义及其困境[J].文艺研究,2005(10):156-158.
[5]谢有顺.不信的世代与属魂人的境遇——论北村小说的人学立场[J].作家,1996(01):66-73.
[6]于京一.从“存在”到“解构”的艰难跋涉———试论北村小说的悲剧性品格[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05):99-101.
[7]马佳,刘贤汉.趋奔神圣和信仰的动姿基督宗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20-24+26.
[8]涂险峰.神圣的姿态与虚无的内核——关于张承志、北村、史铁生、圣·伊曼纽和堂吉诃德[J].文学评论,2004(01):117-124.
注 释
①③④本文中的特殊字体文字部分均为原文,引自北村著.周渔的喊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04.
②汤波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论舍勒与萨特对“羞感何以发生”的还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20,47(05):19-27.
⑤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04).
⑥韩炳哲著,程巍译.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中信出版社,2019.03:12.
⑦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7).
⑧贺雄飞主编.边缘思想《天涯》随笔精品,南海出版公司,1999.10:420.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评章越松著《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