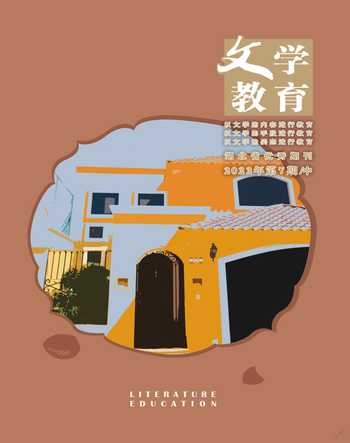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鼠疫》与《白雪乌鸦》灾难书写之异同
赵淑琴
内容摘要:加缪的《鼠疫》与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都将鼠疫作为描写对象。同为瘟疫灾难小说,两部作品中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灾难侵袭后的芸芸众生,无论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躲避,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共通性。但由于两部作品在叙述的情感基调与对灾难的思考方面上存在着差异,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灾难书写。
关键词:加缪 《鼠疫》 迟子建 《白雪乌鸦》 灾难书写 法国文学
灾难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反映,是人性的透视。它虽然伴随着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但其根本目的不是记录和夸大灾害,而是借助灾害宣传和传达生命的尊严和人文精神。加缪的《鼠疫》与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都以“鼠疫”为创作背景。《鼠疫》描述了一場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奥兰城的一场大灾难,刻画了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抗疫者直面惨淡人生、在绝望中怀揣希望,并最终战胜鼠疫的传奇故事。而《白雪乌鸦》以百年前哈尔滨鼠疫的史实为基础,描绘了傅家甸区的老百姓在灾难中的人生百态。二者在人性书写上体现了一定的共通性,无论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躲避,表达了两位作者对积极处世的人生态度以及努力追求生命意义的赞扬。但二者在叙述的情感基调与对灾难的思考方面上存在着差异,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灾难书写。
一.灾难侵袭后的人生百态
《鼠疫》可以说是一部众生反抗荒谬的作品。故事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4月的某个早晨,一些死老鼠的出现,导致鼠疫在人群中悄悄流行起来。但奥兰城政府的错误决断让鼠疫疫情迅速蔓延,随着越来越多的死鼠的出现以及第一个感染人员的死亡,大量市民开始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局面,毫无防范的人们意识到一场真正意义的瘟疫已经到来。这是一场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艰难的战争。政府突如其来的封城措施让市民们处于被迫分离的状态,出行受到限制,交通全面阻断,许多亲戚、朋友和恋人在几天前便约好了见面,而今天,却散发着永别的意味。因为信件可能携带细菌,人们只能通过电报与外界交流。经过长时间的隔离,思念的话语渐渐变得空洞乏味。那些恐慌、空虚感在市民中蔓延、扩散,人们在精神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类似于长期流亡的痛苦,“流放的感觉正是我们经常感到的空虚,是一种确切的激情。”①
当鼠疫逐步显示出令人畏惧的真实面貌后,以里厄医生和塔鲁为代表的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进行斗争,才能将死亡人数降到最小。他们的举措与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立卫生防疫组织,筹划防疫保健工作,并召集大量的居民作为志愿者,在他们的科学带领下,并最终战胜了鼠疫。尽管他们与志愿者都非常清楚在这场抗战中蕴藏着巨大危险,但他们从未退缩、惧怕。作者用冷静客观的叙说,成功塑造了特殊情境下的普通人的矛盾心态和对立冲突,让读者深切地感悟到志愿者们崇高的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真实、可信、可敬。
在《白雪乌鸦》中,傅家甸的老百姓们也遭受了由鼠疫引发的灭顶之灾。随着巴音、吴芬、张小前等人的相继死去,彻底拉开了鼠疫的序幕。突如其来的瘟疫也彰显出了生命的脆弱,这种脆弱感让人们感到格外无助和恐惧,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变得萧条落寞,路上的行人三三两两、各式店铺紧闭大门。然而当鼠疫大范围袭来,死亡人数突增的境遇下,人们却拥有了比平时更强的凝聚力。他们不在惧怕死亡,开始吃肉喝酒,出游交谈,并淡然的准备着自己的寿衣和棺材。在这座瘟疫弥漫的孤城中,车夫、掌柜、算命的,这些平凡甚至卑微的生命开始直面死亡,与瘟疫作斗争。
然而,积极反抗和消极躲避的人是共存的,在灾难面前,人性的恶与善也将全都暴露无遗。突然降临的鼠疫使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疾病的恐惧、物资短缺引发的恐慌,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负面社会心理,无论是在奥兰城还是在傅家甸。《鼠疫》中的柯塔尔,一位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喜欢鼠疫,是因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警察无暇顾及刑事犯,能够让他投机倒把,大赚一笔,最后鼠疫得到控制,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乱世环境,他也因此绝望自杀。而《白雪乌鸦》中,以恶为典型的人物主要是纪永和以及太监翟役生。作为一名商人,纪永和在小说中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性格可谓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听信算命先生的谗言,花高价钱将妓女翟芳桂“娶”回了家,然而这不是爱情,他只是将她作为赚钱的工具而已;灾难爆发之际,想着靠囤大豆发灾难财,却没想到在搬运豆子时不慎感染瘟疫,甚至在临死之前都不忘他的那些豆子。太监翟役生,从小被送入宫中,大半辈子的屈辱生活使得他沦为了一个无赖。鼠疫早期,想靠囤积棺材赚一笔,结果害得情人金兰死去,后来在一座教堂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并奉行着他的无赖哲学:“想活下去,就轻贱这个世界吧。”②他和《鼠疫》中的柯塔尔一样,希望灾难继续下去,以此寻求自我安慰和内心平衡。其实不管是《鼠疫》还是《白雪乌鸦》,作者都是想通过人性之恶来揭露比灾难更恐怖的是人心,灾难始终会过去,而人性之恶会一直存在着我们的身边。
二.团结一致,共同抗疫
虽然加缪和迟子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家,同时两位作者在创作思路、创作特色、价值立场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对灾难进行书写时,他们不谋而合。二者都坚信只有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疫,才能最终战胜瘟疫。在残酷的灾难面前,人性之美才是最值得歌颂的。
作为抗击鼠疫的中坚力量,无论是《鼠疫》中的里厄还是《白雪乌鸦》中的伍连德,他们都毫不畏惧瘟疫的袭击,积极投身于抗战第一线,带领人们走出困境,彰显出人性美的光辉。里厄医生在鼠疫爆发初期就敏锐地察觉到这并不是普通的流行病,他坚持要采取相关措施防范危机。他从未产生过逃避灾难的念头,哪怕是和妻子分隔两地也要参加抗疫,在他看来,这是职责更是担当。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里厄医生的心境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在鼠疫初期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病人的病症,制定防疫措施。然而在法官奥多先生儿子、妻子、甚至是同甘共苦的战友塔鲁的相继去世后,里厄医生感觉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从最开始对于鼠疫何时结束感到遥遥无期变为了对于鼠疫的愤怒,也正是因为愤怒让他积极反抗并坚持到了最后,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同样作为医生的伍连德临危受命,顶住巨大压力成为了傅家甸的防疫指挥官,但在那个不太文明的时代,他的防疫措施不被百姓理解:焚烧堆积如山的尸体;解剖尸体获得病菌样本;封闭傅家甸,为了防疫,冲破教堂的枷锁。小说中也曾多次出现了对伍连德思念家乡、妻儿以及内心独白的描写,这相比《鼠疫》中里厄医生抗疫时的冷酷描写,《白雪乌鸦》中的伍连德医生在迟子建的笔下多了一丝人性的温情。在面对棘手的灾难时,也曾想过放弃,但目睹受苦的百姓,却更加坚定地走在抗疫的最前线,他知识渊博,冷静应对,常常从大局出发,时刻将人民的利益和安全摆在首位。作为职业医生的里厄和伍连德,他们在灾难发生时和人民共进退,这种舍弃小我,无私奉献的精神确是值得称赞。
在灾难面前,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两部作品中那些微不足道却又散发着光芒的小人物也同样不容忽视。《鼠疫》中的朗贝尔公事来到奥兰城,却因突发的疫情隔绝此地,孤苦伶仃的他分外思念在外的女朋友,于是想尽办法离开此地。然而当真正可以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醒悟:“独自一人的幸福,就是可耻的行为。”③朗贝尔自觉的融入到与鼠疫进行抗争的队伍中,实现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融合。政府办事员格朗虽然做着细小的工作,但他却很庆幸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最后因疲惫不堪而感染上鼠疫,或许加缪笔下的格鲁所表现出来的品格代表的最纯粹的善,是作者最想要赞颂的吧。
相比于《鼠疫》的描绘,《白雪乌鸦》凸显更多的是灾难下的人物群像,可以说傅家甸的百姓都是小人物,面对瘟疫,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抗着。傅百川在瘟疫期间打击不良商贩发灾难财,抑制物价上涨,还积极配合伍连德医生的防疫工作,为傅家甸百姓生产口罩;周济主动将家里的点心铺改造成专为病患提供伙食的厨房,不顾危险的为隔离区送饭,最后一家三代不幸感染;王春申与他心爱的黑马每天往返城区与郊区,专门护送逝者,他们不顾自我生命的危险,力所能及的贡献自己的力量,绽放出人性的坚韧之美。
其实鼠疫并不是最大的敌人,而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人性之善恶才是作者的真实的目的。虽然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们始终能保存内心的纯真与善良,散发着光芒。一个人的斗争不能赢得胜利,但团结起来反抗必将走向光明。
三.灾难书写的不同呈现
尽管二者都將“鼠疫”作为描写对象,同时都主张只有共同抗疫,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由于两位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从而整体的感情色彩以及对灾难的思考方面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灾难书写方法。
加缪作为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一直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反抗着这个荒诞的世界。尽管与萨特等人的主张不同,但都从人道主义出发,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他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但他反对用逃避的态度去面对荒诞,而强调以反抗的态度去消解和超越荒诞,“加缪将人认识到世界的荒诞并获得了荒诞感称之为觉醒,并将之作为他荒诞哲学的起点,指出觉醒后荒诞的解决途径就是反抗。”④人究竟该如何生存下去?《鼠疫》给出了答案。首先,加缪将鼠疫作为故事题材,暗射当时二战期间世界的荒谬性,用奥兰城隐喻人民的糟糕困境。在加缪生动的叙述下,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个在鼠疫笼罩下的恐怖时代。人们隔绝于此地,粮食断绝,交通瘫痪,无良商家趁火打劫,高价出售紧急用品,一到夜晚,整座城市进入一片黑夜,这无声的压迫感席卷着内心,此前热闹的城市如今却犹如死城一般,如同阴森的墓场。
其次,在加缪所描画的这个荒谬的世界中,作者还为我们展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的斗士们。“反抗理论”作为加缪荒诞哲学思想的实质,回答了人面对荒诞应该如何自持的问题。在小说《鼠疫》中,他“所描述的人类团结友爱和为援助受苦人而献身的精神达到了基督教纯善的高度。”⑤便很好的诠释了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正是因为这些拥有“荒诞反抗”力量的斗士们,带领着人们走向胜利的曙光,这些带着主观色彩的人物再现了世界的荒谬性。但是在小说结尾处里厄医生却认定:“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亡也不会消失……鼠疫会再次唤醒老鼠,并让它们死于一座幸福的城市。”⑥这具有充满荒诞色彩的结局,再一次印证了作者“荒诞哲学”的实质,拒绝相信绝对永恒的胜利,人类的能力可能无法绝对战胜困难,但直面反抗,团结一心是作者想要通过《鼠疫》传递给世人的真理。
迟子建曾在《白雪乌鸦》后记中这样说到:“我在小说中,并不是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后,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⑦因此,在《白雪乌鸦》中作者的初衷并不是去塑造崇高的人物,她只是想去描绘那些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小角色,通过这些小角色在灾难中的种种不幸遭遇来叙说出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含义,进而展现这部作品的温情力量。作者的温情书写使得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化解了灾难,在苦难中绽放出人性的伟大光辉。
首先,在《白雪乌鸦》中的灾难书写的温情特征体现在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宽容、包容、理解、同情、体贴与关爱等具有积极向上的情感的描绘。小说的前六章只是交代各式人物,描写发生在傅家甸地区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直到第七章,才正式描写鼠疫,故事发展在作者平稳的叙述下进行着,描绘着灾难侵袭下的人生百态。虽然小说中对伍连德医生的描写并不少见,但作者也没有放弃对小人物的坚守,比如王春申,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共同体,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爱情、亲情、友情可以说是小说人性描绘的集成。再比如周家三代,只是用极为平常的基调去描绘这人间烟火,特别是对喜岁的描写,有他之处必有笑声,也让小说在灾难笼罩的黑暗中感受到了些许明亮。以及对纪永和和翟芳桂的刻画,让我们感受到人性之恶与人性之美的两极。
其次,《白雪乌鸦》灾难书写的另一特征是对死亡刻画的中和,也就是说对死亡的呈现往往比较收敛,较少描绘死亡的丑恶。比如作者是这样描述巴音的死:“面色黑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半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已经死透了!”⑧以及对鼠疫大爆发后的状况描写:“有的人是歪歪斜斜走在路上,突然支持不住,抽搐着倒地身亡;有的则是死在家里了,亲人怕受牵连被隔离,而弃尸街头。”⑨很显然,相对于血腥地描绘死亡场面,作者是在刻意地回避死亡之“丑”,很少描绘鼠疫的残酷与狰狞。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风格,削弱了沉重灾难的厚重感与悲伤感。
正如迟子建所谈及的那样,灾难只是重现历史事件,重要的是通过对灾难的书写,来展现人间的温情,述说那些最普通但却足以温暖人心的故事。
灾难文学通过对灾难事件的再现,启迪读者思考生命的意义,引导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爱、希望和生命的意义。同样都是将鼠疫作为描写对象,以虚构城市为背景的《鼠疫》写作极具哲学深思,加缪用他的荒诞哲学以及反抗精神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对人与世界的新的解读方法。而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白雪乌鸦》更加偏向于温情书写,作者笔下的人物群像虽然没有留下光辉一笔,但人世间的这份美好却能照耀他人。尽管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但实际看来,这两部小说都提供了一种在鼠疫中平常民众对待死亡的态度和对死亡的理解,并且都在努力揭示鼠疫不过是生活罢了。
参考文献
[1]加缪.《局外人·鼠疫》[M].徐和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迟子建.《白雪乌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黎醒.灾难中的人性之光·论迟子建长篇小说《白雪乌鸦》[J].安徽文学,2011(9).
[4]刘雪芹.《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外国文学研究,1992(4).
注 释
①③⑥加缪.局外人·鼠疫[M].徐和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46,256,339.
②⑦⑧⑨迟子建.白雪乌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32,235,27,77.
④郭宏安.新中国60年的加缪小说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13,34(02):71-79.
⑤转引自鲍颖萍.分析加缪的存在主义与反抗精神——以《局外人》和《鼠疫》为例[J].名作欣赏,2016(21):142.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