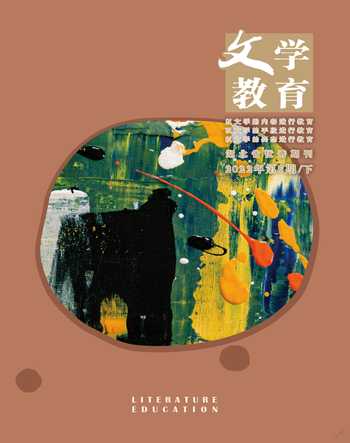论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
刘瑶
内容摘要:随着二十世纪语言学的转向,拉康在其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价值判断与思考。以笛卡尔确定主体性的“我思故我在”为基础,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将其进一步深化,“我不在”之“我”与“我思之处”之“我”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实在界与想象界的映象,也是思考主体与真实主体、言中主体与发言主体、真实之我与伪装之我的直接显现。拉康将不同语境下的我进行区分,是一次打破传统的突破,而这一突破也正是他这一思想提出具有价值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拉康 我思故我在 我不在我思之处
二十世纪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开始兴起,语言逐渐被关注,成为一个符号系统。在此基础上,语言的意义也受时间与思想的碰撞而跳跃,从具有稳定的意义开始向无穩定飘浮的意义而转变。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回归弗洛伊德,提倡无意识理论,他将无意识视为一种语言活动,但并不认为语言与符号等同,他的“我不在我思之处”便深刻的体现出了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这是对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一次大胆推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确立理性的一次伟大尝试。笛卡尔认为万事万物皆可怀疑,我思故我在则是强调“我”的作用,即认为思想是“我”的本质,“我”思想知道有“我”,“我”不思想不知道有“我”,从而引发主体性的觉醒。而拉康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意义推翻,将自我与语言结合起来,将真实之我与伪装之我区分开来,将语言的意义不再稳固化,便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主要从基础、含义、意义三个方面来对拉康提出的“我不在我思之处”进行探讨,旨在分析出拉康这一主张的重要意义。
一.“我不在我思之处”的基础
拉康提出的“我不在我思之处”,除了离不开它的原型,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外,还深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言符号对拉康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背景意义。在这些客观原因背后也潜在着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即拉康自身理论的建构与推动,它的理论发展是这一思想提出的重要导火线。
(一)社会基础:语言学的转向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一大环境的转变影响了文学及各个领域。拉康也深受这一时代的影响,而索绪尔语言学的发展为其理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①,认为每个符号都应该被视为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强调过语言符号的强制性,即“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②这一能指意义的确定,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重要地位,无一不说明了语言符号的重要性。而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中的“我”与“我”,即言中主体与发言主体的不一致性,也就突出了无意识的潜在作用。无意识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之中,而拉康又进一步将无意识与语言结合起来。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但不同之处在于,拉康认为无意识不具备相对应的所指,是种种能指的组合。梦境中出现的意象,并非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它的意义是含混甚至是矛盾,捉摸不定。这是拉康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一次挑战。
(二)理论基础:三界说的提出
拉康的三界说,即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对拉康提出的“我不在我思之处”有重大的影响。其中实在界与想象界是读者正确了解拉康这一思想的关键所在。区分拉康的实在界与想象界,是正确解读“我不在我思之处”的必要前提。所谓拉康的想象界,指的是“自我的领域,是一个由感知觉、认同与统一性错觉所构成的前语言领域。是一个认同与镜映的领域;是一个扭曲与错觉的领域。”③由此可知,想象界是一种身体本身的镜像关系,自身由于想象并在此过程中构成了自我,而这一想象界逐渐过渡到象征界就对应于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之中的“我思”,“我思”在此成为一个阐明的主体,“我”与思考中的“我”并不是同一的,正如拉康所认为的人的存在“总是在别处”④一样,“我”也是受到本能欲望去思考“我”,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可以无限缩小,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和解。而“我不在”在此便成了一个被阐述的对象,即被称为客体。在此,对应着实在界。所谓实在界,拉康认为“实在界是未知的,它存在于这个社会象征世界的边界之上,并且处在与社会象征世界的持续张力之下。”⑤也就是说有别于想象界与象征界而实际存在的一切。“我不在”之“我”即实际存在的主体。犹如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具有一条裂缝一样,思考主体的“我”与思考内容中的“我”也具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此,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可被视为拉康这三重说理论下的一个产物。他的自身理论也成为了他改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有力依据。
二.“我不在我思之处”的含义
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价值,从不同角度来看,它的含义各不相同。如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读,其中能指与所指,言中主体与发言主体的关系是我们探讨的重点;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角度出发,无意识凸显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何为真实之我,何为虚伪之我,是我们认清自我的途径。这些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意义。
(一)语言学的角度:能指与所指的断裂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我不在我思之处”,首先是涉及到能指与所指的问题。“我不在”的“我”与“我思之处”的“我”,同样是“我”但所表达的意义不同。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中的“我”这一符号,更多的可以看作是一种先验的能指。“我”与“我”虽然是同一符号,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不同。“我不在”之“我”可以说是言中主体,“我思之处”的“我”可以看成是发言主体。一个是说的“我”,一个是被说的“我”,二者之间形成一条能指链。这一能指链的作用就是区别差异化,拉康说语言是“把存在弄成欲望的东西”⑥,而推动这一能指链的外在因素即是欲望。“我不在我思之处”从它的发音来看,“我”的重复出现是显而易见的,但重复并不代表等同。正如德勒兹的《重复与差异》,认为重复的同时已经就有差异了,第一是差异,第二才是重复。在这里的同一,其实就是能指与能指的差异,并不断地延异能指,从而导致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拉康的语言学是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对语言的一个重新界定,他打破了传统的语言是系统的符号,而认为语言是一个能指系统。“我不在我思之处”则就是由于能指与能指的差异从而形成一种拉康式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拉康对于语言的使用与定义。毋庸置疑,拉康语言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传统语言学即索绪尔语言学的推翻与扭曲,他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而进入到精神分析学中去,将语言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从而更好的研究精神分析理论。
(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无意识与语言的结合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我不在我思之处”的内涵,其实就突出了人的无意识。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将无意识与语言结合是一次新的尝试。“我不在我思之处”认为真实的我并不在我思考的“我”当中,表面上都是“我”,但是现实的我与思考中的我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拉康认为我们之所以可以看到“我”的不统一,主要是由于无意识。拉康说,“言语的最根本的用途看来是为了掩盖真正的意图”。⑦在我们说话或者思考的过程中“我”的无意识会无意识的凸显出来,例如,“当我正在看电视,妈妈走过来把电视关了并要求我看书,于是我打开书。”在这里的“我”虽然打开了书,并且双眼正在看书,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可能还沉浸在某个剧情情节之中,这种沉浸其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反应。在这一句话中,主体并没有直接表明他的真正想法,但按照“我不在我思之处”的逻辑来看,无意识已经凸显在了语言当中,结合语境我们可以看到语言背后的潜在内涵。再如,“中午了,小明打算去食堂吃饭,于是他打开寝室门,向食堂走去。”在这里也同样如此,主体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的心里可能想的是去哪个食堂吃饭吃什么菜等。同样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而看到主体无意识背后的真正想法。在此,无意识似乎可以看作是语言文化下的产物。但拉康认为,“无意识不仅是语言文化(能指)作用下的产物,而且它还是一个中介,它把语言文化对人类主体的外在影响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影响。”⑧他的“我不在我思之处”通过无意识将真实的“我”与伪装的“我”杂糅在一起,真实的“我”往往隐藏在伪装的“我”之下,这种将无意识与语言相结合的方法,使语言更好的凸显它的价值,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真实之“我”。
三.“我不在我思之处”的意义
“我不在我思之处”这一观点的提出,不论是在精神分析学方面还是在文学阐述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意义或是直接影响,或是间接促进,都具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位置。拉康提出“我不在我思之处”这一观点必然具有他的思考与理由,同时也会无形之中赋予它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一)对精神分析学的意义
作为一位在精神分析学颇有建树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将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联系起来考察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我不在我思之处”在精神分析学上,关于如何通过言语去了解病人的内心,如何发现病人的心理障碍具有重大的价值。在拉康之前,关于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已经进入了精神病临床治疗中。如“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时,除医生和病人谈话之外别无其他,病人说出他的以往经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表示他的愿望和情绪,医生只有静听,设法引导病人的思路。”⑨这一疗法就是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为基础的。在这里拉康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无规律可循的,而拉康认为无意识和语言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他的“我不在我思之处”之中,我们可以通过语言,通过语言中的主体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去发现人的无意识。“我不在”之“我”与“我思之处”之“我”,后者的“我”是对主体欲望加以组织所表达出来的结果,是主体内心中所期待的“我”。“我不在我思之处”在精神分析学中的价值,归结起来就是通过语言的结构去发现无意识,无意识的结构在语言的结构中得到体现。在此,语言就成为了一个中介,起到桥梁的作用。因此,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实验中,分析者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语言,去找到无意识的规律,从而了解他们内心中真正所想的东西,而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就是将无意识与语言结合的一个产物,有助于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
(二)对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
任何一个事物的意义都是多方面的,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也如此,除了在精神分析学领域有意义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具有重大影响。“我不在我思之处”运用在文学领域,首先可以从其表面含义出发,将我不在我所思考地方的“我”理解为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中的作家,作家在创造文本时所表达出来的文字也许与作者内心所想的不具有一致性,或由于时代背景,或由于个人因素等最终导致真正的想法无法得以表达。在此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可以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出发,这一出发点固然对解读文学作品有意义,但在拉康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提到过。其次,可以从文本的语言出发。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可以关注文本,从语言本身去探讨文本意义。由此,解读文本由研究作品与作家的问题变成了研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问题。正如赖特所认为的:“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所考察的文学作品的探讨一直是以分析人的心灵为中心的,而不管它是作者的、人物的、读者的心灵,还是这些人的心灵的结合体。新精神分析学的结构主义式探讨则以分析作为心灵的文本为中心,这种分析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无意识也像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⑩这种转换也是拉康在文本阐述方面,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策略。
拉康的“我不在我思之处”观点的提出与发展,固然离不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思想的提出,固然避免不了受到语言学革命的洗礼,固然不受到自身理论的影响。虽然这一观点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拉康提出的“我不在我思之处”的观点之中,体现了拉康对自我、对主体、对语言的思考,这是一次具有思想性的改写与延伸。而拉康通过将无意识与语言结合起来,也展现了无意识的规则所在,展现了语言的魅力,展现了文化顽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3]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5]伊丽莎白·赖特:《精神分析批评:实践中的理论》[M],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84年。
[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8]黄作:论拉康的无意识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9]张一兵:能指链:我在我不思之处——拉康哲学映象[J],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0]贾克防:笛卡尔论分析方法与“我思故我在”[J],世界哲学,2014年第3期。
注 释
①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页。
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7页。
③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页。
④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73页。
⑤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⑥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⑦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40页。
⑧黄作:论拉康的无意识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41-45页。
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
⑩伊丽莎白·赖特:《精神分析批评:实践中的理论》[M],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