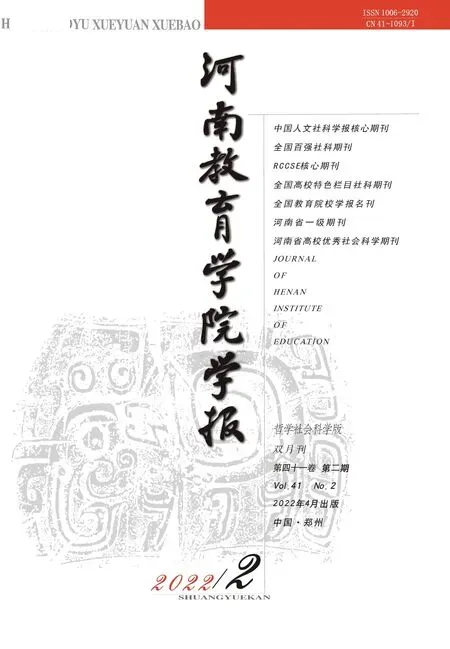《瓶湖懋斋记盛》系民国以近的托名之作
胡铁岩
一、引语
自1973年吴恩裕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以来,关于《废艺斋集稿》真伪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近五十年间的相关争论,详见任晓辉、辛欣的《〈废艺斋集稿〉研究综述》[1]和段江丽的《〈废艺斋集稿〉的来龙去脉及真伪论争》[2]。
《废艺斋集稿》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冠名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残篇是其焦点问题之一。笔者以敦敏、敦诚诗文及同期相关史料文献为参照进行研究发现,《瓶湖懋斋记盛》作者完全不熟悉敦敏、敦诚兄弟诗文的内容,甚至连清代基本制度都不了解,《瓶湖懋斋记盛》对敦敏经历及所涉及的清代基本制度的记述亦存在诸多悖谬之处。现将相关史料及论证报告如下,望方家批评指正。
二、敦敏并无分身术,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不可能在北京
根据《瓶湖懋斋记盛》的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戊寅春天,敦敏在京居住,曾两次去白家疃探望曹雪芹。这件事的前后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跨度:
爰思鉴别字画,当推芹圃;又且久未〔把〕晤,(原注:春间芹圃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值余赴通州迓过公,未能相遇。)苦念綦切,乃往访其新居。几经〔询问〕,始抵其家。……又月余,芹圃〔未〕至。渴念不已,策马再访……闻白媪言,愈思与芹圃一面,以慰渴念,〔而〕动定参商,〔缘〕会不偶。久之,亦无裁答。[3]30-32
然而根据敦敏、敦诚诗文集记载,敦敏这一阶段正在山海关为母守灵。敦敏没有分身术,不可能有此一段“佳话”。
(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敦敏在山海关的时间
敦敏和敦诚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随父瑚玐到山海关当差的。敦敏在山海关,敦诚在喜峰口松亭。北京到山海关共有驿站十站。一般情况下,即使风雨无阻,中间不休息,也要走十天。往返一趟应当不少于二十天。
敦敏之母去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当年腊月,敦敏回过一次北京,有《闻子明兄西归计程应至蓟州潸然感赋·时在松亭作》为证:“旧事凄凉不可论,又从故道走方辕。崆峒山下夜沽酒,风月明朝过蓟门。”[4]150该诗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腊月,敦敏已经快到京城了。敦敏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除夕前回山海关,有《丁丑榆关除夕同易堂、敬亭和东坡粲字韵诗四首,已三年(1758)矣。追忆旧游,因复和之并简易堂敬亭》[4]22为证。
根据这个时间推断,敦敏回到山海关的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上中旬。敦诚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底前后也回过一次北京,再回松亭时,应该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底或二月初。敦诚《松亭再征记》曰:
戊寅正月,自都再赴松亭……至沙河,会子明兄自榆关驰四百里,就予于松亭。值余入都未回,兄与汝猷登松亭山,愀然不乐。越日而返,将之冷口,至此忽遇于村店中……之村舍,晚餐讫,兄欲东之。[4]323-328
敦敏与敦诚在松亭分别。一个月后,敦诚收到敦敏从山海关寄来的信。敦诚《答子明兄书》:“关门马上一别,各仆仆晓风残月中。兄走海上,余赴松亭,今又经一月,前接来札云……”[4]292从敦诚的记述看,敦敏信中并没有提到马上再回北京之事,说明敦敏在给敦诚发信时尚在山海关,且并没有再回北京的想法。从正月底二月初“又经一月”,敦敏寄信之时应在二月底到三月初。
(二)敦敏与敦诚乾隆二十三年(1758)扶柩回京的时间
敦敏扶柩自山海关回到北京的时间,根据富察恩丰《八旗丛书》中的敦敏《懋斋诗钞》“东皋集序”,是“戊寅夏自山海归”[5]1353,但没说具体在几月。笔者在敦诚《四松堂集》中找到一首《送易堂南归》:
往日榆关道,残春送我时。事徂那可忆,酒醒欲何之。
暮雨孤篷急,江天一雁迟。北来多驿使,好寄陇头诗。[4]156
敦诚丁丑二月去松亭当差,其间只回过京城两次。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离京,二月初回到松亭;第二次就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和敦敏一起“扶榇”回京,“戊寅夏”到京。残春是指三月,“残春送我时”只能是指第二次回京。按照敦敏所言“戊寅夏自山海归”,敦敏与敦诚“扶榇”回京时间应在三月中下旬,最晚不会晚于三月底。
“残春”起程,初夏到京,在敦敏与敦诚诗中可以找到佐证。《懋斋诗钞》诗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自山海归”。《水南庄》是《懋斋诗钞》第一首诗。
缓步临流四野赊,水南庄外钓竿斜。小桥野草归村路,隔岸垂柳卖酒家。
芦荻烟深聚网罟,平波水暖长鱼虾。小园终日闲双手,种菜还兼学种瓜。[4]8
诗中出现的“水暖”“种菜”“种瓜”等词语是春暮夏初的特征,足证敦敏、敦诚兄弟“扶榇”回京的时间是在“残春”到初夏之间。敦诚回到北京后的第一组七绝《初夏村居二首》的景色描写与敦敏诗一样,也是初夏特征:
近日耘苗到夕昏,荷锄野老各归村。主人饷罢芗萁饭,狼藉田家老瓦盆。
柳荫初浓麦浪微,杳无人迹到柴扉。日长挂起蓬窗卧,满院野花蛱蝶飞。[4]153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底到三月初,敦敏还在山海关为母守灵,其与敦诚扶柩回京的时间不会晚于“残春”(三月底),二者之间的时间跨度最多不超过一月。一个月的时间内,无论如何也发生不了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才可能发生的故事,除非敦敏有分身之术。
如果《瓶湖懋斋记盛》的“作者”能够稍微认真一点,读一读敦敏和敦诚的诗文集,就不会把这个故事放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
三、敦敏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不可能连续两次去西山白家疃
不仅时间上不可能,所谓两次去白家疃也是不存在的事情。白家疃在北京西山,从城里去的路程比去西山正白旗老屋还要远一些。要证明敦敏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有没有去过西山白家疃,首先必须弄清敦敏、敦诚兄弟曾经去过西山的次数和时间。一直有学者认为,敦敏、敦诚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冬之际,去西山看望过曹雪芹,其依据是这一年敦诚、敦敏的诗。
敦诚《赠曹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3]321
敦敏《访曹雪芹不值》: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4]58
敦诚诗中的一句“日望西山餐暮霞”,常被解读为曹雪芹住在西山,敦诚、敦敏去西山探望曹雪芹。实际上,这样的解读不能成立,其理由有二。

第二,根据敦敏、敦诚兄弟诗文集的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冬之际敦敏、敦诚没有去过西山。先看敦诚。截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敦诚一共去过三次西山。在《秋山纪游》中,敦诚明确交代了三次去西山的时间:“岁次癸未秋,拙庵伯父召游西山。……余顾三子曰:‘西山卅里,朝发午至,而二十年中,始三蜡其屐。’”[4]331-334乾隆二十八年(1763)是第三次。另外两次,一次在二十年前。敦诚《山游纪事》回忆提及:“记余少时尝侍拙庵伯父于此有蜡屐,定呼‘小阮从凿山,频逐谢公游’之句。”[4]346另一次,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敦诚《杂感四绝·悼贻谋》其二诗注亦言及:“壬午春,与弟游西山。”[4]220所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冬之际,敦诚未去西山。
再看敦敏。敦敏第一次去北京西山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八里庄望山》:“平生不识西山路,望眼欣逢一霁颜。两屐未穿幽磴险,孤峰遥接白云间。”[4]49首次去西山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之后敦敏有机会去西山,但他没有去,有《子谦再约西山之游余因事阻书此却寄》[4]51为证。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敦诚去西山时,敦敏有诗相送,《送敬亭游西山》诗中忆及首次去西山的具体时间:
去年四月西山道,柳翠烟浓花正好。嵚崎直上白云巅,眼界胸襟何浩浩。
层峦秀叠重崖垂,招提半属前朝基。君今二月奚囊去,我能历数西山奇。[4]64
这说明,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敦敏确实只去过西山一次。敦诚与敦敏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起去的可以“日望西山餐暮霞”的地方不可能是西山,而只能是西郊。这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很明确:乾隆二十六年秋冬之际,曹雪芹的居所并不在北京西山,或者说并不只是在北京西山。目前能查到的涉及曹雪芹与白家疃关系之文字,只此《瓶湖懋斋记盛》一篇。如果敦敏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去白家疃探望曹雪芹之事不能成立,则曹雪芹是否曾在白家疃居住过,就需要重新考察。
四、史证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入冬至年底,北京只下过一次寸余小雪,不可能入冬雨雪频仍
《瓶湖懋斋记盛》中说:乾隆二十三年(1758)“入冬,雨雪频仍,郊行不便”[3]32。但这一记述,与北京当时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关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北京入冬以后的雨雪情况,陈毓罴、刘世德在《曹雪芹佚著辨伪》中举《晴雨录》证明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冬季没有下雪。[7]然文雷在《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中认为《晴雨录》是记录北京城内雨雪情况的文献,并不包括北京城外的雨雪情况。[8]笔者专门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得当时直隶总督方观承的两件雨雪奏折,再结合乾隆皇帝同期的两首诗,可以证明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入冬到腊月二十四日,北京只下过一场寸余小雪。《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二十九日:奏明尚未得雪情形事》:
直隶总督方观承谨奏:
为奏闻事。窃查直属地方入冬以来,尚未得雪。虽麦田待泽犹可宽期,而节侯已届,盼望甚殷。兹保定省城于二十九日辰、巳两时雪花飘扬旋止,积地不成分寸。所喜沉阴密布,寒冱无风,雪意甚浓,似可即望续降。除俟得雪,一经积存分寸,并各属地已报有得雪之处即行奏报外,知厪圣心轸念,合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二十九日。
朱批:京师亦如之。览。(1)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3-0861-024。
奏报当地雨雪情况,是清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上报的各地雨雪情况并不是各地城内的雨雪情况,而是各地农村的雨雪情况。所以,方观承奏折和乾隆皇帝的朱批是包括北京城郊的。
这件奏折奏报的雨雪情况只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二十九日,距离《瓶湖懋斋记盛》所记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期间有没有再下过雪呢?可查看方观承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十三日《奏报直隶顺天府暨保定城得雪情形事》。在这个奏折中,方观承向乾隆皇帝报喜,保定省城于正月十二日起开始下雪,“除融化外,积地四寸”,而乾隆皇帝在奏折批语中说“京师不过寸余,切望泽也”(2)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25-0086-002。。关于这场雪,乾隆皇帝有诗记其事。《乾隆御制诗二集》卷八十三《夜雪·正月十二》:
迩日春云散复凝,祥花入夕势旋增。可能如愿忧差释,转觉延睋闷不胜。
岂为宜灯还助月,幸逢镂水更裁冰。朝来积地刚余寸,慰与愁兼景懒凭。
接下来一首《即事》:
池冰无月何妨镜,苑树有花都是梅。天意入春频兆喜,更殷捷报自西来。[9]563
从诗中“点缀园林”“苑树有花”看,乾隆皇帝的这首诗写于北京西山,并不是写于城内紫禁城。
以上所举资料说明,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入冬到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十三日,北京下雪只有两次,一次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次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十三日。这两次雪量都很小。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前,只有一次小雪,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雨雪频仍”。
五、不清楚清代最基本的制度,《瓶湖懋斋记盛》作者应该不是清代人
乾隆二十三年(1758)腊月二十四日这天的聚会无疑是《瓶湖懋斋记盛》的重点,但其具体描写中却有两处违背清代基本规制的地方。
(一)违背清朝的朝会制度
余曰:“〔为〕此事久拟备筵谢董公。今者即烦吾叔代为邀请,敬俟孚翁休假〔日〕以〔莅〕。期〔于〕先时见告,容作筹〔备也〕。”过公曰:“何必令汝破费!”余曰:“非仅为鉴别字画也。”遂允为转请。
腊月二十日,得过公示,已代约于二十四日□时,着余备帖往肃董公。[3]32-33
董邦达在腊月二十四日上完常朝后来敦诚的懋斋聚会,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不符合清代规制。清代官员上朝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固定的常朝,一种是临时奉召。董邦达乾隆二十三年(1758)腊月二十四日上朝是提前好几天预知的上朝时间,所以可以确定是日期固定的常朝。这个时间与当时的制度不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296卷“礼部·朝会”:
崇德元年定:元年进庆贺表笺,长至、万寿圣节进表庆贺,与元日同,惟长至不设燕。又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皇帝御殿听政。……(顺治)九年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皇帝御殿,文武百官上朝。……乾隆元年谕:嗣后御门听政,若遇逢五朝期,各官咸补服奏事,不必用朝服,永著为令。[6]692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七十九:
又定:每月逢五常朝日,由礼部咨兵部转行本衙门于黎明启正阳门。[10]649
查《乾隆起居注》,乾隆皇帝这一天没有上朝的记载:
二十四日丙子,上诣慈宁宫大佛堂拈香,诣寿康宫请皇太后安。[11]630
逢五朝会,是清代定制,不存在腊月二十四日有常朝的可能。
(二)违背清朝封印放假及对联撰写制度
〔二十〕四日,晨曦甫〔上〕,人声已〔喧〕,忙于除旧迎新也。民谚曰:“二十三,赶小年;二十四,写大字”,视为吉辰。万户千家,春联争奇句,桃符竞新文。此风尚自宫掖间。每岁是日,诏善书者入值,为诸宫所书楹联,以迎新春。供奉事毕,御〔赐〕有差,给假□□〔日,归〕家理年事矣。[3]37-38
就文字而言,这是典型的画蛇添足之笔。这一节外生枝的插叙,目的是证明作者对当时制度、风俗的了解。然而恰恰正是这段文字,让《瓶湖懋斋记盛》的“作者”露出了马脚。这段文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知道清代有封印放假制度,二是不知道宫中贴对联的时间和负责写对联的人的身份。
第一,有清一代,封印放假是定制。封印的具体时间,虽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旧京风俗志》曰:
每年腊月,如系大建,则于二十日封印,至明年二十日开印,如系腊月小建,则于十九日封印,至明年正月十九日开印。[12]513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的时间比《旧京风俗志》多两天:
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13]93
也就是说,官员封印放假是在腊月十九到二十二这四天之内。腊月二十四无论如何都已经是封印放假之后。封印放假之后,官员不必再到衙门办公。《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三曰:
又定:每年封开印信,豫期由部行钦天监选择日期,行知部院各衙门,均照期封开印。封印后,不理刑名,不办事。如有紧要事,仍行办理。[14]131
董邦达《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题为年节封开印及穿朝服事》曰:
据钦天监呈称:择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壬戌宜用巳时封印吉、次年正月二十二日壬辰宜用辰时开印吉等因,应照钦天监选择日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巳时封印,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辰时开印。自封印日起至开印日止,照例不理刑名、不办事,有紧要事仍行办理。
元旦礼仪:王等以下文武各官以上,照例自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正月初四日止,穿朝服七日。上元节,自正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止,穿朝服三日。命下之日通行八旗、各部衙门、直隶、各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3)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2-01-005-022956-0028。
第二,关于为宫中写对联之事,清代也是有规定的。王昶辑《湖海诗传》卷二十五曰:
封宝前一日,例进门联。……定例,各宫殿门对联撰自翰林,次由工部,每至封印后,工部堂属敬谨悬挂,新春开印后收而谨之,岁以为常。[6]111
对联由翰林或工部的官员书写。董邦达既不是翰林,也不是工部官员,而是吏部侍郎,所以写对联事与董邦达无关。“例进门联”的时间是“封宝前一日”。皇帝的封宝时间与官员的封印时间相同。祁寯藻《十二月十九日侍直作》:
凤阙觚棱晓色开,日高风静挈壶催。玺书封罢千官退,爆竹声中万乘来。
恩舆丝纶金殿出,春随笳鼓玉关回。侍臣更有丰年祝,白雪赓歌仰圣裁。[15]卷11
腊月二十四日并不是固定的“逢五”常朝日,且已封印放假,董邦达这一天无需上朝。《瓶湖懋斋记盛》中让过公煞有介事地事先与董邦达约定这一天上完朝后来懋斋聚会,显属凭空虚构。至于文中插叙让官员为宫中题写对联及题写后赏假之事,更是没谱之事。
六、结语
综上所述,《瓶湖懋斋记盛》的作者不仅不了解敦敏的生活经历,而且连清代最基本的制度都不了解。所以,《瓶湖懋斋记盛》不仅不可能是敦敏的作品,甚至不可能是清人的作品,而是民国或民国以近的作品。《瓶湖懋斋记盛》究竟是20世纪20年代以近的托名之作,还是20世纪50年代以近的托名之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瓶湖懋斋记盛》并非《废艺斋集稿》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只是附于《废艺斋集稿》,所以还不能以《瓶湖懋斋记盛》不是敦敏作品而简单得出《废艺斋集稿》不是曹雪芹作品的结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还需另题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