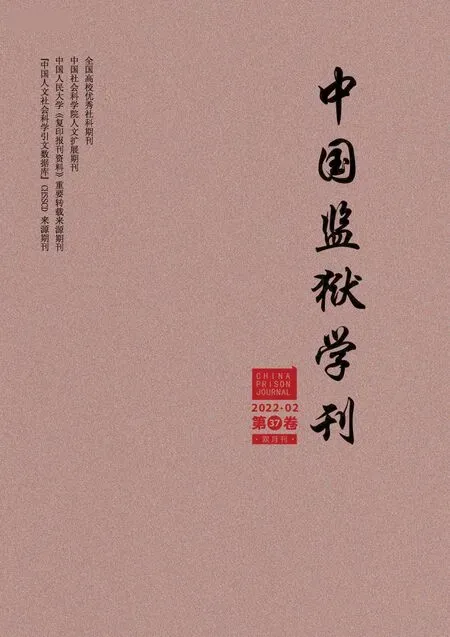罪犯与警察: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演进的两种进路*
——文化主体视角下中国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回顾与反思
汪前臣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市 310018)
引言
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掀起的文化研究热潮,法律文化研究逐步由理论法学向部门法学等领域渗透,出现了刑法文化、民法文化、宪法文化、经济法文化、监狱亚文化等研究〔1〕。其中,以罪犯话语为中心的监狱亚文化在2010年前后成为中国监狱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然而,作为与中国监狱发展密切联系,在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学术和实践话语之一,“监狱亚文化”主体是谁的问题,学界与实务界仍未达成共识,由此对监狱亚文化概念指标体系的建构也不尽完美。范式理论视角下,概念边界定位不清的问题成为制约监狱亚文化研究领域知识增长和累积的瓶颈。
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人在实践中创造了受时代条件制约的文化,同时扮演着历史“剧作家”和“剧中人”的角色〔3〕。因此,只有聚焦监狱中主要角色群体间关系,探讨监狱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表现方式〔4〕,进一步认清监狱“剧作”中的“剧作家”和“剧中人”,才能更好地理解监狱亚文化。本文对国内主要相关文献进行爬梳,拟从文化主体的角度描述范式演进理论意义上监狱亚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试图进一步澄清监狱文化和监狱亚文化的主体指标,以期为监狱社会学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一、范式兴起:“罪犯”和“监狱”指代的分歧
国外对亚文化(subculture)的界定主要有三种不同视角:一是从文化发生学角度,指人类学普遍意义上的可能发生的人类现象;二是以群体为参照,指相对于所处的较大群体或社会而言的群体文化;三是以价值取向为参照,指与主文化价值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的文化〔5〕。尽管“subculture”最初是指群体意义上的“亚文化”,但是由于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对象是移民者、流浪汉、小偷、妓女、犯罪团伙等特殊社会群体及其越轨行为,“subculture”经常被视为贬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国内监狱社会研究领域中的感情色彩。
国内监狱学领域的“犯人亚文化”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对美国监狱研究的引介中,但是其中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阐释〔6〕。随后邵名正和孙晓雳等人于1989年12月出版的《罪犯论》中描述了“罪犯亚文化”现象。他们指出,罪犯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其人身危险性所表现的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是罪犯的反社会性〔7〕。这种反社会性在狱中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公然的反改造行为;另一种则是反社会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8〕,即亚文化现象,比如罪犯特有的语言、文身、暴力行为等。在一定意义上,犯罪的反社会性就是罪犯的反社会性,罪犯亚文化是犯罪亚文化在监狱内的延伸,而反改造行为则是反社会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彼时许章润和孙平同样关注了罪犯“亚文化”现象,却使用“监狱亚文化”的名称。许章润在1991年2月出版的《监狱学》中把罪犯群体界定为“亚群体”,其中指出监狱亚文化是罪犯亚群体在监禁生涯中逐渐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和遵行的与社会主文化偏离或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的综合体〔9〕。在阐述“监狱亚文化”的概念、特性和功能之后,他刻画了十一种监狱亚文化现象:反社会意识,罪犯亚群体及其规则、监禁和仪式,犯罪的非语言符号,罪犯特征,文身,罪犯精神活动产品,监禁反应,监狱适应,监狱经验,监狱人格,监狱烙印等〔10〕。无论是从其对概念的界定,还是对亚文化表现形式的分类,都可以看出,此处监狱亚文化的主体是罪犯,监狱亚文化基本等同于罪犯亚文化。
孙平发表在《法律科学》1991年第4期上的《监狱亚文化研究》,是目前可查到的国内关于监狱亚文化研究的最早的学术论文。孙平认为,监狱是特定的社会组织,罪犯被监禁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内,监狱文化反映的就是这些罪犯的全部生活内容。从形态上监狱文化分为监狱物质态文化和精神态文化,从价值体系上分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其中,监狱主流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由政府通过法律和制度予以认可,作为标准文化在狱内推行。而监狱亚文化是在伦理、道德、宗教、审美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上与监狱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具有低层次性、隐秘性、对抗性、传播独特性、持续性等特征〔11〕。孙平此时对监狱文化和监狱亚文化予以建构,明确指出了监狱亚文化就是罪犯自己的文化,但是却忽略了警察在监狱主流文化即官方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因此也没有能够进一步厘清“监狱文化”“监狱亚文化”“监狱主流文化”“犯人文化”等多个术语之间的逻辑。
描摹某种常规科学,就要为之树立模型,这一模型包含了这一门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就,诸如定律、理论、应用、仪器,乃至研究这一科学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成就又必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这些成就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这种模型的科学家,同时这些成就也留下了等待科学家去解决的种种问题。托马斯·库恩把具有这两种特征的成就称为“范式”〔12〕。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在早期的监狱亚文化研究中,一方面,关于监狱亚文化对象的界定都是处于监禁状态的罪犯。被贴上“反社会性”标签的罪犯身份及其文化表现形式,导致了“亚文化”的“污名化”倾向,为后继的监狱亚文化研究树立了“模型”和“典范”。另一方面,留下是“罪犯亚文化”还是“监狱亚文化”的分歧,及其可挖掘的丰富的表现形式,等待后继研究者的解决。自此,国内监狱学领域开始了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的自觉。
二、范式争辩:莫衷一是的“罪犯”主体亚文化
带着“罪犯亚文化”和“监狱亚文化”的分歧,学界围绕“罪犯亚文化”为何的问题展开探讨,形成了监狱亚文化范式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范例。
(一) 罪犯病态文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监狱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实体物化文化,包括监狱所处的地理环境、监房建筑、劳动场所、监区文化设施等;二是中间层的监狱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既包括警察应遵守执行的规章制度、行为准则,行刑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交往关系、习惯以及警察生活方式、娱乐手段,也包括罪犯服刑期间应严格遵守的监管条例、生活制度和文体活动方式等;三是深层的监狱所有人的社会意识总和,既包括警察的专政意识、政治态度、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等,也包括罪犯群体的认罪服法态度、价值观念、世界观、思维方式、信仰和反社会意识等。从监狱文化主体上,作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的监狱文化,由警察文化和罪犯病态文化两部分组成。罪犯既有病态文化素质,也有正常人的文化素质,他们在被强制吸收积极的社会文化同时,还要遏制乃至消除自身的病态文化〔13〕。在这里,中间层和深层关于警察的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和社会意识都是主流文化,仅罪犯病态文化是亚文化。
(二) 以人为本语境下的监狱文化主体论
从人学的角度,不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还是在西方工业化时代,人的主体性缺位是普遍的,一直以来作为人的罪犯更是作为监狱的客体而存在。直到现代人学和现代文化学视野下,罪犯作为监狱文化的主体才获得理论及实践的认同和接纳。人本主义语境下,罪犯作为独立的文化主体,在监狱文化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消极文化和积极文化的享有者、消费者,也是参与者、制造者。众多角色中,罪犯是不可替代的能动主体,警察则是具有绝对指挥权的强势主体,而与监狱关联的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罪犯亲属、执法监督员、社会公众等也是重要的监狱文化建设的相关主体〔14〕。基于张晶“以人为本语境下的监狱文化主体”论,罪犯文化包括罪犯消极文化和罪犯积极文化,监狱文化主体包括罪犯、警察,以及与监狱发生关系的其他主体。张晶最先从人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监狱文化的多重主体,尽管与监狱发生关系的其他主体是否构成了监狱文化主体值得商榷,但是现代人学角度下的监狱文化多重主体论,为我们深入分析监狱亚文化生成原因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 具有抵抗、颠覆功能的囚犯亚文化
监狱文化是通过监狱制度模式或监狱主体间的关系模式,表达具有“监狱居民”身份的警察群体和囚犯群体特殊生活状态的“意义地图”。其中警察群体的文化是强势的、占据主导地位;囚犯群体文化则是弱势的、处于从属地位。囚犯亚文化形态承载囚犯群体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是囚犯群体文化中具有抵抗、颠覆功能的部分,也是囚犯文化这个大的文化结构中的更小的、地方化的、具有差异性的结构〔15〕。从伯明翰学派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理论视角,刘方冰指出囚犯亚文化对监狱主导文化具有解构与颠覆性威胁,因此监狱主导文化给予其防范性的关注并想方设法予以遏制与收编。“监狱居民社会关系建构”的观点,揭示了警察群体和囚犯群体在监狱亚文化体系中的互动关系。
(四) 属于亚文化范畴的监狱文化
高庸横向对比中西监狱文化状况,指出西方监狱文化研究强调从罪犯的视角去观察监狱文化,而忽视了监狱管理方的存在;国内监狱文化研究更多则是从监狱管理方的视角对监狱文化进行定义,因此容易忽视罪犯是监狱文化主体的事实。他认为监狱文化是发生在监狱这个特定封闭性环境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在警察与罪犯这两个主体之间互动——监管与被监管、改造与被改造——中形成的亚文化〔16〕。在这里,监狱文化作为有别于其他群体或整个社会的文化,属于亚文化范畴,它不但影响到罪犯的行为习惯与价值观,而且对警察的行为习惯与价值观产生影响,因此对监狱秩序、罪犯改造效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五) “对象”“形态”和“场域”三个维度
如前所述,早期孙平关于监狱亚文化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不成熟的。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孙平先后从“对象”“形态”“场域”三个维度,对监狱亚文化概念体系进行了新的建构。在2005年发表的《监狱亚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孙平对“监狱亚文化”的“对象”和“形态”做出解释:监狱亚文化是个整体概念,以对象来说,它包括监狱罪犯亚文化和监狱管理人员亚文化两个部分。以形态来说,它包括主流文化形态和亚文化形态。由于对监狱管理人员文化形态的研究不属于其论述范围,所以要对“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围与名称使用做一定的限制,即,其所研究的监狱亚文化——从对象上不包括监狱管理人员亚文化,从形态上不包括监狱犯人的主流文化形态——因此是与主文化相异的监狱罪犯的亚文化形态〔17〕。如此,把监狱管理人员亚文化从监狱亚文化研究对象中剥离出去。孙平在2012年发表的《监狱的悖论》一文中,孙平进一步明确,监狱文化是监狱这种特定组织内部的文化概括,它包括监狱主流文化和监狱亚文化,监狱亚文化是罪犯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监狱主流文化存在一定的对抗性〔18〕。孙平2013年出版的专著《监狱亚文化》可以看作是孙平关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总结,其中除了就“对象”和“形态”两个维度界定的“监狱亚文化”的再解释,孙平又从空间特点角度出发,指出“犯人”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狱内服刑人员,也包括缓刑犯、假释犯等社区矫正对象,而使用“监狱”这一词语则完成了对“狱内服刑人员”这一研究对象的限定〔19〕。因此可以说,基于“对象”“形态”和“场域”三个维度,孙平实现了对其“监狱亚文化”学术话语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孙平“监狱亚文化”话语体系的成熟。
在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的术语,比如“罪犯亚文化”“囚犯亚文化”“服刑人员亚文化”“犯群亚文化”“监狱主流文化”“监狱管理者亚文化”“干警主流文化”“警察主流文化”等,这促成了监狱亚文化研究范畴的讨论,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状态。监狱亚文化研究历程中重要观点的呈现,既是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的具体的谜题解答,也体现了八十年代以来监管改造事业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历程。
三、范式解题:罪犯生活场景的精细刻画
最初产生之时的范式在应用范围和精确性上都是极其有限的。范式的成功在于将来实现某种选取的预示,而实现这种预示的方法就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20〕。在实现这种预示的同时,范式的解题功能得以不断展现。在范式解题中,罪犯生活场景得到了精细刻画,形成了罪犯自杀、脱逃、暴力、性、伪病、狱霸等亚文化现象的深入解题。
(一) 罪犯非正式群体
狄小华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罪犯非正式群体与罪犯亚文化的关系。传统行刑模式下,警察在行使监狱惩罚性、报偿性和制约性三种权力过程中可能导致罪犯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促成了罪犯积极的、消极的、中性的非正式群体产生。从功能上,暗语、文身、脏话、牢头狱霸等罪犯亚文化产生于消极的罪犯非正式群体,同时对罪犯非正式群体组织具有强化作用,如增强狱内消极非正式群体的目的、隐藏非正式群体活动行为、培育和延续消极非正式群体意识和行为等〔21〕。狄小华还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指出罪犯非正式群体有内部成员之间、群体与警察之间、群体之间的三重人际互动关系,即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与感染、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冲突、成员与警察之间的服从与对抗等〔22〕,为我们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理解警囚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亚文化的集散地
孙平把警察排除在监狱亚文化研究之外,重笔描画了新型狱霸、狱内自杀、暴力、造作病和伪病、性以及文身六个监狱亚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传承过程。孙平指出,监狱是亚文化的集散地,要正确面对正常存在的监狱亚文化,只有通过了解罪犯的行为方式、习惯,发现罪犯的思维方式、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才能够审视监狱亚文化、防止监狱亚文化的泛滥〔23〕。孙平深入监狱生活现场观察罪犯、与罪犯和民警交流,通过田野调查法对狱内罪犯亚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其《监狱亚文化》作为监狱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24〕,引发了学界关于监狱亚文化研究的深入对话,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三) 有序与无序的秩序
宋立军反思了有序即秩序的常识,从监狱职员和服刑者情境互动角度考察监狱秩序问题,指出监狱秩序是在有序和无序中推进。宋立军认为监狱秩序主体由监狱职员和服刑者构成,服刑者日、周、特殊节日和监禁生涯节点的生活场景描述,反映的是时间规则建构的监狱秩序〔25〕;服刑者的自我保护、互惠交换、交往技巧,服刑者与职员间的交往策略,作为弱者的服刑者与职员和监狱抗争,以及作为强者的监狱职员却温柔地对待服刑者等日常交往规则,揭示监狱秩序主体的“活法”〔26〕。空间规则、时间规则和日常交往秩序中的活规则等,展现了警警之间、警囚之间和囚囚之间的阶序,也决定了监狱秩序的权威。
(四) 监狱的隐喻
郭明的《监狱的隐喻》以文学叙事加学术思辨的方式,通过客体性的“事实”与主体性“真实”解读监狱人文现象〔27〕。《监狱的隐喻》前半部分侧重于白描,通过志愿囚“苏林”讲述囚囚、警囚之间产生的关于背叛、脱逃、乱伦、疯癫、相残、自杀、倾轧等故事;最后两章则是采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与但丁、笛卡尔、马克思、福柯等先哲的对话,深入探讨了惩罚与改造的困境,揭示监狱文化是现代性的隐喻。作者将这种特殊的文本形式称之为“骡文本”。他用小说体裁的叙事手法解构监狱和罪犯最终表达深层次的监狱问题〔28〕,实现了修辞性的隐喻诠释和逻辑性的规范定义的认识功能整合〔29〕,为我们研究监狱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五)特殊的法制报告
东台山人在经历监禁生活之后完成了“三黑”法制报告,其中《黑日》描述了在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的诗歌、顺口溜、文身等文化语言,以及蔑视刑罚、等级、性变态、畸形消费、对抗审查、封建迷信、装病、钱权交易、脱逃等现象,指出刑罚造成犯罪者的肉体和精神痛苦是必然且必要的,罪犯为逃避受刑之苦也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试图钻法律的空子〔30〕;而司法队伍玩弄、践踏法律,权力被异化、滥用,基于钱权交易的司法腐败也成为一种必然亚文化现象长期存在〔31〕。
(六)文学的视角
常规科学模型包括研究这一科学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这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32〕。监狱研究者和监狱社会人通过文学视角刻画的监狱场景,也是监狱文化范式描摹的组成部分。如高文先生的《狱城之恋》通过黄泊湖农场的创生、发展、鼎盛和消失展示了新中国监狱的发展历程,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展示两代劳改干部(警察)的理想、坚韧、奋斗和牺牲的精神,描写两代罪犯的卑微、抗争、顺从和报复的个体生命历程。《人性的另1/2》是网络上流传的刑释人员黑鱼逛逛以一名罪犯的口吻讲述了罪犯为了自我保护、谋取利益而不得不进行的谋取“职位”、拉拢罪犯、打击对手、靠拢警察等行为,同时也通过罪犯的“职位”和罪犯间的关系,揭露警察之间合作与排斥的现实问题。文学视角的监狱世界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一些监狱文学对于研究中国监狱变迁的贡献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关于此主题的论文和专著〔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监狱似乎成为社会/人类学者研究的禁区,狄小华、孙平、宋立军继承了民国时期将监狱纳入人类学研究范畴的传统〔34〕,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罪犯监禁生活场景的精细刻画,详尽展现了罪犯亚文化,成为新时期监狱社会学的重要成果。社会学视角之外的监狱社会形象,虽然有一定的虚拟性,但其本质上却是现实的映射。尤其是高文、郭明等,如果没有切身监狱工作经验,也无法刻画出如亲临其境的罪犯生活场景和栩栩如生的罪犯形象,更不可能有对监狱惩罚和改造的深邃思考,他们在本土监狱社会研究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不同的研究路径,拓展了监狱亚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了范式解题功能。同时,众多学者对监狱生活场景的描述,是以罪犯为主角而展开的,尽管不同程度上关注了警囚互动,甚至专门从警囚互动的角度考察监狱问题,但是却并没有深入分析警察文化与罪犯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出作为特殊群体的警察的亚文化问题。仅仅通过罪犯生活场景看监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的现象。
四、范式扩张:“大监狱”范畴下的“科学共同体”
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了多个除监狱之外的监禁机构,包括农场、劳动教养所、未成年犯管教所、拘留所、看守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基于良法之治下“行为”(罪)与“处罚”(刑)之间的不均衡性的考量〔35〕,劳动教养制度于2013年被废除。近年看守所体制“不中立”、羁押程序不健全等问题引起了学界批评与社会质疑,但是由于本部门明显超过预期风险的利益,决定了公安机关并不具备移交看守所的强烈动机〔36〕,现行的看守所体制与监狱体制殊途同归。无论是劳动教养所、看守所,还是其他监禁机构,作为一种监禁实体,它们形成的文化现象是特殊性的也是普遍性的。不同的监禁机构或许因法律性质、地理区位、历史传承甚至气候变化不同而在文化现象上出现细微的差异,但是在其法定限制人身自由角度的监禁属性却有着相似性,因此也决定了它们在社会学意义上因监禁而生成的亚文化的相似性。可以说,劳教场所亚文化和公安监所亚文化研究,都是“大监狱”范畴下的“科学共同体”〔37〕。
(一) 劳教场所亚文化
劳教场所文化是其内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综合体,是主文化与亚文化的结合体。劳教场所主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是社会主文化在劳教场所的体现;劳教场所亚文化则通行于劳教人员内部,是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范、价值、习惯,是劳教人员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劳教人员整体法律意识淡、道德品质差、文化程度低,因此也决定了劳教场所亚文化层次的低劣性〔38〕。
(二) 公安监所亚文化
李记松借鉴了狄小华罪犯非正式群体的研究思路,从组织人际关系的角度指出,公安监所在押人员中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分歧,导致出现了监所亚文化和监所主流文化双重价值体系。非正式群体结构承载着在押人员亚文化,两者共同构成了在押人员群体生活方式中的非官方、无组织的一面,因此公安监所亚文化就是通行于监所在押人员群体内部特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同时,李记松与孙平持有相同的观点,即使用“监所亚文化”表达这一特殊文化形态,既突出监所的场域特点,也把监所外的被追诉人限定在研究对象之外〔39〕。
由于社会传统认知的误区,几乎所有的监所单位都会被划归为“大监狱”范畴,而其在实践层面更是存在着唇亡齿寒的关系。诸如2009年2月云南看守所的“躲猫猫”事件,不仅给全国监禁机构造成了沉重压力,也引起了社会对监狱的深刻误解〔40〕。在学术层面,诸如此类的公共事件和舆论危机,也事实上刺激了关于监狱、劳动教养所和看守所“狱霸”等亚文化现象的共同研究。监禁实体的一致性、研究对象的相似性、研究目标的统一性、吸收文献的同一性、话语交流的“可通约性”〔41〕等,表明了劳教场所亚文化和公安监所亚文化研究都是“大监狱”研究范式的独特范例,它们与监狱(罪犯)亚文化研究同属于托马斯·库恩范式视角中的科学共同体。
五、范式的不足:夹缝中成长的监狱警察亚文化研究
警察站在违法犯罪的对立面,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殊执法者,在社会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作为改善警察管理和推动警务变革的“文化软实力”的警察文化建设〔42〕,也成为众多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同时,与官方主导文化存在分歧、和警队制度规范存在一定冲突、和警察职业道德规范存在偏差或者相背离的警察亚文化〔43〕,也被一些学者关注。在监狱社会中,监狱警察伴随着监狱和罪犯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之长期共存。监狱警察和罪犯,自监狱社会诞生以来就同为监狱剧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监狱亚文化研究中对罪犯生活图景的张扬,背后却是监狱警察生活图景的忽略。尽管狄小华、孙平、宋立军等在描述罪犯生活场景中不可或缺地描述了警察的角色,甚至也把警察视为监狱亚文化的产生、存在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但是却并没有明确提出“警察亚文化”的概念。作为监狱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警察亚文化,虽然在范式演进路径中逐渐凸显,却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成为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的不足。
(一) 通俗的不良监狱文化
从经济学视角看,民警的“轻责重利”是一种不良监狱文化,实质上更是不科学的管理制度〔44〕。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想作祟则是监狱文化建设不足的原因。良好的监狱文化是一所监狱的“软实力”,不良的监狱文化会成为“虚实力”甚至是“反实力”〔45〕,不仅严重影响了罪犯的教育改造效果,还会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重要诱因〔46〕。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独辟蹊径分析监狱现象,虽然没有梳理出不良监狱文化与警察亚文化、罪犯亚文化的逻辑关系,但是把监狱警察作为不良监狱文化的主体并分析不良监狱亚文化之流弊,对于彰显监狱警察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人格化的警察亚文化性格
监狱警察文化是监狱警察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履行职责和使命中所体现出来的关于监狱警察的精神意识、职业行为与精神物化产品形态的总和。从文化“人格”化的角度,文化性格内化于文化之中。警察主流文化性格是居于主流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文化性格,渗透于监狱警察文化的各方面,比如队伍建设、树立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等,都融合着监狱警察独特而又鲜明的主流文化性格。监狱警察亚文化性格,是监狱警察亚文化的反映,比如面子文化和潜规则等性格文化是监狱警察亚文化性格典型的反映。监狱警察亚文化性格依附于监狱警察主流文化性格,但是对监狱警察主流文化性格却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47〕。
(三) 监狱亚文化的整合
连春亮在对监狱亚文化概念整合时,强调了监狱警察在监狱亚文化中的主体身份。他认为,广义的监狱亚文化应是与监狱主流文化相悖的所有文化现象,包括罪犯、监狱警察和监狱其他工作者三个主体所创造的亚文化,以及包括历史传承下来的社会关于监狱的亚文化。中义的监狱亚文化是指由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劳动教养所、看守所等监禁机构里罪犯所创造的与监禁机构主流文化相悖的文化等。狭义的监狱亚文化仅指监狱法所规定的监禁机构即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创造的亚文化现象〔48〕。“历史传承下来的社会关于监狱的亚文化”,应理解为是历史存在过和正在存在的社会意义上具有监禁属性的机构亚文化。如此,从场域和主体两个维度对监狱亚文化概念进行了整合,明确地把警察亚文化纳入监狱亚文化体系中:从狭义到中义,把《监狱法》意义上的监狱则扩大为具有监禁性质的监禁机构;从中义到广义,文化主体上把罪犯扩大到监狱警察和监狱其他工作者。广义上的监狱亚文化就无所不包了。虽然并没有对监狱警察亚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但是连春亮对监狱亚文化概念的整合,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罪犯亚文化”和“监狱亚文化”分歧所导致的范式危机。
(四) 作为“理性人”的警察与罪犯的亚文化互动
警察与罪犯都是理性的。监狱亚文化表现为包括罪犯和警察在内的监狱各类理性人私下奉行的与主流文化显规则相冲突、没有明确显性规范的各类潜规则。其中作为触犯刑律的特殊群体的罪犯,形成了有别于主流文化的特殊的罪犯亚文化;而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的监狱警察则由于工作环境闭塞、工作性质枯燥、工作压力大等,表现出如经济困扰与索贿受贿问题、个人晋升环节的隐性腐败、关系犯带来的执法困境等警察群体亚文化特征。这就是罪犯与警察、基层警察与领导之间,在无风险和有风险两种情形下出现的博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策略的选择〔49〕。李书金等不仅分析了监狱警察亚文化的具体表现,还从理性人博弈选择的角度通过监狱亚文化中罪犯和警察、警察和领导之间的互动清晰地呈现了监狱亚文化现象的生成过程,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斯·韦伯官僚制意义上的监狱架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孙平通过“对象”“形态”和“场域”三个维度完成了其“监狱亚文化”主体的构建,却把监狱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即警察群体隔离在外。除了刻意地限定研究对象范围之外,更多的或是有社会时代的原因。毋庸置疑,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亚文化,而作为典型的科层制的警察机构,强烈的自我保护主义及其不愿接受批评的传统,成为其坦承和自我检视亚文化的重要障碍。如前所述,在人的主体性普遍缺位的时代背景下,罪犯只能作为监狱的客体而存在。即便我们清晰明确了警察与罪犯共同作为监狱文化的主体,但是在彼时,需要权力的外在强制和被迫服从以及更需要理性认同基础上的自觉服从才能树立的警察权威〔50〕,这阻碍了其承担起亚文化主体角色定位的信心;在政治语境下,代表政府的由政治性和法律性双重属性框定的警察形象〔51〕,决定了其难以背负“亚文化”的“污名”。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不足的根源即在于此。
六、反思与展望:未来监狱亚文化图景
警察组织内部存在结构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警察认知和理念的不平衡〔52〕,证实了警察亚文化与警察越轨行为和腐败行为密切相关〔53〕。而顽固的警察亚文化已经成为警务改革的重大障碍〔54〕。同时,监狱作为官僚制机构所具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天然短板〔55〕,以及警察官僚作为人处于权力、法律、关系、利益等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中惯习生成的监狱执法者“隐规则”〔56〕,必然会随着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而逐渐进入管理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夹缝中成长的监狱警察亚文化研究揭示的监狱警察身份从“强势主体”到“亚文化主体”的变化、警察与罪犯之间从“文化互动”到“亚文化互动”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发展,更展现了监狱法治化进程中监狱工作者自我审视的勇气。当然,国内关于警察亚文化的研究早已展开,而当有研究者把检察官、法官、监狱里的司法警察和律师等看作是与警察职业最相近的司法执法者,从而把监狱警察等排除在警察亚文化研究对象之外时〔57〕,监狱警察亚文化研究则游离在监狱亚文化研究边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这也不能不说是监狱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遗憾。
监狱绝大多数的规章制度之目的在于便利监禁工作开展从而维护监狱秩序,而非保护警囚不受伤害〔58〕,监狱社会关系在罪犯与监狱警察之间也总是呈现出分裂与制衡并存并最终持续稳定的状态〔59〕。因此,监狱亚文化是罪犯和警察互动——通过权力和制度的“合作”而形成的。无论是罪犯,还是警察,都受构成监狱亚文化的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和机构运行的影响〔60〕。罪犯亚文化既与罪犯主文化共存,也受制于包括罪犯主文化在内的监狱主文化。而警察亚文化不仅受制于警察主文化,甚至也受制于罪犯主文化,比如罪犯觉醒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助推国家力量纠正了警察暴力执法现象。警察亚文化关系到罪犯的监狱适应问题和罪犯“监狱烙印”的生成与消解问题,因此也正在影响着罪犯亚文化〔61〕。这些复杂的关系证实了罪犯亚文化与警察亚文化的共生共存,也要求监狱领导者和研究者要持续地关注:在罪犯因为获得了“好处”而非常愿意遵守监狱的各种规章甚至与警察合作时〔62〕,是基于合理的制度还是警察亚文化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在警察与罪犯冲突导致警察处于执法风险时,是根源于警察个体,还是罪犯亚文化,抑或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制度;在部分罪犯亚文化现象影响力趋于缓和,而警察亚文化现象影响力越来越强时,如何防止警察利用影响力强迫或诱导罪犯接受他的亚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诸多的问题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宏观上,监狱的研究与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域中加以考察〔63〕;微观上,监狱中的两个主体也时刻处于冲突之中,同时也时刻处于互动之中〔64〕。因此,在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意义上,无论如何都要求我们深刻把握警察和罪犯两个群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构建。不把警察亚文化和罪犯亚文化割裂开来,既是理论研究的要求,也是实践的要求。
笔者认为,从文化主体的角度上,监狱文化由监狱警察文化和罪犯文化组成,监狱亚文化由警察亚文化和罪犯亚文化组成;罪犯亚文化是罪犯与罪犯、罪犯与警察之间在监狱环境下互动的结果;警察亚文化是警察与警察、警察与罪犯之间在监狱环境下互动的结果。从价值取向上,监狱文化由监狱主文化和监狱亚文化组成,监狱主文化符合社会主文化潮流,是社会主文化的一部分;监狱亚文化不符合社会主文化潮流,是与社会文化价值存在差异、与监管官方意志相对立的文化。因此,监狱亚文化是指监狱文化主体即警察和罪犯在监狱环境中为逃避官方规制、谋取制度外利益,在警囚互动中形成的与监狱官方意志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罪犯亚文化是指在监狱环境下罪犯为逃避惩罚、谋取制度外利益,在囚囚互动和警囚互动中形成的与主流价值观和监狱官方意志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监狱警察亚文化是指在监狱环境下警察为逃避管理、谋取制度外利益,在警警互动和警囚互动中形成的与主流价值观和监狱官方意志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见图1“监狱文化的构成”和图2“监狱亚文化的形成”。

图1:监狱文化的构成
纵观国内监狱亚文化研究历程,贯穿其中的关于监狱“文化剧”和“亚文化剧”的“剧作家”和“剧中人”为何的问题,成为左右监狱亚文化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引发了自身的范式发展。相比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理论范式、研究视角等都已经相当成熟和系统化的西

图2:监狱亚文化的形成
方监狱社会学,国内的监狱社会学研究发展较为缓慢,在研究主题内容、研究对象上都呈现碎片化状态〔65〕,对监狱文化的研究体现在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上也是由于过于宽泛而长期悬空未置〔66〕。回顾历史,从亚文化的角度对监狱社会中的罪犯群体的关注,已基本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罪犯生活图景,而未来的中国监狱亚文化研究范式不仅要包括罪犯亚文化研究,还要包括警察亚文化研究,帮助我们看清警察在监狱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但要防止人们在尖锐而负面地批评、指责警察中祛除警察的人性,而且要防止那些毫不置疑的支持性的陈词滥调的颂扬〔67〕——从而通过完整的监狱警察生活图景和罪犯生活图景展示完整的中国监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