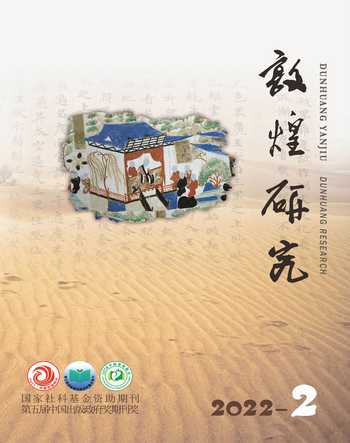浅析敦煌无明代开凿石窟及绘塑遗存的原因
韩冰 汪正一 宋利良


内容摘要:敦煌从明朝取得河西到清康熙经略西域复建敦煌340余年间,主要处于明朝置卫间接管控时期(1372—1516)和吐鲁番政权统治的“后明时代”(1516—1715)。明控关西七卫时期,特殊卫所治下敦煌石窟还略见礼佛朝拜活动,吐鲁番统治时期因人口迁徙和宗教信仰的改变,敦煌石窟未见任何营建活动,形成了敦煌莫高窟较长时间无营建的空窗期,也结束了千年莫高窟营造开窟的历史,本文通过对明代敦煌地区政治、经济及宗教信仰情况的梳理,讨论莫高窟没有明代开凿石窟绘塑遗存的原因。
关键词:明代;敦煌石窟;政治经济;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K234.1;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2-0115-10
On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no Remains of Caves, Statues,
or Painting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t Dunhuang
HAN Bing1 WANG Zhengyi2 SONG Liliang3
(1. Institute of Ar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2.Editorial Department,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3. Digit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Between the time when Dunhuang captured the Hexi reg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time when Emperor Kangxi of the Qing dynasty managed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rebuilt Dunhuang, there was a span of more than 340 years when Dunhuang was either under the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Ming dynasty wei (Ming military garrisons, seven of which were established west of the Jiayuguan Pass between1372and 1516) and direct control of the Turpan regime (1516-1715), also known as the "post-Ming dynasty."Whe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garrisons, some pilgrims still came to visit Dunhuang caves, but when ruled by the Turfan regime, Dunhuang saw no cave construction due to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 This long break in cave building effectively put an end to over a thousand years of cave construction at Moga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no remains of Ming dynasty caves, statues, and paintings at Mogaoby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conditions in Dunhua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Ming dynasty; Dunhuang caves; politics and economy; religious belief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地區自冯胜取河西以后,主要处于明朝置卫所间接管控时期(1372—1516)和吐鲁番政权统治后明时代(1516—1715)。明朝前期通过册封当地游牧蒙古后裔间接管理敦煌等地,先后在嘉峪关以西的敦煌及周边设立了关西七卫(关外七卫)军事卫所(图1),卫内部落酋长及子民均被纳入军籍,隶属于肃州卫统辖,形成隔绝西部威胁的缓冲屏障,在明朝经略西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和罕东卫地属或部分居古敦煌郡内,沙州卫及后续罕东左卫治所沙州。最终明迁七卫部众内附,敦煌遂没于吐鲁番政权统治之下。明代敦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历史和军制等内容[1],明代敦煌无新开凿佛教石窟的原因尚无专门讨论,仅数篇围绕明代游人题记的论文给予关注。在此笔者不揣冒昧,试从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方面,探讨明代敦煌无佛教石窟绘塑遗存的原因。
一 敦煌石窟时代划分无明代
敦煌石窟是指古敦煌地区以莫高窟为主,含周边榆林窟等八个佛教石窟群的总称。敦煌石窟时代划分的下限,各重要出版物中均为元代。如工具书《敦煌学大辞典》(简称《辞典》)“敦煌石窟”词条:“在古敦煌郡、晋昌郡(瓜、沙二州)就岩镌刻之佛教石窟寺……其中,莫高窟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自前秦始,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连续修凿,历时千年)……”[2]正如胡同庆先生所述,“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下限是元代”[3]。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敦煌石窟群时代下限止于元代为大家所认可,“元代的莫高窟佛教艺术,犹如灿烂的晚霞,由于明代的封关,敦煌被置于关外,继之而来的是莫高窟艺术发展史的终了”[4]。胡同庆先生《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下限》一文列举敦煌石窟清代、民国改修、新修遗存,纠正了敦煌石窟艺术时代下限止于元代之说。笔者赞同胡先生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前贤“敦煌艺术实际结束于元代”说法,更准确点应该说是敦煌石窟的开凿时代划分止于元代。从《辞典》“莫高窟”词条后附《莫高窟现存洞窟始建、重修及其他情况一览表》中又于蒙元时期之后,添加了清代时期、民国前期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另有部分出版物将敦煌石窟时代划分为北凉……元、清和民国,明代还是被忽略了,前述胡同庆先生论文,同样略过了明代,仅仅提到敦煌石窟中存有几条明代游人题记。从实地调查看,敦煌石窟中确实尚未发现明代营建的洞窟,新制作的壁画、彩塑和建筑遗存。《莫高窟大事记》明确说:“明永乐二年,置沙州卫,1516年敦煌陷于吐鲁番。元以后海上丝路兴起,路上与西域交通路线亦换,敦煌经济交通枢纽地位尽失;莫高窟自此未再开凿新窟,明代以后更形荒凉,敦煌遂走入历史的黄昏。”[5]那么,明代敦煌石窟中留下了哪些历史痕迹?
二 敦煌石窟中的明代遗存
敦煌石窟的开凿到了元代进入晚期。《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只粗略地划分出莫高窟元代有“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和宕泉河东岸的几座塔”[6],榆林窟有第4、27窟,东千佛洞第6窟等。而且其中的莫高窟第3、465窟目前多数观点认为是西夏石窟。另元代曾对莫高窟18个洞窟、榆林窟9个洞窟予以重修。“元代时期敦煌佛教十分衰微,只是在十四世纪中叶一度兴盛。当时西宁王速来蛮坐镇敦煌……他还重修火焚后的皇庆寺(今第61窟)”[7]。到明代前期设卫间接控制敦煌地区时,“莫高窟在明代没有开窟和绘制壁画,只有几条游人题记……敦煌艺术实际结束于元代,即十四世纪”[7]。
关于明代敦煌石窟,伯希和记录“第12号洞”(现莫高窟第150窟):“至于塑像,我推测与修复的年代一样都属于18世纪。前厅和过道的画面好像与两侧壁画上新加上的画面同属于一个时代,因此可能是明代的。但无论如何,其年代不会更早。”[8]汪正一、赵晓星曾撰文专门讨论莫高窟第150窟前厅和过道后修壁画与主尊彩塑,认为这些内容共同组成地藏十王信仰并属同一时期,为清代遗存[9]。另苏莹辉先生认为“在莫高窟里,只有一个白衣观音洞,似为明代所作”[10]。苏先生所指“白衣观音洞”应该是莫高窟第3窟,此窟开凿和绘制年代目前有西夏、元两种说法,窟内有题记“甘州史小玉笔”,又莫高窟第444窟“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史小玉到此”题记,可以判断第3窟最晚为元代,不可能为明代所作。
目前敦煌石窟中可以确定的明代遗迹只有几条游人题记,这些题记的作者中,有6人是在1516年以前的明控时期前来巡礼的游历者,并以明朝派出的安夷官兵为主。题记相关研究参见王力平《莫高窟汉文游人题记史料价值探析》;陈光文、郑炳林《莫高窟、榆林窟明代游人题记研究》;公维章《明代的敦煌佛教》,此不再赘述。
三 明代敦煌之政治环境与卫所军制
明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西路军攻甘肃河西,傅友德所部远及瓜、沙等地。可以确定的是,敦煌地区最晚在明洪武六年(1373)还在北元控制之下。莫高窟第465窟有 “宣光三年凌住罕到此”游人题记,宣光三年(1373)为北元元昭宗之年号,即明洪武六年。冯胜攻取河西,豳王“元肃州路守臣掠其人马遁去沙漠”[11],“太祖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置不问”[12],不得已“乃以嘉峪关为限遂弃敦煌”[13]。不仅嘉峪关西如此,整个河西袭蒙元时期游牧旧制,如《甘肃镇战守图略》载:“自兰州至肃州,一千五百里,皆屯兵据守,外控番夷,兹地久沦于夷,自金城以西不能复为郡县。”[14]河西地区只能建立起卫所军兵屯田守戍,无纳税郡县。洪武时曾多次用兵关西,形成拉锯战。据《明史·西域二》:“(赤斤蒙古卫)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讨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还,后复为蒙古部人所据……”[15],沙州则是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控制。嘉峪关西明军退走,蒙古游牧部落复回敦煌,敦煌继续为游牧部落所据(图2)。可见明前期弃敦煌之地于关外,实属无汉地居民可领的无奈之举。
明朝最大威胁是北元各部,“今之四夷北虏为急”[13]44,长期的军事对抗构成了明代北方绵延万里的九镇(九边)防御格局。九镇之中,甘肃镇以通道狭长,路程遥远,但又具有隔绝南羌北胡的战略地位,“以守之难易论……甘肃尤难。……甘肃孤悬天末,四面受警也”[12] 485。明朝效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15]8549,然与汉武时国力强盛,移民实边以控西域不同。明廷对西域战略采取守势,政策上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置番卫,御蒙古,和诸藩。河西的防御战线狭长,补给困难,面对的外部势力也最为复杂。明洪武中、后期虽在河西屯田设卫,移入军士户民十数万众,然经历蒙元驻牧统治,建立于元末战乱和动荡之后的甘肃镇,镇内人口稀疏,民族关系复杂。经营异常艰难,恢复定居农耕尤为缓慢,河西走廊人口及农业经济等很难维持甘肃镇及以西用兵的军需供給,建立的偏远卫所实有军额远少于应有军额,边远军需还得以惠商盐引“开中制”来增加供给[16]。
明太祖、成祖时,为建立与甘肃镇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完备边境防御体系,剿抚并举经略哈密、沙州,招抚番酋各部置卫所,以策应肃州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藩篱”[15]8566。于嘉峪关西先建置维持七个番部军制卫所,隶属于肃州卫,形成军民一体的藩篱军卫“关西七卫”[17]。明代前期,关西七卫作为屏蔽西域的藩篱,隔绝西部威胁的缓冲屏障,起到了一定的预警、护卫的积极作用[18]。特别是明军事强盛的初期,关西诸卫以西域要冲哈密为诸番领袖,御防吐鲁番西域各部,维护贡路畅通,护持使节,在明朝经略西北的战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卫所制度是一种军制,分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由指挥使统领。卫所统兵为世兵制,纳入卫所居民成为军户,享受固定房舍、田地和口粮,不承担徭役,战时为兵,平时屯田,自给自足。关西七卫即是招抚设置的部落卫所,居民实际为“职业军人”。加之边关重戍轻屯,训练和屯田为多,自由度受限,遂使宗教活动减少。自洪武初置曲先卫始,到嘉靖闭关前后几次迁徙诸卫部众内塞,明廷间接管理关西古敦煌之地150余年。陈洪谟《继世纪闻》卷六载:“肃州外为嘉峪关,关外蛮夷各因其种类建卫……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无事。”[19]嘉峪关以西七卫的设立,极大地减轻了明甘肃镇的守御压力,“诸夷酋长仍封其爵,第令之受我节制,永为外臣,使西戎、北虏两不相通,则边陲可永无虞,而国家之固如磐石矣”[20]。
但外浸内耗双重作用下,七卫内部并不太平。明关西七卫以哈密卫为诸番领袖,永乐二年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若哈密之失守……蔓延至于西宁,使一带地土不得耕种,士民不得安业,直抵洮岷,颇难制御。”[13]45-46可见敦煌关西诸番卫所关乎西北、西南之守御。关西七卫在宣德正统以前还算和谐,正统年间瓦刺也先盘踞北方,关西七卫经营形势急转直下,七卫各部间嫌隙日多,御外不能同体协作甚至发生内讧。兵部尚书于谦言“赤斤诸卫久为我藩篱,也先无故召降结亲,意在撤我屏蔽”[15]8557。又经土木堡之变,大明军力削弱,明廷勉强延续对北方的守成战略,关西七卫时有互掠人畜财货、贡物之事,亦有部落内部叛乱、仇杀,各为私利(表1)。明廷切责,安抚调停各部,命退还所掠,终或从或不欲。可知朝廷对关西七卫的控制管理大不如前。到明正德时又有鞑靼小王子攻占河套、骚扰北镇,南方藩王叛乱,亦无暇西北,关西七卫又常为吐鲁番所侵掠。
正统时北方瓦刺也先统一蒙古各部,兵围哈密,俘走哈密忠顺王母亲,侵扰沙州等卫。沙州卫不能自立,正统十一年,迁沙州卫居甘州,此为关西七卫部众内迁之始。“沙州先废,而诸卫亦渐不能自立,肃州遂多事”[15]8562,莫高窟第77窟所见正统十二年两处总兵题记,可能正是其迁沙州部众时游历莫高窟所留。明成化间,吐鲁番势大,多次进扰关西七卫,哈密卫几次为吐鲁番攻占[22],莫高窟和榆林窟也留下了明军军士于成化十三、十四、十五年书写的三条祈愿题记,其中有“安攘夷人”“为国安藩篱”等言辞。到正德八年时,哈密忠顺王拜牙弃哈密,投吐鲁番。哈密遂为吐鲁番所有,成为其兵犯河西肃州的前沿。至此关西七卫诸部残破不堪,并陆续内迁河西驻牧。明嘉靖七年夏,罕东左卫乞台部下帖木哥、土巴率居沙州地部众来归,关外七卫之地遂全部没于吐鲁番,“由于明朝消极治边政策的影响、七卫间的内讧对七卫力量的削弱及明廷对七卫受到外敌威胁时支持不力等原因,导致明廷对西北边境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结果‘嘉峪关外,皆为寇境’”[23]。
四 明代敦煌之经济情况与屯田农牧
明控制关西七卫150年间,政治上建立了隶属关系,军事上设置自主的防御军卫机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明代“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12]594,明朝廷与之保持较长时间的贡物贸易,以此怀柔羁縻安定西域。这些贡物贸易多途经哈密、沙州等地,间接促进了当地的商贸活动。明廷北线九镇防御所需军马甚多,亦通过茶马互市换取马匹。关西七卫部众多过着游牧生活,茶叶是其生活的必需品,“非茶则郁闷不解”[21]563。明廷与关西七卫之间茶马贸易频繁,也凸显出关西七卫部众居民对于明廷的依赖,其逐草而生的游牧或半耕半牧生产、生活方式,依然延续传统旧俗没有改变,若遇饥荒还需要明廷接济。
沙州卫:1. 宣德元年,困即来以岁荒人困,遣使贷谷种百石,秋成还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贷为?”命即予之。2. (宣德七年)又奏旱灾,敕于肃州授粮五百石。3. (宣德十年)乃率部众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陈饥窘状。诏边臣发粟济之,且令议所处置。
赤斤蒙古卫:(正统九年)又以其饥困,令边臣给之粟,所以抚恤者甚至。
罕东左卫:(成化)二十一年,甘肃守臣言:“北寇屡犯沙州,杀掠人畜。又值岁饥,人思流窜。已发粟五百石,令布种,仍乞人给月粮赈之。[15]8556-8565
明代河西乃至关外七卫,一直无法建立起正常的郡县,边地卫所重戍轻屯成为常态。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朝在河西的统治有莫大的关系。元忽必烈时期,察合台汗国所部出伯、哈班兄弟东归投于忽必烈麾下,驻牧河西。后出伯进封豳王,并逐步形成镇戌河西的豳王家族[24],此家族对元代以后的敦煌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在敦煌敕封建立的卫所,其部落管理者大多出自此蒙古豳王家族后裔[25]。《元史》中涉及敦煌的史事多为军屯,移军农耕屯田虽也取得一定成效,“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26],但诸王分封游牧性质没有改变,军屯因战调防,时而徙民复业罢屯。至元二十年“河西官府参用汉人。徙甘肃沙州民户复业”[26]258,瓜州“……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26]1451,二十九年 “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26]366,成宗时“给瓜、沙之民徙甘州屯田者牛价钞二千六百锭。……元贞元年……罢瓜、沙等州屯田”[26]385-390。
敦煌地处干旱区,水资源匮乏。蒙元北地承袭旧俗,保持游牧生活,中原南地则行汉法。敦煌旧为察合台汗国属地,承袭北方旧俗驻牧。《元史·武宗紀》:“诸王出伯言:‘瓜州、沙州屯田逋户渐成丁者,乞拘隶所部。’中书省臣言:‘瓜州虽诸王分地,其民役于驿传,出伯言宜勿从。’”[26]483豳王出伯驻牧河西,曾想采纳旧制,乞拘丁隶部,为朝廷所拒。
瓜、沙等地时常发生饥荒,如至元十八年五月“甲辰,遣使赈瓜、沙州饥”[26]231。至元二十二年“敕朵儿只招集甘、沙、速等州流徙饥民”[26]277。不仅河西边陲的敦煌如此,河西走廊地区较为集中的农业区,为诸王贵族所占有者亦为驻牧草场。到蒙哥汗死,诸王汗位之争,河西兵火年年,民户逃亡,农桑之地满目疮痍,至元二十七年(1290),“(肃州路)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26]1450。待至元末明初,河西耕田水利毁坏甚剧,农桑孱弱,人口稀疏。
从敦煌石窟的营建历史看,石窟开凿与当地经济密切相关,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不可能营建洞窟的。元末敦煌人口和经济的凋敝,直接影响到洞窟的营建,并将这一问题遗留到明代。明时敕封游牧部落置卫,水利毁坏、不善耕种尤甚之前,未有改善。
涉及明代关西七卫农耕生产活动的记载很少,零星记载亦不具体。明陈诚《西域行程记》载,出嘉峪关后,西行去哈密,过古敦煌郡内赤斤和卜隆吉见有农耕种田。“城南山下有夷人种田,城西有溪水北流,地名赤斤,安营。……有夷人种田处,富水草,地名卜隆吉,安营”[27]。关西七卫仅沙州卫耕种条件较好,“居沙州三十余年,户口滋息、耕牧富饶,皆朝廷之力”[15]8560。但当北方部族强大时,“方前时甚富庶,赖为中国藩篱,近因吐鲁番劫杀抢掠,部落亦各散亡,贫困不能自存”[21]564。明廷支援农耕种子,“遣使贷谷种百石” “已发粟五百石,令布种”,仅解一时饥困。“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种,离城堡远者弃之,恐达子卒至抢虏人畜。虽云春耕秋收之时有人马护之,亦虚文耳,不能济事。其地专靠水利,近来水利甚微,不能浇溉,说者以为势豪占夺。虽不占夺,其利亦微,不可全归咎于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赐不调,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饥色,又加以西夷北虏劫杀数次,客兵主兵,不时住剳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21]565。河西甘肃镇和关西七卫,在外部敌对势力微弱时,还能一体应对,当外在威胁强大时,即使有来自明廷的支持,但也很有限。
总之,嘉峪关外的关西七卫,因其卫所军事机构性质,卫内又延续传统蒙元时游牧或半耕半牧生活模式,加上河西特殊的自然条件,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耕经济落后。每有外来侵夺,即饥困潦倒不能自立。明代敦煌的贫乏凋敝,使得石窟的开凿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条件。
五 元代以后西北地区汉传佛教的衰落
8世纪中叶,随着穆斯林军事力量往东扩展,伊斯兰教来到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脱黑鲁儿汗不扎儿信奉伊斯兰教,投降了蒙古。“随着蒙古帝国铁骑的不断东征西讨,大批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徙到中国境内,他们被统称为‘回回’,回回主要包括士兵和工匠,他们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并使之兴盛一时”[28]。元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伊斯兰教有了长足发展,元廷设立了“回回掌教哈的所”专管穆斯林宗教事务[29]。蒙元成吉思汗时将广阔的土地分封,形成相对独立的三个兀鲁思,其中伊利合赞汗改奉伊斯兰教并获得元成宗铁穆耳认可。
《马可波罗行记》载,元时敦煌“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这是元代社会多元宗教并存的真实写照。马可波罗所记敦煌偶像教有“偶像食肉”这一特点,说明此时是藏传佛教。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晤,推崇藏传佛教。驻牧敦煌的豳王系蒙元黄金家族后裔,同样以藏传佛教徒自居。敦煌元代开凿的洞窟及出土文物也多是藏传佛教内容,如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图3)。“元代伊斯兰教在内陆主要在穆斯林内部流传,但西北边陲却是例外。元初,伊斯兰教以喀什为中心向天山南北发展,……后期东察合台汗国国君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属下十六万人皈依伊斯兰教,他的后裔发动‘圣战’传播伊斯兰教,迫使异教徒改宗,十六世纪伊斯兰教风靡天山南北”[28]371。到明代,西北伊斯兰教传播广泛,甘肃省博物馆藏有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长老的“阿文铜香炉”(图4),以及装帧书写精美的彩绘泥金手抄《古兰经》一部,这些文物也间接说明伊斯兰教在西北的流行。驻扎肃州、哈密的豳王家族即为察合台汗国同系子孙[30]。明廷剿抚并用,招抚关外诸王纳入卫所制下,其部众信仰伊斯兰教也就顺理成章。明内务府绘绢本青绿山水图手卷《丝路山水地图》,图中蒙古赤斤卫内有“回回墓”地名(图5)。《甘肃镇战守图略》则记“嘉峪关西八十里为大草滩,其地广而多草,滩西四十里为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冢,故名”。可见伊斯兰教已传播到了关西敦煌等地。
关西七卫一体同宗,明置关西七卫各族番酋首领,多出自察合台系豳王出伯、安定王家族后裔[31],部众族属及宗教信仰也大体相仿,其中赤斤蒙古卫、罕东卫、沙州卫、罕东左卫统领部众属蒙古族、西番族和藏族,哈密则以回族、畏兀儿族和蒙古族杂居。
关西七卫中,哈密卫相关史料较为丰富。明陈诚《西域番国志·哈密》载:“(哈密)蒙古、回回,杂处于此,衣服礼俗,各有不同。”[32]波斯沙哈魯使团成员盖耶速丁于永乐年间(1419—1422)来到中国,其所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录吐鲁番、火州、哈密等地的见闻:
(吐鲁番)这个城镇的大部分居民是异教徒,崇拜偶像。他们有极美丽的大偶像寺庙,其中有很多偶像,一些是新塑的,另一些是旧的。坛前有一尊他们称为释迦牟尼的大佛像。
……他们在拉扎卜月19日,他们抵达一个叫做苏菲阿塔的地方。帖尔美兹的一个赛夷,名叫阿克完德—扎答·塔术丁,在那里建有一座济贫院,并在那里定居。他是柯模里穆斯林的长官爱迷儿·法合鲁丁的女婿。
在拉扎卜月21日,他们抵达柯模里城(哈密)。爱迷儿·法合鲁丁在此城中建筑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面对着它,他们筑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其中有一尊大佛。……曼格利·贴木儿·贝叶里,一个极英俊的青年,是柯模里的长官。
……直到他们在沙班月12日抵达一个经沙漠到肃州有十日程的地方,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城市及他们的军事前哨。许多中国官员奉皇帝的命令前来欢迎使节。这是一个欢快的草地。……[33]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永乐年间的哈密城中不仅有宏伟的清真寺,也有管理穆斯林的官员,还有规模宏大、艺术精美的佛教寺院,可见此时的哈密信奉多种宗教。明初“因为哈密佛教信徒众多,明朝于1409年(永乐七年)特设哈密‘僧纲司’,专门管理当地的佛事”[34],哈密卫宗教依然以藏传佛教为主。但15世纪中叶继承忠顺王的到瓦答失里,又名哈力锁鲁檀,可知他已是伊斯兰教徒。弘治十八年(1505)陕巴卒,子拜牙继嗣为忠顺王,拜牙自称速檀,亦信奉伊斯兰教。后拜牙逃奔吐鲁番,哈密遂没于吐鲁番。到明嘉靖时朝议是否闭关绝贡,恢复哈密藩篱时,桂萼《进哈密事宜疏》言回夷“只礼拜天地,不信佛教”[21]563。
关西七卫之一阿端卫的相关史料也能反映一些情况。据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拉失德史》记载,东察合台汗国信仰伊斯兰教的贵族赛德汗对撒里畏兀儿人进行宗教战争,并攻掠了阿端卫,由于“阿端卫的首领和部众中已有伊斯兰教徒,他们主要已不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赛德汗的军队班师时才会说:‘根本没看到或听到任何有关异教徒的情况。’”[35]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崇信和极力推广下,天山南北地区大多皈依伊斯兰教。明嘉靖时,吐鲁番政权占领古敦煌地区,伊斯兰教已完全控制了嘉峪关以西地区,此时的莫高窟,“回人蹂躏,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掩”[36]。
六 小 结
明控关西七卫辖区内的大小石窟均于明代停止了开凿活动 。明廷以夷制夷的策略下,敦煌形成了特殊的半牧半耕的卫所体制。在外部侵掠、内部消耗之下,军户屯田经济落后,人口凋零,石窟开凿活动失去了经济基础。后期明迁七卫部众内附,敦煌遂没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吐鲁番政权统治之下。吐鲁番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其不作偶像的特性,最终使敦煌石窟寂没于戈壁荒野之中,渐被遗忘。
参考文献:
[1]胡小鹏,程利英. 1978—2003年间明代西北政治史研究概况[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4):135-143.
[2]季羡林,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8-13.
[3]胡同庆.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下限[J]. 敦煌研究,1992(4):31-48.
[4]孙修身. 蒙元敦煌石窟艺术[M]//季羡林,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44.
[5] 荒漠传奇·璀璨再现——敦煌艺术大展[M]. 台南:台南艺术大学,2005:398-399.
[6]史苇湘. 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36.
[7]王惠民. 十年来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与研究[M]//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70.
[8]伯希和.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61.
[9] 汪正一,赵晓星.敦煌莫高窟第150窟清代遗迹考察[M]//周天游,主编. 再获秋实——第二届曲江壁画论坛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5-309.
[10]苏莹辉. 敦煌壁画石室发现对中国绘画之影响[M]. 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艺术·第11辑·艺术篇. 新北:正中书局,1966:1-11.
[11]曹学佺. 大明一统名胜志·陕西名胜志(卷之十三)[M].刻本.[出版地不详]:曹学佺自刻,1630(明崇祯三年):3-4.
[12]查继佐. 罪惟录·哈密(列传卷三十三)[M]//续修四库全书:第3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4.
[13]魏焕,编集. 皇明九边考·甘肃镇:卷第九[M]//中华文史丛书:第15册.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350.
[14]佚名. 甘肃镇战守图略·西域土地人物略[M]. 彩绘纸本册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年间.
[15]张廷玉.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8556,8559.
[16]张磊,杜常顺. 明代开中制在河西走廊的实施及其社会影响[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85-91.
[17]唐景绅. 明代关西七卫述论[J]. 中国史研究,1983(3):59.
[18]程利英. 明代关西七卫作用浅析[J]. 贵州民族研究,2006(4):197-200.
[19]陈洪谟,撰. 继世纪闻: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97:110.
[20]罗日褧,著. 咸宾录·西夷志卷之三[M]. 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71.
[21]陈子龙,等,编. 皇明经世文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4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625.
[22]田澍. 明代哈密危机述论[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4):14-22.
[23]纪宁. 明代关西七卫残破原因初探[J]. 青海民族研究,2011(1):120.
[24]楊富学,张海娟.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2):21-35.
[25]胡小鹏. 察合台系蒙古诸王集团与明初关西诸卫的成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85-91.
[26]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514.
[27]陈诚,著. 西域行程记[M]. 周连宽,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0:33-34.
[28]常和平,编. 中国全史·宗教史(简读本):第13册[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366-369.
[29]胡小鹏. “回回”一词起源新探[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57-62.
[30]胡小鹏. 哈密卫忠顺王脱脱身世及相关问题考释[J].民族研究,2010(4):84-89.
[31]程利英. 明代关西七卫探源[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4):45-49.
[32]陈诚,著. 西域番国志[M]. 周连宽,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0:112.
[33]火者·盖耶速丁,著.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M]. 何高济,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6-107.
[34]魏长洪. 西域佛教史[M].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184.
[35]钱伯泉. 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J]. 西域研究,2002(1):25.
[36]佚名. 敦煌县志[M]//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一辑第48卷). 兰州: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