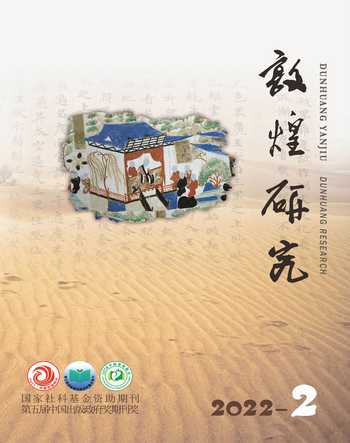“敦煌”得名考原
杨富学 熊一玮






內容摘要: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学界给出了多种解释,或汉语,或藏语,或羌语,或吐火罗语,众说纷纭,长期为学界公案。综观西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前著于史册的五个早期地名——合黎山、黑水、祁连山、焉支山、敦煌,其中四个大体可以确定都属于突厥语,即合黎= Qara,意为“高”,合黎山意为“高山”,黑水= QaraSu,意为“清亮的水”,祁连= Tngri,意为“天”,焉支(胭脂)= y?覿ngg?覿,意为“嫂子”,同于匈奴单于夫人“阏氏”和今天维吾尔语嫂子y?覿ngg?覿。从史书遗留的当地民族的词汇看,先后生活于敦煌一带的月氏、乌孙、匈奴所操的语言皆为突厥语。说明彼时河西为突厥语分布区,从大概率讲,“敦煌”之名亦应为突厥语。突厥语中有tawuz一词,意为“瓜”或“西瓜”,敦煌古以产瓜闻名,在相当长时间被称作瓜州。将敦煌解释为突厥语tawuz的音译,或许更接近敦煌地名起源之真义。敦煌原为区域名称,以产瓜闻名,后因作为敦煌郡治而特指敦煌绿洲。
关键词:月氏;匈奴;吐火罗语;突厥语;瓜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2-0105-10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Place Name“Dunhuang”
YANG Fuxue1,2 XIONG Yiwei1
(1.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2. Division of Humanities Research,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There are many views on the meaning of “Dunhuang” among academics today that differ if the analysis assumes that this name has its source in Chinese, Tibetan, Northern Qiang, or Tocharian language. This long unsolved mystery can be elucidated by looking at the five early place names that existed before Emperor W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four prefectures of Hexi. They are Heli Shan(Heli Mountain), Heishui (Black Water), Qilian Shan(Qilian Mountain), Yanzhi Shan(Yanzhi Mountain), and Dunhuang. Four of these can be confirmed to derive from the Turkic language: Heli, or “Qara,” means “high,” and Heli together with Shan refer to high mountains; Heishui, or “QaraSu,” means “clear water;” Qilian, or means “sky;” and Yanzhi, or “,” means “sister-in-law,” which refers to the queen of the Xiongnu people and is still used in modern Uighur language. Judging from what can be seen i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nguage used by local people, the ethnic groups that successively lived in Dunhuang, including the Yuezhi, Wusun and Xiongnu, all spoke ancient dialects of Turkic. This indicates that Turkic w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system in the Hexi region at that time, and therefore the name of “Dunhuang” is likely derived from Turkic. The word “tawuz” in Turkic means “melon” or “water melon,” and Dunhuang was famous for producing melons in ancient times and was even known as Guazhou(“region of melons”),for a long time. To explain Dunhuang as a transliteration of the Turkic word “tawuz” seems closer to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name of Dunhuang. “Dunhuang” was first the name of an area famous for producing melons and was later used to refer to the Dunhuang oasis region that served as theseat of Dunhuang Prefecture.
Keywords:Yuezhi; Xiongnu; Tocharian; Turkic; mel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注中说:“敦,大也。煌,盛也。”[1]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更是明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2]显然,这都是单纯地从字面上解释敦煌的含义{1}。如所周知,敦煌这个名字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就已存在,彼时当地尚无汉人,何来汉语地名呢?再说,“敦煌”一名在历史文献中又写作“炖煌”“焞煌”“燉煌”甚或“敦薨”,与汉语地名的命名习惯殊异。一般而言,汉语地名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不可随意用同音字替代,而非汉语地名则不同,其名多出自音译,故用同音字替代现象多见。如吉林省的敦化,意取《禮记·中庸》“大德敦化”。如果像敦煌那样将“敦”字改为“炖”,其地名岂不成了“炖而化之”之意吗?从敦煌取名用字的不统一,抑或可窥见“敦煌”一名非汉语欤。
那么,敦煌一名到底为何意呢?学界曾提出多种说法,一者认为“敦煌”是“吐火罗”的音译,二者认为是“桃花石”的音译,三者认为来自羌语,四者认为来自伊朗语,五者认为来自月氏语,六者认为来自突厥语。说法不一而足。敦煌一名的来源,对于探讨敦煌的历史文化又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拟从早期河西突厥语地名、早期河西突厥语部族和敦煌名称之由来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冀以探明“敦煌”一名的来源与含义。
一 河西早期地名多为古突厥语说
我国古代北方地区存在着一种语言——原始突厥语,从现存语素判断,时代最早者当首推匈奴语[3]。此外,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丁零人也很有可能操的是原始突厥语。后来经过逐步发展,至北周、隋唐时代形成了完善的突厥语,并涌现出丰富的古代突厥语文献。著名的鄂尔浑碑铭,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等就是用卢尼文字母拼写的早期突厥语文献。古突厥语后来进一步分裂,形成回鹘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等,统称突厥语族。该语族在我国的分布范围从新疆、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黑龙江流域,这在古今地名中都有反映。
这里先从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古代地名说起。在河西四郡建立之前,见于史册的河西地名甚少,《尚书·禹贡》中所见合黎、黑水、弱水、三危、猪野、流沙等,当有一定数量即分布于河西。这些地名有的地望无法确定,如三危、猪野、流沙,有的明显为汉语,如弱水,这里皆不予讨论。综观《禹贡》《史记》《汉书》的记载,时代较早而名著于史的河西地名有五,分别为河西走廊北缘的合黎山、黑水,走廊南缘的祁连山、焉支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
河西走廊北侧有山名“合黎”,此名最早见于《禹贡》,古代史志与民间俗称“黑山”。山下有水名“黑水”(同见于《禹贡》,以其水量小而又名“弱水”),而俗唤“合黎水”。“合黎”与“黑”互匹,显而易见,“合黎”乃古突厥语词汇,意为“黑”,为“喀喇”之音转。这一点,早由近人陶保廉(1862—1938)于光绪间著《辛卯侍行记》考证明确,认为“合黎、皋兰、贺兰、阿拉四名一地,实即胡语所谓哈喇也”,霍去病作战的皋兰山即今之张掖市北境的合黎山[4]。近期,汪受宽经过系统论证,确认霍去病所征皋兰山即今张掖合黎山,与今兰州市南的皋兰山无关[5]。
《禹贡》乃先秦文献,而“突厥”之名见于史册始自542年,兹将“合黎”与突厥语族的“喀喇”划等号,时代上岂不自相矛盾?实则非也,“突厥语族”只是当代语言学家为表示与突厥语有亲缘关系的一组语言而创造的集合名词。突厥语族语言简称为“突厥语”,其内涵有广狭之分。依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狭义的‘突厥语’指公元 6—8 世纪游牧于漠北高原的突厥汗国的语言,即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广义的‘突厥语’是指在语言发生学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古代突厥碑铭语言及其后来各期文献语言、现代几十种活语言或方言”[6]。在“突厥”一名出现以前,其语言就早已存在,称原始突厥语,操这种语言者,可称作原突厥人。商周、秦汉直到魏晋一直游牧于蒙古草原、阿尔泰山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人(今维吾尔族、裕固族的远祖)操的就是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今新疆南部地区即已存在以原始突厥语命名的小王国,如温宿(《唐书》称“于祝”,今译“乌什”,为ue之音译,突厥语意为“末尾”)、疏勒(当为突厥称suluk“水”的音译)、姑墨(当为突厥语qum“沙”之音译)。敦煌悬泉汉简Ⅱ90DXT0213{3}∶6+T0214{3}∶83有载:“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7]其中的“比胥楗”即为突厥语Bes(五)+波斯语kent(城)构成的。
即使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其实也是突厥语“喀喇(Qara)江”的音转,意为“大江”[8]。突厥语的称谓后为达斡尔族所沿袭,称黑龙江为Har muru,因h音弱化而读作阿木鲁。今俄罗斯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Amur),显系达斡尔语Har muru之转借[9]。推而论之,《禹贡》中的“黑水”,当与“黑龙江”之名一样,都来自古代突厥语,皆为Qara之音译。
以喀喇(Qara)为名的河流,不仅不表示水黑,其意正好相反,表示的是“清亮的水”[10-11]。喀喇(Qara)一词在蒙古语中有借用,作为液体时,一般具有“清亮”“纯净”之意,如白酒称hara arhi,不能译作“黑酒”,白开水为hara us,不能译为“黑水”。以此类推,则合黎山必为突厥语喀喇山(QaraTa?酌)之异写也,意为“高山”;黑水必为突厥语喀喇水(Qara Su)之异写也,意为“清亮的水”。
祁连山呢,其中的“祁连”为突厥语T?覿ngri的音译,其义为“天”,与今天新疆的天山其实是一个意思,庶几可谓当前比较一致的意见。当然,学界对祁连山的名与义也有不同解释,但与突厥语说相比,其他解释皆存在语言学或历史背景等方面的抵牾现象。如有人将“祁连”解释作汉语“天”的急读[12]。彼时匈奴有自己的语言,何以不用,而偏偏采用并不熟悉、甚至作为敌对势力的汉人语言来为自己所崇拜的圣山取名呢?实在难以令人取信。还有人依《汉书·匈奴传》中出现的“匈奴谓天为‘撑犁’”[13]之语而将祁连与吐火罗语kilyom(o)(意为“圣天”)相联系[14]。天山、祁连山,古来有之,在突厥语文献中一直写作t?覿ngri,没有哪个文献写作kilyom(o),再说,兴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竟用来自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语言为自己所崇拜的圣山取名,似乎不合常理。北方阿尔泰游牧民族萨满教习俗,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都会依山傍水驻牧,都会形成当时当地的“天山—神山—圣山”。匈奴人所称之天山有多处,非限于一地,汉代史籍欲令人清楚明了不同天山地望之所在,新疆者以义称之,河西者以音称之[15-16]。
至于焉支(胭脂)山,最早见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攻伐河西之时。《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元狩二年,前121)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17]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汉书·匈奴列传》,惟将焉支山改写作“焉耆山”[13]3768。《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乃如此’。”[18]从匈奴民歌可以看出,焉支山是与祁连山连为一体的,乃祁连山支脉大黄山是也。尤有进者,《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17]2891。上郡位处今陕北西部与甘肃交界地带,言其与月氏、氐、羌相接,言通义顺。
韩中义近期撰文对“阏氏”一词有如下论述:匈奴单于之夫人则被称做“阏氏”。阏氏一词最早出在《史记》:“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17]2888东晋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其可爱如胭脂也。”[17]2888维吾尔语称嫂子为“y?覿ngg?覿”,俗译“羊缸子”,音近匈奴语“阏氏”,而且所指代的都为“妻子”之意。撒拉语中称“新”为“J(y)anna”;“嫂子”为“J(y)anggu”,音译“艳姑”。哈萨克语嫂子为“Jengge”;大嫂为“Jenggey”。土耳其语中新为“Yeni”;嫂子为“Yenge”,其状与今天维吾尔语的情况几无二致{1}。
最早训释“阏氏”音义的唐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在《史记·匈奴列传》下称“阏氏”读音“曷氏”[17]2889。白鸟库吉据之拟音阏氏为hati,进而推定可敦(Khatun)为“阏氏”的音讹[19]。司马贞说为孤例,而且距离汉代相去时代较远,难以遵从。宝音德力根认为:汉武帝让画工画金日母遗像,署曰“休屠王阏支”,王充《论衡》记同一事,却作“休屠王焉提”。钱大昕早已指出“阏氏”读“焉提”。个人得出结论,“阏氏”的读音当为irdi,即《辽史·国语解》中的大臣夫人“夷离的”。irdi这个词,源自古伊朗语irdi——王室女人。词根ir,即突厥官号“伊利”,意为“大人”。男性用时叫irgen,对应于“俟斤”“夷离堇”{2}。
二说迥然有别,那么当以何者为是呢?唐初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曰:“阏氏,匈奴皇后号也。阏音於连反,氏音支。”[13]3749无独有偶,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亦言:“阏,于连反,又音燕。氏音支。单于嫡妻号,若皇后。”[20]《汉语大词典》依《广韵》“阏”“于歌切”而注音“阏”为yè[21]。复观吐鲁番出土编号为TM225的回鹘文契约第6—8行中有yngg一词:
二 早期河西部族多属古突厥种
大月氏来自敦煌祁连间,史有明载。考古学研究也证明,河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以齐家文化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农为主兼事牧业,后期则以牧为主,兼事农业。而且,河西走廊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序列也由此而产生差异,西部形成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东部则为沙井文化,以其分布地域、生业特点、文化存续时间与过程等,可以推定,骟马文化为乌孙的遗存,沙井文化则为月氏的遗存。最可关注的一点是,不管是骟马文化还是沙井文化,都与其前的文化找不到继承关系,也与其后的文化找不到关联。这些因素说明,二者都属于外来文化,其居民都由外地迁来,后来又全部迁出,这一现象与河西乌孙、月氏之西迁中亚何其似也[24]。若将“敦煌、祁连间”置于新疆博格达山一带,那里的考古学文化是否也有如同河西考古学所体现出的民族迁徙特征?不得而知。
将月氏与原突厥相联系,始于德国学者夏德(F.Hirth),他最先论证贵霜翖侯源于大月氏,他在研究突厥卢尼文碑铭《暾欲谷碑》时,将其中的突厥语Yab?酌u(叶护)与贵霜帝国之Yavuga(翖侯)相比定[25]。
贵霜帝国由贵霜翖侯发展而来的,《汉书·西域传》载:
大月氏国……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二曰双靡翖侯……三曰贵霜翖侯……四曰肸顿翖侯……五曰高附翖侯……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26]
揆诸这一记载,贵霜帝国源自大月氏是很明确的。近期有学者指史书记载有误,认为贵霜帝国应由大夏人所建[27-28]。然观张骞笔下的大夏国,其城郭和希腊城邦非常相似。此外,巴克特里亚文字来自于希腊文字母,大月氏仿造的钱币也是希腊风格的,应是对大夏国钱币的直接继承,巴米扬等地的佛教艺术明显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尽管后面几种情况都是公元1世纪至2世纪才见记载的,且证据也有所不足,但毕竟尚有蛛丝马迹可寻,故而笔者宁愿将大夏视作希腊后裔或希腊化人群所建,无法信从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将其与吐火罗划等号。持论者又将吐火罗与大月氏划等号,质言之,月氏=吐火罗=大夏,果如是,《史记》《汉书》所谓月氏“西击大夏而臣之”之载又当何解?况且,大夏是吐火罗的观点没办法解释张骞笔下的大夏完全不是游牧状态的问题,故而只能推测吐火罗接受了农耕生业方式,但自吐火罗人进入大夏到月氏到来仅有十来年时间,生业方式转变似乎没有这么快的。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V 92DXT1210{3}:132言:“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29]II 90DXT0216{2}:702载:“□□□遣守候李□送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国贵人□□国贵人□□□□□□弥勒弥□……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疆、长史□□□□□□乌孙国客皆奉献诣。”[29]203以上二简牍分别为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和建昭二年(前37),其中明言“大月氏双靡翖侯”“大月氏休密翖侯”,大月氏有五翖侯,这里居其二,贵霜帝国为大月氏所建,昭昭明矣,有何疑哉?贵霜帝国为大月氏人所建,通过阿富汗黄金之丘(Tillya Tepe)大月氏墓与蒙古国诺颜乌拉(Noyon Uul)匈奴墓中出土的大月氏靴扣与贵霜帝国王室成员所佩戴的靴扣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者幾乎完全一致,不管在造型上还是佩戴方法上,都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特点,再将之与帕提亚、萨珊等风格的靴扣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大月氏与贵霜靴扣独成体系。这一发现,庶几可为贵霜王朝建立者起源于大月氏之说提供佐证[30]。
大月氏有五翖侯。翖侯者,乃Yavuga之音译也,已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一种意见认为该词相当于早期于阗塞语中的Zauva[31-32],但Yavuga与Zauva二者间差距甚大,基本被否认,今天学界的意见一致认为Yavuga当来自突厥语的Yab?酌u(叶护)[33]。尤有进者,贵霜王朝建立者Kujula Kadphises(丘就却)之名号中的Kujula,显然来自突厥语Gujlu,意为“强壮”[34]。由此看来,大月氏所操语言亦应为突厥语。抑或正因为大月氏操突厥语这一因素,12世纪成书的《克什米尔王记》言称贵霜帝国的三王,即Huka、Juka和迦腻色伽(Kanika)分别以自己的名字为名建立了三座城市,其的Juka王还在自己建立的城市内修建了寺院。“这些王都非常慈悲,尽管其祖先来自突厥种”[35]。这一记载恰好又与后世统治犍陀罗地区的突厥王自称为贵霜帝国第四代君主迦腻色伽之后代的情况相一致[31-32]。另外,收于藏文《丹珠尔》中的《于阗国授记》中还记载:尉迟讫帝(与迦腻色迦同时代)时,于阗被突厥(dru gu)阿木囊属(a mo no shod)入侵[36]。此处的“突厥”似应指迦腻色迦时代的贵霜帝国。这些足以说明,大月氏当为原突厥人。
至于乌孙,史书留下的语言材料仅有“翖侯”而已。《汉书·张骞传》:“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颜师古注:“翖侯,乌孙大臣官号,其数非一,亦犹汉之将军耳。”[37]前言大月氏翖侯为突厥语,果如是,则可为乌孙操突厥语之一例证。尤有进者,学术界一般将乌孙视作哈萨克族的祖先,今天的哈萨克使用的是突厥语,结合当时河西走廊突厥语分布的情况,抑或可以推测乌孙语言亦应为突厥语。
乌孙、月氏相继西迁后,河西走廊的主人便由匈奴取而代之。至于匈奴所使用的语言,学界争议不小,但比较趋同的意見还是认为应属于突厥语[38],如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emusat)、克拉普罗特(M. H.Klaproth)、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德国学者葛玛丽(A. von Gabain)、普里查克(O. Pritsak)等人,尤其是近期丹麦学者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最新研究显示,匈奴语是突厥语族中最早的一种语言[3]。《魏书·高车传》载:“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史·高车传》亦谓:“高车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说明高车语与匈奴语大同小异。高车为丁零、敕勒、铁勒之异称,乃今天维吾尔族的远祖。若《魏书》《北史》所言非虚,称匈奴语为原始突厥语之一种,当无大误。
依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如果早期河西的居民为突厥语民族,那么“敦煌”一名就应该来自突厥语而非其他语言。
三 “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语说
关于敦煌地名之来源,学界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将“敦煌”是“吐火罗”比对{1},然而,吐火罗分布区域在天山南麓,故其前提必须是敦煌、祁连山、焉支山都位处东天山地区。于是,地名大搬家,推定敦煌、祁连山、焉支山不在河西走廊而在新疆博格达山一带。此说缺乏证据,笔者拟另文探讨,兹不复赘。第二种说法认为“敦煌”为“桃花石”的音译[42],而“桃花石”,来源于“拓跋”[43-45]。据《魏书·序纪》,鲜卑拓跋部的历史序幕是从西汉后期的拓跋毛开始的,而拓跋部的崛起,则始于汉末至晋初时期鲜卑索头部首领拓跋力微(174—277),故而力微被奉为鲜卑拓拔氏的真正始祖。拓跋氏的兴起要晚于敦煌一名在史书中的出现,故而可谓了无干系。第三种说法认为“敦煌”来自羌语,为羌语“朵航”{1}的对音,意为“诵经地”或“诵经处”[46]。彼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是无经可诵的。四者认为有可能来自伊朗语druvana,有“健康、固定”[47-48]或“受安全保卫的城池”[49]之意。此说的理论基础与第一种说法是一致的。质言之,以上诸说都无法成立。第五种说法是李正宇先生提出来的,认为“‘敦煌’地名当系大月氏语”[50]。此说与本人的意见接近,惜李先生未作详细的语言学论证。第六种说法是钱伯泉先生提出来的,认为“敦煌”和“莫高窟”二词均来自古突厥语。文中指出,敦煌故称瓜州,而瓜在维吾尔语中写作“tawuz”,其音与“敦煌”接近[51]。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对推动敦煌一名的探讨是有启发意义的。但钱先生文主旨在于探讨“敦煌”和“莫高窟”二词有可能的突厥语含义,惜未能对两个地名的语源、历史背景,尤其是学界争论的祁连山方位、大月氏故乡所在地等问题未予深究。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五个早期地名中,有四个可以确定为突厥语,尤有进者,长期生活于敦煌等地的月氏、乌孙、匈奴亦属于突厥语群体。这些因素可以证明,在西汉统有河西走廊之前,这里流行的语言是原始突厥语。由大概率观之,用突厥语解释“敦煌”的含义,一来可能性极大,二来完全不存在语言学上的障碍。
那么,敦煌一词当为何意呢?钱伯泉先生曾推论为突厥语tawuz(瓜)之音转。笔者查阅古代回鹘语文献,不见该词,但可见于现代维吾尔语词典中。如阿布利孜·亚库甫等编《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中收有tawuz一词,解释曰:“瓜科一年生草本,离蔓生长,叶羽状展开,花淡黄色,果实为大型浆果,球形或椭圆形,水分多,味甜。”[52]德国学者德福(Gerhard Doerfer)曾详细讨论了突厥、波斯语中的“西瓜”,给出一条可能的词源线索:qarpuz(突厥语)<harbuz?摇\?tarbuz(波斯语)<trapusa(梵语)[53]。其中提到了tavuz是新维吾尔语(NeuUigur)[53]381
Tarbus,现代哈萨克语作darbiz和qarbiz,是见tavuz是b变w/v的结果,应为更晚的形式。这种演变形式多见,如维吾尔语 tawa (tawa kawap),在哈萨克语为taba“平底锅”;维吾尔语chivin,在哈萨克语中作chibin“苍蝇”。
从音理讲,“敦”的声母与t同,为双声关系;“煌”是古匣母阳部字,wu中的u是“鱼”部字的元音。匣母是喉音,鱼阳可以对转。又方言中喉音与唇音互转亦常见,如“湖”读fu、“福”读hu等。由音韵学观之,“敦煌”有可能是tawuz/tavuz的译音{2}。
历史上的敦煌就是产瓜之地,《汉书·地理志》:敦煌即“古瓜州地,生美瓜”[1]1614。《续汉书·郡国志》:“敦煌,古瓜州,生美瓜。”{3}王嘉《拾遗记》:“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燉煌献异瓜种,恒山献巨桃核。瓜名‘穹隆’,长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饴。”{4}这些材料均可证明,汉代及以前的敦煌就有瓜的生产,且负有盛名,故称“瓜州”。需要提点的是,“瓜州”一名来历久远,《左传·襄公十四年》:“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汝)剖分而食之。”[54]“瓜州”一名最早見于此,时当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杜预注言“瓜州地在今敦煌”[55]。又《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55]1321,1323杜预为魏晋时人,言彼时的瓜州为敦煌,不误,但言《左传》中的瓜州为敦煌,则方枘圆凿矣。顾颉刚考证认为《左传》之瓜州在今秦岭高峰之南北两坡[56],颇得鹄的。
不管瓜州之名何时出现,但敦煌长期被称作“瓜州”则是无可争辩的。及至6世纪,瓜州正式成为敦煌地方行政建置的名称。北魏孝昌二年(526),改敦煌郡为瓜州;隋开皇二年(582),又把敦煌郡改为瓜州;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在敦煌设置瓜州。三年之后,即武德五年(622),敦煌被改称西沙州。《旧唐书·地理志》:
沙州下,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天宝元年,改为燉煌郡。乾元元年,复为沙州。[57]
敦煌的旧名瓜州则被东移百余公里,成为今天甘肃省瓜州县之名。
总之,言敦煌一名起源于突厥语当无大误,但tawuz是直接借用于梵语trapusa还有间接由波斯语tarbuz转化而言,因缺乏证据,不得而知。尤有进者,在古代回鹘语文献中暂时没有找到使用tawuz(瓜)的用例。在回鹘语文献中,唯有甜瓜的用例,写作qa?酌un[39]1168,可见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58-60],但未见西瓜(tawuz)的用例。如果将来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能够找到tawuz之用例,则敦煌名出突厥语之说即可坐实,毋庸再议了。
《史记》《汉书》均记载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连间”。祁连山为绵延数百公里的山脉,如果将“敦煌”理解为今天的敦煌,行文上似有不通之嫌。笔者认为,月氏所居的敦煌应为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盛产瓜。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敦煌建郡,遂以今天的敦煌绿洲作为郡治。久而久之,敦煌也就成了敦煌绿洲的代名词,由区域名变为城镇名称。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西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前,河西走廊见于《禹贡》《史记》《汉书》的河西地名不多,除地望不详或明确的汉语地名外,时代较早且名著于史的地名仅有五个,分别为河西走廊北缘的合黎山、黑水,走廊南缘的祁连山、焉支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地名都可以用突厥语来解释。即合黎山为喀喇山(Qara Ta?酌)之异写,意为“高山”。黑水为喀喇水(Qara Su)之异写,意为“清亮的水”。祁连山为突厥语T?覿ngri Ta?酌之音译,意为“天”。而焉支山的“焉支”,又作“胭脂”,与匈奴单于之夫人称谓“阏氏”一样,可与古黠戛斯语勘同,而古突厥—回鹘语中“y?覿ngg?覿”可能为其音变,其意皆为“嫂子”或“新人”,是证焉支山同样为突厥语地名。
生活于敦煌、祁连间的乌孙、月氏及其后继者匈奴,使用的都是突厥语,而且大月氏贵霜翖侯所建贵霜帝国,统治者以突厥人自居,犍陀罗地区的突厥王自称为贵霜帝国第四代君主迦腻色伽之后代,这些也表明了月氏的突厥起源,其故地在敦煌、祁连间,也表明了敦煌与原突厥之密切关系。需要说明的,上举地名、人名、称号等有一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与蒙古语共源,有的则与满—通古斯语之间存在共性,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三者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他们中间的共源词汇是很多的[19]56。对于共源词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将这些数量不多的词汇综合起来,只有用突厥语解释可以通达无碍。相反,改用其他语言,虽可解释某一或若干词汇,但若用之于其他词汇就无法通达,甚至与史实相悖。在研究语言的民族归属时,与其根据单词之异同逐个考源,不若将所有词汇溶于一体,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综合的、全面的观察,方能更接近于史实。依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如果早期河西的居民为突厥语民族,那么“敦煌”一名就应该来自突厥语而非其他语言。
敦煌古称瓜州,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才被西沙州、沙州所取代,而且在汉代以前就产瓜。在突厥语中称瓜为“tawuz”,为波斯语tarbuz或梵语trapusa的假借。从音理讲,“敦”的声母与t同,为双声关系;“煌”是古匣母阳部字,wu中的u是“鱼”部字的元音。由音韵学观之,“敦煌”与tawuz之译音恰好可以对上。上述诸因素当不能完全结合为巧合。
总之,笔者认为,尽管敦煌自古以来产瓜,且长期被命名为瓜州,“敦煌”之名从音韵学角度看又与突厥语“tawuz”的音译相合,推测“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语言之成理。但由于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古代回鹘语文献中只有甜瓜的用例,写作,却没有找到西瓜(tawuz)的例词,所以仍不能遽断“敦煌”之名就来自突厥语“tawuz”(瓜)的音译。易言之,维吾尔语中的“tawuz”(瓜或西瓜)与作为敦煌地名的“瓜”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语言学渊源,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1]班固.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614.
[2]李吉甫,著.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M]. 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026.
[3]Peter de Barros Damgaard,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
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J]. Nature,Vol. 557,2018:371. DOI:10.1038/s41586-018-0488-1.
[4]陶保廉,著. 辛卯侍行记:卷四[M]. 刘满,点校.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246-247.
[5]汪受宽. 三皋兰山辨[M]//陇史新探.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25-137.
[6]张铁山. 突厥语族文献学[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3.
[7]郝樹声. 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J]. 中原文化研究,2015(2):65.
[8]杨富学. “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J]. 语言与翻译,2000(3):52-54.
[9]刘凤翥. “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J].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4):82.
[10]牛汝辰. 新疆地名中的“喀拉”一词辨析[J]. 新疆社会科学,1984(4):146.
[11]牛汝辰. 新疆地名概说[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100.
[12]贺德扬. 论“祁连”[J]. 文史哲,1990(3):84-86.
[13]班固.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751.
[14]林梅村. 祁连与昆仑[J]. 敦煌研究,1994(4):115.
[15]刘义棠. 祁连天山考辨[M]//中国西域研究. 台北:正中书局,1997:20-21.
[16]李艳玲. 西汉祁连山考辨[J]. 敦煌学辑刊,2021(2):26.
[17]司马迁.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908.
[18]李泰,等,著. 括地志辑校:卷四·删丹县[M]. 贺次君,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5:227.
[19]白鳥庫吉. 蒙古民族の起源[M]//白鸟库吉全集:第4號. 东京:岩波书店,1970:41.
[20]司马迁. 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634.
[21]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第12册[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128.
[22]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M].大阪:大阪大学出版會,1993:161.
[23]姚大力. 河西走廊的几个古地名[J]. 西北民族研究,2020(3):59-61.
[24]杨富学. 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M]//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9-
45.
[25]F. 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M]//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
eitefolge,T. Ii,1899:48.
[26]班固.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890-3891.
[27]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2-37.
[28]余太山.贵霜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7.
[29]郝树声,张德芳. 悬泉汉简研究[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202.
[30]杨富学,米小强. 靴扣:贵霜王朝建立者源自大月氏新证[J]. 敦煌研究,2020(5):11-21.
[31]Sten Konow.Kharos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oka[M].Vanarasi:Indological Book House,1929:1.
[32]Sten Konow,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J].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vol.12,1933:13-15.
[33]?魪d.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d après le Heou Han Chou[J]. T’oung Pao,8/2,1907:189,note 3.
[34]Eugen Hultsch. Review to Sir Marc Aurel Stein (ed.), Kalhana’s Rajatarangini: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J].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69,1915:176.
[35]Sir Marc Aurel Stein (ed.).Kalhana’s Rajatarangini: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M].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2009:30-31.
[36]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上)[J]. 中国藏学,2012(增刊1):262.
[37]班固.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692.
[38]陈序经. 匈奴史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4-102.
[39]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
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313.
[40]韩儒林. 突厥官号考释[M]//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05-306.
[41]杨富学. 回鹘摩尼教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06-107.
[42]岑仲勉. 释桃花石(Taugas)[J]. 东方杂志:第33卷第21号,1936:63-73.
[43]P. Pelliot.L’origine du nom de 《Chine》[J]. Toung Pao:13,1912:740-742.
[44]Peter A. Boodberg.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No.2, 1936:167-185.
[45]冯家昇. 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J]. 考古学专刊丙种一号(北京),1951:4-5.
[46]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J].青海社会科学,1988(5):86.
[47]Victor H. Mair.Reflections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With an Added Note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Uighur Place-Name ‘Turpan’”[M]//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22.
[48]梅維恒,著. “敦煌”得名考[J]. 王启涛,译.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9):219.
[49]姚大力. 河西走廊的几个古地名[J]. 西北民族研究,2020(3):57.
[50]李正宇. “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J]. 敦煌研究,2011(3):80.
[51]钱伯泉. “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J]. 敦煌研究,1994(1):44-53.
[52]阿布利孜·亚库甫,等,编. 维吾尔语详解辞典(第2卷,维吾尔文版)[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94.
[53]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
teim Neupersischen,Band III[M].Wie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67:380-383.
[54]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6:1105.
[55]杜预. 春秋左传集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902-903.
[56]顾颉刚. 史林杂识·瓜州[M]. 北京:中华书局,1963:46-53.
[57]刘昫,等,撰.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644.
[58]耿世民.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J]. 考古学报,1978(4):502-509.
[59]Geng Shimin. Notes on an Ancient Uighur Official Decree issued to a Manichaean Monastery[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35,No. 3-4,1991:211-219.
[6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J]. 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1/32卷合併號).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