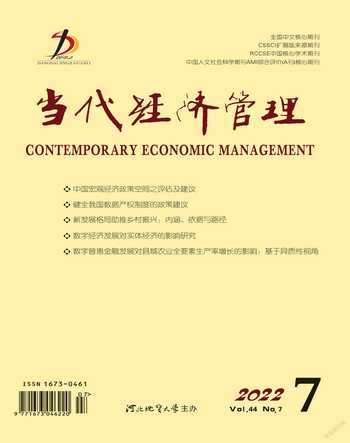资源稀缺如何影响创造力?
王静 李义敏 朱強





[摘 要] 创造力决定了本土企业能否在新一轮战略机遇期中脱颖而出。然而,囿于人、财、物等资源稀缺难题,使企业创新创造的努力和实践受到极大挑战。文章聚焦于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跨学科系统梳理和述评。首先,界定资源稀缺和创造力的概念。其次,根据研究主题确立文献检索方法和研究边界。再次,基于文献分析,总结资源稀缺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问题、现状和进展。具体而言,分别从个体与群体(集体)创造力层面解析资源稀缺的作用,考察资源稀缺的不同形式,并着重从认知、动机反应归纳其中介机制。此外,基于现有研究缺口,从多类型资源稀缺的协同效应、缺失中介机制的探索、群体创造力及其互动过程、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生态环境等角度,展望了资源稀缺与创造力研究的未来方向。最后,归纳研究发现,引入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研究整合框架。
[关键词]资源稀缺;创造力;个体创造力;群体创造力;群体过程;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72.92;C91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2)07-0031-09
一、引言
新时代,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命脉与国际竞争的核心[1]。面对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也必须持续创新才能永葆竞争活力。创造力指产生针对产品、服务、过程或流程等新颖且有用的观点[2],强调新观点的生成阶段,是创新成果和创新绩效形成的前提和重要基础。与此同时,资源稀缺是人类社会的日常现象和普遍问题,包括物质资源贫穷,资金财富稀少,时间和精力匮乏,社会交往纽带缺失。即使在机器化大生产、资源充裕的时代,仍会遭遇资源稀缺的环境线索,感到资源持有量和需求量之间存在差距。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各种稀缺现象。在企业创新创造活动中,财务、人力、物力稀缺,时间压力、任务限制等更是大量存在,创新过程涉及多种资源约束、各类稀缺难题,资源禀赋不足成为企业有效实施创新的重要挑战。
资源稀缺性无处不在,伴随创新过程始终,那么,其总是会扼杀创造力和创新吗?传统智慧和相关研究提出需根除创造性思维蓬勃发展的制约因素[3]。然而,从古至今,国家、企业、团队、个体各层面,创造实践均受到规章制度、有限物质资源和时间压力的限制,“戴着锁链舞蹈”成为常态。作为现代社会和创新环境的决定性特征,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如何有待发现。针对该问题,以AMABILE为代表的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进行探讨,而后,战略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组织行为和市场营销等多个管理学学科领域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和发现,涌现出一定的研究热点和基本论断。但是,围绕“资源稀缺”与“创造力”两个关键词,现有研究中对资源稀缺的复杂、多维形式仍缺乏全面认识,对创造力的作用分析未能兼顾个体与群体(集体)多个层面,对资源稀缺影响创造力的中介机制探索呈现出零散且支离的现象,以至于以往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悖的结论和发现,未能形成清晰且系统的研究框架。
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资源稀缺下的创造力研究,以从多领域、多视角、多层次分析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作用,厘清其内在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以应对创造力理论研究与创新管理实践面临的现实和挑战。接下来,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源稀缺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深入解读,在文献整理与分析评价时采取以下步骤:首先,明晰资源稀缺和创造力的概念;其次,确定文献述评的范围和边界;再次,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个体、群体(集体)层面归纳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影响,相关中介机制和调节变量;最后,基于现有研究缺口,从多个视角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整合研究框架。在此过程中,注重区分资源稀缺的不同形式,阐明多维创造力结果变量,提炼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整合各研究领域的实证发现。以期拓展、丰富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理论研究,同时也为实践者突破稀缺困境并激发创造力提供知识支撑。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资源稀缺的内涵
目前文献对资源稀缺(resource scarcity)的定义和内涵尚未取得共识,出现了不同术语用以描述资源稀缺现象。SHARMA和ALTER(2012)[4]将其界定为经济剥夺,“感到与参照群体比较时财务资源匮乏,‘低人一等’或‘情况更糟’的一种不愉快心理状态”。MEHTA和ZHU(2016)[5]认为资源稀缺指个体成长和发展所需物质资源的感知供给水平。SHAH等(2012)[6]将其视为某种“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觉得“拥有较需要更少”。HAMILTON等(2019)[7]认为稀缺来源于两个方面,包括客观资源的实际缺乏和主观感知到的资源缺乏。而总结对资源稀缺的不同观点,其核心是现实、感知的当前资源水平与满足人们需求或更高理想状态之间存在距离。同时,从其成因来看,资源稀缺存在于多种类型,包括财务、社会和文化等各类资本缺乏,或其他生产投入(如材料、资金、时间等)的约束,并可能来源于个体、群体、社区以及更广泛的范围。那么,结合本研究述评主题“企业创新创造情境下的资源稀缺性”,该构念指:任何可能限制创造力的客观创新资源约束(如资金、时间、材料等),以及创新活动参与者因各种资源获取限制而主观感知到的资源匮乏。
(二)创造力及其影响因素
通常意义上,创造力体现为个体或合作群体针对给定情境所形成的具有新颖性、价值性和可行性的事物或想法,主要指观点、产品方案和决策的革新。新颖性(novelty)和有用性(usefulness)是衡量创造力高低的两个重要指标[8],新颖性强调相对于其他结果的原创性、独特性和出人意料的程度,有用性指结果或创意切实可行、确实有用、符合限制条件。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研究致力于探讨创造力的影响因素。从个体层面看,现代创造力理论认为创造力的产生同时受到认知、动机、个性与社会、环境多种因素作用,是专业、创意思考技能、工作内在动机的综合。除跟个体认知能力(如逻辑推理、隐喻思维)有关,也和性格特质(如模糊容忍度、风险偏好)有很大关联。此外,还受一些高度可变因素的影响,含涉入度、情绪、奖励形式、感官刺激等。从群体层面看,面对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和创新快速迭代,企业实践对创造力的应用往往强调群体创造力,协同合作与团队努力。根据经典的“输入-過程-输出(IPO)”理论模型[9],群体创造力受群体结构、任务特征和情境因素等输入变量,以及群体成员间的互动行为,如社会沟通、决策参与、知识共享、关系冲突等过程变量的影响。然而,相对于个体创造,群体创造的研究较为有限。
三、文献检索与资料收集
基于关键概念界定,为实现多领域、多视角的文献回顾与分析,本部分“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文献检索和数据搜集具体分为四个步骤:①数据库提取文献;②识别主要文献;③手动检索引用情况并获取其他相关文献;④确认高度契合文献。具体而言(见图1),第一,通过国内外数据库获取文献。在确保了解研究概貌的基础上让文献检索范围可控,同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以实现管理学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外文文献方面,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进行外文期刊文献检索,选取2000—2021年时段发表的文章,以“creat*”和“scarc*”/“constrain*”/“restrict*”为组合检索词(TOPIC),文献类型选取Article。中文文献方面,以“创造”和“稀缺”/“约束”/“限制”作为组合检索词(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系统搜索,选择CSSCI期刊为数据来源,发表时限仍为2000—2021年。第二,阅读每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对初步检索结果一一排查,剔除与研究主题界定不符,同资源稀缺对创造力影响联系不紧密的文献。第三,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发现有些参考文献被遗漏,通过文献追溯法,对所选文献的索引和被引情况加以追溯,补充近三年管理学顶级期刊和创造力研究知名学者论文,以保证基本不遗漏最新的重要文献。第四,对整个过程多次进行迭代,确认高度相关中英文文献共68篇(外文文献50篇,中文文献18篇),作为后续文献分析和述评的依据。
四、资源稀缺下的创造力研究
资源稀缺意味着各种资源、资本或投入的缺乏,资源可得性、可用性受到限制,因此,关于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大多从资源约束(resource constraints)展开,聚焦创新任务域中任何客观存在、可量化、可消耗的资源类型,如时间、财务及材料投入等资源,少数则关注主观资源稀缺感知对创造性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创业与创新管理、市场营销与组织行为等多学科领域,均对此现象予以探索。然而,资源稀缺会削弱还是增强创造力,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并多从个体与群体(集体)层面展开,以下将分别予以阐述。
(一)个体层面研究
CUNHA等(2014)[10]认为资源稀缺环境下的产品创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物质资源稀缺时的资源拼凑(bricolage),时间资源稀缺时的即兴行为(improvisation),及富裕客户群稀缺时的节俭式创新。本研究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也发现,可根据资源稀缺的成因细分为客观的财务/材料资源稀缺(有形资源)、时间资源稀缺(无形资源)和主观资源稀缺感知,以厘清不同类型稀缺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
1.时间资源稀缺
早期研究认为,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应是相互对立的。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任何外部约束均会降低控制感和内在动机[11]。理想的创造过程应为非结构化、开放式、不受限制,给予创造者充足的探索时间和空间。自由、内在动机和冗余资源是创造力生成的催化剂。基于此,有学者发现时间约束(最后期限、时间压力)负向影响创造性的认知过程,导致常规性、表面思考和惯性思维模式。HENNESSEY和AMABILE(2010)[12]阐释了时间约束会降低内在动机,进而削弱个体创造力。MADJAR等(2011)[13]也发现,创造力任务中资源易获取才能促进激进式创造性绩效。
然而,另有研究表明任务时间过多不利于创造力。一定的时间约束可被视为某种挑战,从而激励员工表现得更具创造性[14]。例如,BURROUGHS和MICK(2004)[15]发现限制完成任务的给定时间能使人们在特定任务中产生更具创造力的消费解决方案。SACRAMENTO等(2013)[16]分析了调节聚焦导向对于挑战压力源与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当面临高工作要求(工作量和时间压力大、绩效期望高),具有促进导向特质的个体和团队创造力水平更高。SHAO等(2019)[17]搜集了员工-主管配对数据,研究得出,当员工面临繁重的工作负荷和相互竞争的目标需求时,领导者悖论行为(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可提升员工创造性自我效能感,进而在这种挑战性环境下激发其创造力。总体看来,以往研究认为,时间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很可能呈倒U型关系,温和的时间稀缺将推动创造力,且两者关系受个体和情境因素的调节[18-19]。
2.财务/材料资源稀缺
除时间资源稀缺,也有学者关注其他类型的创新资源约束,如资金、物质材料资源等。研究普遍认为,完全缺乏约束的情境会滋生人们的自满情绪和舒适状态,不愿承担风险,改变既有战略路径,这些均不利于创造性绩效[20]。而适度资源稀缺则会赋能创新并激发创造力。譬如,创业领域研究发现,创业的本质是机会和资源,创业者可凭借资源拼凑、“自力更生”以应对稀缺难题。这是因为,从认知机制上,资源稀缺促使其打破既定约束构建独特的资源组合,有利于创业者识别机会,以崭新方式对手头有限的资源进行利用、重组和拼凑,从而创造性地解决所面临威胁或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21]。因此,让创造过程变得困难而非简单,可促进其想象力并获得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资源稀缺不仅不会阻碍创造力,也会因输入端约束所带来的挑战而提升创造力。
总结针对财务/材料资源稀缺的现有研究,大多在消费创造场景进行探索,如新产品接纳和采用、产品自设计、顾客定制化和产品创新使用。SELLIER和DAHL(2011)[22]通过实地消费实验发现,当参与编织围巾、制作圣诞树等创造活动时,限制所使用的材料选择可提升有经验消费者的创造力水平,且产品创造过程的任务乐趣起到中介作用。MOREAU和DAHL(2005)[23]认为材料投入约束能使消费者远离最小阻力认知路径(path of least resistance,POLR),在新产品设计活动中形成更具创新性的构思,但仅限于没有高度时间约束的条件。该研究着重关注资源稀缺提升创造力的认知过程,并分析了物质材料与时间资源稀缺的协同影响。而SCOPELLITI等(2014)[24]则比较财务约束和材料投入约束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差异,发现两者都会激发想法新颖性,但前者引起某種节俭思维(parsimonious mindset),倾向于使用成本较低的资源,并更多遵循自上至下(top-down)而非自下而上(bottom-up)的认知搜索策略,该效应在具有高度求新倾向的人群中更加显著。
也有学者对其他稀缺情形下的创造力予以探索。VAN RIJNSOEVER等(2012)[25]通过实验研究论证,参与者经济地位(以实验点数代表资源现状)与创新行为之间为U型关系。MARGUC等(2015)[26]研究证实,目标阻碍和干扰的存在有助于个体在目标追求中的创造性思维,并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更具变通性,形成较为新颖的目标进展策略。MIRON-SPEKTOR等(2018)[27]对美、英、中等国的公司员工开展了问卷调查,发现职场环境充斥着各种任务、角色冲突和要求,时间、资金有限构成了资源稀缺难题,但拥有悖论思维的员工恰恰能够接纳并被各种冲突所激励,以提升工作绩效和创新能力,悖论思维成为解锁日常工作中稀缺困境的关键。综上,近年来大量研究均表明,财务/材料资源稀缺将积极作用于个体创造力,认知和动机因素为其主要中介机制,个性特质变量成为关键调节机制。
3.主观资源稀缺感知
除创新活动客观存在的资源约束,各方面资源限制也会引起参与者的主观稀缺感。MEHTA和ZHU(2016)[5]在消费实验研究中发现与创新情境无关的资源稀缺感知可提升产品使用创造力。通过降低认知固化(cognitive fixation)水平,资源稀缺带来有价值、更创新的消费体验。另外,消费者创造力还见于对贫困和资源稀缺人群的定性研究。这些仅能糊口的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从事更多创新行为,例如,将不同成分和原料组合做成新物品,创新产品使用领域和用途等。TRUJILLO和ROSA(2017)[28]的调查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通过重新利用产品来解决消费时的约束和稀缺问题,而个体完成任务活动的希望水平对提升低地位消费者的创造力至关重要。并且,儿时生活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能够增强成年后在面临财务资源稀缺时的认知任务表现水平,比较而言,他们拥有更高的任务切换和工作记忆能力,以快速跟踪和更新动态变化的环境信息。这些发現从认知层面上为资源稀缺感促进创造力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依据。进一步,DE DREU和VAN DIJK(2018)[29]分析了人类历史中气候状况与重大科技创新之间的联系,基于欧洲地区1500CE至1900CE的二手数据资料,研究发现当遭受极端气候变化和冲击时(地表温度寒冷、笼罩火山灰),会引发经济社会压力,从而催生出更多的科学探究和技术创新行为以应对资源短缺问题(如农作物价格上涨)。
然而,除了对消费创造的积极影响,另有关于认知能力的实地实验研究表明,资源稀缺会降低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和执行控制力(executive control)[30]。研究者让印度甘蔗农们做同一系列认知能力测试,发现其收获前表现比收获后差,两者区别大约相当于10分的智商“认知税”。这一结论在商场路人实验对低收入者财务困境的操控中也予以验证。由于个体认知因素与创造力密切相关,那么,资源稀缺感和创造力的关系是否因稀缺类型、持续性和反复性、创新情境不同有所差异仍待深入剖析。CANNON等(2019)[31]从自我规制的视角,建立了资源稀缺可变性评估与心理变量、应对行为结果的因果模型。那么,主观感知的资源稀缺如何影响创造力,还需厘清稀缺可变性及相关威胁增强(削弱)因素的调节作用。
(二)群体(集体)层面研究
关于资源稀缺对群体创造力影响的研究极少。代表性的为ROSSO(2014)[32]针对技术研发团队的实地研究,提炼出资源约束类型、社会心理过程和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其中,过程约束、严苛的环境约束会削弱团队创造力,且团队过程和动态(成员间的信任、合作和管理支持等)影响团队对资源约束的理解、接受和应变,进而增强创造力。KHEDHAOURIA等(2017)[33]亦分析了R&D团队成员的创造力,发现中等水平的时间压力可激发认知和动机过程,促进学习导向和知识获取行为并提升创造力,但高度时间压力则会抑制该过程。AKGN等(2007)[34]对美国多个行业新产品开发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参与竞争时,时间压力和意外紧急事件普遍存在,企业通过调动即兴能力迅速反应,将计划和执行融合,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突破约束瓶颈,从而实现新产品开发成功。同时,团队创新氛围、权力距离等调节资源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35]。进而,考虑企业中创造力的集体属性,往往依赖于整个企业的智慧和协作,一些研究延伸至更广泛、更大规模的多个同质或异质个体组合的创造活动。例如,VOGELGSANG(2020)[36]分析了集体创造力(collective creativity)涌现的动态过程,在对医药行业四个产品开发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项目资源约束的交替、转化进程以提升集体创造力,而非静态、简化的约束和自由权衡。于是,从动机、认知和社会互动方面,这些研究试图解构资源稀缺影响群体(集体)创造力的机制和过程。
而实践中,当企业面临人、财、物等各类资源约束时,会进行拼凑以形成独特的资源环境,这成为一种资源全新利用方式的管理逻辑[37],因此,战略管理和创业领域围绕着资源稀缺下的拼凑行为予以探索。近年来,有关拼凑创新效应的实证研究快速增长,例如,AN等(2018)[21]基于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发现资源拼凑影响公司创业,机会识别起中介作用,而学习导向起调节作用。WU等(2017)[37]从两个维度探讨资源拼凑带来的新产品竞争优势,正向影响新产品开发速度,而与新产品创造力呈倒U型关系,技术动荡性起正向调节作用。此外,近期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主要关注了创业活动中的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问题[38-39],将拼凑策略作为调动企业创新的手段[40-41]。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有学者探讨在线消费者社群知识共享、资源拼凑对社群新稳态的实现机理,研究发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创造性组拼有助于企业保有核心竞争力[42]。那么,总体而言,在不确定性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及计划难以展开时,创造群体(集体)可将组织意图、创造力与资源利用有机整合,重新部署现有资源并获取异质新资源[43],资源拼凑成为解决动态环境和资源匮乏所带来创新难题的重要路径。
可以看到,企业创造实践强调集体协作,但在理论上,群体(集体)层面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且尚未探讨创新活动参与者与创新域无关的主观稀缺感知,相关研究仍有很大拓展空间。群体创造力不仅仅是个体创造力的简单加总,更是群体这个复杂系统在创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特性,群体层面资源稀缺的创造力后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互动过程的质量,这对群体资源转化、群体认知和群体智慧生成极为重要。
(三)综合分析与总结
综上,聚焦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文献,依据资源稀缺形式、创造力研究对象、作用方向、中介机制和调节变量等维度对代表性文献进行分类,总结概括见表1。资源稀缺形式包括创新任务域中的客观资源匮乏(无形、有形资源)及因各种资源限制产生的参与者主观稀缺感知,而创造力主要从个体和群体(集体)层面进行衡量。针对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影响,主要结论为:①从理论和实证证据看,资源稀缺与创造力之间很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鉴于以往研究所涉及资源稀缺形式、程度和成因不同,由此产生了不一致发现。②现有研究多针对个体层面,对创造群体和集体的研究甚少,但倒U型关系在多个层面分析中存在一定相似性,可能会因群体交互过程强化了“我们相对于他们”的社会动力机制,资源稀缺激发群体创造力的效力更强,倒U形曲线最佳临界点向左推移。③与创造力前置动因保持一致,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影响效应通过个体层面动机、认知变量和群体层面社会互动变量发挥作用,并受到个体特征、创新任务和情境因素的调节。
五、未来研究展望
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言,创造过程的约束动态可看作“戴着锁链舞蹈”(dancing in chains)。与传统观念相悖,基于约束与自由的“二元性”,压力与挑战并存,资源稀缺可能提升或抑制创造力[44]。但目前研究结论仍存在诸多争议,为系统、深入地阐释资源稀缺对创造力影响的二元性,需进一步厘清资源稀缺构念,区分不同稀缺形式,探讨多重稀缺类型对创造力特别是群体创造力的协同作用。并且,對相关中介机制、边界条件、情境因素的探索也利于明晰资源稀缺影响创造力的方向和过程。基于现有研究缺口,提出以下未来研究展望。
(一)不同稀缺形式的差异及其共同影响
资源稀缺构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围绕创新创造情境根据其诱因不同可分为:①客观资源稀缺(创新任务域本身赋予的任务时限、资金和材料投入限制);②主观稀缺感知(创新活动参与者主观感知的资金、时间匮乏或生理饥饿,可能来自创新任务域或由与任务域无关因素导致)(见图2)。然而,总结已有资源稀缺下的创造力研究还有一定局限:首先,从资源类型来看,大多涉及创新任务有形资源约束和时间限制,对创新活动参与者拥有较少闲暇时间和财富所引发的主观稀缺感较少探讨;其次,从各学科分布来看,研究重点差异较大,战略管理与创业领域强调资金、材料与人力资源缺乏,组织行为领域突出时间约束,而市场营销领域则聚焦创新活动输入端的各种稀缺。鉴于现代社会同时存在多种形式资源稀缺,新冠疫情引发各类资源短缺危机并产生稀缺心态,企业创新实践也经常涉及资源间的替代拼凑,于是,各类型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作用可能产生叠加效应,剖析其对创新参与者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价值。
(二)资源稀缺对群体创造力的作用
当今世界,随着群体参与形式在创新活动中普及,“群体如何共同完成创新任务”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创造是协同合作的产物,创新是团队努力的结果。这是因为,新产品开发是将分布于全球各地的信息、知识、资源和能力高度整合的复杂过程,单靠个人力量无法快速有效地完成,这时凸显了群体和团队的重要性,大规模协作已成为许多领先企业攻克创新难题的“重要法宝”[45],如新产品开发小组,众包平台、顾客在线创新社区等。可是,目前关于资源稀缺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多针对个体层面,群体与集体水平创新创造研究甚少。不少学者认为,群体间的交流、合作和知识共享是提升创新项目质量、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键[46]。群体创造力既来源于成员观点、信息、智力的高度整合,也是涵盖产品、人际和社会身份互动的情绪体验过程,从而,资源稀缺作用于群体创造力的互动过程与动力机制研究也需深化。
(三)缺失中介机制和动态过程的实证分析
从个体层面看,认知(认知灵活性、搜索策略、认知固化)、情绪(情绪效价、唤醒水平、焦虑/专注等特殊情绪)与动机(内在动机、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风险偏好)在资源稀缺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可能起到中介效应,具体心理机制有待未来实证研究验证。延伸至群体层面,资源稀缺至群体创造力生成仍是“黑箱”。而鉴于群体过程对群体智慧水平极为重要,创造性活动中的群体社会互动(人际冲突、交互不确定性)、群体信息加工(信息聚合、信息发散)、群体情绪(情绪基调、情绪二重调整)等变量尤为值得探索。进一步,为更科学、准确地刻画群体创造、社会互动和信息加工过程,除采用传统问卷形式测量、主观报告心理变量外,还可在群体创造实验中运用互动内容编码、观察分析和生理指标探测等直接、客观和多样化的方法,结合开放式创新平台二手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文本分析,以剖析群体动态过程、群体各要素的互动演化机理,揭示资源稀缺激发群体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总结见表2。
(四)数字经济下创新生态环境作为调节性因素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开放式创新、顾客参与创新、创新生态系统等模式不断涌现,推动了创新资源的共享、集成、利用和再创造。然而,关于资源稀缺对创造力影响的边界条件分析,却较少关注数字经济作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独特性,解析该背景下如何匹配最佳环境变量以提升个体创造性及群体动力机制的效果。数字经济已然引发创新支撑、创新流程和创新逻辑的深层次、系统性转变[47],企业创新模式趋于分布式、开放化和开源化。从单一创造模式向多源创造模式演化,在内外共同作用下,知识的跨界传播与交互促进不同主体在数字化空间中密集地 虚拟集聚[48]、共融共生、液态合作(liquid collaboration)[49]。那么,基于数字技术赋能,可调动创新生态圈在价值创造上的协同,以应对企业创新投入“人、财、物、时”等资源约束瓶颈、内部资源不足的挑战。因此,未来研究需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考虑数字技术、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政策和机制等创新要素的新特点,全面阐释数字化、开放式、网络性创新生态环境对资源稀缺与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
六、讨论与结论
综合以上“资源稀缺对创造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文献梳理,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得到如图3所示的整合框架。
常言道,“需要乃发明之母”,于企业而言,资源稀缺不应仅被视为某种威胁,也并非绝对的理想或不理想状态,在一定条件下更可能成为创造力和创新绩效的触发器,转化为企业优势。“戴着锁链舞蹈”能让其更快做出反应,更充分利用竞争者所忽视资源,并创造性地瞄准新目标市场。然而,当前关注资源稀缺情境并探讨其对创造力影响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仍不多,研究历程也尚短,特别是国内研究较为缺乏,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延展,立足中国情境进行研究。而从现实背景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新常态、新环境将驱动企业开展有意义的创新,在资源稀缺更为突出的情形下经营管理,诸如经济低迷和衰退,动态、超强、异常激烈的竞争,匹配金字塔底端资金匮乏人群的需求,在新兴市場追求增长,开发生态友好型产品的环保约束,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各种资源短缺等,那么,有关资源稀缺与创造力的研究具有极大发展前景,以帮助企业实践应对更为普遍、多样和严峻的资源稀缺和约束问题,并实现创造性和创新活动的成功。
[参考文献]
[1]曲冠楠,陈劲,梅亮.有意义的创新: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交互耦合框架[J].科学学研究,2020,38(11):2058-2067.
[2]VAN KNIPPENBERG D. Team innovation[J].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7,4:211-233.
[3]AMABILE T M, PRATT M G. The dynamic 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making progress, making meaning[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6,36:157-183.
[4]SHARMA E, ALTER A L. Financial deprivation prompts consumers to seek scarce good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39(3):545-560.
[5]MEHTA R, ZHU M. Creating when you have less: the impact of resource scarcity on product use creativ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6,42(5):767-782.
[6]SHAH A K,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J]. Science, 2012,338(6107):682-685.
[7]HAMILTON R, THOMPSON D, BONE S, et al. The effects of scarcity on 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9,47(3):532-550.
[8]陈辉辉,郑毓煌.创造力:情境影响因素综述及研究展望[J].营销科学学报,2015,11(2):51-68.
[9]AGGARWAL I, WOOLLEY A W. Team creativity,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style diversity[J]. Management science, 2019,65(4):1586-1599.
[10]CUNHA M P E, REGO A, OLIVEIRA P, et al. Product innovation in resource-poor environments: three research strea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31(2):202-210.
[11]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1): 68-78.
[12]HENNESSEY B A, AMABILE T M. Creativit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0,61(1):569-598.
[13]MADJAR N, GREENBERG E, CHEN Z. Factors for radical creativity, incremental creativity, and routine, noncreativ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1,96(4):730-743.
[14]OHLY S, FRITZ C. Work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 appraisal, creativity, and proactive behavior: a multi-level stud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31(4):543-565.
[15]BURROUGHS J E, MICK D G. Exploring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 creativity in a problem-solving context[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4,31(2):402-411.
[16]SACRAMENTO C A, FAY D, WEST M A. Workplace duties or opportunities? challenge stressors, regulatory focus, and creativity[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3, 121(2):141-157.
[17]SHAO Y, NIJSTAD B A, TUBER S. Creativity under workload pressure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paradoxical leadership[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9,155:7-19.
[18]ACAR O A, TARAKCI M, VAN KNIPPENBERG D.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under constraints: a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ve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45(1):96-121.
[19]BENDOLY E, CHAO R O. How excessive stage time reduction in NPD negatively impacts market value[J].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6,25(5):812-832.
[20]VOSS G B, SIRDESHMUKH D, VOSS Z G. The effects of slack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threat on product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51(1):147-164.
[21]AN W, ZHAO X, CAO Z, et al. How bricolage drives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8,35(1):49-65.
[22]SELLIER A, DAHL D W. Focus!! creative success is enjoyed through restricted choice[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1,48(6):996-1007.
[23]MOREAU C P, DAHL D W. Designing the solution: the impact of constraints on consumers’ creativ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5,32(1):13-22.
[24]SCOPELLITI I, CILLO P, BUSACCA B, et al. How do financial constraints affect creativity?[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31(5):880-893.
[25]VAN RIJNSOEVER F J, MEEUS M T H, DONDERS A R 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status and recent experience on innovative behavior under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J]. Research policy, 2012,41(5):833-847.
[26]MARGUC J, VAN KLEEF G A, FRSTER J. Welcome interferences: dealing with obstacles promotes creative thought in goal pursuit[J].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5,24(2):207-216.
[27]MIRON-SPEKTOR E, INGRAM A, KELLER J, et al. Micro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aradox: the problem is how we think about the proble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8,61(1):26-45.
[28]TRUJILLO C A, ROSA J A. Consumer creativity influenced by hope, integral emotion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17,41(5):576-586.
[29]DE DREU C K W, VAN DIJK M A. Climatic shocks associate with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Plos one, 2018,13(1):e190122.
[30]MANI A,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et al.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J]. Science, 2013,341(6149):976-980.
[31]CANNON C, GOLDSMITH K, ROUX C, et al. A self-regulatory model of resource scarc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9,29(1):104-127.
[32]ROSSO B D.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s: exploring the role of constraints in the creative process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4,35(4):551-585.
[33]KHEDHAOURIA A, MONTANI F, THURIK R. Time pressure and team member creativity within R&D projects: the role of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sourc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7,35(6):942-954.
[34]AKGN A E, BYRNE J C, LYNN G S, et al.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urbulent environments: impact of improvisation and unlearning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7,24(3):203-230.
[35]WEISS M, HOEGL M, GIBBERT M. How does material resource adequacy affect innovation project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7,34(6):842-863.
[36]VOGELGSANG L. Transition rather than balance: organizing constraints for collective creativity in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J].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0,29(3):413-423.
[37]WU L, LIU H, ZHANG J. Bricolage effects on new-product development speed and creativ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70:127-135.
[38]劉振,丁飞,肖应钊,等.资源拼凑视角下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2019,16(7):1006-1015.
[39]孙永波,丁沂昕,王楠.资源拼凑与创业机会认知的对接路径[J].科研管理,2021,42(2):130-137.
[40]李晓翔,霍国庆.资源匮乏、拼凑策略与中小企业产品创新关系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3):41-55.
[41]沈颂东,陈鑫强.资源拼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商业研究,2020(5):10-17.
[42]于超,朱瑾.协同进化的实现:从知识共享、资源拼凑到社群新稳态——基于五大在线社群的经验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8(7):124-135.
[43]王琳,陈志军.价值共创如何影响创新型企业的即兴能力?——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11):96-110.
[44]ORTMANN G, SYDOW J. Dancing in chains: creative practices in/of organization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8,39(7):899-921.
[45]吴增源,周彩虹,易荣华,等.开放式创新社区集体智慧涌现的生态演化分析——基于知识开放视角[J].中国管理科学,2021,29(4):202-212.
[46]ALLEN B J, CHANDRASEKARAN D, BASUROY S. Design crowdsourcing: the impact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of sourcing design solutions from the “crowd”[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8,82(2):106-123.
[47]刘洋,董久钰,魏江.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7):198-217.
[48]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6):135-152,250.
[49]BARDHI F, ECKHARDT G M. Liquid consumption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7, 44(3):582-597.
How Does Resource Scarcity Affect Creativity?
—A Cross-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Wang Jing, Li Yimin, Zhu 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Creativity is the key for local enterprises to ge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However, due to scarcity in human, financial, material, and other resources, endeavors toward creativity are greatly challenge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literature regarding to creativity under resource scarcity. Firstly, the concepts of resource scarcity and creativity are introduced. Secondly, we sort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with respect to the effects of resource scarcity on creativity. Thirdly, consider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reativity and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 scarcit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topics, status, and development concerning to how resource scarcity influencing creativity. Meanwhile, we put forwar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about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responses. Next,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gap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vestigating combinative effects of resource scarcity; exploring potential mediating mechanisms that are missing; examining group creativity and the involved social interac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digital economy. Finally, we summariz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pose an integrative research frame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scarcity and creativity.
Key words:resource scarcity; creativity; individual creativity; group creativity; group process; digital economy
(責任编辑:李 萌)
收稿日期:2022-04-19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众包竞争下资源稀缺对参与者创造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2020EGL009)。
作者简介:王静(1986—),女,四川泸州人,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营销、创新管理;李义敏(1982—),男,河南南阳人,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品牌管理;朱強(1988—),男,山东阳谷人,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