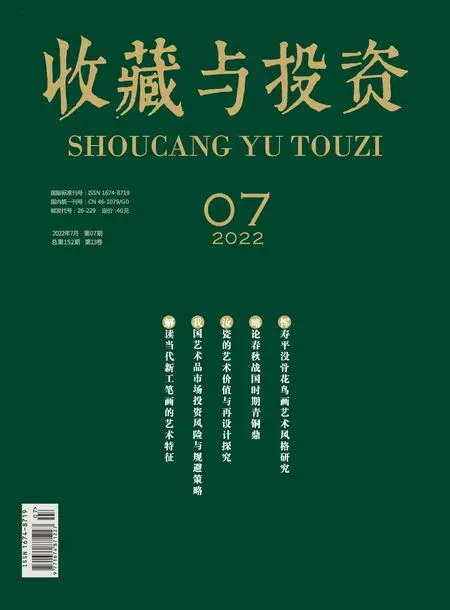苏轼诗书作品的情感互融表达
——以《梅花诗帖》为例
秦文文(韩国全州大学,韩国 全州 22320)
苏轼因《湖州谢表》等诗词中有攻击新法和讽刺时政的词句而被弹劾,酿成“乌台诗案”,入狱达四月之久。他在绝望中悲叹“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道出了作者面对死亡时绝望的情感。他曾一度渴望“致君尧舜”,希望能够辅佐明君成就一代伟业,心怀雄心壮志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此时却自身难保,哀叹自己壮志难酬。后因其弟苏辙上书力保,释放后苏轼被贬谪于黄州做团练副使。出狱后苏轼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轼把自然与人生结合,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诗人对命运的无奈喟叹,寄意深刻。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内心造成了严重的迫害。
木斋师在《苏东坡研究》一书中说:“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了苏轼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不言而喻,在文学界,学者们一致认为谪居黄州时是苏轼书法、诗词、散文等创作的最高峰。纵观苏轼谪居黄州的五年,笔者将其诗词和书法作品的情感表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绝望、悲叹、寂寞、孤独、恐惧到庆幸、欣喜;从晋风唐法的刻意模仿到随意挥洒的写意之风;从“却对酒杯浑是梦”“此灾何必深追咎”等诗到恢复自信,展露其孤傲、坚毅的一面。在诗词《狱中寄子由二首》《出狱次前韵二首》《梅花二首》和书法作品《梅花诗帖》《定惠院日夜偶出诗稿》之中,苏轼的情感表达和心理波动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阶段,从适应贬谪黄州生活到解放自我;从孤独、惶恐、痛苦到回归世俗生活的以俗为美、化俗为雅;从忘怀得失到明朗旷达的人生观;从参禅研佛到直抒胸臆的书作。他在《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与王定国书》之中显露出躬耕生活的独乐情感;在《黄泥坂词》《日日出东门》之中展现出寄情山水、亲近自然、忘怀得失的态度,进入率性豁达的情感世界;在《安国寺浴》《与王佐才书》之中彰显出超脱现实和心绪平静的人生观和情感观。谪黄州期间,苏轼并非一味潇洒、旷达,其间也难免有消沉之情怀,如《寒食雨二首》,除了反映其内心情感变化之外,更深层次地诠释了苏轼追求以俗为美、化俗为雅的倾向。在《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卷》书作中,受禅宗佛法洗礼之后,其笔到之处直抒胸臆。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此论强调运用形象传达情感,本文意在通过《梅花诗帖》书法作品剖析苏轼怎样运用“书法形象”和“诗词形象”来诠释和表达谪居黄州初期的情感。

苏轼《梅花诗帖》局部
一、《梅花二首》诗中残梅写意的情感表达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有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刘勰之语是以情、理来界说“志”,认为诗文是诗人情、理的表现,情、理和言、辞的关系是“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关系。在创作中,诗人的内心情感由隐蔽趋向显露,形成诗词作品,又因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情志的不同而影响作品风格。因内而符外,所以诗词作品的风格必然体现出诗人的个性。
《梅花二首》是苏轼谪黄州途中所作,刚刚从黑暗之狱的绝望、孤独、恐惧中回归光明,看到满山遍野的梅花,内心感慨万千,不能自已。此咏梅诗,是苏轼借梅以言志,并非简单地咏梅的艳丽之美和风雅之趣,而是写出了苏轼此时的心境,写出了他独有的特质和个性。
《梅花二首》(其一)“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第一句用以动衬静的手法写出梅花生长的环境是幽谷之中的荒野草棘中,体现了梅花蓬勃的生命力与傲然不群的品格。对于诗文的内容,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实写的景语,要结合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情志理解其深意。第一句中的“幽谷”和“草棘”是苏轼当时心境与处境的真实写照。“幽谷”道出了因被贬,遭亲朋背弃,饱受折磨的苏轼内心的孤寂。“幽谷”一词体现了苏轼内心的“幽孤”;“草棘”阐明了梅花生长的环境之恶劣,折射出苏轼之前所处的政治环境如荆棘草丛一般。苏轼借梅花生长环境之险恶,吐露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生于如此环境的梅花都可以自由绽放,苏轼的内心也像梅花一样于孤寂中寓有倔强和顽强,于平静中含有奋争和孤傲。随后他借用“的皪梅花”隐喻自己遭遇诬陷的态度。“乌台诗案”并没有让苏轼一蹶不振,其在狱中听闻此案有峰回路转之机,内心的兀傲即显露出来了。在狱中,他曾作咏竹诗,借竹表达自己“可折不可辱”的兀傲气概。第二句暗喻了诗人刚经历的惨痛劫难和内心饱含的怨意。句中“东风”在诗词之中多释为万物复生之象征,而在苏轼诗中则是以“狂暴形象”出现,并不是“复生”,而是任意摧残“的皪梅花”,此处苏轼的心境已不言而喻。
《梅花二首》(其二)“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第一句表达了诗人渴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无奈现在境遇与深幽中的梅花一般,无人赏识、无人问津。“深幽”暗喻了诗人内心的愁怨与哀伤;梅花自开自落,凄凉忧愁,流露出诗人对梅花境遇的同情,同时也道出了诗人内心的无聊、孤寂与痛楚。第二句诗人庆幸大自然的眷顾,可以通过弯曲的清溪顺流至黄州,惆怅之余又有些许惬意。句中“幸”字,体现出诗人矛盾的心理变化。“幸”字指梅花自开自落,任凭“东风”摧残的环境,这是梅花的不幸。反观苏轼,满腔政治抱负遭小人陷害无处施展,此乃诗人之不幸。苏轼并未一味地悲情哀叹,看到梅落清溪,随波逐流而未被污淖沾染,感悟此乃梅之大幸。反观苏轼,因“乌台诗案”脱离了官宦暗斗的职场,追逐自由豁达的人生,此乃苏轼之大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梅花二首》诗文表面为景语,实则为情语;表面写梅花,实则观照诗人内心情感的输出。通篇“以梅寓己”,将梅花的境遇与诗人的境遇融为一体。诗人描述了梅之生长环境,梅之受摧残,梅之不幸中寓大幸,通过“借梅”的手法,输出了诗人对所处环境、悲惨境遇波澜起伏的情感。
二、《梅花诗帖》中狂草恣肆的情感表达
《梅花诗帖》书法作品作于《梅花二首》之后,纵观其书法作品,唯有此作为大草风格。为何以大草形式书写,笔者认为其因素有四。其一,“乌台诗案”给苏轼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后遗症”,孤寂、痛楚、恐惧的情感输出唯有大草能够宣泄。其二,对早期书风,如晋风唐韵的突破和反叛,同时隐喻了书家以大草形式“反击”朝堂奸佞小人对自己的诬陷。其三,“致君尧舜”的满腔政治抱负和治世情怀无处施展,无奈、惆怅、绝望的情感宣泄。其四,大草本体所具有的情感宣泄特征。
未发生“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并不推崇狂草,他曾在《题王逸少帖》和《跋怀素帖》中评价张旭和怀素的草书:“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邵雍,字尧夫)不能辨,亦可怪矣。”苏轼认为狂草是书家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书写形式,呈现出来的是险怪之态,背离了苏轼“乌台诗案”之前推崇的晋风唐法。但是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随着人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苏轼的人生观、情感观、艺术观发生了颠覆。在《跋王巩所藏真书》和《跋文与可论草书法》中,他对怀素和草书有了新的评价。“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苏轼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得益于人生观、艺术观、情感观的转变,得益于草书的本体特征。苏轼有语“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可见,书法和诗词在情感上具有密切的互逆关系,也具有补充和完善书家内心情感的作用。我们从艺术特征、技术法则看《梅花诗帖》是怎样输出书家情感的。
《梅花诗帖》苏轼只写了第一首,前两行书风格调与诗词格调完美契合。行草中寓小草的形式,有端庄严谨的晋唐之风,虽略有拘谨之态,但不失天真烂漫之姿。笔墨如涓涓流水般在纸上自然流动,用笔沉着老辣,笔重墨浓跃于纸上,其形不失灵动之感,潇洒自得。从第三行到最后,神情大变,压抑、愤懑、悲凉的心情涌上心头,苏轼手中之笔突破晋风唐法的藩篱,由行草、小草平和的笔调转为狂草恣肆的笔调,形体结构亦是愈来愈大,内心情感突破了理性的束缚,笔随心动,挥洒自如、潇洒奔放、酣畅淋漓,形随情变,不计形体结构严整与端庄,任笔驰骋。行笔至最后,是苏轼情感宣泄的最高点,是对自己早期晋风唐韵的“颠覆”,是对当下境遇不满和奸佞小人诬陷的“反击”。此帖虽只有二十八字,但是每一笔、每一画、每一形体都表现出了诗人的情感、生命、思想,从行草、小草的平和沉稳到狂草的恣肆飞扬,心寓于笔尖,情满于纸卷,将内心的压抑、愤懑、悲凉的心境一泻而出。“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书法的形、意、韵、节奏是抒发诗词情感的补充和完善。《梅花诗帖》书法情感的奔放酣畅和桀骜不驯与文学情感中“以梅寓己”、坚贞不屈的气质是相互补充和关照的,不能将诗词内容和书法风貌割裂开来看苏轼所表达的内心情感。
三、结语
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谈论文学与情感时说:“情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灵魂和主线,是作家创作作品的灵感,作家就是通过文学创作来传达情感和反映生活的。”宗白华在论述书法与情感时说:“翰墨筋骨之玄妙,可以体现万物神情之精魄,汉字的线条、疾速、力度、结构,同时反映了人的情感,是书法者对物象生命规律、生命结构所应和的情感反应。”诗词运用修辞、言语、隐喻等手法表达诗人的内心情感,书法依靠线条的律动变化、形体大小疏密、篇章布局和气韵节奏抒发书家的精神和情感,文学和书法情感的表达媒介虽然不同,但是在苏轼《梅花诗帖》中二者完美契合。《梅花诗帖》的文与书所表达的内心情感完全一致,即为悲愤。诗文早于书作二十余天,来黄州途中的心境上文已明确陈述,二十天后苏轼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再次还原了当时内心的境遇,形成诗词情感与书法情感的共鸣关系。诗文彰显了诗人愁苦内敛之风,书法呈现了书家狂放不羁、桀骜不驯之态,表现了诗词情感与文学情感在审美上的互逆关系。无论是诗词中的“借梅寓己”,还是书法中的“狂草释情”,都充分而真实地输出了苏轼的内心情感,再现了苏轼的艺术情感状态。
①孔凡礼 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20年.
②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
③谢桃坊.苏轼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2017年.
④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