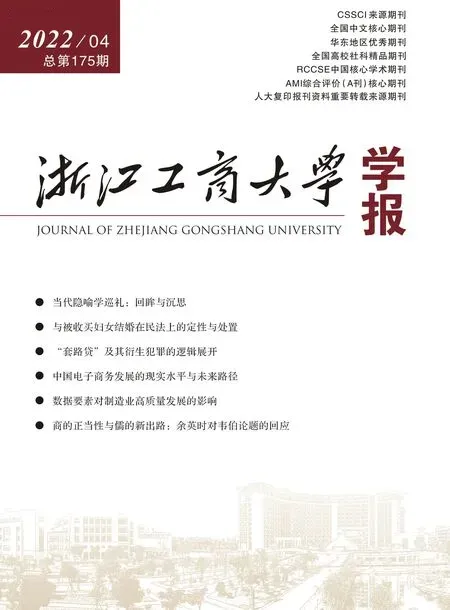当代隐喻学巡礼:回眸与沉思
——写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付梓40周年之际
孙 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一、 引 言
早在2500年前,东西方先贤便先后就隐喻的定义和功能展开了精彩的论述。西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曾高度颂扬隐喻为“天才的标志”(the hallmark of genius),无法后天习得,“无以隐喻,何以交谈”(all people carry on their conversations with metaphors)。东方儒学创始人孔子虽未单独论述隐喻,但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概述,亦在强调隐喻等修辞手段的装饰作用。鉴于两位学术泰斗的“定调”,尤其是亚氏“天赋论”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中西方学界均将隐喻视为一种稀松平常、其貌不扬的修辞格,而将其置于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狭域,着力刻画隐喻作为一种惯用修辞格在文学经典中扮演的角色。
在隐喻作为辞格的研究历史中,先哲学者前仆后继,探求隐喻锲而不舍,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令人扼腕的是,一众研究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热衷于细分隐喻的类型和范畴,剖析和阐释其在语篇和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些研究终究只是隔靴搔痒而难以深入本质。
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70年代末认知科学的腾飞,隐喻研究在修辞范畴徘徊2000多年后重焕生机,派生出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理论、新流派。1979年,美国哲学青年Johnson远赴加州伯克利大学拜访好友兼乔姆斯基的弟子Lakoff。两人通过大量查阅大学生习作并研读Reddy刚发表的《管道隐喻》一文并于次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石破天惊地宣称:隐喻在人们日常交谈中俯拾即是,是人类将无限膨胀的外部世界和无比深邃的内心世界进行概念化的强大武器。隐喻是人们以简单熟悉、触手可及的事物来理解和处理复杂陌生、遥不可及的事物,贯穿于人类交际过程的始终,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须臾难离。究其原因,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汇资源终究有限,加之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类无法为日常交际中的这些新现象一一匹配专有词汇。鉴于此,我们便诉诸先前已经牢固掌握的语汇为新知、未知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铺路、服务,因而成就了隐喻作为概念化工具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究其本质,隐喻就是从源域向靶域的系统性单向映射。人们习惯并善于将已经获取的知识换用、套设在新兴事物上,以期了解、挖掘,进而为其所用。而隐喻将新旧两个概念连接并置,大大减轻了人们的认知负担,成为人们借旧事物掌握新事物、“温故知新”的不二路径和渠道。自此,隐喻不再囿于语言层面。相反,人类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这就是人类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架和限定的原因。隐喻之所以可能成为语言表达方式,是因为在人类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1]。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2020年正值《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付梓40周年。该巨著的正式出版,标志着隐喻研究实现了从传统修辞学和文学批评视角向认知概念化研究视野转变的范式革命。40年间,学界对隐喻的热情有增无减,中外各大学术期刊争相登载隐喻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发现,“隐喻热潮”经久不息。四十不惑,当前的首要任务便是总结当代隐喻理论,尤其是概念隐喻理论发端以来,中外学界在隐喻研究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应归结仍然存在的明显不足与疏漏,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拓展路径。
二、 由“论”向“学”:当代隐喻理论的学科嬗变与进阶
1993年,心理语言学学者Ortony再度发力,在1979年第一版《隐喻与思维》论文集的基础上,隆重推出了该书的第二版。该版最大的修订亮点在于收录了“概念隐喻理论之父”Lakoff所撰写的、多达50页的《隐喻的当代理论》。这篇重量级长文回顾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付梓后十余年间隐喻研究取得的成绩及其存在的不足和缺憾。以此文为标志,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大踏步迈进了当代隐喻理论(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CTM)的新时代。
在传统语言学理论中,隐喻被视为一种与思维无关的语言表象。隐喻表达式被当作与普通、日常语言完全相左的事物:日常语言之中没有隐喻,而隐喻使用的是日常规约性语言之外的机制[2]。该经典理论在千百年来的研究史中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因而并未遭到过多质疑。“隐喻”被定义为一种新颖、诗性的语言表达,其中一个或几个词语使用了非日常规约意义,传递相似的概念[2]。但是,Lakoff的当代隐喻理论认为思维中的隐喻并非偏误或稀少,恰恰相反,隐喻在人类的许多经验领域当中具有高度的规约性、普遍性和高频使用率。这是因为人们除了要与客观具象的物理世界打交道之外,还要量大面广地触及诸多抽象范畴。而这些抽象范畴就需借助隐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简单、具象、临近向复杂、抽象、遥远迁移和跨越。隐喻从原始的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樊篱中跃升而出,使得思维成为其第一性,而语言退居为第二性。Engstrøm[3]将当代隐喻理论的基本假设总结为: (1)隐喻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概念思维问题。(2)规约概念隐喻是一个概念格式塔(完形)结构(源概念)到另一个概念格式塔(完形)结构(目标概念)的部分映射。(3)隐喻映射是从源域到靶域的单向映射。(4)在规约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中,目标概念由源概念的部分内容构成。如果目标概念独立于源概念,我们就会联想到另一个概念。(5)规约隐喻不是命题。(6)规约概念隐喻可浓缩为:目标概念是源概念。此后,Bundgaard[4]归纳出当代隐喻理论的四大主张:(1)人类认知具有具身性,即概念结构的生成和获取都是通过人类身体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作用而实现的。(2)诸如物体、位置、动物等概念和结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由与环境的涉身性和知觉性互动达成的。(3)现实生活中除了存在大量衍生于自身经验和互动之中的概念和概念结构外,还有不少并非直接通过经验和互动获取的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的内容是通过来自生理的、直接体验到的源域结构的隐喻映射得到的。(4)隐喻映射不仅是一种语言操作,更是一种认知机制。隐喻表达之所以在语言中普遍存在,是因为人们只需要跨越字面意义、通过间接获取方式,就能够以更具体的语域来思考更抽象的语域。作为跨域映射的概念隐喻具有心理和神经—生物的真实性,在大脑创造意义的过程中真实运作。
当代隐喻理论从多层面、多角度考察隐喻现象,极大拓展了隐喻研究的疆界。学术的发展、理论的成熟、学科的构建和立足,主要关注两个指标:(1)是否具有一致、稳定的学科框架和是否拥有足够重要且高度聚焦的研究对象?(2)是否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来保证该学科的持续性发展?1993年由Lakoff率先开创的“当代隐喻理论”已经昂首阔步,完全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形成了颇具声势和威望的“当代隐喻学”。我们可以初步将其视为:以“隐喻”为研究基础来探索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门类和领域的一门平行于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学、话语分析、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传统学科分支的新兴语言认知科学。本文接下来将从理论和方法两个角度探讨当代隐喻理论跃升为当代隐喻学的学科演进历程。
(一) 当代隐喻学的理论滥觞与进展
在理论构建方面,中外隐喻界学者分别从自身学养和兴趣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隐喻理论。当代隐喻学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以及词汇语用理论等,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脉络论述如下。
1.概念隐喻理论。以Lakoff和Johnson为代表的概念隐喻学者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性、修辞性的,更是概念性、认知性的,是全人类认识并进一步把握世间万事万物的捷径和法宝。概念隐喻是高度稳定,甚至是固定的跨域实体对应范式[2]。一言以蔽之,隐喻的核心不在语言,而在于我们以一个心理域去概念化另一个心理域的方式[2]。总体而言,概念隐喻理论制定的从源域向靶域的单向映射,可以将原本属于源域的特征、属性、动作、关系等诸多元素投射至有待填补的靶域当中,从无到有,从零到一,以映射为核心运作工具,能够简便而清晰地阐释绝大多数规约隐喻用法。
无限扩容的、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与人类个体相对狭小且更新不及的知识储备之间日渐拉大的差距,迫使我们刻不容缓地借助隐喻机制来泛化、扩大化已经储存在自身长时记忆中的隐喻概念,通过隐喻催生新概念并以现有词汇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就是科学领域中“黑洞”“宇宙大爆炸”“电流”,经济学中“熊市”“牛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政治学中“道路”“旗帜”“舞台”“赞歌”“核心”等术语的派生依据。
2.概念整合理论。1998年美国学者Fauconnier和Turner指出,倘若隐喻机制集中体现人类大脑的运行机制,那么大脑这个“黑匣子”绝不可能像Lakoff和Johnson假设的那样简单易行,他们犯了严重的还原论(reductionism)错误。究其本质,隐喻具有阐释的不可预测性,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语境。基于此批判性认识,两人联手提出了三维立体和更为复杂的概念整合理论。他们认为,隐喻的关键在于两个输入空间的跨空间映射,这使其成为整合构式的绝佳选项。的确,我们已然发现整合空间在隐喻映射过程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除了学界所熟知的从源域到靶域的单向映射以外,整合空间也是隐喻运作的重要认知机制[5]168。隐喻话语的意义可以在概念整合网络当中得以表征。在该网络中,源域和靶域各自架构一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表征其输入空间的共同之处,而整合空间从其输入空间当中继承部分结构并产生自身的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在隐喻中源域兼容性的本质及程度与映射所发生的概念整合网络息息相关,其中涵盖单边网络、对称双边网络和非对称双边网络[6]166。Fauconnier和Turner[7]40提出,隐喻的源域和靶域是隐喻阐释的来源或曰母体,即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两者在隐喻发生时分别向第三个空间(类属空间)投射出两者共享的元素,为隐喻最终阐释奠定扎实的基础,最后再选取相关的元素投向第四个空间(整合空间),在该空间中交织、碰撞,最终形成既具有两个输入空间母体的原本基础,又有为其自身所独有的隐喻阐释项。该理论大大加强了二维、固定的概念隐喻理论的阐释力度和可信度,可用以解释诸多后者长期以来无能为力的新显、在线、实时发生,甚至个性化强、难度高的隐喻。由此,该理论的信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3.词汇语用理论。Blutner[8]于“Lexical Pragmatics”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词汇语用学是试图为与词汇项目的语义不充分(semantic underspecification)的系列语用现象提供一套系统的阐释方案的研究领域。但在文中,Blutner却对人类话语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语义不充分现象——隐喻只字未提。作为“关联理论”开创者之一的英国语用学者Wilson,近年来与其得意门生Carston一道,开辟了词汇语用理论的隐喻研究新路径。根据近来植根于关联理论的词汇语用学(Lexical Pragmatics),获取隐喻性词语的意图意义需要调整语言性编码概念,从而派生出一个外延大于词汇概念的特异性概念(ad hoc concept)。隐喻用法是一种松散的语言使用,与模糊语、夸张和其他意义拓展种类形成一个连续统[9]。Carston[10]将特异性概念视作类似于界域或门槛的概念,阐释者能通过调节或调整字面性编码意义的某一环节,即构建特异性概念,来适应我们的已知世界,而超越该环节则无能为力。就经典隐喻表达“我的外科医生是个屠夫”(My surgeon is a butcher)而言,承Vega-Moreno[11]的观点,我们对屠夫的认知并不包括屠夫是“无能的”和“危险的”这两种属性。受话者认为发话者所赋予屠夫的属性并不在“屠夫”所表征的意义范围内,所以必须通过搜索与屠夫无关的知识来解码这一隐喻。再如,“男人是狼”(Men are wolves)这一表达当中,狼作为捕猎者的属性被转换到男人的竞争属性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男人是肉食性的,即使这一特征确实为男性和狼族所共有。相反,该隐喻表达意味着男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具有攻击性,而这一特征并不专属于狼。笔者提出,所有类型的隐喻阐释都遵循同一个衍推理解程序,即在互调(mutual adjustment)过程中的明晰内容之上添加特异性概念,以确保获得预期的语境含义。Wilson和Carston[12]指出,隐喻总体的最终阐释项只有在满足听话者的关联性预期以及在衍推理解程式得以保证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明白发话者的语义意图。词汇语用理论主张,虽然隐喻可以发生在词语、短语、小句、整句、段落、篇章等各个语言层次上,但归根结底,绝大多数隐喻还是词汇性的,尤其是名词性的,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早已认定的“A是B”的程式。破解隐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便是厘清和确定隐喻的词汇属性。与关联理论一脉相承的是,词汇语用理论认为发话者一张口便是在发出明示刺激信号,而受话者就要据此解析、阐释信号。在隐喻阐释的过程中,词汇的内涵和外延会发生适当的扩大或缩小,与原本意义出现不小偏差。隐喻阐释的第一步,也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搞清楚其内涵和外延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拓展,在哪些方面得到了缩减。词汇语用理论充分考虑隐喻发生的语境因素,对隐喻进行鞭辟入里的合理衍推,为纯粹认知路径的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提供了可选的第三条路径。
诚然,日新月异的当代隐喻学理论发展远不止于此。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隐喻神经论[13]、凸显论[14]、隐喻生涯论[15]、知觉模拟论[16]、“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LCCM)[17]等,不一而足,各具特色,从各个角度不断丰富、充实着当代隐喻学,促其日渐成熟。
继往开来,承续当代隐喻理论过去40载辉煌学术成就,学界如今的首要任务便是将其提升和优化为更高层次、更高级别的当代隐喻学。而这一艰巨工作的第一要务便是为其做出更精确的定义。基于以上对当代隐喻学的理论脉络梳辨,本文将“当代隐喻学”权益性地界定为:一门合适的以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和词汇语用理论等为主要理论来源,以一揽子人类“隐喻”概念化现象为关键词和研究对象的语言认知科学。当代隐喻学已经成为语言学、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考察隐喻机制在本学科、本领域一条“赖以生存”的重要线索。
(二) 当代隐喻学的研究方法盘整
就研究方法而言,当代隐喻理论鼻祖Lakoff和Johnson主要依靠本族语者的敏锐语感和经年积累的学者直觉。这样做的漏洞和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出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当中的隐喻示例是学者凭空“创造”和炮制出来的,不具普遍性,不足以采信。另一方面,无论是初始的概念隐喻理论,还是作为最新发展的概念整合理论,抑或是词汇语用理论,归根结底都还是一种理论假设,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也是迄今为止各家理论甚嚣尘上、各执一词的根本原因所在。基于以上研究方法的劣势和本源性缺陷,当代隐喻学者痛定思痛,为了实现自我救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
1.语料库研究法。目前隐喻研究方法所采集的语言证据通常来源于学者直觉或者少量的文本集合。随意提取出来的隐喻语例,通常并不具备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此背景下,自然语篇当中的证据对于引导和补充学者直觉至关重要[18],语料库研究对隐喻研究的价值显得弥足珍贵。语料库方法论为可靠描述语言性隐喻的定性语境和用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便利与保障。可以手动搜索的小型语料库和超过千万词条的、运用关键词索引(concordancing)和自动生成频率表(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requency lists)的大型语料库,为隐喻分析带来规模可观且合理可靠的语言数据[19]。
隐喻用法的甄别和理解如同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学者只片面地关注后者,而极大地忽略了前者的存在。其实,隐喻的识别与提取是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的前提和基础,决不能等闲视之。由于隐喻不具备如明喻一般明显的“修辞标志语”,没有特定表面形式可寻,这为隐喻的甄别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以早期的当代隐喻研究过度依赖于研究者的内省语料并予以泛化,具有方法论上不可逆的漏洞,饱受实证主义的诟病。
基于扎实的隐喻理论训练的语料库语言学者为传统的当代隐喻学研究带来了方法论方面的革命性进步。该方法倡导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由研究者尽可能构建大规模的特定话语类型语料库;其次,多次、反复地细读小规模语料(至少占语料收集总量的10%);再次,根据研究者自身经年累月的学者直觉大体确定隐喻范畴和领域;又次,查阅全文词典,核实与前一步确定的隐喻范畴和领域相近的备选项和关键词;复次,通过Wordsmith、Antconc等语料库工具初步检索出可能性的隐喻用法;最后,再次定性地根据学者直觉筛查语料库检索结果,剔除可能的字面性用法,最终敲定隐喻用法的总数。另外,还可借助英国兰卡斯特大学Rayson教授于2008年开发的Wmatrix软件为一切词语切分并标注语义域,用作界定和区分隐喻类别的尝试和方法[20]。需要指出的是,Rayson教授设计该软件的初衷并非解决隐喻的提取问题。在初步借助索引程序Wmatrix 执行搜索的前提下,唯有经验丰富的分析者方能剔除那些“不地道的隐喻”。某些隐喻出现在半固定的搭配短语中,或出现于暗示隐喻用法的某个主题中。语料库仅呈现了某词汇场(lexical field)诸多类型中的一个表征,尚有大量的语词分居搜索词(形符)左右。研究者需按照自身对“隐喻”的理解,依循学术直觉,方可判断语词是否为隐喻。
2.神经、心理实证研究法。当代隐喻学的传统研究完全依赖于学者直觉的内省法和文献法。早期隐喻认知研究大多采用的反应时技术和同时期的以Ortony、Gentner、Glucksberg等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相继提出的比较模型、结构映射模型和范畴赋予模型,从心理学角度进一步丰富了隐喻的跨学科维度。
近40年突飞猛进的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为当代隐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可能。尤其是眼动、脑成像及电生理学技术在隐喻理解研究中得以应用,为揭示隐喻加工过程提供了更可靠的证据[21]。具体说来,眼动仪可以观察受试者在阅读隐喻过程中眼动的具体区域和注视点停留的精确时间和轨迹;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可以通过采集头皮生理电来窥探脑区的活动情况,以毫秒级的精确度记录隐喻加工的确切时间;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影像学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血液动力方向的改变,可以精确地锁定隐喻发生时受影响的具体脑区,并可以根据实验目的进行相关干预,适用范围广泛。结合此类先进设备和仪器,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客观地实时在线观察发话者和受话者交谈时的所思所想,这不仅为当代隐喻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实验保障,还为其跻身成为一门令人信服、客观公允的人类社会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有当代隐喻学同仁尝试倚仗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领域的先进设备和仪器,设计眼动、ERPs及fMRI等实验来实时在线考察人类大脑在加工隐喻时的运作机制、左右脑区、激活程度、加工时长、脑电波动、精确激活部位等一系列问题,为其理论假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隐喻是允许我们创造性地拓展词语意义限制的普通语言元素。但隐喻具备的新颖性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在线创造新意义或者从记忆中索回先前已知的隐喻意义。这些变体影响着获取隐喻加工的执行控制力(executive control),而这可以通过记录受试者自然地阅读含有隐喻的句子时的眼动情况(eye movements)而达成[22]。人类语言所具备的高度动态性使得所感知的意义能够与不断快速变化的语境相适应,该适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以新颖的方式去形成原创的意义。ERPs有助于发掘规约隐喻和新奇隐喻以及二者相互切换背后的神经—认知机制[23]。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实验研究作为能够直接观察活体大脑内部运作的新工具而得以蓬勃发展。同时,语言实验研究剥离其初始阶段对字面性语言的聚焦,转而关注更加复杂和有趣的隐喻语言领域。ERPs实验中所检测出来的大脑的电生理性(electrophysiology)便对隐喻语言研究助益不菲[24]。此外,根据Eviatar和Just[25]所做的fMRI实验,语言刺激的新颖性影响着脑半球的参与度。新颖隐喻比直白句在右后上颞回(right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gyrus)部位激活度更高,而熟悉隐喻在左额下回(left IFG)和双侧下颞皮层(bilateral inferior temporal cortex)部位激活度更高。认知心理、认知神经实验的贡献在于其为评估人们无意识地知晓不同抽象概念的隐喻性和涉身性理解提供了多种间接方法[26]。
纵观当代隐喻理论在过去40年间的发展,其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均取得了斐然成就。本文不揣冒昧,将“当代隐喻学”进一步界定为:一门以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和词汇语用理论等学术派别为主要理论来源,以语料库和学者直觉充分结合为基本的隐喻甄别方案,以Eye Tracking、ERPs、fMRI等认知心理、神经生理实验为依托,以一揽子人类“隐喻”概念化现象为关键词和研究对象的语言认知科学。然而,要将当代隐喻学提升和优化为更高层次、更令人信服、在语言学之林占据一席之地的独立学科则任重而道远。本文接下来将从七个方面沉淀和归结该学科目前仍然存在的漏洞与弊端,以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三、 当代隐喻学发展之沉思
斐然成绩已然成为过去,当代隐喻理论作为相对年轻的理论,仍需继续理论探索并寻求更多实证支撑。这不仅需要更加细致地探索语域的概念,尤其是隐喻操作中语域类型和抽象度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参考一系列补充视角来探讨,包括涉及语域的实体性本质(ontological nature)、类属层次(level of genericity)、源域与靶域对应的方式以及隐喻运作的复杂性程度[27]。当代隐喻学已经屹立于传统语言学门类之林,受到了越来越多语言学者的青睐与关注,学术标签日益显著,学术界承认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当代隐喻学发展到今天,光荣与掣肘并存,成绩与不足同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 理论体系整合有待完善,框架搭建还未稳固
与其他地位稳固的语言学派及其相对清晰的脉络相比较,当代隐喻学虽然历经40年的发展,但仍缺乏一套可靠、广为学界承认、具有较强涵盖性和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已有的众多理论流派,包括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词汇语用理论等各自为政,无法说服彼此,理论可信度有限,学术漏洞比较明显。即便已有学者尝试将当前的理论分支盘整、汇聚到一起,将各自的理论优势和特长汇为一处,融为一炉,比如Yeshayahu Shen[28]将图式模型和范畴模型结合、Tendahl 和Gibbs[29]将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结合的尝试较为典型,但总体上规模较小,还未成气候,未见统一。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蓄意隐喻理论和语法隐喻理论将单纯以“认知”为朝向的隐喻研究推进了大大的一步。
隐喻不仅是语言和思维的事物,还隶属于交际的范畴。蓄意隐喻揭示了隐喻的交际维度,与隐喻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一种特定交际途径的价值有关,这一维度在当代隐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弃之不顾。隐喻不仅是一种借由概念结构来嫁接概念域或心理空间的思维产物,还是运用语境中的表达式来标识思维中跨域映射某个方面的语言要素,更是该表达式提示该隐喻是否对于话语者具有特定价值的交际工具。基于隐喻“语言—思维—交际”这三个相互依存的维度,Steen[30]提出,当隐喻的结构暗示出受话者必须暂时将其注意力从话语的靶域转移至由其激活的源域,该隐喻用法就是蓄意性的。蓄意隐喻理论质疑无意识隐喻的解释力,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代隐喻理论所忽视的意识性问题,这一切都是对目前学术方向的修正,能够极大地拓展当代隐喻理论的外延,为其可持续发展平添了一条富有开拓精神的进路[31]。重新审视的隐喻交际维度呼吁我们将传统修辞学最为重视的新颖隐喻与认知语言学流派更加关注的规约隐喻统筹起来,将有意识和无意识结合起来,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除了蓄意隐喻理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鼻祖Halliday顺应隐喻研究汹涌澎湃的大潮而开创的语法隐喻理论。他指出,语言由不同的级层构成,下至词语、短语,上至段落、语篇,而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切换转移。例如,在英语典型的名物化现象当中,动词“modernize”可以转换为名词“modernization”。语言单元之间的移转腾挪促使语言能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符合特定场合的意义。英语当中存在许多与“Mary saw something wonderful”意义相同的表达,诸如“Mary came upon a wonderful sight.”和“A wonderful sight met Mary’s eyes.”等语法隐喻变体,虽然其结构的复杂度有所不一[32]322。语法隐喻学者将具有语义矛盾的隐喻称作词汇隐喻(lexical metaphor),而语法隐喻是相对于缺省性过程的选择,具有语义派(onomasiological approach)和符号派(semasiological approach)两条路径[33]。令人遗憾的是,认知隐喻学派与语法隐喻学派缺少有效的交流互通,不相为谋,没有将各自的理论优势和特长充分地发挥出来,遑论齐心协力地揭开困扰学界千百年来隐喻机制的神秘面纱。
(二) 隐喻甄别程序和隐喻理解的认知神经过程仍未解锁
国际隐喻兴趣小组基本上提出了一系列隐喻存现条件,并以此为契机制定了一套比较理想、可信的定性隐喻提取程序[34-35],甚至有学者基于此提出了多模态隐喻的甄别程序[36]。前文提到,为避免本族语者语感和学者直觉在隐喻甄别中的主观性,研究者们借助于语料库,利用Wordsmith、Antconc、Wmatrix等软件来提取隐喻,为传统的当代隐喻学研究带来了方法论方面的革新。目前学界尚未研发出一套集定性和定量分析优势于一体的、能够穷尽性地提取所有隐喻用法的甄别总程序,两派学者并未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充分融会贯通。
同时,隐喻理解的神经基础也还未锁定确认。隐喻理解究竟涉及大脑的左半球还是右半球,学界仍然争执不休。在首批考察右半球对隐喻刺激理解的研究中所用的方法是观察大脑损伤病人。但由于病人的损伤(lesions)部分和医疗语言干预的潜在影响缺乏同构性(homogeneity),隐喻理解的神经机制研究进展缓慢[37]。此外,在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由于各项实验测试目的、规模大小、受试群体代表性、设计过程统一性、操作时间、设备精确度等各不相同,这些实验的数据结果还不足以支撑当代隐喻学的各项命题,内省法和示例法仍然是当代隐喻学的主体研究方法和路径。眼动、ERPs和fMRI等实验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和长项,合作分工,与行为实验前后鱼贯进行,连续设计,形成合力,勾勒出隐喻发生的整体大脑图景。要解决相关问题,需要现有隐喻研究者拓宽视野,在跨学科的视角下展开更具说服力的神经、心理学实验。
可见,当代隐喻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促进定性与定量融会贯通的隐喻识别程序的构建,同时在心理神经实验的设计上需要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提升实验实证的信度效度。
(三) 多模态隐喻研究领域缺乏普适性证据
在当代隐喻学40载的演进过程中,文字性隐喻一直是研究的核心与重点。但随着当代通信传媒技术的发展,语言文字逐渐让位于声光电等其他传媒形式和渠道。这些交际路径,或曰模态充分利用人类的视听嗅味触等感官通道,多快好省地传递信息和内容,极大地推动和增进了人们接收和吸纳知识的速度和步伐。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Forceville是倡导大规模开展非言语多模态隐喻研究的领军学者,近年成果不断。Forceville[38]将多模态隐喻界定为:源域和靶域分别完全或者主导性地由不同模式表征的隐喻类型。定量的“完全或者主导性地”显得十分必要,因为非言语隐喻经常同时以一种以上的模态暗示源域和靶域。概念隐喻理论的一大严重桎梏在于其长期以来在研究概念隐喻言语表现的同时宣称隐喻“不仅是一种辞格,还是一种思维方式”[2]。这种对概念隐喻言语表现的单边研究注定会掩藏和忽视隐喻以电影、音乐、舞蹈和手势等非言语或者部分言语呈现的方方面面。以语言学为朝向的隐喻理论需要理解隐喻在不同媒介话语当中的作用,从而补充完善其在认知中的功能[39]。但由于其新颖的跨学科属性,多模态隐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未与艺术学、设计学和美学充分地融合、并进,研究对象也基本局限于相对简单、二维的漫画、图片、宣传册等媒介,而对长时间的、实时播放或互动的电影、视频、游戏和VR应用等高水平、三维立体的语域涉足尚浅。
(四) 众多辞格的认知属性有待观照
当代隐喻学脱胎于拥有2000余年悠久研究历史的修辞学和文学批评,但其作为先进的语言认知科学并未显著地回馈本源学科领域,实现共同发展。作为概念隐喻理论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Gibbs[26]片面地指出,“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概念隐喻理论不是修辞性语言理解的总体和普通理论,因为其与反语、转喻和悖论法等修辞语言形式并不相关”。这一判断直接导致来源于同一母体的“隐喻”一枝独秀、独木成林,而除了转喻以外的矛盾修辞法、顶针、夸张、共轭、对偶、移就等一揽子辞格则无人问津,长时间躺在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摇篮里“沉睡”,成为无人待见的“灰姑娘”[40]。笔者坚信,如果隐喻的确是人类概念化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核心机制和锐利武器,那么出身相同的其他修辞格也绝不仅是修饰、装点性的“化妆品”,而在人类认知进化的过程中一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研究者接下来的任务应是条分缕析地厘定“认知隐喻”的存现条件,并将其运用在其他辞格之上,检验其是否符合这些存现标准,逐一考察这些辞格的认知属性,提升其在大脑认知中的作用和地位。
(五) 隐喻话语类型远未实现全景式覆盖和囊括
如果承当代隐喻学所言,隐喻是一个联结概念化和语言的凸显性认知过程,在日常交际和话语当中俯拾即是,那么在人类各种交际场合与语篇类型当中也理应随处可见。已有学者就按照隐喻方式构架的抽象概念的涉足范围予以尝试性地求证,包括情感[41]、自我[42]、道德[43]、政治[44-45]、科学[46]、文学[47]、疾病[48]、心理分析[49]、法律[50]、经济[51]、数学[52]等。但是学界迄今为止并没有就人们所熟知的外交、哲学、伦理、信念、理念、娱乐、教育、艺术、音乐等方方面面当中的隐喻语义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和阐释。研究各领域共有与特有的隐喻,多维跨域地推动隐喻扇面的展开,又能带动相关学科及领域对其自身进行隐喻反思。
(六) 跨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尚浅
单一语言内部的隐喻探索和厘定注定存在局限性。当代隐喻学的先行者Lakoff、Johnson、Fauconnier、Turner、Wilson、Gibbs等均无一例外是操单一语言的英语本族语者。他们凭借自身对隐喻事业的热爱和多年的学者直觉,假设相当一部分的隐喻概念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位于人类认知最底层、基于日常具身性体验的是数目极为有限的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s),而在具体话语情景中随机、突发的隐喻是在这些基本隐喻反复叠加、交织之后生成的复杂隐喻(complex metaphors)[53]。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全部基本隐喻均具有跨语言的相同性,不同的语言以系统的方式呈现出隐喻,这支持了隐喻作为主要概念性的、根植于人类共同经验的认知地位[54]。鉴于每种语言和文化的体验性焦距彼此不一,跨语言复杂隐喻也会以千姿百态的形式出现。任何隐喻表达都是具身性体验和特定文化模型共同作用的产物。学界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献致力于跨语言、跨文化的隐喻对比研究,在若干方面深入浅出地厘清阐明了隐喻的语际异同及其背后深刻的动因和理据。但鉴于全世界范围有7000多种语言,这些努力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较浅显和狭隘,有待大规模继续深化。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用各语言中发现的反例和特例来倒逼和反哺已有的隐喻主流理论,为构建更具概括力的当代隐喻学奠定坚实的语料和语言事实基础。
(七) 隐喻能力尚未与语言教学紧密衔接
当代隐喻学已经充分证明隐喻是人类须臾难离的概念化机制和表达路径。如果隐喻如此普遍地存在并在语言学本体当中且享有崇高的地位,那么其在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当中的重要价值也是毋庸讳言的。已有学者提出并验证了隐喻是本族语者熟练操作、运用母语的核心标志,考察语言能力是否习得和成熟的重要指标即其是否完全获得隐喻能力(metaphoric competence)[55-56]。学界已经展开了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整体是否具有正相关的研究,但是更加精细的隐喻能力与认知风格、性别、性格、动机、出身背景等因素的关系尚未验明,遑论在语言教学当中应当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和应对策略。同时,由于学术背景的界限,大多数的研究目前仅局限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辖域之中,其他语种的隐喻能力培养和一语向二语的隐喻迁移问题还是一片蓝海,亟待开采。目前当务之急是教育主管部门应早日认识到隐喻能力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大价值并将其早日编入教学大纲,做到纲举目张,以便广大教师能够按图索骥地将学习者的隐喻能力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融入并贯穿于语言教学的始终,令其体现在听说读写译等各个培养环节当中,促进语言学习者总体水平真正贴近本族语者的操用标准。
国内学者已凭借敏锐的目光关注到隐喻研究大潮的到来,深入浅出地引介了各派西方经典理论[57-58],也有学者成功地运用当代隐喻理论解释汉语现象[59]。令人扼腕的是,为中国学者独有的标签性成果还乏善可陈。尤其是在中国自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付梓以来,广大修辞学者砥砺前行,将祖国丰富的隐喻修辞资源深挖细耕,将其纵深切分为几百种类型。借助这些合理、精细的分类成果可为当代隐喻学的定义、存现条件、内涵外延、类型范围等关键性问题服务,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隐喻学过程中留下国人靓丽的身影和深刻的足迹。
四、 结 语
当代隐喻理论经过整整一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枝繁叶茂,从语言学大家族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万众瞩目的新兴语言认知科学——当代隐喻学。该学科成果不断,连贯有序,研究浪潮一浪高过一浪[60]。仅就国内“外国语言文学类”来源期刊而言,当代隐喻理论发表以后20年(1994—2013)以“隐喻”为关键词的论文已达到405篇[61],最近5年(2014—2018)又刊载了论文226篇[62],发文量持续增长,蔚为壮观,研究队伍不容小觑,从绝对数量上已可冠称为“学”。与此毗邻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也不遗余力地将当代隐喻学的相关先进原理和认识服务于自身学术领域,不断碰撞交织出璀璨火花,跨学科成果喜人。与此同时,学界同仁应时刻保持清醒的是,当代隐喻学虽已走过40年的发展历程,但其缺点和制约条件还很多,从理论建构到实验证明都远未成熟,未来发展之路还很长。认知语言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回顾当代隐喻理论已有重要成果和反思弊端不足的潮流[3-4,27,63-64],甚至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了改进和提升后的“新当代隐喻理论”[65]。当代隐喻学的定义和学术地位还未被全体学界广泛承认,隐喻的存现条件还未清晰厘定,隐喻的身份鉴定及其神经程序尚未破解,多模态隐喻的组成与表现还未浮出水面,隐喻的理解过程还未得到各种实验器材及实证设计的统一论证,隐喻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个性表征还未见真容,隐喻的跨语言研究还未大规模展开,仅凭英语单一语言所得的推理和结论还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隐喻能力也远未纳入语言教学的议事日程等,不一而足。但只要全世界学者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从沿袭自身学术背景,发挥各自学术特长与优势,集成合力,探索隐喻机制的神妙之处,就一定能够开云见日,终将为解密和开启人类认知的“黑匣子”打磨出一把金钥匙。承前启后,下一个40年是当代隐喻学框架确定、研究路径清晰明确、各种实验反复多次多角度验证和多语言、多领域细节性地研磨、考证的攻坚期,全球学术界重任在肩,系列成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