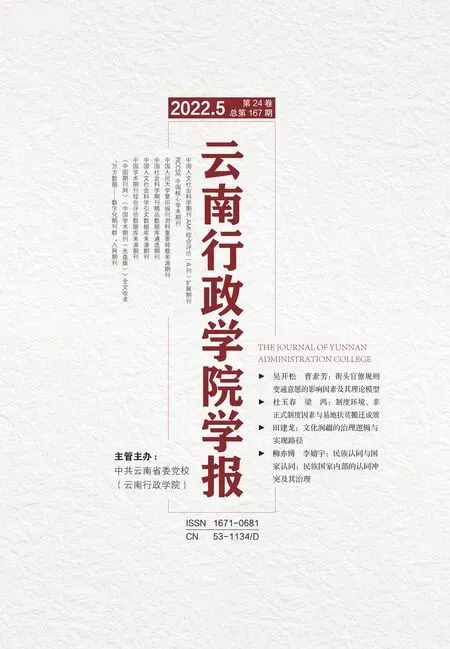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杜玉春,梁 鸿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杨浦 200433)
一、引言
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下,易地扶贫搬迁通过多方面再造,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区域性贫困问题。以“十三五”期间为例,易地扶贫搬迁全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 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 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 万余套,总建筑面积2.1 亿平方米,户均住房面积80.6 平方米①新华社.“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EB/OL].(2020-12-03)[2021-10-08].http://www.gov.cn/xinwen/2020-12/03/content_5566832.htm.。到2020年底,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总体上圆满完成。
然而,在过去几年,关于某个具体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出现不同程度或阶段性失败的新闻报道、研究并不鲜见。举个例子,2019年7月,《半月谈》对西部地区某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最终搬成“半拉子”工程进行了报道②半月谈,搬迁半悬:搬了房子,搬不了身子.(2019-06-28)[2021-10-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 637549954841213863&wfr=spider&for=pc.,记者发现在该县一些村庄里,房子虽已建成,但贫困户却多是“表上搬迁”①笔者注:“表上搬迁”指房子建好了,农户也乐意领新房钥匙,但是不花钱进行最基本的布置,更不在新房内居住,而是继续回到老房子生活。为迎接上级考评,基层单位多以领钥匙为标志,将这些实际还生活在原住房的农户在表上登记为“已搬迁”。。显然,这是建而不搬。现实中,还存在搬迁后又回迁现象。夏艳玲对广西巴马县内5 个易地扶贫搬迁点及2 个贫困村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110 个被调查样本家庭中,已搬迁家庭占比为80%,已经或者计划回迁家庭占比11.9%,未按计划实施搬迁的、也就是建而不搬的占比8.1%②夏艳玲.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09):7-13.。另外,移民搬迁政策在实践中还存在“搬富不搬穷”“背皮”搬迁等执行偏差现象③何得桂,党国英.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6):119-123.。
类似情况发生在不同范围内,概括起来,它们共同反映这样一个事实:易地扶贫搬迁在有些场景下顺利实施了,而在另一些场景下未能顺利运作。那么,政策绩效为何以及如何出现此等差异?本文认为,复合了制度环境因素的非正式制度会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产生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为检验这一观点,笔者以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模式为基础,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基于多个典型案例材料展开了比较分析,并最终予以确证。本研究可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三个:一是拓展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互动的经验研究范围;二是填补原有易地扶贫搬迁制度分析只是单纯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出发而缺乏对它们互动关系考察的空缺;三是丰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能产生过程知识,为实务界提供指引或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在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指(党和政府)“将居住在自然和生存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生产和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改变其现有的居住环境、生活和生产条件,使其能够融入现代社会,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接收到更多信息,受到更好的教育,为其彻底脱贫致富创造条件”④孙永珍,高春雨.新时期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理论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36):14095-14098.。赵双、李万莉从多个角度出发对既有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进行综述,结果显示学者们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论与发展演变、影响因素、效果评价、政策制定和执行、配套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在总体上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也存在数量少、分类不明确、理论和实证研究缺乏等不足⑤赵双,李万莉.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社会保障研究,2018(02):106-112.。许源源和熊瑛的综述性研究结论与赵、李的观点比较相似,发现既有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在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四个方面⑥许源源,熊瑛.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107-114.。
笔者近期也对易地扶贫搬迁文献进行过系统综述,只是集中于制度视角。在最为基础的层面,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一般指合约形式、治理结构或法律、政策和规定,后者指规范、习俗,等等①North Douglass C.,“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in Mary C.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New York,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p.247-257.②North Douglass 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鉴于易地扶贫搬迁本质上为公共政策,所以首先从正式制度出发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结果发现,研究者们或是从整体、或是从政策的某一或几个环节对政策绩效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其中包括了政策观念、问题确认、政策制定(方案)、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或转换等各环节。
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视角下的研究规模要小许多,李文钢基于对全国最大的一个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查指出,民族要素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良好治理不可忽视的因素,建议从个体相互嵌入和群体相互嵌入两方面开展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③李文钢.西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研究——以靖安新区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21(03):114-121.。罗银新等特别关注了迁移人员文化适应问题,认为这是一个从鸿沟到共生的过程④罗银新,胡燕,滕星.从鸿沟到共生:易地扶贫搬迁人员文化适应的特征及教育策略[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05):38-44.。关注移民文化方面的还有吴尚丽、周恩宇、卯丹和方静文,等等⑤吴尚丽.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文化治理研究——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9(06):21-26.⑥周恩宇,卯丹.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69-77.⑦方静文.时空穿行——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文化适应[J].贵州民族研究,2019(10):52-57.。此外,社会资本也是易地扶贫搬迁研究中比较受关注的一项非正式制度因素,农户的人际网络是构成生计能力的重要维度⑧夏艳玲.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09):7-13.⑨徐锡广,申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01):103-110.⑩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探索,2016(06):93-98.⑪周丽,黎红梅,李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J].经济地理,2020(11):167-175.,其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用的同时,可能影响移民的抗逆力⑫魏爱春,李雪萍.类型比较与抗逆力建设的内部差异性研究——以渝东M 镇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177-189.、适应水平⑬张会萍,石铭婷.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基于宁夏“十三五”不同安置方式的女性移民调查[J].宁夏社会科学,2021(03):163-178.、政策满意度⑭张广来,廖文梅.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03):185-195.⑮孙晗霖,刘新智,刘娜.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26-36.⑯曾维莲,杨文凤,孙自保.贫困人口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满意度评价——以西藏易地扶贫搬迁为例[J].科技导报,2020(13):113-121.。
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态度和行为,以及参与机制、信息资源、公开承诺等“非结构性因素”⑰何得桂,党国英.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6):119-123.也会对政策绩效产生影响,但由于易地扶贫搬迁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①王春光.政策执行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01):108-117.和“给予型”②徐欣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给予型政策与地方性秩序的张力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02):19-26.特征,研究者们主要还是从制度角度出发加以考察和分析。也就是说,虽然易地扶贫搬迁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农村社会与贫困农户,但出于在由完整的激励结构所形成的类强制执行机制下,发挥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以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因素的现实,制度分析成为了易地扶贫搬迁研究主要选择,并占据绝对多数。图1用数学集合语言描述了这种现状。此外,不同细分视角下的研究成果规模和占比也存在较大差异。

图1 以正式或(和)非正式制度为中心的易地扶贫搬迁研究成果分布图
当前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制度分析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缺乏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互动情形下政策绩效产生过程的关注及原因的解释。如图1所示,虽有一些研究者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同时纳入了分析视野,例如徐欣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与地方性秩序之间的张力③徐欣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给予型政策与地方性秩序的张力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02):19-26.,又比如马流辉基于西南山区M 镇的调研发现,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城市经济发展冲动一起导致易地扶贫搬迁陷入空间贫困,他们的研究都为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互动角度理解政策绩效差异提供了启示④马流辉.易地扶贫搬迁的“城市迷思”及其理论检视[J].学习与实践,2018(08):87-94.。但有关研究对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的分析几乎还付诸阙如;对非正式制度因素在由以上互动所形成的不同制度环境下如何影响制度成效的机制也未能阐明。本文将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类型,通过对相同社会空间中、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代表性非正式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揭示制度的非正式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成效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框架与假设
1.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在已有关于制度的正式和非正式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及对个体或组织行动的作用的文献中,平乔维奇(Pejovich)和彭玉生的论述被认为最具系统性和完整性①田丰,刘欣.制度环境、非正式规范与中国乡村小学兴办废存[J].社会科学,2019(07):55-66.②Victor Nee,“T he New Institutionalism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edited by Neil J.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49-74.③Alejandro Portes,“Social Capital:Its Originals and Applications in Mor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4,1998,pp.1-24.。平乔维奇首先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类型化④Svetozar Pejovich,“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arket and Moraltity,Vol.2,No.2,1999,pp.164-181.,然后他提出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交互命题。具体的,倘若正式制度的变化与既有非正式制度保持和谐一致,那么它们之间的互动常常会降低行动的交易成本,包括进行交易的成本和维护制度结构本身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富生产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反之,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它们的互动会通过增加交易成本,最终降低个人、社区或社会财富生产规模数量。
彭玉生在包括平乔维奇在内的前人工作基础上,明确了关系的分类依据,使得结果更具操作性⑤田丰,刘欣.制度环境、非正式规范与中国乡村小学兴办废存[J].社会科学,2019(07):55-66.,同时还指出每一类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大小和正式制度可能的执行效果。如表1(a)所示,彭玉生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然后考虑对行为的约束性质,将制度区分为鼓励、禁止和中性三种,最后将它们进行有序组合,得到9 个结果⑥彭玉生.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J].社会,2009(01):37-65、224-225.。9 种交叉列联结果又可归纳为5 种情形。一是法理主义——也就是以正式制度为(绝对)主导,非正式制度不在场(或微弱);二是规范主义——主要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而正式制度不在场;三是两相抵牾与冲突;四是两者耦合、一致;五是无论是非正式还是正式制度都缺失的情形——这是一种存在于理论中或极少数现实情境中的状态——常常不纳入讨论范围。基于其他四种组合,彭玉生提出了表1(b)所列示四个经验命题。

表1(a) 非正式与正式制度之间交互关系

表1(b) 基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所建构的四个经验理论
以上理论观点和判断,已经得到来自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的支持。美国城市中不同的少数族群居住区,它们都生活在相同的正式制度规则之下,但都保留着各自的文化和规范。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在经历快速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习惯。此类社会现实映照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交互性的理论观点。彭玉生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解释了中国乡村宗族网络与计划生育政策博弈过程及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产生。田丰和刘欣在对中国乡村小学兴办废存分析,虽引入了社区成员对达成群体行动的需求和难度概念,但主要还是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类型学上展开①田丰,刘欣.制度环境、非正式规范与中国乡村小学兴办废存[J].社会科学,2019(07):55-66.。还有,熊伟等分析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对PPP 项目实施效率的影响②熊伟,李良艺,汪峰.复杂项目外包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关系——基于2014—2019年PPP 项目的生存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1(05):23-40、196.。
2.易地扶贫搬迁的一般实践。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迁移有所不同,易地扶贫搬迁首先是一项由政府主导、“高位推动”③傅利平,陈琴,董永庆,房亚楠.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 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1(04):119-136、199.、“自上而下”④王春光.政策执行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01):108-117.的公共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虽然每个环节都具有不同内涵,对应着相异的治理任务,但始终承载着高度的政治性目标⑤傅利平,陈琴,董永庆,房亚楠.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 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1(04):119-136、199.。另一方面,不论被动还是主动,易地扶贫搬迁落地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政策对象的深度参与,即要求他们进行社会空间的转换。与此同时,政策实施的区域在农村,而我国乡村最大的特征被认为是乡土性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存在着诸多非正式制度,其中一些还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复苏或繁盛之势。它们一起从个人、家庭和社区等不同层面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以贫困群众为代表的所有参与者或者说行动者,并最终对易地扶贫搬迁成效产生影响。由此,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的现实环境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同时在场,而非某一类型单独作用。在一些时候,非正式制度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有效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成本;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抵牾,甚至完全冲突。
3.理论框架与两个基本假设。基于以上分析,首先建构一个理论框架,即制度因素形成冲突或耦合会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就。它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互动相关理论观点和经验研究成果。在具体综合过程中,我们进行了适当修正以适应易地扶贫搬迁现实。结合易地扶贫搬迁一般实践,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设:H1: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当地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制度环境时,非正式制度因素会导致搬不出、稳不住的概率上升;H2: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当地非正式制度形成耦合或者说一致的制度环境时,非正式制度因素会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先后发挥催化剂和稳定剂的作用,提升搬出、稳住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多案例比较分析
主要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该方法是案例研究与比较分析的一种融合。按照罗伯特·K.殷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双重定义(twofold definition)①(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原书第3 版)[M].周海涛、李永贤、张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2-4.,首先,案例研究核心在于其研究的范围,它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环境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即“案例”,尤其适用待研究的现象与其所处环境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的情境。其次,案例研究的特色是处理有待研究的变量比数据点还要多的特殊情况,案例研究方法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并把所有资料汇合在一起进行交叉分析。这些特征和功能较好地满足了本研究的需要,这成为了选择它的主要理由。倘若仅仅只是运用案例研究这一种方法,那么“从案例中总结出来的‘发现’严格说来只是新的假设”②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J].社会学研究,2010(02):180-210、246.。但比较分析的加入可以满足因果推断要求。诸多比较分析方法中被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遵循密尔因果法则下的求同法(the methe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the method of differeces)③(韩)河连燮.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2 版).李秀峰,柴宝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7。。
(二)案例选择与收集
我们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案例。首先,案例须具有明显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特征。在我国广大农村,虽然非正式规范无处不在,但是许多时候都是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结果。对于最终选择的案例,即便是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人,也要能较为轻松识别出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非正式制度因素而非其他。其次,案例须满足关键求同或求异法的条件。也就是说,需要特别注意对诸多可能作用政策结果的非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控制。再次,非正式制度因素在一定范围内需尽可能具有代表性。最后,案例具有可获得性。除了实地调查,案例报道等文献资料也为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非正式制度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资料支撑。
在以上标准指引和约束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档案资料收集、互联网检索等不同方法收集了可资分析的案例资料。表2列示了案例材料与理论假设的映照情况。

表2 案例材料与理论假设对照情况一览
四、研究结果
(一)原始宗教信仰的作用与影响
2016年初到2020年底,湖南省L 县共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单元869 个。以“搬得出”和“稳得住”作为理想政策目标参照,没有实现政策目标的表现至少有三种:(a)整个家庭不搬迁入住新房,(b)部分家庭成员拒绝搬迁,(c)搬迁后家庭全部或部分成员回迁。表3列示了对L 县LY 镇DB 安置点和YY 镇SQ 安置点的调查结果。

表3 对DB 安置点和SQ 安置点抽样调查的结果
进一步分年龄统计发现,不愿迁入新房或者搬迁后又回迁的主要是老年人。无论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受篇幅限制,相关图表省略),还是对Y 县有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19 个乡镇的相关官员的访谈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
经分析,发现拒迁或回迁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原始宗教信仰,鬼魂和祖先崇拜阻碍了老年人搬迁或引致选择回迁。Y 县是土家族的发祥地之一,当前该县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16 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1%。土家族相信人逝亡之后,魂魄能够离开人的躯体独立存在,并对阴阳两个世界的人造成持续影响。对于一些土家族人,如果认为刚出生的小孩是鬼魂投胎转世,那么在“接生”时会别特别地在门或窗处留一条缝,以便鬼魂进入或离开。母亲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经过河流、山洞、悬崖等处时,要不断呼喊小孩的名字,以防小孩的魄被游离的鬼魂勾走。如果小孩体弱多病,一些人会认为是魂魄丢失所致。如果一个成年人精神无常(实际上可能罹患了某种精神疾病)或偶尔身体抽搐、口吐白沫(多为癫痫),过去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被“最凶恶的邪神野鬼‘麻阳鬼’”控制,解决办法是请被称作“梯玛”的法师施法捉鬼①游俊.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略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4):64-72.。
土家族人对亡魂的认识,还集中表现在丧葬仪式中。举两个典型例子。一是在亲友亡逝后,通常会进行“殡尸”“哭灵”“打丧鼓”等活动。目标是愉悦和告慰逝者,目的是请求逝者魂灵的保佑。二是若亲友死于异乡,则通常认为其魂魄会四处飘荡,相应的其尸身不可进入堂屋或者房内,以免侵扰活着的人。对于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当地人尤其慎重,常常会请法师超度,且不请亡魂入住家中神龛。
易地扶贫搬迁本质上是一种迁移行为,其结果是居住空间的改变。迁移造成故乡和他乡之别,同时通常意味着旧房与新房的出现。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的,老年人群体的死亡概率都相对较高。一旦死亡事件发生,且发生地在他乡或者说新的居住地,那么魂魄被认为很有可能永远飘荡在外——这是一种让人极难接受的情形。此外,若死亡事件发生在新房——通常是后辈子孙将长期居住的房屋,那么亡人的魂魄在“熟悉”和“记忆”机制作用下,被认为返回新房的概率增加,结果是打扰后辈的可能性上升,尤其是可能会对刚出生或年幼的后辈子孙造成伤害——这自然也是老人们特别不愿发生的事情,结果导致不愿搬迁。
相比之下,以下在原始宗教信仰指引下的活动更加具有物质性和现实性,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首先是一些土家族人在世时,到了一定年岁后通常会为自己准备棺材(当地称之为“寿方”),且多放置在自己居住的房屋后面(当地称为“后檐屋”)或左右。他们的观念是:死亡之后,需尽快入殓,以保证魂魄安定而不四处飘荡——棺材适宜大小的空间有助于实现这一观念上的目标。另外,他们认为棺木能够发挥隔绝两个世界的作用:逝者亡魂安定不打扰生者,“孤魂野鬼”也不会打扰或伤害逝去的亲友。这种认识与羊左之交典故背后的部分内容极为相似。而一旦迁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通常是在城市化、现代化观念作用下建成的标准化小区和多层楼房,有着特殊地位和意义的棺木将无处存放。还有,Y 县近年推行了现代化的殡葬改革,虽然这些安置点通常建设在农村地区,但由于现代化痕迹浓厚,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它们同城镇一样改土葬为火葬并葬于政府统一规划的公墓。这种转变也令当地老年人群和一部分年轻人难以接受。由此,结果是一些老年人拒绝搬迁,那些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抗拒情绪尤为强烈。对于那些没有被强制要求实行现代化殡葬的安置社区,它们也可能面临另外一个障碍——丧葬仪式和活动没有合适地点举行。在成熟的城市社区,此类活动可以选择指定的殡仪场馆开展。而在那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通常不具备这类条件。没有合适空间举行丧葬活动也会阻碍迁移行动。
(二)分家析产传统返迁效应分析
先看两个来自重庆市B 县CL 镇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一是CC 安置区。该安置区位于CL 镇CC 村,距集镇约4 公里,于2013 和2014年分期建成(13年为一期工程,14年为二期工程),共安置建档立卡搬迁户272 户1023 人,人均投资7.7 万余元。建设方式为统规统建,安置方式为乡镇安置,地质勘察符合安置区建设地质条件标准,地质灾害评估符合标准,安置住房质量达到验收标准,整个工程竣工验收优。安置区基础设施配套完整,安全饮水、生活用电均已到户,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均已覆盖,安置区道路也已修建到户并硬化,垃圾转运处理、排污设施配套完整,配有污水处理设备。安置区配建有社区管理用房和安置户的室内外活动场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与CL 镇共享,卫生室与所在村共享。同时为方便易地搬迁安置区群众出行,镇政府特请示上级交通主管部门开通了CC 安置区至镇区的城市公交专线,基本解决学生就学、群众出行及镇区内务工交通需要。在当地政府帮扶下,安置区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实现至少1 人就业,就业主要依托产业为种植养殖业和加工制造业;安置区内设有1 个扶贫车间,23 人在扶贫车间内就业,搬迁户从事农牧业生产共31 户,非农业就业户数226 户,安排公益性岗位就业17 人,周边带贫企业共2 个,在周边带贫企业就业人数为25 人。同时该镇属4A 级旅游景区,CC 安置区剩余的劳动力结合该镇的旅游产业,积极地参与旅游服务产业和社区公益事业,经济收入稳定。
另一个DXYM 安置区位于CL 镇BMS 村,距镇区17 公里,2014年建成。安置区类型为一般安置区,共安置建档立卡搬迁户43 户194 人,人均投资9.5 万余元。建设方式为统规统建,安置方式为乡镇安置,地质勘察符合安置区建设地质条件标准,地质灾害评估符合标准,安置住房质量达到验收标准,整个工程竣工验收优。安置区基础设施配套完整,安全饮水、生活用电均已到户,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均已覆盖,安置区道路都已修建到户并硬化,垃圾转运处理、排污设施配套完整,配有污水处理设备。安置区配建有社区管理用房和安置户的室内外活动场所,县异地搬迁户指挥部每年提供3 万元的管理费用用于安置区的日常管理维护,卫生、物业、小卖部等设施齐全,安置区地处县主要公路沿线,交通便利。安置区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实现至少1 人就业,户劳动就业率达100%,劳动人口综合就业率约为70.1%,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养殖业、旅游业及外出务工。
可以看到,上述两个安置点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甚至相同。然而,2019年底CL 镇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回头看”数据显示,在DXYM 安置区最初安置的43 户194 人中,有18 户、70 多人重新陷入住房贫困,需要重新安置,占比分别为42%和36.1%。而CC 安置区相应的比例为2%和1.8%。前者的两个比值是分别是后者的21 倍和20 倍。那么,以上巨大差异如何产生的呢?
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索和分析后发现,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家析产可较为充分地解释以上差异性结果。“从纵向看,分家析产是家业在父子间的代际传递;从横向看,它又是家产在兄弟间的分割。家族共财既是一种有着浓厚伦理意味的财产观念,在中国,更是一项社会基本制度”①张佩国.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43-48.。分家或是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分割和分离,也可能是兄弟之间的分割和分离,抑或是两种情形的混合。其中分割指的是原家庭财产的重新分配,而分离指的是家庭成员分别重组家庭,结果是产生两个甚至多个新的家户。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在家庭权力(集中表现为家长权威和父权观念)或伦理观念作用下,兄弟的出生次序、父代和子代的差别等会产生不平等的分配结果,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形成财富分化②张佩国.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43-48.③周元雄,蔡克骄.名分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中国民间分家习俗研究[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81-86.。常常表现为两个“更多”,即哥哥比弟弟得到更多,子代比父代得到更多。基于上述讨论,比较分家析产前后的各个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通常存在以下一组关系式:
①分家析产前家庭>分家析产后各家庭;②分家析产后子代之间:年长者家庭>年幼者家庭;③分家析产后亲代与子代之间:子代家庭>亲代家庭。
一般情况下,分家析产所形成的上述不等式关系存在一较短时间后会自行崩解,但在某些情况下,上述关系式、尤其是③式可能会长期存在,分家析产会产生严重的马太效应。具体到易地扶贫搬迁情境中,在DXYM 社区,由于安置房单一门户设计,分家析产后,子代之间,稍长群体通常获得安置区分配房屋的居住使用权,而稍幼的被要求另立门户,结果常常是回到搬迁前住房居住;而在亲代与子代的分家析产过程中,子代更多地留居安置区,亲代回到搬迁前住房居住;两相混合情形中,通常是父母带着年幼的兄弟回到老房子居住。
结果,经由分家析产作用,DXYM 安置区搬迁户回迁规模逐渐扩大;此外,由于①②③不等式的存在,回迁家庭的住房贫困率和需要重新安置的比例也就自然地居高不下。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能力总体上位于全社会的最低层级,而分家析产过程中也存在资源在权力和观念作用的再分配——弱者得到更少。结果,经过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的筛选,综合发展能力最为低下的人群回迁的可能性最高。那为什么CC 安置区没有出现类似结果呢?原因在于工程设计人员偶然地将搬迁家庭可能发生的分家析产事件纳入了户型设计中。
前面说到CC 社区和DXYM 社区位于当地有名的旅游区。事实上,CC 安置区坐落于以明清木制古建筑为主的古镇,而DXYM 以自然风景为主。在安置房设计时,CC 社区出于消防考虑,为每户预留了一个安全后门与逃生楼梯相连,在以矩形为主的户型中,安全后门与入户门位于矩形的对角线两端;此外,为了与古镇的建筑式样相统一,建筑多采用榫卯技术,也加入了更多的木材。结果,一些分家析产后需分灶、新立门户的家庭,在无损建筑结构和对房屋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情况下,可将安全门作为了新的入户门,灵活地将一户变成了两户。加之安置房的分配原则是按人口分配①笔者注:政策规定12 岁及以上家庭人员,未婚的可以分配得到一间房(15-18 平方米);已婚的,以夫妻为单位,分配房屋,通常也是一间房(18-20 平方米)。客厅与厨房按人口数量计算,每人平均1.5 平方米。,任何家庭成员都可以主张自己对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结果就是较少家庭选择回迁。而DXYM 安置社区为砖混结构,各方面都不具备将一户变为两户的条件,结果是一些新成立家户被迫回迁。
(三)地方性知识缺乏的失败与教训
另外,调查发现DXYM 安置区长年多云雾的自然环境特征也是促使一些搬迁户回迁的一些原因。DXYM 安置区位于该县一座大山上,该山形似一只船,凌驾于崇山峻岭之中。南北长约22 公里,宽5 余公里,最窄地区仅2 公里。山界上地势平坦,草原地貌,呈小丘陵状。总面积为52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200 余米,最高峰1416 米。夏天平均气温在20 摄氏度左右,冬天气温在零下10 摄氏度。项目选址和建设时间集中在2013年夏季,一方面,因为是首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基层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快速完成了施工建设;另一方面,当地群众对项目缺乏了解和信任,结果导致在工程建设前期,几乎无当地居民关心工程建设过程。最终,项目被选择建设在了一处云雾积聚概率极高的山坡半腰。该处被当地人称为“鬼迷路”,意指长年云雾,鬼走过都会迷失方向。也就是说,DXYM 工程建设时,项目缺乏深度嵌入过程,外部进入的工程人员在相对云雾较少的时期选址、施工,最终忽略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工程限制条件——云雾,几种因素叠加致使该安置区居住适宜度降低,一些搬迁户最终选择了回迁。相比之下,CC 社区及其他许多安置社区没有受到此类环境的影响,居住适宜水平较高,回迁率相应较低。
(四)联山安置点老年学校案例分析
2021年2月,新华网转载了贵州日报有关天柱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一则新闻报道,标题是《老年学校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让易地扶贫搬迁老人“稳乐享”》②新华网.老年学校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让易地扶贫搬迁老人“稳乐享”[EB/OL].(2021-02-14) [2021-11-08].http://www.gz.xinhuanet.com/2021-02/14/c_1127099752.htm.。文章以住在天柱县联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居民杨引兰的故事为切入点,首先展现了“不想搬”到“都不想回老家去喽”的巨大转变,接着明确指出安置点建设老年学校是促成上述转变的重要因素。联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是贵州省集中安置超过2 万人的大型安置点之一,有超过4000 户搬迁群众,老年群体规模巨大。为实现“稳得住”政策目标,在做好其他相关方面工作时,安置点所在街道把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重要抓手之一,成立了在许多大中型城市才会有的老年学校,开办了器乐班、山歌班、象棋班、文艺班等兴趣班。结果许多老年人“乐不思蜀”,返迁意愿下降,生活幸福指数逐渐提升。
可以发现,上述案例与原始宗教信仰解释搬迁和回迁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照。它们所关注的群体都是老年人,具体内容也都是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但是两地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显然,原因在于天柱县联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充分利用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耦合作用。在安置点集中生产当地老人喜爱的文化产品,迎合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要,从而增强了老人们对安置点的接受度和黏性。
(五)GT 镇“为老屋”建设及成效
最后是GT 镇“为老屋”案例。截至2020年底,湖南省Y 县GT 镇全镇易地搬迁共完成286户,共1192 人,涉及18 个行政村(社区),家庭整体搬迁率达到95%,回迁率一直控制在2%以下。2020年该镇曾被省、市两级评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先进集体。事实上,GT 镇在2016年和2017年同样遭遇过在LY 镇DB 安置点和DF 镇SQ 安置点存在的老人不愿搬迁或易回迁的挑战。为搬出并稳住关键的老年人群体,实现政策目标,GT 镇一方面采取以下五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包括(a)为每一个安置点集中建设一间“寿方”屋,集中有序摆放“寿方”,满足老人们相关愿望;(b)为每个安置区配置一间医务室,由家庭医生定时坐诊,满足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看病吃药的需求;(c)特别设置临终关怀室;(d)是开辟专门的丧葬活动举行场地;(e)不强行实施殡葬改革,在老人生前征询老人意见,获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实行火葬的,给予3000 到5000 元的奖励。
另外一方面,该镇创新实施了“为老屋”项目。具体的,安置房分配政策方面规定:若65 岁以上父母跟子女一起搬迁,在计入家庭人口总数的同时,可获得为老屋一间;老人离世后,为老屋可由家人继续最长使用五年时间。举个例子,有贫困户A,家有包括67 岁鳏居的父亲在内的6人,若父亲随迁,那么所分配房屋在按照6 人计算的同时,可获得为老屋一间;若父亲不随迁,那么只能按照5 人计算,同时不可获得为老屋。为老屋位于安置区7 层楼房的底层,面积20 平方左右,基础生活设施齐全,由农用器具储藏间改造而成。为防止老人随迁后又返迁,政策补充规定:申请为老屋的贫困户,除了特殊情况——主要兄弟两户分住堂屋两侧厢房,拆除一侧会威胁另外一侧房屋的,须拆除原房屋,退耕;若老人返迁居住超过10 天(被老人们表述为两场,即两次赶集时间的间隔),为老屋收回。截至调查时间,少有老人回迁。原因一是由于多数原有房屋已经拆除,无法回迁(有些回迁老人是居住在没有易地扶贫搬迁的子女家中);二是若违反政策规定,会受到舆论谴责,社会声誉受损。
为老屋发挥作用的机制包括:一是,“天下父母心”,几乎所有老人都希望为后辈子孙谋取更多福利。一方面,老人随迁可以为子女争取更大面积的住房;另一方面,老人所获得的“为老屋”在某些时候可作为应对分家析产的可行方案。老人入住子女所分配得到的房屋,需新立户的子女临时入住为老屋。二是,在孝文化作用下,子女希望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实现赡养父母的目标——会努力规劝父母随迁。三是隔代照料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需要。四是面对公共池塘资源时的一种理性选择。前文说到,为老屋由农具堆放间改建而成,而后者在其他乡镇是各户均分。在变成为老屋之后,实际占用者就获得了比均分时更多的使用空间。那么符合资格条件的老人申请使用为老屋显然是一种理性的做法。而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住户,在身份资格条件面前,同时叠加敬老文化,他们会表示支持和赞同。但一旦出现占而不用,那么前面已经提及的舆论工具就会发挥监督作用。结果,就少有人回迁了。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易地扶贫搬迁是近些年里影响和作用农村住房、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深刻的公共政策之一。总体上,该项试图改善贫困人口居住环境和发展机会的国家行动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概言之,在大多数安置项目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存在少数项目失败的现象。基于田野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本文认为这种差异是不同制度环境下诸非正式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运用已有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借助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资料,最终比较验证了以上判断。具体而言,在由易地扶贫搬迁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约束和作用参与者的行为及结果,使得易地扶贫搬迁成效打折扣,甚至失败。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会助力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与绩效产生,出现耦合效应。
当前,随着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渡,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逐渐退出了焦点执行序列,但这并不意味它迎来了政策终结。事实上,在两大国家战略目标衔接阶段,易地扶贫搬迁正进入一个更为重要的政策生命周期。一方面,政策目标从“搬得出”上移至“稳得住”和“能致富”。相比“搬得出”,这两个目标更为高阶,意义更为重大,所面临的现实和理论挑战也更多。另一方面,脱贫不脱政策,之前的运动式政策执行进入了常规执行新常态,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而在经验层面,无论是原始宗教信仰、分家析产传统,还是地方性知识等因素,都依然并将长期存在,且会对两个高阶目标的实现过程和结果发生作用和影响。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指明以上诸因素的作用过程和机制,有助于实务界改进执行策略,提升绩效。概言之,在继续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复合了制度环境因素的非正式制度对相关行动者的作用及其结果。广大贫困农民既受正式制度的鼓励或管制,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受非正式制度因素约束。在某些具体或者参与者规模较小的场景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甚至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