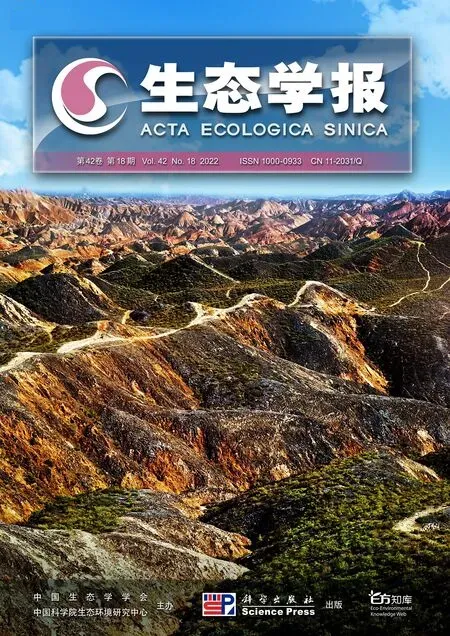山西省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王争磊,刘海龙,2,*,丁娅楠,王炜桥,张丽萍,郭晓佳,2
1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太原 030000 2 山西师范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所, 太原 030000
经济快速发展使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不合理的开采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问题,自然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状态与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生态安全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新主题[1]。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安全、食物安全、空气质量、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2]。生态安全是地理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议题,是人地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更是当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热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生态高质量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是掌握生态环境状况、调控生态安全状态的基础,对区域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科学参考价值,对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国外关于生态安全评价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主要集中在从污染源的角度进行生态风险评估,包括重金属对土壤健康[4]、海湾安全[5]、城市近郊人类生存环境[6]、河流健康[7]的影响等工业开采方面,农药的使用对环境的后效作用[8]、水资源可利用程度[9]等农业生产方面,此外,评价河流与湖泊[10—11]等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健康也是研究的焦点。国内多利用统计数据或遥感数据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12]、层次分析法[13]、综合指数法[14]、物元分析法[15]、生态足迹法[16]等计算区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对森林[17]、绿洲[18]、土地[19]等进行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区涉及行政区[20]、城市群[21]、流域[22]等维度,空间差异的探究主要通过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方法;生态安全影响因素解析主要利用线性回归模型[23]、障碍度模型[24]、地理探测器[25]等方法。总体来看,当前已有研究虽包括宏观、微观、中观尺度,但将三个尺度结合对不同尺度间的空间联系与空间效应的探究较少。大多学者在进行空间差异探究时忽略了不同区域间交叉重叠的影响,影响因素探究时忽略了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本文利用尺度融合进行生态安全评价并探究不同尺度间的联系,能够避免尺度过大导致区域内部信息被忽略,尺度过小无法把握宏观信息[26]等问题;使用Dagum基尼系数探究区域生态安全差异,以此完整反映出区域内、区域间的差异、来源及相互作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从空间角度探究其与周围地区的关联性及溢出效应。
山西省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区域内地形起伏不平,受地形的影响,省内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问题突出[27]。随着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的开采,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生态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基于此,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围绕“典型区域行政区尺度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揭示及关键影响因素识别”这一科学问题,使用PSR模型,通过尺度融合对山西省省域、市域、县域三个尺度进行生态安全评价,使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县域生态安全的区域差异与来源,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空间溢出效应并对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为提升山西省生态安全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东接太行山,西邻黄土高原,介于110°14′—114°33′E,34°34′—40°44′N之间,行政区轮廓略呈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总面积15.67×104km2,下辖11个地级市共119个县区。区域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全省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m以上,生态环境脆弱。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各地年平均气温介于4.2—14.2℃之间,年降水量介于358—621mm。2018年底常住人口为37.18×106人,城镇人口占山西总人口的58.41%;国内生产总值16.82×1011元,增速为6.70%;人均水资源量为328.57m3,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6.6%;森林覆盖率22.79%,略低于全国22.96%的平均水平;优良天数比例为63%,低于全国79.3%的平均水平。
1.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山西省、市、县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山西省统计年鉴》(2001、2006、2011、2019年);DEM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的GDEMV2 30m分辨率数值高程数据集;NDVI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的《中国长时间序列植被指数(NDVI)空间分布数据集》;降水量数据与气温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中国1980年以来逐年年降水量空间插值数据集》、《中国1980年以来逐年年平均气温空间插值数据集》;交通路网数据来自公开街道地图平台(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分辨率为30m×30m;夜间灯光数据来自Harvard Dataverse(跨传感器校正的全球“类NPP-VIIRS”500m分辨率夜间灯光数据)(https://doi.org/10.7910/DVN/YGIVCD);PM2.5数据来自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http://fizz.phys.dal.ca/—atmos/martin/?page_id=140);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自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http://www.ngdc.noaa.gov/);底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1∶400万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为方便数据统计,本文将研究区各地级市的市辖区进行合并,评价单元包括107个县区。
1.3 研究方法
1.3.1指标体系构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建立的PSR 概念模型在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28]。生态安全是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可持续性的反映,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为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山西省生态环境脆弱,人地关系矛盾较为严重,是生态安全威胁较为严重的地区。当前研究区主要面临人口增加、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等生态压力问题,生态安全状态包括地形地貌、污染物排放量、植被覆盖程度、人均资源分配状况等方面。生态安全响应包括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响应。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9—30],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全面性、典型性的原则,以生态安全为总目标,共选取18个指标,构建研究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1)。ESV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所求。依照坡度对社会分工的影响采用分级赋值[30]:(0,10°]赋值为 0.8,(10°,15°]赋值为 0.6,(15°,25°]赋值为 0.4,>25°赋值为 0.2,坡度越大,人类开发难度越大。
1.3.2综合权重求解
权重反映不同指标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31]。熵是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表征不确定性的度量,熵越小表征信息量越大,指标越重要。层次分析法(AHP)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指标权重值,具体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29—32]。为减小主观因素与数据离散程度对权重的影响,本文利用最小信息熵原理对主客观权重进行综合,公式如下[33]:
(1)
式中,W为第j个指标的综合权重值;Wjshang为第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值;Wjceng为第j个指标的主观权重值。
1.3.3综合指数计算及等级划分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山西省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2)


表1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现有研究[34],结合研究区生态环境特征将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表2),并使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模块对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空间格局进行制图,以便分析空间分布规律。

表2 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标准
1.3.4空间自相关分析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事物之间均有联系,联系的强度随地理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利用Matlab软件构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对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分别采用全局Moran′sI指数与局部Moran′sI指数对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如下[35]:
全局Moran′sI指数:
(3)
式中,n是研究区域地区总数;Wkongij是空间权重矩阵;xi和xj分别是区域i和区域j的属性;I>0,表示空间上呈正相关,I<0,表示空间上呈负相关,I=0,表示空间上随机分布。
局部Moran′sI指数:
(4)
式中,S2为属性的方差;Ii>0表示该地区的高值被高值所包围或者是一个低值被低值所包围;Ii<0表示一个低值被高值所包围或者是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
1.3.5Dagum基尼系数分解模型
Dagum基尼系数是博洛尼亚大学Dagum于1997年提出的一种分解基尼比的新方法,用来衡量子群内部的差异及来源,有效解决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以及区域间与区域内差异来源的问题[36]。本文采用此方法对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5)

在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过程中,首先要对子群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平均值进行排序,并划分Gini为子群间差距(Gnb)、子群内差距(Gw)和超变密度(Gt),且满足,Gini=Gnb+Gw+Gt,具体见参考文献[37]。
1.3.6空间计量模型
(1)空间计量模型的选取
经典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OLS)模型是用来解释因变量(yi)与自变量(xi)之间关系的多元线性函数[38],公式为:
yi=β0+∑iβixi+εi
(6)
式中:β0为常数项;βi为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生态安全水平影响因素的外部性可能超越行政单元界限,经典回归模型可能导致结果偏误[39]。为更好体现生态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公式(6)的基础上,建立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40],公式分别为:
Yit=ρ∑WijYit+β∑Xit+μi+λt+εit
(7)
Yit=β∑Xit+μi+λt+φit
(8)
φ=δ∑Wijφjt+εit
(9)
Yit=ρ∑WijYit+β∑Xit+γ∑WijXjt+μi+λt+εit
(10)
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t为时间;εit为随机误差项;β和γ为空间相关系数;ρ为空间滞后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采用空间邻接矩阵建立空间权重。当γ=0,SDM可简化为SLM。当γ+ρβ=0时,SDM可简化为SEM。
(2)控制变量的选取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41],本文以生态安全综合指数(safe)为被解释变量,从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选取解释变量,具体如下:经济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和产业结构(str),社会子系统包括人口密度(pop)和城镇化率(urban),自然子系统包括NDVI(ndvi)、降水量(rain)、气温(temp)以及高程(ele)。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成本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环境,以人均GDP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够反映区域发展方式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发展方式会对生态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以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表征[42];区域内人口增加促使环境发生变化,用人口密度衡量人口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强度越大,生态环境压力越大,用城镇化率衡量生态环境的压力;植被生长状况越好,越有利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健康稳定,生态环境承载力越强,用NDVI表征区域的植被生长状况;降水越多越有利于植被的生长,用年降水总量来表征;气温对地表植被的生长具有重要影响,用年均气温表征区域内植被生长的环境;高程越高的地区开发难度越大,生态环境越脆弱,用高程反映生态环境的脆弱程度。
2 山西省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2.1 省域尺度
从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来看(表3),2000—2018年山西省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3388逐步上升到2018的0.6794,增幅为100.53%,生态安全等级由“敏感级Ⅱ”上升为“相对安全级Ⅳ”,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00—2018年,压力指数不断增加,增幅为47.40%,表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有所下降。2000—2018年,状态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增幅为78.82%,表明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减小,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得到改善。2000—2018年,响应指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增幅为233.41%,表明人类采取有效措施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具体指标来看,ESV、路网密度、第三产业比重等指标的增加促进了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提升。

表3 2000—2018年山西省省域尺度生态安全评价结果
2.2 市域尺度
山西省地级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综合指数均值由2000年的0.3683上升到2018年的0.4165,位于“临界安全级Ⅲ”,生态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不同等级地级市数量上(表4),2000年,“敏感级Ⅱ”地级市数量占比45.45%,“临界安全级Ⅲ”地级市数量占比45.45%,无“危险级Ⅰ”与“相对安全级Ⅳ”区域。2018年,“敏感级Ⅱ”地级市数量占比下降为18.18%,“临界安全级Ⅲ”地级市数量占比上升为54.55%,“相对安全级Ⅳ”的地级市为3个,占比27.27%,无“危险级Ⅰ”区域。就具体指标来看,经济密度、灯光密度、路网密度等正向指标的提升,农业经济水平、GDP增长率、PM2.5年均浓度等负向指标不同幅度的下降,促使大同、临汾、长治等地市生态安全等级的提升。

表4 2000—2018年山西省市域尺度生态安全不同等级数量
空间格局上(图1),2000年,北部的大同、朔州,南部的临汾和长治位于“敏感级Ⅱ”,中部的太原、忻州、吕梁、晋中位于“临界安全级Ⅲ”,阳泉位于“相对安全级Ⅳ”,呈现由中部向南北递减的空间结构。2005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有所提升,北部的大同、南部的临汾由“敏感级Ⅱ”变为“临界安全级Ⅲ”,其他地市生态安全等级未发生变化,空间格局上高等级区域向南北两侧扩散。2010年,北部的大同、南部的临汾、中部的忻州和吕梁由 “临界安全级Ⅲ”变为“敏感级Ⅱ”,在空间上呈“半环状”的空间结构,其他地市未发生等级变化。2018年,中部的太原与南部的晋城提升为“相对安全级Ⅳ”,北部的大同、中部的忻州与吕梁、南部的长治与临汾提升为“临界安全级Ⅲ”,高等级区域向南北两侧扩散。整体上,研究区生态安全高等级区域多位于中部地区,生态安全等级由中部向南北两侧递减。

图1 2000—2018年山西省市域尺度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空间变化Fig.1 Spatial change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t the municipal scale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8
2.3 县域尺度
2.3.1生态安全综合水平时空演化特征
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等级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00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临界安全级Ⅲ”的区域占比46.73%,“敏感级Ⅱ”区域占比53.27%, “临界安全级Ⅲ”区域包括五台县、盂县、娄烦县等50个县域,“敏感级Ⅱ”区域包括汾西县、应县、屯留县等71个县域。2005年,兴县、临县、五寨县等9个县域的生态安全等级由“临界安全级Ⅲ”下降为“敏感级Ⅱ”,与GDP增长率、PM2.5年均浓度、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等指标的下降相关。阳城县、介休市由“敏感级Ⅱ”上升为“临界安全级Ⅲ”,阳泉市辖区由“临界安全级Ⅲ”提升为“相对安全级Ⅳ”,经济密度、人均建筑用地面积、草地面积比例、灯光密度等指标的上升促进这些县域安全等级的提升。2010年,神池县、五寨县、广灵县、晋城市辖区、朔州市辖区由“敏感级Ⅱ”提升为“临界安全级Ⅲ”,与经济密度。草地面积比重、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指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促进生态安全等级提升。榆社县、左权县、静乐县、忻州市辖区由“临界安全级Ⅲ”下降为“敏感级Ⅱ”,阳泉市辖区由“相对安全级Ⅳ”下降为“临界安全级Ⅲ”,这些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大幅增加,ESV、三产比重等有所下降,生态安全等级随之下降。2018年,阳高县、柳林县、汾西县等31个县区由“敏感级Ⅱ”提升为“临界安全级Ⅲ”,太原市辖区和阳泉市辖区、阳曲县、宁武县、五台县由“临界安全级Ⅲ”提升为“相对安全级Ⅳ”,这些地区的经济密度、人均建筑用地面积、耕地面积比重等指标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生态安全等级得到提升。
空间格局上,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带状”分布(图2),形成南部临汾盆地带、长治盆地带、运城盆地带,中部吕梁山带、太行山带、太原盆地带,北部大同盆地带,表现为由中部向南北两侧递减的阶梯状非均衡化空间格局。2000年中部太行山、太岳山、太原盆地及附近区域为“临界安全级Ⅲ”,呈“带状”分布。吕梁山中段、北部大同盆地、南部运城盆地、临汾盆地、长治盆地及附近区域主要是“敏感级Ⅱ”,大致呈现以太岳山的沁源县、安泽县和沁水县为中心的“环状”格局。 2005年,吕梁山中段兴县、临县、五寨县演变为“敏感级Ⅱ”,中部吕梁山及附近区域与北部大同盆地及附近区域在空间上形成大同盆地—吕梁山带。2010年中部太原盆地西北侧部分地区演变为“敏感级Ⅱ”,生态安全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北部以五寨县和宁武县、中部以文水县和方山县、南部以沁源县和安泽县为中心的“环状”格局。2018年,中部太原盆地的太原市辖区、太行山区域的阳泉市辖区、五台县等演变为“相对安全级Ⅳ”,西部吕梁山、北部大同盆地部分“敏感级Ⅱ”区域演变为“临界安全级Ⅲ”,生态安全水平在空间上形成南部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带、长治盆地带和北部大同盆地带。

图2 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尺度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空间变化 Fig.2 Spatial changes of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t county scale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8
总体来看,根据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的演化趋势,大致可分为2个时段,即2000—2010年、2010—2018年。前阶段内山西省生态安全水平虽有所提升,但速度较慢,后阶段内生态安全高等级区域明显增加。2000—2005年,山西省推进“碧水蓝天”工程,制定实施减排节能方案,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2010—2018年,山西省自2010年开始实施全省大气污染排放专项行动,对省内的大气、水等进行全面整治,同时通过产业结构转型调整改进发展模式,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环境改善较为明显。
2.3.2空间集聚特征
基于GeoDa软件对山西省县域2000—2018年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进行全局Moran′sI指数测度(表5),县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空间上均通过99%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存在正向的空间依赖现象,即生态安全指数较高的区域在空间上存在聚集特征,周围县域的指数也较高,反之亦然。

表5 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结果
为进一步说明生态安全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特征,使用局部Moran′sI指数得到107个县域的LISA集聚图(图3),表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之间的空间相互关系。2000—2018年生态安全水平在空间上主要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分布在中部太原盆地、太行山中段及附近,包括太原市辖区、阳曲县、寿阳县等,其中太原市辖区与阳泉市辖区的生态安全水平最高,农业经济比重低,受到太原经济中心的辐射作用明显,从而形成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区分布在南部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及附近,包括临猗县、万荣县、襄汾县等,盆地内部人口密度高,农业比重大,经济基础弱,生态安全水平较低,临猗县生态安全水平最低,导致南部形成低低集聚区域。高高集聚区域由2000年的12个增加到2018年的15个, 低低集聚区域由2000年的16个减少到2018年的9个,表明研究区整体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集聚程度增强。

图3 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尺度生态安全LISA聚类图Fig.3 LISA cluster map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t county scale in Shanxi from 2000 to 2018
2.3.3空间差异及来源
本文根据自然地理单元差异把山西省划分为3个子群:北部(朔州市(5县区)、忻州市(14县区)、大同市(8县区));中部(太原市(5县区)、阳泉市(3县区)、晋中市(11县区)、吕梁市(13县区));南部(长治市(12县区)、晋城市(6县区)、运城市(13县区)、临汾市(17县区)),以此探究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
整体来看(表6),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空间上存在非均衡性特征,区域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差距有所缩小。从子群内基尼系数来看(表7),中部子群内2000—2018年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总体增幅为6.7102%,除2000年和2018年外,其余年份基尼系数均高于均值0.0612,说明中部子群内生态安全水平差异在增大,空间非均衡性有所减弱。北部子群内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态势,其中2000—2005年增幅为2.61%,而2005—2010年、2010—2018年则分别下降8.95%、3.98%,说明内部生态安全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空间非均衡性不断减弱。南部子群内基尼系数呈下降态势,降幅在不断增大,2005—2010年降幅最大(5.30%),说明生态安全水平差异缩小,空间非均衡性减弱。差异数值上,南部均值最大(0.0824),中部(0.0612)次之,北部(0.0571)最小,子群的非均衡性由南向北依次递减。南部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与运城盆地、临汾盆地、长治盆地在地形上呈“川”字分布,生态安全水平差距较大,且生态安全水平最低的临猗县也在南部区域,导致南部内部非均衡性最强。中部太行山、太原盆地、吕梁山相间分布,区域内部虽有差距,但位于太原盆地的太原是山西省经济中心、省会城市,资金充足,有更高水平的环境治理能力,内部非均衡性比南部弱。北部以盆地为主,包括大同盆地、忻州盆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较低,内部各县域之间差距较小,空间非均衡最弱。由此可见,区域内部生态安全水平差异主要受地形与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

表6 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尺度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差异来源及贡献

表7 2000—2018年山西省不同子群内与子群间Dagum基尼系数
从子群间基尼系数来看,中部-北部子群间差异呈波动下降态势,表现为“小幅上升-小幅下降”的趋势,2000—2005年基尼系数出现小幅上升,增幅为9.00%,并未影响整体下降的态势,2005—2010年、2010—2018年不断下降,降幅分别为11.53%、7.56%。北部-南部子群间差异呈波动下降态势,表现为“小幅下降-趋于稳定-小幅上升”的趋势,2000—2005年、2005—2010年降幅分别为5.89%,4.60%、2010—2018年增幅为0.92%。中部-南部子群间差异表现为总体下降的趋势,其中2005—2010年降幅最大(8.46%)。差异数值上,中部-南部子群间的均值为0.0916,中部-北部和北部-南部的均值分别为0.0639和0.0795,中部-南部之间的生态安全水平差距最大,其次是北部-南部,最后是中部-北部。中部地区生态安全水平总体较高,其中太原市辖区与阳泉市辖区最高,南部地区生态安全水平多位于低等级,临猗县生态安全水平最低,生态安全水平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异导致中部与南部差距最大。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受地形影响,北部地区以盆地为主,生态安全水平差距较小,南部地区盆地与山脉相间分布,生态安全水平差距较大。中部的太原盆地与北部的忻州盆地是更为完整的地理单元,区域之间流通性强,北部地区受到太原的经济辐射程度更高,两者差距相对较小。
从差异来源及贡献率来看,2000—2018年,子群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总体增幅为2.20%,子群内部县域之间的生态安全水平差距在增加。子群间差异贡献率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大致表现为“U”型,总体降幅为11.99%,说明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安全水平差距也在缩小。超变密度指不同子群交叉重叠对于总体空间差异的影响[37],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总体增幅为22.62%,说明子群间生态安全水平交叉重叠的影响在逐渐增加。2000—2018年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小于子群间与子群内的差异贡献率,子群间交叉影响对整体生态安全水平差异的贡献程度较小。差异数值上,子群间差异均值高于子群内与超变密度贡献率的均值。由此可见,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子群间生态安全水平的差异,其次是子群内各县域间的差异,最后是不同子群交叉重叠的影响。
3 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由全局Moran′sI指数检验结果可知,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因此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测各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35]。2000—2018年的Moran′sI指数显著为正,LM-error与Robust LM-error检验的统计量显著性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表8),LM-lag与Robust LM-lag的统计量并不显著,故选择SEM。
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000—2018年,空间残差自相关系数LAMBDA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9),相邻县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每增加1%会使本区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分别增加0.7601%、0.7960%、0.6264%、0.6179%,表明本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会对周围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各影响因素的SEM估计结果来看(表9),经济规模、人口密度、城镇化率、NDVI、高程是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空间演变的关键影响因素。经济子系统中,2000—2018年,经济规模系数逐渐变为正数,在2018年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水平提升后,辐射带动邻近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加强生态建设,提升生态安全水平,从而对邻近地区生态安全产生正向溢出。社会子系统中,人口密度系数由负数变为正数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密度的增加促使人类活动范围扩大,通过人为干预调整区域环境状态,提升生态安全水平,对邻近地区生态安全产生正向溢出。城镇化率系数在2000—2010年通过至少10%的显著性检验,但2018年未通过检验,表明人类开发强度需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超过一定程度后,会对生态环境状态起到抑制作用[43],城市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城市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自然子系统中,NDVI系数显著为正数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植被覆盖的提高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从而通过生态系统的联系向邻近地区溢出,促进区域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高程系数为负且最少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高程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区平均海拔在1500m以上,生态环境更为脆弱,环境遭到破坏后使生态系统失衡,通过负向溢出影响周围地区生态安全水平。

表8 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线性回归结果

表9 2000—2018年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水平SEM估计结果
产业结构、降水量与气温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空间演化的次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通过各产业的比例变化反映人类活动强度的变化,主要依靠产业联系与组织关联影响周围地区生态安全,表明目前研究区各区域产业联系网络弱,缺乏较明显的分工协作。降水量与气温的变化影响区域植被生长状况,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状态,对生态安全未产生直接影响。
结合前文的县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变来看,县域生态安全水平较好区域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太岳山、太原盆地及其附近,而吕梁山、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长治盆地却是生态安全水平较低的区域。就山区而言,太岳山的沁源县和安泽县森林覆盖率2000—2018年均在57%以上,太行山中段的左权县、和顺县的草地面积比例与森林覆盖率明显高于其他县域,上述地区道路不畅、开发难度较大、人类活动较为集中,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低,但自然植被状态较好,政府也出台保护森林资源的政策,如安泽县出台《严厉打击毁林违法行为、保护森林资源的实施办法》、左权县出台《左权县脱(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考核办法》,对生态安全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同处于山区的吕梁山中段、北段及附近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与太行山区域相比存在差距,吕梁山附近是矿产资源集中分布连片区和煤炭主产区,截止到2021年,吕梁有91座煤矿,占全省煤矿数量的13.62%,生产能力达12625万t/a,占全省煤矿总产能的12.07%,但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小,粗放的开采方式与不到位的治理措施使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就盆地而言,太原盆地及附近的生态安全指数有较为明显的高值区域,与盆地内地形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高,在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对人地关系进行改善相关,2006—2010年太原累计投入80亿元进行环境污染治理,2008年太原发布《太原市汾河流域环境治理修复与保护工程方案》,对汾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集中整治。与太原盆地相比,运城盆地却是生态安全水平的低低集聚区域,虽同处于盆地,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8年太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88272元,运城为28229元,另外环境治理投入有较大差距,2018年运城投入4000多万元提升生态环保能力,太原支出6.74亿元用于环境治理项目建设,由此可见人类响应对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作用。
综上,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与生态安全空间分布的变化受经济发展水平、开发方式和强度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形条件相似的地区因开发方式和开发强度的不同,导致生态安全水平的差异。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由于各个学者的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各个研究区自然地理状况的独特性,生态安全等级的划分没有较为明确的标准。本文在进行山西省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时,参考相关研究,对研究区生态安全等级化进行划分(表2),使之尽量符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但如何使生态安全等级划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仍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尺度下的生态安全时空分布有所不同,从市域尺度来看,研究区2000—2018年中部的太原、阳泉生态安全等级较高,但县域尺度除市辖区外,其他县域生态安全等级较低,而市域尺度生态安全等级较低的忻州在县域尺度却只有6个县等级较低,表明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特征存在尺度效应。具体表现在:①研究尺度越大,生态安全水平的整体差异程度越小。②生态安全水平越高的区域,研究尺度越小,区域内部差异越不均衡[26]。由此可见空间范围越大,生态系统越稳定,因此,在生态建设中,需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更大范围内平衡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与可持续性。另外,在同一指标体系下对不同尺度进行评价,能够保证不同尺度衡量标准的一致性、对比的可信度。
从生态安全综合水平来看,2000—2018年县域生态安全指数前五名在太原市辖区、阳泉市辖区、五台县、左权县、盂县之间变动,后五名在襄汾县、万荣县、曲沃县、新绛县、临猗县之间变动,虽然生态安全水平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初始生态安全水平较好的地区,生态环境基本会沿着正反馈的路径持续改善,初始水平较差的地区虽在不断提升,但依旧是生态安全水平较低的单元,说明山西省生态安全水平的演化存在路径依赖现象。主要机制如下:生态安全基础较好的地区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通过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投入更多资金治理,然后通过正反馈机制对生态环境产生积极作用,提升生态安全水平;生态安全基础较差的地区生态环境容量有限,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集聚,人口容量逐渐变小,在负反馈的作用下使环境承载力下降,即使通过发展经济去获取更多资金改善生态环境,但由于可分配的资金有限,无法形成可循环的正反馈作用机制,导致反馈效果不足,生态安全水平提升效果不佳。由此可见,传统发展模式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发展具有“锁定”作用,需创新发展模式摆脱其路径依赖,实现路径突破,提升生态安全水平。
通过对县域土地与森林的生态安全评价成果[12—17—30]分析发现,生态安全水平较高地区与以下因素有密切关系:①地形条件,地形决定人类开发活动的难度,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会引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其修复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与漫长的治理过程;②植被覆盖,植被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循环性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后,生物多样性会不断减少,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③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水平的高低决定环境投入治理力度的大小,进而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除上述特点以外,研究区还表现出自然环境状态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较低的情况,反映出研究区以煤炭资源开采为主的初级资源开发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此,将研究区各地理单元划分以下类型:①生态较好—经济水平高,包括太原盆地附近区域;②生态较好—经济水平低,包括太岳山、太行山中段附近区域;③生态较差—经济水平高,包括长治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附近区域;④生态较差—经济水平低,包括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吕梁山附近区域。综上所述,山西省生态安全水平变化是自然地理环境、人类胁迫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状态是生态安全水平的基础,对人类开发活动产生制约作用,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减缓人类胁迫程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维持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状态与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是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4.2 结论及建议
本文对山西省2000—2018年生态安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空间差异及来源,探究生态安全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山西省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不同行政单元尺度下增幅不同,表现为省域>市域>县域,总体生态安全水平较低。县域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片状”和“带状”分布,表现为由中部向南部和北部递减的非均衡化空间格局,生态安全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空间依赖现象,空间集聚程度增强。
(2)县域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异质性程度不断下降,子群内部的非均衡性由南向北依次递减,子群间差异中部-南部最大,其次是北部-南部,最后是中部-北部,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子群间差异。
(3)县域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现象,本地区域生态安全水平的变化会对周围区域生态安全水平产生影响。经济规模、人口密度、城镇化率、NDVI、高程是山西省县域生态安全空间演变的关键影响因素,产业结构、降水量、气温是次要影响因素。
(4)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特征存在尺度效应,研究尺度越大,生态安全水平的整体差异程度越小,生态安全水平越高的区域,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区域内部的差异越不均衡,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平衡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与可持续性。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的变化存在路径依赖,不同地区因生态基础的差异导致发展路径的不同,生态安全提升效果差距较大,应摆脱不合理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5)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变化是自然地理环境、人类胁迫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维持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状态与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是促进区域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根据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山西省生态安全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在保护山区生态安全较高水平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应在吕梁山、太行山、太岳山等区域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推进退耕还林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与整体性,根据主体功能区划推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治理;积极对以煤炭开发为主的初级发展模式进行路径突破,实现产业转型的路径创造,促进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本文在时空演化方面仅选取四个年份,对生态安全水平的演化过程与路径依赖机制反映有限,基于长时间序列的研究能够更完整地表征路径依赖机制,这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