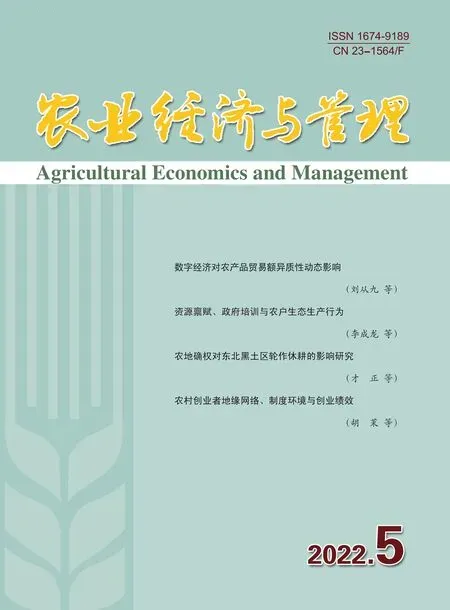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刘 雯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一、引 言
近年来,线上消费逐渐成为我国居民购物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便于居民足不出户即获得物资,为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做了重要贡献,也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充分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2020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2014年的1 800亿元增加到1.79万亿元,规模扩大了8.9倍,但与城镇相比差距仍然明显。我国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认识仍然有待提高,对线上消费的使用仍然存疑,农村线上消费市场存在较大的可挖掘潜力。
与此同时,为提高农村居民的线上消费能力,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完善,行政村4G 网络即将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1 年6 月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9.2%,而城镇则为78.3%,虽然增速已赶超城镇,但仍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不一定意味着农村居民实际使用互联网意愿的提高,而可能只是提供了可及性条件,农村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仍然有限,这些均会影响农村居民线上消费意愿和消费金额。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有关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互联网使用与部分类别消费品特别是电力消费的关系上。如Sadorsky(2012)在探讨资讯通讯技术(ICT)对新兴经济体电力消费的影响时发现,信息和通信技术与电力消耗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有学者关注个体上网本身所带来的费用。Yusuf 等(2008)研究澳大利亚有自费上网服务的家庭在这项服务上的花费。调查结果显示,42%的家庭拥有互联网连接,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在互联网连接上花费349澳元。Ji(2016)则认为在互联网不断普及后,电信服务与其他已有如公共交通等服务间存在愈发强烈的替代作用,并运用了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探讨电信服务支出的变化及与其他类别消费支出间的关系,认为2007年后电信服务价格弹性明显提高。当然,也有学者基于产品供给角度探讨个体网购行为,如Chiou 等(2017)提出消费者会在包括传统零售店和互联网在内的多渠道环境中表现出复杂的购物行为。当企业决定建立网店作为线上渠道时,顾客与销售伙伴关系、顾客对网店购物的接受性及其交互作用均会影响顾客多渠道购物行为的态度。其他关于线上消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探讨影响个体线上消费行为的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如从年龄、收入、性别等方面考察农村居民的网购模式,以确定网购者的特征以及农村地区最可能面临竞争的商店类型(Walzer 等,2005),或者认为婚姻状况(Brown等,2005)、节省时间和资金等的信念(Punj,2011)、是否是管理层(Naseri等,2011)等会影响个体网购行为。
国内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上网对家庭总消费水平和8类消费支出的影响上。有学者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局部地区居民消费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向玉冰,2018;程名望等,2019;张永丽等,2019),有学者使用截面数据研究上网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祝仲坤,2020),也有学者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电子商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福前等,2015)。但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影响居民线上消费行为的相关因素,如易行健等(2015)利用城镇家庭2007年和2009年六个省市的数据研究了家庭收入水平和户主的人口统计特征对家庭网购行为的影响,认为收入水平的上升会提高家庭参与互联网购买的可能性,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也意味着不同的互联网购买行为,主要涉及到年龄、性别和家庭规模。李旭洋等(2018)在分析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环境的影响时,提出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的网络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孙喆等(2020)则致力于研究互联网保险对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且重点关注互联网保险的省际空间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居民线上消费行为,且往往止步于二者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农村居民线上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更为缺乏,较少从互联网使用角度切入,也未提及其中的非线性关系和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相互影响。本文首次构建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理论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农村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尝试性地从个体层面出发探讨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非线性关系,识别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对个体自身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个体效用函数构建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假设个体效用函数为:Ut=u(ct)+θ(zt)v(xt),其中,ct为个体线下消费,xt为个体线上消费。θ(zt)用于衡量个体线上消费相对于线下消费的重要性(刘雯,2018),θ(zt)取值越大,意味着个体的线上消费相对于线下消费的重要程度越强。zt为互联网使用情况,个体对互联网使用程度不同时,个体对线上消费相对于线下消费重要性的判断也不相同,从而影响个体效用水平。为便于说明,本文以两期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为例求解。此时,个体面临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为式(1)-(3):


其中,β为时间折现率,t为时期,c1、x1为个体第1期(可视为年轻时期)的线下消费和线上消费,y为第1期的收入水平,s为第1期的储蓄水平,R为本息率(一般R>1),c2、x2为个体第2期(可视为老年时期)的线下消费和线上消费,假设个体第2期的收入为第1期储蓄的本息和,无其他收入。个体即在预算约束(2)和(3)的前提下,试图最大化自身的效用水平。
联立式(2)和(3),消去储蓄水平后,得到式(4),如下:

利用式(1)和式(4)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有:

分别对c1、c2、x1、x2和λ求导,得到x1关于z1的表达式如下:

命题1:当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对线上消费的判断时,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会影响该个体的线上消费行为。具体而言,如果互联网的使用使个体认为线上消费的相对重要性增加,则互联网的使用会使个体线上消费额增加,否则减少。
由表1看出,裂缝孔隙度很低,这是由于成像测井裂缝识别精度仅为0.1mm,大裂缝不多见。但岩心观察发现高导缝、微裂缝、砾缘缝等微细裂缝发育[8],因此分析认为微细裂缝对储层连通具有重要作用[9]。由图6可以看出,在一定孔隙度条件下,只有当裂缝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有较好的自然产能(如车66、车660井)。
证明:式(6)两边对z1求偏导,

x1关于z1求二阶偏导后的符号并不确定,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进一步,如果假设θ''(z1)≤0,即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相对判断的函数为凹函数或线性函数时,x1关于z1的二阶偏导小于0。结合命题1可知,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线上消费的影响为正,但会随

此时,预算约束并未发生变化。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并对各未知变量求偏导后,得到新的x1关于z1的表达式:

因此,如果互联网使用确实有助于个体判断线上线下消费产生的相对效用水平且个体确实在意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互联网使用情况(δ>0),则有:,即个体所在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会影响该个体自身的线上消费行为。
(二)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农村样本构建logit和tobit模型,首次从个体层面出发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识别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对个体自身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上文提到的命题1-3分别进行检验。本文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时,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引入了ivprobit两步法和ivtobit两步法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在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时,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Onlinecit为个体i在时期t的线上消费,如果是二元变量,则衡量个体是否存在线上消费;如果是连续变量,则衡量个体的线上消费额(对数)。ltimeit为个体i在时期t的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X1it和X2it分别为个体i在时期t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uit为随机扰动项。

即在式(12)的基础上,引入个体i在时期t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平方项,用于衡量二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2018年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CFPS),该数据库每两年调查一次,涵盖了丰富的家庭、成人和儿童数据。本文基于农村个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使用个体所在家庭层面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个体所在村/居层面数据进行内生性检验。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消费方式的不断增加和消费便利性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本文引入两个变量衡量个体线上消费情况。一是二元变量,用于衡量个体是否存在线上消费;二是连续变量(对数),用于衡量个体线上消费额。而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引入了家庭层面的相应变量,用于说明家庭线上消费情况。
2.核心解释变量
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往往影响其线上消费行为。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不仅关注个体是否上网,更关注个体上网时间/上网频率对其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用于衡量个体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具体而言,使用个体每周业余上网小时数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基本的回归分析;引入个体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活动的频率(取值1-7,数值越大,上网频率越高)、个体所在家庭的总上网时间等作为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
3.其他的主要解释变量
在探讨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线上消费行为的非线性关系时,本文引入了互联网使用时间的二次项和上网频率的二次项,用于识别“拐点”的存在;在检验家庭成员间存在的相互影响时,本文引入了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的互联网使用时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检验这种相互影响针对不同个体所呈现出的异质性时,本文引入了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的互联网使用时间与个体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的交叉项进行识别;在基于家庭层面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时,本文还引入了家庭互联网使用时间、家庭所在村落互联网使用时间的中位数水平,用于稳健性检验。
4.控制变量
本文同时引入了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家庭层面: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对数)、家庭规模。②个体层面:a.受教育程度,1-8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b.婚姻状况,取值为1 代表已婚或同居,取值为0 代表未婚、离婚或丧偶;c.年龄;d.性别,取值为1代表男性,取值为0代表女性。除此之外,也引入了年份控制变量用于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分析
互联网使用将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线上消费行为?首先借助Logit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影响,借助Tobit 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线上消费额(对数)的影响;其次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识别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线上消费行为的“拐点”;然后引入交叉项识别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个体自身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最后给出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一)基本回归
农村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是否会提高其线上消费可能性?表2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进行线上消费,第(4)-(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线上消费额(对数);第(1)、(4)列无控制变量,第(2)、(5)列在第(1)、(4)列的基础上引入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年份控制变量,第(3)、(6)列在第(2)、(5)列的基础上引入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随着个体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其线上消费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个体的线上消费额也在不断增加。不论基于哪种形式进行回归分析,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二)非线性关系检验
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个体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否为线性?即关注是否存在影响“拐点”(见表3)。表3第(1)-(2)列同时引入个体互联网使用时间和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平方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第(1)列以个体是否进行线上消费为被解释变量,第(2)列以个体线上消费额(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引入平方项后,互联网使用时间的系数估计值仍然显著为正,但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仍然会使个体线上消费的可能性和消费额增加,但这种边际影响会随着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而减弱。
进一步的,本文引入了以个体互联网使用频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3第(3)-(4)列。上网娱乐频率越高,个体线上消费的可能性越大,且个体线上消费额越多,与第(1)、(2)列结果一致。
考虑到平方项的引入可能带来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本文也构建了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此时门槛变量和门槛效应变量均为个体互联网使用时间,即研究上网时间的多少对个体线上消费额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此时,考虑到个体互联网使用时间里有部分取值为0,本文将个体互联网使用时间按照大小排序后划分为10等份,赋值为1-10,取值越大,互联网使用程度越强,作为互联网使用时间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第(5)-(6)列。不论是否以线上消费为被解释变量,还是以线上消费额(对数)为被解释变量,模型均存在一个门槛值,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个体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呈倒U型,先增加后减少,存在峰值,进一步验证了引入二次项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非线性关系的检验结果
(三)家庭内部相互影响检验
个体线上消费行为不仅与该个体自身是否上网有关,可能也与家庭其他成员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有关。本文这部分即用于检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在其中的作用。
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个体自身上网时间的前提下,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的互联网使用情况确实会显著影响该个体的线上消费行为。即个体会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而提高自身线上消费可能性和线上消费额。

表4 家庭内部相互影响检验的回归结果
进一步,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由第(2)-(6)列回归结果可知,相比其他个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个体线上消费可能性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更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已婚的个体线上消费额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和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个体对互联网线上消费的接触和了解较少,已婚个体对配偶的依赖性更高,更容易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进而改变自身的线上消费行为。
(四)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参考Fisman 等(2007)、周广肃等(2018)的做法,将个体所在省级层面的互联网使用状况作为个体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将扣除个体所在家庭互联网使用时间后的个体所在县区层面互联网使用时间作为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工具变量。这样做的可行性在于,地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往往能够用于衡量该地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从而影响该地个体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同时地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又与个体层面的消费状况无直接关系,满足外生性条件。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使用ivprobit两步法和ivtobit两步法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Wald检验给出解释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的检验结果,均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解释变量为内生变量,需要引入工具变量做进一步分析;AR检验给出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均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可能性;通过给出工具变量影响个体层面消费状况的回归结果(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得到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结果,工具变量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因此,在考虑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线上消费可能性和线上消费额(对数)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个体所在家庭其他成员对个体自身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五)家庭层面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个体消费行为往往与该个体所在的家庭有关,本文这部分基于家庭层面的样本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家庭互联网使用时间对该家庭线上消费行为的影响,作为稳健性检验(见表6)。可以看到,家庭上网时间越多,家庭线上消费可能性越高,家庭线上消费额越多,同样存在“拐点”。

表6 家庭层面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使农村居民线上消费的可能性提高,也使农村居民的线上消费额显著增加,从消费手段维度优化升级农村居民消费行为。
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线上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不断减弱,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拐点”的存在。
第三,家庭内部成员间存在相互影响。在控制个体自身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前提下,家庭其他成员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线上消费行为,且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人均收入较低和已婚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他人影响。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践行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近年来,线上消费不断被农村居民接受,但部分农村地区的网络信号强度、可用于在线购物的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等仍有待补充。为农村居民提供相应的信息基础设施,有助于鼓励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购物,有助于加速线上线下消费融合。
第二,大力宣传互联网+服务,提高互联网使用效率。互联网普及率高不意味着线上消费倾向高,不同农户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不同,线上消费额也不同,且并非互联网使用时间越长,线上消费可能性越大。因此,对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信息辨别能力进行培训,有助于农村居民梳理并理解互联网+各项服务,有效激发其线上消费积极性。
第三,聚焦羊群效应,实现精准网络培训。受教育程度、年龄、人均收入和婚姻状况等变量会通过影响家庭内部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个体线上消费行为。因此,通过对农村家庭中较高受教育程度、年龄较低、收入较高的个体进行互联网使用培训,有助于间接调动农村家庭中其他个体的线上消费积极性,进一步激励更多农户提升消费手段,实现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