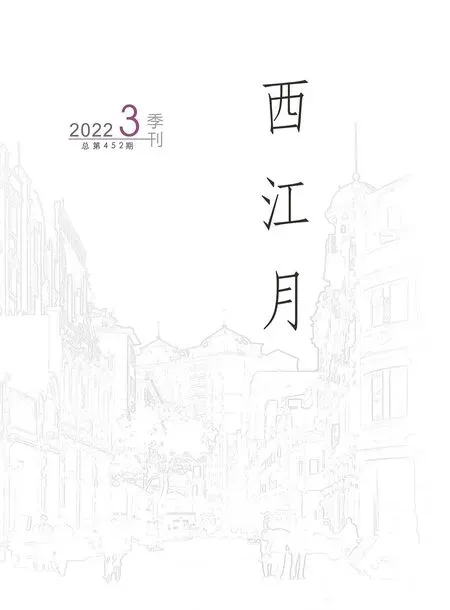非亚小说二题
非 亚
17楼东北角的那套房间
1998那一年初春,肖唯从职工家属区的一幢4层的红砖房,搬到了另外一幢20层的住宅楼,在那里住了18年。那个外墙为马赛克贴面的公寓楼,有两个楼梯,两部电梯,一条开敞的外走廊。每天,肖唯通过楼梯或者电梯上下,会见到一些同事、职工家属,或者陌生人。那个有点矮胖,穿一件深蓝色工作服的送邮件的女人,每天上午会准时过来,往一楼电梯厅绿色的信箱塞进各种邮件、广告和宣传品。肖唯平时上下的楼梯,一楼的下面,住着收发员阿黎一家,他和肖唯算是老乡,他们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了。另一户人家住着一个年纪和肖唯差不多的建筑师,后来搬走了,房子租给别人,做了小学的午托用房。很多原来住在这里的职工搬走之后,很快又住进了一些新的租户,有本院新来的员工,也有来自外面的租户。小区的侧门,通向有各种店铺、私人房的南京路。这幢每层有6户,一共20层的公寓楼,就像小区里的其他楼栋一样,在建成的这些年,发生过一些事,每当夜深人静,这些事有时会涌上肖唯的心头,让他难以忍受和沉默。今天他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就与这一幢楼有关。故事的主人,是一个死去多年后才被发现的男人,一个肖唯曾经见过但叫不出名字的退休老工程师。
那个工程师的房子,位于17楼的东北侧,和肖唯住在2楼西北侧的房子,正好是对称布置的正对面,中间隔着两部电梯和一段朝北的开敞走廊,还有两户小户型的人家。死者是一位设备工程师,和他的老婆早已离异,退休后,他一个人住在这幢楼里。他的儿子远在美国,平时很少电话联系,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工程师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肖唯见过他,认识,但却一直叫不出他的名字,因为大家不在一个设计院里,无论是专业与工作,也几乎都没有交集。那个工程师平时出现在小区或者单位办公楼时,总是微微地弯着腰,身材瘦削,衣着普通,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上衣,款式过时,松松垮垮,头发有点长,脸上带着一种在单位不受重用的小职员的表情。因为没有了妻子的照料,他的生活有点潦倒,外表看上去有点不修边幅。有时他在小区楼下出现,微微笑着,嘴巴似乎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有时他也会出门,离开地方并不宽敞的职工家属区,去交易场和南京路,看路边的小贩如何宰杀一条蛇。他饶有兴趣地观看杀蛇的人左手拧着蛇的下颚,有力的拇指和食指,紧压着蛇的喉部,以至于蛇感到窒息,不得不瞪着绝望的眼睛,张开痛苦的嘴巴,露出几颗不知是否有毒的尖牙。杀蛇的人拿着刀子,把蛇的肚子破开,从靠近头部的腹部位置开始,把刀子一直往下拉,蛇被切开腹部的时候,那些内脏就会掉出来,落在地上。杀蛇的人动作很快地拿刀把蛇的头部切断,然后剥皮,最后干净利落地把蛇在砧板上剁成好几节,并很快地把杀好的蛇,装进塑料袋,递给买蛇的人,然后收钱。
那个工程师每次去交易场买菜,总是很喜欢站在路边看别人宰蛇。他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四处走走。他知道蛇可以拿来炖汤、红烧、油炸,再撒上辣椒粉和椒盐。以前他去过吾州,到过那里的蛇仓,见到过很多蛇,也见过各种蛇酒和用蛇做成的各种美食。因此,每次去南京路,看路边的小贩宰蛇,每次看到一长条的蛇被切割成一节节的时候,他总是会想到自己以前在吾州品尝过的那些美食,总会不自觉地咂咂舌头。
那位工程师有时也会去市中心的朝阳花园,在榕树、扁桃树和木菠萝树下面,看那些街头跳舞、唱歌、下棋的陌生人。那个街头公园人员混杂,除了退休的老人,还有不少游手好闲没事干的陌生人,整日待在那里。外地来邕州的人,有时也会在那里出现。还有一些想寻找猎物的男人与女人,游走在各式各样的人群之中,一旦看上目标,他们就在那里搭讪、调情,甚至在夜幕降临之时,在花圃边和树木下,做出各种大胆的举动。那位工程师在寂寞的时候,有时也会去那里寻找刺激,只是没有胆量成功过一次。他有时会去水街、码头或者菜市买点菜。或者只是从小区侧门出来,在南京路的路边菜市,买点自己今天想吃的蔬菜,东看看,西看看,无所事事地游荡上一圈之后,才返回家里。
在一个人独居的家里,他常常会对着镜子发呆,或者胡乱捣弄着一些手工,修理一些坏了的家具与用具。他不太喜欢看书,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或者开收音机,电视机和收音机的画面和声音传递出来时,他就不至于那么难过。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家里的家具也是简单陈旧,他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可以联系,或者请朋友上门喝茶、聊天。退休在家,年迈的工程师有时会感到自己真的是孤独至极,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最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知道如何排遣自己内心没有人交流的孤独与苦闷。他经常站在阳台那里,瞭望火车站、友爱路和白苍岭方向。有时早上起床后他会出门,去楼下转角的米粉店,吃一碗桂林米粉,之后去菜市场买点菜,见到熟人就打打招呼。有时中午就简单地做个番茄鸡蛋面。傍晚的时候,就在厨房里做一顿简单的晚餐,黄瓜炒瘦肉,加蒜蓉炒菜心,或者蒸鱼,加一份炒节瓜。他的儿子因为他和妻子的离异,对他多少有一些怨言和成见,平时几乎很少会电话联系他,工程师觉得自己很对不住孩子,内心既希望能接到孩子的电话,又害怕电话里和孩子无话可说。在很少联系的儿子面前,他日益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犹如一个多余和无用的物体,虽然掌握了一些技术,但退休之后,似乎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个原因,他也很少打扰孩子,或者主动给孩子来一个跨洋电话。
因为工程师在单位里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职工大院里平时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少注意到这个老头。即使他几天没有下楼,没有出现在职工家属区的空地,似乎也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设计院的办公大楼里上班、工作,在楼下的空地见面时打打招呼,或者彼此聊上一会。他对面那幢30层的住宅楼,一楼理发室那里,因为位于家属区的中心,加上房东除了理发室,也开了一家小卖部,因此经常会聚集一些他们所的女职工,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有一段时间,大院里的人们很少再看见工程师出现,大家似乎也没注意到他已经很少在大院出现这个事情,总是以为他又去了哪里旅游,或者回了一趟外地的老家,或者出门去了哪里溜达,深夜无人的时候才会独自回来。日子就是这样,在一种司空见惯的平常中一天又一天地度过。季节的转换,时光的流转,或者更多的其他事情,让人们彻底地忘记了这位工程师的存在。
直到很多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儿子因为银行的一件事需要找他,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最后只好托亲戚上门,去南京路的职工家属区找他。亲戚到了17楼,敲了半天门,却一直没有人回应。亲戚也问了家族里的所有人,并没有得到他回了老家的答复,大家这才想起,工程师确实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最后迫不得已,亲戚跑到济南路,找来开锁的人,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把房门打开。房门打开的瞬间,展现在亲戚眼里的是满满一屋子的灰尘,交叉的蜘蛛网与房子没人居住的那种荒凉,让人突然惊觉到了某种不祥。
房间内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主卧室的门也都打开着,客厅里摆放着电视机和沙发,茶几上放着杯子、茶叶罐和一只茶壶,一切仿佛是曾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样子。进门右手边的那间房是主卧室,灰尘到处都是,被子枕头摊放在床上,似乎是曾经有人在这里睡过,但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房间。亲戚看到卧室内没有人,就喊了一下,依然是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穿过客厅,走到中间的小饭厅,旁边的小卧室房门敞开着,餐厅的窗户也向外打开,并没有关上。当亲戚穿过饭厅,来到过道的卧室和卫生间的门口时,扭头突然发现卫生间的地板上,竟然躺着一副遗骸,顿时大惊失色,惊叫着连忙跑出了门口,在门口外面的走廊,拨打了110报警。
警察很快过来,一番侦查后,最后证明卫生间的遗骸正是那位工程师本人。死者已经死亡了几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由于房间的窗户是开启的,加上所在的楼层较高,死者死亡后肉体散发的臭气,也因空气的自然流通,没有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事后警察的描述大致是这样——死者应该是半夜上厕所,突然摔倒,或者因为心脏问题,昏迷在了卫生间里。因为无法呼叫,或者呼叫了邻居都没有听到,家里也没有其他人,最后就晕倒在卫生间里慢慢死去。
几年之后,在时间的作用下,潮湿的卫生间,只剩下了一副尸骨的残骸。
这个事情出来后,震惊了设计院和职工家属区,并很快传遍整个城市。人们没想到工程师竟然死在自己家里,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女人们聚集在楼下的空地,议论纷纷,她们既感慨工程师晚年的凄凉和人情淡薄,也怪罪其在美国的儿子对父亲漠不关心,包括其身边的亲戚朋友,平日也没有人去过问、关心工程师的生活,让人们不免感觉到了世态炎凉和感同身受的悲哀。事情曝光后,迅速地在互联网上传播,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市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对独居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联想。
作为居住在这一幢住宅的职工,很遗憾,肖唯和其他职工一样,竟然都没有觉察到身边这个工程师突然消失不见这个事情。旁边的邻居,平时也没注意到那个大门紧闭的房间,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出的事实。也没有聆听到死者临终前发出的呼叫,也许他发出呼叫的那个子夜,所有人都沉沉睡去,没有觉察到他在房间发出的任何声响与动静。肖唯能够想象死者生前那种无人救助的痛苦,他那种无人聆听的晚年孤独生活的独白。他在退休之后,仿佛慢慢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割断了与社会、与亲情、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每一天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着一面又一面墙壁,冰冷的、毫无表情的各种生活用品与用具,在晚年的岁月中,没有人关爱与交谈,回应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交流渴望。在日复一日孤独的生活中,在无人嘘寒问暖的关怀中,在突然降临的意外中,工程师最后在自己的家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人们悲伤的是这个事件的残酷性和亲情断裂的不可思议性。职工家属区的老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也不免心有戚戚。大家都说到年老的时候,如果家里没人照料,应该选择去养老院,或者请一个人陪护,而不是一个人生活到老。那个工程师也许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晚年最后会是这个结局,在他还能自理的时候,没有对未来突然到来的意外做出过任何预案。也许在他晚年孤独的生活中,他有一颗强大的心,去消化这种孤独,甚至他也乐于一个人去享用这种孤独。也甚至,所有晚年面临的问题,对他来讲其实都不是问题,一切仅仅只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不断重复某个轨迹的人生程序而已。因此,当他一个人在家里时,他只是平静地生活着,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晚年时光,他可能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内心的感慨。肖唯平时看到他在小区里嘟嘟囔囔,其实不过是他晚年生命中的自言自语而已。
那位工程师被人发现死在家里之后,在日复一日时间的流逝中,职工家属区的人们也似乎慢慢淡忘了这一件事,甚至不再有人提起。过了几年之后,互联网上再也搜索不到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信息,甚至只言片语。至于那个房子,大家都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似乎也没有人去关心。那扇朝向电梯厅的17楼东北侧的房门,刷着灰色的已经有些脱落的油漆,一直都关闭着,也从来不见有人出入。大家都不知道房子是否已经腾空,转租给了其他租户,还是一直就那样空着,无人居住。
肖唯在设计院那幢大楼前后住了18年,2016年夏天,他和家人离开了职工家属区,搬到了青秀山附近靠江边的一个小区。肖唯从大学毕业开始,在那个职工家属区,生活了整整29年。在将近30年的日子里,肖唯经历了身边一些同事的离职、调动、搬迁、退休,甚至衰老与死亡。他在22岁那一年,毕业分配到这个位于华西路的国有设计院,在那里经历了学徒期的懵懂、成长。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被派遣到外地设计分院工作。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抚育孩子成长,以及忙碌的设计生涯。也经历了和国外事务所的合作设计,设计院的改制,以及人员、机构的各种变动。与肖唯一起来到这个国有大院的年轻人,很多年之后,大家都各奔了东西,甚至彻底地失去了联系。职工家属区篮球场旁边的那棵龙眼树,后来也被砍掉。旧办公大楼也被拆除,在空地上,建起了新办公大楼、架空停车场和活动平台。肖唯也在孩子考上大学之后的2019年,去了更远的魔都从事建筑设计。
假期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肖唯有时也会在夜晚回到华西路,在院子里停好车,然后走去杭州路口旁边的“发艺美发廊”,找多年来一直给他剪发的师傅修理头发。之后肖唯会回到设计院,从侧门进去后,再回到以前住的那幢楼。那幢楼入口的平台,靠电梯外墙与花圃的位置,放置有一张椅子,仿佛是为了让出行或者回来的人们可以有一个临时歇息的地方。那个平台,很多年前,曾有一个年轻人因家庭纠纷,从亲戚家的楼上跳了下来,最后落在电梯一侧的这个入口平台上。出于一种忌讳,肖唯后来很少再走那个平台,而是通过旁边的坡道,或者电梯厅另一边的台阶进去。
一直放在一楼电梯厅里的信报箱,肖唯曾经也在那里取出过无数的信件。现在,属于肖唯的那个信报箱,在肖唯搬离之后,已经几乎不再打开。斑驳脱落的油漆,让那个金属信报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陈旧的物品,或者现成品装置。肖唯原来住的位于2楼的那个房子,门口的信箱经常塞满一些刊物免费寄来的杂志。而肖唯住的那套房子前面,就是设计院的办公大楼。有一年夏天,肖唯突然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从办公大楼16楼的楼梯间窗口那里跳了下来。
在这幢楼和这个职工家属区,发生过很多生与死的故事。设计院的一位空调工程师,退休没几年就无法行走,只能依靠轮椅出入,然后某一年就突然去世了。而与肖唯一起分配来设计院,住在他房子对面的一位工程师,前些年因为癌症,在春节期间突然去世,留下妻子和一个9岁的孩子。另一位他曾经共事过的很有才华的建筑师,只是比他大几岁,后来也因癌症突然去世了。而他们家的房子,正好就在那位死在家中的老工程师的楼上。还有一位肖唯敬仰的,曾经一起工作的老建筑师(他有两个子承父业的儿子),退休后去了审图公司,后来有一年,肖唯在设计院的大楼见到他的大儿子,问起老建筑师的近况,才得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在那幢20世纪80年代末期竣工的住宅楼,肖唯见到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世事无常。
肖唯想起很多年以前,自己住在2楼那间房子,有时在厨房的窗口,会经常看见物业部门的一位女工整理楼下停放的一排自行车。肖唯写过一首诗,把那些自行车称为怪兽。现在,那里已经很少有人再停自行车了。
肖唯想到以前,那个在设计院进出的年轻人,已经人到中年。出入小区和12栋楼的那个诗人,现在也已经离开了华西路,去了另一个城市生活。
而那个无声无息告别世界的老工程师,就像一缕青烟,已经彻底消失在这个车水马龙的世界。
市立医院里的小职员
结束了上午那个一大群人在11楼的汇报会,我们被安排去8楼,和具体管项目的何主任沟通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走进走廊尽头左边那间办公室的时候,里面有几个人,胖的那个,个子不高、下颚吊着两团肥肉的男人,之前也参加了会议,他操着一口本地的方言,以至于我很难听懂他说的话。年轻的那个小伙子,剃着短发,在办公桌旁边忙着整理和分发图纸。地上堆了一大堆外地寄来的图纸,我看了一下,拿专用长袋子(两侧带有提手)装着的,是“某某省建筑设计院”的蓝图。每一份A1图纸,全部装订起来,并加了彩色的封面。说是彩色,其实也就是一种非常难看的湖蓝色,和沉闷的白色搭配在一起。边缘装订的位置,加了一个银色的锡纸封边,看上去能感觉到这家省级设计院的工作既细致、认真,但又无不显示出一种土气。我站在门内,心里想,国有的设计院大概都是这样,不会太考虑美观的问题和因素。另一家国有设计院的图纸,则像以前传统那样,用塑料绳绑扎着每一份折叠成A3的蓝图,装在一个纸箱里。除了何主任、矮胖的中年男人和那个短发的年轻人,办公室里还有三个职员,一个坐在矮胖的中年男人的对面,另外两个男人则坐在靠门口一侧。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个人从桌面上抬起头,看了看我们,然后又低下头,有的人继续看手机,有的人则玩着电脑游戏。也许是一期的项目已经竣工,二期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那几个职员,在那个光线灰暗的房间,看上去有些无聊,无所事事。
我观察了一下房间的布局,门口居中,每两张办公桌作为一组,面对面拼在一起,两组靠在窗口,还有一组靠门口,朝向外面的窗户。何主任坐在最靠里面的位置,抬头就可以看见从门口进来的人,看到这个布局的时候,我的脑子在不由自主地想,应该怎么调整,办公室的布局才会最好。
丁总和何主任交流了一下,然后我们又一起回到11楼会议室,沟通项目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讨论了规划局报规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并梳理、沟通了项目的功能。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会,大概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收拾东西的间隙,丁总提出请业主一起去吃午饭,那个矮胖男人以中午要休息,并且下午还有很多事情为由,推掉了应酬。
从会议室出来,我们又一起下楼,返回8楼何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流着汗,眼睛不停地闪烁着,往办公室里面张望。我们进去之后,我站在门口的一侧,等丁总他们和何主任沟通。那个年轻人走到门口,眼睛继续闪烁着,看着那个矮胖的中年男人,似乎是有什么事要找他。那个矮胖的男人从桌子上拿起玻璃杯,去门口一侧放开水壶的桌子倒开水。看到这个时机,年轻人快步上前,凑过去,和矮胖男人打招呼。矮胖男人之前可能见过他,年轻人一开口,他就抬起头说:“这个事情你去找总包。”然后转过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
年轻人站在门口那里,有点尴尬,不过他还是很快地又跟了过去,站在桌子旁边,对着矮胖男人又说了几句。矮胖男人也站在桌边,听他说了一会,然后说:“我们这边定不了,你去找总包吧。”
我站在旁边,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材料商的业务员,过来推销自己公司的建筑材料和产品。
我知道,只有总包,才有决定权。
结合每个组的表现,参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小组进行考评,对于本学期积分高的前三组进行适当的奖励。对于垫底的最后一组,要求每个组员都要深刻审视自我。
但业主的推荐也很重要。
只是作为建筑师,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那个年轻人走了以后,不久又进来一个陌生人,跟那个短发的年轻人联系。短发的年轻人将几份图纸在签字后交给他。那个陌生人拿着图纸,很快就离开了。我猜他应该是施工单位的人。
坐在那个矮胖男人对面的中年人,在拿图纸的人出去之后,也站起来,拿着保温杯,他从我前面走过时,抬起头,看了看我,然后从门口出去。
我扭头看了看左边,坐在靠门口一侧办公桌边的两个男人,他们仍然是无所事事,在低头看着手机。他们面对面,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也一直没有什么交谈。其中一个男人,有时看一下手机,有时则点开一个电脑游戏页面,看了一会然后又关闭。我不玩游戏,对游戏不了解,我在那里想,他年纪不小了,到底会玩什么游戏呢?
等待期间,我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之前那个推销材料的年轻人不见了。有一个短发中年女人,拿着一沓当地的日报,走进办公室,分发给靠在门口旁边办公的男人。
她分发完报纸,很快就离开。
我猜她应该是收发室的。
何主任也是操着当地的方言,不过说话的声音比较洪亮,他后来和丁总定下来,下午先和分管项目的副院长商讨项目功能的事情,然后再由丁总、娄工和业主一起去规划部门,沟通报规遇到的问题。我和邱工则继续和各科室的负责人讨论各科室功能的安排。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从8楼下楼,离开了市立医院,我们横过马路,去了医院斜对面的一个小酒楼。七月刚至,气候已经非常炎热,位于长江中游的内陆城市,潮湿发烫的空气,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太阳无力地浮在空中,像一台低频噪音的机器,正向大地散发它无处不在的热量。
午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小酒楼休息,等医院下午两点半上班后再过去讨论。
在我们吃饭和休息的时候,酒楼里来回换了几桌人。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一楼的餐厅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坐在一角。我上了位于二楼的洗手间,下楼后,我拉了张椅子,坐在一楼大厅的中间。我头顶那里正好有一台空调,正向下吹着冷气。我跟丁总说,靠窗口那里太热了,这里凉快。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透过酒楼的落地玻璃,看过对面的市立医院,午后的这个时分,太阳像一只火球,猛烈地烘烤着大地,路上几乎看不到有什么人在行走。
混凝土的路面,似乎散发着一层热浪。
我想起下午还要横过马路,去对面的医院,继续找何主任。
我想起上午在何主任办公室遇见的那几个职员。想起他们的保温杯、电脑、办公桌,想起堆放着文件和杂物的桌面,以及他们低着头玩的手机。
我想到他们的生命,日复一日就由这些无聊、沉闷、无所事事的时刻构成,就对这种毫无波澜、死水一般的生活,感到可怕和恐惧。他们在一个单位里,拿着一份工资,过着一种沉闷的单调的小职员的生活,在一日又一日,在无所事事的上班中,慢慢地熬着,一点一点地浪费着他们的生命与时间,失去了热情、激情和斗志,最后在平庸、麻木、自我流放的生活中随波逐流,失去了目标,然后直到退休。
我坐在餐厅的中间,有时也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他们,我是一个单位的小职员,我会怎么样?
我刚刚从都市营造,借调到了中源国际。我来魔都之后,不到两年时间,这是我换的第三个工作单位。我上着班,做着事,不管是参与方案,或者负责施工图和设计过程的把控,不管是在哪一家公司,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哪怕你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仅仅只是一份工作。我跟自己说,你是一个职业建筑师,你要有专业精神,不要在上班中浪费自己的时间,你要对得起你手上的这份工作。
头顶的空调一直向下送着冷气,午后的餐厅,看上去显得有点慵懒和空洞。
我们在小酒楼那里,一直坐到了下午快两点半,之后我们站起来,拿起随身的东西,离开。我们推开门,出去,穿过路边的花坛,然后横过马路,去斜对面的市立医院。
我们出门的时候,午后的热浪像一群狮子,又一次从周围涌过来,吞没了我们。在行人不多的马路,太阳依然像一台年久失修的低频噪音的机器,在我们头顶上嗡嗡地鸣叫着。
在我们沿着斑马线,跨过马路,回到医院的路上,我又想到上午见到的那几个无所事事的小职员,他们穿着灰色的衣服,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看着手机,玩着游戏,或者翻翻刚送来的报纸,处理着每日单调、乏味的事情,做着机械的事情,在走向上午开会的那幢办公楼,在进入电梯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我又一次听到了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
那个声音是这样的——
“我绝不能在无聊和无所事事中,度过自己平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