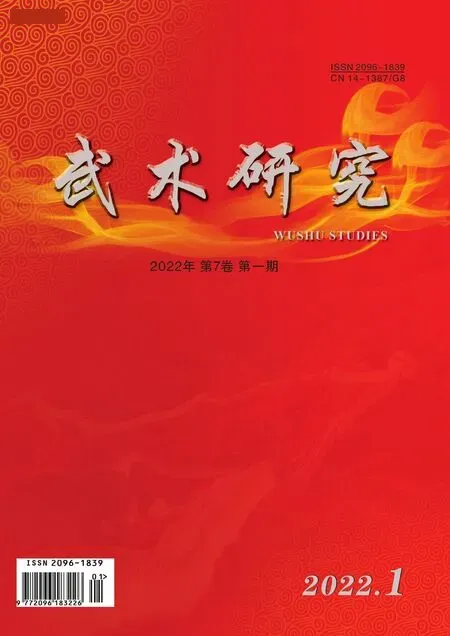秦州鞭杆舞的表演形态及特性探析
庄 园 孙 威 谢智学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鞭杆舞又称“打鞭子”,主要流传于秦人的发源地,即天水市秦州区,秦州区斜坡村一带是中心区域,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鞭杆舞是秦州社火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项目,是地方历史文化中的一块魁宝。社火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结合自己的思想与生活来丰富和改造传统的社火,赋予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社火风格。几千年来,秦州鞭杆舞是在适应和利用生产劳动环境中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涵括了汉民族文化和秦州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研究鞭杆舞的形态及其特性,对于弘扬地方民俗文化,促进民间体育、民间舞蹈的发展,传承地方民间文艺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业界应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1 秦州鞭杆舞的历史渊源
1.1 鞭杆舞起源于秦地
鞭杆舞是一种体育与舞蹈相融合的艺术形式,这一艺术形式的基本内核和特征,无不与其渊源和最初面貌有着无法割舍的密切联系,也与形成这艺术形式的最初环境存在千丝万缕多的关系。鞭杆舞的渊源要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居住在犬丘的秦人先祖非子,因擅长养马,于是周孝王便在汧河和渭河之间的地域让其负责养马,非子用自己独特的养马之技,使得马群的数量疾速增长,成为一名畜牧业的成功者,并被周孝王赐地封赢。可以看出,“秦”是因养马有功得到的封地,是鞭杆舞的起源地无疑。鞭杆舞的基本样态更是表现出古老时期秦人日常与“马”相关的生活状态。
1.2 鞭杆舞形成于牧马
在冷兵器时代,争池略地,车兵、骑兵都离不开马,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一种装备。受战事的影响,马在军事上的地位举足轻重。鞭杆舞的形成是那个年代牧马业备受重视的缩影,而鞭杆舞也就成为“马背上的舞蹈”。秦建国后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马匹之多需要大量的人来管理,在闲暇之时,人们手持牧马的鞭杆在空地练习驱马驯马的动作,后来两人一组慢慢交流切磋鞭马技艺动作,在嬉戏打闹中渐渐衍生出一套动作,这种运动没有场地要求,器材就是牧马时手持的鞭杆。因此,上至高官厚禄,下至白丁俗客都可将其作为一种运动进行休闲。
2 秦州鞭杆舞的表演形式
2.1 有相对固定的表演时间及仪式
从古至今,社火表演是秦州各地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期间是社火表演的固定时间。表演内容丰富多彩,有鞭杆舞、唱小曲、打四川、牧牛等节目,多在庙宇、家庭院落及村庄公共场所表演。初三的晚上必须在庙里举行“官场”的敬神敬先人祭祀仪式,隆重而严肃的鸣炮,磕头的交接仪式等众多习俗都体现出它世代相传的历史性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表演)成为符号载体......来表达象征性内容”。祭祀仪式结束之后,社火活动便正式开始,其中鞭杆舞的表演也愈演愈烈,随着参与人数的逐步增多而推向高潮。直至正月十五的晚上,大家再统一去庙里进行叩拜,社火活动就此结束。鞭杆舞是社火表演的重头戏和不可缺少的节目,一般是活动中的最后一个节目,往往起着压轴的作用。当然,也可形成一个单独的节目进行表演。
2.2 有寓意吉祥的道具“鞭杆”
鞭杆舞的主要道具鞭杆,通常是用三四尺(约90厘米)长的竹竿或坚硬木棍加工而成。生(男)、旦(女)两角的道具鞭杆长短不一。生角的鞭杆稍短,打法更为复杂粗旷,有跳跃性的动作,还有武术的仆步动作等,给人展示的是“武”的刚劲。传承者一般都具备良好的武术基础和身体素质,这样才能更好的展现西北人特有的“剽悍”和“刚烈”的舞性。旦角鞭杆稍长,打法柔美,给人展示的是女性“舞”的细腻。鞭杆两个顶端用绿带和红带缠绕,生角为绿,旦角为红,下面分别扎有红绸和绿绸的彩花,生角红绸彩花为阳,旦角绿绸彩花为阴,象征阴阳和合之意,彩花下面系有四个铜铃,象征八卦,再下面两头镂空分别藏有两枚铜钱,象征两仪和四象,又有招财吉祥的寓意。
2.3 有多种乐器伴奏的配乐及伴唱
《八度神仙》曲
一度神仙汉钟离,头挠抓鬓不整齐,
手里拿的八宝扇,扇搧富贵万万年。
二度神仙吕洞宾,头顶青丝一冠巾,
身后背的二龙剑,杨柳童儿紧跟随。
三度神仙张果老,悠哉骑驴过仙桥,
倒骑驴子仙桥过,口吹云雾上九霄。
四度神仙曹国舅,身穿绣龙滚蟒袍,
当年在朝一品官,修就一座大罗仙。
五度神仙铁拐李,身背葫芦腾云走,
身后背的大葫芦,八仙过海显神通。
六度神仙蓝采和,人人都说是妖魔,
妖妖妖来魔魔魔,少说一句是非少。
七度神仙何仙姑,人人说她无丈夫,
有丈夫来无丈夫,多说一句惹祸福。
八度神仙韩湘子,人人说他是孝子,
手里拿着竹笛杆,走着行着唱道歌。
鞭杆舞表演时所用的打击乐器颇为多样,有堂鼓、乳锣、大锣、小镲、手锣等,拉弦乐器有二胡、板胡、三弦琴,吹奏乐器有唢呐、笛子、管子、笙等。这些乐器视其表演的条件,无固定的规定性,可多可少。现存遗留下来的常用伴奏乐器共有六种,分别是有堂鼓、大锣、小镲、二胡、板胡和笛子。在伴奏节奏上较为单纯, 以平均节奏型为主, 长短、短长等节奏型为辅, 周围还组织数人伴唱助兴,乐队成员都是由年长的传承人担任,唱词大多讲述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但伴奏都是统一的,只有歌词不同,在比较庄重的仪式上伴唱《八度神仙》,而闲暇之时的表演会伴唱《十二月花》。这两首曲子都已具有了上百年的历史。
2.4 有识别角色的多种配饰
最初秦州鞭杆舞的传承方式为传男不传女,以男性担任表演角色,其分为生角和旦角,生角为主角,旦角为配角(男扮女装)。直到2015年,取消了“男扮女装”的这一表演形式。生角和旦角在演出时用不同的服装和配饰来区别。生角的服装是根据秦人服饰制作的长袍,以黑色为主,颇有古朴之风,给人刚毅、忠诚、勇敢的形象。旦角要打扮成女性的装束,也类似于戏剧装扮,头戴假发麻花辫,脚踩绣花鞋。同时,演出时还要对脸部进行丰富多彩的涂抹,涂抹的样式则类似于戏剧脸谱。通过这种涂抹,一方面,作为超脱于人的“神秘”装扮,可达到与神灵沟通而获得神秘力量,驱邪逐疫;另一方面,通过脸部涂抹,与神灵交流,传达某种心理诉求,祈求神灵的庇佑。总而言之,服装道具所流露的文化信息即包括经验性的,也包括超经验的,但无论是哪种信息,它都在传播的“同构”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3 秦州鞭杆舞的舞蹈形态
3.1 有瞬息多变的表演形式
舞蹈的基本步伐分为行进步和固定步,行进步整齐划一,气势磅礴,震天骇地;固定步旋转交叉,或蹲或跃,动人心弦。表演时,有站立舞鞭杆、劈单叉、魁斗踢星、虎抱头等动作姿态,演员按顺序敲击肩膀、前臂、膝盖、脚尖、跳起后勾向上的鞋底等部位,灵活多变,并用鞭梢击打地面,其气势雄厚,鞭随人动,人随鞭狂。演员根据鼓点、节拍变换队形,有大摆尾、鹞子穿林、双进门、同心圆、八卦阵等。生角和旦角的一套动作以八个八拍为一小节,和伴奏伴唱的音乐正好匹配。如:《八度神仙》唱完一段,生角和旦角便打完了一段;第二段循序渐进,循环往复,直至打完八段,基本就结束了。
3.2 有人数不一的表演阵型
鞭杆舞表演时,四人为一组,生角、旦角两两相对,形成了和谐对称的秩序整合。根据表演场地的局限性,既能以组为单位进行,也可组成八人、十二人、二十四人等长阵、方阵进行变幻丰富的表演,人数最多时可由六十四人同时演出,可谓气势磅礴。如在家庭庭院当中进行时,受场地大小的局限,只四人一组进行;在村广场或演出表演时,则二十四人进行,灵活进行;甚至在私下练习时,随着音乐节拍的伴奏,随时增加或减少出场人数,但人数都是以四人一组相加,秦州鞭杆舞对人数也有一定的寓意,在人数上,四人一组逐层叠加,在古代,四人表示祈求四季平安、太平盛世的意义,表示伏羲八卦的自然和谐与天地合一之美。
3.3 有重心低移的行进动态
鞭杆舞的重心低移是从动作姿势、节奏、力量、速度等各个层面所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脚步、膝盖、摆臂、下蹲的运动体态上。这种运动体态的核心为脚步,屈膝、摆臂、下蹲都是以脚步为基础加以形成的,重心低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脚步,因此,想把握好鞭杆舞的精髓,第一步则是学会脚步,脚步乃重中之重。任何运动都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这也是科学与智慧的体现,鞭杆舞的重心低移还表现在起打时的下蹲动作和跳跃动作,这就使运动轨迹做了一个U型,力学原理决定了人体只有将重心降低蓄力,才能获得较大支撑反作用力。由此,也诠释了鞭杆舞伴奏中“重拍”所结合“下蹲再跳跃”的连续动作过程。
4 秦州鞭杆舞的特性
4.1 原始性与古朴性
在今天秦州鞭杆舞的表演中,出现次数最多、占据时间较长的舞蹈图式,即圆形。正如苏珊·朗格所言: “那种环舞或圈舞作为舞蹈形式与本身自发的跳跃毫无关联,它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职能,或许这是舞蹈艺术最圣洁的职能—将神圣的‘王国’与世俗的寰宇区分开来。”这个舞蹈形态是在舞者们围圆移动或面向圆心歌舞的过程中形成的,四人一组逆时针环绕一周移动,舞动时两人相对向圆心而舞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经过笔者走访调研发现,首先,鞭杆舞要在各种形状、场地大小不同的庙宇中、庭院里表演,这些物质的空间普遍较小,太复杂的队形不允许出现,围圆而舞时则可以随时根据空间大小而变化,既节省空间,还能使舞蹈在视觉上具有无限循环的延续流畅效果。其次,围圆而舞是人类流传至今最基本的一种集体舞蹈形式,它是一种较为古老、原始的舞蹈样貌,还映射出原始篝火舞的遗意,历史悠久,古朴质纯。
4.2 仪式性与继承性
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指出,“仪式不应该被看作是‘惊奇怪诞’的,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并非诞妄而恍然的。文化符号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其存在都有现实的价值与意义。秦州鞭杆舞也不例外,一直是民俗社火活动期间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清末民初,秦州鞭杆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表演队伍达到顶峰,当时秦岭乡一带的“老幼、妇孺皆会舞之”。秦岭乡人在农闲和节日时便用鞭杆舞表达着他们最殷切的期待,以鞭杆舞迎瑞祈福,期盼来年庄稼丰收、生活平安的美好诉说。鞭杆舞在一脉相传的发展中,也会受到社会因子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社火活动曾被迫中断,鞭杆舞也淡化出人们的视野,1977年春节是鞭杆舞被挖掘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表演。秦州社火长兴不衰,为鞭杆舞在秦州地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片养分充足的广袤沃土。
4.3 地域性与文化性
纵观秦人全貌,先秦是在陇右天水地区逐渐繁荣而兴起的。其生存环境是四面受阻,东隔陇山与周王室相邻,西、北两面广布戎、狄,秦人在周人与戎狄的夹缝当中生存。[4]在这种状况之下,秦人因地制宜,排除万难发展生产,出现了农牧两旺的景象。而源于秦人牧马的鞭杆舞也不例外,悠久的历史沉淀已将民族文化烙印和地域风格特色深深打入其中,在其诞生、源远流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鲜明、个性的特征。鞭杆舞剽悍、刚烈、粗犷,明显融进了西部少数民族擅长马战,喜好军功的气质,这些也正反映了秦人入乡随俗,虚心学习吸收西戎文化,追求中兴的不懈努力,充分说明天水秦文化强烈的兼容性和博大的开放胸怀,传递出天水秦文化鲜明的功利色彩和进取精神,赞扬了秦人轻死重义、果断勇敢、粗犷悍厉的民族性格,洋溢着不畏困难、跨越障碍、勇往直前的积极精神。
5 结论
鞭杆舞秦人在长期牧马、驯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产生, 它继承和体现了陇右天水秦文化的精髓。并与民俗社火祭祀活动不断相互促进、融合, 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艺术交织状态之中。
就表演机制、舞蹈形态观之,秦州鞭杆舞集社火祭祀程序、道具、配乐、服装、装扮涂抹为一体,通过其服饰扮相可表达出与戏曲文化的关联,其祭祀仪式体现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浸透,表达出原始伏羲文化的遗迹。就特性而言,秦州鞭杆舞具有民间舞蹈的原始性与古朴性,仪式性与继承性,地域性与文化性,传达着“舞蹈是人类生命仪式”的基本人文精神,处处彰显着秦人披荆斩棘、威猛豪放的民族性格特征。只有深刻、准确的了解鞭杆舞,掌握其精髓,才能更好地把握鞭杆舞的审美特征、演绎鞭杆舞的审美风格,使其在推广和传播的过程中、在继承发展的长河中始终保留秦人具有民族特色的象征性的身体语言表达,并在此基础上使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脉相承、不断发展。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