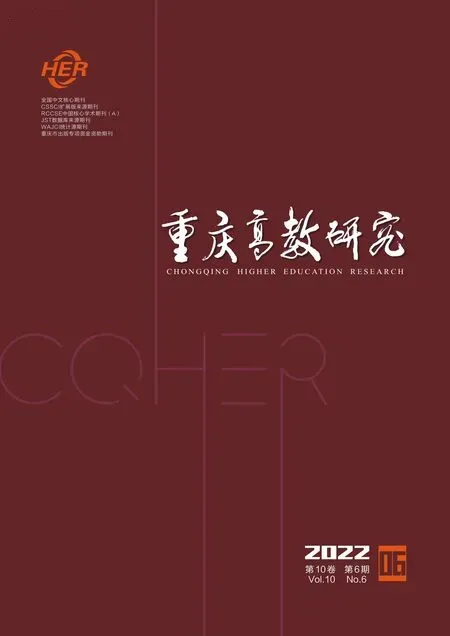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压力与应对策略
——基于3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调查
闵 韡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芜湖 241000)
一、问题提出
以自由探索为特征的学术职业通常被认为是低压力、高社会地位以及令人满意的[1],然而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对于学术环境和学术职业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政府与高校间关系构型的变迁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高校传统的社团模式和决策过程逐渐为科层或准科层的行政管理所取代,聘任、晋升考核与评价制度的深刻变化使高校不再是令学术人感到安适和愉悦的场所,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大的职业压力[2]。英国大学教师协会(AUT)2003年的调查显示,93%的成员感受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62%的成员感受到“过度”的压力,约27%的受访者表示曾“相当认真地”考虑过转行[3]。杨娟等对某“985工程”建设高校 387名教师的调查显示, 53.0%的教师表示自己目前工作压力比较大,38.5%的教师认为自己目前压力非常大[4]。在职业压力成为高校教师普遍生存状态的背景下,作为高校教师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生导师的压力尤为值得关注,然而目前关于研究生导师职业压力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专门针对研究生指导过程中压力的研究尤其少。
从我国当前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及现状看,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压力主要有以下来源。首先是指导责任的强调。2018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5],2019年2月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再次强调“导师是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6]。其次是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及附带效应。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对高素质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研究生培养规模逐年扩大。2020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313.96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267.30万人,博士研究生46.65万人,相较于2010年分别增长了104.08%、108.92%和80.17%[7]。培养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对导师的学术水平与资源、指导能力、时间精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学生入学动机多元化,学习能力、学研态度、心理状态多样化等也给部分导师带来了困扰,增加了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的难度。徐贞2017年对35所高校研究生院理工科博士生的调查显示,纯粹出于“对科研的兴趣”这一内部动机而读博者仅占12%,45.5%的人为混合动机,42.5%的人则为纯外部动机(如“对博士学位的情结”“提升就业竞争力”等)[8]。此外,不少学者也探讨了研究生心理状态、师生关系对研究生培养过程及导师的影响[9-10]。最后,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不断发展,一些整体上有助于培养质量提高的政策、制度在施行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这同样影响了导师的指导压力,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学位论文盲审制度的施行。自200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展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以来[11],学位论文盲审逐渐成为众多培养机构的选择。盲审降低了导师论文评审中的人情负担[12],强化了导师的指导责任,提高了培养单位对于学位论文的重视程度[13]。但与此同时,盲审制度的一些局限性,如不同专家对于论文合格线的把控差距较大[13],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导致不同评审者之间分歧较大[14],个别专家缺乏责任心影响了评审结果的准确性等[15],都给盲审结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导师的心理负担与压力。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培养过程的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压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框架
围绕职业压力的形成与应对产生了若干理论模型,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工作要求-控制”模型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由卡拉塞克(Karasek)于1979年提出,其中工作要求主要包括工作量、时间压力和需求冲突,工作控制则包括技能裁量权(如创造性地完成工作)和决策权(决定如何完成工作)。该模型认为,高工作要求和低工作控制的组合会导致压力反应、降低工作满意度并导致生理上的问题(如高血压)[16]。自20世纪80年代起,“工作要求-控制”模型一直是职业健康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2001年,德梅鲁蒂(Demerouti)等在已有研究和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要求-资源”(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模型。其中工作要求是指“工作中那些需要持续的身体或精神上的努力,并且与某些生理和心理成本相关的身体、社会或组织方面的内容”,工作资源是指“那些有助于实现工作目标,减少与工作有关的生理和心理成本,或者有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身体、心理、社会或组织方面的要素”。该模型认为,过高的工作要求会导致持续性紧张继而损害健康,工作资源则能缓解工作要求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同时产生更高水平的工作动机[17]。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被看作是对“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它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更为宽泛,包括后者用于描述工作控制的内容,如自主感、决策参与等[18-19]。严格来说两种模型并不具备可比性,但二者在工作资源上的不同侧重依然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例如,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哪一种“资源”更有助于降低导师的指导压力,是导师的学术水平、课题项目,还是指导过程中的参与和控制?
(二)研究假设
探讨这一问题前,需要厘清研究生指导过程中的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对于研究生导师而言,其工作要求首先体现在指导责任的落实上。如《意见》规定,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其职责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术创新能力、优化培养条件、注重人文关怀等[5]。尽管不同高校在研究生指导的具体要求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对于大致属于同一类型的院校(如“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导师而言,相互之间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其次是指导研究生数量。一般认知中,学生越多,对导师的学术水平、指导能力与精力的要求也越高。最后,学生的学习与心理状态也是工作要求的重要体现。国外不少以基础教育教师为样本的研究将处理学生的不良行为视为教师的工作要求[20],研究生群体中类似问题并不多见,但伴随着培养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研究生来源多样化、非学术动机偏多、心理问题频发等依然会给导师带来一定的困扰甚至是内耗[8-9]。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越多,指导压力越大。
H2:导师在研究生学习能力、心理状态、学研态度上的感受越消极(对应的压力越大),相应的指导压力越大。
研究生指导中的工作资源首先包括导师的学术水平、课题项目以及指导时间。诸多研究表明,这些要素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1-22]。其次,一些研究将组织支持、社会支持、同事支持等一些人际关系变量视为工作资源[23-24],良好的师生关系作为导师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具有类似的功能。最后,指导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导师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认可,这种对于工作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在一些研究中同样被认为是重要的工作资源[25]。李希特(Richter)和哈克(Hacker)将工作资源分为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前者来自组织和社会层面,如工作控制、决策参与、资格获得潜力(potential for qualification)、任务多样性以及同事、家人、同伴的支持等,后者则体现为个体的认知特征和行为模式[17]。根据这一分类方式,导师的课题项目、师生关系属于外部资源,指导热情属于内部资源。指导时间无论作为一种实体资源,还是作为工作控制的一种表现(时间不足会导致控制感缺乏)[26],皆应属于外部资源。学术水平则既可以视为一种外部资源(资格获得潜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资源(认知特征)。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导师的职称、学术头衔越高,指导压力越小。
H4:导师主持的课题数量越多,指导压力越小。
H5:导师日均用于指导研究生的时间越多,指导压力越小。
H6:导师的指导热情越高,师生关系越好(对应的压力越小),相应的指导压力越小。
导师在指导过程中的参与、控制也是工作资源的重要体现[18-19]。尽管指导时间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控制上的差异,但就具体指导过程而言,学科的影响显然更加深刻。英国学者托尼·比彻和保罗·特罗勒尔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一书中将学科分为“趋同和趋异”“都市型和田园型”等不同类型[27]。我国学者王东芳认为,知识的特性决定学科知识生产活动对空间和资源的需求程度,继而形成学科文化并构成部落人员的关系结构。对于化学等理工学科,知识生产活动对实验室的实体空间及其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经费、项目、论文等作为师生关系的纽带,一定程度上促使师生密切的互动以及导师对博士生的高频率指导。英语作为典型的田园型学科,其重个体化阐释、独立探索乃至寂寞的学科文化,以及对资源和物理空间等社会条件的低需求使得师生关系相对更加疏离化、协商化[28]。现实中人文社科领域导师一般不像理工农医领域导师那样对学生的研究选题、方法、进度等进行全过程详细把控,而缺乏共同的知识基础也使得人文社科领域中学位论文盲审出现争议的可能性更大。此外,理工农医领域中硕博连读者和直接攻博者较多,导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一般高于以普通招考和申请考核为主要入学方式的人文社科领域。部分理工学科的博士生是在入学一段时间或者经过实验室轮转(rotation)后再确定导师[28],而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生往往是在报名时就已确定导师。这些均使得不同学科领域导师在指导过程的参与、控制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7:理工农医领域导师的指导压力整体小于人文社科领域导师。
H8:相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理工农医领域中导师的职称、学术头衔、课题数量对指导压力的影响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笔者参与的“高校教师职业压力状态与感受调查”。调查于2018年4月至6月进行,通过邮寄的方式向3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发放纸质问卷6 000份,共回收来自其中35所高校的3 813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63.6%。在删除非研究生导师、艺术学、军事学以及极端值较多的样本后,共保留2 692份有效样本。其中,男性1 818人(67.5%),女性874人(32.5%);人文社科领域775人(28.8%),理工农医领域1 917人(71.2%);教授/研究员1 173人(43.6%),副教授/副研究员1 230人(45.7%),讲师/助理研究员289人(10.7%);院士6人(0.2%),千人/长江等(1)“千人/长江等”包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优青”“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计划入选者。165人(6.1%),其他省级人才566人(21.0%),无学术头衔者1 955人(72.6%),不同类别导师的数量分布见表1。

表1 不同类别导师的数量分布
(二)变量说明
1.指导压力
问卷中与研究生指导有关的压力题项包括“研究生学习能力压力”“研究生心理状态压力”“研究生学研态度压力”“研究生论文指导压力”“研究生论文盲审压力”“科研团队管理压力”和“师生关系压力”。已有文献关于何为“指导压力”并无统一界定。一般而言,指导压力既可以理解为导师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压力,也可以理解为导师在与指导过程和结果最为相关的方面(如论文指导、论文盲审、科研团队管理)所感受到的压力。限于问卷容量以及研究设计的需要,这里仅将被试对“研究生论文指导压力”“研究生论文盲审压力”“科研团队管理压力”3个题项的评分定义为指导压力(因变量),其余压力题项则用于描述导师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自变量)。所有压力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评分越高表示导师压力越大或感受到的学生状态越消极。
2.工作要求
(1)学生数量。包括指导硕士生数量和指导博士生数量,通过被试填写获得。
(2)学生状态。通过被试对 “研究生学习能力压力”“研究生心理状态压力”和“研究生学研态度压力”3个题项的5级评分获得,评分越高表示导师感受到的学生状态越消极。
3.工作资源
(1)学术水平。由导师职称(从低到高分别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学术头衔(从低到高分别为无、其他省级人才、千人/长江等、院士)两个指标组成。导师的职称和学术头衔为定序变量,数字越大表示职称和学术头衔越高,相应的学术水平也越高。
(2)课题数量。通过被试对“近5年所主持的国家级(包括各部委)纵向课题的数量(0项、1项、2项、3项及以上)”这一题项的单项选择获得。该变量为定序变量,数字越大表示课题项目越多。
(3)指导时间。通过被试对“平均每天用于指导研究生的时间(小时)”这一题项的填写获得。
(4)指导热情。通过被试对“我对指导研究生有极大的热情”这一题项的5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获得。
(5)师生关系。通过被试对“师生关系压力”这一题项的5级评分获得,得分越高表示导师感受到的师生关系越消极。
(6)指导过程中的参与和控制。通过学科差异反映,由被试根据所从事的学科、专业,在教育部13个学科门类中进行单项选择。其中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被合并为“理工农医领域”,其余学科(艺术学、军事学样本已被排除)被合并为“人文社科领域”。
四、研究结果
(一)不同类别导师的学生数量、指导时间、课题数量分布
1.指导研究生数量
不同类别导师指导研究生数量分布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人文社科领域导师平均指导9.26名硕士生和1.93名博士生,理工农医领域导师平均指导7.82名硕士生和2.46名博士生。总体上看,教授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数量远高于副教授和讲师,后两者之间差距不大。除人文社科领域中的院士外,导师学术头衔越高,所指导的研究生数量越多。

表2 不同类别导师指导研究生数量分布 (单位:人)
2.指导时间
不同类别导师研究生指导时间分布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在人文社科领域还是在理工农医领域,随着导师职称的提升,其日均用于指导研究生的时间也在增加,但生均日指导时间(日均指导时间/指导研究生总数)则呈下降趋势。除院士外,指导时间随导师学术头衔的变化同样符合这一趋势。由于研究生指导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讨论总时长更有意义,但过低的生均指导时间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问题。

表3 不同类别导师研究生指导时间分布 (单位:小时)
3.课题数量
不同类别导师主持的纵向课题数量分布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随着导师职称和学术头衔的提升,近5年所主持的纵向课题数量也在增加。

表4 不同类别导师的纵向课题数量分布

续表
(二)不同类别导师的指导压力、指导热情现状与差异分析
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压力以及其他方面压力、指导热情的现状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无论在人文社科领域还是在理工农医领域,除师生关系压力外,其他压力以及指导热情的均值都超过了3,说明绝大多数导师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同时也对指导研究生富有热情。在学科差异方面,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论文指导、论文盲审压力显著大于理工农医领域导师,师生关系压力和指导热情则显著低于后者。

表5 不同学科导师的压力、指导热情分布与差异检验
不同类别导师的指导压力分布及差异检验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在人文社科领域,不同职称、学术头衔导师的指导压力相互间无显著差异;在理工农医领域,不同职称、学术头衔导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以及不同学术头衔导师的论文指导、论文盲审压力相互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教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显著小于副教授和讲师,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总的来看,导师的学术头衔越高,指导压力越小。

表6 不同类别导师的指导压力分布与差异检验
(三)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导师指导压力的影响
为探讨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导师指导压力的影响,以工作要求、工作资源相关指标为自变量,分别以研究生论文指导压力、论文盲审压力、科研团队管理压力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由于导师的职称、学术头衔、纵向课题数量为定序变量,故将其转换成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其中学术头衔、纵向课题数量分别以“无”和“0项”为参照,职称则以“副教授”为参照(样本中副教授占比最高,讲师占比最低)。结果如表7所示:第一,学生数量对导师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无显著影响,对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有负向预测作用。假设H1未得到验证。第二,导师在研究生学习能力、心理状态、学研态度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对其指导压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第三,相对于副教授,讲师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教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小;千人/长江等的论文盲审压力显著低于无学术头衔者。假设H3得到部分验证。第四,相对于无课题者,近5年主持2项课题者的论文盲审压力更小,主持3项及以上课题者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假设H4得到验证。第五,指导时间对导师指导压力无显著影响。假设H5未得到验证。第六,指导热情对导师的论文盲审压力和科研团队管理压力分别有负向和正向预测作用,师生关系压力对导师的指导压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假设H6得到部分验证。第七,即使将导师的职称、学术头衔、纵向课题数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学科的效应依然显著,理工农医领域导师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显著小于人文社科领域导师。假设H7得到验证(2)若从之后的学科分组回归的结果看(见表8),理工农医领域中有课题者比无课题者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大,假设H4只得到部分验证。但考虑到整体结果以及行文逻辑,这里还是如此表述。此外,表8中指导时间对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有正向预测作用,虽与表7结果有差异,但同样与假设H5不符。。

表7 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导师指导压力的影响
为探讨导师的学术水平、课题数量对指导压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学科差异,以学科为分组变量分别输出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导师的学术头衔、职称以及课题数量对指导压力的影响仅存在于理工农医领域。相对于副教授,讲师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教授的论文指导压力更大,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小;相对于无学术头衔者,千人/长江等的论文盲审压力更小;相对于无课题者,有课题者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大,有2项课题者的论文盲审压力更小,有3项及以上课题者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假设H8得到验证。

表8 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不同学科领域导师指导压力的影响
五、讨 论
(一)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压力与指导资源现状
调查显示,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压力,以及用于描述研究生状态的学习能力压力、心理状态压力、学研态度压力均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已往研究有着较高的一致性[29]。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导师依然有着较高的指导热情,特别是在理工农医领域。这进一步印证了托尼·比彻等关于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文化差异的描述,研究生作为科研助手的重要价值在理工农医领域得到了更加显著的体现。随着导师职称和学术头衔的提升,近5年所主持的纵向课题数量以及日均用于指导研究生的时间也在增加,但由于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生均日指导时间则呈下降趋势。对于研究生个体而言,选择高水平的导师意味着在获得更多指导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以牺牲一定的受指导时间为代价,这无疑对研究生个体的学习、科研及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导师的师生关系压力相对于其他压力处于较低水平,其均值未超过3,说明师生关系整体情况良好。
(二)学生数量与状态、指导时间和热情等对指导压力的影响
无论是笔者参与的2017年研究生调查[30],还是本次调查,都没有发现学生数量对于研究生指导的负面影响,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级联指导”(cascading mentorship,由团队中、高级成员对初级成员提供指导)模式的广泛存在能够有效弥补导师指导资源的不足[31]。导师在研究生学习能力、心理状态、学研态度、师生关系方面感受到的压力越大,相应的指导压力越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带来学生入学动机的多元化以及学习能力、学研态度的多样化,很多时候未必能够与导师的期望完全契合,而部分导师对于研究生过于理想化的期待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有研究指出,专业人士往往没有接受过类似于工业界“降低期望值”的培训,或者怀着对于世界的不合理信念,最终导致了幻灭感[32]。其次,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全球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自然》(Nature)杂志2019年开展的全球博士生问卷调查显示,各主要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博士生陷入焦虑、抑郁的比例均高于28%,其中中美两国博士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约为45%左右[33]。国内有调查发现,研究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44.16%,其中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和抑郁3项因子的检出率相对较高[34]。心理问题的多发给研究生本人和导师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内耗,增加了导师的指导压力。最后,师生关系也是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显示,高质量的师生关系在学生对其大学经历的满意度中占比高达93%[10],而糟糕的师生关系则会加剧学术压力的负面影响,导致学生延迟获得学位或辍学[35],直接或间接影响导师的指导压力。
指导时间对指导压力的影响同样有限,仅对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对研究生培养有重要影响的是指导频次(包括非正式的会面)[36],以及指导的深度与质量[37],而非单纯的指导时间。另一方面,指导时间的增加具有多重含义,既可能是因为导师认真负责,也有可能是因为学生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导师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帮助解决[38],这种情况在团队合作相对较少的人文社科领域可能更加突出。指导热情对导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对理工农医领域导师的论文盲审压力则有负向预测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指导热情通常并不能直接解决指导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故而对指导压力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需求-诱导压力补偿”(demand-induced strain compensation,DISC)模型认为,只有当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处于同一领域时,才能较好地抵消高工作要求的负面影响[39]。从指导热情所发挥的作用看,它既可能促使导师更加重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特别是在参与指导较多的理工农医领域),在面对盲审时更有信心,也可能导致对科研团队的过多干预或过分担心,从而产生更多团队管理方面的压力。
(三)学科、导师学术水平、课题数量对指导压力的影响
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指导压力整体高于理工农医领域导师,职称、学术头衔、课题数量对导师指导压力的影响仅存在于理工农医领域,证实了前文关于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学科文化对导师指导压力具有不同影响的假设。在以个体研究模式为主的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学术水平、课题资源对于降低指导压力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从而造成了不同导师 “无差别的”高指导压力。此外,指导过程中的参与、控制相对不足也是人文社科领域导师指导压力偏大的重要因素,其证据在于当导师的职称、学术头衔、课题数量与学科处于同一回归方程中时,学科的效应依然显著。从学科文化的视角看,人文社科领域相对“松散”的指导模式在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探索空间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师生交流的稀缺和同辈关系的疏离[40],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导师的指导压力。 在以“硬科学”为主的理工农医领域,研究生对导师学术水平和课题资源的依赖性更大,故导师的学术头衔与课题资源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其论文指导或盲审压力。不过课题数量的增加也是一柄双刃剑,在为科研团队带来资源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任务协调上的困难,以及团队成员因负担过重、工作时间过长造成的满意度下降[41],增加导师科研团队管理上的压力。在职称方面,相对于副教授,讲师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教授的论文指导压力更大,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小,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双一流”建设高校中讲师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情况相对较少,且一般是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群体,具备一定的指导能力。与此同时,他们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时间较短,接触到的学生有限,对于研究生指导中的困难未必有特别充分的体会,因此其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相对副教授来说更小。其次,教授相对于副教授来说,科研团队管理经验通常更加丰富,或者因“级联指导”模式的存在,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处理科研团队中具体、烦琐的事务,故科研团队管理压力相对副教授更小。在论文指导方面,尽管丰富的指导经验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多年的指导工作同样有可能引起导师的倦怠,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学生、学术环境与日趋严格的问责机制。最后,教师所处的发展阶段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鲍德温(Baldwin)认为,教师会随着职级的提升和职业生涯对他们所提出要求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卡里沃达(Kalivoda)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s)和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s),正教授(full professors)会将“提高学校的质量和声誉”列为更加优先的目标[42]。相对于副教授和讲师,教授更可能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意义以及学位论文的重要性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从而间接导致论文指导压力的增加。不过上述现象为何没有延伸到人文社科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六、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前文中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绝大多数研究生导师具有较高的指导压力和指导热情。其次,作为导师工作要求的研究生学习能力压力、心理状态压力、学研态度压力,以及作为工作资源的师生关系(通过“师生关系压力”反向描述)分别对导师的指导压力具有正向和负向的预测作用;指导过程中的参与和控制(通过学科差异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资源对导师的指导压力产生显著影响,参与控制程度相对较低的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指导压力显著大于参与控制程度较高的理工农医领域导师。最后,其他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变量分别对导师的指导压力产生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指导的博士生数量越多,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越小;日均指导时间越长,人文社科领域导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越大;指导热情越高,导师的科研团队管理压力越大,理工农医领域导师的论文盲审压力越小。导师职称、学术头衔和课题数量对指导压力的影响仅限于理工农医领域。相对于副教授,讲师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教授的论文指导压力更大,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小;相对于无学术头衔者,千人/长江等的论文盲审压力更小;相对于近5年无课题者,有课题者的论文指导和论文盲审压力更小,科研团队管理压力更大。
(二)研究建议
1.完善招考方式改革,推进导师资格动态管理
数据分析表明,研究生的学习能力和学研态度对导师的指导压力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的招考制度往往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科研能力、考试成绩与学科背景,很少或难以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研态度等非认知学术能力。有调查显示,36.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现有的申请考核方案中,有关研究生非认知能力的考核方式、内容较为薄弱[43]。一些直博生获得推免资格后,也出现了主动学习意识不足、状态松懈的现象,导致无法适应之后的学术角色[44]。建议在研究生招考中创新方式方法,对报考者的学术动机、学术志趣等非认知能力予以更多考量。在导师方面,相比于过去的“成就”(职称和学术头衔),其当下的“成绩”(近5年主持的课题数)对于减轻指导压力起到了更加显著的作用。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多数高校依然将“导师”定位为一种荣誉,而非像西方大学那样视其为一份具体的工作,在新增导师的遴选、审查上较为严格,但对曾任导师的审查则较为宽松[45]。这对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完善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在客观上给那些难以胜任指导工作的导师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与压力。重新定位导师资格,严格遴选程序,推进导师资格的动态管理,既是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对教师自身心理健康的一种保护。
2.适当增加资源支持,强化指导过程控制
在理工农医领域,课题资源能够有效缓解导师的指导压力。在人文社科领域,尽管课题资源并不直接影响导师的指导压力,但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对导师产生影响,如指导资格的获得与维系等。总体来看,资源上的差异使得普通导师相对于有学术头衔者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访谈中,有工科教授表示自己40多岁了还没有“帽子”(学术头衔),面临研究转型的难题,每天琐事缠身,很多事情都得自己“跑”;有导师感叹自己难以招收到合适的学生,优秀学生都想跟着“大老板”;有文科教授表示晋升博导后,课题、经费上的压力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一旦出现“中断”,就有可能被取消当年的招生资格。对于培养机构而言,虽然高学术层级的导师贡献非常大,但作为承担了绝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普通导师依然值得关注。在严格准入条件、加强过程控制的同时,也应尽可能地为大多数普通导师创造条件,提供资源支持,以减轻其工作负担与指导压力。
尽管在人文社科领域盲目推行理工农医领域的指导模式并不可取,但对于导师而言,加强过程控制,及时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与困难,至少能够做到对培养过程心中有数,及时应对,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指导压力。潘炳如等的研究发现,在人文社科领域,接受短周期、面对面指导的研究生,其创新能力显著高于接受长周期和非面对面指导的研究生[46]。与诸多研究的观点一致,培养机构和导师应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如课程考核、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环节加强控制[12, 47],从而提高培养质量、减轻导师的指导压力。
3.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国内部分基于《自然》杂志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我国博士生对于出版发表、合作机会、资金支持的满意度略高于或接近于发达国家,但对导师给予心理支持和职业发展指导的满意度与发达国家尚存差距[48],师生关系满意度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9]。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增强导师的相关责任意识,使其能及早发现并参与处理;另一方面,发挥党、团、班及学校各职能部门、专业人员的作用,在研究生心理危机的干预和处理上给予导师充分的支持。应建立科学的导师评价体系,让导师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参与研究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对导师的相关工作要及时肯定、表扬和奖励,健全立德树人成效评价依据[9]。
良好的师生关系一方面会让研究生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增强其追求既定目标的决心[50],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降低导师的指导压力。首先,应严格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这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在经历双向选择、确立指导关系后,可学习国外一些大学的做法,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让师生了解各自的角色和期望,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会议的频率、给导师提交的作业应满足的标准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研究生被视为“训练中的同事”(colleague in training)时,指导关系发挥得最好[51]。最后,针对一些矛盾难以解决或缓和的情况,应在保证程序完备的前提下,给予研究生和导师重新选择或退出指导关系的途径,及时止损,避免师生间长期相互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