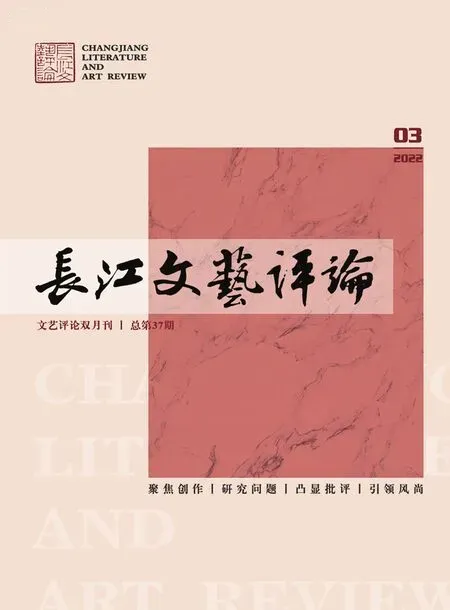工人的影像生活史
——电视剧《人世间》中工人阶级的回归与重构
◆张 斌 王雨晴
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人阶级始终是充满时代创造力和话语张力的特定群体。不同历史时期中工人们的生产活动、命运走向深刻映现了工人身份的嬗变轨迹、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变迁。工人阶级作为电视剧的重要书写对象,也经历了由显渐隐的创作变化。而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让工人阶级在日常叙事中以富有实在生命力、立体存在感的群体形象再次复现于电视荧屏之上。《人世间》将新中国发展的五十年历史铺展为时间轴,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所历经的世事变迁为切入口,以一副全新鲜活的工人命运图景宣告了工人阶级在电视剧中的影像回归,也重构了工人阶级形象的表达。
一、电视剧中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起伏与回归
在中国电视剧诞生的六十余年中,荧屏上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几经起伏,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创作流变。首先,在电视剧诞生初期,与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相一致,工人也经常作为电视剧中的主体、主人公形象出现,是被歌颂与赞扬的对象;其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电视剧对工人阶级的表现由“工人”转移至“改革”,工人成了改革进程中需要被动员和教育的对象,其主体性开始滑落;最后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以工人阶级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庞大的生产总量中仍然占据少数地位,但是以《人世间》为代表的电视剧不仅将工人重新推至荧屏中央,而且重塑了工人阶级在历史变革下的生活世相,更新了工人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书写方式,工人阶级主体性在影像中得以历史性回归。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性地提出文艺表现和服务的主体和对象应该是工农兵群体。这一文艺思想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创作和研究的指导性思想,也为早期电视剧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电视剧艺术诞生初期,其创作受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政策的影响,电视剧的说教性与政治宣传功能较为明显。电视剧创作者在响应党的政治宣传号召下,将具有爱国奉献、吃苦耐劳等精神的工人群体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同时也成为了电视剧艺术创作表现的主体。虽然在我国电视剧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作品数量较少,多以黑白直播电视剧为主,但即便如此,以工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仍不在少数,如歌颂医疗战线全力抢救因保护国家财产被烧伤的上海先进工人事迹的电视剧《党救活了他》;反映上海工人先进事迹的电视剧《红色的火焰》;描写工业战线的技术革新运动的电视剧《生活的赞歌》等。这类早期工人形象的塑造“既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同时,其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又在宣传政府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通过集体化的工人活动实践,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品格,烘托了时代积极、昂扬的精神面向。剧中“英雄式”的工人形象成为该时期影视作品的创作准则,也造成形象书写落入固定化、模式化的桎梏。当历史发展不断前进之后,工人阶级的影像呈现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浪潮中就发生了由主体到边缘的创作转移。
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领域做出了重大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阶层内部发生显著的分化与变动,出现了多元的社会新阶层,因而原本突出而明显的工人的“阶级性”开始模糊不清。电视剧是一门镜像艺术,它通过艺术手段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社会层面的转型与变革直接影响电视剧艺术的创作生产。如果说在电视剧初创时期,电视剧作品通过将工人形象“典型化”处理,进而彰显国家主流思想意志,那么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氛围中,工人形象就开始被糅合进一个个具体的“改革”实践中,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全新影像图景,微观视角的底层叙事转向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主体性减弱的现实境况。无论是《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改革时代先锋人物乔光朴,还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工人改革者刘思佳,这些工人形象均在“大刀阔斧的改革”语境中重新审视着自身的阶级身份,他们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导者,而是成为社会的“被改造者”,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也在“改革”现实下,开始不断自我质疑与否定。新世纪之初,《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主人公张大民作为暖炉厂的工人,已然褪去了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权、先锋性,而是以一种底层“打工人”的姿态和轻松幽默的豁达态度直面人生,小人物的鲜活感展现无遗,引领了中国电视剧的潮流。虽然这一时期电视剧中的工人形象相较前阶段稍显多元,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人阶级因在社会空间和话语空间中的双重旁落,导致群体身份的焦虑和认同的迷茫,直接体现在电视剧中工人形象塑造的凋零与隐身。
迈入新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产业变革越发剧烈,工人阶级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工人群体的社会存在感进一步被稀释。面对高质量发展和人口转变的新趋势,党和国家重视民生政策的出台,被忽视的“工人阶级”得以重新回归到主流话语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大国制造不断突破的战略语境下,也对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原本“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在新时代不断被赋予新内涵。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创作呈现多元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电视剧总体数量上看,以工人为题材进行创作的电视剧所占份额依旧较少、题材零散,但相较上一时期,在为数不多工人题材剧中,工人形象经历了由隐到显,不断激活阶级意识的重塑过程。2007年以来,编剧高满堂的“工业题材四部曲”——《大工匠》《漂亮的事》《钢铁年代》以及《工人大院》先后呈现于荧幕之上,这几部作品均采取宏观+微观的组合叙事模式,以跌宕起伏的个人“成长史”,牵引出国家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史,剧中的工人形象既卸下了“英雄模范”的塑造模式,也缓解了一味底层边缘的书写方式,而是聚焦新世纪以来工人群体的真实现状,通过找寻过去、现在关系中共通的工人精神,力图呈现工人阶级的持久生命力和主体存在感。近几年,在党和国家诸多重大历史节点中,《大江大河》《奔腾年代》《逐梦蓝天》等一批“重大主题电视剧”及现实主义题材剧集中爆发,这些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建构了一批立体、生动、富有理想追求的工人形象,而今年年初播出的《人世间》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却用生动的笔触重返工人群体活跃的历史现场,通过两代工人家庭的情感变迁、命运走向,呈现出一幅以工人阶级家庭为基色、以各大历史事件为点缀的丰富生活样态。由此,《人世间》中的工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刻意突出或强调,而是在和其他阶级的互动中,在和时代发展的同构下进行自我更新与重塑,最终达成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回归。
二、《人世间》对工人阶级的新书写
(一)工人阶级形象的立体重塑
纵观工人形象的影像建构过程,其主要经历了主流“英雄式”的书写,底层“打工人”的白描,以及社会“新工人”再造的过程。相较影视作品对其他社会形象复合撰写,工人形象塑造长期困囿于模式化、扁平化的直线经验,缺乏历史与现实叠加的丰富感。电视剧的形象塑造要求“从局部刻画走向整体表现”,在审美观念上体现出“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疏离与融通”,而在审美理想层面,应当是“时代召唤与‘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这就意味着,需要将工人形象放置于复杂、多元的历史现场,开掘工人阶级内部的多维面向,从而满足对工人形象的当代化重塑。《人世间》作为一幅气势磅礴的时代群像画卷,剧中既呈现众多复杂的社会阶层关系,又涉及多元各异的阶级形象,但工人阶级的命运起伏构筑起全剧的主线脉络。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形象在《人世间》的故事世界中,不再是缺乏“烟火气”的平薄个体,而是通过聚焦工人阶级的内部谱系,赋予工人形象的群体层次感,主要体现在工人阶级的纵向代际流动和横向同世代互动。
首先,周志刚与周秉昆父子的工人身份,象征着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代际更迭,也折射出两代工人形象的内涵迁移。周志刚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是投身祖国三线建设的模范榜样,“八级工”的身份,背后是他对事业的强烈进取心;相比较父辈取得的沉甸甸的工人社会地位,周秉昆的工人境遇则多少显得不遂,从木材厂工人、酱油工人到《大众说唱》的责任编辑,再到饭店的副经理,“工二代”周秉昆被时代裹挟前行,反映出新一代工人与老一辈工人面临的社会结构差异。《人世间》最为巧妙的是将“职业代际”与“家庭代际”关系同构,因为周志刚不仅是一名“老工人”,还是传统中国式家庭的“家长”形象,严厉与慈爱在该角色身上尽显。周秉昆除去不尽人意的工作经历,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与关注是他最大的情感诉求。剧中通过父子俩三场“代际冲突”场面,极具温情地呈现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家庭情感伦理,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两代工人形象的价值情感差异。剧中父子俩之间有关家庭—职业的代际过渡,似乎超越玛格丽·米德对前喻文化“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时代的未来”的特征描述,但却在代际差异的表达中突破了工人形象以往的塑造惯性。
其次,《人世间》中对光字片“六小君子”大量情节戏份的铺陈,描写了特定时代“新青年”的工人阶级形象。这里的“新青年”是工人群像,而不是以往工人题材剧中的特例典型,同时“新青年”的“新”着重体现在“六小君子”迥异的工人价值面向,以及与社会转型同步的生存境遇。以周秉昆为首的“六小君子”,相识于朝气蓬勃的青春时代,他们有的是酱油厂的出渣工,有的是木材加工厂工人等,但共享同世代的工人身份,拥有相似的出身地位,经历了一起买肉、一起打架,以及每年春节,大年初三约定的仪式化聚会。随着剧情的发展推进,“六小君子”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无论是吕川、唐向阳成为知识分子,还是德宝、春燕诸多自私行为,又或者赶超因肾病选择卧轨,都在说明《人世间》在塑造“六小君子”时,采取动态的历史叙事视角,差异的形象塑造方式,展现“新青年”工人在共性体验下的个性选择。在最后温情的聚会中,“六小君子”中有人已离开人世、有人要远赴他乡,最终冰释前嫌实现矛盾化解。曾经作为青年工人群体的“六小君子”,各自为事业家庭忙碌奔波,在时代的洪流中自强不息,如今已然迈入父辈工人的生命阶段。如果说,《人世间》中周家的两代工人形象深刻展现工人精神的时代传承,那么“六小君子”则无疑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永恒生命力、向心力。
(二)工人阶级关系的多维形态
电视剧作为一门开放的叙事艺术,通过组织调动不同角色间的关系逻辑,实现情节内容的合乎情理、自然流畅。传统的工业题材剧在处理工人阶级的关系行为上,视点主要聚焦在工人群体内部,工厂、车间、办公室组成工人们交流互动的封闭场所。而《人世间》则通过最大限度的扩充光字片内部的阶级属性,容纳光字片外部的阶层形态,形成工人家庭内部、工人阶级之间以及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三种关系互动模式。流动、多元、开放的微观社会阶层模型,为工人阶级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更大的形态豁口。
《人世间》着力还原工人家庭的关系形态,将工人阶级糅合进家庭序列中加以审视。周家是典型的工人家庭,“和”的家庭主基调始终贯穿全剧。但“和”却通过“不和”的冲突铺就,深刻诠释了工人家庭对“家”的守望与热忱。故事的开始,就交代了周家五口人即将分别的场景:周父远赴四川三线建设前线;长子周秉义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女儿周蓉追随诗人冯化成至贵州农村;小儿子周秉昆和周母相依为命,预示着周家此后多年的离散状态。后来“不和”又体现在相互的情感羁绊,周父与下一代对于情感表达的理解偏差,子辈之间因身份地位悬殊产生的心理罅隙。无论是空间意义上的“不和”,还是心理层面上的“不和”,最终均通过“和”加以缝合、升华。周父去世前与妻儿时隔多年再次躺在一张床上夜谈,安详地走完了勤劳、勇敢的一生。就是如此平凡的工人家庭,却让周家子女对家始终充满着归属感。
对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罗列,一直是工业题材剧创作的舒适区,《人世间》在处理工人阶级关系时,以“破”的意识超越以往的表达范式。首先,“破”体现在颠覆以往对工人上下级关系的书写,曲书记和“六小君子”之间虽然有着酱油厂上下级的关系存在,但他们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段纯粹珍贵的忘年之交。从曲书记执意把周秉昆调入出渣车间,到改善车间环境条件、督促六小君子学习、一次次在周秉昆陷入迷茫时给予指引,立体、完整、充满性格弧光的曲书记改写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秩序。其次,“破”还彰显在“六小君子”的工友关系中,《人世间》在不经意间将“六小君子”情感从“工友”转化成“挚友”,互相扶持、两肋插刀代替职场中的尔虞我诈、竞争猜忌。周秉昆等好友对失聪工友常进步多年帮助,最后一起出资为其买了人工耳蜗,在常进步口齿不清说出每个人的名字时,底层工人阶级间的温情再次升腾。
在注重叙述工人阶级关系的同时,《人世间》重视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互动,精心布置多个“跨”阶级的关系横截面,为工人阶级的身份属性提供广袤的思考空间。周秉昆是工人阶级“跨界”流动的纽带人物。一方面,周秉义、周蓉官员干部、知识分子的身份,造成光字片“六小君子”遇事就找周秉昆的“人生信条”,周秉昆经常在工人阶层与干部阶层中来回奔波,最后德宝和春燕因房子改造问题求助周秉昆无果后,进而举报周秉义贪污行贿;另一方面,由于郑娟与骆士宾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周秉昆一直保持着和商人阶层骆士宾和水自流的互动,为周楠抚养权问题与之进行多年的拉扯与争夺,最终周楠海外意外身亡,周秉昆和骆士宾因肢体冲突,一个锒铛入狱长达九年,一个不治身亡离开人世。可以发现,工人阶级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互动中,常常暴露出阶级间无法弥合的伤痛与症结,更无法准确、清晰地判定是非对错,但工人阶级正是在与其他阶级的相互流动中,找到阶级的主体意识与价值定位。
(三)工人阶级命运的历史走向
故事人物走向的谋篇布局,直接映现出电视剧的审美气质。《人世间》作为一幅横跨50年,勾画二十多个重点人物的现实年代长卷,工人阶级的命运走向虽只占其中一部分,但却熔铸着全剧的精神内核品质。其中对“周家三代”和“六小君子”的命运勾勒,透视了工人命运与时代变革相互映照的共振关系。同时,工人阶级的命运走向在《人世间》中不再被整齐划一,以一概全,而是在一种开放式的宏观视野下,呈现出戏剧化的命运走向和常规化的人生遭遇的交织。
《人世间》中工人阶级戏剧化的命运段落,是一种“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效果,是从特殊的形象出发,抓住现实中的个别真实形象,遵循普遍性的原理。赶超从查出来肾病、尿毒症,到为了将钱留给儿子上大学,不得已选择卧轨自杀,命运最终的走向仅在两集不到的段落中交代完结,急转直下的戏剧化处理方式,并没有让人有脱离现实之感,只因赶超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的命运特殊性恰好映射工人阶级在时代洪流中的群体普遍性。此外,周父周母的突然离世、周秉义患上胃癌病逝,都在人物自身可预知、合逻辑的范围内进行了戏剧化安排,形成了电视剧的情节化。
相比于让人喟叹的不可控的戏剧化命运,剧中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都在常规化的人生轨迹中砥砺前行,然而这种常规化又各不一样,在平凡的底色中映衬出不平凡的坚持。全剧主人公周秉昆一生的命运走向,是底层工人的鲜活生命史,出生于工人家庭的他憨厚正直,经历过辞职、下岗、再创业的奋斗历程;面对过父子间隔阂、儿子离世、身陷牢狱等至暗时刻;在生活的颠簸起伏中,他付出真心与魄力,也收获肯定与成就。通过对周秉昆命运的大量铺陈与着墨,真实呈现了可感、可触、可共鸣的底层小人物。此外,同是工人家庭出身,“六小君子”中的唐向阳和吕川听取了曲书记的“学英语上夜校”的建议,由此考进了北京的大学,提供了工人阶级不一样命运出路的书写。
《人世间》记录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工人阶级经历了国企改革、下岗失业、下海创业的人生变迁,在骄傲与失落、幸福与困苦、坚守与转型中展现出多样化的命运走向,但对生活的憧憬、对时代的向往、对生命的敬畏,一以贯之,初心不改。
三、《人世间》对工人精神的新表达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从大庆油田到两弹一星,从边疆建设到铁路开拓,是各行各业的工人用他们的臂膀担负起了建设祖国的重任,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工业之歌,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工人精神,虽然普通,却充满着力量,成为砥砺国人前行的精神力量。而《人世间》继承了中国工人精神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对勇于奉献的职业精神、互帮互助的伦理精神、坚韧自强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丰富了其精神内涵。这些生生不息的工人精神给予了工人家庭能够从容面对风雨征程的力量,使平凡的生命也能闪耀出人性与理想的光芒。
(一)为国奉献的职业精神
在以往工业题材的电视剧中,往往会表现出某种概念化倾向,“有的因为急于歌颂,将工人形象定格于‘高大全’,个性化的行为被抹杀了,生活化的细节被阉割了”。曾经“喊口号”式的号召,抽象地希望人们敢于奉献、牺牲的理念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失去了力量,而《人世间》则将对于工人精神的传递内生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其为国奉献的精神追求能在人物的所作所为当中给人以切身理解,如周志刚为祖国建设牺牲小家,周秉义为吉春市的发展奉献自我等,这种代际传承下的奉献精神得以不动声色地彰显出来。
周志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工人,他身上所表现出的为国奉献的职业精神是最为明显的。周志刚家住东北,工作地却远在西南,为了能够更好地支援国家大三线建设,两到三年才能回一次家。这是老一辈工人对国家、对社会所作出的奉献,牺牲了与“小家”的相处时间,成全了“大家”。也正是因为有父亲对工作的高要求、高标准,所以周秉义作为工人家庭的儿子,在耳濡目染之下继承了其父对待工作的奉献精神。虽然后期从政,但是工人精神中尽职尽责、勇于奉献的理念始终伴随着他。身为光字片的子弟,他清楚这里老百姓的真正需求,所以即便在开发光字片的时候查出了胃癌,周秉义也是独自承受,并对郝冬梅说:“如果不把这里建设好,我没有脸下去见父亲。”因此,“正是一个个触及人性人心的逼真细节带来了哲学意义上的诗性,让《人世间》与那些悬浮于真实生活之外的作品深切区隔”,电视剧将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融入电视剧的叙述当中,与精神理念相交织,更能体现出人性色泽与生活现实,于观众而言这是一种宝贵的觉悟。
(二)互帮互助的伦理精神
伦理诉求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是对既有益于生命自身、又能被社会认可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尺度的内心期待”。在《人世间》中关于互帮互助这一伦理精神的阐述上,它不仅仅是期望通过互帮互助这一精神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更是希望在群体关系中建立起一个互帮互助的关系价值。在之前的工人题材电视剧中,对于互帮互助这一精神的塑造会更加扁平化,仅仅局限于双方简单的互利互惠层面。而在电视剧《人世间》中,编剧对周秉昆与乔春燕二者间关系的巧妙处理,体现了互帮互助在人情世故中的原则性;同时又以“六小君子”为代表的友谊群体对互帮互助这一伦理精神进行了深度阐释,期以通过构建“仪式化”的影像场面,更好地唤起观众对这一精神理念的深度认同。
剧中在秉昆入狱后的春节饭店相聚和乔春燕搬进新式公寓邀请朋友来吃饭的场景中,我们都看到了“六小君子”对于互帮互助的理解和追求,恰如肖国庆和吴倩争吵时乔春燕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互帮互助的行为当中,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排遣生活中的忧伤苦痛,自己也成为脱离困境走向成长的重要引领者。虽然周秉昆作为剧中“老好人”存在,但是在为人处事上仍旧有自己的原则,如孙赶超因被欺骗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周秉昆选择帮助;乔春燕找周秉昆帮忙多分一套房,周秉昆则加以拒绝。周秉义在光字片改造过程中对不合理要求的坚决拒绝,对曾经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工人的特殊照顾,也更深入地体现了“权为民所用”的执政逻辑。剧集中对坚贞友情的呈现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分原则给予帮助的话,便落入了之前电视剧创作的扁平化困境之中。除此之外,“六小君子”在供销社排队买猪肉的情节也给观众展现了朋友间互帮互助所展现出正义战胜邪恶的可贵力量。其中的每一人物都是实施互帮互助这一群体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群像的共同互助行为作为伦理精神的载体,能够唤起观众对这一正义行为的高度认同与赞赏,更好地诠释了互帮互助的精神。
(三)坚韧自强的文化精神
《人世间》通过对底层工人艰难命运的书写,映射出在困境中练就而成的坚韧自强的文化精神。该剧并未因对苦难的描写而落入苦情戏的俗套之中,相反,其使得工人个体生命与精神二者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波纹圈层的结构。“在艰难中烛照希望,在困境中坚守自强”,对于这一情感的传递是层层递进、循序渐进的,这不仅彰显了底层工人之间的温暖与情怀,同时也给观众带来生活的信心与希望,正如该剧主题歌所唱的那样,“一生向阳”。
“觉得苦吗?嚼嚼咽了”,这是周秉昆在剧中对周楠说过的一句话,言语虽简单,但却在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工人阶级家庭代际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坚韧”在剧中可以指涉为不论是面对生活还是工作的困难,都要有坚韧不拔的态度;而“自强”则指应当保持始终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的状态。《人世间》中的每一个工人都经历过改革的阵痛,从工厂的福利效益变差到大批工人面临下岗,家家户户都有艰难困苦的时期。在肖国庆身上尤能明显看到对坚韧自强精神的执守,即便被班组里的小混混算计、挨打,也仍旧不屈不挠。电视剧塑造的是肖国庆为代表的“东北汉子”对工作的恪尽职守、对命运抵抗,坚韧不拔地应对生活的挑战,同时坚韧自强作为工人阶级一以贯之的品质与良知精神,在时代的浪潮下依然熠熠生辉。工人群体对于自我的认知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与以往电视剧中塑造的文化水平较低、形象粗俗的工人形象相区别,《人世间》还将工人对于知识的渴求生动地呈现在荧屏上,展现出他们依旧是一个追求先进、有思想的群体,始终保持努力向上的积极状态。如:吕川在曲书记的建议下学英语、上夜校;出身于工人家庭中的周秉义、周蓉考取北京大学。这类人物群像在社会的大变迁下依然保持工人的纯良秉性,在学习与工作中严于律己,面对利益的时候虽然也难免各有打算,但面对生活时却仍然奋勇向前。电视剧通过讲述生活常态化下“小人物”对命运的反抗,将“坚韧自强”精神编织进工人精神当中,以此来书写工人阶级精神传承的故事。
结语
电视剧《人世间》塑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工人阶级,它超越了之前对阶级成分的简单划分,将其转化为对身份与精神的摹写,将新的精神与价值理念注入其中,在历史的见证下生动展示了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在电视剧艺术中的回归。它不仅仅是一部简单展现几代人生命与生活世相的作品,也不仅仅是一幅展现中国50年飞速发展的城市图鉴,而是用真切笔触书写了一个在历经世事之后,仍旧对生活抱有热情、对朋友慰以宽容,对家人怀有感恩的中国式工人家庭的故事,给观众以深切的感动。
注释:
[1]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张广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争做新时代奋斗者》,《工人日报》,2018年 5月15日。
[3]王军强,彭文祥:《论现实题材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审美意识》,《当代电视》,2012年第8期。
[4]【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购问题的研究》,周晓红,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页。
[6]高满堂:《满怀激情地书写工人阶级——电视剧〈钢铁年代〉创作谈》,《求是》,2011年第9期。
[7]周安华:《粗粝现实主义的温情镜像——论电视剧〈人世间〉的主旨与魅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年第4期。
[8]曲春景:《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