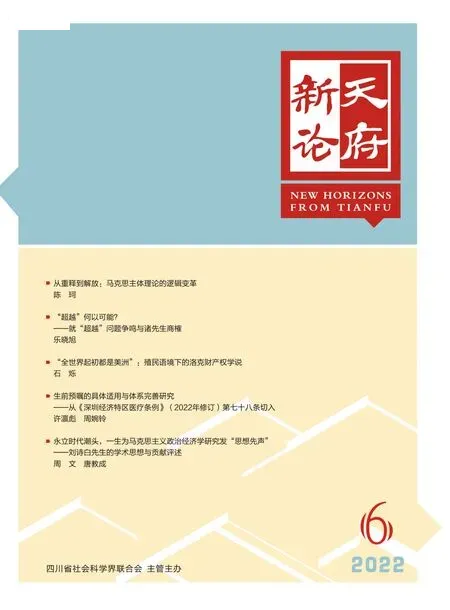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
——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刘希言
爱花之心,赏花之意,自古有之。据周武忠先生梳理,中国花卉文化始发于周、秦,渐盛于汉、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宋,尤其是宋代,可谓中国古代花卉文化的巅峰。(1)周武忠:《中国花文化史》,海天出版社,2015年,第8-12页。因为在此时,花卉不仅得到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关注,而且渗透进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赏花、插花、簪花、食花等各类花事活动极度丰富,以花为题材的诗文、绘画、乐曲、工艺等各种花文化产品极度繁荣。不过,这些实践及其产品虽然都围绕花卉展开,但并不是针对花卉本身的。真正专门性、学术性、系统性的研究,还要属各类花卉谱录。
谱录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的一个类目。最早由宋人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创设,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才正式确立,归于子部之下,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门。从其所收录的文献可见,该类目旨在描述或介绍某一种或某一类“物”,包括该物的品种、名称、形色、性理、源流、工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民俗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专科辞典”。此类书目,虽然在魏晋就已出现,但是直至两宋才蔚然大观,尤其是花卉谱录,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而且所提供的信息也更加全面、更加详细。从前面的解释可见,这些信息固然有一些是“科学的”,但大部分还属于“人文的”,尤其是“审美的”。因此,研究花卉谱录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宋代的园艺技术水平,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
然而,与其他花卉文献,尤其是诗歌与绘画相比,谱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充分的重视。即便有所关注,也多集中在“文献学”与“园艺学”两个领域,对花卉谱录中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审美文化思想挖掘得相对较少。即便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也多满足于现象层面的简单罗列,在分析的深度与阐述的系统性上稍显不足。制约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仅就古代谈古代,缺乏一种今日之眼光或他者之视角。而若以新观念、新理论重新审视之,我们也许会对这类文献所承载的价值或意义体会更深,也许会发现一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实际却不甚恰当之处。而这些成就与不足,正是我们构建当今自然审美体系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故此,本文试图以花卉谱录为研究对象,对宋代花卉审美观念加以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并借鉴西方当代环境美学理论,对这些观念、文化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更客观地评价。
一、审美焦点:容质与韵格
花卉具有审美价值,这一观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历了数代才逐渐形成的。在这件事上,宋人可谓厥功至伟。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2)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宗堂注评:《牡丹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页。孔武仲在《扬州芍药谱》中亦云:“唐之诗人,最以模写风物自喜,如卢仝、张祜之徒,皆居扬之日久,亦未有一语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3)孔武仲:《扬州芍药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3页。诗歌是古人记录自身对自然的审美体验的首选形式。因此,唐代诗文中鲜有牡丹、芍药等花卉的踪迹,这一现象足可以证明,此时此地的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这些花卉的审美价值,或者说,这些花卉还未完全进入他们审美欣赏的视野。这里我们使用了“充分”和“完全”这类强调程度的字眼,因为毕竟如欧阳修所说,仍存在《咏鱼朝恩宅牡丹》这样的作品。但从“一丛千万朵”可见,这些诗人虽然关注到了花卉的审美价值,但其认识显然甚为粗糙,花卉究竟“美且异”在何处,并没有具体描述和详细分说。既如此,那么宋人是如何认识花卉美的呢?较之前人的进步之处又在哪里呢?欧阳修等人可能并未意识到,比起诗歌,他们笔下的谱录更能回答这些问题。
谱录这类文献,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皆没有固定的要求,但再怎么变化,都避不开两项基本内容——分类与描述。分类也好,描述也罢,都依赖于对物之容质的观察、体认。此处的“容”不仅指向花瓣、花蕊、花萼、花蒂等花部,还包括根、枝、叶、实等其他部位。“质”不仅重在颜色这一种感官属性,还包括形态、香气、味道等其他属性。宋人进步之处,首先在于观察得更加全面——涵盖各个部位,兼顾各种属性。沈立对海棠的描述最能印证这一观点:
其根色黄而盘劲,其木坚而多节,其外白而中赤,其枝柔密而修畅。其叶类杜,大者缥绿色,而小者浅紫色。其花红五出,初极红,如胭脂点点然,及开则渐成缬晕,至落则若宿妆淡粉矣;其蒂长寸余,淡紫色,于叶间或三萼至五萼,为丛而生。其蕊如金粟,蕊中有须三,如紫丝;其香清酷,不兰不麝。其实状如梨,大若樱桃,至秋熟,可食,其味甘而微酸。兹棠之大概也。(4)陈思:《海棠谱》,王云校点:《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50-51页。
“柔密”“修畅”“如胭脂点点”“若宿妆淡粉”,语言之优美生动,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知识性记录,当得起文学佳作的美誉。这一评价放在《金漳兰谱》那里更容易使人信服。如“陈梦良”一品:“至若朝晖微照,晓露暗湿,则灼然腾秀,亭然露奇,敛肤傍干,团圆四向,婉媚娇绰,伫立凝思,如不胜情……背虽似剑脊,至尾棱则软薄斜撒。”(5)赵时庚:《金漳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第11页。又如“吴兰”一品:“花头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鸾翥凤,千态万状,叶则高大刚毅,劲节苍然可爱。”(6)赵时庚:《金漳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第11页。在赵时庚笔下,兰花一会儿化身窈窕的少女,一会儿变成飞翔的鸾凤,一会儿又被视为锋利的剑脊。如此诗化的文字,虽然在表达的准确性上失了分寸,但是能带给人艺术上的极致享受,这更能说明花谱所载不是客观的科学认知,而是带有极强主观色彩的审美体验。正如吴厚炎先生所说:赵时庚“对兰花的姿色、体态、容貌极尽描摹比拟之能事”,其“旨趣自不在分类鉴别以给人准确的植物学知识,而在于鉴赏式的品评”。(7)吴厚炎:《“人文文化”与科学——从赵时庚〈金漳兰谱〉与王贵学〈兰谱〉引出的话题》,《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9年第3期。
比之全面,观察之精细更令人赞叹。所谓“精细”即不仅在“细”——关注细节、感知周密,而且在“精”——注重差异、把握特色。一方面,这种精细体现在不同花卉之间。虽然大部分花卉都生有花、叶、枝,但有的重在赏花,如牡丹、芍药;有的赏花的同时兼重赏叶,如兰花、荷花;有的对枝干的欣赏也有所要求,如梅花。同样,虽然大部分花卉具备色、香、态,但有的重在观色,如“色极鲜洁”的牡丹,“艳色绝妙”的芍药;有的重在品香,如“香艳清馥”的兰花,“香气芬烈”的梅花;有的则重在赏态,如屈折苍劲的梅枝,细长优雅的兰叶。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同一花卉的不同品种之间。以菊花为例,宋代之前,菊品不多,故统称为“菊”或“黄华”。直至宋代,尤其是菊谱的出现,人们才有了分类命名的意识。《百菊集谱》所记菊品高达162种,各品之差或在花——有厚瓣、薄瓣、疏瓣、密瓣;或在叶——有千叶、单叶、细叶、粗叶;或在色——有黄色、白色、红色、紫色;或在香——有清香、烈香、麝香、龙脑香;或在状——有金铃、玉盆、佛头、孩儿面。分类叙容,彰显的不仅是认知上的提升,更是审美上的深化。所以,有学者据此提出:“对菊花真正意义上的物色审美是从宋代开始的。”(8)张荣东:《中国菊花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第50页。
“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容质之美总能最先引发人们的关注,最容易受到人们的追捧。中古如此,西方亦然。在西方自然美学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欣赏模式。该模式将色彩、线条等形式特性及其动态组合视为审美欣赏的唯一焦点。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因为形式乃是自然对象本身所有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属性。同时,也标志着自然审美欣赏获得独立与自由,因为对形式的排他性关注使得欣赏者从个人的实用性的、功利性的欲求或目的中跳脱出来,集中注意力于对象本身。
不过,诚如诸多环境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形式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颇多,其中之一是欣赏的范围过于狭窄——对于形式,尤其是如画性的形式的排他性关注导致其他非视觉的审美特性被忽视;二是欣赏的程度过于肤浅——形式仅仅处于自然对象的表层,未能揭示其内在特性与价值。以此反观,诚如上文所言,花谱所叙容质不仅包括形色,还兼顾其他非视觉属性,所以较之形式主义,已经注意到了身体各个感官的全面参与和协同运作。但即便如此,欣赏范围依旧受到限制——只有那些在色、香、态上能够引发人们愉悦之情,或者说,只有具备观赏性的花卉品种才能得到制谱人的青睐,而那些无色、无香、无态之花则被视为缺乏审美价值,因而不值得关注。至于第二点批评,容质的浅表性,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观念,甚至比西方批评更甚。北宋理学家邵雍有一首《善赏花吟》:“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9)邵雍:《善赏花吟》,《伊川击壤集》,郭彧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第160页。这里的“善”即为“恰当”。在邵雍眼中,自然之妙在神而不在貌,一个真正懂得欣赏自然的人,不能只停留在它外在的、有限制的“形貌”层面,而要深入它内在的、无规定性的“精神”层面。而这不仅是邵雍一家的观点,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尤其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之深,即便是以描形写貌为主的谱录也多受感染,典型的表现就是对“韵”和“格”的强调。
《范村梅谱》曰:“梅以韵胜,以格高。”(10)范成大:《梅谱》,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第5页。《玉照堂梅品》曰:“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俯首屏气,受世俗湔拂。”(11)张镃:《玉照堂梅品》,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6页。《王氏兰谱》曰:“撷英于干叶香色之殊,得趣于耳目口鼻之表。”(12)王贵学:《王氏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5页,第46页,第45页。又曰:“兰,君子也。餐霞饮露,孤竹之清标;劲柯端茎,汾阳之清节;清香淑质,灵均之洁操。韵而幽,妍而淡,曾不与西施、贵妃等伍,以天地和气委之也。”(13)王贵学:《王氏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5页,第46页,第45页。《刘氏菊谱》有言:“诸菊或以态度争先者,然标致高远,譬如大人君子,雍容雅淡,识与不识,固将见而悦之。”(14)刘蒙:《刘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页,第26页。综上可见,所谓“韵”,气韵、神韵、韵味也;所谓“格”,品格、性格、格调也。与形色相对,“韵”与“格”皆指向一种内在的、整体的、抽象的精神风貌与个性气质:梅之格,在于清高傲岸、不屈于势;菊之味,在于坚贞高洁、不趋于时;兰之韵,在于纯洁雅致、不流于俗。显然,这些品质,虽称之为花之格,但却属于人之格,更准确地说,乃君子之格。换言之,它们并非花卉本身所有,而是欣赏者将自身的精神追求与道德理想寄托其上的结果。
虽说主观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但必须承认“比德”之说也有其客观的物性基础。谓菊节操自守,是因为它具有晚开、耐寒的生物特性。如《刘氏菊谱》所云:“且菊有异于物者,凡花皆以春盛,而实者以秋成,其根抵枝叶,无物不然。而菊独以秋花悦茂于风霜揺落之时,此其得时者异也。”(15)刘蒙:《刘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页,第26页。《史氏菊谱》也提到:“江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不然。考其理,菊性介烈高洁,不与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黄落而花始开。”(16)史正志:《史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9页。与菊类似,梅得清高孤傲之名,也是因为它剪雪裁霜,凌寒独开,只不过一个是“开得晚”,一个是“开得早”。如“早梅”一品,范成大在释其名时说:“吴中春晚,二月始烂漫,独此品于冬至前已开,故得早名”(17)范成大:《梅谱》,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第5页。。与梅菊不同,兰花之所以能作为君子的象征,靠的不是“时”,而是“处”。兰花性喜阴暗潮湿,故多生于深山幽谷之中。所以,在世人看来,这种花既不与百花争艳,也不因无人欣赏而不芳,极具高洁脱俗之质。正因如此,王贵学才借兰花以自况,直陈自己的才学有如兰花一样,无论是生长于野外深山幽谷之中,还是摆放在家中庭院台阶之下,或是放置于朝廷各机关衙署之内,都会芳香宜人、仁德自守。(18)王贵学:《王氏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5页,第46页,第45页。
观物比德,与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一道,根植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或“心物合一”的文化传统。在古人心目中,自然不是一个外在于、独立于我们,可以静观沉思的、僵死的实体,而是一个与我们相亲相近、通灵通感,同样具有感情、意志的生命体。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人格外重视自然的“兴发”作用,既希望借助自然传达自身的情感意志,又希望通过师法自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花卉的象征意识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成熟还是在宋代。所谓“成熟”就是在“花之德”与“人之德”之间建构起固定的联系,也就是脱离了具体的、感性的“物”之存在,抽象成、固化为某种“文化符号”,且这种观念得到普遍的承认与广泛的流行。如程杰先生所指:“宋人自然审美中处处表现出透过物色表象,归求道义事理,标揭道德进境,抒写品格意趣的特色。具体到花卉审美,则是‘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之象征认识极其流行,因物‘比德’、艺物表德、重‘神’轻‘形’、弃‘色’求‘德’成了最普遍、最基本的审美取向。”(19)程杰:《梅花象征生成的三大原因》,《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这种自然审美取向,类似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的“联想主义”欣赏模式,即将自然对象的审美价值建基于它所引发的一系列个人的或文化的联想之上。必须承认,该模式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审美欣赏的范围,使得那些在视觉上并不出彩的花卉也能走进人们审美欣赏的视野;其次,它提高了审美欣赏的深度,使得人们对花卉的欣赏超越了外在的形式,关注到内在的性理,超越了感性的直观,加入了理性的思考,超越了纯粹的美感,增添了求真、向善的内容;最后,它激发了审美欣赏的活力,即让欣赏者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审美活动的过程中去,而不再像形式主义模式那样只能被动静观。
不过,诚如日本环境美学家斋藤百合子所说:这种自然欣赏模式暗藏着一种预设——自然如果不是被实践的或想象的人类行为“人化”就不能被欣赏,换言之,自然本身没有审美价值,它只有在作为人类愉悦自我、展示自我的工具时才具有价值。(20)Yuriko Saito, “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 in Allen Carlson & Arnold Berleant (eds.),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Toronto: Broadview Press, 2004, p. 150.这种预设同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轻者,一些自然对象会因为无法带给人丰富的联想而被贬低甚至被逐出审美欣赏的大门;重者,则会遭到厌弃甚至责骂,只是因为它们的身上带有某种不好的文化记忆,海棠就是这样的例子。陈思在《海棠谱》中提到了一桩公案——“杜甫不作海棠诗”。杜甫曾客居蜀地八年之久,几乎遍咏当地的所有花木,却唯独没有提到海棠。其中缘由,后人猜测纷纷,至今没有定论,但有两种说法流传最广:一种来自唐代诗人郑谷,他认为杜甫无心吟咏海棠,是因为海棠的飘零让他联想起自己浮沉的身世,遂生出无限惆怅;另一种说法来自宋代诗人王柏,他认为杜甫由海棠联想到杨妃祸国之事,深怀遗恨,所以不作其诗。(21)郑谷的《蜀中赏海棠》:“浓淡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王柏的《独坐看海棠二绝·其二》:“沉香亭下太真妃,一笑嫣然国已危。当日少陵深有恨,何心更作海棠诗。”参见刘蔼萍:《杜甫何以没有海棠诗》,《安徽文学》2009年第3期。无论是愁还是恨,这些情绪显然都不该由海棠来背负。因为所谓的文化意蕴皆是人类强加其上的,并不是花卉本身所有的,它们理应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二、审美评价:感性与理性
《刘氏菊谱》有云:“以品视之,可以见花之高下;以花视之,可以知品之得失。”(22)刘蒙:《刘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页。可见,“品”之一字,除了具有品种、品类的含义外,还可意为品级、品第。换言之,为花“定品”不仅仅指向分类释名,更意在区分高下、辨别优劣,对花卉之审美价值进行评价。这种高下之分不仅存在于不同花卉之间,也存在于同一种花卉的不同品种之间。

由前可知,牡丹诱人之处在于它的容质:花朵硕大、枝叶繁密、花色艳丽、花香馥郁、花态妩媚,既雍容富态又热烈奔放,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与感染。所以说,对牡丹的喜爱,出于直觉,忠于感受,乃是本性使然。这一本性也促使牡丹内部各品种之间有了高下之分。居于王位的“姚黄”,周师厚这样描述:“千叶黄花也。色极鲜洁,精采射人,有深紫檀心,近瓶青旋心一匝,与瓶同色,开头可八九寸许。”(25)周师厚:《洛阳花木记·牡丹记》,王宗堂注评:《牡丹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6页,第82页。稍次一等的“魏紫”,其“叶最繁密,人有数之者,至七百余叶,面大如盘。中堆积碎叶突起圆整,如覆钟状。开头可八九寸许,其花端丽,精美莹洁异于众花。”(26)周师厚:《洛阳花木记·牡丹记》,王宗堂注评:《牡丹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6页,第82页。就颜色而言,“黄”与“紫” (偏红)皆是较为“醒目”的颜色,因为它们的光波较长,有扩张的效果,对人眼的刺激较大。再从形态来看,《天彭牡丹谱》载:“彭人以冠花品,多叶者谓之第一架,叶少而色稍浅者谓之第二架。”(27)陆游:《天彭牡丹谱》,王宗堂注评:《牡丹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6页。对枝繁叶茂的偏爱也是重视感官感受的结果。不过,在以中和为美的大环境下,欣赏者即便寻求视觉的刺激,也不会失了限度,所以才特别强调叶要“不厚不薄”、色要“深浅之中”。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牡丹的花王之位逐渐由梅花替代。作为宋代花谱的集大成者,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将梅花放在了全书第一卷的第一位,与梅有关的内容占了全书近1/10的篇幅。范成大也明确表述过:“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28)范成大:《梅谱》,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11页,第5-6页。于容质处看,梅花似乎难以与牡丹匹敌:它花朵较小,枝叶较疏,颜色较暗,香气较淡,较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它的优胜之处,正如前所述,在韵在神,在格在节,总而言之,在其所彰显的道德理性精神。在理性的烛照下,花叶瘦且疏,色香暗而淡,枝干枯老横斜者,反而更显高级,更富韵味。因为外表越是平淡,越能显示出梅花清新脱俗、低调内敛的品性;越是枯槁,越能展现出梅花风骨凛然、刚毅不屈的精神,即所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正是按照这一标准,范成大否认了南宋初期一些园艺家、画家偏爱新枝嫩条、繁花密叶的审美取向,认为这样的梅花“无所谓韵与格”(29)范成大:《梅谱》,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11页,第5-6页。;同时对“古梅”一品给予了大力关注和极高评价。据陈杰先生所述,古梅其实并非梅花中的一个品种,“古”形容的是其老态。这种“老态”或许是年岁使然,如文中所提到的“偃蹇十余丈”的成都蜀苑梅龙与“如数间屋,傍枝四垂”的清江盘园大梅;或许年岁不高,但却长了一副老态龙钟之相:“其枝樛曲万状,苍藓鳞皴,封满花身。又有苔须垂于枝间,或长数寸,风至绿丝飘飘可玩”,这其实是一种“苔梅”。(30)范成大:《梅谱》,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页,第11页,第5-6页。此二品,范氏赞之曰“奇古”。奇、古都超越了感官一般所能把握的范围,所以要想欣赏之,必然要依靠心灵中的理性能力。正是在运用这一能力的过程中,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故而不再因生命之有限而自怨自艾,而是在与天同体中寻得精神的超脱与富足。故而,陈杰认为,“古梅的发现是梅花审美史的又一大关目,又一大进展”,因为它“把梅花的品德象征发挥到了极致”,引领了后世梅审美的时尚。(31)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86-87页。
花卉地位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审美观念的变化。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由中古向近古转变时衰弱动荡的封建社会后期,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远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比。现实的无奈使得宋代文人不得不放弃“外王”的理想,转而追求“内圣”,即道德修养的提升与理想人格的构建。这种追求不仅存在于认识领域,还渗透进审美,特别是自然审美领域——重神轻形,重理性轻感性,重雅淡轻艳丽成为一种风习。刘蒙对菊花的品评即为典例。在他看来,品菊应先看“色与香”,其次才是“态”。有人质疑说:“花以艳媚为悦”,“态”怎么能放在最后呢?对此,刘蒙回答说:“吾尝闻于古人矣,妍卉繁花为小人,而松竹兰菊为君子,安有君子而以态为悦乎?至于具香与色而又有态,是犹君子而有威仪也。菊有名龙脑者,具香与色而态不足者也……然余独以龙脑为诸花之冠,是故君子贵其质焉。”(32)刘蒙:《刘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页。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此处的“色”与“香”已不再是纯粹的感官属性,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由前可知,菊色以黄为正。而黄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最正统的颜色,乃皇权之象征。因为黄色代表着土地,而土在五行中又居于中位。至于香,更是从屈子开始,便成为品德高洁的代名词,所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正因如此,刘蒙才说:重“色与香”乃是“贵其质”,至于态,则仅属于形貌层面,有固然是好,没有也无关紧要,仅有态者,是难以与其他品种相争的。其实,“无关紧要”还算是一种宽容对待。其甚者,还把“艳媚”视为一个贬义词,将“妍卉繁花”视为“小人”便是这种意识的外露。
虽然说重理性轻感性是宋代自然审美的普遍倾向,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如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就为“艳丽”进行了“辩护”。古人经常用“妖”来形容艳丽之物。《说文解字》云:妖者,祅也,“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3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673 页。。可见,“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非常之态,二是指不祥之兆。故“妖”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作为一个负面词汇而存在。用“妖”来形容花卉,虽有赞其美丽之意,但更多的是批其“不善”,即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规范。与大多数人一样,欧阳修也用“妖”来形容牡丹。但他所言的妖只有“反常”之意,而没有对“不善”的批判。对此,他区分了“灾”与“妖”:“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34)欧阳修:《牡丹谱》,王宗堂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页,第37页。。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种反常正是使美之为美的必要条件:
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痈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一气之偏病则均。(35)欧阳修:《牡丹谱》,王宗堂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页,第37页。
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背景下,欧阳修的这一观点可谓惊世骇俗。一直以来,中国古人都以“中和”为美,但在欧阳修看来,美应该是一种“非常之态”,所以只有“气之偏”者才有可能促成。如吴洋洋女士所说:“儒家美学思想一直对欲望保持警慑的态度,美的感性层面常常无法获得正面肯定。欧阳修‘妖’的观念提出,可视作为花卉审美的感性经验正名。”(36)吴洋洋:《知识、审美与生活——宋代花卉谱录新论》,《中国美学研究》2017年第9辑。这种正名行为,在北美汉学家艾朗诺看来,反而暗示了欧阳修对美的焦虑,即欧阳修意识到自己的审美标准是有问题的,为了给自己的审美趣味以一个合理的说法,他才对艳丽进行了辩解。(37)参见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就欧阳修这一个案而言,这种推测没有充足的证据因而可信度存疑,但它确实符合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在审美领域的心理事实:在情与理、俗与雅之间纠结徘徊。
从环境美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纠结完全是一种“庸人自扰”。因为就审美价值而言,自然对象与自然对象之间本就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优劣之别。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森认为:“所有野生自然本质上都有审美之善。对于自然世界恰当的或正确的审美欣赏基本上是积极的,消极的审美判断在此无立锥之地。”(38)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73.为自然划分等级的观念,大概率是受到了艺术欣赏的影响。“品”之一字起初是在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出现的,如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等。花谱不仅效法了艺术评价的形式,更挪用了艺术评价的标准:无论是容质这样的感性因素,还是韵格这样的理性因素,皆是根据人类主体的审美体验而制定的。换言之,不同花卉之所以有等级之分,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所带给人的感官愉悦或精神愉悦的程度不同。若是我们换一个视角,将审美评价的标准从人类主体移至自然对象本身,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自然对象都有值得被肯定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它们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都参与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运行。面对这样一部部生命传奇,我们如何不为之倾倒,如何不为之拜服,如何还会对其做出否定的审美评价?
不只是“不能”区分高下,立足于环境伦理学,更是“不应”区分高下。因为一旦有了尊卑之心,我们便只会尊重、关爱、敬畏那些符合我们审美偏好的品种,而那些不符合的则会被忽视、贬低甚至践踏。欧阳修曾指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由于牡丹以多叶为贵,所以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这类单叶品种,由起初的万千追捧逐渐沦为无人问津,最终走向灭绝的命运。刘蒙也举过同样的例子,由于时人鄙视艳丽,所以菊花中最为娇艳的一品——桃花菊——逐渐在人们视野中消失。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审美偏见于不顾,花卉的多样性将会越来越低,这将直接影响到该物种的生存与发展。其实,有些制谱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陈思在《海棠谱》中说:“世之花卉种类不一,或以色而艳,或以香而妍,是皆钟天地之秀,为人所钦羨也。”(39)陈思: 《海棠谱》,王云校点:《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49页。赵时庚在《金漳兰谱》中也说道:“万物之殊,亦天地造化施生之功,岂予可得而轻议哉。”(40)赵时庚:《金漳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页。他们两人都认识到了审美特性与审美特性之间只有风格的不同,而没有价值的高低,因为它们都由天地创生,都是天地“生生之功”的具体呈现。然而,受谱录文献内部小语境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语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作者虽然明白说着“不敢轻议”,但实际操作时仍凭着一己之好强分高低,这无疑是时代的局限。
三、审美方式:格物与造境
《王氏兰谱》有云:“天壤间万物皆寄尔。耳,声之寄;目,色之寄;鼻,臭之寄;口,味之寄。有耳目口鼻而欲绝夫声色臭味,则天地万物将无所寓矣。”(41)王贵学:《王氏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页,第45页。寄者,托付、依附也。这句话告诉我们,自然对象的审美属性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借助人类主体的审美能力才能显现出来。换言之,我们究竟能欣赏到何种程度取决于采用何种欣赏方法,“物之体”取决于“人之用”。
由前可知,就花卉欣赏而言,宋代是真正意义上“声色大开”的时代,不仅在广度上大为拓展,而且在深度与精度上也显著提升。之所以能形成如此盛状,除了花卉自身的发展外,还得益于宋儒对“格物”观念的重视与强调。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原,这个本原就是“理”。理化生万物,所以万物皆是天理的具体呈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个别、具体物性的考察与研究把握到普遍的、抽象的天理,这一方法或过程便是“格物”。如朱熹所言: “格,至也。物,犹事也。”(42)朱熹:《大学章句》,《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第1页。“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43)朱熹:《朱子语类》,《四库全书》第701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5页。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谱录之学会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兴起,审美愉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治学”与“修身”,即获得认识和道德上的提升。换言之,在他们的心目中,谱录之学并非仅供娱乐的“小道”,而是求真、向善的正途。王贵学在《王氏兰谱》中就明确表示,他为兰制谱“是格物而非玩物”(44)王贵学:《王氏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页,第45页。。在他看来,观兰草可以“会仁意”,这是“君子养德”的一种途径。陈景沂也在《全芳备祖》的自序中回应了有些人对其“玩物丧志”的批判:“余之所纂,盖人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者也,恶得以玩物为讥乎?且《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之当务也。”(45)陈景沂:《全芳备祖》,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7页。“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最初乃孔门学诗之训,后来发展成君子之为君子的必备修养。如果说“格物”作为一种方法论还太过抽象,那么“识物”便容易理解且容易操作得多。其具体实践,正如谱录所做的那样:辨其类、释其名、观其形、究其性、考其源流……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亲身观察和实践来获取与自然对象相关的知识。
显然,这些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换言之,“格物”之法蕴含着一定的科学理性精神。这种观点得到了李约瑟的肯定。他在评论李时珍奏书中“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 《诗疏》之缺”一句时说:“不论格物和格致这两个词在12世纪时(朱熹时代)是什么意思,但李时珍同我们一样肯定这两个词有自然科学的含义。”(4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第1分册,袁以苇等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正是这层“科学的含义”,让我们有理由将其与环境美学中的科学认知主义模式联系起来。持该立场的代表卡尔森认为,正如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需要关于艺术对象的生产历史信息一样,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也需要这样的知识。只不过,对于艺术对象而言,这些信息存在于艺术史或艺术批评理论之中;而对自然对象而言,这些信息存在于自然史和自然科学之中。(47)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63-64.
在卡尔森看来,自然科学知识之于自然审美欣赏的助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审美遗漏”,即避免忽视自然本身某些客观属性与内在价值;二是避免“审美欺骗”,即避免歪曲自然本身某些客观属性与内在价值。这两个方面在宋代花谱中都有所体现。关于前者,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不了解梅花耐寒、早发的特性,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宋代士大夫为什么对此花如此痴狂,特别是其中“古梅”一品。正是基于对其生存演化历史信息的认识,我们才能从其身上感受到审美愉悦,获得审美满足。关于后者,最好的例证是史正志在《史氏菊谱》中所讨论的一桩公案。昔者,屈子一句“夕餐秋菊之落英”奠定了菊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唯美形象。此后,诗人颂菊常会描绘“落英”这一意象,如王安石“残菊飘零满地金”。对此,欧阳修进行了嘲讽。因为在他的认知中,菊花枯萎时花瓣并不会凋落,“落英”一说其实偏离了菊性之事实,是屈子为了托物言志而主观臆造出来的。对于这桩公案,史正志根据自己多年的栽培经验提出:菊花有落与不落两种,所以无论是王氏之辈,还是欧阳之辈,他们虽在文坛上叱咤风云,但在草木之学领域却欠缺实多。这种欠缺,由上述争论可见,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菊花的审美体验,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判断。“落英”之说虽然可以得到证实,但在史氏看来,屈子此句仍旧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开,芳馨可爱耳。若夫衰谢而后落,岂复有可餐之味?”(48)史正志:《史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7页。史氏的考证,戳穿了意象唯美的假面,还原了落英的本来面目。在人文情怀占主流的中国文化史上,这种较真不仅显示出对客观事实的重视,而且表达了对自然道德伦理上的尊重。
不过,正如余欣女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并不在‘物’,不是一堆关于自然物的知识,而是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的直面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中国博物学的本质,不是‘物学’,而是‘人学’,是人们关于‘人与物’关系的整体理解。”(49)余欣:《中国博物学传统的重建》,《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0期。也就是说,谱录所提供的知识虽然具有一些科学的味道,但是浓度不高;其所体现的“格物”精神,虽然与科学精神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不能完全等同。它们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学术研究,所重视的还是人本身的修养问题。这种文化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是符合知识融通的趋势,避免因分科而走向孤立与片面,并且有利于培养人与自然相亲相近的意识,有利于重建二者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但这同时意味着它不够准确、客观、公正,如此既有碍于我们深入了解、认识自然,也不利于我们培养恰当的自然审美观念。
关于影响审美欣赏的因素,除了性理知识外,宋代花谱还提到了花卉所处的“环境条件”。如南宋张镃,为了使游客真正领会到梅花的神韵格调,不至于做出玷污、轻侮梅花的行径,他在《玉照堂梅品》中提出了五十八条“奖护之策”。这些策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花宜称” (凡二十六条):淡阴,晓日,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苔。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
“花憎嫉” (凡十四条):狂风,连雨,烈日,苦寒。丑妇,俗子,老鸦,恶诗。谈时事,论差除,花径喝道,对花张绯幕,赏花动鼓板,作诗用调羹、驿使事。
“花荣宠” (凡六条):主人好事,宾客能诗,列烛夜赏,名笔传神,专作亭馆,花边歌佳词。
“花屈辱” (凡十二条):俗徒攀折,主人悭鄙,种富家园内,与粗婢命名,蟠结作屏,赏花命猥妓,庸僧窗下种,酒食店内插瓶,树下有狗屎,枝上晒衣裳,青纸屏粉画,生猥巷秽沟边。(50)张镃:《玉照堂梅品》,程杰校注:《梅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51页。
这五十八条皆关乎赏梅的环境条件,“花宜称”与“花荣宠”意指“适宜的”,所以是应积极营造的环境条件;“花憎嫉”与“花屈辱”则意指“不适宜的”,所以是应注意回避的环境条件。不难发现,这些环境条件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然的”,如“佳月”“微雪”等;另一部分是“人文的”,如“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等。薄暮冥冥、月色胧胧、烟雨蒙蒙、寒雪茫茫……渲染了清幽寂远的气氛;一曲《梅花落》、一首梅花吟、一盘梅花棋、一卷梅花谱……烘托了闲适宁静的心情。心与物会,情与景融。可见,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其宗旨或原则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营造一种“雅致”的“意境”。这种意境既饱含着“诗情”,又充满了“画意”,如“夕阳”“佳月”“孤鹤”“清溪”等,使人很难不联想起林逋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薄寒”“微雪”“疏篱”则使人不由吟诵起王安石那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其实,为欣赏环境制定标准并非张镃首创,丘濬的《牡丹荣辱志》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丘濬使用的是“花君子” “花小人” “花亨泰” “花屯难”四种说法。且看“花君子”:
温风。细雨。清露。暖日。微云。沃壤。永昼。油幕。朱门。甘泉。醇酒。珍馔。新乐。名倡。(51)丘璿:《牡丹荣辱志》,王云校点:《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我们发现,与梅花的欣赏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牡丹的欣赏环境处处透露出“热烈”二字。显然,这是根据牡丹本身的气质设置的。梅花清冷,故其环境宜雅;牡丹热烈,故其环境尚闹。如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气质决定了环境,还是环境影响了气质?由前可见,答案应该是双向的。
重视自然对象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连续性和交融性,以一种普遍联系的整体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符合环境美学的基本理念。环境美学家普遍认为,不同于艺术品,自然是无框架的,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与其所属的环境之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换言之,整个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某一部分的审美特性取决于它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这种“环境”特性同时决定了自然与我们人类也密不可分,其审美价值必然会受到诸种个人体验或文化体验的影响。有鉴于此,环境美学提出,我们不能再像欣赏艺术那样,站在对象对面被动静观,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与自然环境建立亲密的关系。这种参与首先是感官上的,我们于自然环境中游走,或看,或听,或闻,或触,让所有感官协同配合,共同运作;其次,我们还需充分调动心灵中的认识能力与理性能力,以真启美,以善护美。
由上述引文可见,身心的全面参与同样也是张镃强调的重点。他不满足于零散地欣赏梅花,故为其造园,并开凿了一条溪涧环绕左右。花开时,他便划船穿行其中,此中乐趣,非亲身体验者不能体会。除此之外,他还对欣赏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首先,忌“谈时事”,忌“论差除”,忌“命猥妓”。这是强调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态度。因为只有摒除一切私心杂念,我们才能集中注意力于自然对象本身,才有机会于其中品出韵味。其次, “弹琴” “吟诗” “作画”说明在保持心境的基础上,最好能具备一定的艺术文化素质,否则欣赏只能停留于表面,很难进一步深入。最后,也是最重要者,忌“俗徒攀折”,忌“主人悭鄙”。这说明要修身养性,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因为在张镃看来,只有仁者才会爱物、敬物,才不会使花儿遭受屈辱。
我们承认,适宜的环境条件对于自然审美欣赏十分重要。但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才属于适宜的自然环境,一定要有诗情画意吗?一定要形成某种“意境”吗?不难发现,对诗情画意的强调意味着我们把自然对象当成了艺术对象,或者说,按照欣赏艺术的方式或标准来欣赏自然。这种艺术模式在中国古代备受追捧,但在环境美学家看来却是一种“不恰当”的欣赏方式。因为它没有尊重自然的本真面目,没有做到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长此以往的后果便是自然彻底沦为艺术的附庸,失去其本身独立的价值。故此,我们认为,适宜与否不能仅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判断——符合人类审美偏好的、符合艺术审美理想的就是适宜的,反之则不是适宜的;而应从自然对象一方来衡量——能够展现、维护自然对象生机勃勃之态的便是适宜的,而遮蔽、破坏其“生意”的便是不适宜的。而按照这一标准视之,一定的艺术文化修养固然重要,但不是必需的,审美活动不应该被精英阶层垄断,而应面向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但是,对道德伦理的要求却是必需的,因为一切热爱都应建立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展开一切自然审美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四、结 论
借助花谱这一窗口,我们看到,宋人的花卉审美意识已颇成体系——审美对象、审美方式、审美评价这些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问题都有所涉及。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也有应该反思批判的地方。故而,弘扬其哲思,改造其不足,便成为我们今后开展研究所努力的方向。我们认为,恰当的自然审美模式应该是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即以生态理念为指导的自然审美模式。
首先,就欣赏对象而言,这种模式既关注自然之“容质”,又重视自然之“韵格”,只不过对二者的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判断某一自然对象是不是美的,依据不是它能否带给人感官上的愉悦,也不是它能否满足人精神上的需求,而是看它是否完整、健康、富有生命活力。简言之,是否具有“生意”。中国古人十分重视“生意”这个概念,尤其是宋儒,认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这种意识在花谱中也有所体现。赵时庚模仿周敦颐提出:“窗前植兰数盆,盖别观其生意也。”(52)赵时庚:《金漳兰谱》,郭树伟注译:《兰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9页。刘蒙虽然极其重视菊花的品相,但在谱录最后却特意提到了两种“生于山野篱落之间”,于色香态度“无足取”的菊品。因为在他看来,这两品菊花虽然并不起眼,但正是因为这份不起眼,才免于遭受人的“剪锄移徙”,才得以“保其自然”。这份自然,在刘蒙看来,与其他品质一样珍贵,所以才将其特别列了出来。(53)刘蒙:《刘氏菊谱》,杨波注译:《菊谱》,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2-83页。
其次,关于自然审美评价,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对自然进行评价,一套客观的评价体系既是自然审美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也是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支撑。只不过,评价的标准需要重新制定:我们首先应当承认所有自然对象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因为它们每一个都为了生存繁衍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即它们都具有旨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是一种善,同时也是一种美。换言之,生命本身就值得人们欣赏。不过,在都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存在高低大小的区分。区分的标准与上述所言一致:本身更具“生意”,或使所在的环境更具“生意”的,我们便认为它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并因此给予它更多的关爱与保护。
最后,就欣赏方式而言,这种模式既要发扬“格物”之精神,又要宣传人与自然共生的“环境”理念。即,既着力保证欣赏的客观性,又试图增加欣赏的丰富性。具备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是保证欣赏客观性的最佳手段,这里所说的生态科学知识包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却不止于此。我们应积极吸收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博物学的研究成果。至于其他非认知因素,我们承认它们在自然审美欣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强调这种介入必须以自然本身及其真实特性为指导,不能听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应以展现、维护自然的生生之态为最终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